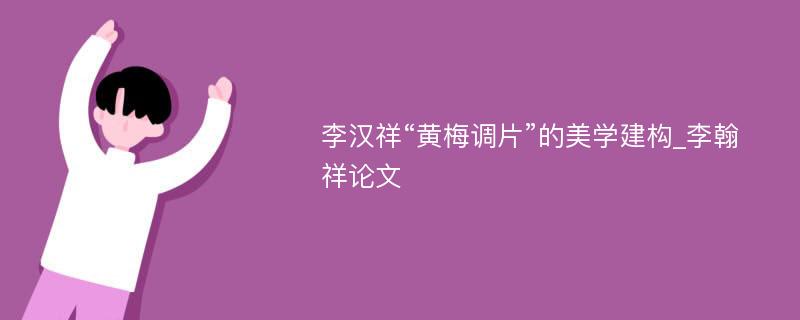
李翰祥“黄梅调电影”的美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电影论文,李翰祥论文,黄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电影在港英殖民政府“行政吸纳政治”的政治体制下,缔造电影工业上的“东方好莱坞”,开辟出建构“文化中国”认同的多元化国族商业电影类型道路,继承和革新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影戏美学”。 一、彩色电影时期的“影戏美学”建构 在1920年代开创出中国国族电影类型“古装片”的天一影片公司,移师香港重组机构,在1957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1958年,邵氏公司推出“全部彩色摄制”的“历史古装宫闱歌唱巨片”《貂蝉》(李翰祥导演),由此“掀起的彩色古装片潮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吴昊语),并发展出独立的“黄梅调电影”“新武侠电影”的有声彩色国语电影类型。 实际上,获得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编剧、音乐、剪辑奖项的《貂蝉》(1958),“将歌唱戏曲、美人、历史、传奇、古典文艺等熔铸成一种新的类型电影”①,正是第一部彩色“黄梅调电影”。此后的《江山美人》(1959)、《杨贵妃》(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玉堂春》(1964)、《状元及第》(1964)、《西厢记》(1965)、《女巡抚》(1967)、《三笑》(1969)、《四季花开(富贵花开)》(1974)、《金玉良缘红楼梦》(1977)、《新西厢记》(1979)等一系列影片,都是沿着“古装(黄梅调)歌唱片”的基本方向,汇聚李翰祥、胡金铨、张彻、岳枫、程刚、宋存寿等电影导演的才情理想,共同构筑出光彩溢目的“黄梅调电影”传奇性世界。 “黄梅调电影”不但确立了在国族电影类型上的商业地位,而且确立了在中华审美典范上的文化地位,“被认为象征着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复兴……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吴昊语),“在60年代初冷战时期……在广大西方世界更被视为‘中国电影’的代表”②。主导着“黄梅调电影”生产的邵氏公司,作为“中国电影历史上(包括世界任何华人地域内)最成功的一家商业公司”,拥有“一所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大、科技最尖端的制片厂”,自觉追求在电影中建构“文化中国”并“成功的建立了大中华群体意识”,使香港电影在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率先确立国族类型商业电影在彩色电影时期的“影戏美学”有效范式。 “带起了黄梅调的浪潮大概有二十年”(李翰祥语)的“邵氏古装片的灵魂人物”③李翰祥,既是彩色“黄梅调电影”的开创者,也是集大成者,在电影中“精雕细琢,从布景、道具、服装到摆饰,都堆砌出一个金碧辉煌的幻想中国”④,摸索出一种彰扬更具化“娭性”精神的古典彩色“影戏美学”,用以“塑造中国人的造形”(蒋勋语),意义既深且远。 站在中国电影工业的角度看,李翰祥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香港、台湾两地电影业界的“风云第一人”,在电影创作上几乎囊括其时所有港台商业类型电影(“唯一没有涉足的是武侠片”),⑤并在1980年代开启香港、内地两地合作制片的道路,“使香港影界的商业电影理念开始大幅度地影响内地”,“无论从电影潮流的带动、片厂美学的发挥,以及对三地电影工业的影响,李翰祥都是华语电影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人物”,其国族古装电影类型的彩色“影戏美学”长远影响香港、台湾、内地三地电影的类型生产和美学书写。李翰祥在电影创作上多样丰富的类型风格,造成“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常出现很大差异”的评价争议,“对其作品和电影事业的系统研究……显得比较贫乏”,难于总体定位。⑥然而,我们可在反复省究后体察到电影多面手的李翰祥,在电影美学的沿创上有着一以贯之的基底:“说书”。这并非简单地指李翰祥电影直接呈现评书、弹词、莲花落、数来宝、花鼓、黄梅调等说唱形式场面,更重要是指李翰祥电影总体上都内在植根于“说书艺术精神”,都是一种“说书叙述文本”。我们只有把李翰祥“安置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大河流中,才能真正领略他的存在意义”,“‘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⑦他的一部部影片,可看成是一篇篇“活话本”。就此而言,在持笔写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时,李翰祥是用文字“说书”;在摄制编导《三十年细说从头》时,他是用电影“说书”。 二、李翰祥电影美学的“说书娭性”精神 在整个中国“影戏美学”的坐标系中,李翰祥电影美学占据着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绝对不可轻视低估,它意味着早期中国类型电影不断自觉的内在“娭性”精神,已经具体夯实为内在“说书性”(或曰“说书娭性”)精神,有着更加充实、持续、有效的心要特性。自李翰祥电影开始,中国国族商业类型电影的“影戏美学”,由“娭性”精神时代正式转变成“说书性”精神时代。在导演资历上稍浅于李翰祥的胡金铨、张彻和李翰祥组成“促成香港电影‘起飞’的三个人”(张彻语),他们也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港台两地最有影响的三位电影巨匠,共同把“说书性”精神落实在当时的港台主流商业类型电影中,泽被后世。李翰祥确立了内蕴“说书娭性”精神的“黄梅调电影”典范,胡金铨首部导演作品《玉堂春》、张彻首部导演作品《蝴蝶杯》,都在有所自觉地内在化“说书娭性”精神,建构“黄梅调电影”的“影戏美学”。 在“说书性”内在精神的开新之下,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观念比费穆的“旧剧电影化”的“古装歌舞电影”观念更进一步,“在‘古装插曲电影’与‘戏曲电影’两者之间”⑧选择了前者。表面上,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是石挥导演的黑白戏曲片《天仙配》(1955)的效仿者,“第一个导黄梅调影片的是石挥,第二个是李翰祥”⑨。实际上,石挥是在“要保留黄梅戏的特色”的任务要求下进行“旧剧电影化”,放弃自己“想完全按照电影形式拍摄来重新谱曲,原来的‘黄梅调’仅仅做为材料,充分运用电影技巧”的初始构想,拍摄出“不应该是‘重新谱曲’的新腔新调而是黄梅调”的“戏曲电影”;⑩李翰祥则是在“戏曲服从电影”的基本立场上,把“‘黄梅调’仅仅做为材料”,“愈唱愈改良”(李翰祥语),糅合“黄梅新旧腔调、京剧、昆曲、山歌民谣、越剧、评弹、蹦蹦戏、都马调等等”(11)曲调唱腔乃至西洋古典乐,把“黄梅调电影”努力“拓展为‘不限地域、不拘语言’的‘泛中国古典印象’”(陈炜智语)的“古装插曲电影”。 借用李翰祥代笔的《翠翠·导演者言》里的话,黄梅调电影“该是地方色彩非常浓厚的戏。但为了地理环境的限制,我不得不把这地方扩展为‘中国’的,一切风俗习惯也普及为‘中国人’的,”(李翰祥语)而不是中国的黄梅人。在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中,“貂蝉的三国、江山美人的明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晋朝都被拉平到一个概念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去,”由此“笼统地传达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并大幅度地简化这个世界中人的组成关系,以这笼统的中国人的人情来感动观众”(12),建构出大中原文化意识(超出更加具体化的地方意识)的中国风俗画式世俗世界。 “说书娭性”的内在精神,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商业定位:满足电影接受者(观众/听众)的审美需求,即满足国族商业类型电影的观影大众的通俗文化审美需求。在“黄梅调电影”中,李翰祥就是一个持摄影机的说书者,“状英雄儿女,摹世故人情,细微曲折,历历如绘”,“其趣味之浓,有胜于读稗官野史”,所以“足使听者忘忧忘倦”。(13)第一部彩色“黄梅调电影”《蝉》直接活用说书形式,开头用字幕说出故事背景:“公元一九零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奸臣董卓欺君殃民,天下愤怒,各路兵马纷起讨董……”紧接用韵语唱出“定场诗”:“汉朝末代乱纷纷,董卓欺君又压臣,关东诸侯兴兵马,遍地黄巾地战尘,奸董卓心胆惊,迁都限日到西京,百姓不愿长安去,放火烧尽了洛阳城……”(长卷画横移镜头),结尾用韵语唱出“下场诗”:“司徒妙计设连环,小说夸张史不传,多少美人关大计,千秋不止一貂蝉”,借说书形式的影像化,带给观影者程式化和趣味化的通俗文化内容形式。继之的《江山美人》,同样在电影开头唱出“定场诗”,结尾唱出“下场诗”,还在剧中呈现“戏中戏”和“曲中曲”的说唱结构,“是通俗演义式的评话电影”(14)。其后的“作为黄梅调电影代表性的地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样沿用开头“定场诗”和结尾“下场诗”形式,说唱:“彩虹万里百花开,蝴蝶双双对对来。地老天荒心不变,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可以说,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不但具有“说书娭性”的内在美学精神,而且具有“说书式”的电影化外在形式,“是一方面反映出说唱的存活现象,另一方面以身试法,承续了说唱的传统。”(迈克语)李翰祥的所有古装电影,总体上“越来越怀念往昔说书人的讲古艺术”(石琪语),“以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连续地说着故事”;他的所有时装电影,“也不过是《陈世美不认妻》和《孔雀东南飞》等等的时装版本,”都是“说书娭性”精神的“影戏美学”作品,“都直接和间接浮现说唱艺术的影响”。(15) “说书式”的电影形式,并不等同于电影语言上的陈陋拙劣,不应把李翰祥“黄梅调电影”卑视作“没有好好经营电影技法……电影语言杂乱无章”(迈克语)的劣制。事实上,李翰祥在掌握电影语言上完全属于行家里手,他是“港台导演最擅用镜头语言的大师之一”,是国族电影美学一代大家,“他的摄影机运动和他的视觉世界(包括布景及人物)是合为一体的”,(16)他的电影中的多种“复杂的镜头运动,国内能运用的导演还极少”。李翰祥的古装电影类型“影戏美学”,是在“深谙镜头美学”前提下的国族电影美学创兴,才华横溢地开扩出“影戏画”“影戏咏”“影戏色彩”美学的新境地。 由于李翰祥对编剧、导演、摄影、剪辑、布景、道具、美术设计等诸方面的“全才型”精通,使他的“黄梅调电影”的“影戏美学”具有打通各个创作环节的气韵生动意味。李翰祥自白:“我觉得要使中国的古装片看来不离谱,很要紧的一点便是先为影片布下那股气韵,那股国画里的气韵。”“最好少取实景,多利用内景,主观地去用灯光和建筑构成一个最近于理想的环境……只有利用再创造的布景,投入以设计过的光线和隐约的烟霭,才能传出那么些味道来。”(17)李翰祥创造出自己融合美术布景和摄影机运动的“商标式的推轨运动”,“透过花叶树石,或是雕栏珠帘,李翰祥往往不惮其烦地铺设起曲折的轨道。拍摄时,让摄影机平稳地跟着轻移莲步的仕女滑动,掩映之间,创造出流畅明丽的动感,然后,镜头停在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画面上,人物动作和背景都被安置在最妥帖的位置”,通过“华丽繁复的镜头运动,使李翰祥较戏剧性的电影能与其内景、外景结合成一个瑰丽的视觉世界,观众往往目不暇接,不会陷于单调冗长的情绪中”(18),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说书世界”。 三、费穆电影美学路向的新探索 在中国“影戏美学”的演进史上,李翰祥的古装电影美学接续着费穆的“空气美学”,把“影戏画”的“画化-幻化”美学开扩成“画化-幻化”和“气化-幻化”美学的新境。换言之,泛义上的“影戏画”美学的内在层次,由单一的“影戏画”层次,演进成“影戏画”和“影戏气”两个层次。在形式技法上,狭义的“影戏画”的典范性范式,是运用特技画化影像画面造出幻化空间;狭义的“影戏气”的典范性范式,则可无需特技而由布景美工搭配摄影机运动,布下“气韵”造出幻化空间。值得强调的是,“影戏气”是对于“影戏画”(狭义)的提升超越,但并不否定“影戏画”的基础性价值和独立性价值。事实上,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同时运用“影戏气”形式和“影戏画”形式,营造“说书娭性”幻化空间。 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手扶祝英台过独木桥一幕,独木桥的造型是一棵横在山涧的虬曲老树,前方一侧绿叶衬底红花争妍,桥后是疏叶远天,桥下云烟霭霭,站在桥上的山伯英台宛若置身仙境,大全景的空间布局气韵流动,形成“影戏气”的美学氛围。电影中的“十八相送”段落,,“用‘集中地’‘实验地’布景、选景,烘托出此一故事所需要的气氛”(19),集中体现出李翰祥的布景和“色彩、服装、道具、摄影角度、美术设计等方面的协助与烘托,……造成它(布景)的时代特征和环境、氛围”的经验技法,营造出多种“气化-幻化”的影像空间。而在电影结尾,则展现出多种“画化-幻化”的影像空间,梁山伯坟墓骤然裂开、祝英台投入墓中后残存的衣角化作蝴蝶、两只蝴蝶飞上天宫云霄等,都形成“影戏画”(狭义)的美学氛围。再如,在《王昭君》(1964)结尾,王昭君在江边焚香祷告,夜间江水一片黑暗,江岸地形尖凸险要,在黄色灯光照亮下,远景画面中的昭君宛如置身千仞高峰上,四周恍若云天,“并不是对景物的‘再现’,主要的是对景物的‘表现’”(20)(李翰祥语)的布景灯光营造出“气化-幻化”的影像空间;而王昭君在祷告结束后的纵身一跳,则形成“画化-幻化”的影像空间。 这些典范性的“气化-幻化”形式和“画化-幻化”形式,往往在电影中处于段落中心性位置,而围绕这些中心“景观”的素常性铺垫衬着,也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影戏画”美学形式。李翰祥在错落分陈布景中设计曲折有致轨道进行长时间推轨,形成在观影接受上的曲径通幽的主观性引导,正是一种基本的、日常的“影戏画”美学形式。 李翰祥“黄梅调电影”的“影戏咏”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把费穆“空气美学”的音效“造气”技法,提升到一个空前的簇新境界。自然发音的黄梅调歌唱,将对白音乐化(同时也可看成是对白的非日常生活化的音效化),承担对白的叙事功能同时超出叙事功能,创造听觉上的“咏化”(音效化)——所听声音的“幻化”,搭配画面形成供观影者(“听书者”)娱遣赏玩“嬉游”的情结性“幻觉世界”。黄梅调的音乐(包括非歌唱的纯音乐)结合画面产生“引起情感共鸣和非情感共鸣的效果”(21)的“增值”,“摄影机的运动,和音乐的合成潜力,将音乐的进行和影像的流动整合,构成一新的音乐电影空间”,而黄梅调的“音乐的加入使得人物的表演多了层表意,强化了叙事”,(22)这是非自然发音的其他戏曲唱腔无可企及的。正如徐复观所言:“唱的腔调,即是感情自身的体现;也可以说,‘腔调’即是感情的自身。”黄梅调正是“黄梅调电影”作为插曲歌唱电影的一个“成功的大秘密之所在”,“它的腔调,反映出民间自然流露出的素朴的感情,而又与自然地语言相去不远,所以把它融入到电影的动作中去,使戏剧化与现实感,容易得到谐和”,而场景氛围里“所蕴蓄的深厚感情,便很自然而然地通过此一纯朴婉曼的腔调,表现了出来,大大地增加了演技的效果”。在此意义上,“黄梅调电影”的腔调既是自然的,又是表现的;其中的黄梅调对白,既是叙事性的,又是表现性的;黄梅调纯音乐和效果声,则更是情结性的音效化;它们的“影戏咏”形式,正适应于国族商业类型电影。 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在烟雾弥漫的树林中亮相,在如画风景中赶路求学,悠悠江南丝乐竹韵的纯音乐渲染人物的游春式欢愉情绪;接着山伯在桥上远眺,清唱“远山含笑,春水绿波映小桥”的独白,四九则唱“看此地风景甚妙,歇歇腿来伸伸腰”回应,既可看作对白,也可不看作对白,任由接受者主观建构;而后山伯在凉亭休憩,周围的各种清脆鸟鸣,可据其声音空间感判断出是模拟现场音的效果音;之后山伯英台对唱出义结金兰之意,在他们背后远处的四九和银心对谈(对话声音不出现),同一时空中的唱“对白”与说“对白”形成反差,暗示四个人所处场景的虚拟性;这些声音,都是构筑“声音幻境”的“影戏咏”形式。再如《江山美人》中的“戏凤”段落,开始是李凤姐和正德皇帝用黄梅调唱出对白,接着李凤姐蓦地说出对白“你来干什么?”正德皇帝则唱出回答:“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李凤姐继续说话:“你——你这人说话怎么不规矩啊!我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在剧中把正德皇帝的“唱”称为“说”。此段落中的“唱”与“说”相间,形成“幻化”的电影声音空间;而剧中人物的指“唱”为“说”,则进一步加深声音空间的“幻化”,营造出别有韵味的说唱“咏化”美学效果。 李翰祥“黄梅调电影”的“影戏色彩”美学,可以视作是沿着费穆“影戏色彩”美学路向的新开拓。事实上,“黄梅调电影”是香港乃至整个两岸三地中国电影中,第一种获得肯定的彩色电影类型,在电影色彩美学上成绩斐然。李翰祥的电影色彩观念正和费穆一脉相承,其奉为圭臬的准则——“拍彩色片要使人有看黑白片的味道”,完全可看作费穆的电影色彩“第一定律”(“不强调彩色,彩色更美。”)的另一种表述;而费穆的“第二定律”(“如果强调了某一种彩色,情绪更美。”),在李翰祥电影创作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在“黄梅调电影”的具体作品中,我们可体知到李翰祥对于电影色彩的精到阐释:一部彩色电影有其色彩主调,主调的素雅是色彩和谐自然的基础,云烟雾霭可促进色彩的平淡蕴藉;在特定场景中有意强调一种色彩(尤其是人物服饰或人工建筑的色彩),可造成此种色彩的情绪化放大,营造出浓烈的主观化氛围。 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色彩主调是宁静优雅的浅蓝色,诸多场景的色彩设置都讲求和浅蓝色彩的和谐,如用深棕色、深灰色、米色等进行搭配,在视觉接受上色彩素淡自然;而“影戏气”美学营造的空气朦胧化,也意味着画面色彩上的淡化,促进着电影色彩上的含蓄。在祝英台拜祭梁山伯之墓时,改着亮白色长衫,迎亲花轿的红色相形之下亦显黯淡,画面上用色彩对比和光线明暗强调出的白色,准确传递出祝英台悲痛悼亡的心境,笼罩整个拜祭场景;在梁祝求学路上初遇时,深绿色的重重树荫传递出春意盎然的明快情绪;在梁山伯临终前,整个画面全蒙上一层深秋橙色,向观影者强调故事主人公生命凋落的悲凉处境;这些凸显单一色彩的例证,显露出李翰祥深谙借色彩深化情绪的观念和方法;而《貂蝉》《江山美人》《王昭君》《七仙女》等一系列电影的色彩处理,说明李翰祥藉由“黄梅调电影”已然确立其行之有效的类型电影色彩范式,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类型电影“影戏色彩”知识话语。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通过类型电影建构“文化中国”的邵氏兄弟公司、国联影业公司等民营电影公司,在承继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出新的彩色类型电影路向及其美学新境,“把中国文化和艺术传统通过影像介绍给不同语言和种族的人”(23)。其中,“国语影坛春秋战国的第一沙场战将”(焦雄屏语)的李翰祥,“承袭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电影风格而略有渐进式演化”(24),“终于逐渐摸索出一些中国人思想方法与造形表达的特色”(25),成功确立不落戏曲电影窠臼的“黄梅调电影”及其美学形式。自言“我这个说评书的”(26)的李翰祥,由此开掘和示范“影戏美学”的“说书娭性”内在精神,开扩出“画化-幻化”和“气化-幻化”的“影戏画”美学新境,开创出说唱有机融合的“影戏咏”美学新境,开辟出彩色电影的“影戏色彩”美学新境,有效建构出“统统与中国通俗文化传统一脉相承”(27)的国族彩色电影类型“影戏美学”知识话语,“显现着人,同时又是中国人的精神”(28)。 ①⑧(11)陈炜智:《丝竹中国·古典印象—邵氏黄梅调电影初探》,黄爱玲:《邵氏电影初探》,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年版,第51页、第130页、第8页。 ②陈炜智:《丝竹中国·古典印象—邵氏黄梅调电影初探》,黄爱玲:《邵氏电影初探》,前引书,第43页。 ③吴昊:《前言—追逐神州故梦》,吴昊:《邵氏光影古装·侠义·黄梅调》,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页。 ④(16)(18)焦雄屏:《李翰祥—台湾电影的开拓先锋》,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76页、第182-184页、第183页。 ⑤“李翰祥的电影类型太庞杂,从素朴沉实的文艺言情,到千娇百媚的古装宫闱,从严谨考究的历史故事,到随手拈来的风月骗术,常令论者晕头转向,无所适从,难以为他定位”(黄爱玲:《序言》,黄爱玲:《风花雪月李翰祥》,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版,第1页。)。 ⑥⑦(15)黄爱玲:《风花雪月李翰祥》,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版,第1-111页、第36-40页、第36-37页。 ⑨(26)李翰祥:《三十年细说从头(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14页、第59页。 ⑩石挥:《〈天仙配〉的导演手记》,《中国电影》1957年第5期。 (12)(25)蒋勋:《李翰祥塑造中国人的造形》,蒋勋:《艺术手记》,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79页、第183页。 (13)陈汝衡:《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14)李翰样:《三十年细说从头(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6页。 (17)但汉章:《作家电影面面观》,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39-40页。 (19)徐复观:《游心太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0)黄北飞:《与李翰祥谈布景》,吴昊:《邵氏光影古装·侠义·黄梅调》,前引书,第67页。 (21)[法]米歇尔·希翁著,黄英侠译:《视听:幻觉的构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页。 (22)叶月瑜:《从邵氏到国联—黄梅调影片的在地化》,黄爱玲:《风花雪月李翰祥》,前引书,第100页。 (23)《远东最大的娱乐供应库:邵氏》,《南国电影》1961年第78期。 (24)陈来奇:《永远的李翰祥》,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7)刘辉、傅葆石:《香港的“中国”邵氏电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8)江青:《依依故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3页。标签:李翰祥论文; 邵氏黄梅调电影论文; 梁山伯与祝英台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江山美人论文; 剧情片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