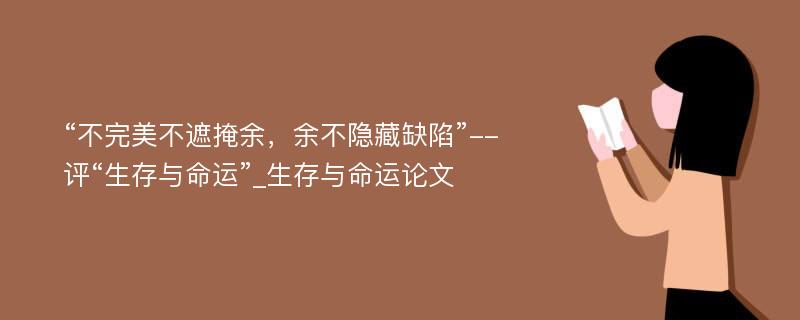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评《生存与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瑜不掩瑕论文,瑕不掩瑜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谈到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他的那部写于60年代初期的最后的长篇时,作家鲍利斯·雅姆鲍利斯基曾这样写道:
“从我1942年最初与他相识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但是,唯有他,第一次说出了那场伟大而又可怕的战争的真实情况。”(注:鲍利斯·雅姆鲍利斯:《与格罗斯曼最后的会面》,载《俄罗斯20世纪文学》,1995,莫斯科出版。)
读过《生存与命运》之后,会觉得这句话并不过分。这部作品具有一般写卫国战争的作品所没有的广度与深度。它既写了前线又写了后方;既写了战时又回溯到30年代;既写了苏联一方也写了德国一方,既写了军事领域也写了学术领域,既写了俄罗斯人也写了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既写了苏联军民在战时条件下的一般的生活,也写了在种种特殊情况下的苏联人的遭遇。作者不是表层地、平面地来写,而是写活生生的人在各种境遇下的内心体验,显示出人在极限处境下的生存与抉择。
作品里感人至深的片断可以说俯拾即是,如像:斯特拉姆的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从犹太人区写给儿子的长信;少校军医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跨入毒气室时所体验的那种对自己的即将殒灭的年轻生命的眷恋和她对犹太人孤儿达维德的母性情怀;柳德米拉在萨拉托夫码头转车时听到那双目失明的伤兵的求助的呼喊时涌上心头的那种无能为力之感;当濒临危境的斯特拉姆突然接到斯大林打给他的电话时那复杂而又难以名状的心境;克雷莫夫被审讯时意外地从当年他为德共党员哈根·弗里茨提供的那页滑头的证词里照见自己灵魂的卑劣时产生的战栗……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的心理深度。长期处于精神低谷的斯特拉姆在一次畅快淋漓的夜谈之后灵感迸发,研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势利之徒当道,他举步维艰。刚正不阿的秉性使他在逆境中不气馁、不妥协,可是,由于得到最高当局的关注而身价倍增之后,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惰性与奴性,以致在严峻的考验时刻做出了一项使自己事后愧悔得无地自容的选择。沉痛的教训使他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没能保持住心灵的纯洁。另一个主人公克雷莫夫是老一代革命者,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多年。对1938年后党的方针与新的干部他感到格格不入,但行动上仍与之保持步调一致。战争爆发后他志愿上了前线,在那里似乎感受到了“列宁主义真理”的复活,很想重新振作一番。但,即使在那里他也难免不时时处处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他人的时代里”。就在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入反攻的前夕他被逮捕并被解回莫斯科、关进了卢布扬卡内部监狱。他被诬告与托洛茨基有瓜葛并且被无端地指控在陷入敌军包围圈时有通敌之嫌。在亲身经受了连续几昼夜的刑讯之后,他终于明白了“告密”与“招供”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时,他开始反省自己、正视自己的“双重意识”,痛切地认识到以往在“清洗”中自己“没有能好好地保护朋友和同志”,也充当了一名可鄙的“告密者”。格罗斯曼不愧是他的主人公的灵魂的审问者。他将他们“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又从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注: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他“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注:鲁讯:《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与同时代许多苏联作家的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不同,《生存与命运》揭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当一部分苏联人是带了战前生活的痛苦的烙印而被卷入那场战争的。比如,在作品中师长罗季姆采夫、中校达伦斯基都是战争开始后从劳改营直接走上前线的。在德国战俘集中营里深受俄罗斯战俘拥戴的叶尔绍夫少校的一家四口在“全面集体化”时被强迫移民北乌拉尔之后全都死在那里了。军参谋长涅乌多布诺夫在30年代军内“清洗”中发迹(1937年在审讯中曾打落达伦斯基两颗牙齿!),尽管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却早已是一名“将军”了,战前曾两次出国,后来由中央军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派往前线,依旧在得心应手地干着自己的“本行”。格罗斯曼告诉我们,在战时斯大林格勒,人们几乎普遍关切着战后集体农庄与“全民强制劳动”是否还将继续下去的问题,而且,越是战斗激烈的地方,越是在那些舍生忘死的人们中间,对社会弊病的非议也越加无所忌惮。同样,在后方,那些从疏散地迁回莫斯科的人们对战前大逮捕时那深夜的敲门声也都记忆犹新。他们不禁在问:“难道那一切又将重演?”作者写道:
“人们与获得胜利的国家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争论支配着人的命运与人的自由。”
作品里像军政委格特马诺夫、科学院物理所新任所长希沙科夫那样善于钻营、巧于权变、不学无术、热中名利、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人,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都正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可是,对于像出身平凡、仅仅凭着才能和实干才由中校升为军长的诺维科夫和核物理学界的佼佼者斯特拉姆这样的人来说,身边环绕着那样的势利小人,就难免不交“华盖运”。作为故事的结局是:在格特马诺夫与涅乌多布诺夫的配合默契下,曾率领坦克军长驱直入、胜利进军斯大林格勒的诺维科夫,终因“违抗军令、延误进攻时间”和不听劝阻、继续与“社会政治面目不清”的叶尼娅保持亲密关系,而在进军乌克兰途中接到了离任、回莫斯科报到的调令。斯特拉姆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决意纠正错误、拒绝在那份表示支持“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与列文医生杀害革命作家高尔基”的冤狱的公开信上签名。这样一来,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个在被德军分割包围时率领战士们主动击退敌人30次冲锋、烧毁德军坦克8辆,坚持"6.1"号孤楼的英雄——分队长格列科夫,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嘉奖,反而被强加以“从政治上瓦解工兵分队”等罪名,即或不曾与那幢孤楼同归于尽,也将会被枪决于指挥员们的队列之前——方面军特别处已经为他立了专案。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厂长斯皮尔多诺夫是敌人疯狂围攻时唯一的一个始终坚守岗位的厂领导,可是,就因为他在红军转入进攻的当日不得不到伏尔加河左岸去探望刚刚在难民船里分娩的女儿,而被认为是“擅离职守”的“利己主义者”,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份,撤职,被派往乌拉尔去了……作者还告诉我们,当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时,“那个用鲜血浇灌的粘土质斜坡上曾经有着平等和尊严”,可是,当战线远离,生活中一旦失去那战时特有的昂奋与单纯,原先被掩盖和冲淡了的社会矛盾便又都显露和变得更加激化起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厂长在战事紧张之际常去车间,与工人不分彼此,可是,战火稍歇,他就不爱理睬那些“工人兄弟”了。厂里的干部都在忙于为自家修缮房屋,调运小汽车,而那些尚未发薪、缺少食品供应、住在土窑或地下室的工人们却无人过问。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一名复员军人,妻子病危、孩子嗷嗷待哺,本人却因“私占公房”而被勒令限期搬迁,被逼无奈,将勋章别在胸前皮肤上,坠楼自尽了……
比起我们从前在苏联小说或电影里看惯了的卫国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时的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场面,格罗斯曼在作品里所显现的画面实在是过于阴郁而且荒诞了。然而,60年代初,他为了要求批准出版这部《生存与命运》而致信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说:
“如果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么,就让读到它的人们,让我30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作出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究竟是真理还是谎言吧!”(注:原信载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88年第10期。转引自《生存与命运·译者前言》,工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可见,他认为这部作品的真实性是经得起生活与时间的检验的。从作品里所显现的那幅阴郁而又荒诞的画面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四、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现实的深重忧虑和尖锐的批判。
格罗斯曼的这种勇于正视和揭示现实的阴郁与荒诞的气魄是与他的对于民众的热爱、对于民众的生存与命运的执著关注分不开的。早在战争期间他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里就表露出了他的那种以民众为本位的倾向。他曾说过,红军战士在强敌面前之所以宁死不屈,“不是由于上级长官的命令,而是出于他们自己争取自由的意志,他们是用整个的灵魂去战斗的。”(注:格罗斯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吴人珊译,上海世界文学丛书,1954年6月版。)到了《生存与命运》里,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人类的意识回首往事时,总是通过悭吝的筛子筛选出伟大事件的凝块”。这就是说,在他看来,那从“悭吝的”筛孔中遗失了的大量存在恰恰是不容漠视的。他还认为,最终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辉煌胜利的,是人民,是人民的争取自由、反抗奴役的顽强意志。他说:“世界名城的特色在于有它们自己的灵魂,战争之城斯大林格勒也有自己的灵魂。它的灵魂便是自由。”与此相联的是,他在长篇里着力地揭示了普通苏联人的灵魂的美。比如:在最后突击的时刻到来之前,格列科夫命令他所爱恋的卡佳随谢廖扎一道远离死亡;叶尼娅义无反顾的舍弃了诺维科夫的爱,回到了那身陷囹圄的克雷莫夫身旁;诺维科夫为了使部队免遭无谓的伤亡,情愿承担重责;达伦斯基为了制止虐待俘虏的暴行,将个人的安危置之不顾;伊扎尼科夫拒绝为德国人修建毒气室,果敢地选择了死……此外,还有那乌克兰偏僻村落里的那位不问来由就给奄奄一息的谢苗诺夫端去一缸子牛奶并毅然地收留了他的赫里斯佳大婶,那些一无所惧地收养了被捕者的子女、无偿地帮助囚犯家属往劳改营里投寄包裹并代收、代转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的老妪和女佣人们……在作品最后,格罗斯曼借幡然悔悟了的斯特拉姆之口说:
“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和纯洁相比,一切都是渺小的!”
他还认为,民众那质朴无华和超越一切利害之心的善是强大而且永恒的,正因为它的存在,人类历史才得以延续。作者通过写主人公们的良心谴责,通过揭示人物的内在的美,通过对民众善良本性的高度评价,赋予了作品以一种人格的和道德审美的力量。这力量为全书增添了亮色。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在充分暴露现实的阴郁与荒诞的同时却不使人感到过分压抑的原因。
格罗斯曼服膺契诃夫的应该“从人出发,关心人、怜惜人、尊重人”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做不到这些,就说明“谈论社会主义还为时尚早”。他特别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按自己的方式去感觉、思维和生活的人,他说,“在人身上,在他那微不足道的特殊性里,在他对这种特殊性的权利中,包含着为生存而斗争的唯一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人,为了捍卫自己正当做人的权利,不应该惧怕死”。格罗斯曼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那90个昼夜里,克里姆林宫,贝特斯加登,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城市。一时间它似乎成为了人类未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和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过去有、将来也还会有普通人的平凡的生活,然而这一点却恰恰被那些为世界命运的阴影遮蔽了视线的人们所遗忘了。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尽管《生存与命运》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而写成的,但,作者注意力的中心却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人,是普通苏联人的生存与命运。因此,可以说这部长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人道主义,才是它的基本主题。
令人遗憾的是,格罗斯曼没有在这里止步。作品中他还设计了这样的情节,即:在德国境内的一所战俘营里,那个以“国社党理论家”自许的纳粹秘密警察利斯深夜提审莫斯托夫斯科伊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将他即将写进一篇论文中的观点讲了一通,以观察那个被提审者的反应。利斯把斯大林与希特勒、苏联共产党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德国的经济体制,等等,相提并论并加以对比,从中找出了“同一性”,进而认为,若不是有这相似的“两极”存在,那场可怕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利斯还将收缴得来的集中营的囚徒伊孔尼科夫所写的一份手记塞给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叫他去读。伊孔尼科夫早年曾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同情农民,30年代长期生活在农村,曾目睹“全面集体化”给部分农民带来的祸患。他在那份手记中将苏德两国的政治制度统通归诸一种“极权暴力”,并且,将人的善良本性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求与“极权暴力”之间的对抗抽象化为“善”与“恶”的斗争。作品进一步揭示了利斯与伊孔尼科夫的论调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意识里所激起的波澜。这个老共产党人暗自里承认在这场灵魂的遭遇战里他是个失败者,败北了,因为无论是利斯还是伊孔尼科夫,他们所引以为据的那些苏联社会的严重积弊不仅是存在的,也是长期以来使他感到无比痛心的。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宁愿逃回到以往的那种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思维模式里去,因为否则就将导致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自己从早年起就信奉的学说和所献身的事业。作者应该说,借利斯和伊孔尼科夫的口或笔提出,又经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默认的那些说法,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们早在作者写作这部长篇之前,从40年代起就先后地以类似的表述方式出现在托洛茨基、哈耶克、萨特等人的著作里了。尽管如此,这里还须指出,评价影响深远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人物,都需要一种客观、谨严的科学态度,任何即兴式或情绪化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比如,说及“二战”的起因、性质和胜负的原因,首先就无法撇开一个举世公认的基本事实,那就是:1940年,当希特勒德国仅用11天就占领了法国,全世界都在忧虑欧洲将陷入千年黑暗的王国时,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顶住了、粉碎了希特勒德国的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的战局。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为了谬误。为国内严重的社会积弊和它们给亿万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忧心如焚的格罗斯曼,当他力图为自己的长篇寻找一个最强音时失去了应有的审慎,偏离了客观的准衡。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就仿佛是一块璞玉中的瑕玷一样。《礼记·聘义》中有言:“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评价这部复杂的作品时不能离开“两点论”。
1998.3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