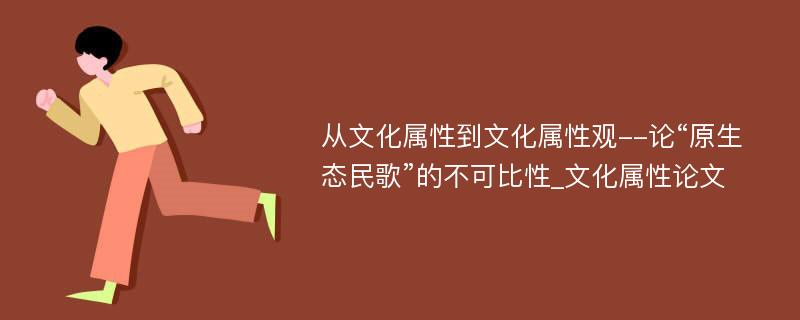
从文化属性到文化属性观——论“原生态民歌”的不可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文化论文,可比性论文,民歌论文,原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08)04-0001-05
随着“原生态民歌”概念的提出以来,有关民歌“原生态”涵义的争论便持续不断。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与其认识论领域的拓展密切相关。这是对前期“民歌”与“新民歌”概念讨论和认识的延伸和扩大。不同的是,如果说“民歌”与“新民歌”主要偏重于名实之争的话,那么关于“原生态民歌”的讨论则已深入到民间音乐的核心议题上来,显然,后者的思考深度较前者有较大的飞跃。
不可置疑,在信息资讯传播方式日益发达的今天,民歌的舞台化传唱和表演是民间文化传播难以避免和取代的重要途径,问题在于,我们该以怎样的尺度、方式和价值观去衡量之。
从此意义上讲,对“原生态民歌”“可比”与“不可比”的讨论,绝不是拘于形式的泛泛之论,通过它,有助于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和本质属性。要弄清“歌曲”体裁的“民歌”和作为“民间文化样式”的“民歌”两者间的本质,势必牵涉到民歌的概念、社会功能(包括一般功能——重要功能),以及民歌的文化属性(一般属性和重要属性)等问题,以及多般要素间的关联。笔者认为,无论就音乐形态还是文化层面而言,民歌真正的“原生形态”均难以展现,甚至是无法展现的。所谓民歌的“原生态”,不过是一个伪命题而已。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空间下的“原生态民歌”,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因为功能、文化属性和审美标准的不同,意义和价值取向也存在极大差异,极难找到评判的共同点,因此,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歌,实则不具可比性。
藉此,我们还应看到,对以民歌为介质的思考,完全可以扩深至民间音乐论域,其认识的深度,直达文化建构的高度,意义非同小可。
民间口头流传的歌曲。它与一般创作歌曲的不同之点是:①不受某种专业作曲技法的支配,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②其曲调和歌词并非固定不变,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地经过加工而有所变化发展;③不借助于记谱法或其它手段,而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口耳相传;④不体现作曲者个性特征,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源于人民生活,又对人民生活起广泛的作用。在群众口头的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中国音乐辞典》。
概念,是通过词语来表达某种事物及其特有性质的思维形式。如果概念不清楚,就会影响更进一步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这两本专业辞书关于民歌的定义是否完全清楚呢?回答是否定的。民歌是“民间歌曲”,不能算作完整的解释,如果说民歌的“曲调和歌词并非固定不变”,那么,我们常说的民间宗教仪式的歌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则是对此解释的质疑。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做到概念准确,就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明确。由此细察,不难发现两本辞书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的描述不具完整性。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对民歌的特性描述不够全面和清晰,对民歌作为文化的特质关照不够,即民歌作为文化,在民间的存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歌曲”,说“对人民生活起广泛的作用”,是表达民歌功能的多样性,但是,音乐的功能是音乐文化属性的反映。民歌的功能和属性,共同构成民歌的深层含义。我们说以上两本辞书的定义对此表达不够完整和清晰,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来讨论民歌的定义,并非刻意针对辞书本身,任何一本工具所阐述的概念,其普适性和代表性,很难脱离同学术理念的时代设定。重视民歌的社会属性和本体构成规律,而忽视了民歌的文化功能和属性的多样性,其中的空缺恰恰是近几十年来音乐学领域研究理论的重大扩展和学术转型。
“音乐作为文化”的观点如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论证,由此表明——“一切音响都有文化的意义”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同理,民歌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审美层面上的意义,也有哲学意义和实用意义。另一方面,民歌是社会的产物,是个体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同时还是文化行为,它必然同社会的诸多层面发生关联,并且在这些特殊的关联中生发意义、产生各种社会作用,凸显出它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上述表明,民歌的意义不仅在其本身,也发生在与社会各层面的关联之中。各民族的民歌不仅风格、内容可能相去甚远,不仅各民族间的民歌文化属性各具特色,甚至同一个民族内部的民歌因文化空间的不同和转移,其属性指向也不同。奈特儿说:“音乐的概念并非普遍存在或到处相同,甚至在同一社会中,一种特别的声音在某些情景中被认为是音乐的声音,而在另外的情境中则被看做是非音乐的声音”。①民间的某些仪式中的吟唱性歌曲便是如此,在仪式中看被是“乐”的手段和行为,在仪式之外,则似乎毫无意义而不具文化属性,它们因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不同所生发不同的意义指向。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定义中,旋律、音高、音色、节奏是音乐的四大要素,而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代,这一切则似乎变得都不重要了,从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到日常生活的声音,甚至人的哭笑声、嘶喊声也都被作曲家充分采纳。仔细追究,这种观念却也并非当代作曲家的首创,在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观中,同样也是将“自然之音”视为“音乐”的存在并在民歌中有所体现,甚至古典传统意义上十分介意的“不和谐”音程如布依族、瑶族、壮族民歌的二度和音也都十分普遍,且成为这些民族民歌的标识和核心特征。同样,在中国传统的礼乐观中,乐是附属于礼的一部分,古人对乐的评价核心标准是以其是否符合“礼”的规范而言的,它的文化属性也具别样。所以,抽离民歌的生活本质,也就使其失去活力,留下空洞的躯壳。民歌的舞台化表演,属于外部作用力所起的作用,而非民间文化自主性的反映。文化表演和自在自为的文化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外力因素驱使下的表演,往往不能真实地体现民歌的内涵和属性,而作为民间文化的民歌,其行为均有与其相对应的事项和动机。表演的本质是取悦他者,而自在自为的歌唱则是表达自身。真实场景中的牧歌、哭丧、哭嫁等等与舞台上的表扬,其本质意义迥然不同,舞台表演难以呈现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我们不能回避他们究竟是为谁而歌、为何而歌。
再而如同属农耕文化的田歌,在土家族可能是薅草号子,在苗族也可能是飞歌,在江西的客家,则可能是采茶歌,他们所呈现的题材内容、音乐样式和审美观,显然也有极大的差异和不可比性。同样,正因为文化属性的因素,对民歌演唱评判的标准的价值观也有诸多差异,除了涉及演唱者自身的技术性因素,也可能牵涉歌唱内容,甚至埋伏着潜在的伦理价值观在其中。如我们熟知的少数民族的史诗,他们的主要文化功能实际上是以传承本族群的文化记忆、经验常识为主,听众即受众者们关注的对象绝非仅仅局限于音色、音质的好坏,更多的是根据唱诵者所表达的内容予以褒贬,在这里,包括声音在内的技术性因素不过是内容的载体和辅助手段。仪式歌曲亦如此,尤其是在具有宗教、准宗教和祭祀特征的歌曲。在实际考察中,我们往往发现,当地人对其的评价跟外来者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站在不同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在其文化圈的内部,人们视神歌、巫歌是有别于一般歌曲的,前者是为神歌唱,后者是为人歌唱,二者的文化功能显然缺乏一致性。毫无疑问,悦神和娱人的性质差异大也。用民族音乐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主位与客位观察立场导致的不同,也是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必有的差异。
音乐的文化属性极其复杂,音乐的意义何在?音乐到底是什么?例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们却必须承认,文化功能和属性存在多样性。其中之异同可能因时因人(族群)而异,古人的礼乐观与今天的音乐观的变化也表明了这一点——音乐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诸多层面是相对应的。就各民族的文化而言,民族性是一个核心问题,表现在演唱风格上,属于文化的审美观和民族风格问题;如果指向精神和信仰的深处,则是哲学观的问题。试想,我们怎能让佛教的早诵、伊斯兰教的晨祷、基督教的诵唱并列演唱而一分高下呢?美感也是存在民族性,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基础不同,美感一样各具特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审美习惯和偏好。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化体系内,而美感的形成、文化的形成,又与民族的心路历程、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南方诸多山地民族民歌的内向与江南民歌的华丽、北方草原民族民歌悠扬的风格,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也正说明了这一切吗?
基于如此思考,我们说,民歌的文化属性因内涵的不同而不同,在民间,人们绝不会将情歌与祭祀歌置于同一层面加以对比,甚至他们所依附的文化空间也是严格区分的。在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情歌只能背着长辈于屋外山野相互对答,而长辈间所唱的情歌与年轻的情歌又是不同的,年轻人也不能与老年人对唱情歌。不同歌种其演唱主体也有严格区分,神歌、祭祀歌曲就只能由巫师演唱。由此我们看到,在真实的民间,歌唱主体、歌唱对象、歌唱内容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性,自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依据。而今天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比赛场合,我们却经常看到这种有悖于普通文化常识的现象。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比赛跟实际生活是有区别的这样那样的托辞加以辩解,但问题是,这种脱离生活的“一较高下”究竟意义何在?我们并不拒绝民间音乐可以做舞台化的艺术加工,很多民族的民间音乐,往往就是作曲家对民歌进行再加工并由此传唱开来从而为世人所熟知,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对维吾尔、哈萨克等族民歌的改编。但这属于另一个问题,即对民间音乐的提炼和艺术升华。民歌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技能。如果说是为了交流、宣传、推广民族文化,为什么又非得用比赛的方式?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完全可以用我们熟知的文化展演、汇演的方式。显然,这是上面所讲的外力作用的结果非民间文化的自主行为。
综上所述,民歌的意义(乃至音乐的意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音乐本体自身、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音乐与外部因素的特殊关联。它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系统,也当归属于各自的社会文化系统,对它们的评断标准也得受其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制约。笔者深信,如果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不甚了解、对其审美习惯和文化价值观不熟悉,对其生活的环境、历史不明了,对其民歌发生的文化空间缺乏体悟,是难以对其做出较为客观的评断的,或者说,这种评断是十分有限的。难怪有评委明确表示出自己的疑惑和不解:“我最不理解就是这个。什么是原生态?各个民族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瑰宝拿出来,以什么为标准进行评价?作为一名评委可能熟悉一个民族的东西,可是很难懂五十六个民族的东西。”“都是各民族上千年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语言、唱法都不一样。你说,龙船调和新疆刀郎木卡姆,苗歌和藏歌怎么比?”②原因即在此。
民歌,是“音乐”的民歌,也是“文化”的民歌,除了声音、歌词、技巧,还包涵太多的因素。民歌,是一个综合体。
对民歌的“原生态”一词,就笔者的理解,大约不会超出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歌曲本体的“原生音乐形态”。其二,指民歌演唱的“原生文化形态”,也就是强调文化空间的再现。其三,指演唱方式的本真和自然状态。那么,我们试加分析,看看所谓的“原生态”是否存在和客观地反映出来。
认同“集体创作”是民歌的特性之一,并具有在流传中不断得到加工的特征,就认同了所有的民歌是在实际生活中叠加累积的产物这一观点,它意味着“民歌”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样一来,每一首民歌,我们都可视之为一个民族心智的历史积淀,都具有各自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特征。既如此,属于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不断加工的产物,那么,谁能说我们目前在一些大赛中所说的“原生态”民歌具有真正的“原始形态”呢?实际上,正因为民歌存在不断加工创作的文化特性,才使之焕发出百态千姿的面貌和生机,这是民歌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一首《茉莉花》,我们能听到众多的版本,不同的版本体现出来的地域性风格差异又是多么的不同——旋律、节奏、语言、音色等等。这样的例子在各民族的民歌海洋中何其多。用生物学的学科理论概括,这些不同版本的《茉莉花》之间的关系实则是次生、再生、衍生之间的关系。民歌的形态学研究,针对的就是在这百态千姿的各种变体中找寻和概括其生成、构成规律。黄翔鹏先生晚年提出“旋律考古”,并从若干民歌实例中查找其历史形态,黄先生说“传统是一条河流”、“要在吴淞口的入海处,找到一滴来自金沙江的水”。其核心思想就是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将其与自己擅长的学科领域紧密结合,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拓展出新的理论思维。因此,从这一点讲,民歌虽在逻辑上存在“原生形态”,但这种在音乐本体上的“原生态”却实实在在属于它的“历史形态”。在以“青歌赛”为代表的各种舞台上,我们所见到和看到的所谓“原生态民歌”,大多数都有专业作曲家加工的痕迹,以“十三届青歌赛”的曲目为例,夺得金奖的“土苗组合”的参赛歌曲——《细碗莲花》,就是地地道道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准确地说,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而不是民间歌曲。至于参赛歌手,更是彻头彻尾的专业人士——分别来自专业团体和艺术院校。这一曲目之所以能假“原生态”之名,是偷换了“原生态”概念,当然也混淆了“原生态”和“原生态风格”之间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如果说,“原生态”概念的提出是旨在强调“原生文化形态”,即包括歌曲在内的整体文化背景的话,我们说,至少在目前舞台化的“原生态”氛围和场景设计也是远远不够的,观众又能从仅仅穿着民族服饰的歌手身上看到多少“原生态”文化?观众通过歌手的表演,又能领略到多少歌曲背后的民族文化面貌呢?就“强调文化空间的再现”这一思路而言,如若连像话剧表演那样对生活场景的舞台模拟都做不到,那么,托现在多媒体科技的福,导演们,请通过舞台上的大屏幕投放与歌曲相对应的背景吧,让观众看看他们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季节、什么环境下演唱这些“原生态民歌”的,看看那些真实、素朴的芸芸众生,看看他们是怎么孕育出这些美妙的音乐,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舞台化动作。
第三个问题,就是唱法的问题。这是“原生态”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青歌赛”的分组设置,将其命名为“原生态演唱组”,这个为分组所取的名字,到底指的是“原生态歌曲演唱组”、“原生态唱法演唱组”、还是“原生态歌手演唱组”?这个问题很是模棱两可。如果理解为“原生态歌曲演唱组”,我们所听到的则大多数都是作曲家创作或经过大幅度改编的歌曲。如果理解为“原生态歌手演唱组”,那么又没有将专业歌手(专业团体背景)或和民间歌手严格区分开来。如果说是针对“原生态唱法”,实际上这个组中很多歌手的发声技巧,又很难说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态”。正如评委李谷一的困惑与质疑:“最初我们界定的原生态唱法,是未经学校学习的、原始的唱法就叫原生态,但现在很多来比赛的原生态是经过包装的,那么这个名字还成立吗?还有,说起原始,到底原始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很难界定的。”③概念含糊,当然就会引发出混乱和争议。田青评委也在比赛现场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族民间唱法”比“原生态唱法”更名副其实,的确切中要害。所谓“原生态唱法”也牵涉到如何评比打分的问题。唱法也是文化的反映,或者说唱法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唱法也有民族性。既然是来自各民族民间的唱法,又该如何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呢?也许我们可以用专业院校的那一套——节奏、节拍、音律、音色、音准等等,不过,这将是自己给自己设“套”,如同用同一尺码的鞋去套各种尺寸大小的脚——因为各民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律制,而有的民歌无论音高和节拍均是无法用西方记谱法记录下来的——这将在客观上对倡导唱法的多元性起到消极作用。
因此,我们说,与民歌有关的“原生态”问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样式,不具“可比性”。原生态,实属一个伪命题。
文化属性,是文化与生俱来、同时不断加深、变化的某种特有属性。一方面,不同文化样式之间的差别,往往就是由其特有的某种属性所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属性的认识,有益于把握和了解文化的个性和本质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她的《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菊花和刀——日本文化的两面性和象征之物的解析,深刻地阐释了日本文化独有的气质和特征,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历史上曾移植了中国唐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到近代又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的观念和制度,经由若干年发展,终于成功地对其本土文化进行了“改造”。日本文化属性的变迁,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文化属性观变迁所导致的结果。人们常说,当代日本文化具有两极对立的特性,一面是社会制度的极端西化,另一面又顽强地保留一部分传统习俗,并由政府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这样一来,西方的现代制度文化与传统传统观便构成了日本文化内部看似对立、却又相互并存的局面。之所以导致这样的情况,这是跟日本近代历届政府,或者说跟日本的社会精英所持的文化属性观脱离不了干系的。
所谓文化属性观,即对文化属性的认识和所持的态度。在西方学术界,历来有存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属性观两种派别。日本当代文化的特征显示出,其现代文化的建构受到了这两种观念的影响。
原生的文化属性观源自启蒙主义的主体论,它预设了文化属性的先验本质。在20世纪,原生的文化属性观受到了挑战。如霍尔(Hall)在《多重小我》中就提出属性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由族群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建构而成的:“‘文化属性’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文化属性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非超越了空间、时间、历史、文化。文化属性来自某处,具有历史。但就像每一件历史事物一样,会不断变形。它们绝非永恒固定于某些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游戏。”“此种建构论的属性观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论述中则变异为杂种形式,霍米·巴巴称为‘殖民杂种’,而哈拉薇干脆命名为‘后现代合成人’,从而完全颠覆族裔本性。这种杂种论的属性理念试图搁置本土化/全球化的二元对抗模式,颠覆种族纯洁性和某种文化的优越性,达成反抗殖民宰制的企图。”③
文化属性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仔细回顾近二、三十年来文化领域的诸多争议,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这命题,诸如关于“维护汉语的纯洁性”等等,只不过具体反映到音乐界,则稍显迟缓。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火如荼,各级政府机构已经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参与其中,但倘若不在理论上加以认真梳理,在具体操作的技术性细节上,必然带来新的问题。
“原生态民歌”概念的提出,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契机,它必将导引众多学者,在民间音乐的本质、属性特征思考得更加透彻。
原生论的文化属性、建构论的属性观是西方学者提出、同时持续讨论的话题,在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将此作为“原生态问题”的延伸部分提出,藉此希望引起同行的兴趣,将这一话题继续深入,这就是在此两者之间,我们可否有更多的选择,以及如何应对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完成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
注释:
①Nettl,Bruno.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wenty-nine Lssues and Concepts[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转引自薛艺兵.仪式音乐的概念界定[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②《李谷一不赞成原生态唱法》、《李谷一炮轰青歌赛:原生态、美声、民族难界定》,中国新闻网。
③文化属性意识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