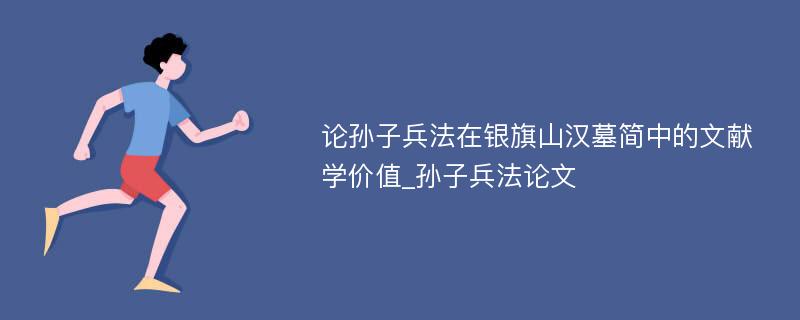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之文献学价值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子兵法论文,刍议论文,汉墓论文,竹简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其中有关古代兵书的竹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兵书竹简对于破解历史上孙子之谜,判断《孙子兵法》成书的大致时代,釐定《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的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的某些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之社会变革性质的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佐证传世古籍的流传规律、恢复或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典状态,均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术价值。
如果将汉简本《孙子》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宋刻“武经本”、“十一家注本”进行对勘比较,认真考察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就导致这些异同之所以发生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原因做出解释说明,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有关出土新资料与传世文献在兵学史、思想史考察方面所发挥功能的认识。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要早数十年到上百年。①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②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汉简本《孙子》对深化《孙子兵法》的研究,首先是给我们就《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编排序列。
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一篇”编排序列,是始于《计篇》,③而终于《用间篇》。在全书的内容逻辑上看,这是成立的,也是合理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是孙子兵学思想的重点内容。《计篇》的中心内容,即是阐述“知彼知己”的基本方法,强调“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估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在他看来,必须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才可以对敌一战。这就是所谓的“先胜”。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认为这才是巧妙驾驭战争的“上将之道”。这就决定了孙子把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的制定和实施立足于“先胜”的前提之上。
然而,如何达到“先胜”的目的呢?孙子认为,必须通过主观上的不懈努力来加以实现,而努力的正确方向,则是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预测各种变数,在此基础上正确筹划战略全局,机宜实施战役指导,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用他的话说,即是“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④由此可见,以“知彼知己”为主要方式的“先胜”思想,是孙子制胜之道的出发点和基础。故曹操有云:“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⑤可谓得其要旨。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可见,孙子所说的“知”,既包括战略层次对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如“五事”、“七计”。也包括对战役、战术层次敌我双方虚实强弱的比较,还包括对战场环境的了解,如“知天知地”,“知战之日,知战之地”。
孙子对“知”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他认为,战争中的“知”包括敌我双方政治、经济财力、军事和自然环境条件诸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首先是战争的决策谋划和指挥者国君与将领,国君必须善于“修道而保法”(《计篇》)、“择人而任势”、“安国全军”,他必须具备“动而胜人”的“先知”,他从不“怒而兴师”,他的政令军令通畅无阻,兵民愿与他同生共死而“不畏危”。总而言之,他文武兼备、智谋超人、治国有道、安民有策、知战知兵。将领必须具有“智、信、仁、勇、严”的素质,必须“尽知用兵之利”、明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善于“形兵”“造势”,深谙“奇正之术”、“迂直之计”,能“伐谋”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深懂诡道,做到“攻而必取,守而必固”,善“修其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还要看兵器是否锐利先进,兵士是否训练有素,粮饷是否充足,编制是否合理,通讯是否通达,信息情报是否充足。还要掌握季节、气候和天气的变化,了解地形、地物、地势、交通情况及行军路线怎样,“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虚实篇》)。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子兵法》有关“知”的内涵其实包含了“知行合一”的根本要素,这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孙子兵法》中有些论述,今天看起来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前后说法颇不一样。如《形篇》中讲道:“胜可知而不可为也。”意即胜利可以预知,但是却不能去强求。然而《虚实篇》却又讲什么“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不可为”变成了“可为”,似乎讲不通,在同一本《孙子兵法》里面怎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其实这并不是传抄之中出现了错简,而恰恰反映了孙子思维理性的深刻与辩证。即:一方面战争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你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从事军事活动;但是同时,作为战争指导者在战争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不是被动的,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创造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胜利的可能及早转化为现实。可见“胜可知而不可为”与“胜可为也”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前者是就尊重战争客观规律性角度发论,后者则是从发挥将帅主观能动性发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⑥
正是由于“知彼知己”的极端重要性,《孙子兵法》以《计篇》为全书的首篇,在其中起到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考竹简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⑦《计篇》亦为其首篇。
然而,竹简本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结束篇,则并不相同。传世本为《用间篇》。考察《用间篇》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其列为整部《孙子兵法》的终结篇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它主要论述在战争活动中使用间谍以侦知、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以及间谍的种类划分、基本特点、使用方式等等。它是孙子从理论上对前人丰富的用间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古代用间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孙子主张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而要“知彼”,即“知敌之情者”,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间。孙子认为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多的好办法。反之,如果因为爱惜爵禄不使用间谍,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才是十足的罪人。接着,孙子充分论证了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方法,他把间谍划分为五大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指出“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主张“五间并用”,而以“反间”为主,并提出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的用间三原则。同时孙子还指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
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绕同心圆,起点与终点重合,即所谓“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这么一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测敌情(《计篇》),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复到《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他在《孙子谚义》中阐述了他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认识:“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⑧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简牍材料中,著录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其内容表明,在西汉初期,《孙子》一书的篇目次序与后世传本的篇目次序有较大的差异。据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统计,两者之间,“十三篇”中只有《计篇》、《形篇》、《军争篇》、《地形篇》、《九地篇》五篇的篇次相一致,其余八篇则次序不同。⑨这中间,尤以结束篇的差异最为引人关注。在竹简本中,“十三篇”的终结篇为《火攻篇》,而非众所周知的《用间篇》。
我们认为:“十三篇”在全书结构中的安排,是孙子颇有深意处置的结果。这里,就有必要认真考察《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知兵而不好战”乃是孙子著述兵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孟子·离娄》也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等等,就是当时战争日趋激烈与残酷的形象写照。《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所以,如果按孙子“慎战与重战至上”的战争观念这一内在逻辑主线,那么,“十三篇”始于“兵者,国之大事”,而终于“安国全军之道”,以“重战”和“慎战”为全书之核心宗旨以贯穿于全书,也完全成立,它遂使《孙子兵法》全书“譬若率然”之势得以毫无滞涩,通贯融会。
很显然,无论是传世本始于《计篇》,终于《用间篇》;抑或竹简本始于《计篇》,迄于《火攻篇》,均是各有理据,可以成立的。其区别在于传世本的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更注重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而竹简本的篇次结构序列排比,尤其注重于“兵凶战危”的宗旨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价值观为出发点。前者关心的是战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后者考虑的是战争理念上的永恒合理性与崇高合法性。概括地讲,是前者侧重和倡导“或然”,后者推崇和张扬“必然”。但由于核心价值规范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根本的指标性意义,因此,竹简本有关“十三篇”的篇次排序,似乎更接近孙子撰写兵书的本意,更有其合法性。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的价值,更体现为其在文献学上对勘、比较、釐定传世本《孙子兵法》文字、文义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它可以在相当程序上廓清传世本《孙子兵法》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所导致的某些文字的歧义,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时代文化精神折射在《孙子兵法》文本演变上的诸多特殊烙印,从而更好地接近或复原《孙子兵法》的本来面貌。
首先,它有助于澄清传世历史典籍中征引《孙子》之文有异于传世本《孙子兵法》文字的谜团,解答由于这类差异的存在而给后人所造成的困惑。
如《形篇》讨论“攻守”问题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十一家注本、武经本等都认为:采取防御,是由于兵力上处于劣势;采取进攻,是因为在兵力上拥有优势。从文义上看,这是说得通的。但是考察史籍,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难解的现象,这就是汉人言兵法、征引《孙子兵法》者多言攻不足守有余。如《汉书·赵充国传》言:“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后汉书·冯异传》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那么,这中间的矛盾与扞格,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赵充国与冯异等人,所依据的《孙子兵法》文本又是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由于竹简本的发现,我们终于得以知道,在汉代流传的《孙子》中,此句当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意为在同等兵力的情况下,用于防御则兵力有余,用于进攻则会感到兵力不足。其文义恰与赵充国、冯异等人有关《孙子》的引文相同,换言之,赵充国、冯异等人所征引《孙子》之言实有所本。传世本作“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乃是后世辗转传抄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误植。
又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意为变更、更换。旌旗,指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车杂而乘之”杂意为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韦昭注:“杂,合也。”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为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意为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表面上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即“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乃作“共”。而“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如祸福与共,《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全句的文义,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杂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从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作“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⑩
再如,传世本《军争篇》:“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此处,“上将军”,《菁华录》谓应作“上军将”。汉简本无“军”字,止作“厥(蹶)上将”,张预注:“蹶上将,谓前军先行也。”贾林注:“上,犹先也。”上将,即上军(前军)的主将。此言若军队奔赴五十里地而汲汲争利,则前军的主将会受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谓田忌曰:……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所引亦称“上将”,而无“军”字。很显然,传世本“上将军”中的“军”字乃衍文,《孙子》原文当为“上将”。贾林、张预之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毕竟是缺乏文献依据的断制,现则凭借汉简本的原始文字而能得以最终确立。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势篇》。传世本“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然而,此处“必”字,注家多释为“毕”义。张预注云:“人人皆受敌而无败”,是其所本当为“毕”字。而王皙注则云:“必当作华”,是其所据本作“毕”。那么,其所据本为何者?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前是无法考究的。现在这一疑窦则赖汉简本的发现而得以涣然冰释了:因为在汉简本之中,“必”正作“毕”。
其次,通过汉简本《孙子》与传世本《孙子兵法》文字进行对勘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多处的差异歧义,但是,这似乎并不影响各自文本文义句意上的顺畅通贯,分别可以作疏通阐释,而不会给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与相关学理造成太大的困扰与障碍,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其语境和文义依然存在着高下轩轾之别,在不少情况下,汉简本的用词显然更为贴切妥恰、切中肯綮,更合乎学理上的逻辑属性,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孙子兵学的深邃哲理与基本原则。
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差异,就很典型地说明在一定的程度上,汉简本的文字表述要优异于传世本的通常描述。
众所周知,军队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这里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这里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孙子指出,在军队管理上,如果没有教化,一味讲求军纪军法,使大家整天生活于恐怖之中,那么必然导致将士离心离德,矛盾激化,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正常发挥,“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行军篇》)。但是如果不严肃军纪军法,单纯宽厚溺爱,行“姑息之政”,也势必会导致将士斗志涣散,各行其是,整支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行军篇》),这同样不利于军队的行动,同样是军队建设上的灾难。所以,在孙子看来,只有真正地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方能够“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上下,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同仇敌忾,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乃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帖,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考汉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可见,其文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义。(11)《易·乾文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是,“令”为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义蕴。据此,则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很显然,按汉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治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而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逊色于汉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训》亦云:“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汉简本相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时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文本与汉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正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改。
又如,传世本《计篇》所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各本皆作“不畏危”。这虽于义可通,但殆非《孙子》原文。曹操、李筌等注家均止注“危”字,云:“危者,危疑也”,杜佑注亦云:“佹者,疑也”,可见,这些注家均不注“畏”字。孟氏注虽注“畏”字,然又云:“一作:人不疑”,“一作:人不危”。意近曹氏诸家之义。考俞樾《诸子平议·补录》。其要云:“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民不危,即民不疑,曹注得之。孟氏注曰:‘一作人不疑’,文异而义同也。《吕氏春秋·明理篇》曰:‘以相危’,高诱训‘危’为‘疑’。盖古有此训,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上,失之矣。”
应该说,俞樾的见解是正确的。今幸得汉简本而予以证实之。按:汉简本“不畏危”作“弗诡也”。“弗诡”即“不诡”,读gui。古训“违”,训“疑”,即乖违、疑贰之意。《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由此可知,孙子言“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弗诡”,其意乃为民众与统治者能做到生死与共,而绝无二心,而并非简单地指民众不畏惧危险。显而易见,汉简本“弗诡”可以纠正传世本“不畏危”的错讹,证实自曹操直至俞樾有关“危”字的释读乃是言之有据的。此解释也很好地说明了“危”字的由来,即“危”系“诡”的借字,义蕴皆为“疑贰”。
类似这方面的文献学贡献,汉简本实不胜枚举。像“王霸之兵”的提法,传世本《九地篇》皆作“霸王之兵”,如“四五者,一不知,(12)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云云。很显然,“霸王之兵”的称谓实非《孙子》原文的提法。按,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王霸”的提法,而罕见“霸王”的称呼。如《尉缭子·制谈》言:“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司马法·仁本》云:“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吕氏春秋·知度》:“夫成王霸者固有人。”又《荀子》一书中有《王霸篇》。故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在校语中指出:“汉简本作‘王霸’胜于传本。”(13)简言之,汉简本“王霸之兵”乃是孙子之原意,而传世本“霸王之兵”则是后人在传抄《孙子兵法》过程中出现的错讹。
又,《用间篇》中,孙子提出“用间”的三个前提条件。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传世本作:“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从文义上讲,这当然讲得通。然而“非圣智不能用间”,汉简本作“非圣□□□□”,“圣”字下残缺四字,疑原无“智”字。“非仁义不能使间”,汉简本作“非仁不能使……”下缺。“仁”下无“义”字。应该说,汉简本的文字当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战国中期之前,单音词使用更频繁,战国中期之后,才普遍使用双音节词,故孔子更习惯于单称“仁”,到孟子那里才热衷于“仁义”并称。(14)《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那时用词的习惯当是“仁”、“圣”相称,而不宜“圣智”、“仁义”相连称。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汉简本保存了《孙子》遣词造句的原始风貌之特点,实可谓难能可贵。
其三,考察和分析汉简本《孙子》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文字差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孙子兵法》其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所受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与规范,看到不同时期文化精神在其内容文字变迁上的折射、渗透。换言之,这有助于人们正确释读不同思想文化观念在《孙子兵法》上所打下的特殊烙印。
《孙子兵法·形篇》有下列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意谓真正能打仗的人取得胜利,并不显露智谋的名声,并不呈现为勇武殊俗的赫赫战功,而于平淡中表现出来。即老子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因此,杜牧注云:“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然而,对勘比照汉简本同段文字,“故善战者之胜也”,汉简本乃作“故善者之战”。更为重要的,是汉简本有“无奇胜”三字,甲本作“无奇□”,乙本作“□奇胜”。而这恰恰是传世各本所皆无的。那么,“无奇胜”这三字是否该有?怎么来解答为何汉简本“无奇胜”三字到了传世本那里而不见踪影的缘由?并进而如何释读与判断汉简本与传世本两者之间,因“无奇胜”三字的有无而产生的优劣高下?也就成了当今《孙子》研究者无可回避的问题了。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常用术语,其含义非常广泛。一般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它包括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变换战术两个方面。具体地说,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军为正,突然袭击为奇。
“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这是古人对“奇正”地位和价值最富诗意的评论。“奇正”概念最早见于《老子》,但真正把它引入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在《势篇》中,孙子用精粹的语言揭示了“奇正”的基本含义:凡是开展军事行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在兵力使用上,要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战术变换上,则要做到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虚实莫测,变化无端。“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在孙子看来,军事指挥员如果能根据战场情势而灵活理解和运用“奇正”战法,做到战术运用上正面交锋与翼侧攻击相结合,兵力使用上正兵当敌与奇兵制胜相互补,作战指挥上“常法”与“变法”交替使用得当,那么就算是真正领会了用兵的奥妙,也为“造势”、“任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袭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下编)·奇正》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尉缭子·勒卒令》说:“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到了《李卫公问对》那里,“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它对“奇正”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比孙子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的逻辑结果。
很显然,如果按照《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范围来剖析,以孙子所提倡用兵打仗必须贯彻“奇正相生”的原则,做到“以正合,以奇胜”等种种迹象来讲,“无奇胜”三字与《孙子兵法》“奇正”理论相背离,传世本不见“无奇胜”显然有其合理性。
但是,问题在于:“无奇胜”三字原本是在《形篇》之中。而《形篇》乃是《孙子兵法》全书中专论“军事实力”建设问题的。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镒称铢”,“决积水于千仞之溪”,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子强调实力至上,以提倡发展实力为优先之务,乃是有其深刻思考的。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力。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天平上的砝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后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由于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势的转换,使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这是战争活动的客观规律。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熬白了头发,累酸了腰腿,“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头来依然是僻处西南一隅,“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太过于悬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众寡不侔,攻守异体”,(15)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后人们除了替他一掬同情的眼泪,“长使英雄泪满襟”,还真的无法再作其他解释。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人心向往统一、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较之于陈后主方面,实乃“以镒称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此可见,孙子对军事实力建设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用专门的篇章加以深入详尽的探讨,这的确反映了其军事思想注重实际、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精神。
明乎《形篇》的宗旨,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属于较早期《孙子》版本的汉简本《形篇》中,会有“无奇胜”这样的文句了。为了突出和强调从事军事实力建设的至高无上性,孙子他可以将“正合奇胜”“出奇制胜”“奇正相生”等一般原则暂时放置一边,提倡一切从根本做起,强本而固基,主张人们不要玩弄小聪明,应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把加强实力作为重中之重。在这种强调与张扬实力优先原则的背景下,《形篇》中遂有了貌似与“奇正”原则相悖,实际精神实质一致的“无奇胜”这类文字了。换言之,“无奇胜”一语在《形篇》中出现,实际上就是孙子为了最大限度突出军事实力的中心地位之文字修饰手法,既是合理的,也是别出心裁的。应该说,这样的特定篇章之特定表述,“无奇胜”的提法并非为个案,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在所多有。如《形篇》言“胜可知而不可为”;《虚实篇》言“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等等,就是类似的例子。它们看起来自相矛盾、扞格乖舛,其实内在统一、浑然一体。仅仅是外在形式表达上的各有侧重而已。传世本的传抄整理者,未能深谙孙子的苦心孤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无奇胜”一词,马上联想起孙子所主张的“正合奇胜”用兵原则,进而判断“无奇胜”与“奇正相生”相背悖乖戾,于是在传世本定型过程中,自以为是地将它删去,还自鸣得意。其实,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弱化了《孙子兵法》哲理的深刻性、睿智度,或多或少使孙子深邃的辩证法思想趋于平淡化,买椟还珠,可谓是《孙子兵法》一书的“罪人”。而让我们感到欣幸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的面世,遂使“无奇胜”这一精言妙语能重见天日,帮助我们对《孙子兵法》一书哲学上的深刻辩证法又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计篇》之中。其言“五事七计”,其中,解释“天”之内涵时,汉简本较之于传世本,除“阴阳、寒暑、时制也”外,又多出“顺逆,兵胜也”五字,为各本所无。这里,所谓“顺逆”乃是以阴阳向背为禁忌,所谓“兵胜”则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16)
我认为,汉简本有此五字,恰好说明它更为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始面貌。《孙子兵法》为“兵权谋家”,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所言:“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包阴阳”乃《孙子兵法》的必有之义。考察今本《孙子兵法》,我们可以发现其涉及“阴阳”的痕迹尚有存在。如《虚实篇》有云:“画地而守之。”李零在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一书中认为,画地本为一种画地为方,不假城池,禁鬼魅虎狼的防身巫术。后来兵家用来指营垒的规划,指出孙子在此处指划定范围,不用沟垒,喻其至易。而这就是“兵阴阳”的特色。这个解释颇有新意,可资参考。(17)又如《行军篇》言:“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里同样有“五行相生相胜”的“阴阳五行”含义在内,也是“兵阴阳”的语言。
但是,《孙子》中“兵阴阳”的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其本质特征,乃是《用间篇》所云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兵阴阳”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显得荒诞不经,乖谬妄戾。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尝言:“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可见,至唐宋时期,“兵阴阳”虽仍存之于世,但影响与作用其实是在一步步弱化之中。之所以不废“兵阴阳”,亦仅仅如李靖所言,是为了“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罢了。缘是之故,汉简本所处的时代为“阴阳灾异”思潮弥漫的汉代,故很自然地保留了诸如“顺逆,兵胜也”等充满“兵阴阳”色彩的文字,而宋代最终付梓刻印的传世诸本,则致力于冲淡弱化“兵阴阳”的痕迹,故顺理成章将“顺逆、兵胜”等文字删去抹煞。应该说,这种文字上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版本异同问题,其背后乃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变迁因素在起着指导引领和制约规范的作用,是打上了深刻的时代文化精神烙印的。
综上,本文通过对汉简本《孙子》与传世的《孙子兵法》宋刻“武经本”、“十一家注本”的初步比较研究,就两者之间诸如“顺逆”、“无奇胜”、“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等关键语词所存在的差异做出自己的阐释,以力求说明汉简本在不少方面较之于传世宋本,更接近于《孙子》文献的原始面貌,更加符合孙子兵学的内在逻辑与核心精神,并试图就导致这些异同之所以发生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原因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当然,汉简本的文献学价值远远不止于这些方面,至少,它还包括了可以为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认识提供可贵的帮助、使我们有可能更恰当地评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史料依据及其价值,等等,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限于水平与篇幅,诸如《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再研究,等等,本文也只能暂付阙如,俟诸他日。
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汉简本《孙子》虽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研究价值,但它的发现并不能对传世本《孙子兵法》的整体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导致决定性的改变,更不能取代传世本《孙子兵法》在今天研究与弘扬孙子兵学上的主导性地位,这一点当是毫无疑义的。换言之,至少在《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领域,所谓“重写学术史”的“曙光”,并没有任何的端倪与征兆。
①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见《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③此为“十一家注本”的命名,“武经本”则作《始计篇》。
④按,“胜乃不穷”,乃“十一家注”本的文字,在“武经本”中,则作“胜乃可全”。
⑤曹操:《孙子注·序》,见《曹操集》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8—119页。
⑥参见黄朴民:《孙子兵法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⑦实为十二篇,《地形篇》有目而未见具体文字内容。
⑧山鹿高祐:《武经七书谚义·孙子谚义》卷一,见《山鹿素行集》,大正元年(1912)右川黄印本。
⑨参见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前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⑩古代兵书中,“善俘”的主张是常见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即有言:“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11)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12)“一不知”,“十一家注”本作:“不知一”。
(13)《银雀山汉墓竹简》[壹]。
(14)刘笑敢的观点似可为本文这一看法作佐证。他指出:在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的是单纯词,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复合词才逐步出现……在几类不同时期的文字材料中,只要每一类材料都有一定的可比性和足够的代表性,那么,使用复合词较少的一类,必然是早出的,使用复合词较多的一类,必然是晚出的。参见刘氏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15)《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张俨《默记》。
(16)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页。
(17)参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第207—208页;《〈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31—4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