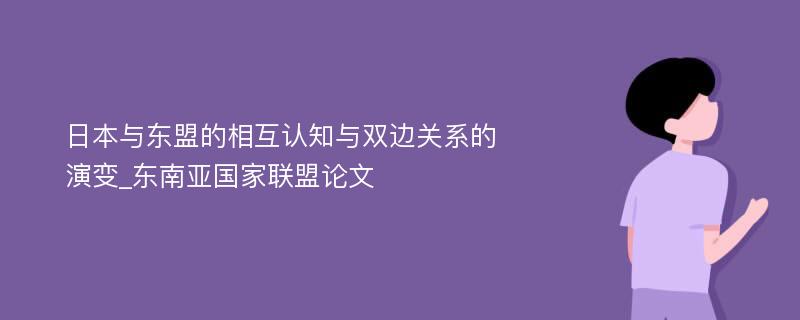
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双边关系论文,日本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和东盟国家均为我国周边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关系样式是我国东亚战略必须加以关注和应对的重要课题。战后以来,东盟—日本关系逐渐发展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双边关系。总体上看,二者间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而政治、文化关系则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本文试图梳理自战后以来这种关系的演进脉络,通过探索双方间相互战略认知的差异,以考察它们之间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演进的历史趋势。
任何决策过程与行为首先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因素,“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要理解国际关系演进的根本脉络,有意义的做法是“察看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以他们现有的方式观察世界”。①认知结构一旦形成就会相应固定下来,并成为观察与因应其他行为体的出发点。因此,日本—东盟关系的发展,不仅与日本如何认识东盟相关,而且还“取决于日本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也取决于东盟国家如何认识日本”。①也就是说,无论日本是否能够或愿意在东南亚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政治姿态,都要取决于其美国盟友、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和公众舆论的推动,以及其东北亚和东南亚邻邦对日本的感知。③日本与东盟关系是一个大国与一组中小国家构成的集合体之间的关系,要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战略认知且定位其关系式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国家属性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战略选择的优先次序不同,它们在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的判断上也不尽相同,由此带来在一些关系到自身和东亚地区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异,这势必对各自的对外战略和相互关系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一、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
综观战后几十年的日本—东南亚关系史,我们可以观察到该双边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调是“经济外交”,经济关系构成双边关系的基本内容。20世纪50年代,日本以战争赔偿的方式重返曾经侵占过的东南亚,并逐渐与该地区国家发展起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1957年,岸信介首相成为战后首位访问东南亚国家的日本领导人。在访问中,他提出设立“东南亚发展基金”的建议。日本首相首访东南亚显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对东南亚关注的开始。但是,日本的外交思维基本上还是“把东南亚当作他们的‘农村’,他们商品的去路”④的“经济外交”,这实际上是日本在战略安全上隐藏在美国的背后,同时也是为了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加强的对外政策模式。这种国家战略思维形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西方工业国是市场区,而亚洲,尤其东南亚是原料供应区和生产区”。⑤平心而论,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对外战略是战后日本的现实主义选择,是其经济崛起的一大注脚,但其负面影响是,在世界上获得“经济动物”称号的同时,日本在东南亚的国际形象也大打折扣。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先后遭到“尼克松冲击”、“石油冲击”和“东南亚冲击”。在三大“冲击”之下,日本政府被迫对“经济外交”政策进行反思。1975年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时,在曼谷和雅加达所遭遇的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就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必然结果。“东南亚冲击”迫使日本不得不审视并制定新的东南亚政策。
第二,1977年福田主义的出台到冷战的终结标志着日本—东盟关系进入到全方位发展的全新阶段。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⑥是战后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拐点”,象征着“日本接近东南亚的顶点”,⑦给双边关系营造了一种相当积极的政治氛围。当时,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对于正着力进行经济发展的东盟国家而言具有颇大的吸引力。对于日本来说,之所以重视东盟,一方面是因为东盟五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异常密切;另一方面,自1976年的巴厘会议以后,东盟已经崛起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区域性组织。对于这样一个在经济上有密切关系,在地区政治和经济有一定发言权的东盟,日本当然会加以重视。与此同时,在美国撤出越南以及印度支那“共产主义化”的国际背景下,基于自身的东亚战略安排,美国支持日本与东盟国家加强关系,在东亚地区形成“日本—美国—东盟”的战略“三角关系”,该“联盟”以日本的经济力量和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依托,以“反共”为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战后历史上东盟—日本关系较为亲密的时期。1989年5月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在雅加达发表《日本与东盟:共同思考,共同前进》的政策演说,强调双方“天然的”盟友关系,他说:“从地理上看,日本和东盟是天然的盟友,历史也注定要相互合作。”⑧东盟方面同样有这种“特殊关系”的评价,其时,东盟政府首脑在外交场合中均称日本是东盟的“一个特殊的密友”。⑨东盟国家的学者同样乐观地认为,当时东盟同日本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日本有关方面另有一种提法是,双方关系已构成太平洋的主要“轴心”(principal axis)⑩。从日本对外战略的角度看,它非常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视之为战后日本摆脱“经济外交”困境和转向“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突破口。“福田主义”出台以后的历届日本政府,一直寻求以密切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力图在政治外交、文化交流方面与东盟国家结成亲密关系,构思在所谓“心心相印”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将东南亚发展成为自己的战略“后院”。
第三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以来新型的东盟—日本关系。这个阶段的双边关系是没有共同意识形态对手的普通关系,从日本人自我期许的“特殊关系”逐渐演变为平衡、互动色彩更加凸显的“普通关系”,日本逐渐成为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亚地区多极化的不断发展,在自由贸易协定(FTA)成为东亚国家密切双边经济政治关系重要手段的同时,该地区出现了许多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3”、“东盟、+1”甚至“东盟+6”的协商机制相继形成,其目的是讨论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促进互信、增加军事透明度、消解地区冲突以及维持并改善地区秩序。东盟在这些对话机制中发挥了“领导”(leadership)作用。日本—东盟关系更多的是通过东亚地区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而展现出来。冷战后日本注重发展与东盟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盟一体化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二是东盟利用“大国均势”外交策略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提供了平台。(11)虽然日本希望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以东盟为自己战略构想的“代言人”和执行者,间接发挥地区领导作用,但是,这与东盟的国际定位并非一致,东盟可能仅仅视日本为其“均势战略”中的关键角色之一。可以看出,冷战后东盟—日本关系演变的轨迹是基于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政策选择及其互动的产物。一方面,美日同盟关系不仅影响着日本对外决策可能的选择,而且界定了东盟—日本关系可能的走向;另一方面,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同时,日本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成为推动东亚格局演进的重要途径。
从以上三个发展阶段来看,日本—东盟关系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双方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上非常紧密,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与日本的资金、技术与生产之间具有相当的互补性。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都是东盟国家最大的援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其次,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政治外交和文化关系。东盟—日本关系并没有如日本人之所愿,发展成为一种紧密经济关系基础上的“特殊”双边关系,而不过是相当正常的国际关系。日本希望扩大与东盟的文化交流,但是它在物质和心理上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比如,在冷战结束的时候,1974年创立的日本国际协作协会(JICA)负责分派所有的技术专家与援助,但是该机构只有980名人员和47个负责考虑并与受援国联络的海外办事处(同期美国类似机构的人员超过了5000人,海外机构有122个)。(12)日本普通民众也并不重视东南亚地区。(13)由此看来,虽然双方都强调双边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为此也做了多方努力,(14)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战后日本长期推行的“经济外交”以及经济关系一直占双方关系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再次,东亚国际格局直接界定了日本—东盟关系的未来走向。冷战结束以来,尤其“9·11”事件之后,东亚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正处于“后冷战”的历史转型时期。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或塑造了东亚国际格局,并据此对地区内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冷战之后亚太地区的战略结构“主要还是依靠中美日之间的三角权力关系”。(15)因此,从地缘战略的视角看,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不仅是决定东亚国际关系走向的基本要素,而且也影响着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以及双方可能的关系式样。
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与东盟国家具有紧密经济关系的日本,未能在政治外交方面与东盟发展与经济关系相称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在战后以来这对关系变迁的过程中有哪些深刻的制约性因素?导致东盟—日本关系未能在“福田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与全球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与日本及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同时也与它们相互间的战略认知及具体政策密切相关。
二、日本对东盟的战略认知及其东盟政策的局限性
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一方面,日本主观上十分重视在东南亚的经营,日本首相频繁走访东盟诸国并不断“兜售”各种充斥着漂亮外交语言的“主义”,福田赳夫之后的历届日本内阁无不以与东盟国家的“特殊关系”为其外交成就和执政政绩;另一方面,从客观状态来看,东南亚在日本对外关系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除了互利互惠的经济关系比较密切之外,双方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关系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主观期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日本的东盟外交的真实写照。这当然与日本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格局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日本对东盟的战略认知决定了其与东南亚关系可能的走向。
第一,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不必然构成与之相称的政治外交关系,有时反而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自然资源是日本寻求与东盟国家发展密切关系的基本战略依据。日本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脆弱性。这是因为它依赖安全的国际海上运输线,而东南亚占据着日本大部分至关重要的海洋航线和交通要冲。地缘战略安全方面的顾虑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看重东南亚的重要原因。此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和资源贫乏的日本之间存在“自然的”互补性,这是战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维持着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重要基础。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为日本的经济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日本的援助、投资和对东南亚资源的需求相应对东盟国家的经济繁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后以来,经济关系一直是日本—东盟关系的主要内容与推动力。首先,在战略安全方面,日本不是东盟国家依托的主要对象。东盟国家认为,美国对于东南亚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日本仅仅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子”,且只能通过美国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其次,历史、种族、地理和政权类型不会决定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形成对日基本态度最重要的国内因素,是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东盟国家维持对日友好关系的基本动因。因此,东南亚与日本的关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互惠的双边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来自“泛亚洲主义”、“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共性上。(16)这种经济交往主导的双边关系固然是双方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对日本的东盟政策却带来了始料不及的挑战:东盟国家对获取日本的投资、援助和技术转让非常热切并寄予厚望,但对包括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在内的其他关系则兴趣不大,其结果是当日本在经济方面不能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达到其螺旋上升式的预期时,日本提出的外交、文化交流计划就会面临东盟国家冷淡的反应,甚至批评。日本的国际形象因此被判定、乃至定格为“经济动物”,处于只能发挥经济作用的尴尬境地。东盟国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正面认可日本经济作用的同时,在看待日本的政治作用方面则态度模糊。”(17)因此,与经济关系相比,日本与东盟的政治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并不理想,这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全方位外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政治大国途径。东盟是日本寄托和寻求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力图促使东盟成为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垫脚石”。地区大国不一定是世界大国,世界大国必定同时也是地区大国。不是地区大国而是世界大国的,就未曾出现过。故地区大国是成为全球大国必不可少的阶段和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与东北亚国家存在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而与东盟国家具有密切“金钱”交往的日本而言,东南亚乃是其展示地区领导地位的理想平台,对于日本寻求全球地位不可或缺。日本是一个颇具大国情怀的国家,它不会仅仅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日本人看来,仅仅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而只是一个不“正常”的“残疾”国家。日本民主党现任党首小泽一郎曾经提出的“片肺国家”概念正是源自这种观念。(18)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就任首相后,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就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它非常渴望获得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内的政治大国地位,且为此做了多方努力。在达成其目的之前,它必须赢得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和外交支持。首先,经济关系和经济手段是它惯常使用的手段。触手可摸的经济关系与政府开发援助(ODA)是其“收买政治支持的一个工具”(19)。其次,东南亚中小国家是日本展示大国风采、汲取大国信心、激发大国自豪感不可多得的对象。在核国家、军事强国、超级大国,甚至中国面前,日本难以争雄比肩。但在中小国家构成的东南亚面前,日本能够体会到大国的优越感与自豪感。在日本人看来,东南亚国家是其天然的“追随者”和优秀的“门生”,日本可以帮助、指引和教导东南亚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日本也由此感觉它是不可超越的“导师”。由于日本一直都是美国的小伙伴,因此它在全球舞台上同样需要一些国家充当自己的“小伙伴”。(20)由此观之,在东盟国家那里,日本寄托了其抒发大国情怀、实现政治大国之志的期许与使命。但非常明显的是,在双边关系的优先政策目标和议程上,日本和东盟国家各有不同的理解。在东盟所优先考虑的经济关系没有达到预期之前,日本在东南亚的政治大国途径必定面临诸多掣肘,甚至可能成为东盟内外战略的政策工具。
第三,难以把握的“政策平衡点”。东盟是日本在“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寻求在美国—亚洲之间找到一个既不打破“美日同盟”这个外交“基石”、又能维系和促进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策平衡点。自封为“亚洲代言人”和充当欧美与亚洲之间的“桥梁”就是日本东西平衡策略的体现。
的确,在对外政策实践中,日本很难摆脱在美国与亚洲之间“首鼠两端”的战略取向。这与日本的亚洲政策及其国民性相互关联。在日本近百年的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理论一直在支配着它的外交政策。一个是“脱亚论”,即脱离亚洲,不屑与亚洲国家为伍,而效仿西方列强“富国强兵”之路;另一个是“亚细亚主义”,即亚洲一体,联合起来对抗欧美强权。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符合国家现实与长远利益的战略就是切实可行的政策抉择。但是,这种战略思维如果隐含歧视与贬低亚洲邻国,甚至损害其切身利益的话,那么包括东南亚在内的邻邦完全有理由对日本的政治合作意愿、动机和行为产生疑虑和不安。对于东盟而言,如果说难以与日本人相处的话,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自其歧视亚洲人之心理”。(21)与此同时,这种东西摇摆的对外战略思维可能导致日本变态的“双重人格”:在欧美面前低声下气,非常自卑;在亚洲国家面前则傲视群雄,非常自大。以如此不正常的心态看待亚洲邻邦,怎会培育出所谓“心心相印”的关系?正如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所分析的,日本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首先便要尊重与信任他人。倘若不愿抛弃日本传统的东南亚观,处处想高人一筹,以自私自利的姿态出现,要消除本地区人民对于日本的“误解”,恐怕是难以成功的。(22)此外,从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关系史可以粗略地看出,日本是个崇尚实力的国家,国家权力是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依据。在历史上,日本无不投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以欺凌东亚国家作为提高国力的手段。20世纪初的《英日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意日《钢铁同盟》以及战败后的《日美同盟》无不如此。依靠强权以求自保的战略取向并无不当,但日本“实力说话”和“唯实力是从”的民族特性,一方面必然导致对外战略偏向美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对发展中邻国的基本态度。东亚国家会明白,在国家实力与日本相差悬殊的历史阶段,是很难与这个国家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的,更不必说“心心相印”、“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了。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战后的东盟国家一直与美国维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均有程度不一的军事合作安排。从战略安全的角度看,美国、日本与东盟之间并无重大分歧。但在经济领域方面则必然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在集体维护东亚地区和国家经济利益上,日本的立场往往令东盟疑虑乃至失望。一方面,日本以东亚或东盟为依托,在欧美国家面前争取自身利益,在面临西方的压力与挑战时寻求亚洲国家的声援和支持。在日美关系恶化的时候,“日本总能赢得地区支持以抵制美国的要求,相反,日美关系的改善则会或可能削弱日本与地区邻国的关系”。(23)另一方面,在东亚与欧美出现争执时,日本强调的是“美日同盟”或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在东南亚看来,日本的政策话语与具体行动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反差。总体上看,虽然其宣传口号十分动听,但日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或损害亚洲国家的利益。比如,日本对东盟1971年推行中立化政策并不支持,认为这对其外交战略偏向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对是否支持一个以中立化为平台的组织非常警觉”。(24)其原因是日本担心这可能对“日美同盟”构成挑战。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79年6月日本在西方七国首脑东京会议上的表现:自诩为东盟密友的日本,“不但在会议中未发挥其‘桥梁’作用,甚至在关系到东盟切身利益的有关问题上,日本也跟着西方国家与东盟唱对台戏。”(25)以自身利益为行动准则,在东、西两边下注,两边摇摆,这样太过势利的对外策略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利益,但对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则必然产生负面影响。
问题的根源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优先选择不是亚洲,而是美国。如果日本被迫在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做出支持谁的选择,那么美国将居于优先地位。(26)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东南亚实际上并不如其外交语言所宣扬的那么重要。有位日本外交官(Nakatomi Hisashi)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继续将对美关系置于优先地位。美国之后,日本应该与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维持友好关系,因为它们是对日本相当重要的邻国。再其次,日本应该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搞好关系,因为它们是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尤其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东盟国家与欧盟同等重要,因为对日本而言,它们在商业和安全方面都至关重要。”(27)由此看来,坚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就难以坚持对东盟的“特殊”关系,因为亚洲国家在维持对美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存在相互竞争的一面。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当然具有不尽相同的国家与地区利益诉求。
第四,并不现实的战略期待。日本期待东盟成为制衡中国崛起的潜在战略力量。东盟是日本东亚战略构想的重要环节,它并不讳言期待东盟能够成为制约中国的重要力量。在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南亚一直是超级大国战略遏制中国的重要地区。先是美国,后是苏联“在中国南翼保持威慑力,并据此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28)东南亚是对中国战略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国东南亚战略的底线应当是:该地区绝对不能为任何大国所支配,并成为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或包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动能。为了延续这个得来不易的“战略机遇期”,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就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在继续坚持双边主义和全球合作架构的同时,也不断创建与参与到各种地区多边主义机制之中,以力图构建有益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其中,维护中国地缘战略安全的政策举措是不得不思索和推行的重要政治议程。在中国看来,“多边主义曾经是包围崛起的中国和干涉内政的一大尝试……中国愿意支持一个由中等国家发起的非正式与灵活的安全对话机制,它不能成为中国安全利益的潜在威胁。对于中国来说,由美国或日本来主导这样的安全机制是不可接受的。”(29)日本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这一前景非常敏感,不乏失落与惊恐之心态,故常有防范之心和制衡之意。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战略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已形成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单极格局和多极化的地缘经济格局。“9·11”事件之后,美国越发明显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美国计划在东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在追求本国绝对安全的同时,相应提高了中国的战略安全风险系数。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在地缘战略安全方面,中国则面临着美国和日本防范与制衡的战略意图与动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不断竭力寻求建立广泛的国际安全阵营,牵制不断发展的中国。它利用重新定义的“日美同盟”,与对中国颇具戒心、坚持“大国崛起威胁论”的美国一道,积极拉拢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推动制约中国的国际“联盟”。在部署反导系统(TMD)、重新规划东亚军事力量、密集举办形形色色的“军演”之外,以日美为核心的“三方安全对话”、“四方倡议”等纷纷出台,亚太地区的“小北约”隐约可见。中国周边国际安全局势十分诡异。
与此同时,在提倡“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日本也在期待东盟能够成为制衡中国的战略伙伴。日本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Nishihara Masashi)对东盟就有这样的期望,他说:“对日本而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东南亚可以充当平衡中国的力量。”(30)冷战时期东西对峙的历史、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位置是日本这一战略构想的理论基础,日美与东盟国家传统的“战略”关系也是日本利用东盟制衡中国的历史依据。
总之,日本主观上有同东盟国家发展全方位密切关系的需求,但客观上受制于自身“功利性”的本性、“日美同盟”的制约、“脱亚论”的影响、东亚国际格局变动的冲击等因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日本的东盟政策有许多局限性,不利于其与东盟国家维持和发展日方所期盼的特殊关系。
三、东盟对外战略思维中的日本
经过40年的发展历程,东盟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区力量。东盟的抱负不仅仅在于它是化解内部紧张关系的载体,它还积极致力于不断增强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一致对外”的力量。继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机制相继出台后,进入新世纪的东盟也一直寻求更高的目标和更深入的制度化建设。2003年10月的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东盟协定宣言Ⅱ》(即《巴厘协定Ⅱ》)。按照该协定,东盟将在2020年之前把东南亚建设成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共同体。2005年东盟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泰国首相他信呼吁东盟提前在2015年建立经济共同体,并决定成立东盟名人小组起草《东盟宪章》,以加强东盟的法律基础,建立更为有力的机构和组织认同。2006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又责成“东盟名人小组”在2007年拿出《东盟宪章》草案,并决定于2015年之前实现东盟的三个“共同体”。2007年11月,东盟首脑新加坡会议签署了对该组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盟宪章》,为东盟迈向制度化、正式化的发展轨道奠定了法理基础。
审视东盟40年的演绎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该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内到外的几个发展特点。概而言之,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实用主义是这个组织不断获取动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法则。简言之,从其发展史可以看出东盟的几个特征:其一,东盟的发展构想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相混杂的产物,其中,在相当程度上,东盟是一个以现实主义看待世界的组织。其二,东盟是一个政治“愿景”与具体行为并不必然挂钩的组织,其主要使命是通过强调多边对话和经济发展来帮助成员国获得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其三,东盟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它不是解决、而是尽量回避国家间历史纠葛的机制。其四,东盟发展的主要动因来源于区域性历史事件或对外部影响力的反应。
东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命运与世界局势和地区国际语境密切关联。在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竭力以集体力量提高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一强烈政治愿望一直是维系这个组织的内在动能。
不可否认,东盟在“愿景”与具体行动和成效之间的确存在反差。我们不应过度强调或贬低其“团结”、“共识”或“集体行动”的程度与能力。它就是那种善于因应国际环境的“外战内行”的“松散集合体”(fragile community)。新加坡学者尖锐地指出:东盟能够存在,仅仅因为这个组织是一个维护国家安全、表达国家看法的便利载体。东盟在某些领域能够成功,那仅仅因为它可以集体面对符合成员国利益的共同安全、政治和经济问题。(31)东盟是基于“区情”的现实主义选择的产物,是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互动的结果。它不可能超越现实历史发展阶段而效仿欧盟模式,东南亚的特殊历史、传统文化必然造就“东南亚的地区主义”。
总体而言,虽然面临许多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东盟40年还是取得了不少不可否认的成就。大致来看,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内构建了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地区环境,掩盖或缓解了东盟国家间长期存在的危机与矛盾,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此外,这个组织寻找到一种适合地区特色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模式,即以“共识”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内容的“东盟方式”(ASEAN Way),为东盟发展乃至东亚地区化进程探索出了一条相对可行的地区合作之路。与地区内的成就相比,东盟在对外战略上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东盟的声誉与国际地位来源于它在处理柬埔寨问题过程中的优异表现,东盟作为一个“外交共同体”(diplomatic community)的概念从此得到广泛认可,(32)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并具有越发显著的地区影响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优异的地区组织,东盟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彰显集体行动的力量。它的“大国平衡战略”也逐渐得以完善,并运用得娴熟自如,最大限度地维护并促进了东盟地区及其成员国的利益。作为东亚两大强国之一、并与东盟有着传统友好关系的日本,理所当然是东盟对外战略议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第一,日本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系其成立之初提出的“和平、自由、中立”的外交目标演绎而来,东盟推崇“地区问题,地区解决”(regional problems,regional solutions)之理念,不希望大国插手乃至主导东南亚事务,它试图通过大国对东南亚战略地位的关注及其相互间的利益与矛盾关系,力求形成一种大国相互制衡、无一国可以支配东南亚的地区态势,最终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并最大化地争取东盟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利益。东盟“则在其中周旋和协调,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发挥主控中心作用。”(33)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所有世界上的大国或主要国际行为体都构成了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中、美、日是其最重要的平衡力量。东盟认为,在这个格局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平衡力量”。(34)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因此“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35)东盟的这一用心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就可见一斑,该论坛的主要目标是“拖住美国、扶植日本、约束和改造中国。”(36)东盟作为亚太的“一极”崛起之后,便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制衡力量,在各大国的矛盾与冲突中起到了重要的协调、牵制作用。(37)
前面提到日本期待东盟成为制衡中国的潜在战略力量,但东盟采取的是积极吸引并同等重视中、日两国的策略。为了因应东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东盟成员国需要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存在,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这当然也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大多数东盟国家看来,“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制约中国霸权野心、防止其违反海上航行自由(尤其在南中国海)的一个手段。”(38)但是,东盟并不必然成为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伙伴。东盟利用并防范中国,同样也在利用并防范日本或其他大国(包括美国)。也就是说,所有大国都是东盟“均势战略”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东南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软弱”的次级区域,很难抵御外部影响,大国常常可以轻易地渗透到这个地区。这是一个“松散的”地区,且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在外部影响力面前,它缺乏保卫自己并捍卫自主权的机制。(39)相对于外部大国,东盟的脆弱性与依赖性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外部大国具有特殊利益并为影响力而竞争的地区。”(40)基于东南亚这种地缘政治特点,单纯依靠某个大国不仅不能促进国家利益与地区战略利益,反而有可能陷入大国之间的激烈角逐之中。比如,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的争斗以及前苏联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激烈较量,带来的不是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是连绵不断的地区冲突。
此外,东盟不可能成为日本制衡中国战略伙伴的另一个原因与这个组织没有形成一套共同对外战略不无关系。不同的地缘战略环境,不同的历史经历和记忆,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政体,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不同的社会种族差异,以及国家正式建立的不同历史背景,都是东盟国家形成不同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虽然东盟强调一致对外,但东盟十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东盟十个成员国在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必然反映在外交上以及对华政策上。从逻辑上看,它们都以本国利益和本国需要为基本出发点,来制定本国的对华政策。各国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往往具有各自更为实际、更为具体的内容。东盟国家在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上自然也有不同的考虑,因此它们共同因应中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们“一直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因而削弱了东盟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41)泰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马来西亚1989年后的对华“接纳”政策,新加坡与中国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中缅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东盟难以有可信的集体力量直面中国。
因此,对于同在东亚的两大巨人中国和日本,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东盟不可能将战略筹码集中于其中一国,而是充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与竞争,多方下注,以获取最大化的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对于东盟而言,“选择其中一个的‘一边倒’绝不是一件轻松舒坦的事情”。(42)东亚两大巨人中国和日本参与到“10+3”的机制中,客观上为东盟的地区力量平衡战略提供了重要机遇。由此观之,日本利用东盟平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委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说是政治现实制约了其政治意愿。
第二,日本是东盟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对后者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东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援助国,就雄辩地说明了双方密切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主义”是东盟国家长期坚持的重要国家战略。这对于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极为关键的基础与前提。“国家弹性”(national resilience)和“地区弹性”(regional resilience)概念是东盟所倡导的重要原则,虽然它主要是“为了维护政权安全,而不是公民和领土安全,”(43)但这是一个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其逻辑是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稳定、政权稳固、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而所有东盟国家的“弹性”累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地区安全保障。强调对外开放、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便利和机遇,一直是东盟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东盟从对日经济关系中受益匪浅,相互间的互补性也比较明显。密切的经济关系构成了日本—东盟关系的强大支撑。
第三,东盟认可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对日本试图以东盟为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垫脚石”、削弱东盟地区主导权的政治意图保持高度警惕。从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史看,柬埔寨问题是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试金石。一方面,日本聚焦于国家利益而忽视地区利益的行为导致双边关系迅速降温;另一方面,东盟对日本企图发挥地区领导作用的行为毫不犹豫地加以抵制。围绕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不仅深化了日本和东盟的相互认识,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双边关系的发展。
1978年12月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之后,日本终止了每年140亿日元的对越经济援助项目。此后,日本一直认同东盟的柬埔寨政策,在1979年之后的年度联合国大会上,日本一直支持东盟提交的决议案,呼吁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其军队。在柬埔寨问题上与东盟站在一起的同时,日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东盟、中国的四边阵营里,丧失了一些自己的灵活性与外交主动权。(44)虽然日本完全支持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柬埔寨和平进程中,日本开始寻求发挥有效的作用,一直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旨在解决冲突的政治行动。1987年底,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召开前,日本举行了一次“茶话会”,试图撮合在柬埔寨问题上对立的四方与美国、苏联和中国进行非正式会谈。东盟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其原因是日本企图在东盟与越南之间搞“等距离外交”,日本企业在越南设立办事处,准备投资,占领越南市场,获取超额经济利益。日本这种两边下注的功利性外交手法当然不利于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且鼓励了越南的侵略行为,也违背了日本对东盟的政治承诺,因而遭到东盟的不满与抗议。东盟的抗议对日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外交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其“自信心可能遭到了沉重打击”(45)。从此之后,东盟似乎对只看重自身利益而不顾地区大局的日本有所顾忌,并对日本产生了不信任。有鉴于此,东盟一直没有接受日本“调停者”或“仲裁者”的国际地位。结果是日本在东南亚进行大国外交的尝试未能得逞,“不得不维持低姿态的东南亚外交”(46)。日本在东南亚寻求地区大国领导地位的尝试因此遭到重大挫折。这一方面是日本“经济动物”本性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日本树立大国威望和东盟维护地区主导权之间相互冲突紧密相关。这也对冷战后日本—东盟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趋向有可能成为未来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付诸行动,作为东盟—日本关系的基石——“福田主义”的精神实质逐渐为日本人所抛弃。东盟—日本关系未来的发展因此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冷战结束后,尤其小泉治下的日本推行极端亲美的对外政策,试图借助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及其政治善意顺利实现自己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反恐特别法案”、派兵海外、部署反导系统(TMD)等举措都反映了日本对美“一边倒”的战略思路。1997年,桥本首相借东盟成立30周年的良机发表政策演说,向内外宣布,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誓言“不成为军事大国”的“福田主义”的使命已经完成,日本将抛弃历史包袱,并在美国的允许下,以大国姿态在亚太地区的政治乃至军事方面大显身手,扮演重大角色。这就是所谓“桥本主义”的精神实质。(47)虽然日本—东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关系,东盟也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但是东盟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一个背弃“福田主义”精神实质的日本?在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下的罪行不知悔改的情况下,同样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国家不可能不对重新军事化的日本心怀疑虑。此外,影响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另外一个前提是日美同盟,这个同盟关系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制约作用是东盟—日本关系顺利发展的基本背景。设若日本摆脱了这个束缚,军事大国的日本能够让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东亚国家放心吗?毕竟“日美同盟”架构下的东盟—日本关系是一回事,没有这个架构制约则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第五,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与东盟并不协调,有时甚至构成这一进程中的障碍。东亚地区合作是冷战后东盟寻求发展动力与突破并扩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日本是本地区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从逻辑上看它应当有能力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推动者乃至“领导者”。但事实上它在这个进程中是谨慎和被动的,这同时也大大延迟了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确,日本一直“不是东亚地区主义的积极支持者”。(48)其原因是东亚地区主义“将有可能影响日美同盟这一日本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49)美国要求日本为其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服务,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这是因为:日本正在寻求新的地区和全球作用;日本有能力为地区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作为一个富裕但脆弱的岛国,日本是当前政治、经济和安全安排的最大得益者;在日美安保协定的架构内,日本的地区行动不会激起邻国的不安和忧虑。(50)日本则期待依靠美国不仅可以稳定西方市场、获取自然资源,而且可以共同对抗中国,乃至实现自己政治大国的梦想。为了迎合和追随美国,日本曾经拒绝签署东南亚无核区(SEANWFZ)条约,因为美国担心东南亚无核区条约会限制其海军在东南亚水域自由通行。日本同样拒绝了东亚经济论坛(EAEC)的倡议,因为日本政府反对在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排挤”美国。与此相对,日美在跨太平洋的亚太地区合作上则步调一致,支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且是该组织的主要推动者。(51)在日本人眼里,东亚地区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仅仅是其与美同盟关系的一个补充,以及改善中韩关系的一个工具。(52)
在历史上,日本曾经是一个积极倡导地区合作的国家,但是其地区构想的前提是必须涵盖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泛太平洋”合作,在东、西间游走,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同时,尽量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比如大平首相推出“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构想就有“避免以日本的地区与全球责任为代价而与东南亚建立密切关系”(53)的意图。
冷战结束后,日本—东盟关系增添了不断强大的中国这个重要元素。中国积极参与到地区合作的进程之中,一方面直接呼应了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成为推动东盟继续合作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间接冲击了日本想象中的地区领导地位,压缩了日本在东南亚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为了竭力维护这个日本人心目中的战略“后院”,它不得不随中国地区合作的“节拍”和动作而反应。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CAFTA)和政治合作不断深化之时,为了在东南亚巩固和争取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力争有利态势,近年来日本重新审视了其相对消极与谨慎的地区合作战略,加速了与东盟政治经济合作的步伐。2003年10月,东盟和日本在印尼的巴厘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后,2003年12月,日本也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还签署了“面向新世纪的日本与东盟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此外,日本在双边主义行动上也有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在继续保护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的前提下,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等东盟国家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推动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弥补了地区化进展缓慢的不足,而且具有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是更好地管理地区内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经济关系的手段。相互依赖导致各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经济挑战并将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这就要求国家间有建立合作机制的必要,以更有效率地管制这样的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所有的国际经济协定最终服从于战略伙伴所共享的潜在安全目标。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巩固和推进与“友好”国家的战略安全关系。日本最近热衷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策略固然有经济合作的考虑,但主要动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竞争性双边主义(competitive bilateralism)思维的产物,它之所以提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积极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提议设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对抗性战略反应”(strategic counter-reaction)(54)。由此看来,“中国因素”不仅有利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具体运用,而且有利于促进东盟的地区与国家利益。中日竞争的战略态势客观上为东盟提供了相对更大的国际行动空间,获得相对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虽然东盟的能力遭到质疑,且有许多操作与发展上的局限性,甚至有人认为它“已经轻易地丧失了其凝聚力和发展方向”,东盟地区论坛(ARF)显然也“已经不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了”。(55)但是,东盟倡导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的策略是成功的,它充分利用中日两国的矛盾及其在东亚地区中的相互竞争,不仅由此争取到了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国际地位,而且在竞相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潮流中大大受益。
总之,自成立以后,尤其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取得了不少值得自豪的内、外成就,其“大国平衡战略”是基于国际现实的实用、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日本的关系也在这个战略架构下不断演进,对东亚、东南亚的地区、国家利益也不无益处。在这个框架下,日本—东盟关系从冷战前相对密切和特殊的关系样式,伴随着东亚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而逐步演进到一种平衡性与互动性更强的双边关系。
四、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
当前,东亚国际格局正处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似乎并不同调。在地缘经济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地缘政治安全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一些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动向。第二,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似乎是东盟的扩展和“放大”,依照“东盟方式”缓步推进,与此同时,也折射出有关各方对地缘战略安全的不同考虑;第三,地区多边主义和国家间的双边主义并行不悖,后者成为前者的重要补充。东亚地区合作是该区域诸国促进地区内国家间关系,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展缓慢以及经济区域化的大趋势下维护地区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地区化进程受制于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双边主义成为东亚国家参与东亚经济与战略安全格局构建的基本策略。东亚国家与主要大国积极使用“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工具,在经济合作乃至战略安全上调控国家间关系。这样的东亚国际格局将界定日本—东盟关系现在和未来的走向。
中美关系事实上是构建东亚国际格局最重要的关系结构。在战略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力量,其战略思想必然是竭力维持这样的“现状”。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东亚主要战略盟友日本视发展中的中国为其潜在竞争对手,在继续依托战略双边同盟机制的同时,在战略安全方面积极构筑战略牵制与防范中国的国际“联盟”。中美(日)之间的战略思维与行动事实上决定了东盟乃至东亚的国际语境,某种程度上支配了该地区合作与竞争的态势,比如,东盟地区论坛实际上由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所主导,那就是中美关系。(56)这样的国际格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维持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对当前东亚关系现状构成严重挑战的国际因素并不特别凸显。这是因为该现状符合美国在东亚享有“霸权”的事实,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周边”的国家战略,同时有利于东盟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目标及其“大国平衡战略”的运作。因此,对东盟来说,虽然可以从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中得“渔翁之利”,但战略风险也是其“不可承受之重”。故“既合作、又竞争”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大国关系最为符合东盟的现实与长远利益。在东亚大国关系结构中,遏制中国的战略思维有恶化地区局势、导致地区分裂的可能性,最终对东盟产生消极影响,因而东盟认为“日本不应成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干扰因素,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对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57)对东亚国际安全格局和中国国际作用的不同认知为日本—东盟战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依据,也为东盟的“均势战略”设置了政策底线。利用和主导东盟的任何战略企图对于日本乃至中国都是不切实际的政治想象,“中立”的东盟可能是比较现实和可以接受的战略态势。此外,如果对东盟的政策目标显得太过张扬与急切,可能招致东盟被大国支配的敏感心态,而激起“一致对外”的排斥性反应。对于当今中国之东盟战略,无论在经济合作还是政治外交领域,“被动接受”合作要远比“主动要求”加强关系更为明智和有效。日本在冷战后期的“傲慢自大”激起东盟的强烈反应就是“前车之鉴”。
影响日本—东盟关系发展趋向的因素复杂多样,与前面所述诸方面及其演进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内、国际因素之中,有三个可以确定的因素对于我们审视未来日本—东盟关系的演绎既不可或缺,又影响极大,那就是中国的不断崛起、日美同盟的延续以及东盟的发展——这三大效应将对日本—东盟关系的演进产生重大影响并决定其可能的走向。
中国崛起的冲击效应。长远来看,中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增强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现象。为了越发全球化的国家利益,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中,这对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也会与日本形成相互竞争的基本态势。随着中国—东盟经济政治合作的不断深化,日本在东南亚的传统经济与政治地位必然受到较大冲击,从长期来看,其发展空间的相对收缩是难以避免的。
日美同盟的制约效应。日美同盟的延续是不以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外交选择,它对日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及其东盟政策是一大牵制。这也是东盟国家在现阶段认可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的依据和条件。日美同盟将继续从积极的(压制日本可能走向军事大国乃至军事冒险)和消极的(制约日本自主的东盟政策)两个方面持续发挥其作用。
东盟发展的平衡效应。虽然受到地区多样性、差异性和地区机制的非制度化、非正式化的制约,东南亚十国的“东盟化”也给这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地区化进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东盟的存在与发展有益于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和共同的地区利益,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尽管还会有曲折,东盟的深入发展还是可以期待的。东盟的进一步发展将提高其对外因应能力,大国在东南亚的均势会存在下去,因为这符合东盟与各大国的利益。日本与东盟关系将基于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借助、相互依托、相互影响,平稳、正常地发展下去。
概而言之,在这三大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朝着平衡性与互动性更突出的方向演进是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
注释:
①〔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②高伟浓、胡爱清:《论战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认识的演变》,《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12期。
③Lam Peng Er,"Perceiving Japan: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in Derek da Cunha,ed.,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0,p.134.
④卓南生:《日本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⑤Donald G.McCloud,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a Region,Westview Press,1986,p.181.
⑥1977年8月18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的政策演说中,提出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三大支柱,即:(1)日本不做军事大国;(2)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关系;(3)以平等合作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的和平以及繁荣做出贡献。
⑦Donald G.McCloud,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a Region,p.182.
⑧日本首相竹下登1989年5月5日在雅加达发表的《日本与东盟:共同思考,共同前进》政策演说,见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6/1,July,1989,p.133.
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1977年8月18日在马尼拉发表的政策演说,见The Japan Time Weekly,27 August,1977.
⑩裴默农:《日本—东盟的“特殊关系”与日本的“太平洋圈”发展战略》,《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
(11)李义芳:《从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看东盟战略地位增强》,《龙岩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2)Anny Wong,"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ultivation of ASEAN Eli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2,No.4,1991,p.292.
(13)Rodolfo C.Severono,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SEAN Community:Insights from the Former ASEAN Secretary-General,Singapore:ISEAS,2006,p.307.
(14)1974年日本开始发起了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活动,每年由来自两方300到350位18至30岁的年轻人乘坐“日之丸”号轮船,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港口停泊,通过游历、访问和家庭小住等形式理解对方的文化,增进相互理解,建立友谊。1980年,日本设立了每年提供100万美元的“东盟青年学术基金”项目,为东盟国家的学生提供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机会。1984年,中曾根首相设立了“面向21世纪的友好项目”,邀请东盟国家的年轻人前去日本进行讲学、学术访问、观光旅行、入户小住并与日本的年轻人交流。到2003年,共计有26000人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活动。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的交流计划有:确定2003年为“日本东盟交流年”,此后三年里日本提供总额15亿美元、包括4万人的交流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在此后5年里接待1万位东盟国家的年轻人来访,并继续执行“日本东盟青年友好项目”等。参见:Rodolfo C.Severono,Southeast Asia In Search of ASEAN Community:Insights from the Former ASEAN Secretary-General,pp.295-306.
(15)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112.
(16)Lam Peng Er,"Perceiving Japan: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in Derek da Cunha,ed.,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0,p.135.
(17)Lam Peng Er,"Perceiving Japan: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p.151.
(18)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日文版),东京讲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9)Lam Peng Er,"Perceiving Japan: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p.143.
(20)Pekka Korhonen,Japan and Asia Pacific Integration:Pacific Romances 1968-1996,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71.
(21)卓南生:《日本外交》,第89页。
(22)同上,第87页。
(23)S.Javed Maswood,"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in S.Javed Maswood,ed.,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6.
(24)Sueo Sudo,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 East Asia: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34.
(25)卓南生:《日本外交》,第108页。
(26)Lam Peng Er,"Perceiving Japan: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p.144.
(27)Hisashi Nakatomi,"A Note On The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in Asia-Pacific Review (Hanoi),No.1,December 1993.
(28)Donald G.McCloud,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a Region,Westview Press,1986,p.179.
(29)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p.116-117.
(30)Nishihara Masashi,"Japa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ASEAN," in ASEAN-Japan Cooperation:A Foundation for East Asian Community,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3,p.157.
(31)Andrew T.H.Tan,Southeast Asia: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2006,p.6.
(32)Jürgen Haacke,"Reg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ASEAN,ARF,SCO and KEDO," in Stephen Hoadley and Jürgen Rüland,ed.,Asian Security Reassessed,Singapore:ISEAS,2006,p.130.
(33)张锡镇:《东盟的大国均势战略》,《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2期。
(34)Michael Leifer,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London:Routledge,2000,p.105.
(35)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版》2003年第3期。
(36)喻常森:《东盟地区论坛的目标及大国的立场》,《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
(37)张晓玉:《东盟对亚太大国关系的制衡》,《当代亚太》1995年第1期。
(38)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112.
(39)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SEAS,2000,p.2.
(40)Wayne Bert,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A Changing of the Guar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143.
(41)Andrew T.H.Tan,Southeast Asia: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2006,Introduction.
(42)Victor Sumsky,"ASEAN and East Asia," in Gennady Chufrin,ed.,East Asia Betwee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Singapore:ISEAS,2006,p.60.
(43)Craig A.Snyder,"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in Craig A.Snyder,ed.,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London:Deakin University,1999,p.113.
(44)Kavi Chongkittavorn,"Japan and Southeast Asia:Searching for Acceptable Role," in Harry H.Kendall & Clara Jpewono,ed.,Japan,ASEAN,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1,p.176.
(45)Ibid.,p.179.
(46)Ibid.,p.175.
(47)卓南生:《日本外交》,第311页。
(48)S.Javed Maswood,"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ra," in S.Javed Maswood,ed.,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9.
(49)Ibid.
(50)David Arase,"U.S.and ASEAN Perceptions of Japan's Role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in Harry H.Kendall & Clara Jpewono,ed.,Japan,ASEAN,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1,pp.265-266.
(51)S.Javed Maswood,"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in S.Javed Maswood,ed.,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p.15.
(52)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116.
(53)Lee Poh Ping,"Japan's Role in the Pacific Region in the 1980's," in K.S.Nathan & M.Pathmanathan,ed.,Trilateralism in Asia: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U.S.-Japan-ASEAN Relations,Kuala Lumpur:Antara Book Company,1986,p.40.
(54)Christopher M.Dent,New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51-52.
(55)Andrew T.H.Tan,Southeast Asia: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2006,pp.6-7.
(56)Ralf Emmer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123.
(57)Michael Leifer,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London:Routledge,2000,p.127.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东盟外长会议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