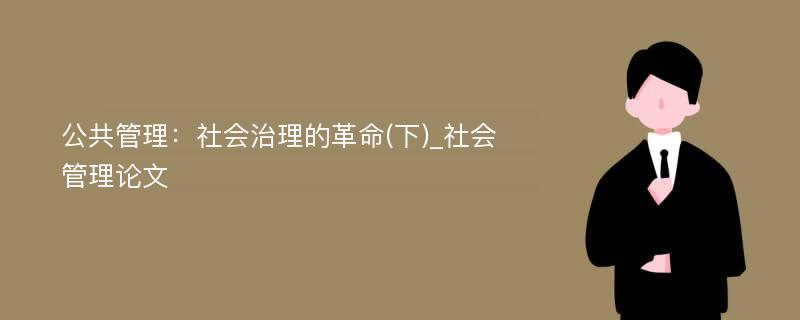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管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公共管理是一种职业活动
人的职业活动,以及在职业活动中生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同领域的分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同领域的分离是以分工的形式出现的,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活动的分化造成了职业活动的专门化。到了晚近,职业活动已经不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扩大到了生产领域之外的许多领域,几乎遍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人们在职业活动方面的区别,也不再仅限于活动意义上的“分工”,而是职业活动主体意义上的“分群”。社会生产的领域有分化、重组、融合的双向运动趋势,而社会生活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领域分离的单向运动。
这种历史发展趋势为现代社会的职业关系蒙上了新的面纱,属于启蒙时期及稍后的一批经典作家们未加深入认识的特殊社会关系。因为,在这些经典作家的研究视域中,社会运动的基本要素是分工,即使对于社会分群,也总是从分工中来加以理解。然而,现代社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一些社会生活的领域,甚至社会生产的部门中,存在着不是由于分工原因造成的人的分群,出现了不仅不是分工导致人的分群,反而恰恰是人的分群造就了分工的社会现象。一个人有资格从事某项职业活动,是因为他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有着同样能力和素质的许多人无法承担他所具有的职业角色,是因为那些人不属于他所在的社会群体。
这样一来,对人们的职业关系不仅需要从分工的角度加以理解,而且还需要从社会分群的现实中来加以把握。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的职业关系,往往是这种关系的传统形式的延续,而那些需要从社会分群的角度来把握的职业关系,或者是一种全新的职业关系和职业行为体系,或者是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革命性变革的从而具有了新质的职业关系。需要借助于社会分群来加以把握的职业关系已经很难再为传统的所谓“科学理解”的思维范式所包容了,更不应当按照传统的“科学理解”来加以建构了。比如,对于那些从分工的角度作出科学认识的职业关系,是可以根据认识所达到的高度来加以重新建构的。然而,对于那些从分工的角度无法作出准确把握的关系,如果还以分工为基础的科学思维范式进行建构的话,就会破坏这些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导致这些关系的畸形化。
公共管理会有着分工的遗迹,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那些人们之间关系的结构形式,必然会在公共管理以及人类未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保留下来。所以,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会满足科学化技术化的原理。其实,公共管理的独特根据不是分工而是分群。或者说,公共管理得以产生的时代已经不是一个需要通过分工来理解社会分群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通过社会分群来理解分工的时代。公共管理的对象有些是由于分工造成的社会分群,而更多的则是由于非分工的因素而造成的分群。即使是由于分工造成的社会分群,在进入公共管理的视域时,分工的因素也并不被着意地加以考虑。公共管理主体内部存在着分工,但它在社会整体中是首先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而存在的,它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需要得到管理对象的合作和参与,它在通过管理而实现对管理对象的服务时,需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具体性。
也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不再主要是由人的分工所决定,而是主要由人的分群所决定。根据社会发展的这一新特征,职业概念与工业社会早期职业概念的内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不再像工业社会早期那样,总是与行业相重合,而是与行业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同一行业中有着不同的群体,不同行业中又有着同类甚至同质的群体。不同行业中的同类群体在社会角色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地位和特征;同一行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角色上的相异性却又是十分明显的。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或交叉或离异或重合的多样性,使职业的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传统的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另一种是现代社会日益生成的社会分群前提下的职业。前者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使职业界线越来越模糊;后者则因社会的进步而使职业界线越来越清晰,个人要逾越这种职业界线是极其困难的。职业界线模糊,意味着职业对人的社会角色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职业界线清晰和不可逾越,则意味着对人的社会角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无论在结构上、在制度安排中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原则才能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和职务上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所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会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法律精神。对于公共管理行为而言,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是作为公共管理服务精神和原则的支持力量而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来的。所以,在具体实践中的表现是:权力和法律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条件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就是服务精神和原则能够得以实现。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是以服务精神和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从而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在现代社会,职业活动是人的社会生命获得的主要途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基本途径。人通过选择职业而选择了他的社会生命的内容。所以,人一旦进入某一职业,作为某一职业群体中的一员,他在此之前通过接受教育等途径所作出的职业准备就转化为现实的职业行动,他在职业准备过程中还处于蛰伏状态的职业意识、职业观念以及职业价值等要素,就会由于他的职业角色的获得而显现出来,成为引导他的职业活动的内在机制。选择一种职业,也就意味着同时获得这一职业中的整个价值体系,特别是在现代职业岗位较为开放的条件下,拒绝接受某一职业价值体系的人是有权利并有能力拒绝这一职业的。根据这一原理,我们把公共管理者看作为自愿接受公共管理价值体系的从业者。既然公共管理是一个德制体系,那么,公共管理者也就是把德制内化为自我行为标准的从业者,德制中所贯穿着的伦理精神,也就是他的灵魂。
公共管理职业与其他职业活动不同,不是那种部分占有从业者生命活动的职业,它要求从业者在选择这一职业的同时,就把自身完全融入到职业生活中去。当然,公共管理者也同样是父亲、丈夫或妻子等,但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在他从业于公共管理的时候,都是这种职业活动的支持力量或辅佐因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选择了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之后,他依然会扮演着其他社会角色,但他的公共管理职业角色是第一位的,他的其他角色都需从属于这一角色。即使这些角色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也必须是无冲突的。如果发生冲突,维护公共管理角色的纯洁性,就会成为首要的选择。否则,他就有着与职业性质相离异的倾向,就会产生他与职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职业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在一切职业活动中,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性特征最为典型。如果说有些职业活动只是在间接的意义上属于社会性的活动,那么公共管理活动则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社会性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完全的社会性活动。公共管理活动的任何一项内容,都是社会性的。当然,作为一种职业活动,包含着公共管理者个人选择生命之存在的动因。也就是说,这种职业活动也和其他职业活动一样,需要满足从业者个人生活方面的要求,在更高的意义上,需要满足从业者的个性发展方面的要求。但是,公共管理这种职业活动的特征决定了它比任何一种职业都更加直接地突出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公共管理者职业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把对社会责任义务的承当放在首要的地位。
六、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其职业活动应当怎样定位呢?是一个对于理解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且对于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的确立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19世纪,当思想家们从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思考而转向对国家官僚的认识时,需要对官僚的性质给以回答。黑格尔根据其三段论的逻辑需要把官僚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中介”,更多的思想家根据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现象而把官僚比喻成“仆人”,即称作为“公仆”。马克思也接受了这个比喻。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频繁地使用“社会公仆”的概念,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避免堕入“旧官僚”发生蜕变的“异化”逻辑。
需要指出,“主”“仆”现象是农业社会等级体系的一种次生现象,虽然是次生现象却又普遍存在。进入工业社会,这种现象作为历史陈迹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还是存在的。但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原则以及法律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出现,使“主”“仆”现象丧失了制度基础。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官僚作为社会治理者所扮演的是职业角色。对官僚而言,他所从事的社会治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无所谓“主”“仆”的问题。在这里,使用“主”“仆”的概念,只是一种比喻。所以,回顾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并认识官僚的性质和功能时,我们认为19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虽然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发现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趋势,以至于所提出的各种批判性的或建设性的意见都很难在规范官僚及其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官僚职业化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历史现象,但着力于从职业角度认识官僚的理论依然显得极其薄弱,即使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在官僚制的理想模式设计中,对于官僚职业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就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而言,社会治理者的职业化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展中的一项积极成就。公共管理是以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得的这项积极成就为起点来进行公共管理者队伍的建设和规范的,对与公共管理者行为相关的一切问题的认识和把握,都需要从公共管理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者的角度出发,需要避免从“社会主人”或“社会公仆”的思维路径出发来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当然,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者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人,权力关系自上而下的作用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社会仆人的姿态出现。因为,权力关系本身就必然强化和进一步造就社会等级,权力执掌者与权力相对人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平等关系。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关系的介入使人们在政治上拥有了平等的权利,但社会治理体系自身的权力关系的必要性,依然决定了社会治理活动中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法律关系对于限制和矫正不平等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由权力关系再造出来的不平等并不能得到根本消除。以至于政治上的平等主张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在人们之间的实际不平等面前,政治平等的理论总是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在“社会主人”还是“社会公仆”的问题上,仅仅在理论上实现了简单的颠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理论如果希望在现实中切实地发挥作用,惟有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而在“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之间所做出的理论上的简单颠倒,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所以,它永远只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念而存在,却不能切实地规范社会治理者的行为选择。
从职业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治理者的性质和功能就不同了。它把社会治理活动看作一种职业活动,相应地,也就把从事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人看作职业活动的从业者,他们执掌和行使权力的事实也不会与政治上的平等原则发生冲突。从而能够使他们完全放弃任何特权意识,进而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普遍的服务精神。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合作的前提,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更是如此。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表面看来也有着合作的现象,而在实际上,任何合作都只是假象。因为,在权力关系的等级差别基础上,相对较高一层级上的社会治理者总会有意无意地拥有盛气凌人、官高位重的官架子,相对较低一层级上的社会治理者也必然会染上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作风,治理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虚伪和尔虞我诈,根本不存在实质性的尊重、谦让、协商、合作。所以,以合作形式出现的治理活动的一致性行为,除了顺从、服从之外,就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沆瀣一气。
公共管理在职业的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平等关系。虽然在治理体系结构上还存在着层级,但公共管理者之间并不因治理结构上的层级差别而造成职业人格上的不平等。在公共管理这一社会治理体系中,他们都以公共管理这一职业活动的从业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是一个相互通过他人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关系,只有以礼貌谦让、尊重互助的形式开展真诚的合作,才能保证每一公共管理目标的真正实现。当然,在公共管理者之间,也会存在着个体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开展公共管理活动的知识和技能上的差别,他们在公共管理体系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也主要是由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差别所决定的,在享有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方面,他们有着同等的资格。
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职业活动中,公共管理是一项最为特殊的职业,是一项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职业。管理型的社会治理也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它把一切治理制度的设置和治理行为的选择,都放置在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统摄之下,特别是把政府中的行政也称作为公共行政了。然而,事实上却客观地存在着政府的自利问题,存在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要求或追求等问题。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既不从属于个人的自利目的,也不以所在组织、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在本质上是“公共的”,特别是它的理想形态,从目的到行为到工具到组织构成到奉行的原则等等,都凸显出公共性质。
从职业活动的重心来看,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是不同的。统治型社会治理要求官吏以“治人”为中心,不仅统治是以对人的统治为核心的,而且整个社会秩序的获得和社会的发展,都以对人的治理状况为转移;管理型社会治理要求官员、公务员以“治事”为中心,一切以事为转移,对事不对人,事中求是,不受人情干扰。在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中,则是以“治利”为中心的,公共管理者考虑的重心既不是“人”也不是“事”,而是透过“人”和“事”或通过“人”或“事”去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种职业活动都会有着相应的职业规范。职业规范是一个系统,其中包括技术性规范、制度规范和以文化或职业习惯构成的文化规范等。一般说来,在应然的意义上,私人领域中的职业活动技术性规范偏重,文化规范稍弱;而公共领域中的职业活动,文化规范应强一些,技术性规范的重要性相形较弱一些。然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领域中发展出了超强的技术性规范体系,反而用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冲击了公共领域中的文化规范。这是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治理职业活动不应有的变异,公共管理职业活动必须矫正这一变异。公共管理的矫正方案并不是片面地去强化文化规范,而是把以往作为文化规范构成要素的道德规范厘析出来,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建构起系统的道德化制度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虽然以道德为基础,却同时兼容了以往技术性规范的全部成就。所以,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技术规范和文化规范以制度的形式统一起来,成为完整的、有机的职业规范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社会治理中的或者“重文化轻技术”或者“重技术轻文化”的制度规范模式。
但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职业活动的领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职业活动将会成为最能自由自主和充分展现自己的“场所”。在社会治理这一职业活动领域中,管理型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官僚制泯灭了治理者个人的个性,以至于社会治理中的人的一切积极因素都会逐渐地退隐。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不同,它是创造性的社会治理活动,这种创造性根源于公共管理制度安排所赋予公共管理者的充分自主性。就公共管理者而言,他用创新理念武装自己,创造性地开展公共管理活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公共管理制度体系赋予他的自主性,充分展现他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创造力,只要一心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他就有着充分的自由和自主。
结语:需要启蒙
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走向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法治走向德治以及用德制来取代法制,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无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变革,这种革命性的变革运动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正如农业文明的出现和工业文明的出现一样,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变革运动。每一次伟大的变革运动都有一次启蒙运动与之相伴。我们看到,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是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18世纪”这个概念所意味着的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现在,人类正处在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也同样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适逢一个启蒙的时代,应当担负起新的启蒙的责任和义务。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早期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和从属于美的原则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杂居,社会出现了等级化,人们之间的等级化关系所要接受的是权力的直接控制,同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要求道德的广泛介入。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化造就的社会治理模式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入到了科学结构之中,在这种科学结构的基础上,整个社会以法制的形式出现。公共管理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以道德为轴心的管理模式,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也要求担负着这种管理活动的社会治理者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所以,需要通过一场伦理启蒙来为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确立行为原则和规范。
发育得比较典型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权制体系是由先秦思想家作出的设计,正是他们,确立了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发展得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由18世纪启蒙思想家作出的设计,正是这一批“思想巨人”,点燃了“法的精神”这一普照之光。在今天,我们所肩负的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的任务,我们所要追寻的,可能是一种适应于后工业社会制度安排需要的“伦理精神”。从“等级观念”的确立到“法的精神”的发现再到“伦理精神”的建构,就是人类的启蒙之路,它所描绘出来的是一条人类文明化的历史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