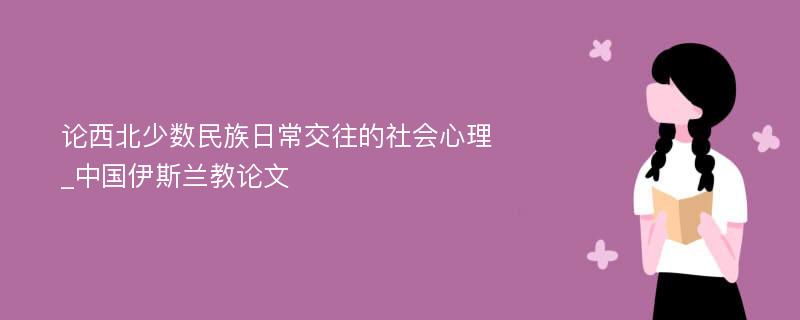
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心态论文,日常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9)05-0053-06
举凡民族共同体所涉及的大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变化,小至每天的见面问候、礼尚往来、工作学习尽被囊括在各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范围内。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是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繁衍的基础,是民族关系的连续性、多样性、丰富性和互动性的最为重要的内容。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深刻含义、独特面貌和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认识和理解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特殊性,也有利于拓展、深化、开辟民族关系研究的领域,体现“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1]的学术理念。
一、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诠释
日常交往指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最经常、最频繁的交往关系,其特点是“视角互易性”为最常见的交往,“变形的自我”为这种交往的主题。“视角互易性”、“变形的自我”均为美国社会学家舒茨所提出。前者的意思是面对面的反复重复的交往,后者的意思是在交往中互相认识和理解。面对面的交往构成了人与人的最基本、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关系。互相认识和理解是自我深层地融入社会和进一步展开日常交往的过程。
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其一,日常生活就是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尼丝·赫勒是代表,她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的要素的集合。”在赫勒看来,个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个人和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2]赫勒认为:日常交往的形式有四种:偶然随机交往、习惯性交往、依恋、有组织的交往。其二,日常生活就是我们之外的客观的社会现实。现象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伯格和勒克曼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认为,日常生活是由语言维持的秩序井然的实在界[3]254。其三,日常交往就是交往行动。交往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就是人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是作为一种交往的行动而存在,交往行动包括支配这个行动的动机、兴趣和由此表现出来的行动类型。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交往行动的兴趣、交往行动的方式、交往行动的类型,包括目的性行动、循规性行动、戏剧性行动、沟通性行动[3]317-318。其四,日常生活就是对社会的适应。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唯一的目就是追求幸福,每个人只有在实现他人的幸福中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所以,每个人只有适应社会的现实,遵循社会的规范,才能得到幸福,否则只能得到痛苦。斯宾塞写到:“他过去,现在,并将长时处于适应过程中,对于人类可完善的信念,只不过是人类将通过这一过程最终成为完全适应其生活方式的信念。”[4]27其五,日常生活就是精神对现实的态度。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摩尔认为精神对生活有三种态度,日常生活就是对实在所采取的态度。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说:“从康德以来,人们习惯于断言:认识、意志与感觉是精神对实在的三种基本态度。它们是经验的三种不同方式,其中每一种都告诉我们一种样式,可以用来思索实在。”[5]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定义的五种观点的共同点可以表述为日常生活就是社会的互动、沟通、交换,就是各种共同体、各类人群互相适应、互相依赖的循环往复的认识理解的深化过程。
“心态”一词17世纪就开始出现在英国。英国为什么最先出现“心态”一词,是有其必然性的原因的。根据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的看法,由于当时英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以清教的价值观作为衡量对错、是非、善恶的标准,造成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默顿认为:“清教主要是明显地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宗教运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作为测量不同社会运动价值的杠杆。”[6]当时的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清教的作用大到连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都可以改变。19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所创立的心态史学将社会心态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确立下来,以社会心态表示一个时期普遍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主流习俗,以概括和反映法国社会新出现的文化共同现象。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多把社会心态等同于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趋势。真正开始心态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在1918年对波兰移民的研究。在我国,对社会心态的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个。王雅君认为:“社会心态是某一社会时期社会群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心民气或者社情民意,简单说就是指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意见、态度或情趣,因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阶层的不同产生差异。”[7]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社会共识、社会情趣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8]我国学者对社会心态的表述可以概括为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提出的“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一个社会里普遍存在的为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意识,是社会共有的思想感情、感觉感受。综合中外关于社会心态的观点,社会心态可以表述为社会共同体的心理共识,是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符号体系的产物。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指西北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里进行交往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是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的统一,也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个人心态与族群心态的统一、文化心态与历史心态的统一,同时还是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心态的统一,是系统化、功能化和有机化的心理状态。社会心态包括三个要件:认知、感情、行为。认知就是对日常交往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的理解和把握,主要指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感情投入对待和处理日常交往。西北少数民族认知的最大特点,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直觉思维与情感思维的统一、社会的自我与民族宗教自我的统一。西北少数民族的认知通常以民族宗教的视角、以直觉直观的感受分析判断对待日常交往的意义和价值。认知所产生的是对民族共同体的维护、巩固和加强的思想观念。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是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认知感情的最大特点和基本表现形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则是西北少数民族的认知行为的最大特点和基本表现形式。
二、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最鲜明的特色是民族性与宗教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这三个特色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在内容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习俗底蕴。
1.民族性与宗教性心态的结合。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人种、性格、外貌、穿着打扮等外在的可以辨认的方面,而且表现在心理、精神、气质等内在方面,特别是表现在由历史和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所形成的独特的认知模式方面。这个认知模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以宗教为触角认识和感受客观世界,回答和解读客观世界提出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西北的回、维、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儿、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西北的藏、蒙、土、裕固、锡伯等5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强调“认主归真”,“真”在伊斯兰教里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个善不仅体现在对真主的信仰上必须坚定不移,纯洁无瑕,而且要把真主诸多的完美品德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对于真主的诸多美德,《古兰经》有很多表述,主要是强调真、善、美的结合,其基本点是以坚强的意志履行对真主的责任,以广博的知识认识真主的全能,以优良的品性与主合一。藏传佛教强调佛、法、僧为三宝,要求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建立佛国净土,返回到自性清静。在藏传佛教里,无我、无常是善的最高境界,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是善的四个范畴,十一个心所(心的归宿)是善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表现。八正道则是达到善的境界的八条道路。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的第一个表现是日常交往的真诚性。在对真主的崇敬、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之下,西北少数民族形成了高尚的真善美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他们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同民族的同胞交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民族共同体外部与他民族交往,表里如一,胸怀坦荡,一诺千金,以诚相待,在民族共同体自己的家族里,则敬老爱幼,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默默奉献。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的第二个表现是谦恭。《古兰经》要求穆斯林对真主必须谦恭,藏传佛教要求教徒对佛法僧三宝必须谦恭。经过长期的实践,在历史和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把这个宗教的谦恭转化到日常交往中,他们不仅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毕恭毕敬,而且对本民族共同体和外民族共同体的长者、尊者、客人也时时处处表现出谦恭的态度。
2.民族性与地域性心态的结合。地域就是民族共同体生存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地域的产物,地域对民族的作用充分表现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中。斯宾塞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单独耸立的一棵树长得粗壮,而在树群中的一棵树就长得细弱;可以肯定地说,铁匠的臂膀长得很长,劳动者的手皮肤粗糙……可以肯定地说,被人漠视的良心会变得迟钝,而被人遵从的良心会变得活跃,可以肯定地说,诸如习惯、风俗、惯例这类名词都具有意义——同样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技能必然会被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状态;可以肯定地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人必然要变得完美无缺。”[4]28斯宾塞关于进化过程中的物种变异的原理,也适合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分析。西北少数民族生活在幅员辽阔、山脉纵横、气候寒冷、多旱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其社会心态与地域特点相适应,表现为待人接物的纯朴性。西北少数民族的纯朴就像裸露的、无遮无拦的青藏高原,令人一览无余。他们不善言辞,没有花言巧语,对本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以行为证实自己的品行,说得少,做得多,对家庭以默默奉献证实自己的感情,对长辈以孝道证实自己的爱心,对外民族共同体以自己的诚实证实着内心的光明磊落。笔者曾经到地处祖国边疆的最西侧、平均海拔在4000米、素有中国冰川之称的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自治县,访问了一个塔吉克家庭,女主人36岁,男主人近60岁,女主人毫不掩饰地告诉笔者她对自己的丈夫爱得很深,为了让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放牧而孤独寂寞的丈夫看到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能够开怀笑一笑,女主人甚至派自己的孩子去叫远在80公里之外牧马的丈夫赶回来见我们。按照塔吉克人的习俗,男女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异,丈夫必须疼爱妻子。所以,女主人不后悔嫁给大她20多岁的对她百依百顺的忠厚老实的丈夫。笔者也能够感觉到女主人生活得很幸福。纯朴的女主人还把远从几百公里外买来的、本地不出产的、一家人舍不得吃的几棵小白菜炒给我们吃,令人肃然起敬。
3.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了民族的四个特征,其中之一即表现于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共同的心理素质是历史、文化与环境长期作用和积淀的结果,也是长期社会交往的产物。心理素质是静态的,必须以心理的倾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感知。心理的倾向性是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意志、愿望与思想的混合物,其复杂性不是单一的心理素质元素能够解释清楚的。对于心理倾向的复杂性,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说:“我们说人的许多行为以思想为基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始终是客观的和理性的。理性依赖于推理的技能,而这种技能并非发展的很好或被有效运用。”[9]17西北少数民族的心理倾向性反映了民族共同体的独特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就情感的表达来说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喜怒哀乐,就其结果来说,最终凝聚为民族认同的心理。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认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热爱和喜欢的人和事,他们不认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厌恶和排斥的人和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西北少数民族的这个心理倾向性着重表现为对反映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符号的认同。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其实就是对符号的使用、解读和转化能力,一个符号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标志。从交往方面看,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符号就是语言,语言是民族共同体互相识别、互相认同的最明显的标志。话语体系则是语言符号的合成和汇集。无论是西北的伊斯兰教民族还是藏传佛教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既有宗教的神圣语言、书面的规范语言,也有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白话式的语言,即大量的富含哲理的、为西北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俚语、俗语、谚语。在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里,大众化、通俗化、社会化的表层结构的语言是字面意义上的交际语言,深层结构的语言则与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紧密结合、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的宗教信仰、性格气质、思想感情、文化历史的独特性的语言。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语言分为两个部分:民族特有的语言与各个民族共同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言。穆斯林群众见到同民族的客人会说“托真主的福我们见面了”,见到外民族的客人则说“感谢真主让我们相识”。藏传佛教的群众见到本民族的客人会向佛像鞠躬感谢,见到外民族的客人一样照此行礼,都会说许多祈祷和感谢佛祖的谦恭话语。这些含有宗教色彩的语言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所特有,包含了他们的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习惯积淀而成的心理因素。
三、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
上述三方面的结合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在形式方面具有规则性、活泼性与包容性结合的特点。
规则性是指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具有规范约束的特点。这个规范约束不是来自法律和政策以及任何外在的强迫力量,而是在传统文化习俗的积累和延续中形成的历史规范,在民族性与宗教性结合中产生的权威规范,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内心世界里孕育出来的自控规范。这个规范的宗教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形成了宗教规范与日常交往的规范合二为一的世俗化的特点。西北少数民族将原本是属于社会认知范围的宗教规范、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原本属于社会心理范围的民族心态规范合而为一,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了日常交往的特色鲜明的具有规范约束的社会心态。他们以这样的心态处理日常交往的人际关系,表达对日常交往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以宗教规范心态为基础的融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为一体的社会心态规范。宗教规范对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规范影响最大。宗教规范来自宗教戒律。伊斯兰教的戒律突出表现在修行方面,要求每个穆斯林不仅在思想上有信仰,而且要严格遵行五种宗教功课,即念、礼、斋、课、朝。伊斯兰教认为犯罪的行为包括:酗酒、偷盗、抢劫、诬陷、叛教等。藏传佛教的佛法有教法、理法、行法、果法四种,其中行法指戒、定、慧“三行”,这里的戒指戒律,是佛教徒的个人修身养性的必由之路,是防止身、口、意不做恶的基本保障。藏传佛教的戒分为止持戒和做持戒,前者指防范各种恶的戒律,后者指奉行各种善的戒律。藏传佛教的戒律很复杂,也很严格,既有对一般在家修行信教群众的戒律,还有针对出家修行的僧人的戒律。无论多少戒律,最基本的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其它的戒律都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发展、延伸和深化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都对信教群众提出了严格、具体和涉及行为、动机、目的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可谓无所不包,什么都管。在这样的戒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规范自然是循规蹈矩。西北各少数民族凡见面必互致问候,长者尊者上座,余者下座,长者尊者讲话,晚辈幼者必洗耳恭听,不得插话或者反驳。凡遇重要场合,穆斯林群众必在仪式开始前高声诵《古兰经》的章节,藏传佛教的群众则上拜天,下拜地,再拜列祖列宗,同时祈求佛祖保佑,普降福祉。西北少数民族与外民族的人员交往,注意民族特色。远道的客人来到家里,要穿民族服装,以民族传统食物招待客人,敬酒时要唱民族歌曲。
虽然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是在宗教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不等于复制宗教规范,也没有以宗教规范代替社会交往的个性。其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既有严守交往规则的一面,也有以活泼热情的形式表现这些规则的一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把交往的规则性看做是应该在交往中遵循的限制性义务。这种限制性的义务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它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该做什么,可做什么的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它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它摆脱了没有规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乏现实性。在义务中,个人达到解放而达到实体性的自由。”[10]其二,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两个部分的统一,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独特的民族性格气质等成分,这就决定了其表现形式必然是生动活泼,充满民族情趣特色。就社会心理的特点看,西北少数民族是天性好动的民族。这与西北少数民族居住的文化区域直接相关。藏传佛教的各民族以游牧起家,与草原、白云蓝天为伴,富有活泼好动、热情似火、磊落大方的性格和习惯,他们身上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征。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一部分以经商起家,一部分也依靠草原文化起家,前者以回族、维吾尔族为代表,后者以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为代表,商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这些民族与藏传佛教的民族同样的活泼好动、热情奔放、心胸宽广的性格和习惯。内容决定形式,西北少数民族必然以他们的性格和习惯,以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形态,表现他们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生动活泼的特点。
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交往模式,仪式化的特点鲜明突出。仪式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交流思想感情信息时借助的某种原则和方法的综合,它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相联系,反映了社会文明风尚的程度,既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又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惯用形式。仪式化表现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被符号化。符号的标志、顺序、位置等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仪式。“符号化涉及人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应用符号的这种显著能力为人提供了改变与适应环境的有力手段。人借助符号加工和转换经验,使之成为指导未来的行动模型。同样他们借助符号给自己经受的经验以意义、形式和连续性。”[9]25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仪式化符号包括个人符号、社会符号和物质符号。个人符号包括言谈举止、着装打扮、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等。社会符号包括宗教标志、民宅住家里的各种器皿、服装、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习俗和仪式等。物质符号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山川河流、独特的民居建筑、独特的宗教活动场所等。这三类符号将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控制在民族化、宗教化、习惯化的网络里,西北少数民族就是凭着这三类符号形成仪式,开展保持日常交往。一般说来,在日常交往时,标志着民族宗教的符号都安排在显著的位置和靠前的序列,而无关民族宗教的符号则被安排到次要位置和靠后的顺序。
包容来自伊斯兰教的“善念”,即善待一切生命体,包括飞禽走兽;也来自藏传佛教的“慈悲”,即对一切生命体发慈悲心;还来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多元文化格局并存的文化传统习俗。笔者走访过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该州下辖7个县,在近60万人口中有24个民族,在该州的临潭县境内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回族和藏族都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寺院,回族著名的西道堂、藏族著名的明代修建的侯家寺都坐落在该县。该县从未发生过民族宗教纠纷。各个民族日常交往以礼相待,相敬如宾,同时,从不干涉彼此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两个民族、两大宗教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如果没有民族的包容的社会心态,决不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史上的独特景观。
四、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的混合体,对日常交往起着定位、定情、定向的作用。
所谓定位就是确定交往双方的位置,以决定交往的距离。这个位置包括对交往对象所属的民族位置的确定、对交往对象居住区域位置的确定、对交往对象的血亲关系、辈分性别等位置的确定,在确定位置后,分别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以不同的心态与之交往。在民族内部的交往中,多采取彼此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和宗教方式与之互动,心态具有全面开放的特点,与各类辈分和不同性别的同族交往,采用传统的敬老爱幼、男女有别的方式与之互动,心态也根据与之交往的对象的不同而作出适当调整,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民族外部人员的交往则多所顾忌,戒律较多,以惯常待客的方式与之互动。
所谓定情就是在日常交往时的感情投入的程度。在同一个民族里交往,则心态里的喜爱快乐的感情居多,对长辈则心态里的尊敬的感情居多,对平辈则心态里的互换的感情居多,对晚辈则心态里的爱护和帮助的感情居多,与其他的民族共同体的人员交往,则心态里的客气的感情居多。
所谓定向指对日常交往的走向的确定。与同一个民族同族的交往,把交往的方向指向民族和宗教的内容而畅所欲言,进行较深度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不过,也分为不同层次。与长辈交往则注意保持交往的距离,与同辈交往则注意保持和发展彼此的情谊,与晚辈交往则注意身份,谨言慎行。与其他民族共同体人员交往则以礼相待,敬而远之。最重要的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行动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以理解为方向的行动”,其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主客平等[3]318。伊斯兰教的“天下一家”、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的宗教民族理念正是产生这个社会学现象的根源。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源于民族共同体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地域环境、性格气质、心理素质,其结果是形成了融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意识、民族思想感情、民族日常交往仪式为一体的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善行”。在此背景下,行善的宗教、虚幻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现实的功利因素,现实的功利化的行善就是参与日常交往为主的世俗事务,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纯粹的宗教活动里。日常交往则是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和赞美在“视角互易性”、“变形的自我”中的世俗化体现,表现在为民族共同体服务和待客的礼仪中。在日常交往中确立的这个现实主义原则与其源头的那些古朴的思想感情相互配合、相互依赖和相互交融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客观实用的风格。就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来说,既然真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而宗教生活、现实生活都能够体现对真主的敬仰,所以,就要在日常交往中保持恭敬虔诚的心态善待各个交往对象。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则在果报观念的指导下,把日常交往看做是行善的机会和广结的善缘,也对此抱以恭敬虔诚的心态与各个交往对象交往,在此背景下,宗教的力量转化成为推动世俗生活的动力,转变成为促进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积极因素。西北少数民族由此形成的宽容、开朗和友善的社会交往心态对各个民族共同体的人员往来、商业互动、文化交流、思想沟通、资源互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个意义上的善行就把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宗教崇敬从神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更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收稿日期:2009-01-25
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文化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个人习惯论文; 政治论文; 古兰经论文; 藏传佛教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