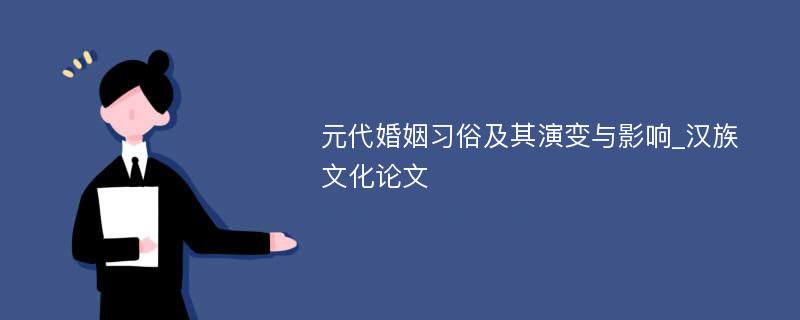
元代收继婚俗及其演变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4)02-0068-03
收继婚姻,是指妇女丧夫之后,改嫁给原夫的亲属这种特殊婚俗。它在我国古代边疆各民族中都曾长期存在。元代时,蒙古统治集团曾在中原地区汉族之中推行这一婚俗,并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是由其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决定的。
收继婚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兄死,弟收寡嫂为妻;弟亡,兄纳弟媳为妇。这是同辈间的收继。另一种是:叔、伯死,侄可娶婶、伯母为妻;父亡,子可收父妾为妇。这是异辈间的收继。
古代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平辈和异辈间的收继都极为盛行。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周书·异域传》:“(突厥)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父死则妻列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在元代的蒙古族之中,收继婚俗也极为盛行。马可波罗说:(蒙古人)“婚姻之法如下……父死可娶其父之妻,唯不能娶生母耳。娶者为长子,他子则否。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1]加宾尼也说:“甚至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可以同父亲的妻子结婚;弟弟也可以在哥哥去世以后同他的妻子结婚,或者,另一个较年轻的亲戚也视为当然可以娶她。”[2]
元朝时,蒙古族进入中原之后,其收继婚俗自始至终一直存在。元世祖女囊加真公主嫁纳陈之子斡罗陈,斡罗陈死后又嫁其弟蛮子台。[3]这是弟收嫂现象在蒙古上层集团内部存在的明证。至顺二年(1331年),浙东廉访使脱脱赤颜“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妻之”。[4]元顺帝时,中书平章阔阔歹死,其侧室高丽氏“誓弗贰适”,阔阔歹正室之子拜马朵耳赤“欲妻之而不可得”。拜马朵耳赤结纳权相伯颜,伯颜奉旨“命拜马朵耳赤收继小母高丽氏”。[5]这是蒙古族子收庶母的具体事例。元文宗时,敕令“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6]这说明为其“本俗”的蒙古人这样作则是合法的。
在崛起朔漠,入主中原之后,蒙古统治集团还曾经在中原地区汉族之中推行收继婚俗。
自从1234年蒙古灭金,在北方地区建立蒙古国的统治,到元世祖至元初年,蒙古统治集团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收继婚。至元八年(1271年)十二月,中书省承圣旨颁行律令:“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7]截止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见诸文献材料记载的有关民间收继婚的事例不断增多。
至元九年(1272年),民户郑窝窝兄郑奴奴去世,其嫂王银银年小守寡,“王银银吩咐郑窝窝收续为妻。”[7]至元十年(1273年),民户傅望伯已有妻室,其兄傅二身死,嫂阿牛守服,傅望伯说服其父母允其接续其嫂,遭到阿牛的反抗,官司打到府司。判决结果,遭受傅望伯奸污的阿牛仍被其小叔“收续为妻。”[7]滑州民户赵用之子赵脸儿与民户张铸换亲,赵脸儿未婚而死,赵用令次男赵自当收继,张铸不肯,告到省部,最后的判决也是“依小叔收阿嫂事理接续”。[7]大都路民户郭阿秦子乞驴与民户李大之女娥儿定婚,郭乞驴未婚而死,郭阿秦“欲令次男冬儿接续”,但李大又将娥儿许配与裴节度使的驱口陈驴儿,并接受了“绫罗缎匹”。最后依“已降圣旨”,判娥儿由郭阿秦次男冬儿接续。[7]
从以上例子来看,已定婚未娶之前,兄死,弟收其嫂,男方家长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女方没有悔婚的权利。已婚妇女丈夫死,叔收嫂要征得其家族特别是自己父母亲和叔伯亲属的同意,以便确定收继的子、侄。收继时也有一定的程式,聘主婚人、行媒是必要的结婚程序。收继婚在元代是夫权的体现,至元八年收继的诏令是对男子婚姻权力的一种保护,从而使妇女嫁或未嫁时都失去了婚姻选择的自由。
蒙古统治者在汉人中推行收继婚,是信奉和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儒士和官吏们不能接受的。他们对统治者多次进行劝谏,要求禁止这种婚俗。元成宗时,郑介夫在奏疏里就明确提出,对于收继婚俗,“除蒙古人外,截日禁断”。“有兄亡而嫂愿改志及守志者,并听;如收以为妻,则比同奸罪,更加一等。”[8]元顺帝时,监察御史、女真人乌古孙良祯针对收继婚俗上言,更主张各族皆禁之。“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9]这些意见虽然没有为元朝统治者所接受,但对限禁汉人的收继婚姻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至元后期到元代中后期,汉人收继婚姻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德五年(1301年),延安路赵胤之女穿针招到养老女婿王安,王安身故,其房弟王安杰强行收嫂,礼部以“凡人无后者,最为大事”为由,准许赵胤“别行召婿,以全养老送终之道”。不准王安杰收继其嫂。[10]延祐二年(1315年),绍兴路“因值饥荒,典卖妻室”,婚姻形式相当混乱,多有夫死妻改嫁,而小叔争理收继其嫂的现象。对此,元政府明令“兄亡嫂嫁小叔不得收”。[10]延祐五年(1318年),大宁路利州民田长宜强迫收继兄嫂阿段,被府司目为“乱常败俗,甚伤风化”,并比照强奸无夫妇人例“杖断一百七下”。[7]
尽管元统治者以法律形式限制其他民族的收继婚俗而保护蒙古族自身的收继婚俗,但在汉族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蒙古族的收继婚俗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女,大德十一年(1307年)嫁给弘吉剌部帖木儿之子雕阿不剌。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其夫雕阿不剌死,“皇姑鲁国大长公主,虽寡守节,不从诸叔继尚,鞠育遗孤”。元文宗时召学士赵世延、虞集“议封号以闻”。[11]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不接受其夫弟的收继,表明其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较深,对本民族的旧俗有所不满。而文宗以朝延的名义对之予以旌表,是封建政府对妇女贞节观念的宣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本族收继婚俗的一种否定。
在一般的蒙古族妇女当中,也出现了抵制收继婚的行为。蒙古雍吉剌氏女子脱脱尼,26岁时,其夫哈剌不花卒。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千方百计向她施加压力,脱脱尼怒骂其子“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只得“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脱脱尼“三十年以贞操闻”。[12]这自然是汉族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所致。
尽管元朝统治者禁限在汉人中的收继婚,但这种收继婚俗的影响在汉族下层仍然存在,婚姻中的收继行为也时有出现。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彰德路民户张招抚次男张平儿本是民户杨阿田的抱财女婿,其兄张大身死,张平儿将寡嫂阿梁“收继了当”;[10]大德二年(1298年),民户刘大身死,其叔伯弟刘三“将嫂刘阿王接续了当”;[10]大德十年(1306年),刘三病故,次年,在地方官者室赤合剌哈孙奥德右丞的允准下,刘大之弟刘君祥将其嫂“受续为妻”。[7]在汉族一般民户中,对嫂子的“乞例收继”,“依体例收了”,可以说是接受了至元八年拟准收继的规定。元政府的司法机构在审判婚姻案件时,经常使用“应继人”的概念。[10]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收继婚观念不仅在下层人民中存在,在政府官员中也是如此。元政府禁限较多的是汉族中的异辈收继和同辈收继中的兄收弟妻,对于弟收其嫂则禁限较少。郑介夫说:“旧例止许军站续,又令汉儿不得收,今天下尽为俗矣。”[8]事实上,在元代汉族之中,收继婚姻的观念及现象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的。
为什么在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中会长期存在收继婚俗,而且中原汉族也很快接受了这一婚姻习俗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收继婚姻体现了父权制之下,妇女传宗接代,延续宗族的需要。父权制下的妇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出嫁之后,就成为夫家一族传宗接代的“生产工具”。亡夫无子,她要和夫弟结合,来完成自己作为“工具”的义务。对于夫弟来说,与寡嫂结合为亡兄生子,也是“尽义务”。古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后汉书》中讲到西羌人实行收继,“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史记·匈奴列传》记中行说曰:“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娶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这正是透露出收继婚姻在传宗接代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以色列人中也有弟收兄妻的规定。《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五章“弟宜为兄立嗣”就将收继婚的实质合盘托出:
“弟兄同居,若死的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在实行收继婚姻的民族之中,实行收继是为家族传宗接代应尽的义务,而且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其二,收继婚俗在买卖婚姻的条件下,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古代婚姻多有厚聘,实行收继,则无需另立婚帖,不必再议彩礼。对于贫苦人家,将减少经济方面的压力。《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婚姻》“舅姑得嫁男妇”条说:“没有小叔儿续亲,别要改嫁呵,从他翁婆受财改嫁去呵”。看来,元代无人收继的寡妇要改嫁,公婆之家还得拿出一笔聘礼。有的民族(如蒙古族)寡妇改嫁时,还要将属于自己名下的一批家产带到新夫家中。这样,不管是从男方还是从女方的角度来看,实行收继,都会减少在财产方面出现的损失和问题。
其三,实行收继婚俗,也是一部分男女当事人在感情方面的需要和愿望。古代的男女和外界的异姓都不大交往,而叔与嫂毕竟在一个家庭中生活多年,他们之间的交往远要比与外界的异姓的交往多得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有一定的亲情,易于产生感情。寡妇和失父的子侄也能得到亲人的照顾。所以,实行收继,也会成为大多数当事人较为满意的选择。
由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收继婚姻之俗不仅在古代的中国,而且在世界其它不少地方,都曾长期盛行不衰。
明朝初年,由蒙古族带到中原汉族之中的收继婚姻这种“胡俗”仍然盛行,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禁止它,曾在《明大诏》中专门下过严禁“弟收兄妻、子承父妾等胡俗”的诏令。《明律》规定:“若收祖父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清代法律中也有过类似的规定。清《皇朝经世文续编·礼政》中有:“其或兄死娶嫂,弟死娶弟妇者,乱伦犯法,莫此为甚。连本人、子女一概摈斥,永不入(族)谱”。对于实行收继者,不但法律要予以严惩,而且宗族对其本人及子女也要予以“摈斥”。明清之后,长期以来,由于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禁止的作用,收继婚俗在我国大多数地方逐渐销声匿迹了。
[收稿日期]2004-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