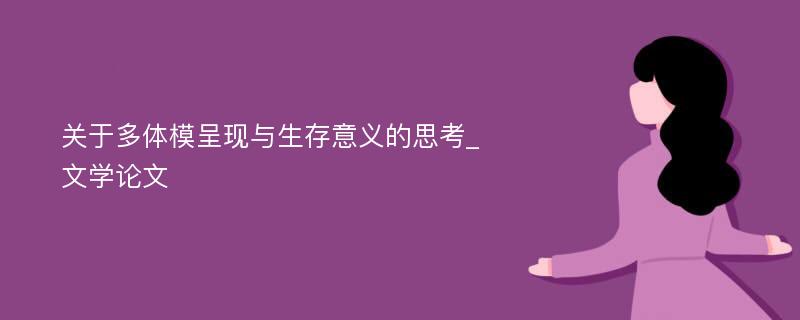
多象纷呈与生存意义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时限1997-2000年,恰恰是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坛眩目的明星当属长篇小说,但这并不意味中短篇小说偃旗息鼓,萎缩不振。新时期崛起的中篇小说,80年代是它的辉煌期,后来虽然有过平淡与滑坡,但总体说它依然顽强生存,孜孜更新,佳作迭呈。获得这届中篇小说单项奖的5篇作品,通过反复评议,层层筛选,可谓优中选秀,秀里拔萃。
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是多元纷呈、管弦齐鸣的,题材风格多姿多态,有历史强音的震颤,又有一隅一角折射的时代之光。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概括90年代文学,只想就这层届获奖的5个中篇小说以及初选组推举的其他几篇作品(详见《小说选刊》10期公布的篇名),简要透析一下其主要特征及其给我们的提示。其一,文学多元多样化的流向,开始进入更为注重个人性与个人化的新阶段。文学多元多样化爆发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它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浪涛,打破了当代文学长期大一统的单一局面。多元化的真正实现,并非仅是突破单一性,也不能停顿于文学旗号与群落(如寻根文学、现代派后现代派、新写实等)的崇尚,作家应该扬起自己创作个性的风帆。当下流行的个人性、个体性或私人化写作,这些提法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和颇多的歧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表明作家正在告别追溯、跟时尚与赶浪头,寻找自我的文学天空,营造自己的艺术思维、审美理想与个性化的文学世界。如将新时期文学流向的三个阶段打一个比喻,即是单一性阶段,文学共同挤在一个梯子;然后在多样的梯子上竞争;第三阶段是每个人营建与攀登自己的梯子。这一景观虽然还没有尽美尽善,但从这届获奖的及备选小说中可以见到,八面来风,张扬个性,各人头上一方天。其二,文学依托的价值意识,由消解而开始回升。没有主体价值的渗润,文学灵魂就失落了支柱。没有独特的审视与价值判断,必定失去文学批判性和自身的尊严,作品将会缺钙与贫血。经济全球化、世界强势文化及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上商品化侵淫文学的肌体,那种理性、正义、真理与尊严消失的“时代官能症”入侵90年代文学,价值意识以及批判意识、崇高意识、悲剧意识在消解,文学呈现了苍白与平庸。90年代中后期小说,价值意识回归仅仅是开始,还须一个过程。但在获奖的与备选的中篇小说中,看到它正在冲击小说中某些闹剧、谑剧与侃剧的无聊,复现了曾失落的文学批判性、悲剧意识与终极关怀的大悲悯情怀的壮美身影。其三,关注生存状态的小说,显示了新的征候。有的兴味盎然地表现商界大亨、官场权势者、白领人士的社会上层,但又有作品面对下层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和生存境域,小说注意将“初级阶段”生存的叙述与人之存在意义的追索二者相融会。还有的不但注视人与社会的撞击,而且开始关注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
2、这届获奖及备选的中篇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年轻作家比重突出,相当活跃。选材,视角,艺术探求,饶有个性,富有创新精神。如群星闪烁,前景看好。《被雨淋湿的河》仅差一票即满。作者鬼子年轻,近年由前卫转向写实。这篇小说颇似流行的打工文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写谋职之难、劳工之苦,它直面现实,带着生存的焦灼揭露市场经济出现的劳资双方的尖锐冲突。晓雷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反对残酷压榨,曾对苛扣工薪与强迫职工屈跪搜身的两个老板发动了抗争。晓雷死于煤场井下瓦斯爆炸,是一个官商勾结暗害的抗争牺牲者。《被雨淋湿的河》叙述的悲剧是双重的,儿子晓雷之死是抗争者的悲剧,其文结局则是一个老实人、懦怯者的悲剧。他老实巴交,小心翼翼,但灾祸一个个降临头上。妻死子亡,女儿晓雨又被一个有钱老板霸占。父亲赖以欣慰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全被夺走了。什么都没有,只留下他那“像一根枯朽树桩”的躯体,最后也倒下了。鬼子小说有一种宝贵的品格,面对人生现实,深深的忧患意识,恪守价值信念,不苟同世俗平庸,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透出悲悯情怀与炽烈的批判精神。
《成长如蜕》主人公弟弟与晓雷年龄相近,但命运截然不同。90年代涌现不少写一代人生长历程的成长小说。《成长如蜕》,顾名思义,写了一个年少纯真的弟弟走向商海的心路历程。作者叶弥出手不凡,弟弟形象意蕴丰赡。小说叙述小弟的成长过程,很注重转型时代,社会习俗和家族三大“合力”的诱导与推引。父与子的冲突,可以说是中外名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父子两代的冲撞,往往标记时代或历史的转弯。弟弟这个亿万富翁家族的纨绔子弟,他所需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都离他远去了,他终于加入了他所厌恶的市俗商海之中。晓雷与弟弟二者性格有别,前者抗争,后者则是顺从与接受,晓雷命运是悲剧,弟弟命运难道就是喜剧吗?很叫人深思。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未尝不可也叫作成长的故事,不过小说中的白大省与“弟弟”成长的年代、环境和性格大不一样了。叶弥从每一个细微末节透视“弟弟”的“变”;铁凝却从白大省念书、初恋、相聚与离散各样情节中,发现她的“不变”。即她作为北京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女孩,那种傻里傻气的纯洁正派,“缺心少肺”的快乐仁义,还有那总是“怀是一腔过时的热情”。在别处,以至在别的小说里,看不到白大省形象,甚至在作者的《大浴女》中也没有,只有在《玫瑰门》依稀可见她的身影。对于这个没有沾染商品与拜金气息、没心没肺的姑娘,作者爱的真恨的也真,只有在铁凝那种又陶醉又清醒、既爱又恨的叙述笔调中,才会实现“这一个”。“典型”一词不大被人提起了,白大省给予美学意义的典型评语也不为过。当然,白大省那憨憨的性格的外在细节与内在的微妙,没有作者创造典型的工笔也是画不出来的。白大省,晓雷,小弟,这三篇小说三个人物生活于新中国的各自年代,各有各的生存境域和价值理想。从这三篇小说,也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的多元多样的审美个性特征。即便是写同题、同一个成长人物,出自三位作家各自的笔端,也是绝然不一。
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与叶兆言的《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这两篇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故事,但不是90年代流行的怀旧小说。二位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对如烟往事的缅怀或挽歌吟唱,不是历史的戏说或野说,而是对过去时代的人物寻找独特不俗的新诠释。叶广岑的小说多是写清末民初皇戚贵族后裔的家族生活,不太注重家族命运与政治变迁史的纠葛,侧重于对各式人物像品评历史古董文物那样,从历史文化视角细细的审视。《梦也何曾到谢桥》的父亲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有两个家,一个金家,他自己的家,贵族之家;一个谢家,平民之家。父亲在自己家他什么也不操心,也不做;在谢家他却无贵族子弟气味,事无巨细的全都管,简直就是当家人。他既眷恋那无法舍弃的贵族之家,又渴望大宅门所缺少的那种无等级、平易、温馨的平民百姓生活。这首鸿沟虽然被统一在父亲一人身上,但又是无法弥合的。小说结尾,谢家的六儿给金家六儿之妹亲手缝制一件衣服,它象征着父亲后代人在新时代里终于实现了弥合之梦。叶广芩一直在守望她自己的文学家园与精神家园。她的贵族后裔小说,读者不是不熟悉,但新作面世人们依旧喜欢品尝。其因不在于题材与风格有什么新鲜或变迁,而是因它浓浓的文化积淀、小说的神韵和深长的意味。如果说《梦也何曾到谢桥》叙述一个家族生活中“衣”的故事,《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从其篇名也知道是“食”的故事。衣与食,人须臾不可或缺。叶兆言很会讲历史故事,不过这篇从高挂大红灯笼的巷院移到了秦淮河畔。金陵美食,宾客纷至沓来。傅家的斜阳楼的兴衰,读来令人叹喟。
毕飞宇的《青衣》显得特立独异,也是一篇很见个性特色的小说。人生如戏,戏似人生,台前幕后,爱憎相绊。毕飞宇说他20岁前忌讳不抒情,二十出头忌讳不哲理,人到中年最忌讳假。他近期小说尤其《青衣》,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对真和真实、对抒情的诗意和人之生存、生命的哲思。作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戏剧同现实社会的种种撞击,有喜有悲,悲喜纵横,笔笔道来,笔墨到位。
3、阎连科的《年月日》的面世,弥补了当下农民和农村生活小说的缺失,而且它那沉重感与厚重感带来新的思索。干旱,灾荒,农民的逃难,老农对土地庄稼以至对一棵禾苗的钟爱与体贴,在农村小说中本不是乏见的。但《年月日》对这一切的叙事,凝结着农民与土地、与稼禾的血肉关系,加之饱蕴深意的近似寓言的笔墨,从具象提升寓象,使读者顿然联想起夸父逐日和愚公移山的形象。先爷并非是历史神话中的英雄,但这位老农形象和他惨烈而壮烈的悲剧令人感到中华民族那种执着、韧性的精神。这篇小说有新意,很厚重,但在追求新意和厚重感时,稍感限制以至妨碍了可读性。
《吹满风的山谷》是获奖小说仅见的一篇士兵生活小说。一提军旅文学常常跟轰轰烈烈的战争或军训、跟冲锋陷阵、雄姿勃发的英雄形象维系在一块儿,可是这篇小说只有山谷与飓风,只有寂寞。这位年轻作家出手不凡,独出机杼,小说重要特征在于它不是在轰轰烈烈中写英雄,偏偏在寂寞之中见英雄本色。小说没有大波大澜的情节故事,却在令人难以承受的寂寞和孤独中升腾起爱的温暖。这篇小说看似单薄,但在单薄中见丰富;虽无完整故事情节,但有鲜活的细节,在质朴的叙事笔调中洋溢着诗意。
角度与取镜,常常是检验一个作家驾驭题材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读迟子建的《逆行精灵》,让我想起莫泊桑经典之作《羊脂球》,它将普法战争背景下的不同阶级不同个性的各色人物,不是一个个分别写来,而是放在一辆逃难的马车上。于是上至贵族绅士,下至底层妓女,这一特定横切镜头将众生相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了。《逆行精灵》也有一辆车,不过将马车换了汽车,作者把所要透视的各样人物,也都装入这辆长途汽车里。雨水把车阻隔在途中一个小站上,正是在这象征顾客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巧妙地演绎了各样人物的生命欲望和人生碎片。迟子建小说有现实感与世俗味,也不乏古典浪漫的情怀。作者如果在那独特角度的透视中,在从容叙述那又平庸又灿烂的故事中,对人物心灵有更加深层的把握,那将把小说推向更高的审美境界。
4、《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与《生活秀》,刘恒与池莉,二位作家一北一南,不约而同走进都市小人物和日常的生活,表现他们生存状态与生命的体验。两篇小说这种不谋而合的视点恰恰是90年代后半期的时代在不同作家身上共同性的投影,是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思潮对小说的推移。关注“初级阶段”平民生存状况的新写实小说,与世界文学潮流相连接,打通了与外国文学互动的轨道。但它在叙述人之生存时有些小说疏离了“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出现了某种失血的现象。从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要求,关注人之生存状态与为人生、探索人之存在价值,二者并不对立,佳品杰作正是从这二者高水平的融汇中诞生。这两篇作品让人看到,写生存与人之存在意义的追询,二者渐趋汇合。二者所写的张家与来家两个大家庭各有矛盾,但二者有一相似的特征,各自实现长兄或大姐的作用,作者笔端伸向维系家庭和睦与和谐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就是孝悌二字。如孟老夫子所云,入则孝,出则悌。在“过日子”的艰辛与坎坎坷坷岁月里,他们重仁义,有凝聚力,活得有尊严且有滋有味。应该说形而上的挖掘人物生活,不是刘恒和池莉的强项,但大民家在那苦涩与贫嘴调侃中,在吉庆街来双扬家有趣与无奈的生活流中,令人感受到人各有活法与怎样活法的味道,可以说这是刘恒、池莉和新写实小说的一大提升。叔本华说“现代人什么都有了,就缺少哲学”。是的,文学倘若只强调写生存,疏离人之存生价值的哲理思索,黄钟大吕之作怎会出现?在这里顺便提一笔,刘恒笔下的张大民形象,
怎么贫嘴,怎么调侃或反讽都可以,但小说的叙事语言或叙述方式的“贫嘴”,似应节俭。池莉在小说雅与俗的和解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似应注意二者结合“度”,对“俗”不能太放纵了。
老作家李国文很愿意写“新面孔”,《垃圾的故事》里的丁丁是以消除京郊垃圾、解除人类困扰为己任的生态环境护卫者,迎接新世纪的一个新面孔、新人类的形象。丁丁形象之新不仅仅职业、事业之新,而是他那现代人的思维、志趣和情感方式之新。这新,特别表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几次毅然拒绝。拒绝国外任职而回归祖国闯事业;拒绝情人杨菲尔码给他铺设的连升三级步入部长殿堂的如花似锦的仕途,宁愿与一堆堆发散臭气的垃圾山打交道。还有,在备选篇目中新人类形象的丁丁并不孤独,胡发云的《老海失踪》里的老海,也将智慧、才能以至生命奉献给生态自然,形象十分感人。
《垃圾的故事》与《老海失踪》,如果归类可列入文坛所称的环境文学。环境文学的存在,提示我们对文学里“人学”的内涵应该作出新的阐释。人类生存包括两大半球,一是人与社会关系,一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长期有一个误解,将文学与囿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将文学中的人与生态自然关系抛弃了。笔者多次提出,环境文学乃是拯救人类地球家园的文学,应有更多文学家更多优秀作品投入环境文学之中。这,不是可写可不写的某一类题材,而是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死安危,关系文学与整个人类的思维大变革,关系“人学”的革命。环境文学拥抱的不是狭小的、片刻的时空小故事,而是全人类和整个地球!它不是稍纵即逝的现时性的作品,而是与大自然生死相伴的未来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