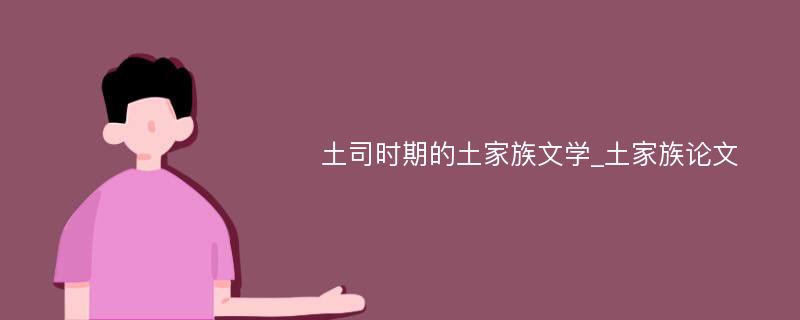
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土司论文,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土家族历史,可以分为传说时期,巴国奴隶制国家时期、羁縻时期、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而土司时期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有特点的时期。虽然封建土朝正式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是在元代,实际上早在唐朝末年土家族地区的强宗大姓已经较固定地在其地实行自治性管辖,并世代相袭。这可以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著名的“溪州之盟”为标志。在湘西,彭士愁统辖溪州等二十个州称“静边都指挥使”后,即“以长子师裕、次子师皓分领其众,师裕为永顺司祖,师皓为保靖司祖。”(民国《永顺县志·土司》)在鄂西,唐元和年间田行皋即被任命为施州刺史,此后田氏也一直世袭治理其他,直至容美土司的正式建立。在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而且在文学发展上也十分富有特色。可以说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丰厚的实绩。
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又由于其地偏僻,山大人稀,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因此汉文化的影响较为迟缓,即使是象施州及附近地区的“熟夷”最早也是到了宋代才有人能以汉文著述,而其它土家族地区普遍使用汉文字则是在明代以后。所以,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以自己的民族语言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是土家族文学唯一的传承和发展形式。直至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才在汉文化的强力影响下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文人书面文学。此后,土家族文学才以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双管齐下的形式向前发展。
由于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民间文学是与羁縻时时期的民间文学一脉相承的,为了更明确地认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特点,有必要对羁縻时期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作一简要回顾。自秦灭巴以来,下至唐宋,土家族地区都基本上处于强宗大姓割据的羁縻状态。强宗大姓长期的割据,造成了相对的封闭局面,从而使土家族地区社会形态的发展脱离了中原地区社会形态的封建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又主要体现为封建王朝与土家族强宗大姓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民族矛盾相对突出而阶级矛盾相对淡化。在此状况下,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十分薄弱,而本民族许多原始的文化因素及事象则得以遗存,所以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多是歌倾民族英雄,反映本民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与心理情感,以及表现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其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歌谣和传说。歌谣的内容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以神灵为吟唱对象的神歌,这类歌谣通常由土家族巫师梯玛在各种巫祀活动中演唱,主要体现为娱神的性质,明显体现着本民族原始宗教意识的传递。另一层面是以吟唱人本身劳动生活的劳动歌。这时的劳动歌主要是传授劳动知识经验,教给人以生存的本领,明显传递着原始先民以生存为本的功利目的,如“洒谷种”、“种包谷”、“薅草”等。这时的民间传说主要是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尤以人物传说最具特色,如《巴蔓子》、《向老官人》等。这些作品歌颂的都是本民族的英雄人物,他们是人们集体智慧、力量和利益的体现,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他们的事迹中有不少是与皇帝作斗争的情节,这是与当时的特定社会生活背景密切相关的。地方风物传说则往往是将某一反抗外族侵略的动人故事依附于土家族地区的地方风物上,借叙述地方风物的来历反映本民族的心理情感,投射着特定的爱憎观念,如《女儿寨的传说》等。习俗传说则表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极富特色的一面,鲜明地昭示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这些传说都体现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和特定的地域色彩。纵观羁縻时期的土家族民间文学,明显带有本民族原始文化的大量遗存,较多地积淀着原始先民的宗教意识和生存繁衍的功利目的,此外更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其鲜亮的民族自立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这一特征在各种传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朗。
到了土司时期,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和人民生活处境的改变,土家族民间文学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为之一大变,体现着前所未有的特点。
土司时期的统治野蛮而残酷,相对强宗大姓割据的羁縻时期来说,土家族人民的苦难要深重得多。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土司统治的显著特征,“凡土官之于土民,主仆之分最严。”(赵翼《檐曝杂记》)在土司所辖境内,土司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对土民可以任意欺凌宰割,“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清世宗实录》)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土司杀人不请旨”。土司所到之处,土民都必须下跪迎接,“土司出,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伏。即有谴责诛杀,惴惴听命,莫敢违者。”(同治《桑植县志》卷八)连居住上也体出了森严的等级,土司衙署可以“绮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如有盖瓦者,则治以僭越之罪。”(同治《保靖县志》卷十二)土司刑法极为残酷严厉,土民稍有触犯即遭酷刑,“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受刑者“剥肤炙骨,惨酷之状,口不能言。”(《容美记游》)土民打官司,不管其有理无理都须向土官送礼,“胜者必送谢恩礼,负者亦送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人口。”(《永顺府志》卷十二)许多土民因此而家破人亡,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土司家奴。有些地方的土司还对土民新嫁娘实行“初夜权”,强霸民女,土民敢怒不敢言。各土司之间争权夺利的仇杀也给土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在经济上,土民所受的剥削程度更甚于羁縻时期,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土民自己极少有土地,因此大部分土民实际上都沦为土司的农奴,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土司则奴婢成群。沉重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使广大土民生活十分悲惨,“土民如在水火中”。(《清世宗实录》)以上可见,在土司时期,黑暗的土司统治使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广大土民生活的苦难悲惨也是空前的。在此社会生活土壤中产生的民间文学也就鲜明地体现了揭露社会黑暗、控诉土司罪恶、倾诉民生疾苦的主题,阶级意识及反抗意识十分浓烈,斗争性极强。这就是土司时期土家族民间文学的突出特征。
由于社会生活形态的变更,这一时期的民间歌谣体现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吟唱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内容上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更宽广,形式上则在以前较为单一的劳动歌基础上又产生了时政歌、苦情歌等新的类别。这时的劳动歌除了少数仍具有传授劳动知识经验的意味,大多数作品则一变前调,以劳动者本身为吟唱对象,广泛涉及到对劳动的辛苦、劳动者的心理情感、劳动者的悲惨状况和苦难生活的吟唱,大都体现着悲剧性的感情基调。如“大田栽秧栽四蔸,捡个螺师往上丢。螺蛳晒得张开口,栽秧儿郎黑汗流。”又如“一块大田四四方,守住大田哭一场。长年累得收谷子,看看不够半年粮。”现实生活的苦难太深太重,而且无处申诉,人们只能借助歌谣来排解一下心中的苦痛,自忧自解,从而支撑生存的信念,这就产生了专门吟唱各种生活苦难的苦情歌。它是土司时期土民悲惨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其基调较劳动歌更为凄凉。如“说起穷来硬是穷,娘盖蓑衣火铺头。爹爹没得蓑衣盖,夜夜抱根吹火筒。”又如“酉水行船好遭孽,好比血盆抓饭吃。颈上吊着生死牌,龙王提前点鬼笔。”等等。土司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已使土民苦难不堪,一遇到天灾人祸土民的悲惨处境更是难以描述,而“时政歌”常常成为记录特定时期人民苦难的一面镜子,很有认识价值。如《嘉庆十八年》:“说起嘉庆十八年,如同一座鬼门关。难中难来苦中苦,孙猴子过火焰山。豆子包谷没过手,粟米谷子没过镰,豌豆绿豆没踪影,高梁只剩光杆杆。园子菜蔬绝了种,南瓜只剩干藤牵。十字路口贴告示,一个婆娘几吊钱,卖了婆娘卖儿女,卖了田土卖祖先……。”由于这一时期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薄弱,中原地区的封建礼教还极少投射半封闭的土家族地区原始性文化因素遗留甚多的社会形态,而自古以来土家族不避男女之嫌,妇女地位较高,相对汉族女性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男女婚姻也较少受门第、财产等因素的制约,“歌为媒”的古老习俗在男女婚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情歌仍极可贵地体现着人性、人情较自由的舒展,格调欢快,坦率无拘,极少压抑之苦。如“高坡起屋不怕风,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两情义好,无油炒菜味也浓。”又如“十七八岁姑娘家,独坐闺中懒绣花。想起红尘阴阳事,心里好象猫扑抓。”等等。而到了改土归流之后,随着封建礼教在土家族地区的滋蔓和逐渐根深蒂固,情歌风格也就为之一变,吟唱压抑、控诉之情成为主调。由此看来,在土司时期,男女婚恋方面是唯一较少受到土司黑暗统治戕害的一个领域,因此,在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民间文学中,唯有情歌体现出了一抹人性舒展的亮色。
需借助于某一依附物而创作的传说,在这一时期逐渐减少,所产生的一些作品也多是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折光反映,由以前的歌颂基调转为控诉基调。在艺术创作上能更方便、更直接了当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民间故事在这一时期却大量涌现。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故事中,揭露土司的野蛮残暴以及与土司作斗争的英雄人物故事占着突出的重要位置。这些故事都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矛盾,笔调辛辣,战斗性强。揭露土司残暴的代表性作品有《玩火龙》、《鸡腿哪里去了》等。《玩火龙》中说到,由于土民只能以茅草盖屋,所以经常失火,而土司则认为烧房子很好看,于是规定三年放火烧一次老司城供其享乐。土民无法忍受苦难,只好流亡他乡。作品中虽没有直接表现与土司的斗争,但从侧面反映了土民的愤怒与反抗情绪。表现与土司作斗争的英雄人物故事则直接地反映了人民反抗土司黑暗统治的心声,如《磨力卡铁》、《鲁里嘎巴》、《唐好汉斗土王》等。这些故事中塑造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而且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情感和愿望,集中体现了土家人民的优秀品质特别是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富有理想化色彩。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司的残暴镇压下,人们的反抗都最终失败,因此作品中的这些英雄人物也大都具有悲剧性色彩,但其中所张扬的斗争精神很能鼓舞人心。其它一些民间故事或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或表现民族特有的风情习俗,或嘲讽人们自身的恶习,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本民族的生活、心理、情感和文化传统,极富于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
上述可见,由于土司时期阶级矛盾的激化和人民苦难的加深,这一时期土家族的民间文学体现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阶级斗争意识,揭露土司的罪恶、反抗土司的欺凌,倾诉生活的苦难是其普遍性的主题。这些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社会形态的真实反映,是土家族人民生活与心理情感的真实记录,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土家族文学在土司时期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文人文学的产生。在此之前,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是土家族文学的唯一形式。土家族文人文学的产生是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更确切地说,是与汉文化的直接影响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封建王朝的官吏就曾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学校,但其时入学者只是限于土家族地区的汉族官员子弟。到了唐宋时期,汉文化的影响较前更为广泛,在接近中原的施州等地,土家人中已有人能以汉文著述,还有人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因此史称“施州蛮”为“徼外熟夷”。(《宋史》卷四百七十)。到了土司时期,封建王朝在加强对土家族地区控制的同时,也更注重施行文化同化政策,试图以儒家思想及礼仪规范对少数民族进行心理思想上的改造,因此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下令规定:“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这样就把接受受汉文化与土司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土司阶层被迫入学。此时土家族地区各县大都设立了学校,专门培养土司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这些带强制性的文化同化政策,在客观上却有力地促进了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有利于土司、土官文化素质的提高。在此特定的文化气候下,土家族统治阶层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文化,用汉文著书立说、考取功名入朝为官者也逐渐增多。土家族的文人文学便是在此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此时入学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仅限于土司及其子弟,所以土家族的文人文学便是从土司阶层中产生的,先天带着阶级的局限性。土司时期的土家族文人文学一经产生,便呈现出它的鲜明特点,即作家是以土司家族作家群的整齐阵营登上文坛,一鸣惊人,令人瞩目。这一时期在土家族地区几乎同时涌现了两个较大的土司家族作家群:一是四川酉阳土司冉氏作家群,一是湖北容美土司田氏作家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中说:酉阳于“永乐中改隶重庆府,建立学校,俾渐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开酉阳土司文化创作之风的首推十五世纪中叶的冉天章。《冉氏家谱》称其“幼好文翰,娴吟哦”,所著诗集今已散佚,仅留下《题仙人洞》七律诗一首。冉舜臣、冉仪、冉元祖孙三代都有诗作传世。冉舜臣的作品中有《飞来山记》一文,散文在当时土司文人创作中是极少见的。二十世土司冉御龙及其子冉天育、孙冉奇镳、重孙冉永涵也都创作了大量作品,但残存极少。更值得一提的是容美土司田氏作家群。田氏作家不仅传承五、六代,而且有名诗人达十余人,且人人有诗集问世,与当时汉族名士广泛唱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首开容美诗风的是田九龄,字子寿,著有《紫芝亭诗集》,《湖北先贤诗佩》中亦选有其作品。《宜昌府志》称:“容美司以诗名家,自子寿始。”此后,容美土司诗人辈出,作品丰瞻,涌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如田家文及其《楚骚馆诗集》,田会及其《金潭吟》、《意笔草》和《秀碧堂诗集》,田圭及其《田信夫诗集》,田珠涛及其《田珠涛诗集》,田霈霖及其《镜池阁诗集》,田既霖及其《止止亭诗集》,田甘霖及其《敬简堂诗集》,田舜年及其《白鹿堂诗集》等。可惜散佚甚多,在今存的《田氏一家言》中仅存诗488首,不到原作数量一半,但由此也可见田氏作家群创作成就之一斑。他们的创作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多与当时汉族名士往来且获得了高度评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如南明太史严首升评田九龄的《紫芝亭诗集》:“先生诗风骨内含,韵度外朗,居然大雅元音。虽间落时蹊,未去陈言,而造诣深厚之力不可诬也。诸绝尤有朱弦洞越,一唱三叹之致。”他们丰瞻的创作实绩无疑标志了土家族作家文学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土家族文学在历史上正式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坛。
由于这些文人都是土司及其子弟,先天的阶级局限就使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取材较为狭窄,以写景咏物、吊古咏史之作为多,较少涉及下层人民的生活与疾苦,仙风道骨意味颇重。这恰与同时期的民间文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如冉天章的《题仙人洞》:“洞里神仙渺莫猜,海风幸不引船回。四周苍苔雕虫篆,一脉灵泉撒蚌胎。花自无拘开又落,云如有约去还来。谁能静习长生术,向此烧丹扫绿苔?”写景咏物之作虽较少深刻的社会生活意蕴,但其中不乏独出机杼、清丽优美之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如田玄的《竹下芙蓉》:“湘裙淡染鹦哥绿,粉颊微施小茜红。不知何事秋风里,半掩羞容愁杀侬。”一些描绘民俗风情的作品更是别具风采,神韵生动耐人寻味,如田圭的《澧阳口号》:“家家临水作岩楼,半是村街半是浮。十八小娥槛内绣,停针坐看上滩舟。”吊古咏史之作虽以历史遗痕为题材,但其中往往寄寓了作者特定的思想感情,常能引人深思。如田九龄的《刘生》:“马首黄金意气横,由来侠客有刘生。凭得尺八专诸铁,报尽人间世不平。”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着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冉天育。冉天育曾从戎援辽,特定的戎马生活使他的诗作在内容上独树一帜,对边塞风光及战争的残酷作出了生动描绘,其格调刚健悲壮,风骨凛然,撼人心魄。如《从征左经阵亡处举酒酹之》:“日惨更风号,千军血一刀。黄沙平地起,白骨比山高。国帅生为戮,健儿死亦豪。裹尸何处所,薄奠借村醪!”面对国事危急,诗人一腔热血,抱定慷慨捐躯的决心,节义凛然:“长城临海复依山,万马萧萧晓度关。警报频闻休细问,男儿死国当生还?”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思想蕴含在土司作家群中确实屈指可数。
在土司家族作家群中,成就最高的要推田舜年。田舜年广交汉人名流,经常切磋,如孔尚任、顾彩、严首升等皆为其友。他学识广博,著述颇丰,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二十一史纂要》、《六经撮旨》、《容阳世述录》等。他还将田氏作家群历代先贤所遗诗作汇编为《田氏一家言》,共十二卷。南郡人伍骘在给田舜年诗集所作的序中说:“韶初使君博极群书,风采如高冈风,珠玑如万斛泉,重振大雅,苦心构句,烂乎如金谷之芳春,萧然若山阴之欲秋……。”他的诗作意境高远,清新流丽,诗中有画,颇有唐代王维之风。如《山居》组诗中不乏佳句:“静约烟箩月,残霞未敛红”,“对云觅好句,临风认欢容,鸟语杂分籁,溪烟淡著松”,“水落添清响,樵吟送远腔”等等。田舜年不仅创作丰瞻,而且还有自己的创作审美观点,这在他给三个诗集所作的“序”中明确反映出来。他认为诗要有“自然之律吕”,要有真实的生活感受为基础,“十五《国》风,大都井里士女信口赠贻之物,今咸为经”,而不能“果若人言,绳趋尺步”。他还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因地域差异而受到文化上的阻碍,“清庙明堂之上有传书,崇山大谷之间亦有传人,其势恒足以相埒。”创作上应是“异地而神交,旷世而相感”,有着共同的审美感受。在这里,他对自己民族作家群的创作成就是很自信的,认为少数民族不必妄自菲薄,而事实上田氏作家群的创作成就也足以为世人所称道。田舜年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观点无疑是土家族文学理论的发端。
从这一时期土家族文人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看,多是诗词,极少散文。这与土家族喜好歌谣的民族文化传统有关。民间歌谣的创作为文人诗词的产生在韵律、格调、语言以及表现手法上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民间的歌谣艺术无疑对文人诗词的产生起到了良好的熏陶。从土司作家群众多文人的诗词作品来看,意境悠远,格调清新,音韵和谐,节奏铿锵,对仗工整,格律严谨,技巧娴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受到了同时代汉族文士的高度评价。土司时期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程度由此可略见一斑。
以上可见,在汉文化强力影响下的文化背景中,土家族文人文学应运而生。它一开始就以阵容整齐、令人瞩目的作家群登上文坛,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唱和,成就蔚为可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虽也产生过一些家族作家群如三曹、三苏等,但他们多是中原名门望族,且身居高位。而象冉氏、田氏土司家族作家群这样历时之久、人数之多、创作甚丰的作家群,则是产生在人们视为“不通教化”的“边徼之地”,产生在人们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之中,这就具有了特殊意义,也特别难能可贵。这不仅在土家族文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们的产生,标志着土家人在文化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标志着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进入了空前深入的历史阶级,标志着土家族文学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这时起,土家族文学便从单一的民间文学形式和狭窄的地域中超越出来,真正步入了审美艺术的殿堂,真正登上了中国文坛。这对后世土家族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土司时期是土家族文学的一个空前发展时期。这时的民间文学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空前广泛深刻,阶级斗争意识明朗,思想性有了很大提高,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文人作品则反映了汉文化的良好熏陶,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二者相映成辉,引人注目地昭示着土家族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取得的丰厚实绩,同时也为本民族后世的文学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