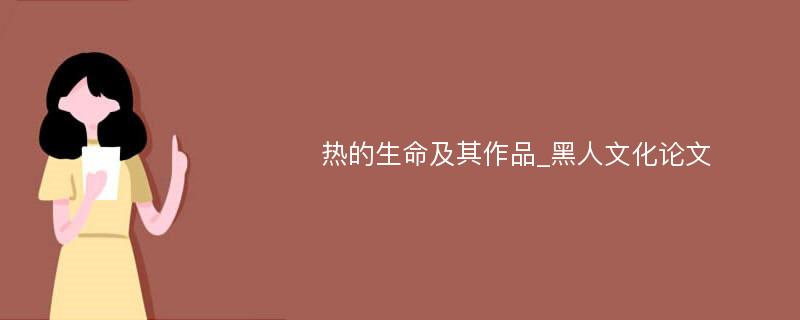
让#183;热内的生平及其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五十年代初期,鉴于战后的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法国不少前卫的或被称做先锋派的戏剧家视当代人生的荒诞性极为广阔。于是,以下这四位国籍不同的剧作家——原籍俄罗斯高加索的阿·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1907—1970)、法国的让-路易·巴洛(Jean-Louis Barrault,1910-1994)和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以及原籍罗马尼亚、 母亲是法国人的尤金·尤涅斯库(Eugène Ionesco,1912-1994),成为荒诞派戏剧的大师。他们的戏剧创作手法以及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下面我主要介绍过去我因为找不到翔实的资料而介绍得极不详尽的热内。1996年春,我应法国文化部邀请赴巴黎学者访问期间,有机会在那里接触到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他详尽的悲惨不幸之一生,并重新研究了他的代表作品。
让·热内生下后并不知谁是他的父亲,他的生母在他几个月大时就撒手人寰。可以说,他既是个弃儿又是一个孤儿。但是,人间毕竟还有真情在,他的养母很爱他。当他在小学读书时,他的功课很好,名列前茅,经常得到老师们的表扬。他的拉丁文学得尤其出色,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优秀生;同时他还在天主教圣诗班唱歌,并且歌声优美动听。但是,教堂的神父不给圣诗班的孩子们发钱,热内抗议,领头带着圣诗班的童声合唱部罢唱,神父则无可奈何。在他十岁那年,他被控告行窃,于是不幸的他被关进教养院,前后竟长达整整10个年头。
《花之圣母》是热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其中他主要描写了他的一位同学。1924年,热内来到巴黎附近上学,他不喜欢那所学校,当年就离校出走,那年他才13岁。他跑到了地中海边上的旅游胜地——兰色海岸之美丽怡人的尼斯城,但不幸却被遣返回原地读书。他15岁时,有一位医生发现他神经系统不大正常。1926年他独自去马赛,又被送回巴黎。不久,他再次出走,登上去波尔多的火车,不买车票,四处流浪。同年他又因没买车票就上了火车,在巴黎被警方以犯流浪罪而拘留。后来,不知他用什么办法弄到了180法朗,再度出走。 但是因为他尚未成人,还要受社会监护,3个月之后他才重新获得了自由。他总想出走, 再次又于火车上被捕。他被当局视为是犯有轻罪的少年,在监狱里被关了整整两年半。
不幸的热内属于特殊儿童。1920年他年仅10岁时就和将近六百名同龄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只要稍犯错误就会受到无比严厉的惩罚,每天还被迫要做长时间的祈祷。
热内18岁那年,他终于从孤儿院逃了出来。他十分喜欢旅行,还参了军。他开始有了自信心,觉得自己已经被视为是一个男子汉了。1931年,他离开军队,去了当年的法属北非殖民地摩洛哥,后来他又到卡萨布兰卡给卜投(Bouteau)将军当秘书。他先在摩洛哥工作, 后来又去了中部非洲,还去过西班牙,再步行穿过法兰西全境。他曾经写道,自己毕生都应在旅行中度过,但是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还希望有钱。然而,不幸的他却分文无有,因为他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当他到了西班牙名城巴塞罗纳时,竟然感到自己孤寂无比。他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里,他从一座城市徒步旅行到另一座城市,有时还在街头乞讨,在穷困街区居住或者索性露宿街头,生活困苦无比,甚至还在教堂里行过窃。
1934年,热内返回法国,此时他第三次参军,被派遣到法属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当兵。当兵必须满四年,但是他又一次于半途中逃跑了。前前后后,他一共当过六年兵。此后,他返回欧洲到处流浪,去过东欧的捷克,还给一位他倾心的女士写过信,又去了波兰流浪。他寄期望于那位女士能爱上他,向她大献殷勤,但对方却自始至终无动于衷。
1937年,热内返回法国。抵达巴黎之后曾经在某大商场行窃,当即被捕并被关进监狱整整一年。次年,他被遣送到马赛,警方认为他神经不正常,因偷饮料又被关入监狱两个月之久。因他经常乘火车到处流浪,后又在巴黎被捕。再度出狱后,热内在欧洲多国到处流浪,用的是一个假的军人证明。
此后,热内在监狱里写的小说陆陆续续出版了。然而,这位不幸的小偷作家仍因为多次犯流浪罪而被关进监狱,等于和牢狱结下了不解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1940年,热内又在巴黎的书店里犯了偷书罪而被捕入狱,时间竟然长达8个月。 聪明过人的热内毕竟是一位奇才,首次读过他的书的人竟是一位书商,而且热内曾先后在该书商的书店里陆陆续续偷过他5本书! 这位书商还发现热内曾因在巴黎圣母院桥边的一家店铺里因偷过衣料而被捕入狱整整3个月, 出狱后又再次入狱!
热内被捕时,他曾断断续续在多座不同的监狱里写过许多诗篇。尽管他一座座监狱进进出出,但睿智的他毕竟才华横溢,确实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法国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科克托 ( Jean Cocteau,1889—1963)非常欣赏热内的诗歌和他的小说《花之圣母》。然而,科克托首次阅读他的《花之圣母》时并没有赞赏这部作品,但是在他们俩相识之后,他再次阅读热内的手稿时则十分赏识后者的才华。许多人在阅读这部长达三百页的小说《花之圣母》时,仅仅看出此书的一些色情描写,但是却不明白其深刻性,原因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热内自幼童至青年时期的那种坎坷贫困孤苦无依的不幸生活与心境。科克托阅毕这部杰出的手稿之后,对热内的才华倍加赞赏,另眼相看。许多人认为这部长达三百余页的《花之圣母》属于色情文学,其实不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明白或悟出一个“槛外人”的热内之作品的深刻性。
1943年,热内因再度犯偷书罪被捕入狱长达3个月。应该说, 他属于精神不正常的病人之列,何况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剧作家兼小说家呢!科克托院士亲自出庭为热内辩护。热内在法庭上受审的场面宛如中世纪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受审时一样地轰动。法官审问他何以偷书,热内的回答振振有辞,即他因为深知该书有价值所以才拿它来阅读。法官对他亦无可奈何。
科克托在为热内作证时,他说如果逮捕热内,那么就是抓了“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此后,爱才的科克托经常接济热内,给他钱用。但是,竟然有一天,热内把科克托的书也偷走了!
热内的身体越来越坏,然而他的精神却始终在思想领域里自由翱翔。他在狱中每天要纸要笔从事写作。尽管处在极其吵闹的恶劣环境里,他照样能聚精会神、无视一切地专心创作。应该承认,他确实是一位思维敏捷、聪慧过人的诗人兼剧作家。
1983年,73岁高龄的热内再度被捕,又被关进了精神病犯人的监狱。他希望能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写的《花之圣母》这部作品,以期能够得到版税,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幸运的是热内这位20世纪法国文坛和剧坛的奇才,得到了当代大文豪萨特等人的认可和推崇。萨特还为他的作品全集写序言,指出热内理性上的不幸与悲哀在于他在为全人类处境的悲惨而呼号,而他所要的仅仅是战胜寄居於他心灵深处并自始至终紧紧地攫住他的那些魔鬼。
热内的戏剧处女作《女仆》(1954)、《阳台》(1956,於1960年首演)、《屏风》(1961)的问世以及首演均强烈地激起过剧坛、文坛以及评论界的一场又一场骚动或风波。理由即他的作品实际上被视为冲击了当时在法国盛行的“介入文学”。热内这位毕生潦倒的剧作家、作家兼诗人,在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史、戏剧史上仍然有着他的一席之地,尽管他本人是一位因犯有轻罪而多次被关押入狱的犯人。
热内的早期作品为一首哀歌《死囚》,那是他被关押在弗赖涅的监狱时写的作品,时间应为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际。此后,他开始创作小说,或者不如说那是些以散文体形式出现的诗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花之圣母》(於1942年由健康出版社出版)。他还创作了《葬礼的盛大仪式》、《布列斯特的争吵》以及他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
1947年,热内开始涉猎戏剧创作。他的戏剧处女作为《女仆》,这部戏於同年由法国著名导演路易·茹维(Louis Jouvet,1887—1951)於巴黎雅典娜剧院首演。《女仆》的演出惹起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观众无一例外,众口同声一致谴责这是一部可耻的、引起公愤的龌龊之作,于是只得停演。1954年,这部戏在巴黎余舍特剧院再度由女导演塔妮娅·巴拉硕娃(Tania Balachova)执导。1961年, 第三次由当代法国著名导演让-马利·赛罗(Jean-Marie Serreau,1915—)於巴黎的奥德雍-法兰西剧院演出。
1949年,热内之新作独幕剧《高度监视》於巴黎马杜兰剧院首演。之后,热内宣布他要摆脱戏剧创作。然而,他仍然回到戏剧上来了,因为这毕竟是他挚爱的艺术。1957年,他的新作《阳台》於英国伦敦之艺术戏剧俱乐部里在极其少数的有限观众面前首演。又于1960年在巴黎体育馆再度上演,由举世闻名之英国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1925—)执导,十分成功。
1959年,《黑人》由法国导演罗吉·布兰(Roger Blin,1907 —1984)执导。首演式为10月29日,这一天被视为是欧洲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布兰启用的演员是一群来自非洲格里奥部族的黑人演员,舞台美术设计师是安德烈·阿卡尔(Andre Aquart)。他们的通力合作使得这部荒诞派剧作的演出成为50年代的巴黎前卫艺术之最为标新立异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於观剧之后曾经说道:“这是人的存在与表象,以及幻想和现实的回旋。”实际上,这出由黑人演员们饰演的黑人是在向黑人展示白人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在舞台上扮演白人的演员们实际上全是戴上了白人面具的黑人。这出戏可以说是在一个灵柩台子前演出的,在台子上面摆着的是被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强奸并且杀死了的白种女人。
然而,这纯属子虚乌有,在这部戏结尾时,黑人演员们对舞台上的伪白人施加以一场伪屠杀。这意味着热内所追求的所谓仪式,它仅仅只是这个仪式自身而已。这场一切都是幻影与假象的戏剧,旨在转移观剧的白人观众对在暗处或幕后表演之故事情节的视线。可以说,热内的戏剧要向台下的观众展示的仅仅是戏剧自身的戏剧性——它就是人类所处的社会条件之真实状态。
让·热内曾於他的《小偷日记》中写道:“我的懒惰和我的梦幻,把我引到了设在梅特莱的轻罪犯人改造所,我在那里一直呆到了‘21岁’。我从那里逃了出来,然后我参军,为的是终于可以当兵入伍还能够得到津贴。没过几天,我偷了几位黑人军官的皮箱就逃跑了。我曾经一度以偷窃为生,然而卖淫则更符合我懒惰的性格。那时,我年仅20岁。”热内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尽管他的语言往往有如垃圾一般地龌龊,却同时又对戏剧有着高度的认识与理解,是一位完完全全摆脱掉了鄙俗的剧作家。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
热内的剧作《高度监视》描绘的是呆在监狱里服刑的同性恋犯人。他们是几个非常俊美的男囚,其中之一的绰号是绿眼睛;还有高大体面的勒佛朗,以及小巧玲珑又漂亮俊美的牟利斯。绿眼睛因犯杀人罪已被判处了死刑,并且不久即将执行。惯偷勒佛朗掐死了牟利斯。绿眼睛存心犯罪,因此心甘情愿去死。最终只剩下了勒佛朗,他重新跌入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
《女仆》是热内专门描绘仆人心境的剧作。在一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房间里,后者搧了她的女主人一记耳光。但这仅仅是在做游戏,原来克莱尔是在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她的妹妹索朗日则饰演克莱尔。这是她们姊妹二人每逢女主人外出时都要玩的游戏,为的是发泄她们的反抗意识,因为她俩同样痛恨和瞧不起她们那位年轻貌美、有财有势的女主人。尽管女主人对待她们很客气,但是却把她们俩当做物品来看待。为此,她们无比地憎恨“夫人”,还给警察局写过匿名信控告“夫人”的情人曾经被捕过。然而,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当只有她俩在家时,她们就以此“仪式”为游戏,克莱尔饰夫人,索朗日饰女仆。最终则成为假戏真做,索朗日竟然承认,是她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姐姐。
后来,让·热内於1963年曾经承认:“当我创作这部戏时,我讨厌我自己,甚至还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什么样儿的人。我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使观众席里的看客们都感觉到他们亦为此而不好受。”
热内自诩他的《阳台》为一部“颂扬反射的图像之作”。其具体内容为:在一座教堂的圣器室里,一位主教“头戴主教帽、身披宗教礼仪用之金色长袍”正在发表热忱虔诚的演讲。错了!这恰恰是个假象!其实他只不过是个煤气工人,他是被依尔玛夫人主持掌管的这家“大阳台”里的种种幻觉迷惑住了。这里的一切都布置得既精巧又雅致,来到此地的那些化了妆的客人们人人皆可充分满足他们朝思暮念的飞黄腾达之美梦,以及他们拟定之巧取豪夺的欲念,还有他们那种种施虐狂的怪诞想法。在进行忏悔和宽恕人们罪过的主教身边,有着沉溺於被告呼叫的法官,还有着乐於光荣地死去之将军们诸色人等。
然而,在这个大阳台之外,热内构想的恰恰是大独裁者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那里即将爆发革命,革命者们的首领是罗吉,他是一位曾经在大阳台干过活儿的铅管工人。反革命的首领是警察局长,他还是伊尔玛夫人的情夫,并且和她同为她住所的共同房主。忽然传说王宫发生了爆炸,女王和她的随从们全体同归於尽。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扼杀革命来欺骗民众并传播假新闻:依尔玛夫人扮演了女王的角色,而她的嫖客们则纷纷饰演了主教、法官和将军等人。
这场革命被制服了。然而,扮演成主教、法官、将军的这些人物却自诩他们确实夺取了政权,再也不会放弃他们的这个梦幻。此时,被打败的反抗者们之首领罗吉来找依尔玛,他期望能成为极权国家的警察总监。当他得知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他阉割了自己。最后他被埋葬於这座梦幻之家的一座陵墓里,而他本人的图像则会由镜子之永恒的反射而长存。原因在于这一切不过仅仅是个骗局,是荒诞,是一场徒劳无功的纠缠。理由是这个宇宙所认可的仅仅是毁灭与虚无。
热内在《黑人》这部戏里的前言中写道:他的一位朋友曾要求他创作一部完全由黑人演员们饰演的戏剧作品,他接受了。他的意图在於他打算通过这些黑人去表现所有被创造的但同时又是被放逐的人们。他们这些人尽管活着,但是却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不过是一些“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边缘人”,就像是“辉煌亮丽的人们之影子或是其反面”。热内还特殊强调,这部戏应该仅仅演出给白人观众看。《黑人》应该是一出“滑稽戏”,或者像是一场“进行严厉谴责的悲剧”,而且它还没有任何行动。在这部戏里,仅仅展示一群黑人演员通过表演对一个白人妇女举行死刑的仪式,把灵柩台停放在舞台的正中间,来满足他们受白人欺压奴役之复仇的梦想,这场演出应该由别的黑人坐在楼座上并且俗不可耐地都化妆成为白人来观看,还要表现出白人在殖民压迫制度下的虚伪和法利赛人式地那种伪善。
在观赏完毕这场表演之后,女王陛下和她的宫廷随员们一同去了她的殖民地。她率领他们到原始森林里去的用意在於她要惩罚的是她的黑人民众。不料黑人的女王却百分之百地战胜了白人的女王。这部戏以黑人演员们跳小步舞结束了全剧的演出。全体宫廷成员们取下了他们的面具,此刻,该剧的导演阿尔施巴德向演员们致答谢辞。他说:“表演结束了,你们该消失了。……你们出色地饰演了各自的角色。”这意味着热内有意识地把《黑人》这部戏以化妆舞会的形式搬上舞台,目的是要有一个间离效果,以期使观众不以为这会涉及到殖民主义和有色人种间的微秒问题。
热内的下一部戏《屏风》是一部半史诗性、半梦幻式的剧作。它由17场戏组成, 共有上百位演员在露天舞台上演出。 《屏风》这部戏於1966年在法兰西剧院首演。当时正是阿尔及利亚进行反对宗主国法兰西、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战争年代。《屏风》的舞台由层层叠起的四层舞台面组成。所有的屏风都可以由演员们直接移动,这些屏风上面绘有所要表现之物品及风景。换言之,也就是按照剧情发展的需要随时更换布景。这意味着热内要在人们的良知面前,用这些“屏风”来掩饰人类那些可耻的感情、伪装以及借口。
实际上,这部戏是在影射当时法属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屏风》的核心人物是赛依德,他是一个不幸而又可怜的当地老百姓。他的老婆莱依拉是全国最丑的女子,因为赛依德最穷,所以他只能娶最丑的女人为妻。
参加阿拉伯抵抗运动的一位成员席·斯利曼尼被欧洲殖民者杀了,这激起了当地百姓们的愤怒。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全体掀起了强烈的抵抗运动。战争爆发了,无处不是恐怖与残暴,杀人,剖腹,开膛,挖心,肢解……无所不为。最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殖民主义者与被迫害奴役屠杀的阿拉伯人和当地不同部族的黑人纷纷攀登到了舞台顶层的屏风处,那里就是死亡的王国。最后,敌对双方均发现胜利者就是这块土地上原来的真正主人——阿拉伯人。
热内的这部戏是在颂扬阿尔及利亚人民为独立战争做出的奋斗与牺牲。他所指控的乃是人类自身的荒诞、虚伪、盲目、狂热的一面。他在这部戏里用了极其优美的文学语言,同时又插进去各种各样下流的脏话以表现善与恶的殊死搏斗。
可以说, 让·热内与法国的残酷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Artaud,1896—1948)有着不少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两位都十分厌恶西方戏剧。热内说过:“甚至西方最优美的戏剧也使我产生一种肮脏的感觉。在舞台上展示的情节总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他的观点是:戏剧应当是人与人之间最高尚最优雅的交流,它理当和东方一样地建筑在仪式或典礼之上,而演员们应当是这种宗教的神职人员,观众则是他们的虔诚的教徒。
热内还说过:“当代最高级的戏剧就是两千年以来每天清晨在教堂里举行的弥撒仪式。……它永远使得我们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然而,热内每次於舞台上树起的弥撒祭礼仪式却总是一场黑色的弥撒。他的每一部戏无一不像是一场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而且都是让参加演出的演员们宛如圣徒们歌颂真善美一般虔诚地、激动地去讴歌假恶丑,而这恰恰就是热内戏剧的实质。
热内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擅长於借助镜子的游戏和反光的折射,来展现现世人间的一切均不过是幻觉、是谎言、是恶梦而已。在他眼里,他认为我们以为是真实情况的事实其实不过是个表象而已,而且它将会再次去覆盖另外一个假象。这就有如让- 保罗·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大师所说过的那样:“最后的表象使所有其他的表现都不能够实现。”
在热内创作的人物中,有相当数目的人物恰巧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是他们的影像或倒影。在《阳台》里,刽子手和被告是法官的镜子;在《黑人》里,黑人能够生存并活在世上来自於白人幻觉的恩赐。在《女仆》里,她们俩人都在另一个人的存在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并用她的方式去思维,而且她们还在对方的影像里看到了她们的女主人的影像。于是乎,舞台上所呈现的一切无一不是最为虚假的假象而已。
总之,让·热内在反戏剧的剧作家行列里,充其量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形象。他对自己笔下产生的人物从来不进行心理分析,但是他却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思想行为或心理观念。另外,他的舞台语言既不僵化也不荒诞。
可以说,让·热内所接受的新戏剧观念是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戏剧观念与结构手法,他所要真正表现的是人的不幸与苦难,是人的处境之孤独以及他所依附的价值自身的虚无。这就是在荒诞派戏剧家中,因自己遭遇过最多苦难的热内之毕生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