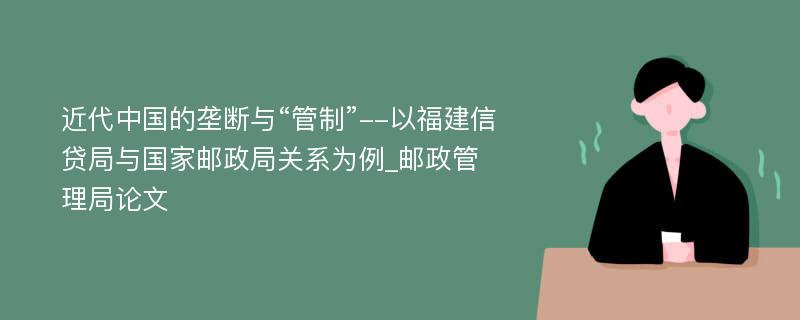
中国近代的垄断与“规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规制论文,邮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F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5-0101-07
自20世纪90年代始,学界对垄断产业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大多从政府或规制机构等“公”的层面介入,主要关注规制者和垄断企业的关系、解决措施及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对垄断企业与行业内非垄断企业之间关系的探讨存在不足,而且忽视社会民间团体和消费者对垄断企业的“规制”作用。本文以1928-1949年国营邮局与福建批信局① 的关系为例,从历史经验探讨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可行性,以及社会民间力量对垄断企业的“规制”。②
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由美国学者鲍莫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假设:(1)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与现有企业相比,潜在进入者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成本等方面不存在劣势;(2)潜在进入者能够根据现有企业的价格水平评价进入市场的盈利性;(3)潜在进入者能够采取“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自由进出市场,有利可图就进入市场,无利可图就撤退。由于不存在任何沉淀成本,因而企业也不存在退出市场的障碍。潜在企业进出市场可以完全自由,因而可形成近乎完全的可竞争市场,潜在进入是约束垄断压力的强有力手段,尤其是交叉领域,可竞争市场不存在任何超额利润,垄断行业会被迫消除生产和管理上的低效率,成为有效率的垄断,国家干预和治理就没有必要。[1] 可竞争市场理论为探索政府规制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它突出沉淀成本、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重要性,强调潜在竞争对促进产业效率的积极作用。该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批评主要集中于假设部分,尤其是沉淀成本为零的假设,认为它不符合实际,存在很大局限性。[2]
批信局主要经营华侨及眷属的汇款与信件,随款信件多无详细地址和具体收信人姓名,邮局根本无法寄递;此外还提供上门收送信款、AI写作信件等服务,形成“帮号”制、三盘制等特殊经营制度。[3] 由于各种原因,邮政总局1934年取缔民信局时保留批信局,允许其“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4] 311因此,国营邮局虽然处于垄断地位,但不能取缔批信局、将其彻底驱出侨批市场,这为可竞争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福建侨批市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首先,侨批市场进入壁垒低,批信局可以自由进入。批信局“非一种买卖之营业性质,纯系一种传递之性质,全属于有限之劳力代价,亦无资本之必要”,“以挑夫计”。[5] 406批信局对资本和技术要求都不高,营业全凭个人信用,只要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和信用便可筹办。[6] 475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信局收取他人资金而代送至乡里,因此自己不需要特别的资金。”[7] 8720世纪30年代王家云调查显示,每家批信局资本约700至1000元,17家平均资本只有871元。[8] 由此可知,侨批市场进入壁垒极低,潜在业者随时可以进入市场。
其次,侨批业利润丰厚。利润包括侨汇收益和邮资收益,前者是主要来源。侨汇收益包括手续费、汇率、运用侨款以及山票等收益。由东南亚至厦门的信汇一般收0.8%的手续费,票汇不足 0.1%,经厦门转汇费约为2%-3%;批信局更注重汇率,通过汇率差赚取利润,这是最大宗收入,远超过手续费;[9] 17兼营进出口业务或期货交易的收益;将侨眷低息或无息存款转存银行或贷给企业,银行利息足够内地分局的日常费用,若贷给工商业者收益更丰厚;[10] 福建批信局还发行没有资金保证、在市场流通并具有货币功能的山票获利,如晋江捷兴等批信局每家资本从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但发行的私票却有数万甚至近十万。[11] 除侨汇收益外,批信局还有少量邮资收益。
最后,沉淀成本少,批信局可以自由退出市场。批信局规模较小,员工不多,组织结构简单。批信局以天一局规模最大,鼎盛时总分局33个,雇用职员556人,其中国内163人,国外393人[12] 176,每局平均人数也不过17人。30年代晋江批信局员工最多的为45人,最少的仅2人。[8] 组织结构也非常简单,一般而言,批信局有负责招揽业务并与他局往来的经理一人、负责出纳与会计的管柜一人、专司带送厦门至内地信件或汇款的跑街一人、负责登记信件数目及其他事宜的伙友及学徒数人。[13] 内地分局多由商店兼营,人员也多由商店人员兼任,最多另设司账一名,雇用几名信差。[14] 71有些批信局甚至只按邮路雇用派送员(差头),信差由差头自己招募,信局不付工资。[9] 103由于沉淀成本极低,业者退出市场损失非常小,无利可图时随时可以退出市场。
以上分析表明,侨批市场已形成可竞争市场,从福建批信局数量和更新频繁度也可见一斑。 1931-1949年,福建全省批信局总号最少也有97家(1945年),最多达255家(1931年),其他年份都在110家以上(除1944年99家)[4] 361,若计分号更多,最多时达2469家(1946年)。[15] 另外还有很多家没有登记或借用他局牌照营业,厦门1949年无照经营达30多家。[16] 另外,批信局更新频繁,多在十年以内,超过二十年的甚少,短的仅一年。[17] 21-22因此,批信局可以采取“打了就跑”策略与邮局周旋,进退自如,从而实现对国营邮局的“规制”。
邮政总局虽然允许批信局继续存在,但并未放弃彻底取缔之心,而是加强管制,极力限制其发展,“采用逐渐取缔办法,以期其自归消灭”[4] 341,实现国营邮局的完全独占。批信局也动用各方面力量周旋,邮局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规制”,独占企图并未实现。总体而言,国家邮局与批信局的冲突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进入壁垒
国营邮局试图通过严格执照管理、限制执照颁发来提高进入壁垒,以此遏制批信局。1930年,邮政总局颁布《民信局挂号暂行办法》,各批信局必须于该年年底前到邮局挂号领取执照,此后每年换发新照,并停止发放新开业牌照。[18] 211由于各种因素,领照时间又顺延一年。由于很多地方邮局根本无法满足服务要求,邮政总局不得不让步,“未设有邮务局或信柜,或其他为村镇信差投递所不及,准暂由民局自行寄递”。[19] 711是项表明,在邮政设施不足之处,邮政总局不得不放宽批信局的经营。在此期间,厦门银信业同业公会曾要求总局完全放开执照申领,不过未获同意。在国内和海外批信局交涉下,邮政总局还是放宽了经营国外侨批业务的登记对象和时间,专营国外侨批业务、在国外设有联号或总号、经当地邮局认可并领有执照可资证明者,国内允许挂号并发给执照,每年一期,补发执照延至1934年底。[4] 312与邮政总局的强硬相比,这些让步已经是侨批业公会与邮政总局交涉的一个突破。其后,申领执照再次顺延一年,总局规定凡新经营批信局者非承顶执照无法开业。[20] 1601935年12月,总局颁布了“批信事务处理办法”,详细规定执照管理办法,如名称、地点、营业人姓名、年龄、籍贯与营业范围,分号及代理人的详细情况,巡视员可以“随时调验”,若停业“应将原领执照缴由该管邮局转呈注销,不得私自转让或顶替”[4] 317,以此提高进入门槛。
虽然邮政总局试图提高进入壁垒,毫无疑问,批信局处于弱势,侨批业者却有各种规避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邮局垄断的“规制”,使其不能如愿。厦门批信局以谎报牌号二度领取执照;有的还没有成立就预先申请执照谋利。[21] 没有执照的潜在业者或购买转让牌照者,或借用同业牌照营业。此外,业者还买通邮局人员给予方便。虽然新牌照停止申请,但旧牌照仍然有效。由于经理人不能更换,有的经理已去世,申请表仍旧填其姓名。[12] 4-5
不少批信局因战争而停业,邮政总局1948年修订“批信事务处理办法”时专门规定“批信局停业已逾一年者不得再请复业”。[4] 350同年三月,邮政总局将核发执照的权力下放给福建省,由省邮局自行决定。[4] 354此后,执照管理更趋严格。批信局虽极为不满,但也无力改变,因而干脆无照经营,仅厦门就有三十多家无照经营,甚至影响到有照批信局的业务,侨批业公会为此还向厦门邮局投诉。然而,厦门邮局调查时发现,无照批信局“多悬牌营业”,“内中则附于已领照之批局作为护符”,批信也装入有执照的批信局信件内寄递,邮局对其“按欠资办理一面予以警告”,但他们“一经警告后即将招牌更换照常营业”,邮局也无可奈何。[4] 347
(二)邮资、分号、自带信件等具体业务冲突
其一,邮资问题。由于总包制、按重收费和国际邮资半价优惠,批信局能获取部分邮资收益。邮政总局多次提高邮资,以1933年邮资改革最艰难,除提高邮资外,还实行双程收费,贴足国际邮资的批信送往内地须缴纳内地邮资,回信寄往国外时也须缴纳。邮政总局虽然提出汇率变动、东北邮权丧失等诸多理由,局长还亲自解释,还是遭至厦门同业公会和旅京华侨大会的反对。厦门侨批业公会先后与外交部、行政院、交通部、上海邮政总局等各中央机构交涉;旅京华侨召开大会,痛陈民情,强烈反对增加邮资。[22] 这些运动反响甚大,不过新邮资标准还是按期实施,但对1947年邮资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7年,邮政总局决定邮资改革,改变了先前单方制定政策的做法,而是先与厦门市华侨银信业同业公会协商,达成共识后才提高邮资。自1947年7月起,总包制(按总重收费)取消,实行按件收费;允许批信局总分号间的进口批信按件数80%缴纳双程邮资后领回自带(后定为89%),回信也可由批信局自带回总号,由总号汇成总包交邮局寄递,这改变了过去总分号间的批信与回信必须由邮局寄递的规定。[23] 邮政总局以邮资优惠和批信自带换取批信局让步,从而取缔了延续多年的总包制,实行按件计费。不过,批信局并不愿意,其后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会长林树彦回国调查侨汇时,就提出恢复按重收费,被总局拒绝。[23]
其二,分号问题。1948年,邮政总局开始限制分号设立,国外批信局不得在国内增设分号,只能委托有执照的国内局为分号,“以粤闽两省内各批信局现已呈准设立分号之所在地为限”;国内批信局“不得在国外添设分号”,已经存在者暂时维持现状。[4] 350此举遭致厦门、泰国、新加坡等地汇业公会和中华总商会反对,他们纷纷向国民党各部门致电致函要求撤消,中央侨务委员会也出面交涉,要求允许未申报者追补登记,均遭拒绝。[4] 3581949年8月,邮政总局更规定更换或添设经理人要受邮局节制,营业人如有亡故或申请将业务转交他人接办时,接办人只限于法定继承人。[24] 52-53
其三,自带批信。此项存在争议最大,充分体现了批信局等私营行业及组织对邮局的“规制”作用。1935年,福建邮政管理局规定,东南亚各地发来的批信“逐封贴有国际邮资”后“准予自行携往内地投送”,“至于内地之批信局分号所收揽之侨民家属回批,亦不得自行带送来厦,仍应照纳国内包封邮资后,交内地邮局发来思明邮局转给各该批信局总局收领。如批信局自行带运回批在轮船、汽车及码头等处查获者,即作走私论。”[25] 由于厦门银信业同业公会强烈反对,而且汕头邮局允许有执照的批信局“能自行派人带递者,不加限制”,“其不能自带者,可在内地添设分号”[25],省邮管局还是允许批信局自带信件。
1946年7月,邮政总局一改战前宽松政策,要求总分号之间的信函均应纳足邮资交邮局寄递,“凡未经邮局盖戳之批信或回批,无论贴足邮票与否,均不得私行递送或投递,一经缉获,概按走私论罚”;邮政总局还增加了许多繁琐手续,进口批信要在邮局“当面开拆加盖邮戳”,总分号间的总包必须由当地邮局“重行逐一盖戳,作为确系交邮寄递之凭证”。[4] 345两次开拆并逐一加盖邮戳大大减缓了寄递速度,削弱了批信局的快捷优势。厦门市华侨银信业公会迅速向省邮局交涉,认为此举改变了战前惯例,对批信局极为不利;泉州等地“邮局狃于戳售邮票之恶习,对各批信局自带之贴足国际邮资侨信妄指为走私,无理刁剔,横加阻梗”;[4] 346还联合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汇业公会声援,阻止邮局实施。最后,交通部和邮政总局综合各方面意见,允许批信局在“当地邮政局所投递界以内者自行派人带送批信及回批”,“不在当地邮政局所投递界以内者,概应纳费交邮寄递,批信局不得擅自派人带送”,而且自带的批信不能享受总包优惠,若批信到达的地方没有批信局分号,批信局应将批信缴费后交邮局寄递,然后派人领取就地投送,收取的回批也应缴费,由该地邮局寄回总号。如有必要,批信局可以指定专人派送批信,但此人必须持有邮局颁发的证明文件(贴相片)。[26]
1947年,厦门同业公会请林树彦再与总局交涉,要求回信自带,被一口拒绝。不过,总局提出了替代方案:厦门批信局一致同意要求自带分发,并由厦门同业公会提交申请,担保“决不走私”,邮局可以允许自带。[23] 1947年邮资改革后,自带批信争端才彻底解决。
(三)走私标准与处罚的争议
邮局不断扩大查缉权力,如以前对信函并无搜查权,后以防止夹带、匿报和走漏邮资为由,对批信随时随地开验。华侨常在书信中为他人捎带短信及款项回国,分号也常会在回信中夹短信缴还总号。1937年,厦门邮局严厉查处,一旦发现便扣留、处罚或吊销营业执照。厦门和新加坡侨批业同业公会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少量夹带为华侨习惯,不足以构成走私,而且处罚过严,因而纷纷提出控诉,并在报纸上攻击厦门邮局“违法处罚”,厦门邮局最后不得不同意“夹带、匿报不超过五封,免予处罚”。邮政总局获悉后,收回了福建地方邮局吊销执照的权力,责令此后类似事宜呈报总局核夺,并规定走私次数改按年度计算,即隔年不计。[24] 46在各方面压力下,邮政部门被迫做出让步。
抗战胜利后批信走私更频繁,“厦门信局走私几无日无之”,1946年马尼拉侨批业同业公会托菲厦线试航飞机代运批信,许多批信局竞设法利用该机返程偷运回批,晋江仅破获一家就达数千件之多。[24] 42走私花样层出不穷,如报刊中夹寄或伪装成私人信函由普通或航空寄递,或夹带、匿报批信数目等透漏邮资,战后又“创造”一种变相回批的走私方式:采用“即刷单式”及“汇票单据”代替回批,以此免纳邮资。邮政总局随即规定此类单据必须逐件照纳邮费。1947年,批信局又仿照银行以票据形式使用“回文单”,不用回批,导致邮局“由外洋寄来的批信已有减少之势”。邮政总局以批信局未领取银行执照为由要挟,劝令其按回批邮资标准逐件贴付邮资,并暗示:如不就范,邮局将向主管机关检举取缔。然而,邮局又担心逼得太紧会使批信局专营汇兑,影响邮政收入,而且回文单并没有通讯性质,邮局只好“劝令”,并未举报。[24] 46批信局并未理会,走私之风更炽。
由上分析可知,邮局和批信局在进入壁垒、邮资、分号、批信自带和走私标准及处罚等方面存在纷争,邮局一直试图削弱批信局的竞争力,限制其发展,最终实现独占局面,但是批信局借助同业公会和海外华侨的支持,维系了自身的生存,进而极力与邮政周旋。国家邮局虽然在邮资、分号和走私处罚等方面达到了目的,但始终未实现取缔批信局的长远目标,而且批信局自带批信、自由进出市场等,对国家邮局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规制”作用。
虽然批信局与国营邮局的竞争并不对称,处于弱势,“规制”作用也相当有限,但有限的“规制”也有积极作用,国营邮局被迫提高经营能力和竞争水平,试图借鉴批信局的经营方法,并借助其发展业务,争取在侨批市场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借鉴批信局经营方式,试图“信款合一”。
信款合一是批信局的优势之一,邮局办理信件寄递,直属邮政总局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汇兑,但并未从事侨汇业务,二者并不能有效协调。1937年2月,邮政总局决定开办侨汇业务,于是事先详细调查批信局的经营办法等,充分借鉴其优势。(1)邮局以批信局总分号及代理处的分布决定营业网点的开设。邮局虽有广泛的营业网络,但经营侨汇还需“添设新处所若干处”,“大半为村镇邮站”,以接近分款地便捷经营。邮局先在较重要村镇试行开设,“并给人员以相当之训练”,“新处所不必一时统行开设”,“虽有时须雇专差投送汇款,然比较上较为经济”。[4] 390(2)邮局雇用批信局人员发展业务。邮局内部对录用批信局人员存在争议,但邮管局从发展业务和减少阻力考虑,决定“择优雇用之,以资熟手”。[4] 391(3)薪资制度。邮局充分借鉴批信局的利润分配方式,按代办人经办侨汇多寡发给保结津贴,比例预先规定。若另雇专差,其费用由代办人自理,邮局不负责。1942年以前,福建省邮政储汇局有侨汇经办正式员工135人,临时工高达301人[27],可见批信局之影响。
其次,借助批信局增加邮政业务,提高邮资收入。
鉴于批信局良好的服务网络,邮局也委托部分批信局为代办点,如天一局等。邮局从侨批寄递中获取了不菲收入,福建省内邮局1947、1948、1949年就从香港和东南亚等地收到批信及回批 2842808、2959135、1405770封。[4] 359另外,从邮局对批信局的政策也可窥之一二。1946-1949年侨汇逃避严重,“国库外汇收入减少,论者每归咎于侨汇之走私,而批信局之大量揽收侨汇尤为各方之攻击目标,每来函请予取缔”;[28] 广大侨胞和侨眷也纷纷致电请求政府采取措施,“以免侨眷遭受损失”。[29] 邮局有此“民意”基础完全可以取缔批信局,但并未施行。1948年11月,厦门侨汇管制委员会取缔批信局,邮局认为“邮资收入将受锐减”。[4] 430这足见邮政总局不取缔批信局之旨趣。
从以上国营邮局与福建批信局的关系分析,本文可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就本文的考察而言,批信局与国家邮局的关系证实了可竞争市场理论具有一定可行性。由于侨批市场进入壁垒低,批信局“进出”完全自由,形成了以国营邮局为主导的可竞争市场。虽然这种可竞争市场存在过度竞争之势,但批信局与国家邮局的确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局面,国家邮政的部分社会职能通过批信局得到较好实施,民众(海外华侨及侨眷)的社会利益也能得到有效保证,国营邮局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也有所提高。在竞争的刺激和压力下,国营邮局试图借鉴批信局的经营方式,同时借助批信局发展邮政业务,提高邮资收入,最终被批信局“俘虏”。但是,由于邮局为国营垄断企业,本身既是企业,又是管理者,因而使二者竞争成效有限,即批信局对国营邮局的“规制”效果有限。批信局的信件收益趋微,还承担双重邮资,实际上是“无偿”为邮局派送批信,只能通过“交叉补贴”补偿成本,即经营侨汇的收益“补贴”批信寄递的损失。邮局此举损害了侨民利益,有效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垄断程度,以较低成本(只有稽查和周转成本)增加了一笔不菲的邮资收入,一定程度缓解了来自批信局的竞争压力,降低了市场竞争的功效。虽然就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而言,国营邮政占据垄断地位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在某些细分行业,如侨批业,由于技术水平低、业务特殊等因素,垄断行业完全可以转变为非垄断行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二,引入社会力量“规制”垄断企业。学界多注重从政府或规制机构层面探讨对垄断企业的限制和改革,将社会力量和消费者作为置于事外、无能为力的“沉默大多数”,纯粹讨论政府或规制机构与垄断产业的关系,忽视了社会民间团体的力量和消费者的重要性,本文的考察充分证实了社会团体和消费者本身的重要性。国家邮局属侨批市场的“后来者”,在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下,试图取缔批信局,以图“独此一家”,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批信局的顾客,即华侨和侨眷支持。虽然国营邮局被迫允许批信局继续存在,但并未放弃取缔之旨,而是采取渐进步骤,通过一系列措施,如提高进入壁垒、提高邮资、限制分号设立和自带批信,以及严厉打击走私、降低其竞争力、增加其经营成本,力图将其“驱出”侨批市场。然而,收效甚微,批信局极力与之周旋,通过交叉补贴维系了自身的运转和发展,并用邮资收益将国营邮局“俘虏”。批信局能有如此绩效离不开同业公会、侨眷和海内外华侨的支持。在同业公会等的支持下,批信局与消费者形成了较好的互动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从而通过团队力量与政府谈判博弈,“规制”垄断者,从而形成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局面。这对今天的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启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上述结论对改革被“俘虏”的规制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垄断企业与政府部门或规制者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牵涉,相互勾结,新进入者如何应对?本文也提供了一种思路: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遏制政府部门或规制者和垄断企业。
注释:
①批信局名称繁多,有“侨批局”、“批信局”、“民信局”等十多种,较正式称呼为“民信局”或“批信局”。所谓侨批,俗称“番批”,闽南语称书信为“批”,回信则称“回批”,侨批指以汇款为主、华侨汇集成批寄回国内的家庭书信。因日本侵略战争,福建侨批业1939年后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结束,故本文不涉及1939-1945年。
②所谓规制,一般指依据一定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进行规制的主体有公共机构和私人两种形式。由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对私人以及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制称为“公的规制”;由私人进行的规制称为“私人规制”。我国经济学界主要从“公”的层面使用“规制”一词,本文的“规制”主要从“私”的层面使用,并用引号以示区别,指私营经济组织或社会团体对垄断企业的限制和制约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