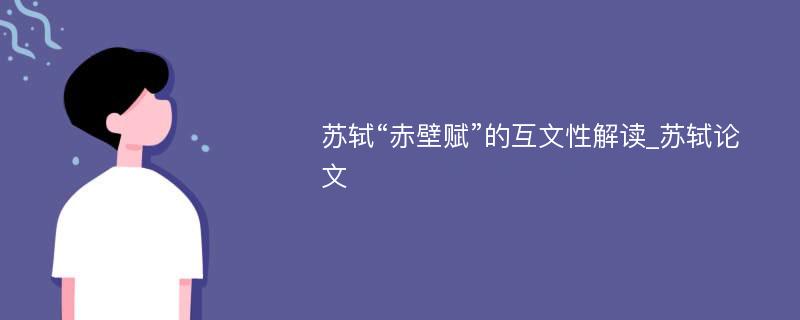
苏轼《赤壁赋》的互文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赤壁赋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轼以夐绝千古的才情受到历代读者的倾慕,其《赤壁赋》更是因高邈难攀的文境而深得后世推崇。对于这篇旷世之作,人们往往读出的是作者超旷的胸襟、缥缈的禅意和随遇而安的“乐观”。这种解读显然是依据“言为心声”的理论,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对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所作的阐释,虽未为不可,却不免有郢书燕说之虞。如果立足于文本本身,从互文性视角重新观照,或许会别有所得。
此处的“互文”非指我国古代“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而是20世纪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文学文本阐释理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法国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①。“这一术语,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echo)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互相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累积的参与等。”②根据这一理论,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独白式封闭体,从创作到接受都要以其他文本作为参照,并会在文本的符号形式形成后成为其他文本的参照体。因此,每一个文本都同其他文本处于相互参照、彼此勾连的互动关系中,从而形成一个潜力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这种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不同文本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每位读者都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会重复出现。比如,钱钟书就曾指出,欧阳修那句著名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与谢朓的“风帘入双燕”、陆龟蒙的“双燕归来始下帘”、冯延巳的“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等诗句具有承续关系。至于“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就更是如此。这种“踵文而非践实,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③的做法其实就是对“互文性”理论的不自觉运用。所谓“互文性”也就是指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所发生的这种关系,它可以是文本内语词、语句、语段间的互文关系,也可以是文本间意象与隐喻层面的语言联系,还可以是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间的文化关联。互文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引语、用典、拼贴、模仿、抄袭等等。它不仅是文本创作的基础,也是阅读体验的基础。
借用这一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互文现象在《赤壁赋》中频频出现,文中有许多对前在文本的引用或模仿,这些被引用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与《赤壁赋》构成了互文关系,而这也为我们探求《赤壁赋》的意旨提供了新视角。
苏轼与好友在初秋月明之夜泛舟赤壁,面对“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江上美景,不禁意兴盎然而“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明月之诗”“窈窕之章”与《诗经》中的《月出》篇存在互文关系。《月出》原诗是:“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是一首古代男子思慕“美人”的恋歌,诗中飘荡着一缕怅惘寥落的幽思。接着,在“月出于东山之上”后,苏轼又“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此处“一苇”又与《诗经》中的《河广》篇构成互文:“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河广》篇里身在异乡的主人公离家并不遥远,却因故无法返回故乡。本诗所表达的是一种深切绵长的思乡之情。
显然,《月出》和《河广》都隐含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式的怀念与忧伤,其情调是低沉、幽怨的。它们与《赤壁赋》互文,便形成意义互为指涉的和谐整体。这样,读者自然会把《月出》与《河广》中落寞惆怅的情思投注到《赤壁赋》中,这便使《赤壁赋》也涂染上了一层哀婉幽怨的色调。
而接下来的“扣舷而歌”则提供了这种怅惘失意的具体内涵。
面对江月美景,苏轼“饮酒乐甚”,进而放声吟唱:“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显然是在有意模仿屈原《九歌·湘君》中的“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和《九章·思美人》中的“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这种仿拟不仅是文辞的相仿,而且是对“楚辞”文学传统的追怀。“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当然不是实写,而是一种象喻,寓托着作者的美政理想。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早就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屈辞与苏轼仿拟二者间的这种互文性,自然会引发读者去领会苏轼笔下的“美人”意象所隐含的“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的象喻性内涵。
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苏轼年轻时便确立了“书剑报国”(《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之二)、“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人生理想。后虽身遭“乌台诗案”,其忠君忧国之志并未改变。在抵达黄州的当天所写的《到黄州谢表》中,苏轼表达了对宋神宗的耿耿忠心:“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门。”其情之忠贞与屈原何其相似乃尔。元丰四年所写的《与滕达道书》中他也表示“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显然,苏轼虽身遭“废弃”,但并未消极颓唐,也没有弃绝世事,忠君用世仍然是他的人生信条。这样看来,“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中所传达的悠游与超然是颇值得怀疑的。表面上看,水天浩淼、明净澄澈的月夜秋江滤尽了世情俗虑,苏轼仿佛进入了一种了无挂碍、逍遥自任的空明境界。但他不可能真的忘记自己的遭遇与处境,也不可能真的“遗世独立”。在对“美人”的吟唱中所深藏的,正是因怀念“圣明天子”所生出的抑郁之情和“忠而被谤”的失意之悲。可见,月夜泛舟的畅快不过是苦中作乐,苏轼只能试图暂时忘掉心中的烦忧。
苦中作乐的苏轼“扣舷而歌”,洞箫客便吹起洞箫“倚歌而和之”,这与《九歌·湘君》再一次构成互文关系,因为《湘君》中的湘夫人也曾“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参差”就是洞箫。西汉王褒的《洞箫赋》中就有“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之句。临风企盼的湘夫人因湘君的爽约而黯然神伤,于是吹起“参差”来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湘君》与《赤壁赋》的这种互文关系,同样引发读者去体味苏轼和洞箫客内心的怨慕、落寞情怀。
对于这位洞箫客,前人早已考证出他就是苏轼的好友杨世昌。这种考证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说似无必要。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洞箫客的出场是为了引出后面的主客问答。众所周知,虚设主客问答来组织篇章,这并非苏轼的首创,而是汉赋惯常的结构形式。这种具有很强的虚构性的文体特征与《赤壁赋》互文,便使苏轼笔下的洞箫客也具有了虚幻性。因此,不妨把“主”与“客”看做是作者心中的两种对立思想,“客”就是虚化了的苏轼自己,主客问答也就是苏轼的内心独白,是他思想矛盾斗争的过程。因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人生感伤、“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生命感叹,这些因世事的难料、个体的渺小、人生的短促所产生的哀痛不属于别人,它们正是苏轼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片阴翳。这也再一次让人窥探到苏轼那潇洒绝尘的“飘飘乎”的背后所深隐的苦闷。
这种苦闷虽源自仕途失意、人生苦短等现实情怀,却又超越了物我得失的思想局限,从而进入到了对天地宇宙的冥思之中。而引发苏轼哲理思考的是“水”和“月”两种意象:“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此以“水”“月”的变幻与恒常喻指人生的短暂与无限,而这一组合意象又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形成互文关系。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营构了一个“江天一色无纤尘”的清明澄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意象就是江(水)和月。在这个世界中,月楼闺思的凡情俗念被作者置于对天地宇宙的诘究之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对江、月意象的观照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于是发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生命质疑,在这种怀疑主义的生命体验中隐含着的是人生苦短的感伤,尽管这感伤并不沉重。为排解这种感伤,作者开始自我劝慰:人生代代延续,没有穷尽;江月年年相伴,从未改变。江(水)、月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同样,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生命又是无限的。面对瞬息万变又亘古长存的天地宇宙,作者试图从无常中祈求恒常,孤高出尘的感伤中便浮生起博大空明的生命体验,而这种生命体验里充溢着一种虽辽远却又寥落的哲理意味。
《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月意象与《赤壁赋》互文,两个文本借此形成互相渗透、互相指涉的关系,《赤壁赋》的意义和感情内涵也就变得丰厚起来。而当《春江花月夜》那轻快的感伤投落到《赤壁赋》与《诗经》、屈辞所构成的意义网络上时,张若虚那轻盈的叹息便化作苏轼的深沉喟叹。借助这一互文关系,人们又一次感受到高蹈绝尘的苏东坡内心深处所深隐着的面对广漠宇宙之时所生出的孤寒之感。
表面上看,苏轼以庄子的相对论观照江、月,这让他消解了物我得失的人生苦闷,获得了超越的精神和力量,但字面上的超旷放达却难掩内心深处的荒凉寂寞。对宇宙永恒的了悟是以对其短暂性的痛苦感受为前提的,正因为有这种痛苦感受,才有摆脱这种痛苦的努力。没有沉迷就没有超越,没有执滞就没有旷达。因此,苏轼的水月高论也就不免有自我劝慰之意。而这种自我劝慰本身就说明作者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心深处的孤寂之感。
被贬黄州后,苏轼没有走向消极沉沦。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帮助他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在与天地宇宙的一次次对话中,作者艰难地完成了对生命的伟大超越,走向胸次的清旷。但超越不是弃绝红尘的超脱,清旷不是无拘无执的逍遥,豁达的胸襟和高远的情志也不意味着对世事的了无挂碍。佛、道思想没有使苏轼脱离人道,清空洒脱的生命诉求也无法让苏轼获得心神的彻底恬适。无论是初到黄州时《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中的“凄怆”,还是比《赤壁赋》稍早的《定风波·咏红梅》中的孤傲、《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感叹,还是比《赤壁赋》稍晚的《后赤壁赋》中的萧瑟、《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的孤寒,所有这些人生苦痛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儒家人生信条的眷恋与持守。
有人说,苏轼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形成了一套“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这种人生哲学使得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文,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一个广博深厚的领域,达到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同化’的新境界。”④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苏轼借助佛老思想排解内心苦闷时表面的逍遥自任,却没有察觉到他悠游后的孤寂,清旷中的苍凉。在苛酷的生存环境下,苏轼暂时搁置了儒家的淑世情怀,但他并没有彻底弃绝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他虽借助佛、道思想来消解心中的苦闷,但这并未使他倒向佛老,成为佛教徒或道教徒,因为他对佛、道思想一直怀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他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而这种批判精神正来自他那种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生命诉求。他知道,只有借助儒家道德人格的支撑,才不至于沦入佛老的懒散颓放。这种对佛老既喜爱又批判的态度表明,苏轼的生命本色仍是源自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积极用世的精神,而这也正是苏轼人生苦闷的真正根源。
正是基于这种无法割舍的儒家情怀,虽借助佛老思想,苏轼也不会“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借用“互文性”理论,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参照中,苏轼的生命底色隐然可见。
注释:
①[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第94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②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73页,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钱钟书《管锥编》第364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④马银华《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