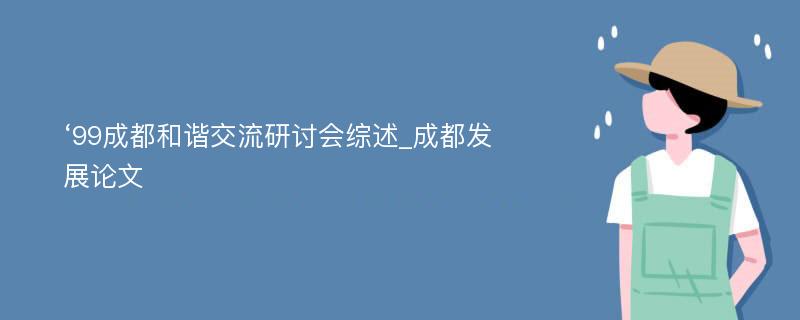
’99成都和谐与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儒学、道学、佛学研究中心主办,法国利氏学社给予合作的“’99成都和谐与交流学术研讨会”,3月29 日至31日在成都举行。来自法国、美国的汉学家和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以“和谐”、“和平”、“交流”为主题,以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海内外学术合作为宗旨,进行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
关于若干基本观念的探讨
古往今来,各国人民都赞美和谐,向往和谐。应当说,“和谐”是一个多义概念,它既可以指相互关系或处世态度,也可以指美学境界或社会状态;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范畴,其内涵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人们的和谐观又与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联。对此,与会学者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德述分析了《周易》中的和合思想,认为它集中表现在阴阳这对范畴之中。易卦十分强调天、地、人的和谐与统一;易卦中包含着各种复杂的联系和关系,具有多元性、异质性、差异性、对待性,同时又具有平衡性、和谐性,因此,易卦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丰富的和合体;易卦之间也具有和合的性质。《周易》所特有的易图(太极图、河图、洛书)是一种阴阳对立、统一、协调的和合图式,揭示了客观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和合性,概括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易传更是包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如中道和合、交泰和合、消息和合、既济和合等,它们与易卦、易图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形成了《周易》和合思想的完整体系。《周易》的和合思想,为和合学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远国指出,在道家、道教的理论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如道法自然的原则、人与天一的理念、三才相盗的思想、贵生戒杀的观点,即是其学说中的精髓。“道法自然”,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这里的“自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法则,是强调道也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人与天一”,揭示了人与大自然的统一性、相互依存性;既然如此,就必须善待自然界,保护生态环境。“三才相盗”,是指天地、万物、人互相“盗取”,彼此利用,其核心是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万物昌盛、天人共安的理想社会。“贵生戒杀”,是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其它生物,都是大自然的杰作;生命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人和万物都在一个共同的天地中共处;在承认人类主观作用的同时,亦否定以人类为中心的自大狂妄态度,承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些思想主张,是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观点不谋而合的。
台湾辅仁大学副教授郭梨华认为,先秦时期诸子针对周文化的衰弊,提出针砭,“和合”则是一种要求与期望。对于“和合”的基础或者根源性的探究,先秦诸子努力的方向大致有三:一是以儒家的宗法、伦理为和合基础的探究,二是以道家负阴抱阳的冲气之“和”为万物生存的基础,三是以墨家强调的“兼爱”作为和合的基础。这三种探究“和合”的方式,是否有一可融通的根源,值得认真研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由于政治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突,道家的“和合”基础观,也许更有益于处理冲突。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方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指出早在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就开始连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用,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在此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进事物的发展。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同时又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和合思想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还介绍了中华和合文化研究的概况。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沈清松认为,“和谐”观念的兴起,是以人的实存经验为基础,同时也指向人所向往的理想存在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必须有和谐才能活下去,但实际上往往只能享有局部的、片断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神的和谐,构成了人存在上的三层和谐。“和谐”的理念应当放在关系的存有论的脉络中分析。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英国圣公会)都属于关系的存有论。人在既冲突又和谐的现实处境中,一方面至少要能“保和持适”,既能适己之适,又能适他者之适,尽量保持局部的和谐;另一方面,更要进而追求充量的和谐。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刘干美认为,和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的层次,二是人际关系的层次,三是全体存在的层次。要达到和谐就必须突破自我。
研究“和谐”,必然要涉及与之相关的“宽容”、“宽恕”、“对话”等概念。对此,一些学者作了积极的探讨。
关于“宽容”。法国社会分析中心研究员杜艾岚根据欧洲的历史,认为文化、宗教、意见的多元性是构成欧洲国家,也是形成整个欧洲的要素,这种多元性所以能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宽容的德行。“宽容”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充实的概念。首先,宽容意味着容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其次,宽容要求人们尽全力去了解他们不同意的事情;第三,宽容指的是承认公开表达自由生存的权利的存在;第四,宽容指对于他人与自己相异的生活方式,拒绝提出理由指责,这实际上是承认有一部分真理自己还不了解,或者是有一部分真理不出于己。作为一种美德,宽容的落实是一段漫长历史的结晶,经历了血与泪的代价。
关于“宽恕”。法国利氏学社主任魏明德认为,宽恕是基于社会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当我拒绝原谅别人时,我也谢绝了让别人原谅我的机会;然而,“谁又敢大言不惭地说他永远不需要别人的宽恕呢?”当一个人发现他需要被宽恕、被了解的根本性需求时,也会决定宽恕他人,了解他人。因此,提出宽恕是为了让大家共同活下去。真正的宽恕是一条漫长、痛苦、不完备的道路,但永远具有创造性,永远在为重新开始作准备。宽恕,就是重新开始,就是创造社会新的关系模式。宽恕的价值需要在既定的文化基础上加以激励、滋养和拓展。一个社会如果欠缺宽恕的精神,这个社会将无法长久延续。一种文化只有明了拓展宽恕价值的重要性,才能有一份开放的态度,再创新的文化契机。美国传播工作者丁松筠认为,宽恕就是承认他人跟自己一样。
关于“对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桂权研究了当代著名思想家玻姆的对话精神,指出玻姆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宽容不同的观点,二是对对话中的共同意义抱有基本兴趣。真正的对话需要具备五个必要条件:共同的语言,平等的对话角色,交往能力,宽容精神和不固执己见,非强制性或自由性。其中,“宽容精神和不固执己见”最难做到;而不固执己见,随时准备接受对方的正确观点尤其难以做到。个人的认识总是有片面性的,为了减少片面性,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通过对话来沟通。这种对话精神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伟大传统,体现了开放精神。开放、融合、进步,这是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哲学、科学、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法国利氏学社研究员狄明德强调,在市场社会中,为了市场能够正常运作,必须让个人能充分参与社会对话,也就是让个人能够在与他人交谈中表达意见。真正的交谈,正是要求对方真实表达自己的看法,容忍别人阐述自己的立场,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别人。
关于和谐与交流的历史体验
和谐与交流不仅是人们的生存需要,也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尽管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征战杀伐,出现过一轮又一轮的改朝换代,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民总是冲破重重障碍,战胜种种困难,努力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并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上达到了和谐。认真回顾和总结这样的历史体验,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万本根、研究员段渝回顾了巴蜀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历史,指出巴蜀文明的诸要素,从总体上来说是独立产生的,并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亚型;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各种因素,巴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间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以至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趋同。从青铜器、古文字、早期城市等文明要素来看,上古巴蜀文化既自成一系,又与中原文化有着某种共同因素,并存在相互影响。在古史传说中,黄帝、黄帝正妃嫘祖、大禹均与古代巴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在古蜀文化来源之一的岷江上游地区,其文化面貌与大禹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关系,三星堆文化的某些因素也同夏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到了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因结构改造而发生转形,同秦汉文化整合起来,同时保持着自身的风格特色而显示出内在的发展连续性。经过长期的互动交融,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才最终合流,成为积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基本成分之一,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新建论述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整合,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历经多次的大动荡、大分化,发生过民族之间的战争和磨擦,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仍然把中华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个凝聚力,就是民族之间因文化交流而产生的认同感、亲近感、和谐感。可以说,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整合以至融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呈现出这样一些规律:(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和谐精神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动力。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向世山指出,儒、释、道三家(古称“三教”)的关系,是中国从汉至清思想界乃至政界一直关注的大问题。三教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调和,还有互摄,呈现出纷繁复杂的交错关系;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走向调和,也就是“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主旋律。回溯三教之间的历史关系,把握住“三教合一”这根线,便能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走向,亦能了解至明清时期正统思想已呈“大团圆”的历史渊源。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分析了“三教会通”的诸种立场、“三教会通”的模式和主题。
法国塞夫尔哲学与神学研究中心负责人贾乐为回顾了欧洲由分裂逐步走向联合,形成欧盟的进程,认为有关国家是在承认矛盾冲突的情况下,通过承认对方,彼此协调和妥协,来达到和解与和平。在这里,宽容精神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共识。不过,欧洲国家至今还存在许多纷争,距真正和谐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与会者认为,尽管当今世界充满着矛盾冲突,但和平与发展却是时代的主题,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努力促进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谐的发展,为人类21世纪新文明的重建作出有益的贡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茂才研究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文明是一种财富。21世纪将是经济全球化程度愈益加深的时代。由经济一体化走向不同文化的沟通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谐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必然趋势。1998年11月4日,联合国第五十三届大会决定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为此,有关方面正在筹建“中国东西方文明研究中心”,加强对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并倡导起草《东方文明发展宣言》,向世界展示东方文明的光辉成就和巨大作用,把东西方文明各自的贡献综合起来,创造新的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本次研讨会的议题与此是相通的,希望中外学者共同关心和支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多学科、跨地区的学术会议,自始至终体现了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和谐精神,取得了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