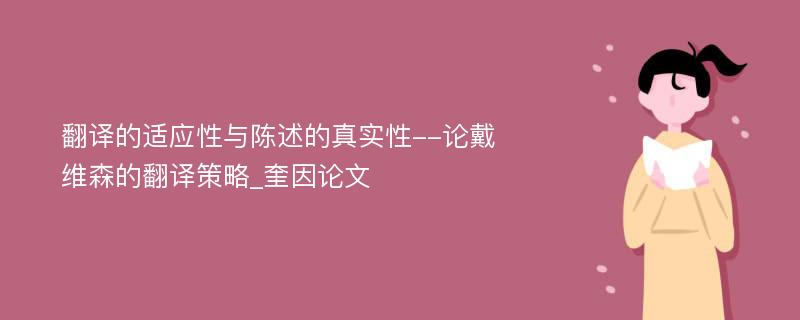
翻译的适应性与陈述的真——论戴维森的“可释性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应性论文,策略论文,戴维森论文,可释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8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
罗蒂(R.Rorty)需要一个支点来实现他对分析哲学所作的实用主义转向,对分析哲学本身的批判,无疑是这个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蒂指责分析哲学[以达米特(M.Dummett)为代表的这一派]与传统哲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它与传统哲学一样假定哲学的根本任务是为知识奠定基础)只不过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表现知识的语言上,而不是传统哲学所侧重的思想上。他认为语言哲学的基本主张并没有完全脱离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的旧框框,他称其为新二元论。这种新二元论就是承认语言与事实之间的二元分立,戴维森(D.Davidson)明确地将它作为“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加以摒弃。他将这一教条刻画为概念构架(conceptual scheme)①与经验内容(empirical content)之间的二元划分,简称为“构架—内容”二元论。
在这里,我不打算针对罗蒂对分析哲学所进行的总体性批判本身加以评论,原因很简单:首先,目前将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教条已经是广为接受的事实;其次,正如罗蒂所希望的那样,那种狭隘的逻辑实证主义目标正在受到普遍的怀疑;另外,对自然语言的关注本身也表明语言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任何早期分析哲学家,如罗素所制订的伟大方案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所指出的并被戴维森冠为“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即所谓的“构架—内容”二元论。
按照罗蒂的理解,戴维森是在努力贯彻奎因(W.V.Quine)的主张,即消除意义问题与事实问题之间的区别。②既然“事实”(fact)不再被作为独立的一元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不能再假定有那么一个独立于语言的“事实”,它可以被视为陈述的意义参照系与陈述的真值的判定标准。这样一来,对于陈述的意义与真值问题就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寻求解决方案。《对真与解释的探索》(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当中收录的大部分论文都体现了戴维森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他消除这种二元论的策略包括:从塔尔斯基(Tarsky)那里寻找灵感,在意义理论与真值理论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发挥奎因关于“强译”(Radical Translation)③以及“指称不定性”(The 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的观点,探讨理解与信念、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关系;当然,他对“概念构架”这一概念本身所进行的直接的批判无疑是最能代表他的这个取向的。
关于语言的可译性/可释性(the translatability/interpretability of language)的探讨,是戴维森所提出的策略之一,即他在哲学实践当中为探讨意义理论并消除所谓第三个教条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此,为了陈述的便利,我且将这一努力点简称为“戴维森的可释性策略”。
关于他所要反对的这种“概念相对论”和“概念构架”,戴维森有明确的描述:
概念构架,据说,是组织经验的方式,它们是赋予感觉材料以形式的各种范畴体系;它们是那些不同的个人,文化,或阶段对于世事所持有的那些不同的看法。一个构架或许不可能被译为另一个构架,在这种情况下,标志着一个人的个性的那些信念,欲望,希冀以及知识碎片,对于使用另一个构架的人来说是没有真正的对应物的;在一个构架中被视为真的东西,在另一个构架中却未必被当作是真的。
……
概念相对论是一个迷人而充满异域色彩的教条,或者,如果我们能从中见出什么意义的话,它可能会看起来如此罢。问题在于(在哲学中常常是这样)一旦我们将某些东西变得更加清楚明白时,它看上去就不那么今人兴奋了。④
他的矛头所指一般被理解为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但是,他在这里明确表示了概念构架问题不仅限于此。他所批判的对象还包括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所持的概念相对论,如普特南(H.Putnam),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和库恩(T.Kuhn)。另外,个人与文化的观念性差异也是一个主要论题,并且最终落实到对“实在”(reality)的理解上。尽管以上这三个方面可以笼统地合而为一,但是细究起来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比如,支持文化概念相对论的人不一定会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赞同康德式的先验综合——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相对论;康德的追随者在实在论上有可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尤其是考虑到戴维森用以反对概念相对论的主要论证是从具体的人类语言间的可译性与可释性入手的,那么,就更有必要将以上这三个方面区分开来。
在这里,我需要简略声明的是,本文无意为所谓的“构架—内容”二元论本身进行直接的辩护⑤,尤其是不打算从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角度来为这种二元论做辩护。本文旨在从两个主要的方面对戴维森的可释性策略本身进行质疑:首先,戴维森没有对语言的两种偶然性进行区分,即区分同种语言中经由概念的演变所体现的那种偶然性与不同种语言之间由于语言的构成性差异而体现出的偶然性——作为一种结果,他没有将解释与翻译明确分开;其次,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对源语言(original language)的重塑,即源语言对目的语的适应性问题,向戴维森的可释性策略提出了挑战:语言的可释性并不直接支持语言的可译性或互译性,因而也不直接支持陈述的意义与真值。下面我将对以上这两点分别加以阐述。
一、两种意义上的语言的偶然性
语言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是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们用来反对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依据。如果说语言本身是偶然的,那么对语言进行分析本身就不可能像分析哲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为知识提供任何保障或者基础。然而,我认为,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的偶然性。一种是罗蒂所讲的偶然性,是指在语言中词汇与概念的出现是偶然的。在这里,“语言”是在普遍意义上讲的人类语言,如“科学语言”中的“语言”一词,它不是指任何一种具体形式的自然语言。另一种是将各种不同的具体人类语言进行比较的意义上来讲的语言的偶然性。这里所讲的“语言”是具体存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语言,如英语,汉语或法语等。这第二种偶然性不仅表现在不同语言中所特有的词汇与概念上,也体现在各种语言间的不同结构以及语言构成的深层概念性差异上,这包括语音、语法、文字形式、表达习惯,以及从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方式。在这里,我且将第一种偶然性称为“纵向的”或者“时间性的”,它是从超语种的意义上来讲的。这是将人类语言作为一种虚拟的共同体,考察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偶然性。在这个意义上,各语种间所存在的差异被忽略。我将第二种偶然性称为是“横向的”或者是“地域性的”,它是从跨语种的意义上来谈的。在这里,各语种间的具体而细微的差别是考察的重点。第一种偶然性所要求关注的重点是概念的可释性;第二种偶然性所要求关注的重点是语言的可译性。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罗蒂详细探讨了上述第一种偶然性,即纵向的偶然性。他举的例子集中于不同时期科学用语间的差异,比如亚里士多德与牛顿关于运动的不同定义。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如伽利略前后的天文学用语;爱因斯坦前后的物理学用语等等。因为罗蒂所考察的是不同时期的科学语言,所以他的重心自然也就放在了“意义”(meaning)与“信念”(belief)上面。一种看法认为,词语的意义没有改变,而是人们的信念改变了;另一种看法认为,词语的意义与人们的信念是一致的,因而意义的改变也就是信念的改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罗蒂所考察的与其说是纯粹语言的问题不如说是知识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意义的实在性问题。他着重分析了普特南所持的实在论与其他实证主义哲学家(如戴维森⑥)所持的反实在论是如何对峙的。戴维森所走的是非认识论化的道路,并且他主张意义理论不是对个别词项意义的“分析”的总合,而是对语句间推论关系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意义不是一种先天知识,而意义理论也就成为一种经验性理论。无论如何,罗蒂所说的语言的偶然性并不直接涉及到不同种语言间的翻译问题,但是它却似乎更能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概念构架。用亚里士多德的“力”概念来结构的经验自然不同于用牛顿的“力”概念所结构出的经验,问题在于这种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否将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语言“翻译”为牛顿的力学语言?它们是否是相容的,或者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另外,这种不同是否真的能用来支持或者反对“构架—内容”二元论呢?从实在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概念上的差异体现着对世界认识的根本不同;从非实在论的角度看,这种差异则是相对的。它们需要被放在一个大的语言整体里来考虑,其意义是与其他的语言因素相关联的,而不是由所谓的“事实”来决定的——或者,反过来说,它们真实或者不真实地“反映”(reflect)或“体现”(represent)了“事实”。
可以说,这种纵向的语言的偶然性所暴露出的问题更主要是关于赞同或者反对康德式的认识模式的,因而不是我们所要考察的重点。我在这里所要考察的是语言的横向的偶然性,即在不同种类的语言间所呈现的差异中所体现出的那种语言的偶然性。在《论概念构架这一观念本身》(“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中,戴维森将这两种偶然性放在一起来谈论,作为概念相对论(Conceptual Relativism)的内容来加以批判。对于这种概念相对论,戴维森有如下描述:
有时,一个观念(如相对论中所定义的共时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整个科学都为之焕然一新。有时,对于在某一原则下才为真的一组句子的修订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感觉到其中所包含的词语已经改变了意义。在相距遥远的时间与地点之中进化而来的各种语言,其处理这一或那一类现象时可凭据的资源相差甚远。对于一种语言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能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就变得相当困难。并且这种差异会导致在风格与价值上明显的不对称性。⑦
在这一段引文里,前两句讲的是我所说的那种语言的纵向的偶然性,后两句讲的是我所说的那种语言的横向的偶然性。戴维森没有将二者明确划分开来,自然他对它们的批判也是笼而统之的。戴维森反对以上这种所谓的概念相对论的第一个理由看起来相当简捷: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尽管有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却并不是多么不可思议,其实,这些变化与差异是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来加以解释和描述的。⑧
他认为尽管这些差异实际存在,但是它们可以由同一种语言来加以解释和描述,这似乎是说这些差异因而是非实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森在这里用的是“解释”(explain)和“描述”(describe)这两个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反对戴维森这一观点:比如,你可以向英国人解释什么是“道”或者“气”,但严格来讲,将这两个词翻译成对等的英文词,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进一步来说,即使你可以依照字面将“stag night”与“hen party”译成中文,但是因为在汉语里没有对等的词(同时在汉文化中尚无相应的习俗),你还要向读者解释它究竟在英语中是什么意思(即英国文化中的那种风俗是什么)。⑨这也就是说,可释性并不等于可译性,可释性根本不能消除不同语言中所呈现的相对概念缺失或者语言本身所存在的其他构成性差异。
在同一篇文章中,戴维森解释了可译性何以对于概念构架而言意义重大:
我们或许会接受将拥有一种语言与拥有一个概念构架联系起来这一教条。这种关系可以被这样来假设:因为概念构架彼此相异,所以语言之间也是如此。但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可能会共有一个概念构架,因为存在将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法。研究翻译的标准因而就成了专注于研究概念构架同一性的标准的一种方法。⑩
在这里戴维森用的是“翻译”(translation)而不是“解释”(interpretation或explanation)。也就是说,翻译之所以成为关注的重点,是因为可译性直接与所谓的概念构架的假定相关联:如果两种不同的语言具有可译性,即说明它们共享一个概念构架;或者反过来讲,如果两种不同语言具有相同的概念构架,那么这两种语言就应该是可译的。这一对应必须严格局限于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或者互译性(intertranslatability)上(11),而绝不是可释性(interpretability)上。而这一问题最终归结到是否存在不可译的语言这一问题上来(限于篇幅,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
由于戴维森用以反驳所谓概念相对论的基本论述都是其“强释”模式中引申出来的,而他的“强释”模式是在奎因的“强译”模式的启发下而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奎因的“强译”模式中缺少了什么,考察一下他这个设计的意图是什么,然后再来继续探讨戴维森可释性策略。
二、奎因的“强译”模式中缺少了什么
在奎因(W.V.Quine)所设计的“强译”(radical translation)场景中,假定进行翻译的一方对所要翻译的语言是一无所知的。他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他所要考虑的是理解与信念之间是如何相关联的。可以说,这是奎因为了探讨意义问题而设计的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翻译者是在根本不懂得对方所操的语言的情况下,企图达到理解对方所说的话的意思的目的。这个人可以用来借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具体的物理环境,说话人在说话时所伴随的动作和表情等,当然,还有奎因想要突出的那个因素,即翻译者的信念。
在奎因的这个强译模式中,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对翻译的界定问题:如果对所要翻译的语言一无所知,那还能称其为翻译吗?“Translation”本身就是指两种语言间的事,否则就谈不上“trans-”了。奎因所设计的“强译”确切地说是臆测,是猜测性的判断。我们可以假定,当戴维森将奎因的“强译”转化为“强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时,他实际上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意在强调在奎因场景中的解释因素,同时也更突出了对语义与行为的关注,使他所关心的理解与信念的问题更加突出。就解释是对语言的意义的阐述这一点而言,它既存在于对母语的理解中也存在于对外语的理解中。戴维森对此十分清楚:
解释问题既是同种语言内部的又是不同语言间的……所有对于别人话语的理解都包含强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但是,专注于那些明显需要解释的例子,如将一种谈话中的术语解释为另一种谈话中的术语,会使我们免于全然忽视这些假设。(12)
如果我们把戴维森在这里所说的关于“interpretation”的话与前面他所说的关于“translation”的话联系起来,我们自然会发现他对于这二者的不同是十分清楚的:他由奎因的“强译”发展出“强释”的目的就在于强调理解与信念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这里,戴维森看到了将这二者加以区别的重要性。(13)然而,在戴维森的具体论证当中,尤其是在论述“强释”以及反对“概念构架”的直接论证当中,虽然他所要谈论的是不同语言间的“互译性”问题(intertranslatability),但是他仍企图通过分析“强释”场景来达到这一目的。(14)这也就是说,尽管在戴维森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出某些片断来表明他对“翻译”与“解释”的不同是有所认识的,但是在他的关键论述当中,他仍然是用语言的“可释性”来支持语言的“互译性”——在戴维森的这些论述中,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将翻译与解释明确区分开来,并表明要根据论证问题的不同来加以分别对待。
如果需要在这里对“解释”和“翻译”进行一个粗略的定义的话,我大致可以作如下限定:“解释”是用听众可理解(或者至少是解释者认为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阐述听众原本不理解的那种语言表达方式;“翻译”(狭义)是在一种语言中寻找与另一种语言中对等的词或者语句。正如我所指出的,一方面,戴维森强调语言间的可译性是考察概念构架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他用语言间的可释性作为支持他否认概念相对论的理由。然而,可释的不等于是可译的;可译性考虑的是具体的语词或者语句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性,可释性的重点在于找到一种听众可理解的表达方式;同种语言中存在解释问题,但不存在翻译问题。解释问题所关注的是概念间的差异,可以是同种语言内部的不同概念,也可以是不同语言中的不同概念;翻译问题所关注的是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它包括概念的差异,但不止于此。因此,解释与翻译对于“概念相对论”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粗略地说,就针对“概念构架”这一观念而言,研究“解释”是侧重于考察康德式的认识论模式,因为在这种认识模式中概念是重点,而这种概念所属的语言是一种假定的普遍的人类语言,是一个虚拟性的存在。相反,研究“翻译”侧重的是不同语言内部的概念构成,这里所指的语言一定是某种具体的人类语言,而概念构成也是具体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对事物的表达与描述的方式,而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讲的先天概念与经验内容之间的关系。在戴维森对意义理论的探讨中,他并没有严格地将可译性问题与可释性问题区分开来,即分别来考察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及可释性)问题与同种语言中的可释性问题对于意义理论的适用性。(15)在我看来,正是不同语言间的通常意义上的熟练性的翻译所针对的才是语言的横向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所体现出的问题与纵向的偶然性不尽相同,后者集中在概念间的可释性问题上,并且通常是假定处在同一种语言中(或者将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忽略不计),而前者则关系到语言的表层及深层结构以及固有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等等。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奎因的“强译”模式与自然的语言学习过程有着重大差别。无论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语言学习,或者是一个成年人被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学习一种绝对陌生的语言,在这些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臆测、试错与校正是必不可少的。奎因的语言实验设计与真实的语言学习的根本不同在于:在奎因所设计的“强译”场景中,语言的自然习得过程中所必经的试错与校正因素缺失了,因而它不能被当作一个真正的学习语言的特例来进行理解。我们就知道,当对一种语言一无所知时,真正的翻译是无从谈起的。翻译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一种语言是建立在对这种语言本身以及这种语言所属文化的基本了解之上的。
这种戏剧性的“强译”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两种语言间的翻译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前提是翻译者对源语言与目的语均要有充分的知识,并且译文要在尽量准确的前提下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为了便于对比,在这里,我将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翻译称为熟练性翻译或者“巧译”(skillful translation)。尽管这种翻译不利于达到奎因原有的实验室目的,但是,我认为,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实用翻译却正能体现出不同语言间的深层结构以及创造与使用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与表达的不同。跨语言意义上的偶然性在“巧译”中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实用翻译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至少是两种语言间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差异,具体的翻译行为也是体会这种差异的一个最生动的方式。对这种实用翻译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们会看到语言间的具体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意义。即使我们不能说这种差异直接支持了戴维森所批判的“概念构架”或者概念相对论,但是它所反映出的语言的横向的偶然性会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语言的意义与陈述的真值问题进行思考。
三、翻译的适应性与“概念构架”
在“巧译”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到翻译的适应性。所谓的翻译的适应性,在这里我是指在将源语言译成目的语时,必须要考虑到目的语的语法、习惯表达方式以及源语言中具有而目的语中缺少,或者目的语中具有而源语言中缺乏的那些因素。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举例来说明。
(1)在将源语言中的单词或者短语翻译为目的语时,要补充那些源语言缺乏而目的语具有的语法因素。比如,在将英语中的名词译为法语时,就要增加原本在英语中所没有的性,即要表明它是阴性名词还是阳性名词(16);再比如,并不是所有汉语中的量词在英语中都有对应,因而在将英语转译为汉语时,要添加适当的量词。(17)
(2)在不同语言中,词汇的繁衍与构成模式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被翻译的句子或者文本的意义与这种构词方式有关,那么在翻译时就有可能需要通过注释来解释这种不同。一些纯粹文字性的幽默和喜剧性片段之所以是不可直译的,其原因多在于此。(18)
(3)在翻译句子时,要考虑到句法结构的因素。各种句子成分的合乎语法或者陈述习惯的排布顺序,在不同语言中也不尽相同。(19)
(4)如果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各种语言所体现出的深层观念也不尽相同。所谓的语言的深层观念,即语言在构造上所体现出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比如,相对于法语来说,汉语在描述事物时呈现出中性,普遍性与概括的倾向。动词在汉语句子中基本保持不变的形式,没有性、数与人称上的差别,并且其时态与语态都是通过副词或者助词来表达的;而法语中的动词则要与具体的时态、语态、性、人称与数保持一致。英语与法语中的普遍时态是由一般现在时替代的,而在汉语中则有一个独立的普遍时态(或称“中性时态”或者“无时态”),这使得汉语在叙述上呈现出自己的“普遍”与“中性”的特征。(20)
(5)各种语言中所包含的特定的词汇和范畴,并不一定都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的词汇和范畴,这就要求在翻译时要么进行音译、附加注释或者创造新的词汇等等。这种活动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词汇的引入或者移植。(21)
(6)在翻译中,一些源语言中所具有的带有固定文化特性和内容的成语、缩略语、比喻和讽刺,在目的语当中找也常常找不到对应的表达式,而只能通过寻找近似表达式或者通过解释来达到意义传达的目的。
以上分别从单词、词语的构成、语法、句法、范畴和文化内涵等等方面分析了翻译的适应性,这些现象同时也表现了各种语言间的差异,即语言的横向的偶然性。那么,这种翻译的适应性是否支持概念构架的存在呢?在进行这一论证之前,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戴维森用来反驳概念构架存在的那些论述和论证。
在《论概念构架这一观念本身》(“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一文中,戴维森给出了两个关键性的论证:
论证一:
在各式各样的概念相对论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比喻似乎陷入了一个隐含的悖论。不同的观点可以都成立,但仅仅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存在一个用以确定它们的公共坐标系;而存在这样一个公共体系与所声称的那种戏剧性的不可比性不相符。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是考虑如何界定概念的对比性。有建立在悖论和矛盾上的极端假设;有我们不存在任何理解困难的谦逊的例子。是什么决定我们由全然陌生或新颖走向荒谬呢?(22)
戴维森认为,概念相对论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承认存在不可比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同的观点具有意义的前提是它们必须处在同一个坐标上,即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参照系。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公共体系存在,这种理论所声称的那种概念间的戏剧性的不可比性就难以成立。
让我们来试着将这里的意思表达得简练一些,看一看戴维森的反驳是否成立。我们可以用数学语言这种人工语言为例,把概念限于自然数的概念,而将这些数字概念间的可比性看作是数字之间的可通约性。假设a与b是两个不同的数字,a与b属于同一个意义参照系N,即自然数,在N中另有一个数字c,它是a与b公约数。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a与b之间可能的关系:
第一种可能性:c为a与b的公约数且a可以为b所约。(如:c=3,a=12,b=6)
第二种可能性:c为a与b的公约数且b可以为a所约。(如:c=3,a=9,b=18)
第三种可能性:c为a与b的公约数但a与b彼此之间不可约。(如:c=3,a=6,b=15)
如果我们将是否可以为对方所约看作是可比性,那么,以上例子表明,尽管两个数字之间可以经由第三者来进行比较,但是它们之间却有可能是不能进行直接比较的(如果将我们的考察扩大到实数或者整个数学领域,那么,以上的情形就会更加突出。)。在以上例子中,戴维森的论证仅仅对于前两种可能性是有效的,而对于第三种可能性是无效的。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同意概念相对论确实假定在不同的概念之下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参照系,这也不能证明这个意义参照系本身的存在就瓦解了任何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可比性。因为这种可比性是以第三者为衡量标准的,而这个第三者并不是这些概念获得意义的那个基础本身。
在这段引文的最后,戴维森认为概念的相对性(conceptual relativity)其实是概念的对比性(conceptual contrast)。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后者做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对比性与所谓的相对性的本质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论证二:
我们可能会将各种概念构架认同于各种语言,那么,或者更好一点,将它们认同于可互译的各种语言的集合(这里允许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不只有一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构架)。我们不应该将语言看作是与心灵相分离的;操一种语言并不是一个人在保持思想的同时可以丢掉的一种特征。因此,一个人根本不可能通过暂时放下自己的概念构架而居高临下地在概念构架间进行比较。(23)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不可能平等地用一种语言来思考另一种语言?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天生双语者(24),至少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在思考另一种语言时,是否需要完全丢弃自己的语言呢?这几乎是一个近乎荒唐的假设。当我们将一种语言本身作为一个思考对象时,我们的确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考本身不能进行。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在思考,所以才能看出作为思考对象的语言与用来思考的语言之间的差别。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摆脱了自己的概念构架的前提下才能思考另一个不同的概念构架呢?如果说理解一定要建立在完全对等的或者完全相同的概念或者概念的关联之上,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那样,那么我们的语言中的所有可理解的词汇就只能是同义词。若是我们在这一点上与戴维森分道扬镳,那么,我们就很难苟同他的以上论述。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是否赞同他接下来的思路:
如果两个人所操的语言间不可能进行互译,我们能不能因此说他们拥有不同的概念构架呢?(25)
按照戴维森的思路,支持概念相对论的人其实是在主张:如果两种语言是不可译的,那么概念构架就存在。因而,问题在这里就集中到“是否有不可译的语言”上来。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语言的整体性问题,即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将语言看作一个整体。除了语言发展的时间性问题之外,还有自然语言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其次,即便语言作为整体不存在界定问题,语言之间的可译性问题仍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一种语言中有一些词语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有对应的词,而另一些词语则没有,那么我们是称这两种语言是可互译的还是不可互译的呢?
如果我们不得不从日常语言的应用习惯出发,把任何一种现有自然语言本身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以下观点:如果一种语言的一部分(哪怕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可能被翻译(狭义)为另一种语言,那么,这种语言,相对于那一种语言,在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可译的。在这里,我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考察不同语言间所具有的差异来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如,下面所要讨论的不可译与陈述的意义及真值条件问题。如果说“概念构架”问题只是戴维森的批判兴趣所在,那么,意义问题可以说是他的理念核心。
四、不可译性与陈述的真值条件
当我们从不可译性的角度来考察戴维森关于意义的理论时,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
假设在一种语言(L1)中有一种在另一种语言(L2)中没有的语法现象,并且这一语法现象对于包含它的短语或者陈述的总体意义会产生影响。这一缺失,使得L1中凡包含这一语法现象的语句都不能够在完全意义对等的基础上翻译成L2。
其实,要想找到一个实际的语言中的例子并不难。比如,在现代汉语中没有与英语中的定冠词“the”相当的词,而这个词在英语中是有实在意义的。因而,在汉语中也就没有与限定性描述(由the引导的名词性短语)完全对等的语法现象。这一重大语法差别所引出的问题在我试图将罗素关于限定性描述的理论(即“摹状词理论”(26))译为汉语时充分显示出来。罗素著作的汉语译者与解释者们往往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依照通常英语到汉语的翻译习惯,这一理论的关键部分就会流失。从原则上讲,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解释限定性描述这一语法现象以及罗素的理论,而无法用汉语来精确地翻译任何一个限定性描述。
在将英语中的限定性描述(摹状词)译成汉语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要么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将其译为一般性描述(并不是特指),比如,罗素常用的两个限定性描述:“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被译为“当今的法国国王”而“the author of Wavley”被译为“《威弗利》的作者”;要么(为强调其特指的功能)译为指示性的描述(相当于英语中由指示代词“this”或“that”所引导的短语),如将“the cat on the mat”译为“垫子上的这只猫”,将“the man in green”译为“穿绿衣服的那个人”。
就罗素的两个例子而言,以上的翻译虽从纯粹翻译的角度上无可厚非,但是正是在翻译过程中,英语中的那个“the”所包含的限定性意义流失了。因为“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和“the author of Wavley”皆为单称特指,而“当今的法国国王”和“《威弗利》的作者”都没有排除其所指是复数的可能性,即它们不排除法国当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王和《威弗利》有不只一个作者的可能性。(27)而后一种译法则以指示代词来代替“the”的译法则又将这种限定变成了直接指示。
如果遵从这样的汉语翻译,而不加以特别的说明与解释,我们实际上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罗素原本所要讨论的限定性描述的指称问题,而是一般性描述或者指示性短语的指称问题。罗素的理论显然与它们都不相干并且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困难本身并不是由于具体的翻译技巧造成的,而是由于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本质性差异造成的。也就是说,与其说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翻译问题,不如说反映的是一个不可译问题。
为了突出这一重要的语法差异对于陈述意义的影响,并同时为了检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我现在要用戴维森的意义公式对一个包含限定性描述的具体句子进行一下演算。通过这个演算,我们希望向读者表明,可译性在这里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选择一个包含限定性描述(摹状词)的英语语句:
(1)“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essey is Greek”。
首先,让我们遵从习惯将之译为一般性描述:
(2)“《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
然后将它们分别代入约定T:
(T1)“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yssey is Greek”is true if and only if 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yssey is Greek.
(T2)“《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为真,当且仅当《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
(T1)与(T2)表明(1)与(2)的真值条件是不同的,因为(1)的主语被限定为单数的,而(2)的则没有。也就是说,如果这两部史诗不只有一位作者(如大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陈述(1),即“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yssey is Greek”,是一个虚假陈述,而陈述(2),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则不是。这表明,在这种习惯上的适应性翻译当中,原有陈述的性质被改变了,因而其真值条件也发生了变化。
下面,再将(1)与其汉语翻译分别代入戴维森的意义公式:“(M)s意味着在L中,p。”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翻译上的选择:如果我们仍采取习惯的译法,即(2),在将其代入戴维森的意义公式后,我们得到(D1),而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D1),“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essey is Greek”意味着在英语中,《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
在(D1)中,元语言(metalanguage)中的句子“《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与对象语言中的句子“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essey is Greek”的真值条件不同[见(T1)与(T2)],所以它们是不等值的,并且其意义显然也是不同的。关键在于,戴维森的意义公式是建立在语言的绝对可译性或者充分互译性基础之上的,并没能将不可译的那些因素考虑在内。
当然,为了挽救这个意义公式的有效性,我们也可以试着根据对象语句的语义来对元语言的语句加以限制,以求在意义上使二者达到最大可能的一致。如,将(1)“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essey is Greek”译为(1-1)“《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唯一作者是希腊人”;或者反过来,将(2)“《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译为(2-2)“Either 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essey is Greek or the authors of Iliad and Odessey are Greek”。
让我们再分别将它们代入戴维森的意义公式:
由(1)与(1-1)得:
(D2),“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yssey is Greek”意味着在英语中,《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唯一作者是希腊人。
由(2)与(2-2)得:
(D3),“《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是希腊人”means that in Chinese,either the author of Iliad and Odyssey is Greek or the authors of Iliad and Odyssey are Greek.
(D2)当中所呈现的对象语句与元语言语句在语法上的以及句子结构上的不对称性在(D3)中尤为突出:在(D3)中,对象语言中的句子是一个简单句,而元语言中的句子是一个复合句。这表明,虽然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对于对象语句的原有意义的忠诚,但是我们却是以牺牲句子结构的对称性和其他语法因素的对等性为代价的。
从我们所定义的极为狭义的“翻译”上来看,(D2)与(D3)中元语言语句不是对对象语句的翻译而是对它所进行的解释——为了最大可能地确保两者意义的接近。只要我们追问一下这种不对称性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这是由英语与汉语在结构上的根本差异造成的,也可以说是由于两种语言的部分不可译性造成的。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语言称为部分不可译的语言(partially untranslatable languages),但是这种部分不可译性一定是针对这两个具体语言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以上企图挽救戴维森意义公式的例子中,我们通过解释做到了使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中的两个陈述的意义最大可能地接近,但是,严格来讲,它们的意义仍然是不同的:在(D1)中“the”与“唯一(only)”并不完全相同;在(D2)中的汉语句子的意思虽然在逻辑上等于两个英语子句意思的析取,但是它本身却并不“means”那个复合句。我的结论是,实际上,我根本无法通过解释对象语句来弥补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任何一方所存在的语法缺失;当这种语法对于陈述本身的意义有所贡献时,它的这种贡献本身因而也是不可译的。
小结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意在表明自然语言间所存在的部分不可译性,提醒我们重新考虑为戴维森所极力否定的概念构架问题。无论我们将对所谓的“概念构架”进行什么样的界定,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两种语言在结构与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使精确的对应式翻译不可能时,我们要么在翻译中力求尊重不同语言在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性而牺牲意义传达的精确性(我们可能会因此使译句的真值条件不同于原句的真值条件,使句子本身的性质发生改变);要么我们为了追求意义上最大可能的接近,而以解释代替翻译,这无疑是承认了语言的(至少是部分的)不可译性。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向戴维森提出了挑战:前者质疑他的意义理论公式,后者质疑他对语言的不可译性(进而是概念相对性)的否定。
注释:
①李幼蒸在汉译本《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将其译为“概念图式”,也有人将其译为“概念构架”,本文从后一种译法。因为就戴维森而言,他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康德式的知识论,即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以概念去组织或者结构经验。
②见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4页。
③有趣的是,就怎样将“radical translation”译成汉语本身就已经极为radical了。齐林等人将它译为“彻底解释”,当然在字面上无可挑剔,然而,这一短语的特定内涵没有体现出来;叶闯赞成将其译为“原始翻译”(见叶闯《理解的条件——戴维森的解释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第30-31页),并常常用“新大陆翻译”来指代。“新大陆翻译”将这一短语自奎因那里所具有的设计意图体现无余,甚至可以从中窥视英美人不自觉的“殖民心态”,可谓别具匠心,并且在汉语陈述过程当中有助于读者领会。略感遗憾是“新大陆”在原文字面上没有照应,这本身就不是translation而是interpretation了。出于本文自私的考虑,为了与后面所提出的适应性翻译,即“巧译”(skillful translation),形成对照,窃将其译为“强译”,“强”既有“强硬”又有“勉强”之意。
④"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in Donald Davidson: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4,p.183.
⑤我在这里不打算做任何直接评论,主要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于“概念相对论”、“概念构架—经验内容二元论”以及所谓的“文化相对论”究竟指的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而一致的理解。即便我们承认自然语言间的构成性差异表明在自然语言形成时期人们在概念取向上是存在差异的,并且也有可能从中导出某些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差异本身就可以直接用来支持某种相对论——我们毕竟要看这种相对论所主张的究竟是什么,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现象是相关的,以及这种相关性本身是否仅仅支持了某种相对论而排斥兼容与进化理论。如果这种相对论本身不排斥语言间的相互交融,那么它所讲的“相对性”本身就是相对的。
⑥很显然,戴维森本人对于罗蒂贴在他身上的这个“实用主义者”的标签感到很不舒服。见Donald Dvidson,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Introduc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4.
⑦"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in Donald Davidson: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4,pp.183-184.
⑧同小注⑦,p.184。
⑨在这里我没有将文化融合的因素包括在内,比如“Susi”和“Qi Gong”已经成为当代英语的一部分,而“圣诞老人”也成为当代汉语的一部分。究竟文化的融合是支持还是反对概念相对论,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另外,多大程度上可以将某种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也是一个问题,语言的变化与文化的变迁是同步的:一旦外来文化本土化了,外来语也就成为本地语了。同样,语言的开放性或非整体性是否可以用来支持或反对概念相对论,仍需要相当深入的思考与论证。
⑩"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in Donald Davidson: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4,p.184.
(11)尽管从翻译学上看,翻译与解释的界限可能是相当模糊的,但在这里,出于所探讨的哲学问题的需要,我不得不将纯粹翻译局限于极其狭窄的意义上,即局限于词到词的对等翻译。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从纯粹翻译的角度来谈概念相对性问题。
(12)"Radical Interpretation",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p.125.
(13)在英语中,一个interpreter既可以用来指翻译员也可以指解释者,但这不等于说,在英语中“translation”与“interpretation”就没有严格的区分。
(14)见“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和“Radical Interpretation”。
(15)这并不排除在不同种语言之间也存在着解释。
(16)例如,“my family”要译为“ma famille”;而“my pencil”则要译为“mon crayon”。
(17)例如,“a horse”要译为“一匹马”;“a pig”要译为“一头猪”;而“a sheet”则要译为“一条床单”。
(18)例如,“Mr Ben is on his alcoholiday!”对于经常空腹饮酒并渴望度假的英国人来说是相当形象的,但是其中“alcoholiday”这一人工合成词所体现的文字趣味却很难被直译为汉语。因为在汉语当中,“酒”与“假日”在构词上没有“alcohol”与“holiday”中的那段可共享的部分。如果将这句话翻译为“本先生在度他的酒精假日!”尽管在意思上无可厚非,但是其中的文字幽默尽失。
(19)例如,在将“我很爱你”译为英语时为“I love you very much”,主谓宾的顺序保持不变,但是状语的位置不同。
(20)从这个角度上看,刘半农发明了“她”就不只是一种诗意的浪漫,而是对原有汉语传统的一种侵犯:第三人称指示从此在性别上变得赤裸裸。但是,好在,他不是侵犯汉语语言传统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语言的整体性总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能够称为语言传统的东西就更是如此。
(21)比如,许多中国哲学范畴在英语中采取了音译,“气”译为“Qi”;“性”,“理”和“仁”译为“Xing”,“Li”和“Ren”。我们也将犹太人的上帝的原本只能默读不能发音的称谓“YHVH”译为“耶和华”或“雅卫”,因为汉语作为象形文字无法进行相应的单词分解与缩略。
(22)"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p.184.
(23)"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p.185.
(24)严格来讲,语言是习得性的。这里所谓的“天生双语者”,是指生长于一个双语的环境当中而自然使两种语言成为平等母语的人。
(25)Ibid.
(26)本人倾向于将“definite description”译为“限定性描述”。一方面是为了与一般的英语语法书中的译法取得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英语中的限定和非限定描述都不是词,而是短语。
(27)一种解救办法是采取以上所说的第二种措施,在汉语译文中对之加以限定,即将二者分别译为“那个/这个当今的法国国王”和“《威弗利》的那个/这个作者”。虽然在这里限定性问题由单称指示词解决了,但是另外两个问题又会涌出来:1 英文原文是限定性描述,是“the…”,而不是指示性的短语,不是“this…”或“that…”;2 这样的译法不免在汉语中引起误解,因为它本身具有暗示有不只一位国王或者不只一个作者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