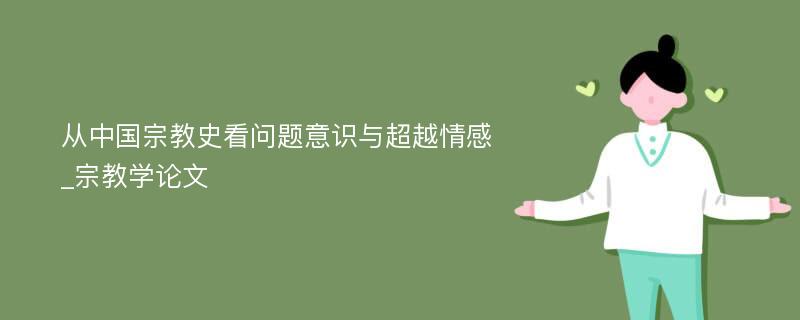
从中国宗教学史看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学论文,中国论文,情怀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五十年:意识与问题共生
在中国,宗教学的产生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就其思想基础而论,作为客观的、理性的人文学科的宗教学所必需的摆脱传统宗教(在中国主要是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气候,可以说才正在形成之中,造就这种思想气候的中国式的启蒙思潮,其实正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宗教学所必需的现代学术方法之吸纳,又只能是绵延多年但此时才开始形成规模的西学东渐的结果。总而言之,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的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宗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并不显现为某种现成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作为造成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因素之一,参与到造成重大历史变革的历史活动之中。
中国宗教学在产生之时即与社会变革“亦因亦果”,与时代问题密切共生的情形,至少可从三个方面看到。
第一,假如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变所需的真正的“启蒙运动”,那么,宗教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恰恰构成了这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那个推翻了专制政府、但两千年专制造就的社会尚待改造的时期,绝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不遗余力地猛烈批判旧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特别是高举起“打倒孔家店”的鲜明旗帜。从中国宗教学的产生条件来看,这种批判使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以往两千年只站在一教(多半是儒教)的立场来论说和评判宗教的状况,而有可能采用理性的方法,站在客观的立场,独立于“三教”或任何宗教之外来看待宗教,从而开启全新的宗教研究,即现代意义的宗教学研究。某些摆脱了对传统宗教(首先是儒教)依附地位的宗教学思想,本身就是这种思想气候的组成部分,甚至促成了这种气候的形成,而这确实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第二,中国宗教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20世纪前半叶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宗教史学的突出地位。只需略举陈寅恪、陈垣、汤用彤、胡适等几位大家的成就,读者已可略见一斑。而这正是西方宗教学中盛行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重视历史、重视考据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现象,正是那个时代西学东渐蔚成气候,而某些杰出学者既向西方学习,又将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运用于宗教学研究的鲜明反映。
第三,中国宗教学第一阶段发展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是宗教界内的学术活动具有重大的贡献。这个特点同样也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思想状况密切关联,并反过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状况。
首先,当时在思想上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学东渐”,包括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引进,有不少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教会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促成或完成的。
其次,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宗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尽管具有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点,但都从反面给宗教界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
最后,从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来看,这种理性的温和态度反过来对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某种良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宗教学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经历表明,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其赖以产生的意识条件,其产生之后的意识状态,都是同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共生共长、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
二、后五十年:超越不等于超脱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的学科历程证明,同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学科相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同社会历史问题的联系更加密不可分,因而更加无法超脱出社会历史环境,可以说是与社会进程共命运,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同某些在当时至少保存了形式或名称的学科(如语言学、考古学之类)相比,宗教学和另一些连形式或名称都被取缔了的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之类),就同社会历史问题更加血肉相联,可以说是与社会生活同生死了。
这一点,从宗教学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终于确立,全中国的社会生活由此开始全面复苏,其中包括宗教生活和宗教学研究的复苏。
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停止了文革时期禁止宗教活动和迫害信徒的做法。从80年代开始,久已绝迹的宗教活动不但迅速复现,而且迅速发展。
1982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重要文件。该文件作为中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宗教问题相结合,将宗教界定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改变了以往仅仅把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
与此同时,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宗教的关注很自然地重新兴起,并直接推动了宗教学的迅速复兴和发展。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了一批宗教研究所,各从不同的侧重面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一些省市的社科院还开始招收宗教学方面的研究生。中国宗教学在不到20年时间内,就从死里复活并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几乎堪称学术发展中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发生,不但同“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条件直接相关,而且同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造成的思想气候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宗教学发展史上被戏称为“鸦片战争”的那场学术争论之中。争论本身虽然激烈,但是双方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应该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和教条的理解,全面地、准确地、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在这场争论之后,宗教学术界采取了更加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这就不但解除了宗教研究者头上的政治紧箍咒,而且使他们敢于摘下各色各样的有色眼镜,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己所眼见的事实,具备了真正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气候在中国宗教学领域的另一表现,是“宗教文化论”在九十年代取代“宗教鸦片论”,成为学术界的最大共识,并在宗教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之或好或坏,确实直接决定了中国宗教学之或兴或亡、或盛或衰,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宗教学同别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又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又可以对国家乃至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发生或大或小、或正或负、或直接或间接、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或影响,并且不得不活动于自身帮助造成的社会条件之中。
正因为如此,问题意识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才是中国宗教学的前途所在。
三、未来展望: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不断涌现、旧问题相继复活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宗教文化,已经不可能超然于俗世的困扰;这样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也愈发可以同信仰的激情相互启发。对宗教学而言,这里所谓“信仰的激情”,首先应是某种“超越情怀”。这种超越情怀起码应超越世俗的利害考量,但又要对俗世有某种承担精神。这种承担精神,在学术上就应体现为某种问题意识。所以,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确实不仅是可以相结合,而且是应该相结合的。
我们在此想知道的是,这种“可以”和“应该”,能否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
当前中国宗教学界还十分关注两个事关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问题,一个是“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另一个是“宗教间对话”的问题。
宗教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自身做起,努力把问题意识和超越精神结合到自己的工作之中,尽管这样做要克服许多难为人道的巨大困难。
问题意识可以是对千种万种不同问题的意识,超越情怀可以指涉千种万种不同层次的情怀。但是我想,对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而言,尤其是对中国宗教学的学术工作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应是对中国人精神状态及其问题的意识,最需要的超越情怀,应是对中国人精神幸福的超越功利的关怀,应是对包含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