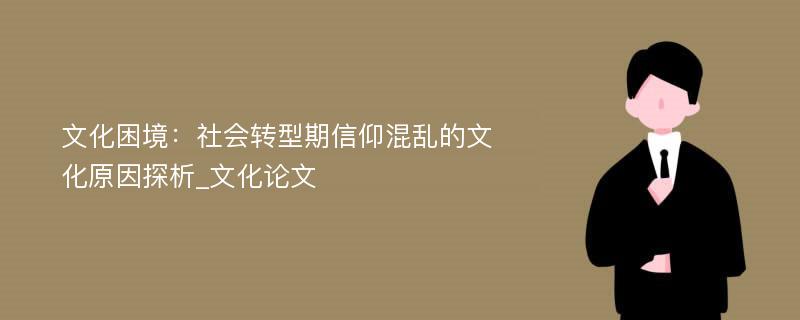
文化困境: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因探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转型期论文,困境论文,迷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仰隶属于文化,信仰的生存也仰赖于文化。目前人们普遍感到的信仰迷茫,首先有其文化方面的深刻的背景和原因。深入这种背景和原因,会十分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积极的对策。
一、本土文化的多元并存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它的独特的品质在于,虽然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与更替,它的整体状貌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但其某种精神气质却一定在经济、政治的变迁中传承下来。正因如此,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就我们本土文化而言,也是多元并举的。当然,多种文化之间的主次、轻重、范围是不同的,但它们却同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制约我们的选择,规限着我们的信仰。这种多元文化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
1.伦理性文化
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法等诸多学家流派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当儒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其它的学派也均成为“儒学之补”),那么,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一元”文化(这里的“一元”是指没有整体上和它相对立的文化)。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把文化“伦理化”,因而可以称其为“伦理性”文化。在学界的讨论中,有人不同意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性”文化,而主张“伦理政治型”文化的提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儒学文化的理想结构中,伦理与政治是同构的,家与国是同质的;家是国的微型形态,国是家的扩大形态。个人与国的关系是个人与家的关系的合理外推。父母相当于君王,兄姐相当于上司,妻室相当于同僚,弟妹相当于下级,子女相当于子民。反之亦然。这种文化中,所谓参与政治,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伦理情感施之于国,在家孝父母,出仕忠君王,始于事父,终于事君。这就是说,人们虽然从事着繁忙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活动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说,政治并没有像我们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对文化形成“霸权”。人们从事的是政治活动,通贯的却是伦理精神。所以,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政治型文化”,不如说是“伦理性文化”来得更为彻底。
当然,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开始,经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这种伦理性的本土文化经历了一个土崩瓦解的过程。最初,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人们仍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只是在器物层面上接受西方文化,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中国在激烈的军事和经济竞争中失利,人们开始部分地怀疑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性,并部分地认同和学习西方文化,力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建立起与西方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最后,随着清王朝帝制的覆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本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受到全面的冲击。其间也有一些诸如“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文化调和主义,也有一些坚守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但都无碍于传统本土文化的整体败落。
解放以后,取而代之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政治性文化”(下一问题论述)。但是那种伦理性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仍然支配、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使文化获得了相应的解放,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面临着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冲撞与挤压,在这种情况下,本已被现代文化解构的传统伦理性文化,在首先被西方后现代文化从特定的角度和意义上看好的情况下,又被不加限制的“阐扬”和“光大”,甚至大有使其“重振雄风”占据文化霸权地位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进入后发展时期一些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构性,中国传统这种伦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十分强劲的影响,甚至成为在目前人们多元文化选择中“行情”较高的文化形态。
2.政治性文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政治并没有真正形成文化的霸主地位,而是附着于伦理精神,那么当传统文化被整体性地解构以后,这种政治性文化便真正地形成了。基于计划经济社会那种特殊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要求,政治占据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地位”。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按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来运行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按政治目标的需要来确定的,甚至“抓革命”也能“促生产”。在这种社会中,伦理精神算不得什么。如果说在过去是伦理精神通贯于政治活动,这个时期就正好相反,是政治精神通贯于伦理活动。一阵时期,家庭不是按血缘伦理关系组织,而是按政治关系“排列组合”。那个年代,出现亲兄弟俩个或亲父子两个,同喊“×××万岁”的政治口号将双方击毙的事情,也是不足为奇的。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这种文化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它却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是因为,第一,从社会制度发展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从单纯的经济制度而言,尚没有渡过转型期,更莫说社会的政治结构及相应的思想观念了。计划经济时期所造就的政治性文化,比之于那种传统的伦理性文化,更加直接地影响着已处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人们。第二,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短兵相接”,昨天的计划经济和今天的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体”直接重合。如果说“向前看”是人的向往,那么“忆往昔”更是人的情怀,更何况,有许多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大利益既得者,这就更加剧了政治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3.经济性文化
如果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至上的文化,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是一种政治至上的文化,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一种被完全“经济化”的文化,可以简称为“经济性文化”。这种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时期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对传统伦理性文化和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性文化的整体扬弃之上。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如果说伦理性文化和政治性文化多少还保留一些精神追求(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因而还有一点“神圣”的成分或气质,那么,经济性文化则是地道的世俗性文化,它简直就是把文化“世俗化”了。目前的中国,如果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层面,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历史潮流的同时,还力图保留和坚守人文精神的操持,还向往着一定的精神的神圣境界及与此相应的终极关怀,那么,大众文化则是一种经济性文化。在人的本能性欲望的驱使下,这种文化几乎完全变成了纯经济的躁动。
二、西方文化的多元并存
经过近百年的对中国本土文化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观念的层层逼进和步步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西方文化已多姿多彩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看,不同形态的西方文化似乎比中国的本土文化内涵更为规范,特点更为鲜明。
1.古典性文化
所谓古典性文化,是西方的“传统文化”。若从空间结构和文化性质上,以现在颇为流行的“传统就是现代”或“传统蕴含在现代之中”的方法来考察,是很难给它一个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在文化历史的历时性维度上它是很清晰的,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前的“前现代性文化”。有学者称其为“神圣性文化”。它以三种精神构架而成:一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二是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三是罗马的法制精神(注:参阅赵敦华:《超越后现代性: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可能性》,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虽然经过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示的人类精神(和文化)的世俗化运动的清洗和荡涤,古典性文化被视为几乎等同于“神学文化”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正像怀特海所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洋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这种古典性文化或被“改头换面”(如宗教改革),或被“抽取吸纳”,它的精神气质在一定的形式中却延流至今。众所周知,韦伯竟然从它的身上(基督教为内核)找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源地,从而被视为“巨大贡献”在整个文化界引起狂飙巨澜。不仅如此,在对它进行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平地起家的现代性文化,经过几百年的辉煌发展而耗尽能量并越来越暴露出它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时候,古典性文化便冲破包裹它的现代化形式直接地显露出来,紧接着,显露出来的古典性文化,又被以否定和清算现代性文化之弊端为使命的后现代性文化作为其价值征战的“开采地”(这一点非常类似于“新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阐扬光大)。古典性文化终以比它的原始装束更加光彩照人的面目呈现在当代人的面前。现在的景情,正经可以用黑格尔的“提起古希腊就有一种家园感”的名言来形容了。
2.现代性文化
现代性文化是指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开端的,在否定古典神圣性文化基础上所形成的崭新形态的文化。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规定为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基本内涵(这里的“理性”相对于“神性”、“人本”相对于“神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性文化是伴随“世界历史”的形成,即世界历史从传统农业社会(文明)到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现代社会转型而形成的,同时也是支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它的形成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质的飞跃。众所周知,在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支撑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才得以形成;资产阶级正是仰赖于它所造就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整个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类创获了辉煌无比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如果说古典性文化崇尚的是理想价值,那么,可以说现代性文化完全崇尚的是世俗生活。
当然,现代性文化正是在它崇尚世俗生活的过程中,被片面地作为“工具理性”无限制地开采和征用人类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因而暴露了它难以克服的弊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弊端的最有力的揭示和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性文化才闪亮登场,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和方式,甚至不惜以怪异荒诞的方式,对现代性文化尖刻讽刺、无情玩弄和激烈批判。它们试图给人类营造一个福祉无限的新型文化。或至少说以某种方式在某一侧面为这种文化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但是,正像现代性文化并不能全盘否定古典性文化的价值一样,后现代性文化同样不能完全否定现代性文化的价值,甚至连现代性文化在目前仍然要占据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和主流地位这一点都不能否定。对于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就更是如此。尽管我们已经能够理性自觉地审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但占据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在历史文化运作的时空中和我们所确立的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应该说仍是这个现代性文化。
3.后现代性文化
后现代化性文化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一种文化,它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对现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它并不是现代主义文化的后继者,毋宁说,它只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这种观点陈述了三条理由,其一是后现代性文化继承了现代性文化反传统的激进批判精神,像启蒙学者反对神圣文化传统那样反对一切文化传统;其二是后现代性文化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样割裂了与传统的联系,它与一些“现代文化”思潮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其三是后现代性文化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注:参阅赵敦华:《超越后现代性: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可能性》,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稍仔细一点地辨析便会看到,这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后现代性文化究竟是反传统还是不反传统?第一条理由说它“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第二条理由马上又说它并没有“割裂与传统的联系”,“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第二,后现代性文化到底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还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持论者把这当作一回事来理解,但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在我们看来,问题就出在持论者极力想否定“后现代性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毫无疑问,后现代性文化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它脱胎于现代性文化,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是“承袭”了现代性文化。它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而主要是反“现代性文化”这个传统。它表现形式上似乎是反对包括“古典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传统,但它的“内在精神气质”或“终极的目的”或“最深刻的动机”却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古典性文化”上回归。
那么,后现代性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在何种意义上影响着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呢?如前所述,若仅仅从“理论建树”上而言,毋宁说,后现代性文化所主张的流浪者的思维、哲学的终结、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殒落、结构的颠覆、价值的削平、视角的多元化、解释的游戏化、方法的反传统化等等,和目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因而对于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和对现代性文化尚有急切渴望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一种荒诞不经的怪异之说,只能从总体上遭到暂时拒绝和悬置。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文化之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目前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相当的影响的文化形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提出了多少高明伟大的理论——在这方面它和古典性文化相差甚远;也不是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实际影响(它还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层)——在这方面它又和现代性文化相差甚远,而是因为它在向西方传统文化回归的同时,又从“外来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看好”,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精神气质上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暗合”之处,这样,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显现,它被中国人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接受。
三、多元文化的间架格局
以上我们只是逻辑地把文化划分为中西两大系列,并陈述了它们各自的“多元”。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却决不像“土豆”块一样地作用于我们。对于中国来说,近代百年的历史正是古今中外文化冲撞、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中西多元文化的支流“条条道路通罗马”,全汇集到了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之中。因此,要想探索它对人们的信仰危机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还须对这种文化的总体格局作出梳理。
第一,从中西文化融合的态势看是交错对接。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中国的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虽然都是一种文化历时态的“流化”,但当它们汇集到当代中国社会中,却并不按历史的顺序汇合对接,而是错位对接。具体地说,西方的后现代性文化对接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文化;中国的经济性文化对接的却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剩余的中国的政治性文化和西方的古典性文化则有相当的“亲和”之处。这是非常奇妙的文化景观。应该说,它的主导原因乃在于中西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时代落差。
第二,从相互交融后的文化“重量”上看是外来文化大于本土文化。众所周知,在百年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由于经济落后和不断挨打的根本原因,参照和模仿西方文化已深深地积淀到我们的心理结构,并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的本能。在中国经济性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对接中是西方现代性文化占绝对优势。看一看如今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生活状态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中国政治性文化与西方古典性文化的对接中,人们则更着眼于对特定时代的中国政治性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一个明显的小例子似乎可以深刻地说明这一点:过去人们总是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中世纪”相比,一起进行批判和否定,可是,现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在一定的意义上肯定“中世纪”的苗头。至于西方后现代性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性文化的对接,虽然,后现代性文化的作用被洇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之中,但是,它却有方兴未艾的势头。新近以来,中国文化界对西方后现代性文化的关注有增无减,决不亚于对现代性文化的探求。
第三,从文化驻足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上看是文化创新强于文化继承。正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无论中西古今文化是怎样的交错与对接,它们决不能回归于某一文化的原始形态,一定有新的时代的因素汇入而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那种热衷于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与阐场,也坚决地声明要“综合创新”、“现代转换”;那种对现代性文化的追求与模仿,也决不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是传统文化,不仅因为它是“过去”的,更因为它是“历史悠久”的,而之所以是历史悠久的,正是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那样的“大一统”、“超稳定”,因而在它的运作机制中总是传承大于创新。然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飞速,政治变革频繁,文化转瞬即逝,传统文化即是被“传承”也仅只能占“一席之地”,文化的整体态势是“向前看”。
四、多元文化挤压所造成的信仰迷茫
信仰隶属于文化,而文化已经如此这般了,信仰岂能不迷茫。
第一个迷茫是信仰之文化认同的迷茫。信仰隶属于文化,因此,信仰首先需要有文化的“家园”。也就是说,信仰首先需要认同一种文化。我们在信仰危机的学理性探讨中曾指出,克服信仰危机、建立新的信仰的“第一步”就是“文化认同”(注:参阅拙作:《试论信仰危机》,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那么目前我们的信仰,真不知该认同哪一种文化:如上所述,姑且我们承认目前文化的总体格局的特点之一是“西方文化重于本土文化”,那么,仅就西方文化这条线而言,情况就令人十分尴尬:全盘接受、部分接纳、完全拒绝,都一定有相应的诸如“极端的保守主义”、“温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或“当代虚无主义”等等“帽子”向你扣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言过其实。在他们看来,近百年来古今中西文化虽然多有冲撞,但总体来说,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古今文化结合并产生新的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成为中国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以后就更是如此。是的,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划时代的发展,文化也呈之以新的面貌。但是,谁能否认,历史的实践后果同马克思的理论初衷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中西文化之精华在实践中的最理想的“结合”,那么,结合了几十年还是如此状况,能不令人产生文化的困惑和信仰的迷茫吗?
当然,历史总要前进,历史给我们交了高昂的学费,使我们毕竟找到了“邓小平理论”,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预示着我们在文化上的新的曙光,预示着我们的信仰的新的“文化归宿地”。
第二个迷茫是价值选择的迷茫。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所以文化认同的困惑必然导致价值选择的迷茫;信仰又是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所以价值选择的迷茫的最后结果是信仰的迷茫与危机。
价值选择的迷茫,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层面是现实价值选择的迷茫。人们现实生活的法律、道德、艺术、教育、乃至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功利活动,都仰赖于人们的现实的价值选择。然而,多元文化并存,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因而人们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道德行为找不到唯一的解释标准。人们赖以解释自己行为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分裂。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是法律领域的唯一的价值标准,然而在文化多元的冲击下,由于权力关系、亲情关系甚至金钱关系(政治性文化、伦理性文化、经济性文化的表现)的渗透和干扰,这一价值标准却往往失去范力,遭到扭曲,以致于人、权、法、情、钱的关系仍是市场经济下的“热门话题”和“理论难题”。有人说得好,如果说这种价值选择的迷茫,在过去主要表现为选择机会的匮乏,那么现在却是选择尺度的遗失。选择尺度的遗失,使人只能“跟着感觉走”,而当选择仅仅依赖于感觉时,也就没有选择了。可见,现实价值选择迷茫,在现实中往往有两种极端的形式: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什么都行”。两极相斥相通,将人置身于价值选择的“真空”状态。
价值选择迷茫的第二个层面是终极价值选择的迷茫。多元的文化尚使现实的价值选择陷入困境,也就更不用说终极价值的选择了。一方面,目前的文化从总体上就没有给我们很好地提供一种“终极价值关怀”。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总体文化格局的“现代文化大于传统文化”的特点,使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终极价值关怀”被淡化、稀释、瓦解;其二是受当代“解构神圣价值”的种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目前的文化本身,就极少提供一种“终极价值关怀”。另一方面,即使目前的某种文化提供一种“终极价值关怀”,也因在文化整体选择上的困境所限制,不能轻易地被我们所接受。
信仰是现实性和理想超越性的统一,是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的统一。现实价值选择的迷茫,使它的现实性和现实关切无处着落;终极价值选择的迷茫,又使它的理想性和终极关怀难以寄放,信仰能不陷入危机?
第三个迷茫是人格崇拜的迷茫。信仰的心理基础是崇拜,没有心理上的崇拜,信仰便难以发生。崇拜的较高对象是自我,因此信仰是最高的自我状态。自我的外化便是一种人格,因此,可以说,信仰需要一种人格崇拜。人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但人的本质却又是社会的,因此,人格中最基本的矛盾应是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如果人格已无法塑型,那么,毫无疑问,信仰必然危机。目前的多元文化都有人格的蕴含,都有关于个人、社会及其关系的看法,但是构架不同,理路不同,追求的目标更为不同。我们陈述过那诸多的“文化”,他们对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都各有主张。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忽视乃至否定个人价值的“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文化,它源远流长,绵延不息,从旧时代的“伦理性文化”一直延续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性文化”之中;再如,改革开放了,个性解放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性文化又占据了文化的主战场,如此等等。蕴含在古今中外文化之争的底层的,实质上是人格塑造的分歧,或展开说是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和路径的分歧,因而可以说,有多少文化,就有多少人格形象,就有多少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信仰需要以某种人格为崇拜对象,以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表征自己,并制约和牵导人的从现实到理想的升华。如果什么人格都信仰,那也就没有了人格;如果一个“可信”的人格也寻找不到,那信仰就失去人格崇拜。人是信仰的主体,人尚无法成型,何谈人之信仰!
标签: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