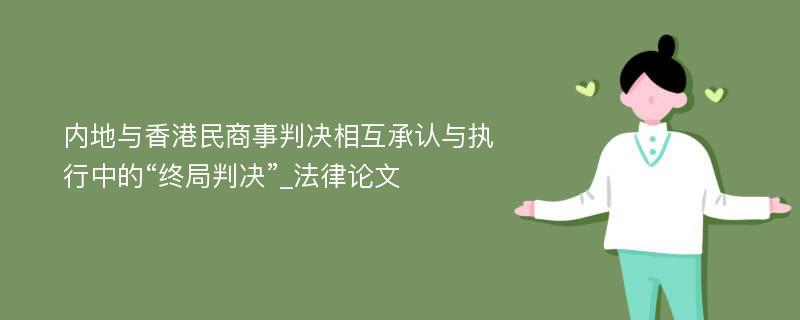
内地与香港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中的“终局性判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决论文,香港论文,内地论文,民商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地与香港已就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事宜进行了多年协商,至今尚难达成一致,其中争议较多的是双方对“终局性判决”的含义理解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内地法院判决是否为终局性判决是阻碍实现两地相互执行商事判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内地与香港在讨论两地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条件时,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判决的确定力问题:即香港方坚持,在请求香港承认或执行内地的商事判决必须是“不可推翻的终局性判决”。正如香港人士指出的那样:“有关终局判决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却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法律冲突问题”。(注: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副法律政策专员黄继儿:《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民商事宜在司法方面的合作和互助》(提纲初稿),广东省法学会港澳法研究会2002年度学术年会论文。)因为根据香港法例规定,“判决对诉讼各方而言,是最终及不可推翻的。(注:香港法例319章3(2)a.)香港法院在有关的判例中拒绝承认内地法院的判决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因为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认为“内地的判决并不是终局性判决”。(注:香港高等法院林哲民VS林志滔案(CACV354/2001)及集友银行VS陈天君案(Chiyu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V Chan Tin Kwun HCA 1168 of 1995)。香港法院对该两案件均以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法院的判决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终及不可推翻的判决,从而拒绝执行两法院的判决。)特别重要的是,香港政务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相互执行商事判决的安排建议》中指出“有关安排只容许执行最终且不可推翻的判决”。(注:立法全CB(2)1431/01-02(01)号文件。)而在对建议的咨询结果的有关文件中,有回应者则认为,要坚持采用普通法的方法处理终局判决的问题。也有回应者强调在有关安排中清楚界定“最终及不可推翻的重要性”。(注:立法会CB(2)2020/01-02(01)号文件。)香港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内地不存在终局判决,因为内地实行二审终审判,另外还设有审判监督程序,依据该程序,理论上任何生效判决都可能被推翻后再审,包括再审后的生效判决也有可能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综观香港安排建议的内容以及香港法律人士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内地与香港在内地法院判决是否为可执行的终局性判决问题上分歧较大,短期内是难以协调的。这个问题已成为阻碍实现两地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有关中国内地判决不是“终局性判决”质疑
的确,根据普遍的国际惯例,判决国的判决要在他国(法域)获得承认和执行,判决国的判决所确定的权利必须是确定的、具体的和可执行的,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非经特别的程序不得变更。正如在国内法上具有执行力的判决也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各国(法域)将我国需在外法域申请承认和执行判决的确定性作为该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条件是合理的。赋予权益已经确定的判决的执行力,一方面避免了重复诉讼带来的双重浪费,也避免了对判决胜诉一方的无理骚扰,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但是,由于内地和香港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系,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很大,香港法律界人士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了解甚少,以内地存在着两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以此认定内地判决并非“终局性”判决,从而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内地的判决,这既与中国的实际不符,也同国际上普遍通行的有关可供执行判决必须是“确定的判决”有偏差,甚至也违背了香港本身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一)国际上有关“终局性判决”的含义
各国国内立法或相关的国际条约都规定,本国只承认和执行外国确定性的判决。这里的“确定性判决”,即香港所指的“终局性判决”。关于“确定性判决”或“终局性判决”,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和理解。日本学者就认为,确定的判决是指对私法法律关系方面的诉讼有管辖权的外国司法机关所作的终审判决,即外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已经终结,已经不能因不服而提起上诉的那种判决,中间判决不属于此例。(注: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中译版,第200页。)《日本民事诉讼法》第515条第2款第1项规定,在没有证明外国法院判决是“已经确定的判决”时,可以驳回执行请求。
英国普通法所指“终局性判决”,是指享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必须是已经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且不会变更的判决;是偿付税后金钱和利息已经在判决中确定的终审判决;是没有对判决的事实或适用的法律提起上诉,并且上诉期已经届满的判决。(注:威廉·泰特雷:《国际冲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页。)
1971年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第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承认执行判决的条件之一为:“判决在原判决国不能再作为普通程序的上诉标的的”;第2款还规定:“为了使在被请求国可以执行,判决应该在原判决国是可以执行的。”1968年欧共体布鲁塞尔《国际民商事司法管辖权与判决执行公约》第29条也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外国判决不能成为实质性再审的对象。”(注:卢峻主编:《国际私法公约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页。)
(二)“终局性判决”并非是绝对不可变更的判决
应当特别指出,“终局性判决”或是“确定性判决”并非是绝对不可变更的判决。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其中尤以普通法与英国和美国法律的规定最有代表性。
英国法理论认为:判决是终局的,这并不是指这个判决必须是用任何方法都不能企图变更的判决。对于这个判决,或许可以提起事实审或法律审上诉,或者上告;即使上诉尚在进行,也不妨碍英格兰法院将判决作为终局的判决对待。即英格兰法院也会承认和执行这类外国判决。英国成文法也有这样的规定。1993年英国《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第1条第3款规定:为适用本条的目的,即使某一判决在原判决法院国的任何法院中可能存在一个对该判决的上诉抗辩,或仍然可以被提起上诉,也应该被认为是终局的和确定的判决。(注:《国际司法协助条约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译,第105页。)美国法上的终局判决,指的是法院最终判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及诉讼中的一切争点,致使该法院不用再作出任何解决整个案件争议的判决行为。终局判决的范围比确定判决广泛,可以变更的判决和可以上诉的判决,都是终局判决的种类之一。对于这两种终局判决,美国法院多数愿意承认和执行。对于可以变更的外国判决,根据美国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美国法院在倾向于承认和执行的同时,允许当事人在执行法院提起变更之诉。对于可以上诉的判决,美国法院也愿意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同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保护败诉方当事人。
有关国际条约也有相关的规定,如1971年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规定判决确定力的意义是“判决在原判决国不能再作为普通程序的上诉标的的”。这里面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即运用原判决国的法律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如果外国判决依据原判决国的普通程序已终结,即使根据其诉讼法的特殊程序可能对判决变更的,也不影响判决的确定力,他国也应当依公约的规定对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终局性判决”或“确定性判决”是根据判决国法律认定的
对于终局性判决的认定,主要涉及判决终局性认定的依据、与终审性判决的关系以及与法律补救程序的关系等几个问题。
首先,对于终局性判决的认定的依据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某一外国司法判决是否是终局的判决应该依据外国法院国的法律,而不是内国法来解决,因为只有作出判决的法院才有权决定其作出判决的法律意义。如美国《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第481条之评论5就认为,在确定某一外国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的问题上,应当适用判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而不是美国的法律。
其次,对于终局性与终审的关系,根据各国的实践,许多国家以外国法院的中间裁定或判决,如先行给付的裁决、诉讼保全的裁决等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因此,终局性或确定性不应该仅仅限于终审判决。“终局性”不等于“终审”,事实上,“确定性”的用法也许更为合理而不至于产生歧义。
最后,在终局性与法律补救程序的关系问题上,判决的确定性无疑是重要的,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即使为了保证判决的确定性,以维护法律权威的目的,也不能完全抹煞法律补救程序的作用。毕竟法律往往会涉及剥夺当事人的权利、权益甚至自由、生命,设置一些必要的法律补救程序,使得某些确实错误的判决有转弯的余地,也是保障民主与人权的需要。为了防止滥用,可以限定严格的适用条件,但是毫无疑问,该制度是不能完全被取缔的。所以,即使是终局性判决,也应该可以满足一定条件时求助于特别法律补救程序,如请求撤销、重审、或提出合法性异议。
(四)申诉、再审、审判监督程序不改变中国法院判决是可执行的确定性判决的法律性质
1.中国法院的判决是可供执行有法律拘束力的确定判决,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中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相互承认外国民商事判决的程序和条件,其中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条件中,规定了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或裁决必须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中国法院的判决需要在国外申请执行的,也必须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见《民事诉讼法》第267-268条)。中国内地与世界30多个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中,在有关相互承认和执行民事判决规定中,各以判决为“确定性判决”或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为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前提条件。迄今,尚未有以中国判决不是“确定性判决”而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发生,这说明依中国法律程序作出的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可为其他国家法律承认和执行的有效裁判。
2.中国有关“确定性判决”理论同国际上通行理论是一致的
在中国,一个“确定性判决”和“终局性判决”应该是相似的。一个确定性判决可以定义为:“由一国法院或有审判权的其他机关按照其内国法所规定的程序,对诉讼案件中的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所作的具有约束力,而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当某一判决不能再被提出法律补救的争辩时,它就是一个‘终局性判决’,但即使终局性判决也可以求助于特别的法律补救程序,如请求撤销,重审,或提出合法性异议”。
3.根据香港的法律,有关“终局性判决”并非是绝对不可变更或不可执行的判决
前文已说明,在普通法的惯例上,外国判决即使可以上诉,甚至上诉在判决国正在进行,也可以是终局性判决,也可以在被请求国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就是说,外国判决要在被申请国有效,不一定必须是不能向高一级法院上诉的判决,所谓“终局性判决”是指作出判决的法院必须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
香港法例第319条第3(3)条也承认普通法的该项惯例:“即使在诉讼法庭的国家的法院中,针对有关判决的上诉仍未了结,或仍有可能针对有关判决提出上诉,该判决仍须当作最终及不可推翻的判决。由此可见根据香港法律,中国内地申诉、再审、审判监督程序不改变经中国终审程序作出终审判决的法律效力。中国内地实行二审终审判,任何民商事案件经二审审判作出判决就是有法律拘束力的可执行的终局性判决,非经特别程序而不得予以变更。香港不能因内地有此程序的存在,而得出内地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性判决的结论,更不能以此作为推翻承认和执行内地法院判决的理由。
三、参照国际条约的规定解决内地与香港有关“终局性判决”的争议
有关中国内地法院判决是否为“终局性判决”的争议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地就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作出安排。解决争议的办法,不是一定要根据中国内地法律规定,也非依照香港方的要求,改变内地长期形成的司法制度(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内地与香港都可参照最新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调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199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开始制定的并即将获得通过的《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的规定,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有关争议的思路。
2003年3月25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正式工作小组对判决承认执行的初步草案在第三次会议作出了评论报告,在该报告中的第7条和第4、第5项详细地讨论了该草案第7条是否应当包括提交承认或执行的判决须为“终决”及在原审国有定案效力或执行力的要求的问题。
在1999年文本中,为了在条约中被承认,一项判决必须在原审国有定案效力。在2001年文本中,认为技术术语比如说“定案效力”或“执行力”可能在所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统一的含义。因此,讨论组试图通过不进一步强调第2条(1)(C)所包含的定义来避免此类术语,并且,作为第一步,将第7条关于承认和执行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判决。然后,为了保护被告并且为了达到2001年草案第25条(2)-(4)所作出的不同的内容所希望的目标,会议认为需要增加下述保护条款:
第7条(4)讨论了在终决和定案效力上,为了不使用此类术语而得到承认和执行的问题,条文阐明了一个判决在被申请法院不能比原审国有更优先的效力。因此,在原审国,一项仍然提交复审的判决还没有对当事方产生任何拘束力(虽然是暂时的),该效果也同样适用于被申请法院。
然而,仍然提交复审的判决在原审国是有执行力的,在第7条(4)下,在原审国该判决原则上可执行的,在该阶段,第7条(5)引进了保护败诉方的进一步的机制。即:“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可能会被没有偏见地中止或终止,如果在原审国家判决是有争议的或寻求一般的救济的时间的期间还没有结束”。
在这里,“没有偏见地中止或终止”的语句在国内程序中是根据存在的不同而使用的。在一些国家,对外国判决拒绝承认或执行仅仅建立在该判决仍然提交复审的事实上,或是在原审国一般复审的期限还没有届满。在这些国家,这样的判决将排除申请者在排除申请障碍之后重新递交的申请情况。在其他国家最初的申请在排除障碍之前仅仅是中止。因此,“选择”的提法将保证一项对原审国判决承认或执行的申请仅仅因为该判决仍然提交复审,或在原审国一般复审期限尚未届满而被拒绝的情况可能在稍后的时期内不被重新申请执行排除在外,即使内国程序也规定先前的申请被一项判决或命令所排除。
在原审国一项判决实际已在复审中的情况下,足以引起第7条(5)的适用。尽管没有要求上诉,然而,第7条(5)要求寻求一般复审的时间限制并没有届满。
由上可见,海牙国际私法全文对该问题的思路是为了避免各国对“终局判决”等提法的不同含义产生歧义和误解,从判决在原审国与申请国的效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判决在被申请法院不能有比原审国更优先的效力,并且对问题的处理提倡的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给法院一种自由选择的幅度,对复审中的判决可以根据各国实践中止或终止,但是又强调这种中止或终止必须是“没有偏见的”。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规定,值得内地和香港借鉴学习,以便从中找出解决争议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