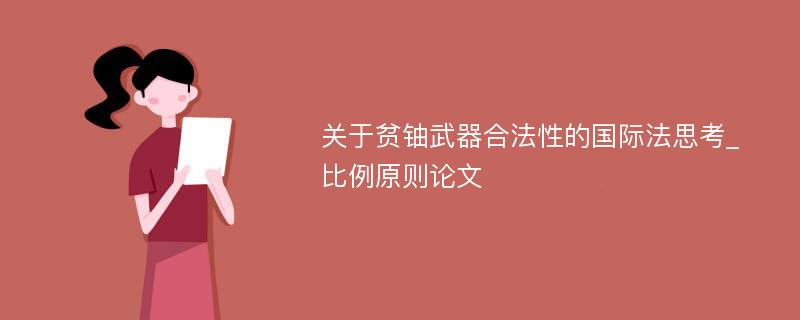
贫铀武器合法性的国际法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铀论文,国际法论文,合法性论文,武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1)02-0077-07
2010年12月8日,第65届联合国大会第60次全体会议通过55号决议《使用贫铀武器弹药的影响》,其中148票赞成,法国、以色列、英国、美国4国反对,30个国家弃权,另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缺席[1]。2007年第62届联合国大会、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均曾通过同名决议,三年来,赞成票数不断增加,弃权国家不断减少,缺席国家不断减少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使用贫铀武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潜在有害影响。本文拟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使用贫铀武器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贫铀武器简介
贫铀是浓缩核武器原料和核电站燃料铀235的副产品[2]53,易燃易爆,在室温条件下能够自燃,撞击或摩擦可发生爆炸,加入钛制成贫铀合金其强度和硬度远超出钢[3]。广义的贫铀武器是指以贫铀为原料制成的枪弹、炮弹、炸弹和地雷的总称[2]57-63,由于各种口径的炮弹占大部分,本文所称的贫铀武器特指贫铀穿甲炮弹。贫铀武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坦克装甲日益坚硬,原有的穿甲材料不再理想,必须寻找穿甲能力更强的材料,其次由于贫铀本是有大量库存的核废料,制成武器是一举两得的处理方法。海湾战争期间,美英军队首次使用了贫铀武器,随后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继续使用贫铀武器。
贫铀武器引发了关于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巨大争议,据信,所谓“海湾战争综合症”和“巴尔干综合症”与使用贫铀武器有关[4],学术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因此展开了多项研究或调查②。贫铀对人体和环境的损害往往不是即刻,而是受剂量、地形、气候、植被等多种因素影响缓慢呈现出来。一般承认贫铀对健康的短期影响主要归因于其化学毒性,而长期影响是放射损伤与化学毒性的联合效应,特别是贫铀释放的α粒子,其致癌性不容忽视[5]。即贫铀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长期影响,需要更多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果。
贫铀武器不发生核裂变或核聚变,不属于核武器,也不是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四个附加议定书调整范围也不包括贫铀武器。考虑到贫铀武器对人体可能造成的损害,将其归为有毒武器(poisonedd weapons)似乎符合逻辑,而相关国际公约③和国际习惯法④明确禁止使用毒物(poison)或有毒武器,然而国际法上并不存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定义。根据常识,毒物是指“无论天然抑或合成的任何物质,当达到一定剂量时,将损害活体组织或造成伤亡”[6]。如果以此为标准,当造成伤亡时,贫铀武器将构成有毒武器进而被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明确禁止,然而,国际法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993年《前南刑庭规约》第3条第1款规定,前南刑庭对于“使用蓄意导致不必要痛苦的有毒武器或其他武器”的违反战争法或国际习惯法的行为具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其1996年《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以下简称《核武器咨询意见》)中认为在国家实践中,“毒物或有毒武器”通常是指“主要甚至唯一效果是导致中毒或窒息”[7]26;负责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6年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中第20条“战争罪”第5款第1项采取了与《前南刑庭规约》第3条第1款完全一致的措辞。这些规定意味着只有“蓄意”造成不必要痛苦或“主要或唯一效果”是导致中毒或窒息的武器才是有毒武器,而贫铀武器主要目的⑤和功能是穿甲,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损害是副作用而非“蓄意”导致,以此推断,贫铀武器不属于有毒武器,因此不被有关国际法禁止。然而,除了贫铀武器的主要使用国美国和英国强烈支持这种观点⑥,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明确将“毒物或有毒武器”仅限于主要或唯一目的是导致中毒的物质或武器[8]。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2项第17目规定“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构成战争罪,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犯罪要件》就该目规定了四项犯罪要件,第1项规定“行为人使用一种物质,或一种导致释放某种物质的武器”,第2项规定“这种物质凭借其毒性,在一般情况下会致死或严重损害健康”。贫铀武器可能产生“致死或严重损害健康”的结果,因此符合《罗马规约》该目关于战争罪的规定,结合《罗马规约》第30条“心理要件”⑦,如果意识到在一般情况下会产生致死或严重损害健康的结果,使用贫铀武器将构成战争罪并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或证明贫铀武器会产生“致死或严重损害健康”的结果,如上所述,学术界对此有很大争议,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将贫铀武器归为国际法上某类武器的做法未能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使用有关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进一步分析。
二、贫铀武器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
国际人道法的四个核心原则分别是区分原则、军事必要原则、不必要痛苦原则和比例原则,实际上所有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问题或事情都可以通过这四个原则予以检验,这四个原则不仅是有关联,而且是无法分开地交织缠绕在一起。任何不必要的即缺乏军事必要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不必要的痛苦,并导致平民死亡很可能不成比例,而不成比例的攻击往往违反了区分原则。违反这四项原则中的一个也违反了另外一个,常常是两个,有时是三个[9]。
区分原则是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始终对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加以区别,是国际人道法最重要的原则,没有区分原则,国际人道法便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区分原则在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⑧中均得到确认,如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惯例公约》⑨、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1977年《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对日内瓦第四公约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实际上成为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最主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第48条规定“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因此,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中认为国际人道法的第一个主要原则是“保护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以及确立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国家绝不能将平民作为攻击对象,而且因此绝不能使用无法区分平民与军事目标的武器”,并且“无论是否批准了包含这些基本规则的公约,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因为它们构成国际习惯法不可动摇的原则”[7]35。从区分原则中衍生出若干具体规则,如比例原则⑩,既有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一般保护,又有对特定行为如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报复攻击等的禁止,以及对文物和礼拜场所、对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自然环境、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等特定物体的保护,也要求在进行军事行动时,应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居民、平民和民用物体,即采取预防措施(11)。其中,无论使用何种作战方式或手段,均禁止攻击民用物体、文物和礼拜场所、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贫铀武器也不例外,因此不在讨论范围内。贫铀武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文将讨论。与贫铀武器之间的关系不能立刻判定的规则包括: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及比例原则(《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1条第4、5款),对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4条),采取预防措施(《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7、58条),这些规则都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范(12),适用所有国家。
(一)贫铀武器与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
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1条“对平民居民的保护”第1款首先阐明“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受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总的原则,然后用具体规定确定对平民的保护。第4、5两款关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第4款开头便阐明“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进而列举了三种情形,第5款接着列举了两种应被视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的情形。第4款第1项规定“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也就是说,任何作战方法或手段,包括贫铀武器,如果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则不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如果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则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因此该项本身并不禁止贫铀武器,只要贫铀武器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第2项规定“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但贫铀武器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而且事实上精确打击正是其实现穿甲功能的必要手段,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武器以实现精确打击为主要特征,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包括贫铀武器在内的很多武器不受该项制约。如果以效果为标准推测该项的含义,即使用效果会“溢出”特定军事目标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又会使接下来的第3项显得多余,因此,按字面意思理解该项较为恰当,即贫铀武器不受该项调整;第3项规定“使用其效果不能按照本议定书的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即尽管使用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是针对特定军事目标而且能将其作为对象,但实际效果如果不能按照《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的要求加以限制,也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该项并没有说明《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的要求具体指什么,按照逻辑,议定书中所有关于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要求均包括在内,如第51条第1款这种原则性要求和第55条“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第56条“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的保护”等具体要求。至此,可以发现第51条第4款的逻辑顺序是按照“对象—方法或手段—效果”层层递进的,关于效果的规定意图穷尽所有可能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而且使用了“按照本议定书的要求”这样解释空间很大的措辞。问题在于,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对平民及民用物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第3项规定的效果即平民伤亡或民用物体的损坏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即根据比例原则不超过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应有的伤亡或损坏限度,否则任何军事行动将无法进行,国际人道法调和折中人道精神与军事必要的目的便失去根基。比例原则在第51条第5款第2项中有所规定,“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即违反了比例原则的进攻应被视为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而予以禁止,在第57条“攻击时预防措施”第2款第1项第2目也有类似反映。适用比例原则最大的问题在于标准无法量化,如何判断“过分”与否没有明确依据,只能一事一议。贫铀武器给人体和环境带来的损害需要较长时间才可能显现,而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损害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可能“过分”,但有时也可能不会,即使用贫铀武器是否构成第51条第4款第3项或第5款第2项规定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贫铀武器与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4条第1款禁止以作战方法使平民陷于饥饿,第2款禁止攻击、毁坏、移动或使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失去效用。对使用任何作战方法或手段来说,以作战方法使平民陷于饥饿或攻击、毁坏、移动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是无疑被禁止的,但贫铀武器能否使这些物体“失去效用”,并不能立即得出结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大量的贫铀很有可能进入供水系统和食物链”[10]vi进而污染水源和食物。根据第2款,“……基于使……对平民居民失去供养价值的特定目的”,即要求行为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蓄意的,而贫铀武器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是穿甲,污染环境是副作用,因此,如果不能证实使用贫铀武器是蓄意使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失去效用,单凭其造成水源或食物污染的结果,尚不足以说明使用贫铀武器违反该条规定。
(三)贫铀武器与预防措施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7、58条规定了在攻击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及尽一切可能减少攻击对平民的影响,其中第58条规定将平民和民用物体迁离军事目标附近、避免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稠密区或其附近、采取其他必要预防措施使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军事行动危害等适用任何作战方法或手段,不在讨论范围内。第57条第2款第1项第2目规定,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在选择攻击方法或手段时,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以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平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第3目规定“不决定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重申了比例原则。也就是说,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如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无论实际效果如何,都违反了有关规定。贫铀武器对人体和自然环境造成损害的必然因果关系和损害程度虽有待进一步确定,但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贫铀武器并非独一无二的穿甲武器,常规穿甲材料钨合金可以起到同样作用,只是效果稍差。简而言之,如果“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即用常规穿甲材料代替贫铀武器,完全可以避免贫铀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损害,因此,使用贫铀武器违反了该规定。
三、贫铀武器与军事必要原则、不必要痛苦原则
如同比例原则与区分原则紧密相连,军事必要原则与不必要痛苦原则亦密切相关。军事必要原则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后两个发展阶段,其含义也发生很大改变,二战前军事必要原则强调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解除战争法的约束力,二战后军事必要原则强调在军事必要性与人道精神之间寻找平衡[11]。军事必要原则包含允许和禁止两方面,一方面允许使用任何“根据现代战争法和战争惯例合法的且对于确保战争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一方面禁止使用任何不是“不可缺少的”且不是为了确保战争目标的手段[12],军事必要原则也要求不应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超出所需的武力或暴力[13],即不致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首次提及军事必要原则,在开始的第一段话中即宣告“……普遍同意确定战争的必要应服从人性的要求这一技术限制”,在结束的最后一段话中又提及“……调和战争的必要与人道法的要求”,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序言中均提及“……在军事必要允许的情况下,受减少战争不幸的愿望激发……”,公约附件第23条第8款均特别禁止“摧毁或没收敌方财产,除非是基于战争的必要”,《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2项第13目也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措辞。实践中,军事必要原则常常与不必要痛苦原则和比例原则联系在一起。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性质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是一项久已确立并得到广泛承认的国际人道法原则,在多个国际公约中有所规定并形成国际习惯法规范(13)。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首次对禁止使用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这一原则进行了确认和编纂(14),其后,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附件第23条第5款特别禁止使用具有引起过分伤害性质的武器、投射体或物质,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附件仍在第23条第5款对此作出规定,但措辞略有不同,特别禁止“使用蓄意导致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体或物质”,学界因此通常使用“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这种说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5条第2款宣布“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性质的武器、投射体和物质及作战方法”为关于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1997年《渥太华禁雷公约》、1998年《罗马规约》均对此作出规定(15),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中认为国际人道法的主要原则包括“禁止引起战斗员不必要痛苦,相应地禁止使用带来如此伤害或无用地加剧痛苦的武器”,并且“无论是否批准了包含这些基本规则的公约,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因为它们构成国际习惯法不可动摇的原则”[7]35。
尽管不必要痛苦原则得到多个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法的确认,但实践中会遇到若干问题。首先,如何确定哪些作战方法或手段受该原则调整?标准或根据是什么?应该说,不必要痛苦原则使用抽象的措辞正是意图全面禁止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方法或手段,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作战方法或手段会标明自己能否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这就必须按照比例原则、军事必要原则进行具体分析。已有的实践证明,某些武器无论怎样使用,都会产生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如《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涉及的碎片无法检测的武器、地雷、燃烧武器、激光致盲武器等;但其他武器,如贫铀武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会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产生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而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会,因此只有一事一议予以判断。其次,该原则是本身足以起到禁止作用,还是需要根据特定的国际公约来补充或执行?目前已被完全禁止的武器都有相对应的国际公约加以详细规定,但如果不必要痛苦原则本身不足以自行,那么有关公约条款又意义何在?《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6条“新武器”规定,“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缔约一方有义务断定,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该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所禁止”,即确认了反映不必要痛苦原则的第35条第2款以及其他国际公约有关条款可以独立适用。
四、贫铀武器与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马尔顿条款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或手段在多个国际条约和公约中有所规定(16),并已成为国际习惯法的规范(17)。《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5条第3款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手段或方法”为关于作战方法和手段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对民用物体的保护部分中又以第55条第1款规定“在作战中,应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不受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这种保护包括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这种损害从而妨碍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手段或方法”。第55条第1款实际上是重申和进一步说明第35条第3款,其第二句中使用“包括”一词意在举例。根据这两款规定,只要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就违反了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或手段原则,无论是否“妨碍居民的健康和生存”。但《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并未说明什么构成“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国家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共识。贫铀武器确有可能损害环境,但如上所述,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而且,即使贫铀武器确实会损害环境,但这种损害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又需要证明。已有的研究、调查和报告声称“未发现贫铀对地表的广泛污染”,“未在有关地点发现空气、水、植被受污染的重大危险”[14],确认贫铀武器对地表污染只局限于受影响地点几十米范围内[10]vi,土壤深处可能埋藏有大量贫铀,可能在未来造成地表水和饮用水污染[15]。目前看来,不能认为贫铀武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一般意义上的“长期、广泛和严重的损害”,因此也无法认为使用贫铀武器违反了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或手段这一规则。
马尔顿条款(The Martens Clause)最早出现在俄国律师、圣彼得堡大学国际法教授马尔顿起草并于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提交的陆战法规惯例公约草案中[16]125,后来出现在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序言中,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5条“一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2款采取了与《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几乎一样的措辞,宣布“在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定所未包括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1977年《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即《日内瓦四公约第二议定书》)前言也规定,“在现行法律所未包括的情形下,人仍受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保护”。但是,马尔顿条款本身并未规定违反后将如何处理,其主要组成部分“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也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国际法原则或规则,马尔顿条款主要用来作为解释国际人道法的原则指引,即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则应按照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予以解释;在关于国际人道法的渊源问题上,马尔顿条款可以降低国际习惯法对通例的要求,同时将法律确信(opinio juris/opinio necessitatis)提高到比一般承认更高的层级中[17]。简而言之,马尔顿条款是为了“对付军事科技的迅速发展”[7]35,因为法律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现实,而尚未被国际条约禁止的未必就是合法,马尔顿条款对国际习惯法起到保障作用[18],在缺乏具体条约规定时适用[19]。根据马尔顿条款,国际条约不禁止贫铀武器不说明贫铀武器不违反国际法(18),即使现在或将来国际条约均未禁止贫铀武器,贫铀武器仍需遵守国际习惯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则,如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军事必要原则、不必要痛苦原则等。
五、结论
贫铀武器作为一种穿甲性能卓越的新式武器,并不受已有的禁止使用特定武器的国际公约调整。使用贫铀武器在某些情况下会构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也会导致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违反区分原则、比例原则与军事必要原则。如果不是蓄意,使用贫铀武器不违反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这一规则。使用贫铀武器也不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或手段的规定,但违反预防措施规则。因此,总体来看,贫铀武器不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和规则,并不合法。贫铀武器与相关国际人道法原则或规则间之所以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贫铀武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的是潜在的或长期的而不是即刻的影响,只有通过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贫铀武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人体健康和环境。但无论如何,贫铀武器有损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险,应根据预防措施规则禁止使用。
收稿日期:2010-11-10
注释:
①2007年第62届联合国大会第61次全体会议以136票赞成、5票反对、36国弃权、15国缺席通过第30号同名决议,2008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第61次全体会议以141票赞成、4票反对、34国弃权、13国缺席通过第54号同名决议。参见A/RES/62/30,ANNEX XII Vote on Effects of Depleted Uranium[DB/OL].[2010-12-18]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7/ga10666.doc.htm; A/RES/63/54,ANNEX XIII Vote on Use of Armaments and Ammunitions Containing Depleted Uranium[DB/OL].[2010-12-18]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8/ga10792.doc.htm.
②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来自医学界和生物学界,国家如美国于1998年和2000年发布过关于海湾战争期间使用贫铀武器的报告,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发布过多项关于贫铀武器的调查和报告,还有一些其他主体如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兰德公司等也发布过有关报告。
③如1899年和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附件第23条第1款均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谴责并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液体、材料或装置”,规定这种禁止“应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为普遍接受,对国家的良知和实践都有约束力”。
④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51-254;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590-1603.
⑤有学者正是将“主要目的”作为反对使用贫铀武器的一个出发点,认为使用某种武器是否“想要”(intended)对平民产生有害后果应取决于事实上是否会产生负面效果,使用贫铀武器的国家单纯从“主要目的”来辩解使用贫铀武器不是想要产生化学和放射效果,“如同阿拉丁否认神灯中有精灵一样”。参见Owen Thomas Gibbons.Uses And Effects Of Depleted Uranium Munitions:Towards A Moratorium On Use[J].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2004,(Vol.7):227.但是,不能否认,当初之所以研发贫铀武器,正是因为贫铀合金出色的穿甲能力,而且贫铀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附带损害,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利益可言。任何武器,早在设计之时,就一定有其主要目的,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也会有除了主要目的外的其他效果,例如,我们不能因为炸弹确实会把地面炸出大坑,就认为炸弹“想要”把地面炸出大坑。不考虑主要目的或将目的与效果混同,会导致论证有瑕疵,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禁止使用贫铀武器的说服力。
⑥参见US.Written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ICJ,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20 June 1995[R].1995:24; UK.Written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ICJ,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16 June 1995[R].1995:para.3.59 and 3.60.
⑦该条规定,“只有当某人在故意和明知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物质要件,该人才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并受到处罚”,而“故意”包括“就行为而言,该人有意从事该行为”和“就结果而言,该人有意造成该结果,或者意识到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该结果”,“明知”是指“意识到存在某种情况,或者事态的一般发展会产生某种结果”。
⑧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76;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450.
⑨不过这两个公约并没有以专门条款明确提及战时对平民的保护,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在其序言中阐明“……居民(populations)和交战者仍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1907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在其序言中阐明“……居民(inhabitants)和交战者仍受万国法(law of nations)原则的保护”,但无论如何,这两个公约是将交战者和非交战者(居民)区别看待。
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比例原则视为从属于区分原则,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46-50.
(11)参见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50-58条。
(12)关于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7-45;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 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47-296;关于比例原则,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46-50;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97-335;关于对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89-193;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148-1165;关于采取预防措施,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51-76;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36-450.
(13)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37-244;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505-1554.
(14)《圣彼得堡宣言》宣布缔约国在彼此间的战争中放弃使用任何轻于400克的爆炸性或装有易爆易燃物质的投射体(projectiles),其序言阐明:“战争期间国家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武装力量;为该目的使尽可能多的人丧失能力已足够;如果使用无用地加剧已丧失能力的人的痛苦或使其死亡不可避免的武器,便超出了该目标;因此,使用这样的武器和人道法相悖。”
(15)参见《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序言,第二附加议定书第6条第2款、1996年修正后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第3条第3款;《渥太华禁雷公约》序言;《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第2项第20目。
(16)除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外,还有1976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98年《罗马规约》等。
(17)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Ru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43-158;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844-912.
(18)有意思的是,前南刑庭恰恰持相反观点,前南刑庭在其2000年关于北约轰炸南联盟最后报告中认为“没有特别条约禁止使用贫铀投射物”,因此目前并不违反国际法。参见ICTY.Final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by the Committee Established to Review the NATO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R].2000:Section A,part ii,para.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