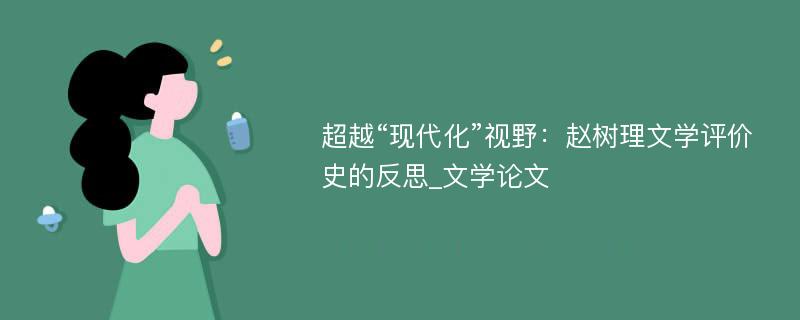
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野论文,评价论文,赵树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3)04-0054-07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存在。这种暧昧性,直接地表现为各个时期对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不稳定性和评论尺度的内在分歧。这也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史形象常常是模糊的与不确定的: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赵树理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作家,而另一些评论者则可能认为,正是这种“土”本身却是极为“现代”的产物;一些人认为赵树理不过是40-60年代政治文学运作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正因为对抗这一政治运作才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一种观点认为赵树理只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契机造就的宣传家,和执著于过时的保守观念的旧式农民作家,而另一种观点可能认为在“宣传性”与“固执”之间,赵树理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创造……
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所有价值判断所无法涵盖的剩余物,并不总是表明赵树理文学是某种“不成熟”的产物,而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借以做出这些判断的理论框架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与限度。所谓“削足适履”,也就是赵树理文学具有着超出这些理论框架的丰富内涵。赵树理之不断被命名而又反复地不能得到命名,显示的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赵树理文学的暧昧性,不仅表明中国现代文学评价尺度的内在不统一,更显示出了其自身的丰富性与无法被单一现代性想象所涵盖的复杂性。正视赵树理文学评价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
问题的讨论,可以从赵树理文学的评价史,即各个时期具体的也是历史的批评实践开始。
一 赵树理的“新奇”性
1940年代,当赵树理带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出现在中国文坛时,人们用以评价他的最重要语汇,大约就是“新奇性”及其出现在文坛的“突然性”。周扬在那篇奠定了赵树理基本文学史地位的重头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中,称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郭沫若则把赵树理和他的作品看作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与那些“庭园花木”相比,“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②。作为赵树理同代作家的孙犁,在1979年写作的回忆文章中,则干脆用“陡然兴起”、“时势造英雄”来形容赵树理出现的突然性③。
用“新奇”与“突然”这样的语汇来评价赵树理文学,这本身就包含着暧昧的张力。一方面,人们用这样的语汇来表达一种欣喜,好像期待许久的事物“突然”被一个不知名的新作家所实现。周扬在赞扬与提携赵树理这样一个“新人”时,称赞他“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他的出现“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孙犁在时隔30年后则这样写道:“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④。茅盾的评价略显犹豫,他一边赞美《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他也有所保留:“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⑤。不过,就在茅盾发表这番言论的第二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的创作路径被推崇为样板性的“方向”:这次座谈会的结论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为题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⑥。
与“不期而遇”构成张力的,是“新奇”、“陡然”这样的语汇,同时隐含着赵树理文学在中国文坛出现的“突发性”、“偶然性”和“不连续性”。也就是说,赵树理文学无疑是“新”的,但他却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必然”的和“内在”的产物,而携带着相当多难以指认或标准之外的“剩余物”。正是这些剩余物的存在,导致对赵树理评价的种种分歧。
多种赵树理传记都会提到,赵树理成名之前,与抗战期间的太行山区文联主流观念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也导致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发表过程的曲折和艰难⑦。即便在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明星”作家亮相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前后,关于《邪不压正》引起的争议仍在继续。如果考虑到在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当时,“解放区文艺”被认为是“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讲话》的方向,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⑧,那么,竹可羽等人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出赵树理小说没有揭示出“历史的本质”、“人物创造,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批评⑨,就显得意味深长。
此后,即便在1950年代赵树理被授予“语言艺术大师”这种崇高称号的时候,人们还是不忘记同时提醒他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壮阔波澜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⑩,对人物的思想描写和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11)。这几乎也成了1949年以后,当代文坛关于赵树理文学评价的一个定论,以致中央领导也需要特别地安排赵树理的读书活动:“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12)。但到了1960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的作品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铁笔”、“圣手”。但这种评价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赵树理的改变,而是在“现实主义深化”这一理论命题下人们评价标准的变化。这意味着曾经被视为“缺点”的赵树理文学的某些构成要素,这个时期又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批判现实的文学品质。
可以说,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转移导致了评论界对赵树理文学的不同评价。而有意味的是,这些不同的评价,却是以对赵树理文学的某种一致判断作为前提的。
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外
在40-60年代的主流话语框架中,在左翼文坛批评话语内部,赵树理评价的暧昧性实则突出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源自前苏联、而被中国文坛视为创制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理论原则——自身包含的两义性与摇摆性。正如佛克马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即是一种“折衷方案”,意思是“既要描写那些可以被看作是现实的东西也要描写那些还不是现实的东西”;侧重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还是“浪漫主义”成分、作家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作为“教育家或宣传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回答”(13)。也就是说,从“浪漫主义”(“社会主义”)这一维度还是从“现实主义”这一面向,即便是同一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评判结论。这一创作设想在1930年代即引入中国左翼文坛,在1953年亚洲冷战格局明朗化而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形下,则被确定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4)。竹可羽式的主流批评和60年代初期对赵树理的重新肯定,正是将这一理论原则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两种不同后果。
在80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中,竹可羽式的批评(其极端形态表现为1959年武养对《“锻炼锻炼”》的激烈否定),常常被视为“极左”文艺路线对赵树理创作的恶意歪曲和武断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并不采取一种辩护式的研究姿态,即在批判“极左”路线这个前提下把研究作为回护赵树理文学价值的方式,而是进一步观察两种分歧的内在理路的话,可以发现,40年代关于赵树理的“发现”和“命名”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种激进批评的可能性。
40年代批评界对赵树理文学的命名始终包含着两个面向,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的说法,一是“政治性”强,表现在反映“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矛盾”(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面向),一是创造了“民族新形式”,表现在“选择群众的活的语言”、“着重写故事”、“不作与现实斗争无关的叙述和描写”(这被理解为其“现实主义”的面向)。但是,这两个面向在不同的评论者那里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赵树理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突出的是前一面向;强调赵树理小说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文学形式,突出的则是后一面向。更复杂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原则的两面性,其实呼应的正是“当代文学”得以诞生的基本历史语境内在的矛盾性。可以认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和1939-1941年由左翼文坛扩展至国统区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构成了塑造“当代文学”的两个主要话语事件。而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在《讲话》所侧重的“工农兵文艺”这一阶级维度与“民族形式”所侧重的文艺大众化这一民族维度之间,始终存在着并不明朗的紧张关系。如果“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学观中的主导的方面;5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口号的提出,是合乎逻辑的展开和延伸”(15),那么,竹可羽、武养式的激进批评(或批判)正是在这一脉络上的深入,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政治观念与理想的“历史本质性”。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则突出的是塑造一种包含普遍性的“国民文艺”构想的诉求。“工农兵”与“国民”之间的裂隙,并不能很快弥合。关键就在于,那些赵树理所最擅长书写的“落后的”“旧式”农民,到底应该在作为政治概念的“农民”/“阶级”意义上批评其不够先进,还是在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农民”的意义上赞扬其在文学中得以出场?这一分歧,不仅是“浪漫主义”(或“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延安文艺传统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分歧,它同时还表明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将自身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纳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现代世界的文学时,所必须完成的“质”的跳跃。
就赵树理文学的评价而言,如果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都能在赵树理文学中找到它们需要的东西,又同时感到不满足,那么就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即赵树理文学可能是一种既不能由“浪漫主义”也不能由“现实主义”加以描绘的文学形态,它可能根本就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得以出现并寄身其中的现代文学体制的“外面”。
无论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断裂和转型,它们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体制的创制,却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构造一种具有普遍涵盖性的国民文艺(文艺大众化),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和最终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试图在明确的政治实践层面上创造出“工农兵”这一能动的阶级主体,是对“国民”文艺的超越和更高意义上的实践,背后关涉的始终是现代国家、民族认同、国民、阶级、政党与现代文学体制的互相塑造。赵树理之“野性”,不仅因为他不在“文坛”(赵树理用以描述现代文学机制的语汇)之内,更在于他存在着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游离出“现代”的视野和文学实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现代理念与“现实主义”的历史经验之外或之中,赵树理或许塑造了一种新的历史想象方式。这也使得人们需要正面讨论,所谓“社会主义”到底该如何理解?赵树理的“社会主义”想象是否可能与当时的文坛主流、与政府推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是后来在“文革”中被妖魔化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别样的关系?如果说“现实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学体制的一种内在的创作原则,它乃是一种诞生于18-19世纪西方的现代认识论装置(借用福柯和柄谷行人的表述),那么赵树理的经验再现和现实书写与此会有所不同吗?或者说,赵树理是否创制了一种“别样”的而又是“现代”的文学?
——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视野来重读赵树理,或许可以在“是”或“不是”之间、“肯定”或“否定”之外,寻求另一种思考视野。
三 “现代”、“个体”及其外
与40-70年代评价的暧昧性相比,有趣的是,1980年代基于“反思”乃至“告别”40-70年代主流文学这一基本诉求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实践,给予赵树理的倒是相当明确的判断。不过,这种判断的明确性,与其说是对赵树理文学性质的准确概括,不如说更直接地凸显了“新时期”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限定。
在70-80年代之交完成的几本当代文学史(16)中,赵树理是被作为“17年文学”少有的几个经典作家而享有单章书写的殊荣的。但是,随着80年代中期的话语转换,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中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新启蒙话语,则将赵树理视为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代表作家而予以否弃。其典型论述,则是李泽厚所说的“文艺界古典之风空前吹起”、“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17)。赵树理文学,成为“农民文化”、“革命文化”、“前现代文化”、“封建文化”之间对等号的代表性呈现。在这种批评话语中,赵树理文学是“革命”的,但却是“封建”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论框架之中,填充的是中国农民文化、西方文化(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而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根本就是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启蒙文化,而导致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复辟。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整个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内在逻辑。
有意味的是,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格外明确地指认出了赵树理文学与“封建文化”(农民文化、前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后者其实也是《讲话》所强调的“工农兵文艺”,与“民族形式”论争所关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要在国际共产主义地缘政治格局中赋予中国革命以“中国性”的要素。在“新时期”的启蒙现代性视野中,中国的现代性本身似乎是不需要任何地缘性因素和“地方性知识”来确认其合法性的。但奇怪的是,在同一时期一篇更重要的近乎宣言性文章中,李泽厚在批判革命救亡导致西方文化启蒙在中国的不彻底并造成了封建主义复辟的同时,却又提出了“创造性转换”儒家文化传统的解决方案,似乎新儒家的传统文化与他所批判的“封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18)。将赵树理文学与“革命”、“封建”、“前现代”一同打包,扔进历史垃圾堆,不过是一个现代化意识形态高涨时代的政治策略。但无法忽略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赵树理文学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遗忘”(19):不止是赵树理的作品丧失了被人们阅读的兴趣,而且这些作品所书写的中国乡村社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得面目全非。
无论新时期文学出于何种意识形态需要而否定赵树理文学的意义,但不能否认的是,如何言说赵树理的“现代性”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其实也是伴随着1940年代赵树理成名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问题。
可以说,批评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其实就是用左翼的革命语言批评他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在1940年代访问过赵树理的一位美国记者那里,这一问题的表述则直接得多。1948年亲身进入中国解放区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一面说赵树理是“解放区除毛泽东、朱德之外最著名的人”,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不满:赵树理小说“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却没有反映出来”(20)——人物扁平化,缺乏心理描写和内在激情,也就是在说赵树理作品中不存在作为“现代”最终标志的个体/主体。显然,这与李泽厚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的日本中国学界,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具备现代性这一问题的争论,以罕见的理论深度展开。这就是两位日本学者近乎迥然不同的评价: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文学不具备“现代”的资格,而在竹内好那里,赵树理文学却是“超越了现代”的新颖文学(21)。不论是“不现代”还是“超越了现代”,总之赵树理文学都不是一般的现代文学,不存在一般现代文学的主体形象、心理描写与内在情感逻辑。这正是所有争议的根源。1980年代的李泽厚称赵树理文学乃是所谓“古典之风”,其实并不是格外的偏见。这种否认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现代性的观点,始终是如何评价他的一个焦点,而在那些贬低性的评论中则更是随处可见。不过,真正的问题,正如竹内好所提出的,不在于赵树理文学是否是“现代”的,而是评论者所持的现代文学观。如果意识到人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可能是特定语境下历史建构的结果,“现代文学”的主流观念并非意味着那是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全部,而存在着“别样”的现代文学的可能性,那么,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现代的争论,就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是”或“不是”的层面,而需要进一步追问:具有内在心理深度的个体是现代文学的必要前提吗?现代文学与“作为主体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关系?人们所理解的和所熟悉的现代文学,是否包含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将某种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现代创制物,视为普遍性的存在?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普遍”标准其实带有着这样的地方性印记和出身,那么该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的“中国性”,以及基于中国本土历史经验而创制的别样的现代文学的可能性?
——当“现代性”这一普遍评价标准本身成为问题时,关于赵树理文学是否“现代”的争议,或许真正显示出的是这一作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其作品中那些无法被普遍的现代文学框架所包容的“剩余物”,将迫使评论者反思自己所谓“现代文学”之“现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四 “民间”、“地域文化”及其外
进入90年代,赵树理及其文学作品开始逐渐地以另外的评价方式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
在“重写文学史”这个脉络上,从1994年开始,上海学者陈思和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22),提出了“民间”这一理论范畴,赵树理文学被作为“民间”文化的典范。相对于新启蒙论述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农民/知识分子的二元论,陈思和构建出的是一种三元格局:“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赵树理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在于“唯有他,才典型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文化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龃龉”。陈思和并从《“锻炼锻炼”》等小说中勾勒出了一条与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与知识分子)相抗衡的民间文学传统及其“隐形结构”(23)。
这种探讨赵树理文学的方式,显然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史关注的历史视野。“民间”这一范畴,启动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当代文学主流之外的历史因素,这被史学家表述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差别,也涉及包括民间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界所反复论及的“民间”与“正统”、“本土”与“现代”的分流,同时还使人回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民谣运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正统论”这些曾经的主流论述。就当代文学的发生而言,最重要的是,“民间”无疑也曾是1930-19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的一个关键词。但陈思和的“民间”概念,作为一个文学史范畴的涵义并不明晰,而更像一种价值观的表述。“民间”所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它比“国家权力”更为“真实地”表达出了“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同时也比知识分子文化更接近于“人类原始的生命力”。这事实上也就是说,它的涵义和价值始终是在对抗国家、知识分子的过程中被赋予的。固然可以说“国家权力”、“知识分子文化”这些东西是“规范性”的、建构性的乃至暴力性的,但也不能因此认为“民间”的文化就是“自由活泼的”。这背后依据的“文明”(生命力受压抑)和“原始”(生活本身)的对立,不过是一种自我/他者的镜像二元论而已。而且,在国家、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化这三者之间,并不能说民间文化始终是一个对抗性的存在,更准确的说法毋宁说这三者始终是变动不居而互相渗透的。具体到赵树理和他的文学创作就更是如此。
但是,陈思和的“民间”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在于,他使得人们需要去关注赵树理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因为正是在陈思和所揭示的三元格局中,“中国”与民族-国家想象、“文学”与启蒙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被有意无意间凸显出来,而赵树理的“民间”属性所开启的,则是当代文学之为“当代”的特殊性所在。尽管在陈思和的问题意识中,他所瞩目的完全是三者的对抗性而非同构性。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赵树理所调用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的国族想象之间的关系,赵树理创制的当代文学与新中国政治运动及国家构建方式之间的互动,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反省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缺陷”等,也开始成为“问题”。如果说赵树理文学并不是“农民主义”的传统文艺形态,那么,在国家、乡村、农民、民间、文艺传统与现代的“文学”等范畴之间,该如何解释赵树理的存在?
事实上,如果在一种后设的历史视野中,来看待陈思和于90年代提出“民间”这一范畴的针对性,关于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和关注也存在某种历史一致性,这就是在80年代式的“宏大叙事”内部去寻找差异性表述。如果说“农民”是一个太笼统的范畴,它总是要在与“知识分子”的并立中得到理解,那么“民间”则希望进一步在“国家”、“知识分子”之外划出一种话语表述的可能性。
与这种寻求差异性表述的诉求一致,“地域文化”也是90年代评论界重新阐释赵树理的另一路径。其中的代表性论著,是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这本书从地理环境、民风民性、地方民俗、作家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学文本的表述方式等方面,详尽地阐释了赵树理及马烽、孙谦、胡正、束为等被称为“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是在怎样的地域文化语境中被塑造出来,同时又如何最终受制于这一文化背景(24)。“山药蛋派”涉及的这些作家,在1950年代曾以山西省文学刊物《火花》为阵地发表作品,周扬等评论家也曾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来加以倡导,用以推进当时文学创作的“个性、独创性”。但“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被命名,则是80年代初期的产物,同时被命名的还有以孙犁为核心的河北作家群“荷花淀派”(25)。这种追认4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的做法,显然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着力寻求甚或发明“一体化”文学时期的内在差异性的历史诉求直接相关。事实上,朱晓进的著作本身就是一套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由曾以研究现代文学史与文学流派而著称的严家炎主编,由王富仁、钱理群、凌宇等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组织并推动,写作者则是80-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新生力量。这套丛书将“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范畴独立地提出来,强调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26)。
强调并关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特定“区域”的地理条件、文化传统、人文景观等的“小传统”,也就是关注“中国”的内在差异性。但与“流派”、“民间”等范畴不同的是,在这里,地理空间的差异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它使人们去关注在笼统而整一的“中国”国家内部,由于地理环境、行政区划与自然条件构成的独立地域里面存在的差异性文化传统。关注这种以“地域”显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事实上也并非文学研究界偶一为之的举动,可以说,在90年代,当代文学创作界、历史学界与思想界,特别是大众文化市场,“区域”(或“地域”)文化都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在史学界和思想界,“区域”(地域)成为突破传统的国家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其中产生影响的重要著作,有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27)、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28)等。这种研究特色曾被汪晖概括为“区域作为方法”(29)。这一脉络的历史研究,可以概括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海外中国学界的影响、思想界寻求一种能够突破国家主义视野的研究框架的努力等不同因素结合的后果。而在文学创作界,90年代初期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人们发明了“陕军东征”这一说法,以强调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特定地域(省)文学的突出影响。而以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为代表的“上海热”,以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三位作家为代表的“河北三驾马车”,以及各省文联、作协等文化机构全力推动各种关于本省(区域)文化特色的宣传策略与文学创作,表明“区域文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重组当下中国文坛格局的关键语汇。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导向性,也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侧面。这个侧面并不止是文学史著作或教材的重写,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宣传举动(诸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重新将本省领域曾在历史上出现的作家作为地域文学的“传统”而发明出来。赵树理在这种情境下也是一个重要典范。2006年,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显得格外隆重。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歌剧《小二黑结婚》也被重排演出。与此同时,山西省设立“赵树理文学奖”、修建赵树理文学纪念馆,赵树理的家乡及其写作过的地方,则被开发为旅游重点区域。显然,这种突然兴起的“赵树理热”也是不同力量介入的后果:既有新世纪“三农”讨论引起的对农村问题的广泛关注,也有“红色经典”怀旧的消费动力,更有在新的文化市场和旅游业促动下对地域文化的消费与发明。
正是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文化脉络与建构力量的耦合之下,赵树理又一次被人们热烈关注。在“农民”、“乡村”、“民间”、“传统”等关键词之上叠加的“地域”(或“区域”)这一维度,似乎将赵树理研究引向了更为“在地化”的文化实践场域,但同时也或许在塑造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赵树理形象。赵树理固然是植根于山西、三晋这一文化区域的,但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作家”。更重要的是,正如程美宝所指出的,所谓“地域文化”必须被视为一种“现代建构”的结果。如何叙述“地域文化”,本身是中国从晚清帝国的“天下”转换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环节,它由中国“读书人”所建构,并且“国家观念和地域文化观的论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辩证关系”。问题真正的关键之处是,并不存在着“地域文化”这样的历史实体,诸种被称为地域文化的形态其实一直是其被建构出来的过程中,“各种势力讨价还价的结果”(30)。在新世纪的“地域文化”热中浮现的赵树理,同样需要这样历史地看待。
五 “现代性”视野的“内”与“外”
1990年代以来关于赵树理文学的这些重新评价,促使人们需要再度面对与之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50-1960年代,赵树理无疑表现出了更多“民间”的“非主流”色彩,那么这种“民间性”由什么构成,其具体涵义该如何表述,其与所谓“主流”(包括国家与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具体交互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而从侧重“地域性”的层面,赵树理文学的语言、叙述方式和文化资源无疑与山西“本土”的文化空间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但却不是对这种地域文化的镜子般的“反映”,而包含着赵树理关于乡村、地域、中国、现代等不同层级的问题的思考。事实上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也正是赵树理与乡村的文化惯习、地域的生存空间与普遍的生活愿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现代文学的体制运作等一系列“势”与“力”“讨价还价”的结果。
该如何描述这种在直接回应在地的、也是普遍的文化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创制,显然需要超越基于单一话语框架和历史视野的“一孔之见”。赵树理文学史地位的暧昧性,正因为从1940年代开启的赵树理评价史,始终是在特定的现代性想象中展开的。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革命”与“新启蒙”、“乡村”与“城市”、“一体化”与“差异性”、“地域差异”与“国族统合”等等的对抗与矛盾,不过,在一个重要的起点上,这些批评话语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它们始终是在“现代”的“文学”与“中国”想象这一话语体制的内部视野来评价赵树理的。如果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建制来加以看待,不能意识到一种超越这一现代建制的历史视野的可能性,赵树理文学可能就始终是“似是而非”的。赵树理所携带的那种当时以及今日的人们感到不适的、难以指认的剩余物,正因为他在“文学”与“中国”之为“现代”的一些前提性条件上,保持着与这一话语体制的张力。
因此,需要在重新追问“现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被历史地构造这一基本理论前提下,来重读赵树理文学。如此探讨赵树理的历史意义,不是要在“是”或“不是”、“支持”或“反对”现代文学的意义上扭转甚至颠倒既有的赵树理评价,将其塑造为另一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而是重新进入赵树理文学文本实践自身,探讨不同的文学力量如何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既要重新面对赵树理在文学书写中如何与不同的力量“讨价还价”,也要把这种“讨价还价”的方式本身作为问题,从而重新进入具体的文化、知识、权力关系格局中承受的历史压力及其蕴含的理论性思考。
我们仍旧置身于赵树理所面对的“现代世界”。但与赵树理及其同时与后代的人们不同的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彻底现代化”(也可称“全球化”、“后冷战”、“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赋予了我们历史地思考现代性的契机与诉求。如果不能历史地理解“现代世界”如何被建制出来,如果不能触摸到这个世界的“边界”与它的内在运转机制,“反思”现代性不过是一句空话。赵树理的暧昧性,他的“似是而非”,他与曾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现代化潮流之间的“龃龉”和种种不适,为我们提供的是某些反思性的历史张力点。借助这些张力点,我们得以进入历史的“裂缝”、触摸不够光滑的历史接榫点,并理解因“不合时宜”而显露的“时”之建构性。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的反现代英雄,毋宁说,深刻地浸淫于中国乡村世界的内在文化、惯习、情感的肌理,以及在现代世界的“失败”经验所促成的反省与自觉,还有特定情势造就的历史动力与曾经“作为英雄”的自信,使他相信自己熟悉、能够理解并用文学加以塑造的世界,可以构造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赵树理文学在今天仍具有重读价值的关节点。
注释:
①周扬:《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②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49期,1946年9月26日。
③④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
⑤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1日写),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第379-38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⑦参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赵树理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⑧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再谈谈〈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⑩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5-6期。
(11)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7月。
(12)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收入《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0页。
(13)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3-109页。
(14)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16)主要包括郭志刚、董健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2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1-2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7)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6页。
(18)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49页。关于这篇文章内在矛盾性的分析,参见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59-2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参见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20)[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21)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参见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23)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5)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第118-132页。
(27)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9)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第6章“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43、31页。
标签:文学论文; 赵树理论文; 现代性论文; 农民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艺论文; 陈思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