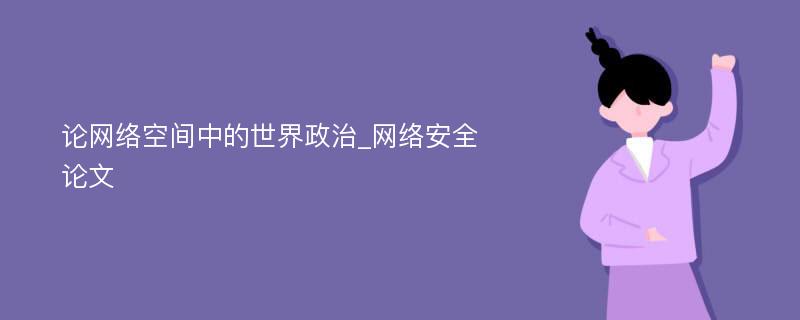
试论网络空间的世界政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空间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社会见证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三大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其中,网络空间问题尤为引人瞩目,它作为一个新问题,特别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政治议程。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彼得·辛格(Peter W.Singer)所言,“在这个(中美)双边关系中,没有哪个议题像网络安全一样快速升温,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了种种摩擦”。①与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问题相比,网络安全问题尚处于一个刚刚兴起的阶段,它常常被比作“19世纪的美国西部”:缺乏治理和法律,尚未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全球共识和固定的国际磋商制度。
网络空间以电子电磁技术的应用为特征,它通过网络化的系统和相互连接的物理设备来储存、修改和交换数据信息,是一种由计算机维持、访问和生成的、全球连接的多维人造虚拟存在。②网络空间可分为技术问题和非技术问题两种,而非技术问题是国际政治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网络安全、互联网自由和互联网治理三大内容。在网络安全方面,国内外学者围绕着网络空间的安全化、网络安全悖论、网络战与网络威慑,以及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③互联网自由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的一项对外政策,网络公域论则是该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网络空间的全球公域性质、互联网自由与网络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政策与中美关系等议题而展开。④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兴起和美国互联网自由政策的实施,网络空间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国家间互信与正常交往的一大阻碍。为此,互联网治理,包括互联网与全球治理、网络安全治理和应对网络犯罪问题等,也成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⑤
网络空间问题是一个新兴的全球公共问题。关于网络空间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分析,仍处于迅速增长但发展明显滞后的状态。以网络安全为例,人们对网络安全概念内涵的认识各不相同,常常把它与计算机安全、互联网络安全(network security)、信息安全等术语交替使用。尽管官方文件、媒体和计算机科学广泛提及各种网络不安全问题(cyber insecurity),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安全研究文献明确解释把安全与网络(cyber)两个词语连在一块具有什么含义。⑥用埃里克森(Johan Eriksson)等人在2006年分析信息革命带来的安全影响时所给出的总结,来评估当今的网络安全研究仍然十分恰当:“大部分信息社会与安全研究都没有认真关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安全议题。大多数专业研究文献都具有政策导向特点,并且极少与国际关系或者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相关”。⑦再者,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少有学者关心“网络空间问题为何能够迅速实现世界政治化”这一议题。从进程上讲,网络空间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次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最后才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全球公共问题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全球公共问题都能够成为显性国际政治议题。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讨网络空间问题迅速实现世界政治化的内在原因。
二、界定世界政治化
中文“政治化”一词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赋予政治性的过程,二是获得政治性的结果,分别对应英文"politicize"和"politicization"两词。在(国内)政治学中,政治化常常被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成及个体政治参与的一个连续体”。⑧也有学者采用一种更为宽泛的界定。例如,麦克莱特(Aaron M.McCright)等把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企业游说、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科学家的政治行为,以及立法与行政部门的举动,都视为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的内容。⑨随着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国际政治学者也针对国际经济关系、专业性国际组织,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政治化现象进行了分析。⑩然而,由于仅仅着眼于某一具体领域的政治化现象,这些研究大都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概念界定,也没有提供一个可用于分析不同议题政治化现象的一般框架。
简言之,世界政治化是指全球技术性议题的政治化,它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11)世界政治化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它们呈现逐步递进的关系:第一,技术性议题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如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15次非正式会议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一个重要议题,并发表《悉尼宣言》,阐述了各个成员就此达成的共识。第二,实施“挂钩”政策,为技术性议题国际合作的开展设置政治条件,把技术性议题当作解决政治问题或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将政治性议题带入技术性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是世界政治化的一个常见现象,例如,自1973年以来,中东问题几乎在所有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中都有过讨论,而这些专门机构的绝大部分都与中东问题不甚相关,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才是它们的职责和使命。(12)第三,技术性议题领域成为国家间利益博弈的对象和权力的竞技场,其本身完全转化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例如,在哥本哈根与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碳排放大国与小国之间围绕减排责任、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唇枪舌剑和激烈交锋,使得哥本哈根与德班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国际政治弈局,而非一个国际气候治理舞台。如果用字母T代表一项议题的技术性,P代表其政治性,那么上述三个层面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第一层次(T>P);第二层次(T=P);第三层次(T<P)。
三、网络空间的世界政治化征象
网络空间由一系列相互连接、可以储存和使用电子信息并进行通信的计算设备组成,它包括人、信息、逻辑模块、物理设备四个层面。从用途或目的上来讲,网络空间可用于操作、处理和开发数据信息,能够促进、增强人与人之间的通信交流以及人员和信息的互动。(13)一方面,同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四大自然空间不同,网络空间完全属于一种人造空间,数字化和虚拟性是其重要特点。另一方面,与四大自然空间的一系列问题相似,网络空间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世界政治化的征象。具体而言,网络空间的世界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网络空间议题之一的网络安全问题迅速升温并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网络空间与政治理念相结合,互联网自由是其最重要体现;美国积极宣传和推行“网络公域论”,网络空间成为一个新的权力竞技场。
1.网络安全:迅速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
一项议题世界政治化的基本表现是该议题成为国际谈判的内容,其相关国际制度逐渐生成。自新世纪以来,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来促进国际社会重视网络安全威胁并展开合作。联合国大会第55/63号决议提议,各国应确保其法律和做法能够摧毁向非法滥用信息技术的人提供的安全庇护所;在调查和起诉非法滥用信息技术的国际案件时,有关各国家之间应协调开展执法合作;在打击非法滥用信息技术方面,各国应就所面临的问题交流信息等。(14)联合国大会第60/45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个政府间专家小组,继续开展关于信息安全威胁与潜在威胁问题可能进行的合作的研究,并要求该小组向大会提交一份研究报告。经过四次会议,由来自中、美、俄、印等15个国家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总结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威胁,并就通过建立信心等措施以减小误判提供了多项建议。(15)尽管这些决议、建议与一项网络安全条约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它们标志着网络安全问题作为一项新兴议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
推动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是联合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中的又一次努力。在其附属的国际电讯联盟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在2001年决定举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峰会分两阶段,先后于2003、2005年在日内瓦和突尼斯举行,并通过了《日内瓦宣言》、《日内瓦行动计划》、《突尼斯承诺》和《突尼斯议程》等成果文件。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多数全球会议一般都只讨论全球性威胁问题,而信息峰会则是讨论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这种全球资源来促进发展的独特会议。尽管如此,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管理权问题的争论,使得峰会带有不少的政治安全色彩。
在地区和双边层面,网络安全问题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欧洲,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推动制定了第一个关于互联网犯罪的国际条约《网络犯罪公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论坛,来探索保障其成员之间网络安全的一般路径。在亚太地区,亚太经合组织电讯和信息工作组在其“2010-2015战略行动计划”中,把促进信息通讯技术环境安全当作一个优先事项;《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宣言》指出:“信息领域存在的现实安全威胁令人担忧。具有全球和跨国性质的网络犯罪问题要求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广泛开展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愿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加强协作。”(16)除此之外,东盟、欧盟、八国集团、美洲国家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也都设立了网络安全工作组。(17)网络安全议题在双边反映层面上的可以中美两国为例,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主办的“中美互联网论坛”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进行了六届,互联网安全及其治理越来越成为“中美互联网论坛”的重要内容。
2.互联网自由:网络空间与政治理念相结合
技术进步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对国内和国际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具有即时性、低准入和网络性特点,互联网成为高效的政治传播和组织动员工具。国内政治学者从网络空间的社会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方法、虚拟现实的政治学影响,以及网络社会的权力转移、数字民主、电子政府、政治控制等方面,对网络政治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18)在国际关系中,互联网对财富、权力、身份和规则等因素的影响也迅速显现,网络外交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19)作为一种独特、新兴的“解放工具”,互联网的发展与民主化、政权更迭、人权保护等问题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现实。(20)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政治理念的结合是网络空间世界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一问题上,自封为民主和自由灯塔的美国更为积极,其极力宣传推广“互联网自由”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美国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政策立场主要体现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和2011年2月发表的两篇讲话和美国政府在2011年5月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中。希拉里引用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四大自由”演讲,把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网站或与彼此连接——称为第五大自由。(21)在2011年2月,希拉里又公开宣称,美国将承诺支持互联网自由,像保护其他方面的人权一样来保护网络人权,包括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22)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中,美国政府再次强调“互联网自由”,并承诺把保护基本自由、隐私和信息自由流动作为核心原则,以应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挑战。在外交实践中,美国将“互联网自由”当作推动相关国家的民主化和政权更迭,以及基本人权保护的重要工具,这在自2010年以来席卷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权巨变中已经得到体现。从美国官方文件和对外实践来看,美国所主张的“互联网自由”不仅指使用互联网的自由(freedom of the internet),即个人在网络空间接受信息或发表言论时不受政府监控、审查,还指通过互联网实现自由(freedom via the internet),即使用互联网的自由度越大,人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网络空间之外的自由。(23)但从维基解密和棱镜门事件(24)来看,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政策具有很大的虚伪性:一方面它大力宣扬互联网自由,指责别国的互联网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外行非法网络监听监控之实,从而将互联网自由问题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通过把网络空间与基本政治理念相结合,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政策进一步推动了网络空间的政治化。
3.网络公域论:网络空间成为新的权力竞技场
技术性议题世界政治化的一个根本标志是该议题成为各国在世界范围内争权夺利的对象或平台。围绕网络空间的权力和利益争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互联网主导权和管理权的争夺,如俄罗斯等国在国际电信世界大会等会议中多次提议,试图从“互联网名称与编号分配机构”(ICANN)等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手里夺取对互联网的控制权;中国等支持利用政府间的国际电信联盟和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来管理国际互联网,而美国等一些国家则坚持通过ICANN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进行管理。二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对网络空间之外的权力和利益开展的竞争,如各国竞相发展网络军事技术,组建网络部队来增强传统的军事安全;美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开发各种网络技术来支持和推动相关国家的政治运动和政权更替等。网络空间成为权力竞技场的一个新近表现则是美国和相关国家围绕“网络公域论”的博弈。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本来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将南极、海洋、大气层和气候指定为“全球公域”。(25)在美国,这一概念被带有浓厚军事背景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得到借用和发展,成为美国近期维持其霸权地位的重要理论学说。“全球公域”起初仅包括海洋、天空和太空三方面,后来又将网络空间包括在内。西方学者常常把网络空间比作19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西部,缺乏规则、制度和中央权威,而自助是网络行为体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网络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不仅需要从军事安全方面来保卫一个新兴领域,还围绕着如何确立网络技术优势、获得网络话语权、主导网络空间的建章立制并最终建立网络霸权展开激烈博弈。(26)与海洋、天空和太空不同,“网络公域”具有“倍数效应”,并起着一种枢纽作用,使得其他公域内权力和财富的获取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一国在网络空间的位势。使用网络权力不仅可以在网络空间之内,而且能够在网络空间之外的其他领域取得利好结果。(27)正是因为网络权力的重要性在当今迅速凸显,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其网络权力。例如,美国军政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使用“网络公域”等词语,并将之写进《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09年四年使命评估报告》、《2010年四年防卫评估报告》等文件之中;国防部成立隶属美国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以应对网络战争与网络安全挑战;资助开发躲避网络审查的技术,为国外政治反对派集会动员,进行政治变革提供技术支持。美国推行“网络公域论”,建立网络霸权的努力自然为许多国家所警惕和抵制。不但中、俄以及中东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政治渗透高度关切,许多西方国家也对美国垄断互联网治理权、建立网络霸权的努力表达了不满。
四、安全相关性、威胁渲染与互联网霸权
网络空间是一个新近产生的事物。如约瑟夫·奈所言,我们常常忘记网络空间是如此之新。万维网(World Wide Web)始于1989年,全球最大搜索引擎谷歌成立于1998年,维基百科在2001年诞生。1992年,全球仅有100万人使用互联网,15年之后,这一数字增至10亿。(28)网络空间成为一个世界政治议题的过程则更为迅速。5年以前,网络空间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似乎还是一个边缘议题,而如今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热点,在中美元首峰会、多边外交中被频频提及。网络空间问题为何能够迅速实现世界政治化?互联网内在的安全相关性、政治家和媒体的过度渲染,以及美国出于维护霸权目的而予以积极推动,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天然的安全相关性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互联网集通信的即时性、成员的网络性和空间的虚拟性于一体,它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和实施不对称攻击的难度,并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新的便利。网络空间具有天然的军事安全相关性。互联网起源于阿帕网(ARPAnet)——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在1969年建立的网络,它把美国的几个军事及研究机构用电脑主机连接起来,并处于美国国防部高级机密的保护之下。阿帕网的目的在于建立分散但又互联的多个军事指挥中心,以防止美国全国指挥系统在单一中心被苏联核武器摧毁之后陷入瘫痪。(29)时至今日,围绕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讨论仍然具有浓厚的军事安全背景,国际上关于“网络战”、“网络攻击”的争论一直是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除了与国家军事安全密切相关之外,互联网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对非军事性国家安全、企业与个人财富的安全保障也形成威胁。黑客与国外政府侵入一国电网、交通运输、金融系统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能力不断增强,而且,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网络经济犯罪的可能增大,对企业和个人财富安全形成挑战。(30)据互联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报告显示,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间,网络攻击给全球带来了1110亿美元的损失。(31)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现代军事、政治、经济、学术、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发展的“互联网依赖”不断提高,其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上升,人们对互联网安全的恐惧情绪得以蔓延,并为政客和媒体的过度渲染提供了空间。
在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最易被提上政治议程。军事安全是一国最优先的政治,征召网络军事技术人才、增加网络安全财政投入、组建网络安全机构等都是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再者,网络犯罪的兴起以及民众恐惧情绪的蔓延,同样要求政治家予以重视,将之纳入国内政治进程。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又是一个新兴的全球公共问题,它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合作应对。安全相关性与全球公共性的特点推动了网络空间特别是其安全问题的政治化,并跨越国界上升为一个世界政治议题。
2.威胁渲染
随着现代社会对互联网依赖的增强,网络空间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并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然而,当前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关切又具有渲染过度之虞。首先,在新闻媒体乃至学术领域,“网络珍珠港”、“网络9·11”、“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词汇频繁地被用来形容网络空间的危险性。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迈克·麦克奈尔(Michael McConnell)在2010年撰文指出,“美国今天正在打一场网络战,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就可能造成的经济和心理影响来看,网络战堪比冷战时期的核武器威胁”(32)。因此,美国需要制定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战略和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美国的网络空间安全。麦克奈尔的网络战争论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莱恩·辛格(Ryan Singel)就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开放互联网的最大威胁不是中国政府黑客,不是贪婪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s),而是前国家情报总监麦克奈尔。美国并没有面临什么网络战争,只是间谍活动而已。军工复合体与安全公司对金钱的追逐是渲染互联网威胁的真正背后动因,并对互联网本身构成威胁。(33)再者,把技术缺陷引起的正常问题宣传为恶意攻击,把一般的网络攻击夸大为网络战的做法十分普遍。例如,2007年俄罗斯与爱沙尼亚政治纠纷以及2009年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期间的网络攻击,常常被称为典型的现代网络战案例。然而,从技术上来看,如果这些网络攻击的对象是亚马逊或者谷歌等美国电子商务网站的话,它们(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将彻底失败,甚至可能根本引不起重视。(34)最后,就中美关系而言,网络安全威胁被过度渲染的一个表现在于,只要是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在美国都往往立即被描述为中国政府或军方支持的行为。然而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确认这些网络恶意行为的归属问题非常困难,一国的某个行为者利用他国的电脑去攻击第三国的系统在技术上易行,在实践中也很普遍。(35)
政治家与新闻媒体的威胁渲染是网络空间问题加速世界政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黑客攻击和网络安全的报道充斥着西方各大媒体,关于网络战与网络军备竞赛的书籍、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政治家在网络安全与互联网自由方面频繁地相互指责与反驳。新闻媒体需要用“网络战争”、“网络恐怖主义”这样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网络安全公司需要互联网用户对网络安全感到担忧焦虑,各国军队则迫切需要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新敌人。在权力和利益的推动下,政治家、新闻媒体、军工集团、网络安全公司等,一道将网络安全问题渲染为一个与每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事关国家军事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通过将网络空间问题安全化,网络安全成为一种当务之急的国内政治问题,并迅速被纳入世界政治议程。
3.互联网霸权
占主导地位大国的积极推动有利于一项议题的世界政治化。在网络空间问题上,美国就互联网自由、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积极动员和大力宣传,以及以此来确立、维持和扩大互联网霸权的努力,推动了该问题的世界政治化。同时,网络空间问题的世界政治化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维持和扩大。
首先,美国对互联网霸权的追逐推动了网络空间问题的世界政治化。互联网霸权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技术上的互联网管理权。如美国通过控制其商务部属下的ICANN,来负责互联网协议(IP)地址的空间分配、协议标识符的指派、通用顶级域名(gTLD)以及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cTLD)系统的管理、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如美国用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来界定互联网自由并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军事上的“制网权”,即通过组建网络安全部队、开发网络武器,在互联网战场上获得绝对优势。围绕着互联网霸权,美国与各国之间展开了长时期的角逐,并由此将网络空间问题带入世界政治舞台。在互联网管理权方面,出于对ICANN在IP地址分配上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政府干预可能的担忧,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各种信息与网络会议中多次提议,由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来替代ICANN负责管理国际互联网。但这种提议屡次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36)针对美国进攻性的互联网自由战略以及对网络攻击的指责,各相关国家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各种方式予以驳斥,互联网自由与网络安全问题也迅速上升为中美等国家关系中的热门议题。最后,在美国的刺激下,各国纷纷出台网络战略文件,通过各种手段来应对网络空间的军事挑战,网络军备竞赛初露端倪。美国对互联网霸权的追逐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的应对和挑战,将网络空间问题推升为一个显性问题,迫使各国寻求国际合作之道。在美国的推动下,网络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高度关注,并成为各国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的重要对象。
其次,美国推动网络空间世界政治化的努力有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维护。强调与盟国之间的合作是美国互联网自由及网络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宣扬共同价值观和面临的共同威胁,发起一系列网络安全与互联网自由的倡议,使得网络问题的世界政治化为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提供了机会。通过网络政治渗透、为政治反对派提供网络支持,以及将网络空间问题与其他议题挂钩等方式,美国利用网络空间问题打击、削弱其竞争对手以及相关国家,从而为维护美国的霸权提供了支持。这样,作为网络空间世界政治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在其中又成为主要受益者。
网络空间与安全(包括个人、国家与全球安全)存在着天然相关性,这为政治家、媒体和互联网安全公司渲染网络空间的潜在威胁提供了条件,也是美国竭力维持并努力扩大其互联网霸权的重要原因。
技术议题的世界政治化利弊兼有。然而,在网络空间问题上,尽管其世界政治化趋势提高了各国对该问题的重视和外交投入,但是它的消极影响则更为突出显著。国家之间围绕网络权力、互联网自由与网络安全的相互指责和彼此竞争,加剧了原本存在的战略互疑,成为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家关系的新生阻碍。网络空间问题的世界政治化增加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并进而增大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在媒体、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过度渲染中网络空间问题实现世界政治化之后,政治性而非技术因素越来越成为一国的优先关注对象,网络安全与互联网自由问题难以仅仅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缓解,甚至也难以通过一方的重大让步而得以解决。而且,政治化容易,去政治化困难。网络安全的去政治化需要各国彼此长期合作和共同努力。
尽管去政治化十分困难,但是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一些举措来降低网络空间问题政治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首先,客观地看待当前的网络安全问题,避免和约束媒体的过度夸大。在并未获得确凿的技术证据之前,避免想当然地把网络攻击来源国视为发起国,避免随意把一般的网络攻击渲染为迫在眉睫的网络战。其次,增加相互接触,确定最小共识,稳步推进关于网络空间原则规范的建立和基本制度建设。各国在源于网络空间的风险(risks through cyberspace)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在保护关键基础设备应对面向网络空间的风险(risks to cyberspace)方面业已形成不少共识。(37)在现有共识基础上逐步扩大合作有助于网络空间问题的解决。最后,重视比较与借鉴的意义。网络空间问题虽然是一个较新的全球公共问题,正处于政治化进程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在应对传染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议题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积累并形成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治理模式。这些领域的治理经验对于探索应对网络空间问题世界政治化的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①当然,网络安全只是网络空间问题的内容之一。李侃如,彼得·W辛格:“网络安全与美中关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国防计划”研究报告),2012年2月,第vi页。
②Nazli Choucri,"Introduction:Cyber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21,2000,p.244.
③参见Lene Hansen & Helen Nissenbaum,"Digital Disaster,Cyber Security,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9,Vol.53,pp.1155~1175; Richard Clarke and Robert Knake,Cyber War,New York:Ecco,2010;董青岭,戴长征:“网络空间威慑:报复是否可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沈逸:“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④参见Dr.Greg Rattray,"Chris Evans and Jason Healey,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Cyber Commons",Contested Common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January 2010,pp.137~176,http://www.cnas.org/node/4012,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杨剑:“‘美国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的全球语境矛盾及其本质”,《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Richard Fontaine and Will Rogers,"Internet Freedom and Its Discontents:Navigating the Tensions with Cyber Security,"in Kristin M.Lord and Travis Sharp eds.,Americas Cyber Futu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 Ⅱ),2011,http://www.cnas.org/cyber,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奕文莉:“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与合作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7期。
⑤参见Milton L.Mueller,John Mathiason and Hans Klein,"The Internet and Global Governance:Principles and Norms for a New Regime",Global Governance,Vol.13,April-June 2007,pp.237~254; Abraham D.Sofaer,David Clark & Whitfield Diffie,"Cybe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on Deterring Cyber Attacks:Inform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ing Options for U.S.Policy,http://cs.brown.edu/courses/csci1800/sources/lec17/Sofaer.pdf,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⑥Lene Hansen & Helen Nissenbaum,"Digital Disaster,Cyber Security,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9,Vol.53,p.1156.
⑦Johan Eriksson & Giampiero Giacomello,"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Secur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relevant Theor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Vol.27,No.3,p.221.
⑧参见Roberta E.Koplin,"A Model of Student Politic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N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68,Vol.1,p.374; Daniel Goldrich,"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Poblador",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70,No.3,p.178.
⑨Aaron M.McCright & Riley E.Dunlap,"The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s Views of Global Warming,2001-2010,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11,Vol.52,pp.155~194.
⑩余锋:“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以GATT/WTO为例的分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晋继勇:“试析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柳剑平:“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形成与发展”,《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1)此处用世界政治化而非国际政治化,意在强调政治化的范围与程度,二者无本质区别。
(12)余锋:“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以GATT/WTO为例的分析”,《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82页。
(13)David Clark,"Characterizing Cyberspace:Past,Present,and Future",ECIR Working Paper,Version 1.2,March 12,2010,http://221.176.14.94/web.mit.edu/ecir/pdf/clark-cyberspace.pdf.
(14)联合国文件:GA Res.55/63,http://www.un.org/chinese/ga/55/res/a55r63.htm,访问日期:2013年9月15日。
(15)联合国文件:GA Res.60/45,http://www.undemocracy.com/A-RES-60-45,访问日期:2013年9月15日。
(16)涉及网络空间问题的政府间机构可参见David A.Gross,Nova J.Daly,M.Ethan Lucarelli and Roger H.Miksad,"Cyber Security Governance:Existing Structures,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in Kristin M.Lord and Travis Sharp eds.,Americas Cyber Futu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Ⅱ),2011,pp.110~113,http://www.cnas.org/cyber.
(17)Abraham D.Sofaer,David Clark & Whitfield Diffie,"Cybe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Proceedings of a Workshop on Deterring Cyber Attacks:Inform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ing Options for U.S.Policy,p187,http://cs.brown.edu/courses/csci1800/sources/lec17/Sofaer.pdf,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18)刘文富:“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9)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Nicholas Westcott," Digital Diplomacy: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Research Report 16,July 2008.
(20)Larry Diamond,"Liberation Technolog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1,No.3,2010,pp.69~83; Richard Fontaine and Will Rogers,"Internet Freedom:A 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 in the Digital Ag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1,http://www.cnas.org/internetfreedom; Ian Bremmer,"Democracy in Cyberspace:W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nd Cannot Do",Foreign Affairs,Vol.89,2010.
(21)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22)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23)Richard Fontaine and Will Rogers,"Internet Freedom and Its Discontents:Navigating the Tensions with Cyber Security",in Kristin M.Lord and Travis Sharp eds.,Americas Cyber Futu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 Ⅱ),2011,p.147,http://www.cnas.org/cyber,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24)“棱镜门事件”: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在2013年6月5~6日先后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由此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此事一出,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25)唐霜娥:“保护‘全球公域’的法律问题”,《生态经济》2002年第8期,第71页。
(26)参见William J.Lynn Ⅲ,"Defending a New Domain:The Pentagons Cyberstrategy",Foreign Affairs,2010,pp.97-108;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27)Joseph S.Nye,"Cyber Power",Paper,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Kennedy School,May,2010.
(28)Joseph S.Nye,"Cyber Power",Paper,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Kennedy School,May,2010,p.3.
(29)互联网的起源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eworld/2010-05/27/c_12150220.htm,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30)参见William J.Lynn Ⅲ,"Defending a New Domain:The Pentagon's Cyberstrategy," Foreign Affairs,2010,pp.97~108.
(31)参见http://net.chinabyte.com/322/12420822.shtml,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32)"Mike McConnell on how to win the cyber-war we're losing",the Washington Pos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2/25/AR2010022502493.html,访问日期:2013年9月15日。
(33)"Cyberwar Hype Intended to Destroy the Open Internet",http://www.homepagedaily.com/Pages/article9270-cyberwar-hype-intended-to-destroy-the-open-internet.aspx,访问日期:2013年9月15日。
(34)Gary McGraw and Nathaniel Fick,"Separating Threat from the Hype:What Washington Needs to Know about Cyber Security",in KristinM.Lord and Travis Sharp eds., America's Cyber Futu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Volume Ⅱ),2011,p.44, http://www.cnas.org/cyber,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35)参见[美]李侃如,彼得·W.辛格:“网络安全与美中关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国防计划”研究报告),2012年2月。
(36)“互联网:美国的还是世界的”,http://archives.clbiz.com/story/29786/,访问日期:2013年3月20日。
(37)Ronald J.Deibert & Rafal Rohozinski,"Risking Security:Policies and Paradoxes of Cyberspace Securit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Vol.4,2010,pp.15~32.
标签:网络安全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互联网自由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网络空间安全论文; 网络自由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