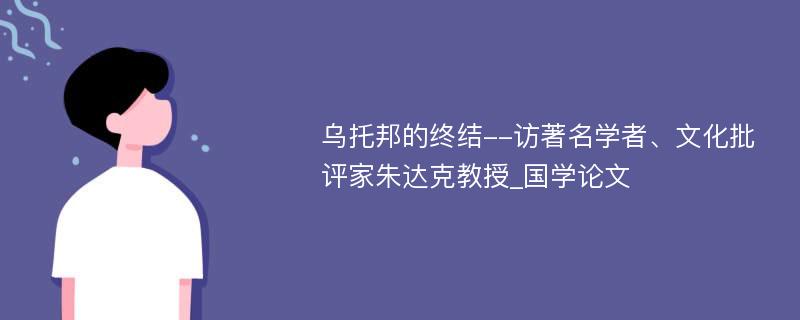
乌托邦的终结——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采访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批评家论文,学者论文,采访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哲学博士。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
2006年入选《凤凰生活》杂志推荐的“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代表性著作:《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乌托邦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
记者观察:朱老师你好,你近来关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的相关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触动了社会的神经,有人称之为“中国最犀利的反思”。想请你先谈一下,中国的信仰危机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朱大可:准确地说,信仰危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邓丽君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这就是乌托邦反思。它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他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年到1986年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在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信念危机
记者观察:按你所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仰危机其实还未对整个国人的信仰构成太大的冲击,传统的信仰即你所说的乌托邦信仰仍然占据社会主流。但我注意到,你在说到上世纪80年代时用的是“信仰危机”,而在表述上世纪90年代时用的却是“信念危机”?
朱大可:是的,是信念危机。信仰指涉了宗教层面,而信念则仅仅指涉一些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像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之类普遍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民族、国家信念。
1989年前后,整个知识界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3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那个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来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独立的批判立场,而是引向集体皈依(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契约、项目、资金、权力)的主流。学院知识分子大步行进在余秋雨倡导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国家主义的亲密结盟。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转型,获得了来自官方的热烈称赞。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称:“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次日,头版再次发表《久违了,“国学”》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层进一步表扬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这些接踵而至的褒扬,意味着“高校国学”已经获取知识界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混杂在“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热”,则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独立学术传统的缅怀。这是一场与“国学”内在错位的隐形思潮,显示出知识分子捍卫自我人格的企图。而这种对陈寅恪气节的追思,还可以视为一次文化血统的认归。陈氏所坚守的,不仅是文人的学术道统,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训诫里,寄存着少数批判知识分子的孤寂信念。
但无论哪一种精英叙事,都只能是广场叙事向书斋叙事的退缩,成为象牙塔里的絮语。在知识分子的背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话语权力真空。1993年开始呈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消费主义奠定了政治基调。就在这一年,上海各大餐馆开始出现殖民地时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费的现场,身着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场,被典雅的欧式壁灯所照亮,重演女性身体的殖民地神话,藉此表达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间接想象。
“月牌女”的复活,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超越。以“文革后一代”为主体的小资阶层出现了,开始精细地消费和时尚地生活。在第二产业大规模解体的同时,歌厅、按摩院和洗脚房大规模涌现,成为中国服务业的主流,藉此表达对身体的极度关怀。这是最奇特的中国式经济,在经历了20年的打压之后,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赋予它放纵的权能。享乐主义一举填补了信念丧失的空白。这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大的事变,它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的统治。在数码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声援下,大众消费文化接管了中国民众的日常事务。
毒食与弊政: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记者观察:那么进入到新世纪,整个社会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要用“诚信危机”来形容呢?
朱大可: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简单梳理。2008年5月,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新京报》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黄晓菊的谈话。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该报同时刊载评论称,多元价值观30年来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早已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恋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机,以肖志军事件为代表的医疗制度信任危机,以及华南虎事件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机,作为三大代表性事件,谱写了零年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病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仅仅是“毒食中国”的冰山一角,它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怀疑。“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问题消费”的代名词,它指向了制造、检验和管理的整个链索。
农民工肖志军拒绝在临产妻子的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母婴双双死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不仅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中国医疗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深刻质疑。
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被地方林业主管部门高调确认,却被网民揭出其造伪真相。这场看似无法讼断的奇案,最终以周正龙入狱告终。而当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变得卡通可笑起来。
2006年上海高校芯片造假案所代表的科技腐败、2009年罗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员贪污案所代表的教育腐败、2010年清华抄袭门所代表的学术腐败,以及遍布全国的师生论文抄袭潮流,已经让中国学界臭名远扬。但这种由体制支撑的腐败,却受到世人的广泛同情。抄袭成了师生的常规策略和时髦手艺。
各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才是构成信任危机的主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轴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褪色。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2009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2009年的上海“钓鱼”事件、2010年福州“诽谤”案等等,当地政府的诚信,皆因弊政和谎言而趋于解体。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说谎——拒绝道歉——异地抓捕——剿灭真言,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那些滥用公权的违宪手法,捍卫了某些官员的乌纱帽,却让当地政府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它不仅加剧与民众的疏隔,而且碾碎了信用的基石。
所以,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现在,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中国涌现。它分布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体育、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深刻摇撼四种基本信用结构: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货币信用和专家信用,并最终完成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