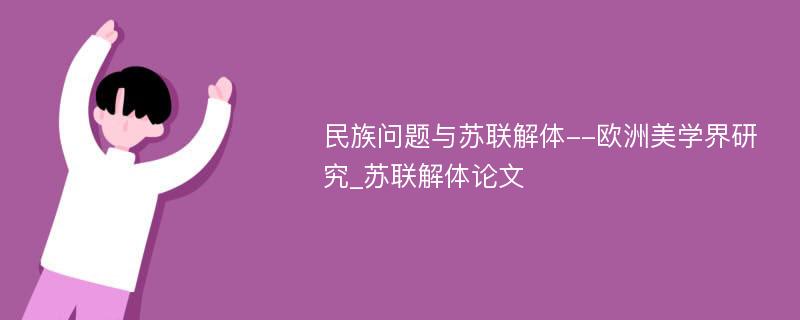
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民族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在这项研究中,欧、美学者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诚然,部分欧、美学者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具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的许多评论也未必切中要害,甚至有违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借鉴。
本文将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归纳为八个方面:民族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与苏联解体;联邦制变形与苏联解体;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与苏联解体;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苏联解体;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与苏联解体;外部因素的推动和民族问题的激化与苏联解体。前七个方面是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内在因素,最后一个方面是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外在因素。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及苏联解体是多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民族问题产生及苏联解体的内在因素
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内在因素时,欧、美学者分别论述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联邦制的变形、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人口迁移政策的失误、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并且强调了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欧、美学者把民族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及民族压迫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的“基因”。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Gregory Gleason)等认为,沙俄帝国在数百年间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统治、疯狂的迫害与掠夺,沙俄帝国被形象地喻为“各族人民的监狱”。① 二是苏俄时期民族政策的失误及民族问题的滥觞。美国学者S·佩特(S.Pate)、L·特罗特斯基(L.Trotsky)指出,列宁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也曾有过很多过失,如把“格鲁吉亚事件”的影响扩大化等,致使苏俄时期遗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这也是苏联时期民族问题十分尖锐、复杂的原因之一。② 三是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美国学者乔格·利博(Jorge Libo)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苏联的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失误和错误,这是苏联境内民族矛盾长期存在的直接原因。③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并未制定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本已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后期阶段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④
有些欧、美学者特别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失误而导致了苏联解体。其具体错误是:
第一,忽视苏联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美国学者马克·R·贝辛格(Mark R.Beissinger)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不仅缺乏民族工作的经验,而且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味颂扬苏联民族工作的影响,对苏联的民族关系状况持盲目乐观的态度。⑤ 美国学者沃尔特·A·肯普(Walter A.Kemp)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上任之初,不仅对当时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而且忽视了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他认为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⑥
第二,崇尚“公开性”,致使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泛滥。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巴乔夫视“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改革的灵魂和动力”,提倡在评价苏联过去的事情时“不留历史空白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公开性”将使苏联享有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多元主义”,在苏共领导下的多元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争论将会成为苏联的“财富”。⑦ 英国学者马丁·玛利亚(Martin Malia)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大谈“不留历史空白点”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提法会引发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对苏联民族工作的全盘否定,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公开性的逻辑无可挽回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因此而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涨潮”。⑧
第三,实行“民主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夺权提供了机会。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民主化的实行不仅使苏共丧失了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其他反对派政党纷纷建立,也给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膨胀提供了条件。⑨ 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也认为,实行“民主化”的结果有违戈氏的初衷,“民主化已经远远不是培育人们支持改革的共识,它揭示的是,在苏联内部存在着对苏联和苏共的权威与合法性形成挑战的日益增长的观念的多元化”。⑩
第四,实行主权国家联盟,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Robert Strayer)、雷切尔·登伯(Rachel Denber)以及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对高度集权的中央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时,遇到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向中央夺取更多权力以及分裂统一国家的强大压力。关于联盟中央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原来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而叶利钦却提出“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11) 在1989年9月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把这两个提法并列在一起,即:“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12) 实际上,这是一种折中的提法,它仅仅说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却没有指出强大的苏维埃联盟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这种提法在客观上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争夺主权、把各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在于步步退让,致使联盟中央丧失了领导权。(13)
英国学者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反对过分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苏联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及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对苏联的解体负责”,但还不能“将苏联解体的责任全归到他一个人身上”,“戈尔巴乔夫在任时期苏联政府制定的所有民族政策都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批准”,“他和助手们都对处理民族问题没有经验”。(14)
关于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有如下观点:
其一,关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美国学者格特鲁德·E·施罗德、约翰·B·邓洛普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70多年,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随着现代化经济、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因而其民族自我意识日益增强。此外,由于苏联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比较广泛,社会比较开放,受到“改革”潮流和“民族复兴热”的影响,各民族的自我意识迅速膨胀。(15)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政策,更加诱发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最终导致苏联解体。(16)
其二,关于“民族精英”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美国学者乔格·利博认为,苏联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还造就了一批具有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民族精英”,他们强烈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并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逐步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17) 意大利学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对苏联来说,这些“非俄罗斯民族精英分子的越轨行为”造成的危险,大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以至于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仍一再重复说,他对苏联解体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并为自己对苏联解体一事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说:“就这样乌克兰结束了俄罗斯长达300年的统治。”(18)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格雷戈里·格利森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实行,诱发了“民族精英”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一定的作用。(19) 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由于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及其实践中的一系列错误和失误,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增强,有些民族知识分子甚至成为支持民众脱离联盟的领导者,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20)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苏共的“上层民族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后做出的决策。在他们看来,占据着苏联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上层民族精英”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苏联解体。(21)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库尔伯格(Judith S.Kullberg)认为,大量事实证明,当时苏联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对记录在案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苏共“精英”中,只有9.6%的人赞成共产主义;(22) 12.3%的人赞成民主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23) 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而在1990年前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只有5%—20%左右的人支持实行资本主义,80%以上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24)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学者还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而支持资本主义,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感觉可以得到物质上的私人利益。197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1975年以后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屡遭失败,可能会使一些“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苏联“党政精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做过比较。(25) 美国学者保罗·库比克和英国学者艾瑞·寇根、罗伯特·V·丹尼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持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相似或相近的观点。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最后使得戈尔巴乔夫改革派实验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的,正是由各个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出于个人利益而加以运用的民族主义。”(26) 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了与“自上而下的革命”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27) 美国学者布扎西斯基等强烈反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在导致苏联解体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在促使苏联解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很小,因为苏联建立了严密的国家安全制度和警察制度,使知识分子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或只是在私下里议论,根本无法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形成挑战。还有一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如美国学者库克萨斯、R·缪勒等认为,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市民社会并得以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得以提高,这对共产主义的权威形成了挑战,但并未对国家政权产生强大的冲击。(28)
其三,宗教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美国学者R·博赫丹(R.Bohdan)指出,实践证明,苏联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从现象上看,在一定时期内,教堂被关闭了,大批神职人员被监禁,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一些公开的宗教活动也沉寂了。但实际上,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都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还与民族感情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内聚力与强大的抗压力,“这就为日后政治上的对立和民族间的分裂准备了条件”。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出现以后,“宗教组织就把另一种社会目标神圣化”,把“宗教热”推向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29)
其四,民族文化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语言问题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英国学者亨利·R·赫滕巴(Henry R.Huttenbach)认为,在苏联,许多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和文化不受重视的状况颇为不满,这种不满又与苏联整个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的导火线之一。(30) 美国学者S·恩德斯·威姆布什认为,苏联政府有意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与历史,贬低少数民族为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却夸大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引起了民族矛盾。(31)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反对过分强调苏联政府着意压制民族语言和文化对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以民族为基础的地区中,“民族语言和文化受到鼓励,在某些例子中得到重建。本土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它鼓励使用当地语言与习俗,实施‘防止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行为’,在共和国的国家和党的机器中采取亲少数民族的招募和升迁政策,并促进土生土长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共和国的组织中发展。虽然这些政策在集体化时代遭到反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但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再度抬头”。(32)
在谈到被扭曲的联邦制损害了民族关系而导致苏联解体时,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苏联国家结构的变形伤及民族关系进而导致苏联解体。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民族主义及联邦关系的混乱所引发的问题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在改革进程中失去控制力,从而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政治因素。(33) 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认为,苏联在用联邦制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充分地体现了领导者们的主观意愿。在他们看来,联邦制不过是体现苏联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种手段,一旦国内的民族问题得以解决,联邦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社会就可以向更加集中的单一体制转化。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指导下,联邦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践。(34) 二是苏联宪法中有关“民族自由分离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提供了借口。美国学者阿拉斯泰尔·麦考利(Alastair McAuley)认为,“民族自由分离权”的相关法律条文不完善以及该权力在实践中被严重侵犯,强烈地刺激了民族分离主义,客观上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创造了可资利用的条件。(35) 美国学者S·A·雷姆特(S.A.Ramet)则认为,民族分离主义者虽然借用了苏联宪法中“民族自由分离权”及“入盟自愿”、“退盟自由”等原则的规定,但“决定他们使用这些规定的还有苏联其他民族政策和实践出了问题,如移民问题、语言问题、民族意识问题等,而不仅仅在于这些规定及其实践本身”。(36)
关于民族经济利益的冲突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集权式管理模式及其后果。美国学者雷切尔·登伯认为,斯大林时期全面集体化的强制推行、高度集权的中央体制的迅速建立,剥夺了各加盟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民族利益,由此引起它们对此体制和联盟中央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下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恶化,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37)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施普尔伯认为,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的初期,人们普遍将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现象日益加剧视为可以纠正的缺陷,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两种缺陷看成党、政全包体制下的不治之症。(38) 二是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利益的冲突。英国学者M·卢因(M.Lewin)认为,苏联政府曾以“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的名义限制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迫使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造成民族地区经济部门残缺不全、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不能独立,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依附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民族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39) 三是经济改革的失误及其影响。美国学者卢伯迈·哈杰达(Lubomyr Hajda)、马克·R·贝辛格等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联盟崩溃近30年的情况来看,苏联的国民经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主要是由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4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对上述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并未认真研究和吸取以往的教训,他虽然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却没有解决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并且忽视原本就很复杂的民族问题,很快就把苏联推进了政治斗争和民族纠纷的漩涡。(41) 美国学者M·蒂特玛(M.Titma)反对过分强调经济改革失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她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就积累了很多民族问题”,并非仅仅“因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民众和民族情绪的变化”,“叶利钦等一批民族精英引导民族分离主义肢解了苏联”。(42)
关于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20世纪30—50年代的民族迁移政策及其危害。美国学者格哈德·西蒙(Gerhard Simon)认为,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苏联当局曾以各种名义强制迁移了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由此给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造成的伤害及给苏联带来的危害,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仍能感觉得到。(43) 美国学者R·康奎斯特(R.Conquest)认为,不能把20世纪30—50年代的民族迁移行动看成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把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与其整个民族等量齐观,主要是表现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俄罗斯人在战争中也有叛徒,却并未把整个俄罗斯民族迁移”。(44) 二是民族聚居区内俄罗斯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美国学者艾豪·卡门埃特斯基(Ihor Kamenetsky)认为,苏联政府对各民族实行利益捆绑的政策,它在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强制性迁移的同时,又将大量“贴心”的俄罗斯人迁往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45) 这些俄罗斯人得到苏联政府的庇护,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常常以“主人”的身份自居,由此而导致民族间的种种矛盾。(46) 美国学者K·裴波斯认为,因俄罗斯人迁入和苏联政府的相关政策而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在有些地方已经导致了反抗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的暴烈行动,1957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暴乱和1972年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的自焚事件可谓典型例证。(47) 三是驱逐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梅斯赫特人等民族出境事件及其影响。美国学者乔纳森·埃伊尔认为,20世纪30—5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以叛国罪等名义将日耳曼人、鞑靼人、犹太人、梅斯赫特人等驱逐出境,使这些民族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驱逐事件”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使他们产生了对当局的愤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的民众。(48) 法国学者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elene Carrere D' encausse,又译埃莱娜·唐科斯)认为,泪别国土的人们——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的情况表明:摧残民族权利不利于苏联民族一体化,这种摧残不但未能使少数民族屈从,反而导致了民族反抗。(49) 英国学者布雷斯·马什(Brace Marsh)反对过分强调“驱逐事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相对于苏联的总人口来说,驱逐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往往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即使有联系,联系的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态度不会对国内的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说这些人对苏联解体起了多大的作用。(50)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术界有如下观点:一是俄罗斯人民族本位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E·巴洪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境内泛起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俄罗斯人的民族本位主义,这种思潮强烈要求维护俄罗斯人的民族利益,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和整个联盟做无谓的牺牲,这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起了很大的作用。(51) 二是俄罗斯人的“悲情”意识加剧了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倾向。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在经济上,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吃了大亏”。在苏联,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与所谓的“俄罗斯帝国精神”背道而驰:在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中,俄罗斯联邦是输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52) 三是积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当联盟中央试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的独立运动时,俄罗斯联邦发表声明谴责联盟中央的镇压政策,并号召其他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联盟中央的极端行为,从而给予立陶宛独立力量以强大的舆论支持。(53) 美国驻苏联前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认为,当1991年8月20、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告独立时,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强大支持使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潮流无以阻挡;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功不可没。(54) 四是俄罗斯人对联盟的态度。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亲资本主义联盟——坚决要求苏联解体,这使苏联的崩溃不可避免。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尽管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反对分裂联盟,但仍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力量在起作用。事实上,此时已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叶利钦,及以其为代表的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已经下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实现俄罗斯的独立。(55)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认为,历史常常说明,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往往是一些手握重权并能娴熟运用政治技巧的王公、权臣,而非一般民众。而苏联最后阶段在其心脏地区俄罗斯,恰恰失去了“上层民族精英”集团的支持,苏联的解体自然是不可避免的。(56) 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叶利钦本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或特殊作用。关于叶利钦对联盟解体的推动作用,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一是他极力推进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分离。“无数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被政治家用作其政治斗争的工具”。(57) 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领袖,他号召俄罗斯人民脱离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以奉行“俄罗斯优先”的政策,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国家,最终导致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58) 二是他积极支持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行为。美国学者格韦茨曼·伯纳德(Gwertzman Bernard)、迈克尔·T·考夫曼(Michael T.Kaufman)等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采取行动,那么苏联仍将会存在。它的崩溃不是军事失败所致,如像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俄罗斯与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殖民帝国也不同,它并非不愿放弃代价高昂的同要求独立的抵抗运动的斗争。如果当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不采取保护波罗的海国家的措施,那么戈尔巴乔夫要想控制它们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叶利钦首先表达团结的愿望,接着在1991年1月呼吁俄罗斯官兵不要参与镇压,最后在1991年2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59) 英国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Daniels)反对过分强调叶利钦本人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叶利钦是上层民族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中的重要一员,他在利用民族主义解散苏联方面功勋卓越,但他只是民族精英中的重要一员”,“如果不是精英阶层倒向西方变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苏联是否解体还很难预料”。(60)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历史和波罗的海人的民族性格决定了这三个国家重新走向独立。美国学者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认为,某些政治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混为一谈,但根据历史和国际法,这样极不公平。这三个国家不同于1940年以前的苏联其他地区,就像当时每个欧洲国家一样,它们是完全独立的,而且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波罗的海人教养有素,但是秉性坚韧、外柔内刚、喜怒不形于色。他们对希望的象征不是激动挥舞的手臂,而是燃烧不息的蜡烛”。这种民族性格也决定了波罗的海三国必然会再次走上民族独立之路。(61) 二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和冲突促使它们走向独立。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雷·塔拉斯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在1940年加入苏联,是在面临法西斯德国的入侵与苏联的“保护”之间所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这三国入盟苏联并非出于自愿。(62) 三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起了导向作用。美国学者雷切尔·登博认为,自并入苏联几十年来,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向往实现国家独立、不甘于俯首听命的强烈民族意识始终没有泯灭。这种独立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政局剧变的条件下,终于迸发并迅猛发展,这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起了导向作用。(63) 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r)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整个联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立陶宛的决定不仅影响了那个共和国本身的利益和命运,而且也影响了苏联人民和全国的根本利益和命运”。英国学者盖尔·W·拉皮德斯(Gail W.Lapidus)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讲,由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所引起的互动关系远远超出了本地区,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它的影响。(64) 美国学者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反对过分强调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运动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联邦及其总统叶利钦的支持,立陶宛的独立很可能就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了”,其实,到20世纪90年代末诸多共和国已有了分离的打算,“即使立陶宛不宣布独立,也会有另外几个‘立陶宛’站出来宣布脱离苏联”。(65) 还有一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美国学者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认为,一些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受到波罗的海三国分离运动的影响,而另一些加盟共和国则没有受到影响。当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成功时,“其他共和国并不想要完全独立,却发现独立不知怎么回事就硬塞给了他们”。(66)
二、民族问题产生及苏联解体的外在因素
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外在因素时,一些欧、美学者分别论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演变、德国的统一、阿富汗战争的震荡、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冲击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在谈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演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时,美国学者沃尔特·A·肯普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精神被苏联占主导的联盟(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概念所掩盖,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对苏联模式及俄罗斯文化的认同取代了对本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认同。由此可见,苏联的压力和干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是抑制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外在因素。英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4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1982年的“波兰危机”等,均可被视为具有反苏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67)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认为,这些“革命”虽然大多受到了挫折,但却给由此而得到启发的波罗的海诸国、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共和国埋下了“革命”的种子。(68)
在分析德国统一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时,美国学者安杰拉·E·斯滕特(Angela E.Stent)认为,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是苏联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进入世界事务的“助产婆”,而1990年德国的统一又决定了“苏联帝国”的最终瓦解,它敲响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统治及自身最终解体的丧钟。她指出,二战后,为了阻止德国再次入侵,苏联策划并建立了民主德国(东德),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领导人却做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判断,即认为东德能够与西德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这个判断给东德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与西德缓和关系导致了东德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其实,在这之前苏联早已决定缓和与西德的紧张关系,但事与愿违,苏联的这项“缓和”政策不仅使东德社会内部,而且使整个东欧集团出现了不稳定,进而影响到苏联本身的稳定。一些加盟共和国国内原本被压抑的民族情绪开始显现和膨胀,有些地方出现了民族骚乱和冲突,到20世纪80年代时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一旦苏联决定不再使用武力维护其“帝国”的东欧一翼,苏联集团,包括苏联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了。(69) 德国学者H·诺伊贝尔教授也认为,东、西德的合并不是一种解放或成功的壮举,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70)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反对过分强调东欧地区前期所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受到了东欧地区出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主要是苏联政府“制定、实施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多过错,也没有比较成熟的民族理论来指导解决民族问题”,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民族关系也开始出现骚动,以至在90年代末出现了民族动乱,这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影响”。(71)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震荡对苏联解体的作用,法国学者亚历山大·贝尼格桑、亚历山大·本尼森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战争,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未达到控制阿富汗政权的目的,反而促进了中亚穆斯林与阿富汗穆斯林的团结和交往,推动了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72) 美国学者安东尼·阿莫尔德(Anthony Amold)认为,随着苏联境内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兴起,激进的、带有明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复兴党也趁机成立并开展活动,对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73)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反对强调伊斯兰势力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尽管中亚诸伊斯兰共和国有它们强烈的民族/种族特性,它们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堡垒,只是在此过程即将结束之时才转向独立之路。这是因为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受到联盟中央直接的保护,而它们的资源消耗高度依赖苏维埃国家体制内以政治动员为目的的重新分配过程。”(74)
关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为了瓦解苏联,美国多年来一直拨出巨款(仅1991年就达150亿美元)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扶持“民主”势力;“美国之声”、“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舆论工具用俄语等数十种语言进行宣传,给苏联民族主义势力以精神上的支持;西方国家支持苏联侨民(如在美国有150万人左右的乌克兰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与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另外,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也波及到了苏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意引导这两种势力与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结合,共同促进苏联向“民主、人道的国家演变”。(75)
关于东、西方的竞争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德国学者埃克·考普夫认为,苏维埃时期国外反动势力从经济封锁到武装进攻的猖獗活动及二战后的军备竞赛使苏联遭到了损害。(76) 日本学者宫川彰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普遍下降,为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西方国家竭力防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外“扩张”,于是它们加大了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直至把它们压垮。(77) 有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异。如美国学者R·G·苏涅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积极努力的结果,因为苏联长期处于混乱、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状态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从华盛顿的观点看,苏联的解体就并不可取”;“美国经受不起发生以下情况的打击——苏联彻底解体,眼下已显示出其特征是黎巴嫩化,再发展下去更不得了,或者等待着让一个新的、残暴的中央权威接管苏联,不论它是由军队发动的还是由俄罗斯帝国主义或法西斯发动的,总之它将是一个由苏联后帝国通过武力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设计一种鼓励苏联继续坚持公开性和民主化,但保留最低限度的中央国家权威的政策,在替代苏维埃联盟上,美国可以利用其一切可利用的影响,来促进建立一个松散的主权国家联邦(应为邦联——编者注),以自愿的方式将各共和国联系在一起,那样至少可以提供一种中央权威负责防务和核武器;也可以作为互相竞争的共和国之间的第三者——调解人;也可作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仲裁者”。(78) 与东、西方对抗加剧苏联解体进程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的学者谈到了“东、西方缓和”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如德国学者恩斯特-奥托·岑皮尔认为,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极大地减少在欧洲的东、西方安全竞赛及实现国内政治体系自由化来获得使用西方技术的权力,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维护苏联在全球的利益。但这个方法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缓和战略与政治自由化使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民族主义力量得以释放,造成苏联四分五裂。(79) 美国学者罗纳多·斯托尔(Ronado Stalr)反对过分强调“东、西方缓和”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他认为,“并不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使苏联、东欧的民族主义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对苏联来说,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民心涣散,给民族分离主义分子闹独立提供了机遇”。(80)
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对苏联解体的作用,英国学者巴里·阿克斯福德(Barrie Axford)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俄罗斯民族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除了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的特点以外,在影响范围和内容上也主要不是大多数非西方主要国家所遇到的经济上的受益不对称和政治上的主权受侵蚀的问题,而是“它使苏联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进而造成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泛滥,促使苏联最终解体”。(81)
三、民族问题视角下欧、美学术界的主要分析方法
欧、美学者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如总体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等,是值得注意和借鉴的。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总体分析法主要是指对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个人因素、外部原因等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得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如美国学者格哈德·西蒙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的分析。(82) 因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与苏联的客观实际情况较为接近,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比较全面,它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民族问题在导致苏联解体方面所起作用的全过程。但由于这种方法试图把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因素尽可能地都考虑在内,似乎所有的因素都是有影响的,因此就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一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个案分析法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只研究某个国际事件或某个外部因素或某个人在某一时期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如法国学者亚历山大·贝尼格桑、亚历山大·本尼森关于入侵阿富汗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的研究,(83) 美国学者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对导致苏联崩溃的作用的研究,(84)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关于“上层民族精英”的自决论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的研究等。(85) 运用个案分析法的优点是可以把全部研究力量集中于某个研究对象,就该研究对象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得出比较深刻和具体的认识;缺点是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以偏概全,所总结的经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回顾总结出一些经验,“以史为鉴”来阐述苏联解体的原因。如美国学者多米尼克·理温(Dominic Lieven)、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格雷戈里·格利森、罗伯特·A·帕斯特等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并非始于联盟建立之后,而是根源于沙俄时期。在沙俄存在的三百多年间,其凭借武力兼并了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邻国土地,统治着一百多个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并对这些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迫,这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基因”,学者们对这一根源做了历史追溯和探析。(86)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还对自己所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运用历史分析法的优点是,因历史事实具有既定的特性,所以以历史为据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缺点是,因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历史的传统和经验可能不适合用来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87)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比较研究法主要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进行对比研究,如美国学者卢伯迈·哈杰达、马克·R·贝辛格对俄罗斯联邦、中亚地区、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88) 夏夫丹·辛格·查汉(Shivdan Singh Charhan)对苏联和美国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89) 通过探讨,他们总结出苏联政府制定、实施民族政策的错误与失误,认为这是苏联最后阶段民族问题大爆发进而导致联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使我们从求同研究中把握苏联与他国之间、苏联不同地区之间民族问题的共性;从求异研究中揭示出苏联与他国之间、苏联不同地区之间民族问题的差异性,因各种民族问题的积累、爆发而导致苏联解体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比较研究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也可能导致肤浅、片面乃至错误的结论。
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心理分析法主要是指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分析,大致有早期经验心理分析、避免被伤害的心理分析、权力欲望的心理分析、复仇欲望的心理分析等,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莱斯利,霍尔梅斯(Leslie Holemes)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心理活动分析。(90) 无疑,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日益增强,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正在从心理学领域中汲取越来越多的“养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欧、美学术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但因国家利益的需要、政治观点及历史文化的差异,欧、美学术界在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时,有许多地方是违背客观历史事实的。如一些欧、美学者错误地认为,列宁在位时遗留下大量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因此苏联最后阶段出现民族问题大爆发进而导致联盟崩溃是必然的;还有一些欧、美学者从苏联解体得出“社会主义彻底终结”的错误结论。除去上述谬误与偏见,欧、美学者在从民族问题的视角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时,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甚至不乏真知灼见。有些欧、美学者的分析视角和方法比较新颖,如从德国的统一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等。此外,欧、美学者大多从历史根源上分析苏联解体的缘由,因而就一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显得有理有据。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苏联民族问题最后大爆发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关键。因此,他们更多地着墨于苏联民族问题的内在矛盾的分析,这也符合矛盾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美学术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思考和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委,更加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探讨当代国际社会中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科学地探索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妥善地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走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Gregory Gleason,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Struggle for Republican Rights in the USSR,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0,p.20。
②参见S.Pate,The Geopolitics of Leninism,London,HSS,1982,pp.96-98; L.Trotsky,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Corne University Press,1977,p.343; L.Trotsky," The Russian in Lenin" ,in Current History,No.19,1933-1934,p.1025。
③参见Jorge Libo," The Soviet Unions'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n Nation and Race Studies,vol.14,No.1,January 1991,pp.27-32。
④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140、186—193页。
⑤美国学者马克·R·贝辛格认为,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时,从其前任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不仅戈氏本人及其政治盟友认为苏联经过70年的努力已建成了“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苏联绝大多数民众包括其政敌也持这种观点。这大大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政治盟友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判断与解决。参见Mark R.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in Europe-Asia Studies,vol.55,No.4,2003,p.639。
⑥参见Walter A.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A Basic Contradiction? ,New York,St.Martin' s Press,Inc.,1999,p.192.
⑦参见〔英〕卡瑟琳·丹克斯著、欧阳景根译:《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⑧Martin Malia,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From the Bronze Horesman to the Lenin Mausoleu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04-407.
⑨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28、137、188—193页。
⑩〔英〕卡瑟琳·丹克斯著、欧阳景根译:《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第36页。
(11)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New York,M.E.Sharpe,Inc.,1998,pp.176-177。
(12)参见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2,p.278; Walter A.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A Basic Contradiction? ,pp.193-194。
(13)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187; 〔英〕卡瑟琳·丹克斯著、欧阳景根译:《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第48页。
(14)Stephen White,After Gorbachev,London,Summit Books,1990,p.64.
(15)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著,刘靖北、刘振前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5—178、180—201页。
(16)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31—140页。
(17)参见Jorge Libo," The Soviet Union' s 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n Nation and Race Studies,vol.14,No.1,January 1991,pp.27-32。
(18)〔意〕朱利叶·托基耶萨著,徐葵、张达楠、王器、宋锦海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有关“民族精英”以及民族干部在民族分离中的作用,还可参见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pp.150-170。
(19)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 Gregory Gleason,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Struggle for Republican Rights in the USSR,pp.106-107。
(20)参见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69-174。
(21)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44页。
(22)库尔伯格认为,“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过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除了带来经济的衰退、军事的衰退外,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参见Judith S.Kullberg,"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Elites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6,No.6,1994,p.945。
(23)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坚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理念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社会哲学”。参见Judith S.Kullberg,"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Elites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6,No.6,1994,p.944。
(24)参见Judith S.Kullberg,"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Elites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6,No.6,1994,pp.929-953。
(25)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69页。
(26)〔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27)参见〔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28)参见Leslie Holemes,Post-Communism:An Intruction,Cambridge CB2 IUR,UK:Polity Press,1997,p.268。
(29)参见R.Bohdan,Bociurkinm,Soviet Nationalities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85,pp.94-102。
(30)参见Henry R.Huttenbach,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Ruling Ethnic Groups in the USSR,London,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1990,pp.206-218。
(31)参见〔美〕S·恩德斯·威姆布什著、杨允译:《苏联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对非俄罗斯人的回答》,载《民族译从》,1980年第2期,第6—13页。
(32)〔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第44页。
(33)参见〔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第39页。
(34)联邦制是在强大的中央和懦弱的但却保持着分裂倾向的周边地区之间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妥协。斯大林对此的解释是:“美国与瑞士是世界上现存的实行联邦制国家的典型代表。历史上它们都是由独立的国家形成的,从邦联走向了联盟,但后来它们都逐渐成为单一制的国家,仅仅维持联邦制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斯大林在位期间苏联实行联邦制的实质。以上参见Gregory Gleason,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Struggle for Republican Rights in the USSR,pp.19,52。联邦制的结构形式曾帮助斯大林击败了其政敌。参见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p.113。
(35)参见Alastair McAuley,Soviet Feder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Decentralisation,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31。
(36)S.A.Ramet,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Boulder,Westview,1991,pp.129-130.
(37)参见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pp.116-118,273-274。
(38)参见〔美〕尼古拉斯·施普尔伯著,杨俊峰、马爱华、朱源译:《国家职能的变迁——在工业化经济体和过渡性经济体中的私有化和福利改革》,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39)参见M.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2-106。
(40)“高度集权的、僵硬老化的计划经济形式,等级森严的、管理劳动过程的权威主义模式,均已失去了有效性。曾经在20年代创立了苏联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独特形式,显然已经招数使尽,也无力为苏联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了。随着快速增长的终止,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都走向深重。”载〔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65页。
(41)参见Lubomyr Hajda,Mark R.Beissinger,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0,pp.55-56。
(42)M.Titma," Soviet Federalism"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No.3,1991,p.64.
(43)参见Gerhard Simon,trans.by Karen Forster and Oswald Forster,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1,pp.179-180,189,199-203。
(44)R.Conquest,The Nation Killers,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London,John Murray Ltd.,1988,pp.47,164.
(45)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过与德国“协商”,苏联强占了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国土,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北部等地区。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期间,苏联政府下令向上述地区移民,致使苏联西部地区的俄罗斯人增加了2300多万。其中,乌克兰西部增加了870万俄罗斯人,白俄罗斯西部增加了460万俄罗斯人(有134万俄罗斯人在前波兰境内),比萨拉比亚地区增加了320万俄罗斯人,布科维纳北部地区增加了50万俄罗斯人,爱沙尼亚增加了110万俄罗斯人,立陶宛增加了200万俄罗斯人,拉脱维亚增加了300万俄罗斯人。参见Gerhard Simon,trans.by Karen Forster and Oswald Forster,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p.174。
(46)参见Ihor Kamenetsky,Na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USSR,Colorado,Libraries Unlimited,inc.,1977,p.210。
(47)参见〔美〕K·裴波斯著、李有义译:《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看法》,载《民族译丛》,1979年第3期,第20页。
(48)参见〔美〕乔纳森·埃伊尔著、刘东国译:《苏联各民族与外国》,载《民族译丛》,1990年第3期,第16页。
(49)参见Helene Carrere D' encausse,trans.by Martin Sokolinsky and Henry A.La Farge,Decline of an Empire: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New York,Newsweek Inc.,1979,p.209。
(50)参见Brace Marsh,The Emigratio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rom the USSR,Stockholm,Memento,1990,pp.223-227。
(51)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著,刘靖北、刘振前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前途》,第127—128、221—223页。
(52)参见〔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第45页。
(53)参见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175-178。
(54)参见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175-178; 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p.176-178;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吴乃华、魏宗雷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09页。
(55)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92—193页。
(56)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p.168-170。
(57)Walter Laqueur,The Dream that Failed--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94,p.201.
(58)参见〔英〕卡瑟琳·丹克斯著、欧阳景根译:《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第38、44页。
(59)参见Gwertzman Bernard,Michael T.Kaufma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s,New York,Times Books,1992,pp.349-350; Roanld Grigor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51-152。
(60)Robert V.Daniels,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1993,p.164.
(61)参见〔美〕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著,杨绍彤编译:《波罗的海的风潮》,载《苏联研究》,1990年第4期,第55—57页。
(62)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著,刘靖北、刘振前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前途》,第302—330页;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167-169。
(63)参见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p.443。
(64)1989年10月27日,波罗的海三国被允许在苏联范围内制定法律,以建立各自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这项法律上的许可在1990年10月迅速影响了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参见Walter Laquer,The Dream that Failed--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p.203; Gail W.Lapidus,Victor Zaslaxsky,Philip Goldman,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3。
(65)Ronald Grigor Suny,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pp.67,69.
(66)〔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著,张定淮等译:《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7—258页。
(67)参见Walter A.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A Basic Contradiction? ,pp.1-20; 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121-146。
(68)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p.79-81,122-127,174-194。
(69)参见Angela E.Stent,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Unification,the Soviet Collapse,and the New Europ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4-9,18-27,41-151; Walter Laqueur,The Dream that Failed--Reflections on the Soviet Union,pp.163-183。
(70)参见〔德〕H·诺伊贝尔著、郑异凡摘译:《德学者谈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载《国外理论动态》(旬刊),1997年第17期,第135页。
(71)Alexander Dallin,Soviet Union:From Crisis to Collapse,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3,p.167.
(72)参见〔法〕亚历山大·贝尼格桑著、龚羽翼译:《苏联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危机》,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0年第4期,第1—8页;〔法〕亚历山大·本尼森著、龚羽翼译:《对伊斯兰教的回顾》,载《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第26页。
(73)参见Anthony Amold,The Fateful Pebble:Afghanistan' s Role i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Calif,Presidio Press,1993,p.26。
(74)〔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慧琦译:《千年终结》,第45—46页。
(75)参见Ian Bremmer,Ray Taras,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pp.261-288。
(76)参见〔德〕埃克·考普夫著、鲁路摘译:《考普夫教授谈德国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期,第17页。
(77)参见〔日〕宫川彰著、刘元琪摘译:《伊拉克战争与世界经济》,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5期,第43页。
(78)〔美〕苏涅著、王寅通译:《苏联的民族问题和外部世界——华盛顿的观点》,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4期,第27—28页。
(79)参见〔德〕恩斯特-奥托·岑皮尔著、晏扬译:《变革中的世界政治——东西方冲突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礼,2000年,第2—12页。
(80)Ronado Stalr," The Change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Soviet and the World(1988-89),p.69.
(81)Barrie Axford,The Global System:Economics,Politics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28.苏联解体后,有一种观点曾经非常流行:随着全球化大潮的冲击、资本主义的扩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加强、共同价值观的扩展,世界各民族间的差异将消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在东欧和苏联地区,并不一定能消除民族主义(参见Walter A.Kemp,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A Basic Contradiction? ,pp.211-212);“‘全球化’也许可以改变民族(国家)政治的实质,但民族主义仍会存在”(Tom Nairn," Nationalism after the Deluge" ,in Legal Conference Paper,Glasgow,September 6,1991)。有关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苏联政治、经济以及联盟体制的影响,还可参见Alastair McAuley,Soviet Feder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pp.197-198。
(82)参见Gerhard Simon,trans.by Karen Forster and Oswald Forster,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83)参见〔法〕亚历山大·贝尼格桑著、龚羽翼译:《苏联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危机》,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0年第4期,第1—8页;〔法〕亚历山大·本尼森著、龚羽翼译:《对伊斯兰教的回顾》,载《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第26页。
(84)参见〔美〕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著,杨绍彤编译:《波罗的海的风潮》,载《苏联研究》,1990年第4期,第55—57页。
(85)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69页。
(86)参见Dominic 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London,John Murray Ltd.,2000,p.263; Richard Pipes," Birth of an Empire"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May 25,1997,p.15; Gregory Gleason,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Struggle for Republican Rights in the USSR,pp.20-22; 〔美〕罗伯特·A·帕斯特著,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87)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p.18-20。
(88)参见Lubomyr Hajda,Mark R.Beissinger,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89)参见Shivdan Singh Charhan,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USA and USSR:A Comparative Study,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1976。
(90)参见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pp.87-122,174-194; Leslie Holemes,Post-Communism:An Intruction,Cambridge CB2 IUR,UK:Polity Press,1997,pp.20-28。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巴乔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