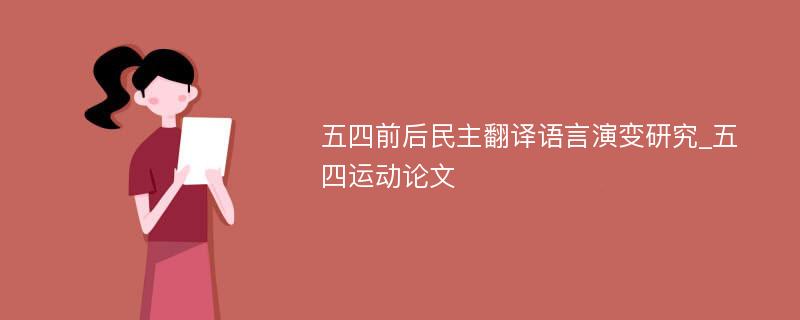
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Democrac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emocracy一语于19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不久就有“民主”、 “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民政”等中文译语。在时人心目中,它意味着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后建立起的民主政治制度,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人们的这种认识部分地来源于对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国家组织形式的表面观察。同时,也由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保留还是推翻皇帝,实行立宪还是建立共和等问题,人们还难以把Democracy 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思想文化联系到一起。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有识之士目睹政局混乱,野心家专权的状况,认识到仅仅依靠政治革命推翻一个皇帝的统治,挂上块共和招牌,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民主的获得须以整个国民心理的转变、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参政意识的增强为前提。这一点导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同时也成为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Democracy含义的动机之一。
1915年6月政论学者张东荪首先提出用“惟民主义”作Democracy的对应语,认为:“近世国家新式政治得一言以蔽之曰:惟民主义也”,此“惟民主义”“在英语为Democracy与Popular govemment”。该词“本译‘民主政’或‘民政’,实则不仅近世之共和国足以当之,而今之立宪国,亦莫不可以此字冠之,如英伦乃其好例也,故易以今名”。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惟民主义,乃为人民以自身之能力运用其政治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须人人具有“独立人格”,有“发展之能力与自觉之活动”,做到“自强”、“自由”、“不托庇于大力者”、“不由伟人之率导”等等。(注:东荪:《行政与政治》,《甲寅》第1卷第6号。有关张东荪“惟民主义”思想的详细分析,参见拙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惟民主义”》,载《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
很显然,张东荪的“惟民主义”强调的是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人地位的实质,而不是“国家之机关皆由民选以组织之”的形式。同时由于他着重陈述的是政治体中每一分子,即人民群众中每一成员的民主意识及能力,这样就流露出把对西方民主的理解从政治制度层面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的意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张东荪的上述主张可以说是以3 个月后《青年杂志》创刊为起始标志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突出宣传“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先声。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一度都从张东荪那里接受了“惟民主义”的译语和他对该词的解释。有趣的是,张东荪本人却在两年后发表的另一篇长文中放弃了“惟民主义”,而采用“庸众主义”和“平民主义”取而代之。他写道:“庸众主义之发生可远溯于太古希腊之雅典。自毗兰克来斯以后,平民主义已臻极度……贱民跋扈之风日甚,民会中常占多数……使社会上高尚浮华之气,优秀超群之风,一变而为卑劣猖獗之习,堕落苟且之行。当时忧时之学者咸太息痛恨之,遂定有Democracy一词。所谓Demos者,此言贱民,即含讥贬之意。”(注:东荪:《贤人政治》,《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号。)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将“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作了多方面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民之政府即为人民而设之政府,亦即由人民之秀者而成之政府”一语所诠释的“贤能主义”比“人民之政府即为人民而设之政府,亦即由人民而成之政府”所诠释的“庸众主义”更符合于民主政治的现实要求。(注:此句中的两段引语分别出自美国前哲学家柏哲士和前总统林肯。)这篇文章充分表明了张东荪赞同“贤人政治”的立场。
张东荪对“惟民主义”的阐释和对“庸众主义”与“贤能主义”的讨论,不仅在翻译用语方面,而且在思想倾向上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成份。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渴望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又觉察到当时的中国没有建立美好政治的条件的矛盾心情。
和张东荪不同,陈独秀不赞成“贤人政治”的主张。他发动新文化运动,致力于启蒙,试图帮助人们摆脱传统观念的重负,使他们能“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以实现“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这也正是他大力宣传“人权”与科学的原因。
很多研究者根据陈独秀发表于1919年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把《新青年》的“罪状”归结为拥护德、赛二先生的内容,断定陈独秀在1915年时所提出的“人权”就是Democracy,就是民主。 这一断语值得商榷。上面已经说过,Democracy 最初是被作为与国家政体相关的政治词汇来理解的。谭平山发表于1919年初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写道:“普通皆谓‘德谟克拉西’者,国家组织之一种”,(注: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说明当时很多人仍是从政治的含义上去理解Democracy。 张东荪的“惟民主义”稍稍逸出了政治学的范围, 但其出发点仍是“近世国家新式政治”。 1915年时的陈独秀对“惟民主义”的理解和张东荪相近。从陈独秀当时使用“人权”和“惟民主义”这两个词汇的情况分析,它们在含义上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人权”一词,可能得自法国《人权宣言》。在陈独秀的观念中,它与“君权”、“教权”、“经济生存权”、“男权”相对立,是自由、解放的相关语。“惟民主义”一词与“民主”、“国家”、“共和国体”这几个词相关联,大体表示国家的性质。“人权”与“惟民主义”的联系在于前者的获得是后者实现的前提。人民只有得到充分的自由——“人权”、“独立人格”和参政权利,才能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和热情,才能实现“惟民主义”政治。相比之下,“惟民主义”一语更近于Democracy的愿意。(注:参见陈独秀《敬告青年》、 《今日之教育方针》、《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87~88、108页。)
由于陈独秀所说的“人权”与“惟民主义”,亦即自由和民主之间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掀起的民主与革命潮流涌入中国,人们开始重新深入探讨Democracy含义, 并把一切反抗专制、争取解放、实现平等和自由、铲除剥削压迫等内容都归到Democracy名下时,陈独秀将《新青年》宣传的“人权”、 “惟民主义”、“国民政治”、“自觉”、“自治”等统统说成是“德先生”,也就不足为怪。
在张东荪提出用“惟民主义”翻译Democracy 到陈独秀宣称《新青年》主旨即在宣传“德先生”之间,有两位具备较好政治学理论知识的人看到了用新译语翻译Democracy的必要。一位是李大钊。 有关情况留在后面详述。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法科教授陈启修。1917年初陈启修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的《国宪论衡》一文中首先采用了“庶民主义”一语。他解释说:“Democracy(法文,即英文Democracy)一语,吾国向译为‘民主政治’。‘民主’二字与君主对立,与Democratie 原意嫌有未尽,近有改为‘惟民’者,义较贴切,然犹恨偏重Pour le peuple(意为“为了人民”), 而与Du peuple (意为“通过人民”)及Par
lepeuple(意为“属于人民”)之意不能兼含。”故他主张译为“庶民主义”。(注:陈启修:《国宪论衡》,《学艺》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庶民主义研究》一文, 较详细地叙述了采用这一译语的理由。首先,他指出当时国人对Democracy 一语的理解分为两类:一些人把它理解为一种理想;另一些人把它理解为一种政体形式。理解为理想者将其译为某某主义,理解为政体形式者将其译为某某政治。他认为“今世之德谟克拉西认定社会本相为互相扶助,认大同联合为社会进化公例,主张完成各个人之人格,以增进社会全体之文化”,这是一种理想,应该译为“主义”。其次,他列举了当时日本、中国学者采用的对Democracy的8种译法,并逐一做了评论:
1.“民众主义”或“众民主义”。他认为“众者,寡之对也”,众民或民众主义“不免有误为多数主义之嫌”;
2.“民权主义”。他认为“民权为国权官权之反对语”,此译法使人产生“仅认民之权利而不认国之权利之感”,实际上Democracy “主张民权与国权之调和”。
3.“民本主义”。他认为“以民为本”是古昔“仁君贤相”标榜的政治,当时日本学者采用此译语,反成为官僚、武人托名“爱民主义”,实行专制的口实。
4.“民主主义”。他的说法与张东荪相同:“民主对君主而言,然君主国家,未尝不可行Democracy”。
5.“平民主义”。 他认为:“平民者, 对贵族而言之语也, 然Democracy盛行之国,不必尽属平民”。
6.“唯民主义”。他认为此二字“意义太泛,且使人生有民无国之感”。
7.“民治主义”。他认为“民治对官治而言,有人民自治之义”,比较贴切,但有“偏于政权使用之点”之憾。
8.“庶民主义”。即是他的主张。他认为:“庶者,all之谓也。 庶民者,全体之民也,即国之总分子也,不偏于民,亦不偏于国,且意甚浑涵,无偏重主权、政权之行使,或政治目的之弊。”
接着,陈启修进一步总结了时人对Democracy含义的广泛理解。 他指出:Democracy的意义极其复杂,“因其应用之范围日益扩张, 每依所用之地之不同,而意义不无广狭之差”。 他把时人理解的Democracy的含义归纳为4种——最广义:指“尊重世上各个人之人格, 使各个人能本其完全之人格,行有益人类之活动,以增进世界之文化而言”;广义:指“民族自觉主义”及“狭义庶民主义而言”;最狭义:指“狭义庶民主义之片鳞寸爪而言”,如把Democracy 仅理解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人民自治主义”等;狭义:即政治学家主张的,指“包含(1)以民福为本;(2)主权在人民;(3 )由人民自己行使政权三者之主义而言”。此外,陈启修还从人生哲学、国家学说、心理学等角度讨论了Democracy的理论基础。 (注: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
陈启修的《庶民主义之研究》一文在当时被称为对研究Democracy有功的文字。“庶民主义”的译语也为一些人接受。但仍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译法,如刊登在《新教育》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陈启修所用的“庶”字和“众”字实际上没有差别,认为Democracy的原意“包含很狠广,若要用中国文两三个字,浑括他的全义,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按翻译佛经时“五不翻”中“多涵不翻”的规矩,音译为“德谟克拉西”。(注:仲九:《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1期。)此种音译法在当时亦为广泛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陈启修所举其时流行于日本和中国的8种Democracy译语中,除“庶民主义”、“唯民主义”(即“惟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外,“民众主义”或“众民主义”在个别翻译日文文章里有使用的,未见多数人接受。“民本主义”为梁启超等热衷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阐发出现代民主思想的人使用,但并非特指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当其作为Democracy译语为人们使用时, 在有些人那里并不意味着思想守旧。至于“民治主义”和“平民主义”亦留在下面叙述。
其实,五四时期除陈启修所举的多种译语外,作为Democracy 翻译语的还有“平权主义”、“现代民治主义”和Democracy 的衍用语“平民政治”、“全民政治”等流行。所以说后两个词是Democracy 的衍用语,是因为它们本身并非译自Democracy。
“平民政治”一语早在辛亥革命前即已出现,到“五四”前夕已较为流行。它的外语来源大抵有二,一是英语的Popular govemment, 意为“‘普通人’的或‘平民’的政治”。这一名词大概是伴随西方国家下层人民要求打破限制选举制度,争取普选权与参政权的斗争而产生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建立彻底民主政治的愿望。二是来自民国初年共和党政友社翻译英国政治家勃拉斯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著作《平民政治》。该书原名“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似应译作《美利坚合众国制度》或《美国联邦政治》。译者大概是要区别同时翻译的介绍法国民主制度的著作《民主政治》,
并根据对Commonwealth 一词的意会(Commonwealth有“共和国”、“联邦”之意,是由common——“共有的”,和wealth——“财富”两字构成,但common的复数形式commons 意为“平民”。故整个字也可能被理解为“平民的财富”,转义为“平民共和国”或“平民政治”。)采取了以上译法。此书连出多版,在当时影响很大。 “平民政治”一语辗转流行, 便成了“民主政治”、 亦即Democracy的对应语。
“全民政治”一语来自“五四”期间廖仲恺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威尔考斯所著“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廖译《全民政治论》,较切原意。该书内容是详细介绍“创制”、“复决”、“罢官”“三大民权”, 因此又名“The Initiative,The Beferendum,And
TheRecall as Instrument of Democracy”,廖译《创制权、复决权、 罢官权于民政之作用》。该书是在孙中山提出“直接民权”主张之后译就的。后来,“直接民权”思想成为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一部分,“全民政治”成为当时国民党争取的目标。这一名词也成了“民主政治”或Democracy的代用语。
最后谈谈“民治主义”译语的采用和“平民主义”译语的流行与早期中共党人李大钊和谭平山对采用此译语的理由说明,以及他们所理解的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平民主义”一词最早出自梁启超所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46页。 )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人使用过。(注:鸿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谓》,《河南》第4期,1908年5月。转自《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 卷,第278页。)1917年, 蔡元培到北大之后在几次讲演中使用了这个译语。(注:《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5、217页。)同时也有人把这个词简化为“平民”,作Democracy的译语。但直到这时, “平民主义”或者“平民”还没有被赋予新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掀起了研究、宣传Democracy的热潮,于是有了“经济的德谟克拉西”、 “教育的德谟克拉西”、“文学的德谟克拉西”、“社会的德谟克拉西”等名词,和“平民文学”、“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平民政府”等口号,以及社会上较普遍的“平民化”倾向,从而形成了“平民主义”思潮。“平民主义”作为Democracy的译语流行渐广, 并且成为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民主观念。(注:参见拙著《五四民主观念研究》第2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用过“惟民主义”、“平民政治”、“民主政治”等多种译语。作为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又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同陈启修一样,是有较好的政治学理论功底的学者,他亦敏锐地觉察到采用恰当译语以副Democracy 原意的必要。1917年7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民主’一语, 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Democracy, 以示吾民非仅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俾其他‘贤人政治’,‘有限民主’诸说,皆不得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注:《李大钊文集》续编,第101页。)但一年后, 他又在《Pan ……ism 之失败与Democracy 之胜利》一文中提出:Democracy一语“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 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注:《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1页。)值得注意的是, 他这时理解的“平权主义”已经是指包括德国社会党的“民主”,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民主”,英国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民主和工人、女子要求提高政治、社会地位的民主,并在美术、文学、习俗等等方面“罔不着其采色”的民主在内的概念。正是在这概念的基础上,他不久后提出社会主义亦是Democracy 的一个进程的看法。他从这样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民主,比陈启修及其他一些论者要早近半年。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固执一时之见。1919年初,他又提出“现代民主主义”的概念, 并一度接受“德谟克拉西”音译法。1920年,他开始使用“平民主义”译语。(注: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册,第375页。)1923年, 他以《平民主义》为题,出版了研究Democracy的小册子。 在谈到采用“平民主义”译语时,他写道:把Democracy译为“民本主义”、“民主主义”、 “民治主义”都不很适当。“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因为它可以示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而表明一种民众政治。但要用它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它政治的意味过重, 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 “民治主义, 与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但由于Democracy政制的历史演进“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最初‘统治’的意思,已不复存,而别生一种新意义了……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此,“民治主义”译语亦“不十分惬当”。他认为在众多的译语中,只有“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意的地方较少”。而采用“平民主义”是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在李大钊的观念中,现代“平民主义”是遍及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风靡世界”的伟大潮流。它“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注:《平民主义》,《李大钊文集》下册,第588~590页。)的观念。这些认识不但在当时年轻的中共党内,而且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都是较为深刻的。
谭平山五四时期曾为“新潮社”成员。他在1919年3 月撰写了一篇在研究Democracy 概念方面不亚于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的文章《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其中反映出他所理解的Democracy 是一种表现于诸多方面的“人类生活的形式”。(注:《新潮》第1卷第5号。)一年后,他放弃了“德谟克拉西”音译法而采用“民治主义”的译语,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以反对资本的托拉斯作出发点,故以劳动中心主义作中坚,而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注:《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新潮》第2卷第3号。)这时,他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了。应该说,对 Democracy内涵理解的变化,是他向革命者过渡的重要表现,也是促成这个过渡的重要因素。
从李大钊和谭平山的例子看,五四时期Democracy 译语的变化和人们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动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