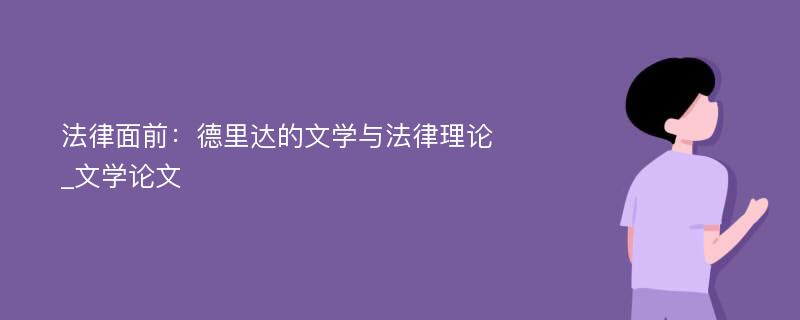
在法的前面:德里达论文学与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文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4-0131-03
一、文学的建制
在《在法的前面》一文中,德里达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是谁决定、谁判决,又是按照什么标准,说这篇叙述属于文学呢?”[1]德里达思考的是文学的建制,即将某一文本视为文学的机制。德里达认为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这一文本具有四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它们保障了该文本的类型。首先,这个文本具有同一性、独特性和统一性。它有开篇和结尾、界限和范围,收录于德国正式注册出版的卡夫卡作品集里。原始版本的出版是法定的,它得到了法的保护和授权。法定条款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性。但是它在授予权利时,俨然是自然法,似乎是没有历史的。德里达指出:“不是说文本因此就是去历史的,而是说历史是由可重复性(iterability)构成。没有可重复性就没有历史,在整个语境或者语境的某些要素缺失的情况下,可重复性也让踪迹继续发挥作用。”[1]法的绝对性恰恰依赖于重复性,法离开历史的重复和解释的重复,就不可能获得其非历史的绝对特征。法置身于可重复的结构之中,具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性,同时法对于独特性的授权也是似是而非的。
第二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这个文本有一位作者卡夫卡,这是取得公民资格由法保护的真实名字。德里达认为正是基于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同一性、独特性和统一性才有可能。区分真实和虚构的根据在于法,这种法还只是晚近版权兴起之后的产物。德里达指出,这种区分对于任何时期、任何作品都是脆弱的。文学有着绝对单独的署名和日期,但它又是重复的。德里达提出了副署(countersignature)概念:“副署通过确认他者的签名来签名,但也在一个绝对全新的、创立的方式中签名,两者是同时的,就像每一次我通过再签一次来确认我自己的签名: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方式,而每一次又都不同,是又一次地,在另一个日期。”[1]一个作者的签署总是等待着一个他者的副署,而一个文本最终签署的永远是他者。每一次签署都意味着需要再次签署,一次不同的但又牵制于历史性的签署。
第三个前提是这个文本被认为是叙述出来的,而叙述几乎不假思索地被认为是文学的特性。叙述是对文本的组织方式,将文本的每个部分安置在叙述的整体之中。编年史是叙述,但它并不属于文学。同时,虚构、比喻、象征或寓言的叙述也并不是文学的唯一特性,也有很多文本具有这些特点但仍然不属于文学。并非所有的叙述都属于文学,也并非所有的文学都属于叙述。在文学和叙述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但是叙述并不构成文学的文学性,并不足以说明何谓文学。在《播撒》中,德里达认为写作就是嫁接:“写作即嫁接(graft)。这是同一个词。言说某物,就是复归其被嫁接状态。嫁接不是发生到某物本己性的事物。”[2]文本是一个织体,是各种文本的嫁接。唯有凭借嫁接,写作才是可能的,叙述才是可能的。叙述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嫁接的方式来叙述,因此在叙述的内部就有着与叙述自身无法同一的异质性。
第四个前提是一篇作品的标题。标题位于文本的开头,且与文本拉开一定的距离,具有法的效力。加上标题独立发表的《在法的前面》与《审判》中神父所讲述的故事是不同的。德里达论述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其文章标题直接引用了卡夫卡原文的标题“Vor dem Gesetz”。德里达认为这是同音异义的修辞策略,展现了标题的差异和功能。《在法的前面》摘录于《审判》第九章神父向约瑟夫·K所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审判》中是用引号标记出来的。从《审判》中括在引号中的故事,到删去外面的引号加上标题独立发表的《在法的前面》,再到德里达以同音异义的标题论述这篇小故事的《在法的前面》,这在故事、引号、标题之间展开的文本穿插触及了文学的建制。以上所述的四个方面即同一性、作者、叙述和标题构成了文学的基本建制,作为决定何种文本属于文学的双重问题即由谁决定和按照什么标准,这种文学的建制就是文学的法。但是文学的法始终在独特性与历史性、署名和副署的差异和折叠之中。
二、禁令/被禁止的
从标题的位置入手,德里达展开了法的地志学和拓扑学。在卡夫卡单独抽取出来的作品《在法的前面》中,标题是文学的组分,但它又并不完全是文学的,它起着文学建制的功用。在标题“在法的前面”和文本的开首语之间是题语“在法的前面”的双重性和分裂,因为它既是标题又是开首语。在标题和开首语之间,有着一条分割线,它划分了不同的版图。在法的前面,标题和开首语相对,这种相对也是法的授权与文学的建制。两位主人公也如同标题和开首语,被传唤到了法的前面。但是门卫背对着法,而乡下人却朝向法,两人以对立相反的方向面对法。“两位主人公都在法的前面出场,但一者与另一者相对,分别处于倒转线(a line of inversion)的两边,这条倒转线在文本中的标记恰好就是标题与叙述整体的间隔。”[1]因此,在门卫和乡下人之间,在标题和开首语之间存在着间隔,一个间隔的倒转线在分离、切割。间隔是一种差异,是无尽地生产差异的方式。但是间隔同时受着法的支配,或者说法支配着间隔的差异,然而间隔的差异始终要从法的建制中生产出来,法的建制甚至依赖于间隔。德里达找到了这个文本的间隔位置,这正是法的发生地。
德里达不仅论述了标题与文学的内外关系,还论述了高低关系。卡夫卡在文本中说:“当他现在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穿着皮大衣的门警,看到他那高高的大鼻子,他那鞑靼人的稀稀拉拉、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决心宁可等下去,直到他获准进去为止。”[3]德里达将卡夫卡和弗洛伊德关联起来,认为门卫的鼻子象征着生殖区。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法正是鼻子和性区之间高度差异的压抑和转化。道德法是超离和净化的运动,是无上的命令,它就是康德语境中的尊严、良知,它是崇高的,似乎没有历史。但弗洛伊德指出道德法的高低关系也有其历史性,道德法的历史性维系于对父亲的谋杀。然而,道德法真的能够追溯到弑父事件吗?德里达认为道德法的本源即弑父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非事件:“道德起源于事实上不杀害任何人的无效罪行,罪行来得太早或者太晚,不能终结任何权力;事实上,由于悔恨和道德只有在罪行之前(before)才是可能的,罪行也就不能创立任何东西。”[1]弑父事件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事件。弑父的罪行永远都不可能在场,它总是太早或者太晚,人永远都不可能与它相遇。但正是这一虚构的事件,或者说事件的虚构性才使得道德法成为可能。
标题的内和外的位置,道德法的高和低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内外、高低的拓扑关系中法在间隔地带发生。法闯入了间隔,使得区分成为可能。法做出了区分,区分正是法的权威。法命令门卫守护它的不在场。法的区分力量恰恰是自身延迟的。法通过自身的延迟、自身的不出场来闯入间隔、做出区分。法的门卫背对着法,他与法不相遭遇。法的门卫所要守护的并非是法本身,而是法的自身延迟、法的不在场。法的力量正表现为法的自身涂抹。法作为禁令,是不可显现的,正如德里达所说:“现在法的禁止不是强迫性约束意义上的禁止;它是延异(différance)。”[1]法是不设关卡的,通往法的幽深道路是敞开的。但有一个门卫,门卫不是在禁止,而只是说“现在不行”,他的职责在于拖延、延迟,设置一个无限延迟的阻隔。门卫是延迟通行的法的代表。法在延迟,门卫在延迟,乡下人也在延迟。当乡下人看到门卫的鼻子后,他决定不断地延迟。乡下人被门卫和法所延迟,法的力量就在于使乡下人不断地处于延迟之中,法在延迟中并不出现。因此,法的逻辑是禁令/被禁止的(For the law is prohibition/prohibited)。法的逻辑是双重悖反,它是一个禁令,却是被禁止的禁令。法的禁令是自身在禁止自身,于是门卫在法和乡下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分割线,门卫以一种双重姿态出现,即拦阻者和信使的双重身份,这一双重身份的叠加正是法的自身延迟。文学的建制作为一种法,也正是一种被禁止的禁令。
三、类型法则的混杂
德里达已经指出卡夫卡作品中法的逻辑是禁令/被禁止的,是一个自我禁止的禁令。但是在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中,“我”和法的关系不是越界的关系,而是双重的肯定。德里达认为法律起源于过量的“是的,是的”。这种双重的肯定与小说中的“既不……也不……”相对应构成联姻,《白日的疯狂》的第一句就是“我既不是没有学问也不是愚昧无知”。双重肯定的“是的,是的”与双重否定的“既不……也不……”同时出现在小说之中。两者相互腐败对方的边缘,从而使自己进入对方的类型之中。德里达和布朗肖将双重肯定的话语落在了女性或者阴性这个类型(genre feminin)上。德里达说:“法律体现在阴性/女性中。”[1]在法语中,法律的名词是阴性的。阴性的法律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幻象,就如女性:“根本就没有女人的本质这类东西,因为女人逃避了,她逃避了自我。出离了深不可测的无底深渊,她吞没和扭曲了所有的本质性、身份和特性。”[4]女性/阴性是没有实质的,法律作为一个阴性的廓影,才可以不断地变换自身,不断地自我逃避,她那无尽的双重肯定与创世纪的七日联系起来,法律是白日的疯狂。没有白日的光照,就没有法律。法律需要代表,需要“我”的诱引、文学的叙述。如果法律没有寄生者,没有代表和文学,那么法律就无法呈现自身,因此法律自身也是寄生的。
阴性的法律与阳性的类型之间构成了奇特的婚姻(hymen),它们之间存在着性别/类型的混杂交叉。法则首先意味着区分和分类。德里达认为类型是技艺(technē),它闯入了自然和法则之间的间隔,使得自然和法则的区分成为可能,但是同时类型又依赖于这种区分。类型就是自由穿行在自然和法则之间的阴性法律。德里达思考类型法则的法则即混杂寄生的逻辑。德里达注意到《白日的疯狂》中两次出现了同样的双重否定句:我既不是没有学问也不是愚昧无知。第二次出现的双重否定句构成了文本的凹陷或卷叠,它打破了文本线性叙述和发展的逻辑,在上部边界的边缘卷叠起来,使得在总集合的内部构成了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形成了一个子集,一个内部的凹陷的口袋。由于这个口袋自身也是无尽的,使得这个口袋的凹陷要大于总集合本身。同样,在两次关于“叙述”的叙述中,我们无法分清各自的叙述疆界,它们各自的内边缘和外边缘均被瓦解,两次叙述成为了没有框架和轮廓的叙述。建立在叙述这种类型上的文学建制是脆弱的,因为在其内部就存在着腐败和凹陷,使得叙述的法权没有基础。
一切类型法则的法则都存在着内在性的分裂:“特征的内在分离、混杂、腐败、污染、分解、倒错、畸形,甚至癌变、普遍扩散、总体败坏。所有这些分裂破坏的‘异常’就会发生——这是他们通过重复(repetition)共享的份额与位置,是他们的共同法则。”[1]布朗肖在小说中指出阴性的法律在诱引“我”,而“我”并没有逃避她,虽然也不能说顺服她,“我”对法律的态度甚至是一种乱伦和诱奸。德里达认为:“他说,她不满足于、贪婪于他的荣耀——他就是他自己必须服从的那个法律的作者,他就是生成她的人,他即她的母亲不再知道如何说‘我’或完整地保存记忆。我是法律的母亲,目睹着我女儿的疯狂。这也是白日的疯狂,因为白日或白日(day)一词在其播撒(disseminal)的深渊中,就是法律,就是法律的法律。”[1]“我”实际上就是法律的生成者,就是法律母亲的生成者,但是“我”和“我”的女儿即阴性的法律发生着乱伦。在法的禁地中,恰恰是法的乱伦使得法的显现、法的白日成为可能。在法的尊严和崇高中,是法的淫秽在增补她的起源,她的起源是一个乱伦的故事,而这个叙述需要“我”来叙述。“我”不可能叙述,“我”和阴性的法律处于一个非位置的位置上,那些法的代表者要求“我”做出一个不可能的叙述,因为“我”所要叙述的是一个非事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作为被禁止的禁令,做出类型的区分,但类型恰恰建立在混杂的基础上。
四、文学、法律和正义
德里达对于法的思考是和文学、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看到文学的类型依赖于一套受到法律保护的建制。同时,他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建制存在仍然是晚近之事。让文学成为一种类型得到编码、分类、判别的恰恰是那些非文学的因素。在法的前面,文学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内容。然而,文学又并非完全规训于法的建制,总是有着对一切建制的溢出,这种溢出正是文学的文学性所在。德里达认为存在着一种不可减缩的文学性,但是它少得可怜。在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时,德里达指出在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偷盗和失窃,这是文学的自身缺失,或者说文学的文学性恰恰就在于缺失。文学性不是实存,而是幻影和效果。所有的文学都有着虚构,虚构似乎是文学的基本成分。但是虚构是不可把捉的,并没有一个称为虚构的实在摆放在文学文本的内部,虚构毋宁是文学本身的织体,同时也是文学的不可能性本身,是文学无内容的框架、无边缘的内容。因为文学惟有建基于缺失,它才可以作为幻象不断地变幻自身,不断地延异,从而对法构成挑战。
文学的文学性正在于自身的缺失,而这缺失构成了对在场的解构,也就构成了法律的解构。德里达解构还原到身体在场的残酷戏剧,认为需要继续还原到文学自身的不在场和缺失,文学首先是对缺席的经验。阿尔托仍然求助于文学的在场,从而对古典的法、古典的上帝进行弑父,但是德里达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构表明所谓的弑父,那个法的起源事件不过是一个文学事件,是一个非事件的事件。然而,有谁能够低估这种虚构的事件,有谁能够无视非事件的事件,这正是一种文学的事件、文学的行动。德里达在所谓的伦理学转向之后,一直都在寻求解构在政治和伦理领域中的不可能性的行动。文学行动自然是这种不可能性的行动的重要成分,甚至是一切不可能性行动的原型。文学作为虚构,作为不在场的织体,是一切不可能性话语的先锋和例子,是一个独一的解构场域。
不可能的文学性、文学的虚构使得文学以奇特的方式越界,它在法的保护下僭越法的边界。德里达指出:“文学是允许人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被建立的虚构(instituted fiction),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fictive institution),它原则上允许人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通过翻译将所有形象聚集成另一个人,通过形式化予以总括,但讲述一切就要打破(franchir)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的每一个领域,去释放自己(affranchise oneself)。文学的法则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1]文学在法的保护下允诺了人们可以讲述一切,可以冲破法的边界,因为一切对法的越界只要在文学的界限之内就仍然是一种虚构的越界。虚构的越界,已经作为文学行动向着政治行动和最大限度的民主开放,向着未来的民主开放。文学的不可能性的行动提供了超越法的方式,提供了没有法的法、超越法的正义,而这是不可能的正义。一方面,德里达承认要有法,因为文学的类型和建制离不开法,离开了法就没有文学。另一方面,德里达又认为文学可以解构法,可以在虚构的限度内超越法律朝向正义,如果文学不解构法律、超越法律,如果文学不是朝向正义进行虚构,那么也就没有文学。在文学、法律和正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寄生、污染机制,同时又存在着复杂的解构和超越的关系。文学在独一性和重复性之间作为一个例子,作为对习语的培养和保护,正如德里达在对策栏的论述中所说的,是去复兴一种死语言(a dead language),[5]这种死语言作为幽灵性的语言,可以对法的暴力进行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