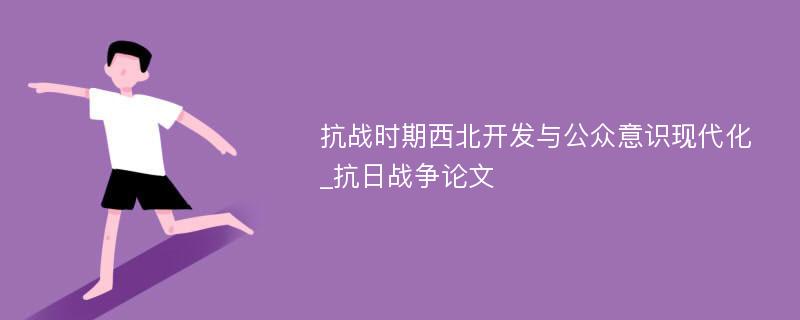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民众论文,意识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2-0088-04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自身生存而进行的一场自卫战争。为了坚持抗战,国民政府曾着手大力建设西部地区,使其能成为抗战的基地,承担起民族的重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北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也对西北地区的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对国民素质的提升起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政权对西北的开发建设开始于1935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告急,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对日作战和大后方建设问题。同年7月蒋介石在对日整体战略中提出:“以川黔陕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注: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史概要》第二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第2版,747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注: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104页。)这样西部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在西北规划了绥新、西兰、甘新、西汉公路,并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国营公路运输管理局。1936年又兴建了沟通西北与内地的九省长途电话工程。但因这一时期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后方建设进展极缓慢。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部的建设大规模推开,国民政府为了转运苏联军援和战时经济需要,对西北地区交通事业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当时以经新疆入甘转川、转陕的国际公路干线建设为主,辅以甘青、甘宁、陕川、陕鄂等省际公路,初步完成了西北地区公路干线网建设。并对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进行了扩充,营运车辆由1936年的124辆猛增到1939年的1240辆,(注:《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7页。)使西北的交通运输业得到了空前加强。在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工厂数量大增:据1942年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有工厂539家,其中发展最快的陕西省由战前的78家增加到385家,(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三联书店1962年版,97页。)甚至青海也建起了以马家官僚资本为核心的8大工厂;工业规模扩大:到1944年陕甘两省平均每厂拥有资本82.29万元(实缴资本),工人71人;(注: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转引自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6页。)工业门类也大为增多:水泥、玻璃、酒精、造纸等行业兴起,特别是重化工有了大的发展,甘肃1944年全省有机械工业34家(民营27家)。(注:《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甘肃人民出版杜1989年版,5页。)在农业方面主要是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牧业品种改良以及病虫害防治。抗战时陕西省先后修建了黑惠渠等一批水利工程,受益面积达210万亩。甘肃先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3处、小型43处。新疆到1942年全疆水渠总长约36000公里。而在宁夏青铜峡等地设立了10个水文站,为灌区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国民政府还在陕、甘、宁等地成立了省农业改进所、西北羊毛改进所、耕牛繁殖场、种羊场、畜牧兽医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成立对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无疑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商业上也出现了空前繁荣。据估计1942年甘肃全省私营商家约25000家,从业人员10万,总营业额28亿多,(注: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4期。)在陕西出现了三原这样拥有商户7300余家的商贸大县。此外,在文化教育、邮电通信等行业也取得了较大成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尽管有许多方面还很不完善,但毕竟是西北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对西北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相对封闭保守的民众思想产生较大冲击,并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后的经济生活要求,实现角色的转变和自我的社会化,并同时带来了民众思想观念的整体变迁和精神面貌的改观,使其加速向着近代化方向迈进。抗战时期民众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风气的开化。社会风气属精神文化领域,主要涉及到知识、观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问题。一般而言社会风气是一种非强制性约定俗成的群体行为规范,它与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相互配合、补充,调整着社会的各种关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气虽属于非主流文化,但它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对社会整体的进步起推动或迟滞作用。因而一个地区社会风气开化与否,对当地社会影响巨大。而西北地区社会近代以来变迁极为缓慢,甚至在1925年国民军入甘时,兰州厅、道官吏仍依清制绿呢大轿,军官如同戏中武生。省城尚且如此,地方落后可想而知。在这种落后的主体文化影响下,社会风气不开,近代工业文明在西北成长艰难。左宗棠曾寄以厚望的兰州机器织呢局,命运多舛,百余万两白银办的厂子仅生产了三年。后时办时停,直到抗战被军方接管。创办于1908年的陕西制革厂也同兰州织呢厂命运相仿。至于在新政期间一度在陕西关中兴起的民营企业,也大都夭折在襁褓之中。商业在一些地方虽有相当规模,如甘肃省城兰州在抗战前有店铺五六百家,资本也有高达数十万的。但大都属旧式商人,经营理念落后,所得利润多用于捐官或投入土地兼并。农牧业方面更为落后,传统的经营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如“新疆虽以畜牧著,惜墨守成法,致品种日趋衰劣,每遇瘟疫动辄死亡千万”(注:杨赞绪《开发新疆实业之管见》,《开发西北》1934年1卷1期。)。青海藏区更为落后,农作物种收、畜群疫病均请喇嘛算定。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心的西移,人们在改变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逐步改变着自身,大规模建设给西北的社会经济注入了活力,许多交通要道和重镇,不仅新式工商企业迅速发展,而且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工商致富,以土守之”的传统经营观念有了明显改观。如新兴的汽车修理业,到1945年仅兰州就有36家之多,其中民营达22家。(注:陈鸿胪《甘肃之国有工业及新兴工业》,《西北问题丛刊》3辑。)商业经营方式在外来商业影响下也迅速改变,许多老“字”、“号”、“房”开始改组,经营领域扩大,专业化加强,分工也较明确。据1942年对甘肃34县调查,共有商店1.3万家,其中兰州市有2095家,年营业额10亿多元,(注: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4期。)民间投资工商业的热情从中可见一斑。在其他地区这种进步也很明显,如原商业基础较好的西安的各种商号增长了三分之一左右。在农牧业中社会风气的开化也很明显,除了诸如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青海西北畜牧公司等一些官办新式企业外,农牧民对一些新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尽管在许多方面还只是开端,但风气开化对农村社会的进步意义巨大。
二、近代科教意识的提高。西北地区交通信息封闭,传统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民众受教育率很低,思想观念保守,思维方式多是具体的、类比的,充满了感性和直观,强调眼见为实。而对于新事物往往持怀疑态度,科技意识更显淡漠。如1936年在甘肃夏河初创畜牧改良,因民众的不信任业绩不佳,致使从美国引进的种羊、设备损失殆尽。抗战时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建设,用事实教育了民众。随着近代交通、工业由中心城市向边远、民族地区扩散,农牧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增强了人们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对科技由怀疑、观望到追求。如工业领域人们不仅热衷于办企业,还注重技术改进和开发,在宁夏、新疆设立了工业试验站,一些像雍兴公司这样的大企业还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农牧科技事业随着国民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也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仅在陕甘推广的小麦品系就有十多个,玉米五六个,还有国外引进的棉花、蔬菜瓜果,其中最有名的白兰瓜成为兰州的名产。畜牧业品种改良在汉族聚居区和民族地区也逐步被认可推广,如甘南畜种场给马匹配种,很受当地藏民欢迎,而新疆仅1942年种马交配骡马数达17100匹,种牛交配数13950头,种羊交配262140只,其中30%为人工受精。(注:李溥林《十年来新疆的经济建设》,《新新疆》(民国三十二年)1卷1期。)
民众对科技的追求还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西北近代教育事业虽起步于1902年清政府“新政”时期,但长期难以得到发展。就高等教育而言仅限于甘陕两省。民族教育发展更为艰辛,长期“人民对学校教育之意义,本无相当之了解,而于学校需要更无丝毫之感觉。”(注:青一《创办中央蒙藏学校青海分校计议》,《新青海》1934年2卷3、4期。)新疆南疆地区“缠民闻招入学则皆避匿不往”,为“防其逃逸,闭置室内,加以桎梏,故缠民闻入学则曰凡差皆易,惟此差最难”。(注:袁大化修《新疆图志》卷38,学校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页。)迫使清政府宣布在南疆废除新式教育。而青海到民国十七年,办了几十年的蒙藏教育几呈中断之势。抗战爆发后随着西北经济建设的加强,民众对文化教育的认识逐步加深,民众知识化的要求迅速增强。陕甘两省高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相继成立,原有的高校如甘肃学院等得到较大充实。职业教育在西北发展尤其迅速,到1946年仅甘肃累计毕业生2651人,相当于抗战前近三十年毕业生总数的4倍。(注:《甘肃省志·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36页。)民族教育成就引人注目,在新疆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全疆少数民族学生达250726人(而同期汉族学生为24250人),涉及到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注:傅希若《论新疆教育》,《西北论坛》1948年1卷5期。)甘宁青的回民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小学教育有了较大普及,西北回民中学、陇东伊斯兰师范、宁夏贺兰中学等中等教育很快兴起。甚至宗教界对近代教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32年青海广惠寺明珠活佛创办小学时,曾遭一些寺院反对。但经抗战之洗礼,寺院对近代教育也有了一定认可,青海办起了喇嘛国文讲习所,明确提出:改进边疆教育、增进藏民文化、宣传三民主义、阐明抗日国策。甘肃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在甲班开设的19门科中,10门属于自然和社会科学,9门为应用技术。1943年西道堂创办的甘肃临潭西凤坪启西女校,更是开西北回民女学之先河。
三、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民族大格局早已形成,普遍的爱国心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成为中华民族之魂,也是炎黄子孙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但我们也应看到,因一些历史原因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隔阂依然存在。特别是从清末到抗战前,西北地区民族间误解很深、利益冲突不断,加之各族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拨弄其间,民族间信任度降低。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各民族交往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动员全民族抗战而采取的一些民主化和改善民族关系的措施,以及西迁后对西北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定程度关切,无疑对西北地区民族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复苏。这种整体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强化,不仅有效地调解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也调解了各族间的矛盾,形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气氛。尽管战时经济紧张,物资匮乏,人民的负担相对过重,但相对而言抗战时期是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社会较稳定、民族较和睦的时期。连地方各派系军阀在这种大气候下也不得不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重,或出兵参战或转输军需,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抗战爆发之初,西北地区的各族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救亡斗争中去,新疆抗日救国会、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相继成立,《抗战通讯》、《西北青年》、《回声》、《妇女阵线》、《学生呼声》、《老百姓日报》等一批抗战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迅速转化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如新疆抗战爆发后到1938年8月仅战斗机就捐献了10架,自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全疆各族人民捐款折合现洋332万余元。(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版,32页。)地处边陲的温宿县的一位维族寡妇甚至将丈夫生前留给她度日的27个元宝也献了出来。陕甘广大民众除了“献金”、“献机”运动外,还大量认购抗日公债,在征购、征借名义下献纳公粮等。以仅600余万人口的甘肃为例,1943年就认购了“同盟胜利公债”7108.7万元,征借公粮160万石;1944年又征借185万石;(注:《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95-296页。)从1943到1945年共献马万余匹。广大宗教界也行动起来,拉卜楞寺所属108寺派出代表到战区慰问将士,并捐献飞机30架。(注:《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甘肃文史资料选辑》3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60页。)
除抗日宣传和物质支援外,西北各族民众为了保证苏联军援和中国外贸运输,还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千里戈壁荒滩、崇山峻岭之中,仅甘新、西兰公路甘肃段就投入军队和民工4万余人之众,而从霍尔果斯横贯新疆到星星峡段,总共耗费工日320多万个。1938年后日寇海上封锁加强,中国西南地区的外贸物资也不得不由西北转出,致使西北运输量暴增,西北的民众在国民政府号召下,又自带干粮奔赴在千里运输线上。他们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原始的交通工具创造了一个个奇迹。1940年有批军用物资须在5个月运完,汽车承担了3040吨,剩余的4300吨全由驿运完成。(注:龚学绪《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07页。)抗战八年间仅甘肃驿运完成的货运量就达36.2万多吨,货物周转量14843.6万吨/公里。(注:《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21页。)大量的西北各族子弟还应征入伍为国效力,在甘肃师管区每月的新兵补充额达5000名(后削减到2000名)。(注:《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73页。)1937年8月,由回、汉、藏、撒拉、东乡、保安、土族8000多子弟组成的骑兵暂编第一师奉命开赴河南前线,在同日军多次血战中全师官兵伤亡2000余人,二旅旅长马秉忠战死沙场,被誉为“西北铁骑”。(注:参见《青海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147-153页。)宁夏马鸿宾1939年率3旅之众在绥西与日军长期作战,并在著名的伊克昭盟会战中,成功击退了日军。显然,抗战中日益强化的近代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各族民众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顽强奋斗、流血牺牲,所焕发出的对祖国和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西北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新的、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了升华。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北的开发建设,对西北地区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除了物质层面的影响外,更为深远的在精神方面。可以说抗日战争对西北各族民众而言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精神洗礼。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西北民众不仅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时也在考验过程中提升了自己,使得自身的思想意识从中世纪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并逐步向近代化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的西北开发,既是一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民众意识的近代化尤显得难能可贵,它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2-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