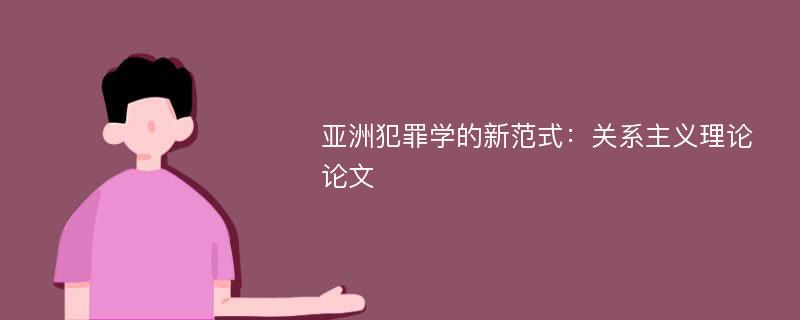
亚洲犯罪学的新范式:关系主义理论
刘建宏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澳门 999078)
摘 要: 基于对《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发展亚洲犯罪学范式:理论策略与未来方向》《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等文献的回顾,概括了发展亚洲犯罪学的“三阶段”路线:检验既有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亚洲语境下的适用性;修订相应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并将亚洲社会的特有文化纳入其中;提出基于亚洲社会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关系主义理论是遵循上述路线图的最新思想成果。关系主义是亚洲社会普遍具有的基本范式,它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依恋家庭和社区、看重荣誉、追求和谐、偏重整体思维。关系主义理论对于进一步推动亚洲犯罪学的发展及在“获取正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亚洲范式 亚洲犯罪学比较 犯罪学关系主义 获取正义
1 引言
本文回顾并总结了我在过去数年间对于亚洲范式理论的思想成果。最早的一篇文献是我在 2009年担任《亚洲犯罪学杂志》主编之初发表的《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1],其中为亚洲犯罪学的发展设置了基本的议程。除此之外,还有两篇稍微晚近一些的重要文献,其一是2017年发表于“南半球犯罪学”文集中的《发展亚洲犯罪学范式:理论策略与未来方向》[2],我在文中进一步发展了“亚洲范式”(Asian paradigm)的概念;其二是2016年发表于《当代刑事司法杂志》上的《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3],我在文中讨论了亚洲范式理论在获取正义方面的政策意义。
鉴于我在推动亚洲犯罪学发展以及在亚洲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对于犯罪与司法问题的实证研究等方面的贡献,我非常荣幸地在2016年被美国犯罪学学会授予了“弗雷德·阿德勒杰出学者奖”(Freda Adler Award)。尽管我自认为尚不足以比肩于Farrington等曾经获得该奖项的其他学者,但是我被授予这一奖项至少说明了西方犯罪学界对于发展亚洲犯罪学的兴趣与支持。在2014年于日本大阪召开的亚洲犯罪学学会的年会上,Braithwaite在主旨演讲中将我称为唯一地提出了亚洲特色理论的亚洲犯罪学家。这些溢美之词一方面可能夸大了我的学术贡献,但在另一方面则真实地表达了对于亚洲犯罪学未来发展的期许。与西方犯罪学家相比,亚洲犯罪学(以及更广泛的非西方犯罪学)的现有资源更为匮乏,亟待克服的困难更多。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亚洲犯罪学家致力于发展与完善亚洲范式理论。本文将清晰地表明,相比于在美国接受犯罪学博士教育的时期,我对于犯罪学的普适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而不意味着它就是亚洲犯罪学发展的唯一路径。
2 亚洲犯罪学的前途与挑战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亚洲的重要地位都在提升。在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在此之后,快速工业化的中国逐渐跻身于强国之列。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评论了多元化的亚洲社会,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现在看来,当时应该更加关注印度,它的发展潜力不容忽视。正如Belknap(2016)[4]指出的,即便在一个国家,也难以精细地描述出其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所有发展,因而将亚洲看作单一的整体可能是很不准确的。许多政治人物和媒体人士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意味着亚洲社会不但应该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应该在文化上、知识上推进包括犯罪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发展。
作为根在中国的犯罪学家,我在美国接受了犯罪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犯罪学发展的质量与规模。从外部来看,犯罪学似乎有着某种统一的范式,其中的每个从业者都遵从着一些类似的基本假定,例如,推崇定量方法来构建或检验某个理论。然而,我现在意识到上述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犯罪学中的某些研究传统有着不尽相同的假设。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犯罪学学科通常被置于法学院之内;而在美国之外,犯罪学家对于定量方法亦存在着褒贬不一的意见。尽管如此,犯罪学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科学”[5]的基本特征。
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讨论了阻碍亚洲犯罪学发展的一些制度性原因。其一就是某些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尚不完备。资源丰富、学科齐全的高等院校是犯罪学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大学里,刑事司法实务工作者和学术研究人员才能够象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开展交流与合作。作为较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建设了多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迅速地发展了高等教育体系。然而,在整个亚洲社会,犯罪学还是一个相当弱小的学科。在国家层面上,这将表现为相关资源的严重匮乏——研究项目缺乏充分的经费保障、缺乏犯罪或刑事司法统计资源[6]。
在支持区域性项目方面,亚洲犯罪学同样面临着资源匮乏的窘境。亚洲社会不象欧洲国家那样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之后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将影响到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犯罪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校之间还缺乏充分的交流与合作。亚洲犯罪学学会为此提供了一个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学术平台。然而,由于昂贵的交通费用,主办地之外的亚洲犯罪学家们很难参加亚洲犯罪学学会的年会。既往的年会举办地分别为中国、印度、中国台湾、韩国等,未来的几届年会将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召开。绝大多数的亚洲犯罪学研究成果是以各不相同的母语在本地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语言不通是亚洲犯罪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尽管欧洲犯罪学界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3.2.2 自我控制理论
更为复杂的是,我曾在早前的研究中揭示了包括城市化在内的社会变迁对于中国的社会控制及犯罪水平的影响[8]。为了解释亚洲社会的低犯罪率及其变化趋势,上述的各种因素都是不容遗漏的。
3 一种新亚洲范式的提出
有许多证据表明,日常活动理论更加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解释效力相对不足。例如,在西方国家,单身人士的被害风险更高,但是,Messner等(2007)[36]发现在中国并非如此。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一发现是很陌生的,但是,该研究则发现这一结果。Messner等人认为,应该将家庭主义这一跨文化变量引入到日常活动理论之中。婚姻状况(即是否单身)对于被害风险的影响程度还依赖于家庭主义水平,这是一种思想观念或文化价值。修订后的理论更加复杂,它在日常活动理论中纳入了更加宏观的制度背景。在修订这一理论时,Messner等人使用了“等级因果模型”方法。Kuhn(1996)可能会认为这种维护既有范式的做法过于复杂,但是它使得修订后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跨文化背景下的犯罪被害问题。
3.1 第一阶段:检验西方理论
美国犯罪学家提出了许多有关犯罪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质使其可以通过定量方法得到检验。借用库恩的术语,犯罪学通常表现为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尽管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传统及其变体,如紧张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等。定量研究具有累积性。在此基础上,一些犯罪学家提出了普适理论以求解释所有社会中的犯罪。
由于同类样品玻璃片中组分差别不大,而稀释比又比较大,玻璃片的体积密度可认为相等。因此,玻璃片的体积可以用质量表示,也因此,计算中使用玻璃片的体积和质量得到的校正结果是一致的,也与目前的文献广泛使用质量校正(稀释比)方法一致。设Ci为玻璃片中i组分的含量,mi为玻璃片中i组分的质量,mg为玻璃片的质量,则,玻璃片中各组分的含量由公式(1)计算;当干扰因子为零时,XRF分析经验系数法的基本校准曲线方程为公式(2),其中,一次曲线为公式(3)。
越来越多的犯罪学实证研究使用了来自亚洲社会的数据,其中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美国获得了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因而比较熟悉西方犯罪学的理论传统。这样的检验大多证实了普适理论的适用性[9],但是,有些研究表明某些西方理论需要进行修正,甚至某些西方理论并不适用于亚洲社会。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细介绍每项研究,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理论检验,只能概述性地介绍这些文献。其中的许多文献刊登在《亚洲犯罪学杂志》上。借由这些普适理论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发展出一种新亚洲范式理论。
3.1.1 差别交往/社会学习理论
这是被亚洲社会的许多实证研究证实的一个西方犯罪学理论。基于该理论的预期,与犯罪人或越轨者的社会交往会导致更多的越轨行为。西方国家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10],11]。基于中国数据的许多研究支持了差别交往/社会学习理论[12-18]。某些人可能会质疑到,为什么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来检验那些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判定为真的问题呢?实际上,基于定量化量具(如态度量表)而在不同国家进行的经验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者可以科学地展示其发现。
假设消防减缓系统等级为最低,消减系统对燃烧与爆炸后果面积的消减系数见表9所列,则factmit=0.05。氢气泄漏后无法自燃,计算后果面积时只考虑其不可能自燃的情况。氢气泄漏时为气态,分析类型为0,计算结果见表10所列。
3.1.2 一般紧张理论
学生从入学学习中医伊始,就每日清晨利用30分钟时间诵读,感受经典的古韵,提升中医人的行为素养。期间的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诊断学学习中也会涉及《内经》原文的出处,由于每日诵读,自然会加深印象;当时学生不一定能够理解其义,只觉朗朗上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深入,自然会深入理解,铭记于心。这期间教师要注重在阅读方法上给予指导,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学期末可以以诵读比赛的形式激励学生,既可以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又丰富诵读的内涵。
紧张理论可能是更加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因为它在解释美国社会的犯罪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Agnew(2015)利用一般紧张理论解释了亚洲社会的犯罪[19]。该理论预测到,引起紧张或压力的各种负面经历将导致犯罪行为,除非出现有效的应对机制。一般紧张理论的科学目标是识别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紧张。Agnew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紧张:在追求社会认可目标时遇到阻碍(这一类型源自Merton的紧张理论);无法获得正向刺激;出现负面刺激。在美国,一般紧张理论经受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有些质疑意见认为,犯罪与紧张似乎是等同的,因而紧张理论并不是强有力的、因果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尽管如此,“一致的证据表明,暴露于紧张将提高犯罪的可能性”[11]:77。在亚洲,一般紧张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持[17,20-23]。还有一些研究为其提供了部分支持[24]。但是,也有些研究发现,在使用亚洲数据时,一般紧张理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解释效力。
一项以中国台湾青少年为样本的纵列研究表明了适用一般紧张理论时所遇到的困难[25]。该研究发现,一般紧张理论中的抑郁因素可能在东方社会更加重要,而在西方社会中,愤怒因素更加有效。即便在东方社会中最为发达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如儒家精神和集体主义世界观”[25]:49-50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文化差异告诉我们不能不加修正地照搬西方犯罪学理论。
3.1.3 自我控制理论
按照2012年《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之一,即纳污红线。水功能区达标率考核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要求。水功能区达标率的指标,确定充分考虑了不同流域(区域)的开发利用程度和河流现状水质的差异性,以及污染源控制的长期性,在时间上按照不同水平年,确定了相应的水功能区达标率指标,如按照水利部的指标分解,长江流域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2020年为87%,2030年为95%;西南诸河2020年达标率92%,2030年为95%。
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西方犯罪学理论是自我控制理论。它宣称可以解释所有时间、所有空间内的所有犯罪。Gottfredson&Hirschi(1990)刻画了构成自我控制的、可以通过问卷法加以测量的各种人格特质,其中包括“倾向于冲动、冷漠、尚体、冒险、短视、寡言”[26]:90。
TRF是肝脏合成的结合金属的糖蛋白。在正常情况下TRF无法通过肾小球滤过膜,因此若在尿液中检测出TRF,则说明肾脏出现一定的损伤。如据钟巧玲[8]试验研究发现,在糖尿病早期肾脏损伤的患者中,检出TRF的数值为(11.38±7.04)mg/L,而在健康人群中,TRF检测数值仅为(0.89±1.22)mg/L。
3.3.1 西方范式
无论是美国的研究,还是亚洲的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更加复杂的因果过程。本文难以尽述,仅举其中一例。Jo & Zhang(2012)[32]在韩国检验了自我控制的稳定性假设。该文在一方面发现了与美国研究类似的结果——在使用态度测量法时,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具有稳定的发展轨迹。但是,该文也有些不同的发现:在使用行为测量法时,存在着“高降低”、“低增长”等不同群体。这表明在韩国语境之下,自我控制的绝对稳定与相对稳定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
社会控制理论测量群体或社区在减少犯罪方面的效果。Jiang等(2013)[33]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基层社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时,社区居民主观估计的财产犯罪数量将有所下降。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但是也有些结果是不同的。例如,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当半正式控制较强时,社区居民主观估计的财产犯罪数量反而上升了。该研究在结论部分指出,尽管可以用西方犯罪学理论作为一个起始的参照,但是为更加有效解释中国的犯罪问题,必须对其作出必要的修订。
心绞痛一直被认为是严重威胁我们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疾病之一,该疾病目前已经并不只发生于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而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急诊心绞痛大多发生在情绪不稳定的心绞痛患者身上,介于稳定型的心绞痛和急性的心肌梗死之间,属于不稳定的心肌缺血综合征,患者一旦发病,相当危急,更严重的就会有猝死的危险。所以,正确及时的急救护理不仅能够缓解急诊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症状,还可以避免疾病进一步恶化,及时挽救患者的生命。然而,该病患者一般会担心心绞痛突然发作,疼痛难忍以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加上患者对该病认识的不足,容易失去治疗的信心,导致该病患者负面情绪严重,经常会过度的紧张、郁闷、恐惧和焦虑。
3.1.4 社会控制理论
3.1.5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连结对于犯罪行为的影响。一项在日本进行的研究[34]发现,尽管如同社会资本理论预期的那样,友情群体与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但是,在社区层面的社会纽带与犯罪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这一发现引起了研究者的困惑。如果一个理论不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那么它自然不能被称作“普适理论”。这也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探究日本社会的哪些特有文化和社会制度可以解释上述差异。Jiang等(2013)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借鉴美国犯罪学理论之前,中国需要考虑到自己文化与其他特性,从而进行自己的经验研究”[33]:220。“普适理论”尽管可能有所助益,但是必须要批判性地评估它的适用性。
上述对第一阶段的小结表明,在应用西方犯罪学理论来解释亚洲社会的犯罪问题时,研究者们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结果。这促使亚洲犯罪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因地制宜的修订。对照之下,尽管西方犯罪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诸如自我控制、社会控制等概念在不同国家或社会具有不尽相同的适用性,但是他们仍然在致力于提出并检验“普适理论”。
3.2 第二阶段:修订西方理论
库恩论述到,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新的观察或实验所获得的事实时,就会出现一个引爆点。一种反应就是进一步发展理论以使其能够解释这些变异。其中不能只是小修小补,或者对各种差异作出权宜性的解释。它需要对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必要的再造,以使其能够解释亚洲社会的不同语境,甚至是认知上的差异。这种修订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修订后的理论要能够完美地解释世界各国的犯罪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亚洲社会。美国犯罪学家Messner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合作者已经对某些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这些修订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笔者强烈建议读者去参阅原始文献。本节只简要地介绍我们在日常活动理论、自我控制理论、情境行动理论、制度性失范理论等方面的修订工作。
3.2.1 日常活动理论
美学视域下的旅游景区是以美学学科的思维方式为考察标准,针对特殊化的对象进行研究。在媒介设计上,旅游景区的规划需要针对现实个人旅游活动的规划,围绕现实个人和活动对象整体之间的关系,开展审美向度的规划。利用简单的规划方式进行艺术形象上的设计,避免在旅游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产生破坏性和负面效应。在开展艺术形象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现阶段的美学特征进行规划,全方面考核市场的需求,保留历史景区的个性化特色。从感性角度上来说,是以个人感性活动为基础条件进行艺术形象设计的[1]。总之,要从美学视角下对旅游景区进行规划,呈现感性学美学视角下的界面。
日常活动理论是由Cohen &Felson(1979)[35]提出的。它提出了著名的“犯罪三角”——有动机的犯罪人、适宜的犯罪目标、保卫的能力。日常活动理论认为,只有当上述三个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聚合时,犯罪行为才会发生。
亚洲犯罪学家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发展出一种统一的范式,它既是整个犯罪学学科的一部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亚洲社会的特性。亚洲范式并不意味着摒弃西方犯罪学文献,而是要充分地认识到它们在解释亚洲社会的犯罪水平和刑事司法时的优势与局限。本文认为,为了发展出新亚洲范式,需要经历一个“三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检验既有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亚洲语境下的适用性;第二阶段是修订相应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将亚洲社会的特有文化纳入其中;第三阶段类似于南半球犯罪学家们制订的研究议程,我将在本文的结尾部分评述这一理论进路。
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还讨论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许多西方犯罪学家对亚洲社会的低犯罪率颇感兴趣。他们也试图使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某些犯罪学家认为亚洲社会普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则面临着一些困难。尽管亚洲社会的整体犯罪率较低,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该如何解释呢?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变量也引起了犯罪学家的兴趣。某些国家的警民比要高于西方国家。一些低犯罪率的亚洲国家建立了社区争端调解机制,而这在西方国家则是没有的。亚洲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儒家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尽管其重要性也有一定的差异)[7];然而,在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则是伊斯兰教;而在缅甸等其他国家,佛教文化则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刑事司法体系。
自我控制理论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效的儿童养育。其基本假设是,健康的、适应良好的个体会发展出较高的自我控制水平。但是,由于某些人“倾向于冲动、冷漠、尚体、冒险、短视、寡言”,因而更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
Messner(2015)修订了自我控制理论,使其纳入了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观点,西方思想家们在讨论自我概念的形成方法时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体能动性的性质。Kitayama&Uchida(2005)[38]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能动性:独立型、相依型。在独立型能动性下,“自我主要是由个体内在的一些属性所界定的,如行为人自己的目标、欲求、需求、人格特质、能力等”;相较之下,依存的能动性则承认在某些社会中存在着强连结,“有所关联的他人的目标、欲求、需求与行为人自己的是同样重要的”。在西方社会,独立型能动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依存型能动性则在“东亚社会的文化中是相当主导性的”。如果自我控制在东、西方社会中是不同的,那么自我控制理论可能就不应该被称作普适理论了。
3.2.3 情境行动理论
对于企业来说,物流是第三利润,通常情况下,企业总成本当中物流成本的所占比例大概为四成左右,而生产成本只有一成左右;物流时间为九成左右,制造时间仅为一成左右。因此,企业物流水平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率的,且物流体系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资产损益表等均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若能够将物流总成本最优作为基本原则来开展企业的整体规划与整体运作,则企业财务业绩会获得大幅提升。
另一个获得了较多学术关注的普适理论是情境行动理论[39]。行为人通过其提出的“情境动力机制”而认知到了某些行动选项并在其间加以选择。其中需要测量的两个变量分别是行为人特征、环境的性质。情境行动理论在测量行为人特征时使用的概念是“犯罪倾向”。如果行为人有着较强的“道德过滤”,并且有着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么行为人就不太可能犯罪。环境既可以减少犯罪的机会,也可能是犯因性的。环境的某些特征可能促进了或者说未能抑制犯罪。情境行动理论认为行为人的犯罪倾向、即时环境中的激励与反激励因素共同决定着行为人是否选择犯罪行为。
Messner在《当西方遇到东方》指出,情境行动理论亦没有考虑到更宏观的背景。该理论假定在各个国家的每个行为人有着同样的认知模式和社会取向。然而,文化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了,“认知选择过程”这一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存在着文化界限的。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解释犯罪行为差异的自变量之一。然而,这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人可能由于其集体主义取向而表现出不同水平的“犯罪倾向”。由此看来,只有将情境行动理论加以适当的修订才有可能解释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行为人如何作出犯罪决策。
3.2.4 制度性失范理论
在美国出现的最早的紧张理论是由Merton提出的。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了社会设置之间的关系之后,Merton提出了自己的紧张理论。这与后来的理论所具有的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取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照。紧张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有效发挥其功能的某种社会设置可能会与其他社会设置的需要相冲突。Merton指出了不同社会设置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因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某种道德价值观被经济增长的需求所削弱。Merton使用的另一个概念是“失范”。在迅猛的经济、社会变迁的条件下,传统的社会设置难以维持既有的秩序,也难以阻止犯罪。在犯罪学领域中,这一社会学理论被发展为“制度性失范理论”。研究者更加关注了不同社会设置之间的“权力平衡”;此外,在不断变迁的现代社会中,主流价值观与社会设置内部的紧张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
脱胎于公共行政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是一个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法学、社会学等研究视角与方法于一身并不断向更多元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的新兴学科,其学科特性决定了在本科生的培养过程中,必须搭建一个宽泛的学科基础平台,并着眼于分析、研究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全国设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院校的本科生招生情况来看,主要是按大类招生和分专业招生两种,不论是前者和后者,最后都会落脚到具体的专业方向选择,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因而在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上,两种招生方式基本上是如出一辙,这就决定了无论采取何种招生方式,导师制都能体现其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适应性和推动性。
制度性失范理论认为社会团结与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然而,这并不一定以同样的程度适用于亚洲国家,因为在亚洲国家,通常存在着相对更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制度失范理论所使用的许多概念有助于解释西方社会的犯罪,诸如: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设置之间的平衡、规范性秩序的生命力。然而,在亚洲社会,存在着机会主义的集体价值观、以及更加强大的中央政治控制。上述差异提示我们应该再造而不是简单地修补这一理论以使其适用于有着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非西方社会。
3.3 第三阶段:基于亚洲社会的新概念和一种新理论
有没有可能超越对西方犯罪学理论进行修修补补的阶段呢?这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发展出亚洲社会的犯罪学理论,另外,一些犯罪学家可能已经习惯了西方犯罪学的发展模式。Braithwaite(2015)专注于恢复性司法,并且基于对亚洲国家的司法实践的观察而提出了恢复性司法的五个基本假设[40]。《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则进一步论述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社会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而构建了“关系主义刑事司法理论”。下面,我将再次概括一下关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美国,自我控制理论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它们大多发现具有上述人格特质的行为人在面临犯罪机会更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尽管现在依然存在着某些方法论上的争议,如自我控制的量具、高犯罪风险的测量,但是,总体而言,自我控制理论可以有效地适用于美国社会[27]。类似地,这一理论在应用于亚洲社会时出现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其中某些研究得到了支持性的结论[28-30],而另一些研究发现了不具统计显著性的因果关系[18,3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状况 未治疗时,在SAS、SDS两者分值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治疗,两组的SAS及SDS均较治疗前SAS及SDS得分差异,观察组分值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西方的刑事司法体系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尽管一般认为适用于所有的西方社会,但实际上每一个特征都具有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特异性。
第一,西方的刑事司法体系是“个体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核心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哲学中的个体主义传统。此时,犯罪被定义为行为人个体违反了国家意志的行为。在西方思想中,个体是起点。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通过“社会契约”让渡了某些权利,但是司法体系仍然主要关注个体。这种个体主义的传统在一些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罗尔斯。
第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由于国家比个人具有更大的权力,因此需要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从西方国家的法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英国的司法体系中,程序正义与法治被视为核心理念;美国宪法包括了许多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
第三,大量使用抗辩性的方法以寻求真相。西方刑事司法体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之上的。
(3)如果容量为1MW及其以上的发电机定子绕组和引出线出现短路,需要装设纵联差动保护。其保护配置作为发电机内部短路的主要保护,能及时、灵敏地切除内部所发生的故障,确保动作的选择性与工作的安全性。
3.3.2 亚洲范式
从亚洲视角来看,很难全盘接受西方刑事司法体系的上述假设。这在部分上是由于亚洲社会通常认为,司法不仅仅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便在西方体系之下,被害人尚未充分地获得程序正义的权利。亚洲社会有着刑罚之外的不同目标。亚洲司法体系的目的是治愈社会、提供赔偿、恢复和谐的社会关系。
割草车在农业、园林等领域应用广泛,而节能优化设计可以使割草车在同样能耗下行驶更长距离,进行更长时间的割草工作。割草车的主要工作部件是割刀,因此刀片的节能优化设计对降低能耗具有重要的意义[8-9]。本文应用Fluent软件对某割草车刀盘和刀片进行模拟计算,分析刀片在刀盘中的运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刀盘角区和刀片的形状进行优化。
亚洲国家的关系主义特征具有四个要素:
第一,更加看重对于家庭和社区的依恋。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国家的犯罪率较低。个人不能忍受来自更大群体的反对意见。这在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物质满足的重要性。
第二,亚洲社会的个人与群体都更加注重荣誉。无论是中国家庭,还是韩国或日本家庭,都把维护家族荣誉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这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作“要面子”。偷东西的人被认为是丢了全家的脸面,甚至导致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研究表明,亚洲社会将集体主义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对于亚洲人而言,与家庭、社区、宗教组织等各种不同群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人对于家庭、朋友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41]。甚至可以说,家庭和社区对于其成员的行为负有集体责任。在其他国家,集体主义有着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印度,社区在影响和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方面更加重要;在中国,家庭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而社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其中的共同特点是集体主义。这导致了共通的行为和情感。在东亚社会中,个体被嵌入到许多社会关系之中,而在西方国家,个体的社会关系则要少得多。“关系主义”(relationism)这一概念清楚地表达了东亚社会的特征。关系主义司法理论认为,这些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在影响着亚洲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
第三,对于亚洲社会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追求和谐或避免冲突。这与西方刑事司法体系更加注重冲突与惩罚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笔者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所讨论的,亚洲社会存在着许多非正式机制,其中包括了恢复性司法、习惯法等,它们都试图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前来解决纠纷。这些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群体内部的和谐,而不仅仅是惩罚或改造犯罪人。
第四,亚洲社会更加偏重于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而西方社会则偏重于分析思维(analytical thinking)。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按照Nisbett等(2001)[42]:293的定义,整体思维是指“将背景或场域视为整体的一种倾向,其中包括对焦点客体与场域之间关系的关注,并偏好以这些关系为基础来解释或预测事件”;对照之下,分析思维则是指“将客体与其背景相脱离,倾向于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以将其归类,并偏好使用分类规则来解释或预测客体的行为”。该文的观点是,东方文化更倾向于将事件、客体与个人或群体关系联系起来,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使用脱离了背景的某些因素进行预测。
如果亚洲社会的确拥有独特的、关系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会影响到它们如何理解犯罪与司法。此时的关注点不是个体的犯罪人,而是群体。此时的核心目标是恢复家庭、社区等群体的和谐,并修复犯罪人对这些群体的依恋。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对抗性的冲突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各方的合作而实现的。在恢复性司法中,目标是改变犯罪人的心态,因此它更加强调道德教育,而不是报应性的刑罚。
支持者们认为关系主义司法体系要比西方司法体系更加有效。有证据表明,前者的再犯率更低、被害人获得了更好的结果、法律得到更多的尊重。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估或描述这种不同的司法体系是如何在亚洲社会运行的。首先的工作是注意到在亚洲社会的确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理念,而且在亚洲社会的不同法律体系中体现着类似的原则。它更加强调达到公正的实体正义,即便这有可能脱离了正式的法律条文。中国法律中有一个应该深入探究的概念,就是“天理人情”。
还应该更加关注非正式的习惯法。在中国,不但有“天理人情”的概念,还存在着一些地方性的传统或乡约民规。在这些非正式程序之下,民间调解人员会综合考量整个案情,而不是机械地或孤立地考虑问题。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程序上的保障,而且鼓励行为人自己的认罪悔罪。然而,调解人员必须要兼顾各方的权利和利益、避免极端(即坚持中庸之道)。其目标是避免耗钱耗时的法律诉讼(即无讼)。
3.3.3 关系主义理论对于“获取正义”的意义
在《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中,我论述了亚洲范式理论将如何有助于政策规划,这也是西方社会和国际组织感兴趣的问题。它就是如何保证居民获取正义的问题。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切是法律援助的预算正在被削减。在亚洲国家,居民接受法律服务的入口更少。在此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其人均GDP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Agrast等(2011)[43]给出了一系列表格来描述亚洲社会在获取民事和刑事正义方面的较低水平。由于城市化率较低,因此这一结果并不令人奇怪。亚洲的城市化人口占比47.5%,而在北美地区这一数据为81.5%。中国的数据并不高,仅为53%;印度的数据更低,仅为32%。农村人口难以承受在城市的较高消费水平,通常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服务。
由于上述差异,因此使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在获取正义上的水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当社区承担着很大的调解纠纷作用时,将是不是获得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作为衡量标准也是误导性的。恢复性司法只是众多实践中的一种。还有一些习惯法在发挥作用,这比成文法更加物美价廉。这种做法更加有效,而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讼与和谐是儒家的正义目标。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调解在当代中国有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层面上,这些传统做法也受到了推崇。例如,在2010年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鼓励和支持就地调解民间纠纷。地方政府为人民调解工作给予官方的支持和保障。在人民调解的工作机制下,当地社区、行为人、被害人共同协商解决方案。
类似地,在印度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存在着非正式的法律体系。我并不是说这些替代法律的做法就不存在困难,也不是说这些做法应该被西方社会所借鉴。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不同地方的国家或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是没有差异,那么就难以提出有效的改革方案了。亚洲范式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在亚洲社会中既有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无论在经济角度还是在文化角度都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
4 结语:未来的研究方向
如前所述,基于以往发表的三篇文献[1-3],本文概括了笔者对于亚洲犯罪学以及亚洲范式理论的最新思考。Braithwaite在亚洲犯罪学学会的第六届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亚太地区涵盖了世界上许多最灿烂的文化和多样化的语言。因此,亚洲对于国家犯罪学的最重要贡献不应是借助东方的经验来调整、检验、修订西方理论,而应是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西方理论。在国际犯罪学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学者分别在各自的社会中对于西方主流理论加以检验,而亚洲犯罪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检验西方理论在亚洲社会的适用性或者适当地修订那些理论以适用于亚洲社会。现在到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时候了。现在到了由亚洲学者提出亚洲本土的犯罪学理论的崭新时代了。……我希望这些理论能够为刘建宏教授提出的犯罪控制的关系主义理论添砖加瓦”[40]:183-184。
丁小慧还有很多小事,都让许诺在她的身上看出了自己的问题,他尝试着改变自己,也更努力地投入事业。他的表现终于赢得了岳父的认可,主动给他介绍一些资源,帮他扩大了规模,在这个城市的加工业,许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一部南半球犯罪学家的文集中[44],作者们发现了国际犯罪学发展过程中的类似问题。由于在知识生产中存在着一种等级观念,因此亚洲犯罪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难以得到认可。比较犯罪学研究通常是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弥合南北犯罪学的落差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有许多途径来推进上述研究进程。现在不但有机会来检验那些具有亚洲特色的既有理论,而且有机会发展出更多的新理论。将亚洲刑事司法体系的特点纳入到研究问题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研究者在形成和理解研究问题能够考虑到特定国家或社会的具体特点,那么这些研究问题就会变得有所不同了。例如,在中国和印度,环境污染问题就要比欧洲和北美地区严重得多。此外,我们在研究亚洲社会的犯罪与控制时,有必要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许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认识犯罪问题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进路。为了弥合南北犯罪学的巨大落差,我们需要巨大的努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能够有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共同发展犯罪学,这是我们这一代犯罪学家的幸运。
参考文献:
[1] Liu J.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9, 4(1):1-9.
[2] Liu J. Developing an Asian criminology paradigm:Theoretical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A]//In Carrington K, Hogg R,Scott J, &Sozzo M. (Eds.), Palgrave handbook on criminology and the global south[M]. London: Palgrave, 2017.
[3] Liu J. Asian paradigm theory and access to justice[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016(3):205-224.
[4] Belknap J . Asian criminology’s expansion and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and crime control practices[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6(4):1-16.
[5]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c revolutions(3rd ed.)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6] Liu J. Data sources in Chinese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J]. Crime Law & Social Change, 2008(3):131-147.
[7] Liu J. Principle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China[J]. EuropeanForum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2007(1):2-3.
[8] Liu J, Zhang L, Messner S.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in a changing China[M].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1.
[9] Messner S. Social Institution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ise of Comparative Criminological Research[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4(1):49-63.
[10] Pratt T, Cullen F, Sellers C, et al.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eta-Analysis[J]. Justice Quarterly,2010(6):765-802.
[11] Lilly J, Cullen F, Ball R.Criminological theory: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5th ed.) [M]. CA, Sage Publication,2011.
[12] Cheung Y. Family, School, Peer, and Media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997(5):569-596.
[13] Wong D. Pathways to Delinquency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South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001(1):91-115.
[14] Ma H, Shek D, Cheung P,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eer and teacher influences o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of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J]. 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2(2):157-168.
[15] Davis C, Tang C, Ko J. The impact of peer, family and school on delinquency: Astudy of at-risk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4(4): 489-502.
[16] Ngai N, Cheung C. Predictors of the likelihood of delinquency a study of marginalyouth in Hong Kong, China[J]. Youth and Society, 2005(4): 445-470.
[17] Bao W, Haas A, Chen X, et al. Repeated Strains, Social Control, Social Learning, and Delinquency: Testing an Integrated Model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in China[J]. Youth& Society, 2014(3):402-424.
[18] Cheung N, Cheung Y. Self-Control, Social Factors,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8(4):412-430.
[19] Agnew R. Us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to Explain Crime in Asian Societies[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5(2):131-147.
[20] Cheung C, Ngai N, Ngai S. Family strain and adolescent delinquency in two Chinese cities, Guangzhou and Hong Kong[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07(5):626-641.
[21] Bao W, Haas A, Pi Y. Life strain, coping, and delinquen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from a matching perspective in social suppor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2007(1):9-24.
[22] Cheung N, Cheung Y. Strain, self-contro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linquenc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Extend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2010(3):321-345.
[23] Liu R. Strain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delinquent participation: A China study[J].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011(4):427-442.
[24] Wong D. Pathways to Delinquency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South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001(1):91-115.
[25] Lin W.General strain theory in Taiwan: A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approach[J].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2(1):37-54.
[26] Gottfredson M, Hirschi T.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0.
[27] PrattT, Cullen F.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meta-analysis[J].Criminology, 2000(3):931-964.
[28] Cretacci M, Craig J, Fei D. Self-control and Chinese deviance:A look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s, 2009(2):131-143.
[29] Chui W, Choon H, Chan O. The gendered analysis of selfcontrol on theft and violent delinquency: An examination of Hong Kong adolescent population[J]. Crime &Delinquency,2013(12): 1648-1677.
[30] Cheung N. Low self-control and co-occurrence of gambling with substance use and delinquenc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4(1):105-124.
[31] Wang G, Qiao H, Hong S, Zhang J. Adolescent social bond,self-control and deviant behavior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02(1):52-68.
[32] Jo Y, Zhang Y. The stability of self-control: A group-based approach[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2(2):173-191.
[33] Jiang S, Land K, Wang J. Social tie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perceived neighborhood property crime in Guangzhou,China[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3(3):253-269.
[34] Takagi D, Kawachi I. Neighborhood social heterogeneity and crime victimization in Japan: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4(4):271-284.
[35] Cohen L, Felson M.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9(4):588-608.
[36] Messner S, ZhouL, Zhang L, Liu J. Risks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lifestyle/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J]. Justice Quarterly,2007(3):496-522.
[37] Messner S. When west meets east: Generalizing theory and expanding the conceptual toolkit of criminology[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5(2):117-129.
[38] Kitayama S, Uchida Y. Interdependent agency: An alternative system for action[A]// In Sorrentino R, DovC, Olson J, Zanna M.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The Ontario symposium[M].Mahwah: Erlbaum, 2005:137-164.
[39] Wikström P, Oberwittler D, Treiber K, Hardie B. Breaking Rules: The Social andSituational Dynamics of Young People's Urban Crim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0] Braithwaite J. Rethinking criminology through radical diversity in Asian reconciliation[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5(3):183-191.
[41] Komiya 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low crime rate in Japan[J].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99(3):369-390.
[42] Nisbett R, Peng K, Choi I, Norenzayan A.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2):291-310.
[43] Agrast M, Botero J, Ponce A. Rule of law index 2011[M]. WA:The World JusticeProject, 2011.
[44] CarringtonK, HoggR, ScottJ, Sozzo M. Palgrave handbook on criminologyand the global south[M]. London: Palgrave, 2017.
The New Asian Paradigm: A Relational Approach
LIU Jian-ho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Developing an Asian criminology paradigm: Theoretical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d Asian paradigm theory and access to justice, the roadmap of “Three Stages” was outlined in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sian criminology. The first stage is to test existing Western theories in Asian contexts. The second stage is to revise those theories so that they take account of the distinctive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 The third and final stage is to develop new conceptsand theories within Asian criminology.The relational approachas a new Asian paradigm is emerging as a result of this roadmap. Relationism, including four elements of attachment to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caring for honors,pursuit of harmony, and preference for holistic thinking, is regarded a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n Asian societie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s instructive for both further developing Asian criminology and access to justice.
Key words: Asian Paradigm, Asian Criminology,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Relationism, Access to Justice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39(2019)05-005-09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9-07-13
作者简介: 刘建宏(1954-),男,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亚洲犯罪学学会创任会长,亚洲犯罪学学会大会主席,国际犯罪学学会科学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比较犯罪学研究。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基础教研部 杨学锋 译)
(责任编辑:王 薇)
标签:亚洲范式论文; 亚洲犯罪学比较论文; 犯罪学关系主义论文; 获取正义论文;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