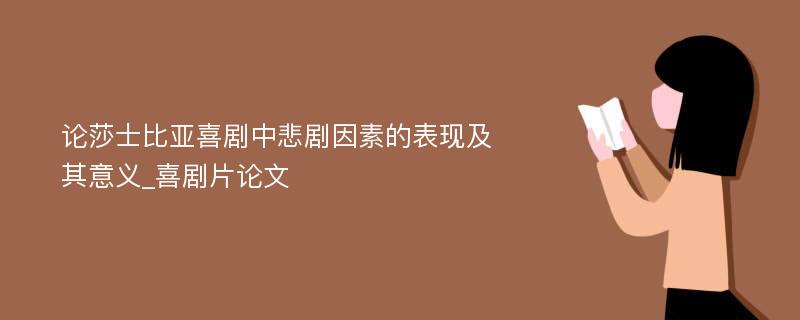
论莎氏喜剧中悲剧因素的表现形式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现形式论文,喜剧论文,悲剧论文,意义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中,学者们对莎氏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探讨颇多,而对喜剧中的悲剧因素的注意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莎氏喜剧中的悲剧因素远比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在推动剧情发展,加深人物性格刻划,增强作品批判力度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表现方式也极具特色。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色,才使得莎士比亚将悲与喜、美与丑、崇高和滑稽溶合得浑溶无间,构成了莎士比亚别具一格的喜剧体系。本文拟对这一常被学者们忽略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重点讨论莎氏喜剧中悲剧因素在各种喜剧中不同的表现形式。
莎剧专家们通常根据不同题材和风格将莎氏喜剧分为喜庆剧、问题喜剧和传奇剧三大类。当我们分析这几类不同喜剧的情节和结构布局时,不难看出,悲剧因素在莎士比亚不同时期的喜剧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其表现形式至后期作品中也愈臻完美。在早期喜庆剧中,悲剧因素通常表现在背景或框架故事中,在问题喜剧中悲剧因素多渗透到人物性格之中;而到晚期的传奇剧中,悲剧气氛几乎笼罩全篇。所谓“悲剧因素”,即是指戏剧情节中包含的“主人公无辜受难”的过程。朱光潜先生曾指出:“通常给一般人以强烈快感的,主要就是悲剧中这‘受难’的方面”。但这类悲剧因素却在莎氏喜剧中启动了基本的戏剧情节,构成戏剧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推动剧情发展。
以《错误的喜剧》为例,剧中叙拉古商人伊勤为寻找失散的妻儿进入了敌对国,身陷囹圄,面临杀身之祸。这种悲剧性情节导致了一连串的喜剧性误会场面,然而伊勤的悲剧命运到最后全家团圆时才得以改变。莎士比亚在此创造了在喜庆剧中用悲剧故事框架套喜剧情节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在《皆大欢喜》和《仲夏夜之梦》中尤为明显。在《仲夏夜之梦》中,伊吉斯反对女儿赫米娅和拉山德的恋爱,并以死刑相威胁。恋人们为追求爱情逃离雅典,进入丛林,在林中展开了主要的戏剧行为。同样,在《皆大欢喜》中,男女主角奥兰多和罗瑟林为逃脱篡位公爵的迫害而逃入丛林,在那儿表现了妙趣横生的恋爱求婚的场面。
喜庆剧中的悲剧因素有时只表现为一种氛围,或自然界的某种恶势力。如《第十二夜》中女主角微奥拉女扮男装,一面爱慕着她所侍候的奥西诺公爵,一面又受到伯爵小姐奥西维娅的求婚,充满了幽默与欢乐。但是剧中仍不乏悲剧意味,剧中开头渲染了好几个死亡的形象;微奥拉在海中遇救时目睹了其兄在风浪中挣扎逐渐沉没的情景,心中因此而蒙上了兄长遇难的阴影。奥西微娅出场时也满面愁容,陷入了对亡父亡兄的哀痛不能自拔。与这些悲哀情调相呼应,剧中小丑弗斯特唱的四首歌曲中,有三首的主题与死亡有关。他在《过来吧,死神》中道:“莫让一朵花儿甜柔,撒上了我那黑色的棺材;/没有一个朋友邪候,/我尸身,不久我的骨骸将会散开。”(莎士比亚全集四卷39页)所有这些死亡形象,与沉浸在爱河里的恋人们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感到爱情和幸福受到有限的人生和无情的自然界势力的制约。显然,这里的悲剧因素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这个世界能给人带来幸福,也能给人带来灾难。
悲剧因素在《仲夏夜之梦》中表现为社会习惯势力对恋人们爱的世界的威胁。伊吉斯反对其女赫米娅和拉山德自由恋爱,这种反对是非常专横、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为女儿安排的对象狄米特律斯和赫米娅的意中人拉山德无论在地位、财富还是外表上都相差无几,伊吉斯执意要女儿服从他的选择,无非是为了维护他的“父道尊严”。这种父母包办婚姻的风俗,虽不合情理,却受到雅典法律的支持。雅典公爵忒修斯虽同情赫米娅,却不得不服从他所代表的宫廷而对赫米娅依法办事:她如不从父母之命将会被处以死刑或受到一辈子当修女的惩罚。虽然恋人们在几经周折后终能如愿以偿地结成伉俪,但社会习惯势力对爱的世界的威胁,又在最后一幕匠人们演出的闹剧中再现出来。闹剧中提那摩斯和提斯柏由于父母的反对而不能结合,双双在月光下惨死。临死前提那摩斯痛苦地呻吟道:“墙啊,你常常听到咱的呻吟,怨你生生把咱共她两两分拆!”看到这里,人们不禁想到正在剧中看戏的少男少女们可能因社会势力这堵墙遭受到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的厄运。
喜庆剧《皆大欢喜》中的悲剧因素来自恶棍式的人物——篡位公爵弗莱德里克和男主角的兄长奥列佛。前者迫害女主角罗瑟林,将她赶出宫廷,并派人追捕罗瑟林和其恋人奥兰多,后者多次企图谋杀其弟奥兰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为逃避迫害,追求爱情,男女主角先后逃进亚登森林并在那儿展开了热恋的喜庆场景;但是前文所说的两个恶棍仍然率兵追踪,威胁着男女主角的生命,这种威胁直到剧终才得以解除。弗莱德里克和奥兰多无疑是喜剧世界、即爱的世界的仇敌,但他们对喜剧世界的男女主角的仇恨却来自于对男女主角所具有的美德的忌妒。这或许正是他们不像《终成眷属》中的唐·约翰那样无可救药,最后得到感化、改邪归正的原因。
由此可见,喜庆剧中的悲剧因素造成这类喜剧的剧情发展一般历经由悲到喜或转悲为喜的转折,主人公由祸转到福;这种情节使我们由开始的紧张、压抑很快转为轻松愉快,而作为主人公遭受苦难原因的社会传统势力的代表或恶棍式的人物在剧情的喜剧性转折中成为真正的喜剧人物,他的乖戾性格、可笑的行为或愚蠢的表现都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由于觉察到他的失败而感到他行为的可笑。在这类喜剧中,最初经历磨难的主人公不同于悲剧中的悲剧人物,他们能凭自身的力量走出逆境,因此,“心情和悦,接受一切失败和灾祸的谑浪笑傲”(黑格尔,第三卷下册333页),使他们也成为符合喜剧本质的喜剧人物。 莎士比亚把“主人公遭受苦难”的悲剧性故事作为喜剧情节的开端或框架故事,即“喜剧用作基础的起点正是悲剧的终点”(黑格尔),使他的这类喜剧体现出接受失败和超然失败之上的豪迈气慨和幽默精神。
问题喜剧中邪恶势力往往使男主角与恶行为伍,甚至险遭灭顶之灾。这种模式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就已显露端倪。这条悲剧线索直到普洛丢斯的丑行被彻底揭穿,灵魂得到拯救,决心改邪归正时才得以终止。类似普洛丢斯式的人物,有《终成眷属》中的勃特拉姆,以及《一报还一报》中的安格鲁等。他们都在剧中经历了一个改造过程,在不同程度上与恶行为伍,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受到伦理道德的净化后被原谅或饶恕。他们没有得到悲剧性的结局是因为在改造过程中灵魂受到净化,悲剧因素被消除。
问题喜剧中的男主角还常常由于对真善美缺乏坚定的信仰,无意中和恶势力合谋,从而形成威胁爱的世界的悲剧因素。以《无事生非》为例,剧中唐·约翰无中生有诽谤淑女希罗,使她蒙受不白之冤。唐·约翰显然是《奥赛罗》中依阿古式的人物,以破坏他人的幸福为人生的最大快乐,然而他用以害人的卑鄙伎俩必须依靠受害者的轻信与“合谋”才能得逞。不幸的是,剧中男主角克劳狄奥十分轻信,容易受骗上当,对希罗的美德视而不见。约翰告诉他希罗与他人私通,克劳狄奥立即化爱为恨,在教堂里举行的结婚仪式上当众羞辱希罗。于是,一个贞洁的处女无端受到陷害,受到像王子、将军等正直人的无情谴责。连希罗的父亲也不得不痛斥自己的掌上明珠的“失贞”行为,说她现在落进了污泥坑,大海的海水也洗不尽她的秽行。(全集二卷142 页)而当其父也错误地谴责女儿时,剧情的悲剧色彩就更加明显了。如美国莎学研究者享特所指的那样,父爱,特别是父亲对女儿的爱,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纯洁的感情纽带。这条纽带一旦断裂,像《李尔王》和传奇剧中出现的那样父不认女,就必然在爱的世界产生骚乱和悲剧性结局。显而易见,爱是莎士比亚喜剧世界的基础,由爱转变成的仇恨,有时要比恶棍的丑行对喜剧世界的威胁更大。谴责一个处女失贞,无疑是对一个女子最沉重的打击。虽然希罗遵神父之嘱,假称死亡,实际上,希罗业已名声扫地,她的“死”和由此而引起的悲剧意识直到将近剧终前都一直压在男主角克劳狄奥和她的挚友们的心头。
这里克劳狄奥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他那趋于恶的行为似乎是由追求完美的欲望推动的,他使自己的恋人希罗遭受痛苦和伤害,但同时也伤害了自身。他的行为完全符合黑格尔为悲剧人物下的定义:“悲剧人物所定下的目标,单就它本身来看,尽管是有理可说的,但是他们要达到这种目标,却只能通过起损害作用的片面性引起矛盾的悲剧方式。”
在《一报还一报》中代表恶势力的安哲鲁并非是天生的恶棍,而他之变成恶棍乃是由于人性本身的脆弱,但他却更能威胁喜剧世界。威尼斯法律支持夏洛克,保护一磅肉的契约,但最后的定论不是由夏洛克,而是由《威尼斯商人》中的公爵来下,所以夏洛克的凶残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然而安哲鲁是摄政公爵,操生杀大权,当他以权谋私时,就比夏洛克更为危险。安哲鲁一出场时道貌岸然,受到剧中人众口一辞的称赞。但当依莎贝拉为其弟克劳狄奥向安哲鲁求情时,他立即为依莎贝拉的美貌所动心,无力抑制心中的欲火,在自己非理性的感情冲动面前败北。因此,他蜕变为恶势力的代表,决心“一不做,二不休”,逼迫依莎贝拉奉献出自己的肉体来拯救她的弟弟。
安哲鲁一方面自己罪恶深重,一方面却不顾劝阻,坚持要处死克劳狄奥,妄图杀人灭口。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惊人蜕变:一个近乎完人的正人君子竟无力克制心中的欲火而一步步滑向罪恶深渊,犯下了通奸、谋杀罪行(尽管由于公爵的暗中操纵,安哲鲁没有得逞),险些完全自我毁灭。安哲鲁的蜕变过程向我们揭示:人性是如此脆弱,善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防线,在考验和精神危机中,有人会不堪一击,受恶势力主宰而变成危害爱的世界的代表。同安哲鲁十分类似的还有《终成眷属》中的男主角勃特拉姆。他色迷心窍,违背婚誓,抛弃妻子,破坏处女贞操,出卖传家宝指环以换取淫欲的满足,一步步陷入罪恶不能自拔,使自己的妻子远走他乡,因而使全剧笼罩着浓厚的悲剧气氛。
众多问题喜剧的悲剧人物体现了莎氏对人性的探索。他显然认为人自身的弱点——嫉妒、轻信、野心、报复心等是造成人的不幸的重要根源,但在这类剧中,人性的邪恶最终被爱的力量所化解、所战胜,避免了全剧转向悲剧性结局,因而这类喜剧仍然表现了莎士比亚对人性的乐观看法。
传奇剧可以看作莎氏戏剧由喜剧向悲剧的过渡,这类喜剧中,不仅人物性格含深刻的悲剧性内核,而且剧情的发展也很难纳入喜剧的规范。照黑格尔的理解:“喜剧性一般是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动作发生矛盾,自己又把这矛盾解决掉,从而感到安慰,建立了自信心。”而在这类传奇剧中,人物自身已经无法将矛盾解决掉,而必须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大团圆的结尾在这里已经纯粹成为一种“光明的尾巴”。
在传奇剧《冬天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人类自毁的情景。剧本的前半部中,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给自己带来一个又一个灾难,剥夺自己王位赖以支撑的基础。像安哲鲁、勃特拉姆一样,里昂提斯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和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人向他挑唆引诱,没有任何犯罪的借口。他不象克劳狄奥那样受到唐·约翰的挑拨,不象安哲鲁那样被依莎贝拉的美貌所诱惑,使他陷入恶行的是他自己的变态心理。
《冬》剧的开头展现的西西里王朝是一幅安乐美景,充满了温情和友爱。里昂提斯深爱着妻子赫米温妮,盛情款待他的平生好友——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但不久他就捕风捉影地猜忌自己的妻子和挚友,整个身心陷入病态,靠想象来解释事物。于是里昂提斯变成威胁爱的世界的恶势力,他的充满仇恨的头脑驱使他恶念丛生,滥杀无辜,杀友,杀妻,甚至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变得比虎狼还凶狠。他打击他周围所有的人,摧毁他自己幸福的基础,几乎整个断送掉他那原本安定有序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恨来自于他对其妻的爱,来自于由爱而生的妒火、无中生有的猜忌;来自于他对人的本性的悲观看法——他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荒淫的星球”,人生本恶,由此而产生了他的变态心理。里昂提斯十分象悲剧人物奥赛罗。他们开始都深爱自己的妻子,由于无端猜忌转而对妻子仇恨,从而使剧情向悲剧方向发展。当然里昂提斯的恶行由于受到手下朝臣的暗中阻止,没有发展到奥赛罗那样严重,并最后得到拯救,但两剧的前半部的悲剧气氛相差无几。然而里昂提斯为自己的罪孽所付的代价比前面讨论的各个喜剧中的男主角要大得多。当他最后幡然悔悟时,他已失去爱子、二个爱卿,十二年没见到自己的妻子,他的黄金年华在自己无可挽救的恶果和不尽的悔恨中度过。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喜剧中的悲剧因素一般作为剧中的喜剧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一方面,它是喜剧行为本身所包含的悲剧性因素,并参与导致戏剧性冲突;另一方面,它又形成对喜剧世界的一种威胁,危害剧中男主角的命运,破坏喜剧世界的正常秩序,甚至使剧情罩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只是由于这些恶势力最后都被爱的力量所化解,才避免了全剧转向悲剧性结局。
从上文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莎氏喜剧获得巨大成功的因素固多,但最关键的在于:莎士比亚基于他对生活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和研究,首先打破了悲剧与喜剧的界限。因为人性和人类生活本来就是十分复杂的,往往美与丑并存,崇高和卑下相共。莎士比亚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因而在他的喜剧创作中,他不但写到了喜剧人物也有美德,更重要的是,他更深入一层,尽力探寻隐藏在喜剧人物乃至恶棍式人物背后的悲剧性潜流,并进而探求其社会根源。如上举他对《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蜕变过程的描写,就足以显示出作者探索人性的深度。莎士比亚式的喜剧,大大拓展了了戏剧的题材,同时也大大加深了文学反映生活,描写人物的深度和力度。他的开创性的成功探索,无疑对雨果提出“美丑对比”原则,特别是对别林斯基主张写“含泪的喜剧”的著名理论有莫大的启迪作用。更重要的是,20世纪大量悲喜溶合的新喜剧的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莎士比亚在喜剧中溶入悲剧因素这一独特的喜剧理论遗产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