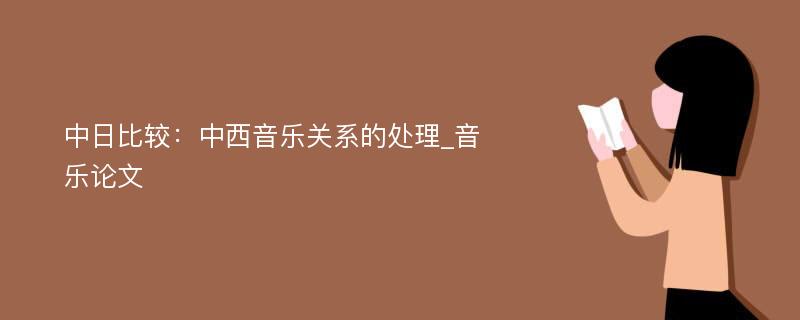
中日比较:音乐的东西方关系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中日论文,关系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日两国在音乐的东西方关系处理上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并置比较;提出建立全球音乐文化大生态,以及在全球视野中看待各国音乐文化的必然和必要;归纳出音乐文化发展的四种具体类型或品种,即原型、变型、杂交型与新型。
在20世纪中国音乐思想的“四大死结”[①]中,中西关系是其中一个难解的历史困惑。翻开日本的近现代史,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进入,从观念到实践上亦有与中国相似的情形,而对音乐的东西方关系的处理,又有与中国不同的地方。世纪末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与展望,对于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东方人来说,或许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一、两国历史的异同——并置的比较
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的国际背景上,中日两国是相同的,那就是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和掠夺。这种背景直接呈现出西方的强势和东方的弱势,这对中日近现代的新音乐发展在社会心态和音乐文化当事人的群体行为上都造成一种定向。西方列强在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强大,给东方人一种它们的文化也更优越、更高级的错觉。这种错觉便是音乐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得以在东方立足并长驻不退的根源之所在。
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的方式上,中日两国亦大体相似,即一方面西洋音乐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打进来的,另一方面却是中国人、日本人主动出去学回来或迎进来并主动在本土传播的。那些重要的新音乐文化当事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深入学习过西方音乐。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曾去西方国家求学。他们的求学行为显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在中国为“反封建、反关闭、富国强兵”,在日本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二者何其相似。中日两国共同的社会心态是力求摆脱在西方对比下的弱势地位。要转弱为强,就要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发达起来,而要在各方面发达起来,就必须寻找快捷的路径,于是向强者西方国家学现成的东西便自然地成了一种便利的选择。不同的是,日本是用国家力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及设备,聘外国专家和派遣留学生来培养人才的[②],而当时的中国在留学方面则更多是个人的自发行动。
日本比中国更早一步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这样便为稍迟一步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桥梁,许多中国音乐家是从日本学到西洋音乐的。
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教育。中日两国的音乐教育都采用了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在日本是由政府有意识地派人赴欧美考察,之后在本土按西方教育样式建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及实业学校三种教育体系以及普及小学等等[③]。1872年左右西方音乐被引进日本学校,成立了音乐调查所,制定了学校音乐教育大纲,使西方音乐进一步占领了日本学校,这对本世纪日本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生活都起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的几代受教育者都被培养成了“西方音乐的耳朵”。中国虽然先靠了个人的努力,但政府也给了相当的支持,例如蔡元培的办学。五四以后新创办的师范学校音乐科和音乐专科学校,基本上都以学习西洋音乐为主,至今,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仍以西洋音乐教育为范式,以西洋音乐为基础。
从中日两国的音乐创作情况看,由于作曲者绝大多数都学了西洋音乐,并且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音乐作曲法从事创作,因此无论是中国的“新音乐”还是日本的“新日本音乐”或“新邦乐”,大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西洋音乐风格的色彩,尤其是那些采用了西洋乐器、西洋音乐体裁、西洋音乐语言的作品,如交响曲、交响组曲、交响诗、协奏曲、序曲、西洋乐器的室内乐、清唱剧,某些歌剧、合唱、艺术歌曲等等。在具体做法上,中日两国作曲家都从两个方向着手进行创作。一个方向是将传统本土音乐向西洋音乐靠拢,例如新日本风格的筝曲、中国新音乐的二胡曲等等。另一个方向是将传入的西洋音乐往本土靠拢,例如将本土音乐改编为用西洋乐器演奏的乐曲。所不同的是,在创作观念上,日本作曲家似乎不象中国作曲家那样受到社会政治或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跟两国的历史国情不同有直接关系。
在音乐理论、音乐思想上,中日两国音乐当事人都曾认为西方音乐高明,而本土音乐不足。正因如此,才主动向西方学习。中国音乐家们的思想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以西洋音乐作为发展新音乐的参照。主张全面学习西洋音乐的人自不必说,那些以改进国乐为立场的人们,也一致认为要以西洋音乐为参照来改进国乐,在整个思想观念上还是认为西洋音乐比本土音乐更为“科学”。持这种观点最典型、影响最大的是王光祈和刘天华。王光祈认为要改进国乐,应“先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方面辛勤采集民间的流行谣乐,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的方法把它制成一种国乐,……”(《欧洲音乐进化论》之《著书人的最后目的》)王光祈的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典型意义:从今天中国大多数作曲家的创作行为看,依然多采取这种“以我之材料,以彼之方法”来制乐的做法。刘天华则于1927年6月在《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中发表了《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提倡“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他的这一思想跟王光祈的观点非常一致。此外,作曲家黄自提出新音乐应走“国民乐派的道路”,赵元任提出音乐创作除了共性之外,还应有“国性”。联系他们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核心实际上跟王光祈和刘天华是一致的。这些思想又在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中得到创造性再现。所谓“创造”,是指毛泽东的方针在本质上具有深刻的政治实践性,它远超过了“国乐改进”本身的意义和音乐家们对改进国乐的目的的认识。而19世纪70、80年代开始的日本音乐家按照西方风格来改造传统音乐的种种努力,包括按照西方音乐学的样板对日本音乐的基础和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同样说明了认为西洋音乐具有优越性、先进性的思想的存在。
在当时的社会音乐生活方面,中日两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西洋音乐成为时尚,模仿西洋风格的音乐也成为时尚。中国人用国语唱西洋歌,就象日本人用日语唱西洋歌一样,尤其是学校里的学生。在中国,还有黎锦晖等人模仿西洋流行音乐写的歌曲、乐曲或电影音乐,日本亦有类似的情况。
在对待传统音乐方面,中日两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音乐家在时兴的西洋音乐大量传入的情况下提出改进国乐的主张,而所谓改进,多半是向西洋音乐靠拢。日本不一样。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最初几十年间曾因社会整体文化上倾向于西方文化而在音乐上做得过头些,“但是人们总算没有不加思索地用新事物去代替旧事物,而只是把新事物并列在旧事物的旁边。”[④]例如能乐,无论是否受到人们的欢迎,其表演形式几乎毫无变化;在19世纪唯一的改革只是出现固定的能乐剧场。而从1848年至1853年在大阪形成的新风格“新叶狂言”以及1870年能乐乐师吉吉左卫门、长歌的三味线演奏家杵屋滕三郎和能乐派观世宗的鼓手共同创造的“东能狂言”,也只限于本土音乐的结合[⑤]。再如宗教音乐如佛教音乐“声明”、神道教音乐“里神乐”等,无论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几乎都保持着原样。“19世纪时,里神乐的舞蹈和歌曲得到了培植和保护。没有证据说明它们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很少有变化的可能,因为明治维新日本的对外开放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并没有触及宗教音乐,特别是神道教音乐。”[⑥]中国清末曾有过戏曲改良运动,以胡适、钱玄同为首引起“旧剧改革”争论。多数人对传统戏曲持否定态度,极端者甚至视之为封建“国粹”,而保守者相对少得多[⑦]。但在实际行动上,当时传统戏曲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革,中国戏曲引进西方音乐因素主要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例如西洋管弦乐并入传统乐队的京剧“样板戏”和其他剧种。只有个别戏曲如粤剧,则早在20年代就在音乐上加入了小提琴等西洋乐器。[⑧]
在民间音乐或民众音乐方面,中日两国的情况亦有所不同。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中叶就有所谓“新民歌”即革命民歌或工农革命歌曲。它们有的是用传统曲调填上新词,有的则是革命音乐家的新创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创作的革命歌曲中,有些是采用或接近西洋音乐风格的。最典型的是聂耳创作的、现在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崇尚西洋音乐,而轻视传统民间音乐,基本上是随它自然生灭,直到20世纪才开始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尤其是下半叶。[⑨]
二、对待历史的态度——反思与反拨
今天,中日两国无论在音乐观念、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教育或在现实音乐生活诸方面,到处都可看见西方音乐文化的明显印迹。从西方音乐输入并站住脚跟开始,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中日两国对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是不断进行着反思的,在行为上也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和反拨。这些反思与反拨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深入。一般规律是,西洋音乐初入的二三十年,主要是吸收、接受的阶段,人们在态度上更多地是向西洋音乐倾斜,随后,热潮略退,人们能较理智地看待问题,便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过火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初步的反思与反拨,在对西方音乐文化输入进行思考的同时,往往牵涉到对传统音乐文化继承和发展诸问题,这便出现了处理东、西音乐文化关系的需要。耐人寻味的是,人们虽然很早就反省自己,警觉于西洋音乐文化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覆盖,并且一直有复兴本土音乐文化的呼吁,但西洋音乐仍然在中日两国扎下了根并且开花结籽直至今天,而本土音乐虽然未因此被替代被灭绝,相反,有的还有很大的发展,可是整体上仍处于需要扶植的境地。
1973年前后,日本文部省组织调查普通音乐教育情况,并制定指导计划和共通教材,以及编写学校音乐指导资料。从中学音乐指导资料第1集《日本音乐指导》中可以看出日本有代表性的对西洋音乐输入本土之后的历史和现状所进行的反思和反拨。
其一,明确指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传统音乐受到当时全社会物心两方面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洋音乐输入的影响,同时对受到此影响而促使传统音乐追求新变化和发展的“整体倾向”予以肯定。
其二,明确指出音乐生活、尤其是音乐教育的现状的偏差与不足。也即在西洋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对比上,前者大大超重而后者过于萎缩。主要表现有两大方面:一是社会音乐生活方面,“国民的大多数都可以说是生活在西洋音乐的环境中”,人们接触的西洋音乐远比接触传统音乐多得多。二是学校音乐教育方面,在以西洋音乐为主体的音乐教育中,以音乐理论为首,全部以西洋音乐为尺度来考虑问题,结果在不少场合造成了所谓离开它就是在艺术上低劣的错觉。不仅学生如此,教师亦然。“现在教育工作者的大部分,对传统音乐没有接受过教育,因而,其中甚至有对传统音乐感到不能接受的人。”
其三,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欧洲中心主义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生了根:“问题不在教材的多寡,而在于把西洋音乐看作是音乐的全部这种对音乐的片面看法。”同时,也指出了改变现状的困难之处:“由于把西洋音乐吸收于教育经历了百年岁月,它所形成的对音乐的看法不能急速地改变。”对现代学生而言,他们接触西洋音乐已习以为常,在课堂听本土音乐的共通教材反而难以接受。
其四,阐述将传统音乐引入学校教育的意义重大。第一,它关系到音乐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传承;第二,它对培养学生广博丰富的音乐感觉性是必不可少的。
其五,明确指出改变现状应该采取的立场,即否定将欧洲音乐作为音乐价值标准,“采取承认各国家、各民族以及各时代的音乐的存在价值、认识各自的音乐特质的立场。”也就是站在世界音乐的立场,而把欧洲音乐仅仅看作各种音乐之一种。
其六,提出将传统音乐引进学样教育的目标和具体方法。目标即面向未来,努力培养能够理解东、西、古、今多样的灵敏耳朵和幅度广阔的音乐观。所提出的方法贯穿着目标所包含的精神,例如“不能在与西洋音乐的比较中来听”,也即不能按照西洋音乐的尺度来听;“提高对乡土音乐的认识”,“对现代日本的音乐也应积极地接触”,还要“让学生理解世界的民族音乐”,等等。
从上述“指导”的中心思想中可以看出日本对西洋音乐的地位、西洋音乐的影响及其后果有很深刻的认识,对改变现状中不合理的部分,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日本文部省把眼光放在全球和未来,并且动用行政等各方面的力量从教育入手打开通往未来的大门,这是很有远见、胸怀很宽广的策略。
中国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在争论中西关系问题。到了世纪末的今天,再度掀起了对中西关系问题讨论的热潮。如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行的《中国音乐年鉴》笔会,就以“音乐的中西关系”为主题,召集了许多理论家进行了专门讨论。与此同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连续五年举办了专门的跨地区学术研讨会,其中最主要的专题就是音乐的中西关系。在中国,不仅音乐理论家关心这些问题,作曲家也经常讨论这一话题,因为跟他们创作上的选择密切相关。例如1990年举行的“京、闽音乐创作研讨会”,1992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交响音乐创作研讨会”,1993年举行的第一届“京、沪、闽音乐创作研讨会”,以及1995年举行的第二届“京、沪、闽音乐创作研讨会”等等,作曲家们曾就与创作有关的中西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生动的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西洋音乐创作技法,如何解决采用西洋作曲技法与体现作品的民族风格和传统精神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新音乐如何走向世界和未来。
概括中国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于本世纪末关于音乐的中西关系问题的讨论见解,主要有下列几种:其一,坚持走东、西结合的道路,也就是沿袭王光祈等人在世纪初所提倡的用本国传统音乐教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创作国乐,并将此思想贯穿在理论与教材之中。其二,对现行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等领域产生的“西化”结果加以否定,提出恢复传统音乐原貌,并以此为起点重新发展。不少人正在为建立“中国音乐体系”而努力。其三,否定中、西或东方、西方的分界,指出现代文明进化结果已使地球变小,全球文化交流已使各种界限模糊,提出以“地球村的公民”为身份来进行思维和行动。其四,从音乐文化生态需要各种不同的音乐这一元理论出发,赞同“音乐多元化”思想,并提出建立“音乐生态学”、“音乐品种学”、“音乐文化地理学”、“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哲学人本学”等思想或学科体系,否定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否定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实践上,中国当代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生活诸方面也都出现了上述各种思想观点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结果。从总体上看,虽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反对音乐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都支持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都积极思考未来的出路,然而还没有象日本文部省所做的那样具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纲领、统一行政指挥等等的系统举措。中国音乐文化正处于多方位选择的关口。目前,又加上市场经济浪潮、商品文化包括流行音乐这些与西方经济、文化有着直接和间接关连的事物的冲击,使对东、西方音乐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变得更为复杂起来。
三、走向未来的策略——选择与超越
以未来作为背景,回过头来看待音乐的东、西方关系,人们将看到什么呢?地球的东方和西方,精神的东方和西方,不就是大宇宙的地平线上的两棵并排站立的小树吗?人类未来的家园需要一大片文化森林,而不是两棵小树,更不是两棵小树中的某一棵。
因此,人们不能不这样看待西洋音乐、中国音乐、日本音乐或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那只是很多音乐文化原型之中的一个原型。同样,人们不能不这样来看待象中国和日本历史所发生的、由于西洋音乐的输入和影响而产生的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音乐”——那只是两个不同原型媾合而生成的杂交型。
其实,人们早就可以这样来看待不同时期的西方音乐或东方音乐——在各自的物种中,后一时期的音乐样式不过是前一时期的音乐样式的变型。其实,对每一音乐种类的最初原型的追踪是困难的;但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选择某一时期某一较完备的音乐样式作为该种类的原型,而把它在自身约定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当作它的原型的变型。
人们同样可以这样来看待“十二音体系”、“音色旋律”、“观念音乐”、“太空音乐”、当代的“原始音乐”等等这些至少在某些“维度”与传统音乐原型及其变型存在断裂的所谓“创新”、“新潮”或“先锋”音乐——那都是一些新的品种的新原型。
这样,我们就至少有了音乐文化的四个品种:原型、变型、杂交型、新型。
为了造就未来丰富多姿的音乐文化生态,我们应着手做的工作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其一,收集、整理并保护所有的传统音乐原型,视之为人类共有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这些原型彼此间是等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其二,让各原型在各自的进化轨道上充分发展演化,以得到各种丰富的变型。其三,各原型之间、非近亲的各变型之间、非近亲的原型与非近亲的各型之间均可杂交、再杂交、多重杂交。对中国或日本来说,西洋音乐绝不是唯一可以跟本土音乐杂交的品种;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可供杂交选择的音乐品种。其四,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尽管如此,人类仍然要竭力突破自己的本质局限去实现更高的超越。要充分利用人自己的巨大潜力创造更多的全新的音乐种类,以充实未来的文化生态。
历史河流的动势造成强大的惯性,人类的思维定势亦具有强大的惯性,社会文化习俗同样具有强大的惯性。——这便是历史的因果律之一个侧面。然而,错误的惯性将把人类引向贫乏的沙漠,因此,有时候人们必须逆水行舟,为弥补自己的过失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愿不要经常地为无可挽回的过失付出代价)!比如对于人为造成的音乐品种的减少,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从历史因果律上讲,西洋音乐输入中国和日本并产生许多直接和间接的结果,这是过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的评价,对东、西方音乐媾合进行的评价,应该纳入上述音乐文化杂交的范畴。显然,杂交不是唯一的道路;西洋音乐不是唯一可交之品种;以西洋音乐取代传统音乐,或杜绝与西洋音乐的结合,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
就当前而言,日本已走在中国前面进行了拓广眼界、妥善处理东、西方音乐文化关系的工作,正如日本比中国更早引入西洋音乐一样。仅从上述1973年日本文部省所做的工作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开放的局面愈来愈稳定,这给拓广眼界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音乐家正在从事世界音乐的研究和介绍,以期突破原有的“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洋艺术音乐”的狭窄眼界。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世界音乐”将在所有人的眼界中定位;个别国家、地区、民族、时代的音乐都将被看作“世界音乐”的一部分,而不再会出现一叶蔽目的现象。
注释:
① 参见宋瑾《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思想的四大死结——音乐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的反思与求解》,载《比较音乐研究》1994年第4期、1995年第3期。
②③钟永明、曾清祥主编《世界近代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36页。
④⑤⑥⑨F·博泽(Fritz Bose,1906-1975)《十九世纪的日本音乐》,见罗伯特·亨特编之《十世纪的东方音乐文化》一书,金经言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5月版,第157、162、163、175、179页。
⑦⑧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9、40、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