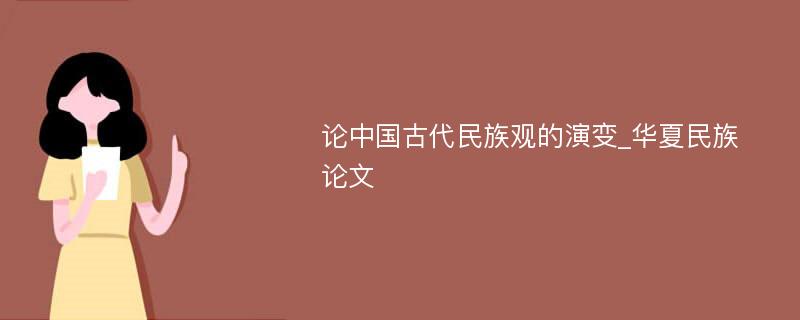
论我国古代民族观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民族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境内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而且随着自身的繁衍和与其他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在人数上也越来越占绝对多数的汉族(最初为华夏族)居于中原地区,而其他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而人数也较少的众多少数民族则散居四周。这种地理分布格局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且不断明朗化。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的这种特点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先决条件,就中国古代民族观而言,其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夷夏观。而夷夏观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则是中国古代夷夏观形成并长期延续的更深层的原因。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夷夏观就开始逐渐形成。自其形成并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演变,夷夏观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对立的方面:〈1〉夷夏对立。其最典型的观点则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天隔的思想。〈2〉夷夏一体或华夷一家。这两种对立的夷夏观或夷夏观中对立的两个方面,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乃至整部中国史的演进过程中,孰强孰弱皆视具体的政治环境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而定,表现出一定的反复性。但就整个发展的趋势来看,则是“华夷天隔”或夷夏对立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而渐趋淡化。华夷一体或夷夏一家的观念,由于和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吻合及其自身的进步性,则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与前者相反的历程,即由淡而浓,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沉淀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在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向心力和凝聚力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夷夏对立观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早在夏朝建立之前的五帝时代,我国境内已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即以黄河流域的黄帝和炎帝部落构成的华夏民族集团(后来融合周围各族渐形成为汉族);同时还有夷、戎、蛮、狄四大民族集团各居东、西、南、北四方。尽管这种划分不一定十分科学,而且当时的民族集团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大致的划分已表明,当时人们已开始对不同的民族集团间的区别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因当时不同民族集团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不高,因此相互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当时夷夏对立观念极为淡薄,甚至处于浑沌状态。这里的华夏集团即是后来的中国传统“夷夏观”中“夏族”或“华族”的雏形;而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则是后来“夷族”的雏形,至少也在概念上已有了这种区分。这已可以视为夷夏观的萌芽。正是这种模糊的认识,在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之后,经过各民族之间各种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战争等多种形式的交往,这种夷夏之别的观念就显著增强。尤其是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在中原地区建立,它既是以一个国家政权的面目出现,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它以行政、军事、文化等多种形式强化了夷夏间本已存在的相异之处。加之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视野的开阔,对于夷夏之别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武王伐纣之时即利用羌、庸、卢、濮、蜀、髳、微等四方之民(1)。而到了西周时期,西周亡于犬戎,使“天下共主”的西周大惊,这也无疑强化了早已有之的夷夏观。及至西周亡而东周起,统一局面被纷争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所打破,自夏至周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以天子为中心而构成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正是在这种现实纷乱的情况下,夷夏对立观进一步走向强化。《礼记·王制篇》中便有:“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2)我们暂且先不论这种对于民族的划分是否科学,但由上面可以看出,就四夷的衣、食、住、行而言,都是极为原始落后的。而这时所谓的“中国”即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央王朝,则在各方面都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即“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3),以冠带之国而自居。华夏族处于中华文明发源的中心地带,认为自己为天下之中,众国之中,为其以华夏为中心的优越心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华夏族与四夷在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服饰上的巨大差异,使其理所当然地对周边衣皮、穴居而又生食的“四夷”产生歧视,而自己则以“礼义之邦”“冠带之国”自居。此后对于夷狄的歧视之辞则充斥于官家经典。“内诸夏而外夷狄”(4),“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5)“……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6),“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7),甚至产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狭隘的认识。接着“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的夷夏大防的思想和“以夏变夷的”思想也随之产生。所有这些思想言论都反映出夷夏对立的观念在趋于强化。
随着秦汉大统一王朝的建立,不仅继承了上古时期夷夏殊异的民族观,同时又以夷夏间事实上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不断强化着这种民族观。《汉书·匈奴传》赞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威,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及其国。”(8),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北各族大量内迁,中原各族(以汉族为主)惊呼“夷狄乱华”,使“华夷天隔”的观念愈演愈烈,达到极点。进而有江统的《徙戎论》出台和冉魏政权对胡族的大量屠杀。这可以视为夷夏对立的极端表现形式,造成了华夷间不仅是心理上的仇恨与隔阂,而且引起华夷之间的民族仇杀。有的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乱华”及汉族统治者政权的丧失,使其优越感几乎扫地以尽。但事实并非如此:〈1〉汉族统治者向以华夏正统自居,即便在这种纷乱时期,这样的正统观依旧根深蒂固,自然其内心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不变。曹操即认为“夷狄贪而无亲”。认为“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9)曹操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传统“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汉族统治者的典型代表。〈2〉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以“五胡”为主的西北各族大量内迁,由于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冲突,加上各族首领所执行的某些政策失当,民族仇杀、民族歧视与长期积累的民族隔阂都因相互间的直接冲突和互相面对,变得愈加尖锐。
一般来说,动乱时期因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民族意识也随之更加强烈。“五胡乱华”可以说更加强化了汉族统治者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夷夏有别和对立的观念。于是在汉族统治者诬四夷、防夷狄之论盛行之时,江统的《徙戎论》出笼。首先,他对夷夏对立的论述无所不尽其极“夫蛮戎夷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10)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徙戎于其旧土的主张:“四夷乱华,宜杜其萌。”认为“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内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这实际上已明确表明,其徙戎之主要目的在于严华夏之防,使戎不得“猾夏”。进一步指出“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1)大民族主义的优越和自傲溢于言表,而对四夷的歧视甚至敌对情绪袒露无遗。〈3〉就当时内迁的各少数民族的观念而言,夷夏对立的观念也很强烈。他们要么以继承华夏正统自我的标榜,如匈奴人刘元海、前秦氐族政权的苻生、苻坚皆有这样的托辞:“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12)以真命天子自居;要么自知为蛮荒夷地之人,在经济、文化方面都远比自己先进的中原华族面前自愧弗如,“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13),“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14)因此内迁各少数民族大多仰慕中原文化,当时的十六国政权一般都重用汉人,提倡儒学。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夷夏对立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尽量采取与中原华族逐渐接近,进而求得与华族的趋同,以求自身的进步和立足于中原地区。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夷夏对立观的极度强化时期,无论是当时各族的思想观念还是各种史实中都反映出这一点。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各族之间多形式多渠道的相互联系、交往及冲突乃至仇杀,也使传统夷夏观受到强烈冲击。魏晋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及其效仿汉制,提倡儒学的政策,也正是对汉族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外夷狄内诸夏”的夷夏观以事实上的巨大冲击乃至改变。因此,才有了隋唐时期“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的较为进步的民族观的出现。
这一时期夷夏对立观的渐趋强化,除了反映在上述思想言论方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于历代的民族政策方面,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历代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尽管历代具体的民族政策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重于严华夏之防。
夏商周时期,中央王朝处理与四方之民(边疆各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上主要通过“荒服”、“要服”制来维系四夷对中原天子的一定臣属关系。三代相因,无甚大的区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15)这种制度既反映了华夏族和蛮夷戎狄各族的客观存在,也反映了他们与天子间的臣属关系。中央王朝一方面采取“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16)的柔夏伐夷的政策;同时对于四夷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安抚和羁縻政策。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7),“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18)“蛮者,糜也,……縻系之以为政教。”(19)可见,尽管此时已有夷夏之殊的观念,但夷夏之防的民族政策并无明确的系统,表明这时夷夏对立的观念还较为淡薄。
随着秦汉统一大王朝的建立,夷夏之间的内外之分因中央集权及郡县制的确立而在地理概念上有了明确的区分。尽管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最初也是起自戎地,它曾“益国十二,遂霸西戎”,但在与其余六雄逐鹿中原之后,秦最终灭六国,一统天下。对于为患最大的北方劲族——匈奴,一则以武力征服,二则筑长城以拒之。而对于南方诸夷越之族则采取安抚政策。汉因秦制,又有所发展。一方面在行政设置上继承秦制而又进一步明确化,设立了郡县、属国“掌蛮夷降者”。(20)而且两汉还增设了都护、中郎将、校尉等官制,扩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范围。如汉朝的西域都护一职“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21),“屯田校尉,始属都护。”(22)另一方面又针对不同民族地区专设有相应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从而“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23)可见其对各少数民族所推行的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夷夏对立的观念。
这一时期这种观念的逐渐强化还表现在对边疆各少数民族是实行镇压还是招抚政策上。汉代护羌校尉段熲认为羌“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则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根本,不能使殖。”(24),故对羌族进行大规模斩杀政策;同时又有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样做“伤和致灾”,“羌一气所生,何能尽诛,山谷广大,不可空静”(25),应进行招抚。这种争论依旧是围绕如何严华夏之防而展开的。即使从当时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而言,也是取决于汉匈间经济、军事实力之间的对比关系,结为“生舅之国”,而非平等待之。夷夏对立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26)。视匈奴为“天下之足”,故对于向以中原正统自居的汉王朝来说,与匈奴和亲且奉贡物,乃为屈辱之事。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必反其道而行之,令匈奴遣使纳贡,俯首称臣。武帝初年,汉室强而诉诸武力对付匈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击之。”(27)。此番言辞似有标榜之嫌,但由此可见和亲之策不过为权宜之计。武帝之志,“在绝胡貉,擒单于。”(28)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除了西晋王朝的短期统一之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分裂动荡之中。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但其民族政策基本承袭两汉。而西晋对内迁各族最初采取了“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的政策,以“矜来远之名。”(29),或争取兵源和劳动力。但随着西晋政治走向腐败,内迁诸族承受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而西晋统治上层内也为如何对待内迁诸族各抒己见:晋泰始四年(268年),傅玄上疏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盛。本邓艾苟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30),至太康元年平吴后,峻夷夏之防的呼声愈高“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条策也。”(31),乃至江统的《徙戎论》出台,主张将诸族徙回原居地,峻夷夏之防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这种作法在当时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则,自汉魏以来即有许多少数民族内迁,并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促进了各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共同进步,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进步趋势,“徙戎”主张必然会遭到各族人民的共同反对;二则就西晋统治者自身而言,若迁出内徙各族,对它自身的兵源和劳动力的来源也是一大损失。故未采取徙戎主张,而是加强了对诸族的军事控制。置“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案武帝置四中郎将,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增设许多控制少数民族的军事机构。十六国时期,北方诸政权大多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因此其民族政策也都基本延袭前代。其中尤以氐族所建前秦政权为典型。由于前秦统治者自身汉化很深。苻坚积极推行历史上传统的汉族封建理想的治国之道,大力宣扬封建化,并重用汉人王猛为相。这种总的治国之道表现于民族政策上,则实际上也是“内中华而外夷狄”,以“羁縻之道”抚育“荒外”,以夏变夷思想和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而统一北方诸族政权的拓拔鲜卑建立北魏政权,为了适应中原汉族地区的统治需要,其从政权建制到文化、习俗乃至服饰、语言都经历了汉化和封建化,对历代中原王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仍奉行不辍。设置了“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校尉”等。(32)视边外诸族或政权为“荒外之地”,藩属之国,采取羁縻存抚的政策。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汉族建立的统一政权,还是内迁各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推行的民族政策都大多延袭前代中原王朝的政策,而其所体现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夷夏观也渐趋强化。这种重在强调夷夏对立的民族观至隋唐,才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隋唐时期夷夏对立观的淡化
传统夷夏观中夷夏对立的一面在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期间,逐步由模糊走向明朗化并渐趋强化。但这并非意味着传统夷夏观中与此对立的另一面即华夷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不存在。中国包括夷夏在内的各民族经过自先秦以来长时期的交往,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仇杀,也同时经历了空前的交流和融合,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隋唐。而传统夷夏观几经演变,其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民族观中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支配主导地位发生移位,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夷夏对立观逐步被夷夏一统、华夷一体的夷夏观所取代。李唐明主李世明的夷夏观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民族观的变化:“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33),其原因即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34),他还进一步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性与中夏不殊。人主盖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6)。这种视夷狄与华夏为一家,并对其“爱之如一”的夷夏观,有唐一代,一直为唐朝各君主奉行不衰,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夷夏观中夷夏对立观念强化的趋势,并使华夷一统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究其原因,略析如下:
〈1〉自先秦以来,中国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的事实及华夷一统思想的积淀,既是隋唐时期视夷夏为一家的进步民族观的序曲,也为这种夷夏观的最终明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作了准备,这在前面已有论及。
〈2〉以“礼”为区分夷夏的主要根据,也使视夷狄与华夏为一家的夷夏观更容易产生,从而摆脱那种仅以相貌、服饰、种族关系来区分华夷的陋见。春秋时期,区分夷夏的主要标志是语言习俗、礼仪及经济方面的差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但“礼”的标准却高于族类的区别,视其行为是否合乎“礼”,华夏亦可互相易位而称。对此,汉时大儒董仲舒评论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与彝狄而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彝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言而从事。”(38),故“礼”是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即便是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的孔子也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表明,只要行为都合乎“礼”的标准,则可亲近、抚爱之。这种观念也向华夷一统的思想迈进了一步。
〈3〉大统一的思想根深蒂固。历代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尤以一统天下、安定万邦作为其成王的最高理想和标准,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评说历朝君主功绩的主要标准之一。而一统天下、混一六合则成为历代君主平定天下、建立自己政权的最堂皇也最有号召力的旗号,从而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滨,莫非王臣”(39)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大统一的思想亦被迁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效仿、奉行。苻坚就有“非为地不广,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的感慨。这种大统一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华夷一统的观念。而到了隋唐,则被明确化为夷夏一家,且华夷同重的思想。
〈4〉夷夏对立观在隋唐时的淡化,也缘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迁徙和对流的直接冲击。这在前面已有论述。
〈5〉就唐太宗自身而言,提出对夷夏“爱之如一”的开明民族观,除了对历史上进步夷夏观的继承和吸收之外,还因亲历隋亡,善于从中总结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以“仁义”治国的思想,反映到夷夏观上便是对华夷的“爱之如一”了。唐太宗虽未能完全摆脱夷夏对立的观念,他曾说:“中国百姓(指汉族),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42),但与“华夷天隔”的极端宣扬夷夏有别的思想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了。因此其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也因其积极进取和富于开拓性而被历代奉为成功民族政策的典范,而唐太宗也被各族奉为“泱泱中华”的“天可汗”。
隋唐时民族政策的成功,不可否认是得益于前代民族政策的经验且有所创新,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隋唐历代君主基本奉行较为进步的华夷同重的夷夏观。其对于四边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夷夏对立观和峻夷夏之防的观念的淡化。对于“兵少力弱”的突厥突利可汗进行“抚驯”,“以为边捍”。(43)加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朔州筑大利城供他居住,使之感激不尽,故上表云:突厥诸部落“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枯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与大隋典羊马也。”(44),另外,隋朝还继承了和亲、设置郡县等前代曾采用过的民族政策。但其短祚,因此一系列开明和富有成效的民族政策至唐代才出台。
唐朝开国的第二年(619年),高祖李渊即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复。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祗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中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如亲……静乱息民……,布告天下,明知朕意。”,这一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经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明确为胡越一家的民族观。“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46)的开明的民族政策,反映了夷夏对立观念的淡薄。唐代一度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52)、“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贺朝,常数千人。”(53)盛唐的这种繁荣局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夷夏对立观的淡薄。自此以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和汉文化的正统观所反映的夷夏对立,在封建专制下仍表现出一定的反复和强化,但从整个夷夏观的演变趋势来看,则是华夷一统的思想观念渐被重视。
三、宋、元、明、清时期夷夏观的变化
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李唐王朝的繁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唐末五代的分裂动乱,使唐朝形成的大一统局面七零八落,也使一度和睦稳定的民族关系又趋于紧张。一般来说,民族关系紧张之时,常常也是排斥异族的狭隘民族意识强化之时。北宋建立时,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西北部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后来女真族灭辽建立金朝。形成宋、辽、金、夏相并存的局面。作为中央王朝继承者的北宋虽以正统自居,却并未完成一统天下的任务,且北有辽、金的虎视耽耽,加上西夏的威胁,这种多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给宋朝统治者的心理上罩上了紧张的阴影,故夷夏之防自然又会被置于首要位置,隋唐时一度淡化的夷夏对立观又一次被强化。以礼别华夷、视夷狄为“禽兽”的议论一时甚嚣尘上。“圣人先本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内地,夷狄外地。”(54),以“本”与“末”喻“夏”与“夷”,并以此区分内外,讨论如何严夷夏之防。“人统御之策夷夏不同,虽有戎虏之君向外宾服,终侍以外臣之礼,羁縻勿绝而已。或一有背叛,来则备兵,去则勿追,盖异俗殊,方视如犬马,不足以臣礼责之。”(55)。重提“德以柔中国柔,刑以威四夷”的春秋老调。最典型的是石介的《中国论》中的夷夏论。他从宋时官方正统哲学程朱理学出发,论证了内外有别的华夷之辩及纲常伦理关系,是不变的天理与秩序。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并且认为“中天之外,是夷狄之位,长幼卑尊无序。”,若夷夏居地无序,则“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将“国不为中国矣”。故“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谬论反映了宋朝受制于强大的少数民族时狭隘的民族观的强化。但多个民族政权对峙并存的事实,也强烈地冲击着宋朝以正统自居、强调夷夏之别的民族观。认识到“北虏虽有夷狄,然久渐圣化,粗知礼义,故百余年间,谨守明誓,不敢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56),且认为今之契丹与西夏不同于古之夷狄,二者“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立中国家属,行中国法令”,其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骑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故对其“当以中国劲敌待之。”(57),可见在强族并立的现实情况下,宋朝统治集团也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建立元朝的蒙古和建立清朝的满族两大少数民族,本以游牧为业,却凭军事武力强入中原,如强飚狂进,摧毁向以正统自居的汉族政权,先后建立全国性的大一统政权。这种夷夏移位的事实强烈地冲击着夷夏对立的观念。而元、清两朝又皆奉行历代王朝的大一统和封建专制,以中央王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因此这时的“中国”、“中华”、“华夏”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不再是汉族的专有名称了。
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凭武力征服他族。故以武力、征服为尚。作为驰聘蒙古高原的劲族,强大的武力造就其大民族主义的优越心理,以征服他族为其乐事。被蒙古族奉为民族英雄的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58),“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59),而没有中原汉族那一整套自古以来都奉行不辍的伦理、纲常和礼教观念的束缚,在他们的意识里没有传统夷夏对立的观念,只相信武力,所以将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都分等而待,而将本族置于首位。对于中原地区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先进生产方式的汉族,则更是视为仇敌,甚至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60)面对这种局面,向以优越自居的汉族士大夫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和屈辱感,每“遇谈国事,辄悲鸣烦促,涕泪潸然。”(61),而拒降元朝的宋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则备受汉族尊敬。这种情形表明,在蒙古族入据中原,且将汉族纳入自己统治之下时,两种不同民族观的冲突和斗争,更反映出传统夷夏观在这种事实面前的挣扎,以及中原汉族对外族的仇视。即便在元亡之后,汉族士大夫仍对此不能认同:“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62),可见,怨恨之气犹存。另有:“昔之入主者,颇皆用夏贵儒,惟元不然。”(63),还有更严厉的指责:“自古夷狄未能有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至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乌得而不亡?”(64)可见,尽管传统夷夏对立观依旧存在,但以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使“天下为一”,将包括夷夏在内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其“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65)的广大版图之内,以少数民族取代汉族传统的正统地位,加之各族之间的联系、交流的加强以及各民族的融合,这些变化都无不对传统夷夏观予以现实的冲击,也造成了华夷一统共有天下的局面。当然其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给予各族以平等的对待(如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四等级的民族政策),但随着其对汉法的采用及汉人的重用,这种民族压迫政策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出阶级压迫的色彩。
元亡明兴,汉族得以重建自己的政权,恢复了昔日的“正统”地位。夷夏对立观从元朝时潜伏的压抑状态下得以发泄出来,又开始堂而皇之地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显然,朱元璋即从这种夷夏观出发,提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故要“驱除胡虏,恢复中华。”(66),这种观点也为明朝的朝臣所一致认同:“臣闻易之为书也,贵阳(而)贱阴。春秋之法,内中国而外夷狄,盖中国者,阳也,夷狄者,阴也。”(67),这显然是重弹夷夏对立的老调。
但明廷君臣上下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元代民族融合的现实,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前几代汉族帝王相比,要稍稍淡薄一些。太祖申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68),成祖也指出“华夷本一家”,“天之所复,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69),“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70),“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其间于华夷。”(71),成祖主张不分族类任人唯贤,且驳斥了朝臣中严防“夷狄之患”的陋见:“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禅,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正是不知明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固用夷狄之人致败。……近世故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72),由此可见,明朝统治者的夷夏观与传统夷夏观所强调的夷夏对立,已有很大出入了。
清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以前被华夏士大夫称为“夷”的满族创建的清王朝统治区被视当然之“中国”、“中华”、“华夏”族的内涵空前扩大,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称。中华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自古以来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夷夏论的猛烈抨击。雍正帝指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问化者,由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评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73),可见,不分内外,夷夏一家的民族观已上升为支配地位。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而且传统的“夷”的概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非指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成为清代对西方入侵者的代称。西方列强开始对古老的中国虎视耽耽,使包括夷夏各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受到威胁,中华各族为一家的观念在这种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空前强化,而传统夷夏观中所反映的狭隘民族观,在由反映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走向反映整个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淡化,传统的峻夷夏之防变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抵御,而用夏变夷的思想则演变扩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如何学习西洋的船坚炮利,从而有效地抵制他们的入侵。所有这些变化都反映了在整个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和动荡之时,传统夷夏观中两个对立面即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就是夷夏对立观转化为华夷一体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而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化过程。
注释:
(1)《尚书·牧誓》。
(2)《十三经注疏》上册,《礼记·王制篇》。
(3)《尚书·武成》。
(4)《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5)《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
(6)《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7)《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
(8)《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9)《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10)(11)《晋书·江统传》卷56。
(12)《晋书》卷112,苻坚载记。
(13)《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4)《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
(15)《国语·周语上》。
(16)《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17)《礼记·王制篇》。
(1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何休注。
(19)《周礼注疏》卷29,贾公彦疏。
(20)(21)《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22)《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
(23)《后汉书》卷47,《班超传》。
(24)(25)《后汉书》卷65,《段俊传》。
(26)《汉书》卷48,《贾谊传》。
(27)《汉书》卷6,《武帝纪》。
(28)《盐铁论》,《诸子集成》第7册。
(29)《晋书》卷97,《四夷传》。
(30)《晋书》卷47,《傅玄传》。
(31)《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
(32)《魏书》卷113,《官氏志》。
(33)(34)《通鉴》卷198,贞观21年5月。
(35)《通鉴》卷197,贞观18年12月。
(36)《左传》鲁襄公14年(公元前559年)。
(37)《春秋繁露·竹林篇》。
(38)《诗经·小雅·北山》。
(39)同(12)
(40)《贞观政要》卷9。
(41)《隋书》卷51,《长孙晟传》。
(42)《隋书》卷84,《突厥传》。
(43)《册府元龟·帝王部》武德2年。
(44)《贞观政要·征伐》。
(45)《通鉴》卷98。
(46)《国朝诸臣奏议》卷129。
(47)同(54)
(48)同(54),卷142。
(49)同(54),卷135。
(50)《史集》卷1,第2册,第266页。
(51)《元朝秘史》,第225节。
(52)《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53)《宋遗民录》卷2,《谢翱传》。
(54)《草木子》卷3,克谨篇。
(55)《诚意伯文集》卷首,叶式《题诚意伯刘公集》。
(56)《明太祖实录》卷53。
(57)《元史·地理志》
(58)(59)(60)《明太祖实录》卷26,109,53。
(61)(62)(63)(64)《明太宗实录》卷264,126,32,134。
(65)《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第5页。
标签:华夏民族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民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唐朝论文; 汉朝论文; 华夏论文; 华夏集团论文; 中原论文; 周朝论文; 甲骨文论文; 突厥论文; 史记论文; 隋朝论文; 商朝论文; 南宋论文; 辽朝论文; 东周论文; 东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