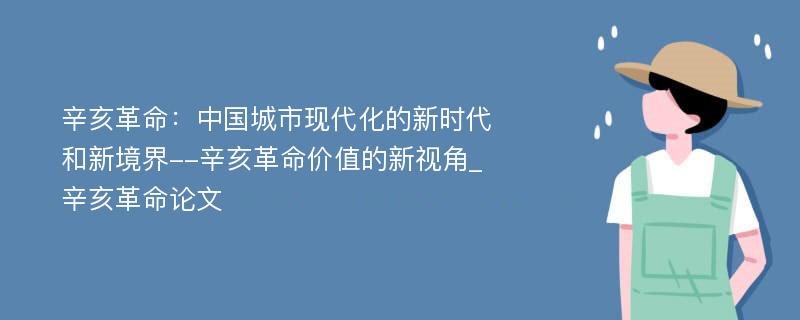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提供一个反观辛亥革命自身价值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提供一个论文,中国论文,新境界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比较注重辛亥革命对农村影响的分析,忽视辛亥革命对城市现代化应有作用的考察,因而对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总体评价就显得不够公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史的成果不断问世,但是很多论著没有从整个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来考察城市,忽视了民主革命、尤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城市现代化的贡献。这样,不仅妨碍了对辛亥革命作出正确全面的评价,同时也制约了现代城市史研究的深入。
本文拟就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影响、持续性影响和在经济、社会整合中的一些规律性影响,以及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城市各利益集团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同、经济和社会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效应等问题,论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变革性推动作用。
一、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直接性影响:革命本身的效应及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城市现代化的目的获求取向
1.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辛亥革命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虽然有的地方改厘金为附加税,但是过境税毕竟取消了,“遇卡抽厘”的现象不复存在。与厘金相比,附加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如浙江省军政府改厘金为统捐,不属于统捐者如生丝、茶叶、酒等设特别捐,两者的税率都较以前为轻。原来运丝80斤需要正附捐税29元,光复后,运丝100斤只收正附捐税20.2元。这样,就降低了工商企业的原料价格及产品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在上海,前清时的所谓落地捐、筹防捐是上海商人“独受之虐政”,所谓捕盗船捐,“捐数较巨,船商苦累不胜,比年以来,曾迭次禀恳裁撤,迄未邀准,怨愤之气,郁积已久”。上海独立后,沪军都督府将上述苛捐通令废除。以上成果,毫无疑义是辛亥革命本身强大变革效应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现代化对于传统体制的首先突破。
2.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整合中,对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的获求。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曾力图保护工商,发展实业,“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页。)南京临时政府还派员参照西方国家城市建设和租界区市政,草拟了规划,其中包括重建新式商店、人行道及明暗排水沟等公共设施和改造街道和市容。武汉当局发布的《示谕维持汉口商市文》,强调重建汉口规划的意义,认为这是“吾国第一次开辟商埠之伟大事业。”稍后又参照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城市设计,综合测量绘图,马路分为4丈、8丈、12丈三类,中央敷设电车道,两旁为马路人行道,左右植树。市区中央设大公园,街侧房屋以三层为限。计划筑路费400万元,建房费2000万元。(注: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但上述武汉重建的思路被后来的地方当局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所参考。
3.南京临时政府在社会整合中,对于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社会改造措施的获求。在辛亥革命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它既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的弊端,使人民能够从现代化、城市化中受益,故南京临时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的改造。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临时政府通令“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实行司法改革。为赋予人民政治权利,临时政府宣布“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律享有,毋稍歧异。”临时政府还通饬外交部、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出口。(注: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7、29页。)这些都体现了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原则,是对人民的一次政治解放,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热情,广大商人们充满了实业救国的豪情,珍惜革命运动带来的新机遇,树立起开放思想和竞争意识。一时间,各种实业团体在各大中城市中涌现,主要有: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工商勇进党、民生团、经济协会、西北实业协会、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等。它们一般以大办实业、开展竞争、挽回利权、建设城市为宗旨,其倡导人或发起人多为有实绩的资本家和有实业知识的知识分子,有些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几乎天天都有新的企业和公司注册,在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一股经商办企业的热潮。
总的说来,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在总体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开拓了道路,其政策措施有利于城市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以后北洋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和城市现代化政策产生了某种示范效应和持续性影响。
二、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持续性影响:北洋政府这一现代共和政体对于城市现代化的回应
研究民国初年的城市现代化,就不可能绕过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民国初年兴办实业、建设城市的热潮,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权在政治上反动,但是为了强大其统治,它不可能完全不考虑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3页。)北洋政权政治上的职能表现为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镇压,以保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它的社会职能就是组织恢复发展经济,同时又因为城市现代化是历史发展潮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而它就得注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如不认真履行其恢复发展生产的社会职能,便不能有效地执行其统治压迫人民的政治职能。
1.北洋政府实行了部分有利于城市现代化的经济政策。北洋政府成立后,实行保护和奖励城镇工商业的政策。1913年7月,袁世凯发布修订保护实业的经济法规的命令,声称:“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以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倡导。”他一面责成农林部、工商部迅速将各种应该修订的法律分别拟定草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颁布施行;一面希望拥有资金者特别是华侨商人踊跃投资,“尤望我流寓异地之素封,共念国计艰难,民生困蹙,投资兴利,相率言归。”(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1912年12月,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的首先发明和改良者,废除了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在各业、各地自由设厂的条件。(注:黄逸平、虞宝棠:《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为了扶持国内贫弱的工商业,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创设公司,北洋政府1914年1月制定和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政府拨出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年以其利息借助有关公司,作为公司的股本而保其利息。棉织业、毛织业、制铁业为甲种公司,按实收资本金额的6厘而保息;制丝业、制茶业、制糖业按实收资本的5厘而保息。归还保息金的期限也比较宽松,凡被保息的公司,自领到第一次保息金后第六年起,每年按所领保息金总额1/24摊还。政府不得随意向被保息公司摊派,被保息公司非实有赢余时,不得于保息定率外分派官利。(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页。)为了鼓励手工艺品的生产和贸易,以利出口创汇,1915年2月规定,凡销往外国的草帽辫、地席,减半征收出口税,通花绸布、通花夏布、发织髻网,以及蜜汁、果品等,“无论运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征各节。”(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由于北洋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页。)成为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增长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这一发展比率超过了1949年以前旧中国的任何时期。就1912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而言,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5%,即使将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抗日战争时期排除在外,那么1912年至1936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9.2%。(注:参见张约翰《前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一种定量分析》(John K.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再如,棉纺织业这个民族工业的先行部门的增长率也表现得尤为显著。1913年间,民族资本中锭子和织机仅分别为484192枚和216台,到了1920年间,锭子和织机分别增长达842894枚和4310台之多。(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4页。)
2.北洋政府顺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北洋政府不仅鼓励保护私人资本企业,而且还利用政府的力量,创办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和股份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创办“华兴纺织公司”,创办资本为1600万元,官股1/4,商股3/4,总厂设在天津,分厂设在德州、石家庄等城市,“以新法从事纺织”,计划成为华北最大的纺织公司。同时间里,周学熙还创办“通惠实业公司”,以“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总公司设在北京,分公司设在上海、广州、汉口。该公司的显著特点是将中国从南到北几个最大的城市进一步联结起来。(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3页。)1913年在陕西西安成立了“陕西制革厂”。该厂的建立,还带动了陕北、关中的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现代牧场公司。(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8页。)这类工厂的设立对西北传统城市迈上现代化的轨道具有积极作用。
北洋政府1912年设立湖南第一纺纱厂,该厂逐渐发展,至1920年成为现代化的工厂,厂址位于长沙湘江西岸银盆岭,厂基面积200余亩,厂房占地60余亩,机器、厂房和其他不动产价值约310万元,流动资本35万元,纱锭5万,织机248台,全年棉纱34000件(每件420磅),棉布2800件(每件20匹计42码)。所产纱、布运销湖南各县及江西、贵州、四川等省。这类工厂对于华中地区中等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尤大。
北洋政府不仅兴办现代化公司,还对前清的一些企业进行改造,更新设备,扩大投资,增加技术含量。这类企业有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所、广州机器局、武汉纱、布、丝、麻四局、汉冶萍公司等。如江南造船所在前清时,“范围狭窄,机器制造力亦薄弱”,民国之后,新购各种机床76部,新建合拢厂、压气厂、造船铁工厂及木模厂,扩充了原有的打铁厂、打铜厂、铸铁厂及造船机器厂。
3.新体制构建为城市现代化带来的活力。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注: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6页。)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10年后的20年代,新体制带来的活力,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开足了马力驰骋于市场经济广阔天地,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注: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民国初年城市现代化发展确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1914年至1919年的世界大战使欧美各国家忙于欧洲战争,无暇顾及其在东方的利益,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剥夺,放松了对中国工商业的排挤,使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获得一个好的机会。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以面粉业的发展为例,“昔日所产之面粉品质不良,仅能供本地之消费,毫无输出之价值,故恒输入超过。”世界大战爆发后,“不惟可供国内之消费,且能行销外国,反由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则面粉业之方兴未艾,竿头日上。”世界大战前,全国面粉厂只有38家,到世界大战爆发后,增加到133家,战前日生产面粉4000袋,大战爆发后日生产面粉12000袋。(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应该说,民国初年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是辛亥革命开辟现代化的前景,是北洋政府履行社会职责以及世界大战使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一个总的合力”所促成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形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78页。)面粉业的大发展,因国际市场的需要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热情、机器的使用、生产技术的改进,面粉业的大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从前的面粉业是小规模生产,应用人畜之力,辛亥革命后,面粉业开始使用机器,磨面的技术大为改进,面粉的质量大为提高,不久又赶上了世界大战,面粉业才得以大发展。(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三、辛亥革命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整合中城市现代化的规律性影响:城市、人口、城市化率、城市精英、社会阶层等的嬗变
1.工业城市普遍崛起,城市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现代城市是因商而兴起、因商而发展的,城市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城市商业革命。其缺陷是商业畸型繁荣,工业不发达。辛亥革命前,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这种缺陷在民国初年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所改变,城市中现代工厂大量出现。城市现代化不仅表现为商业的繁荣,而且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盛。如上海,“各类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开设起来,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本省的水路运输费用最便宜。可以说,哪里有宽阔的通往江河的水道,哪里就会有工厂。”(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一批现代工业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等迅速崛起,使中国城市现代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1912年以来,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且可以与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全国的新式工业集中于上海,大规模的工厂不下250家,资本总额达3亿元,产业工人达30万人。
江苏的无锡,民国以来,新式工业突飞猛进。该市纱厂1916年时不过2家,纱锭43832枚,到1928年增至6家,纱锭达150800枚。无锡还是面粉工业中心,1921年有面粉厂6家,资本共200万元,每年可出面粉700包,有丝厂5家,置缫丝机282台。另外,无锡还有水泥工业及其它轻工业。
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十分迅速,1922年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棉纺织业中心。另外,武汉的面粉工业,历史虽短,但在民国初年颇有发展。还有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公司,均为中国规模甚大的重工业企业。
山东济南亦为中国工业大城市之一。济南工业的发达,完全为民国初年的事情。济南的新式工业门类较多,有纺织、面粉、造纸、火柴、皮革、肥皂、制糖、水泥等,其中以面粉工业为最发达,在1924年共有面粉厂10家,资本达590万元。
天津为中国北方的大工业城市和大商埠,是东北货物的集散地,其进出口贸易,与武汉相伯仲,占全国第二或第三位。纱厂在1916年仅有1家,纱锭1920枚,其后增至6家,纱锭增至226808枚。天津工业的发达,与济南、无锡相仿,亦为民国年间的事,自1917年至1925年,新设的工厂达41家。(注: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455页。)
哈尔滨为中国东北的第一工业大城市,各类工厂无不具备,尤以面粉、榨油、酿酒、毛纺、制材等行业最为著名。成发祥面粉厂、东兴火磨面粉厂、安裕面粉公司,资本都在20万元以上。裕庆德毛织工厂资本多达65万元。中东制材公司资本50万日元。(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369、415页。)
根据北洋政府统计,在722家(包括外国资本、中外合资)较大规模的工厂中,上海、无锡、武汉、天津、济南、哈尔滨有347家,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此外,工业较集中的城市有青岛、北京、南通、广州、长沙、奉天、重庆、成都等。(注:《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421页。)
至民国初期的1919年,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超特大城市已有上海(240万人)、广州(160万人);100万以下5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有天津(90万人)、北京(85万人)、杭州(65万人)、福州(62.5万人)、苏州(60万人)、重庆(52.5万人)、香港(52.5万人)、成都(50万人);50万以下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汉口、南京、济南、扬州、武昌、汉阳、长沙、哈尔滨、无锡等60个。(注:《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内部稿)。)
2.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率急剧提升。由于辛亥革命使得旧的体制解体,经济奇迹为城市化提供了难以阻挡的新的推动力。伴随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工业中心城市普遍崛起,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从而引起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率。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特别恶化,而是贫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他们部分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个差事,部分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获取都市居民的特权以接受新式教育。这些都反映了发展中的城市对农业社会的吸引力。城市范围扩大了,城郊形成了。为了促成新城区与老城核心区之间的联系,旧城墙也被拆除了。
内地的城市化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如山东济南,1914年至1919年市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2页。)天津城市人口在1920年时为320000人,但至1921年却为837000人,一年内增长了2.6倍。沿海大城市的扩展,主要是大量移民持续涌入的结果,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业人口。青岛城市人口在1911年为54459人,到1921年人口已聚至837000人,10年中增长了53%。
城市人口的年增长在上海最为明显。若将各个区的人口加在一起计算,那么它在1910年有约130万人口,至1927年则翻了一番,达到260万。(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21页。)其中移民占了72~83%。(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上海行政区内的商业区和工业区也在扩大,它北向闸北发展,东越过黄浦江向浦东扩展,南穿过古城墙向南市发展。外国租界区的人口大为增加,在法租界,1910年估计有居民11.5946万人,1925年则达到29.7072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9076万人。公共租界占地面积约为法租界的2倍(约22.6平方公里),但人口也显得更多:1910年有居民50.1541万人,至1925年达到84.0226万人,人口密度自然也远远地超过了法租界,它在1910年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191万人,而到1925年则达到3.7178万人。(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15页。)
人口的激增导致了地价的猛涨,而且后者常常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公共租界,1911年每亩土地为8281两,但25年后竞达到每亩1.6207万两。在主要的商业区,地价以十倍的速度猛涨。例如公共租界中心区域(中区)南京路和四川路的交叉路口,1929年每亩达到35万两,但在1915年的要价仅3万两。比较起来,公共租界北区和西区也保持着相应的上涨比率。在河南北路,每亩价格从1921年的1500两上涨到1929年的1万两,而在静安寺路则从3千两涨到2.5万两。(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季刊,1932年第4期,第16页。)
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在1910至1925年颁发过8.1903万件建筑许可证,这与前此15年的情况相比,显然增加了47.2%。(注:《理查德·菲瑟姆的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Richard Feetham,Report of thd Hon Richard Feetham: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字林报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1931年,共2卷,第1卷,第347页。)新建的建筑大多是居民住房,但工业用房也大为增加。据估计,在1910年至1925年期间,整个上海兴建了大小工厂816家,而在前此15年中,仅创办了77家。新建的建筑以商业大厦最为雄伟壮观。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商业大厦于1919年在上海开业。大约在同一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新建大楼也告竣工,它矗立在著名的外滩林荫大道上,位于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现代化建筑的旁边。
市区向外扩展,城郊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沟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注:《费唐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两卷,1,第347页。转引自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3~844页。)
重要通商口岸的多重结构(既有华界,又有外国租界)导致该城市各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存在。但在辛亥革命后,华界人口的发展,即人口净增长率要比公共租界高。1910年至1927年间,上海城市总人口由1910年的1289353人,增长至1927年的2641220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04.8%,其中华界由1910年的671866人,增长至1503922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23.8%;公共租界则由201541人,增长至840226人,人口增长率高达67.5%;法租界则由115946人,增长至297072人,人口增长率最高达156.2%。(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据1925年的数据)
3.城市新精英队伍出现及各社会集团的分化重组。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相互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的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
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城市精英们的权力增长了,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注: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7、846页。)城市精英的发展加重了其与士绅的分裂,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
随着城市精英队伍的扩大,他们在地方性议会中的席位逐渐居于优势,并取支配地位。辛亥革命后,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有穆湘姅(穆藕初)、陈光甫、江顺德、丁文江、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聂云台等。此外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一同时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由于绅士阶级的衰落,资产阶级成为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些城市精英无疑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产物,是“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旧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
结论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国,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亦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为其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路径。辛亥革命排除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障碍,仅就这一点而言,就是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就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建设性作用不只是体现在城市化的理论构思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革命之后(民国初年)的城市现代化发展上。上述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无疑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极具革命性的巨变,其功不可没。任何贬低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功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然而在着重强调其正面效应的同时,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的这一贡献表现是不平衡的。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和市民阶级,因此这场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相反,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费氏的确看到了一个辛亥革命后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在中国这片小生产的汪洋之中,资产阶级已难以担当大任,真正能够实践这条道路的只能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