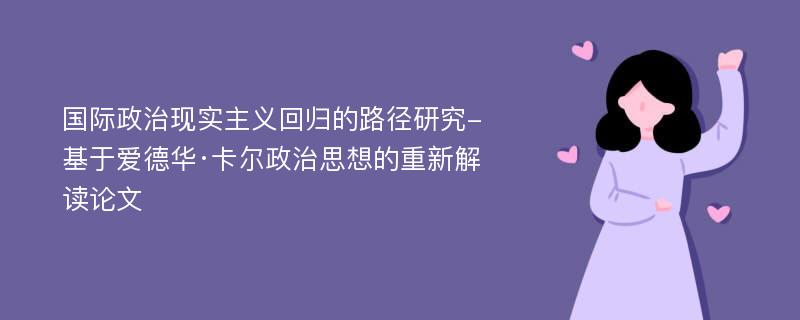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回归的路径研究
——基于爱德华·卡尔政治思想的重新解读
赵明晨
(山东行政学院 政治学教研部, 济南 250014)
摘 要: 爱德华·卡尔思想价值的最大体现是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实现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并为后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对回归路径研究更是集中展示了这一成就和内在逻辑,这个路径和逻辑沿着对国际政治认识论第一性的揭示、对理想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现实原则解构和国际利益、道德单元和权力主体的辩论回归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层理叙述而实现的。其中,爱德华·卡尔围绕理论与实践、愿望与现实、理性与经验这一基本关系,既有对理想主义潮流的哲学基础和政治现实的批判,又有现实主义对道德理性的纠正,同时也有对现实主义自身的自我否定,从而为解决权力匮乏的政治无力和权力政治的道德化这一两难问题作出了基础的论证,也进一步使权力这一核心内容从理论上回归了政治。
关键词: 现实主义; 爱德华·卡尔; 理想主义; 形而上学; 权力回归
一、引言
20世纪上半叶是国际政治,特别是帝国主义行为集中展现的历史时期。爱德华·卡尔(E.H.Carr)(1939:4)作为现实主义旗手,在第一次国际政治理论思潮中使基于理想目标的“小儿阶段”的政治理论——理想主义回归了现实范畴。在爱德华·卡尔之前的时代,理想主义伴随着国际自由贸易和经济古典自由主义而盛极一时,然而它并没有解决自斯威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欧洲国家间战争和世界性战争一直走到了二战。他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而不是理想目标的假定和设计——即是分清了应然与实然之后,批判了一战前后的理想主义国际政治观,认为排除掉权力因素,将和平和利益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是一种乌托邦,他将人们把道德和权力对立起来的三种形式进行了总结:乞望道德控制的不抵抗式和平主义、追求没有政治存在的道德社会式无政府主义,以及坚持世俗社会中政治与道德分离和政治的必要而不道德性。因而,空想的人们无法解决缺少权力的政治无力和恶的权力的道德化这一两难困境。他批判了完全的现实主义和完全的乌托邦主义“典型缺陷”:一个是思想的贫瘠,一个是思想的幼稚,其实质就是前者完全落入到忽视“善的理性”的囹圄,而后者则陷入忽视实践的形而上“目的论”范畴。他认为政治必然包含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也只能存在于理想和现实融合的环境中,因为只有基于政治现实的才是能被实现的。对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主要代表爱德华·卡尔的研究,另一名国际政治大师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2003:71-84),就认为现实主义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取代了乌托邦,而爱德华·卡尔将“是什么”与“应是什么”截然分开,从而理清了纠缠不清的国际政治的“蛛网”,破除了那种将自由理想主义从同质的国内转嫁到异质的国际秩序中的迷信。历史学研究者王黎(2012)对爱德华·卡尔的实然与应然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关系观察后,认为其具有强烈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思想烙印。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Dougherty)(2013:71-72)则将爱德华·卡尔视为“实用主义者”,就是基于对乌托邦主义和极端现实主义的双重批判,从而构建了一个健全的政治理论。对于这种实用主义变现手法,余意(2006)用“三分法”予以表述,秦亚青(2005:28)、李少军(2014:49)分别关注了爱德华·卡尔思想的内容及其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但均未触及现实主义价值转向和理论回归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问题。
二、认识论第一性的辩论
爱德华·卡尔(2005:71)以几乎严苛的态度对现实和愿望进行了界清,“现实主义者的任务是摧毁整个乌托邦主义的不坚实的结构,方法是揭露乌托邦主义赖以立身的理论是空虚而无意义的。”其目的就在于将政治思考和关于政治的生活回归到事实的起点上,而不是基于虚拟的目标上。他以“人生而平等”“和平不可分割”等为对象,例证了这一将愿望的表达作为事实陈述的理想主义“隐性基础”(爱德华·卡尔,2005:14)的荒谬;基于此,爱德华·卡尔进一步理清现实与理论的统一性,批判了古典现实主义将理论仅仅看作是事实派生出来的衍生物这一机械主义“发生论”观点,又批判了理想主义的理论是“目的理性化的结果”的“决定论”观点,从而确定了既要重视“理性化过程”的理论意义,更要重视政治现实的过程与结果这一客观思维。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差别,爱德华·卡尔(2005:15)首先通过分析基于先验思维方式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认为其具有强烈的意识理论性,但他又补充说明了没有建立在“社会民众的态度恰恰是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和实践上的知识阶层的理论创造和政治活动,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国际和国内风险。紧接着,爱德华·卡尔用政府官员的经验引导出经验主义的不足——本身就受到各种具体观点的影响、遵循先例的保守、空洞的形式主义和“现实存在即是正确的”的局限,这种经验与理性结合的不足和某一方面的僵化;在国内最明显的例子在爱德华·卡尔看来就是英国工人运动漠视理论指导而变得进展缓慢、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自动解体;在国际上的例子则是,一战后以威尔逊和塞西尔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将原因归结于控制外交和国际机构的官员的理性的不足。这一点对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民众影响是巨大,一度产生了反对秘密协议运动和和平主义的社会心态,可以说理性不足对政府公信力和国际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20世纪初之所以产生了这么一种基于理论和实践、现实与理性、事实与愿望的争论,甚至在欧洲各国一度划出了知识阶层的左和右的身份界定。根本上来看,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基于自由主义无限市场的利益和谐论的崩溃和强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使得权力国际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国家行为。这种因殖民地带入世界范围内利益的竞争行为与过去欧洲范围内的统一国家形成的领土战争具有巨大的不同,这让军事外交和国际行为过去仅属于政府行为、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知识界并没有长足的理性积累和其被允许公共介入的情形充分暴露了出来,国际层面现实主义政治论述可以说正是在一战之后的国际现实基础上产生的。
三、对理想主义的现实危机解构
爱德华·卡尔对国际政治事务的理解和分析,以及对理想主义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方案的批判是通过对理想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批判来完成的。
(一)理性原则的现实重构和形而上学批判
自然法则从希腊人的内在直觉,发展到了基于17、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给予的推论方法的科学道德法则,理性作为道德法则的来源和途径,也从中世纪神权伦理和政治道德的一体性,走到了文艺复兴后基于个人主义的“良知即理性”。第二次理性重构来源于工业革命后英国生活和思考方式对法国的优势,边沁(Jeremy Bentham)和他的学生穆勒(Mill)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约翰·穆勒,2008:7,34)这一善,并将“幸福道德”当作了它的最终约束力,从而将理性路径建到了“舆论”和“舆论法庭”上,后者更是将“舆论正确”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建立起了“证据+结论=道德上的确定性”和“多数人正确=最大影响”的理性公式。这个理论和公式塑造了19世纪的理性乐观主义,它们的“善的追求=正确推理”“知识传播=多数人的正确推理”“正确推理=正确行动”理想模型试图从理性落到国际政治具体行动上,以期能够自我实现,建立国际政治的“理想国”。在这一点上,民主和平论就认为,不同于君主国家的君主意志的非理性可能,建立在多数民主的多数理性制造出和平,舆论有效的共和体制不会发动战争,普及教育可以塑造和平,因为知识增长可以使得理性感召增强,就会有共同的行动。第三次理性重构来源于美国的繁荣和其在国际政治的参与。由于思想理论者和观察研究者只能从个人理性上进行自我建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多数理性的建设是微不足道的,而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家和他的代理人——元首或首脑的行为实践,真正意义上让理性主义既实现了理论的实践,又检验了理性的效果。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是兼具学术和政治的时代意义的,他首先让一个18世纪以后在英国国内力量结构随自由资本主义变动而决定生成的自由民主思想作为一个先验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早期自动纳入各国发展的“目的论”范畴,而后又大力的倡导他的理想主义。然而他极大地忽视了时代、国别、发展阶段和具体社会需求的差异性,因而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从某种程度某种范围上讲,“用洛克自由主义原则建设国际秩序机制”(Mayer,et al,1939:202)将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去,作为这一理想机制的结果——国际联盟正是这样这一理想国的展示,而一战和二战也正是对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失败的宣告。
北京市快递运输主要集中在街道、小区及各个单位。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快递业务员的服务相对满意,而小区、街道需要提高。反映的问题主要是送货时间不准确、等的时间太久、业务员态度不好等。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况还有:服务热线过“热”,很难打进去,接电话的态度有时候恶劣,对于事故采用回避的处理方式。
国内农业需求冷清;工业方面,环保压力较大,复合肥和胶板企业开工率保持低位,对尿素随用随采,需求较少。出口方面,虽印度展开招标,但国际供给充足,价格下跌,对国内市场难形成利好支撑。供给方面,煤炭、天然气进入供暖需求旺季,价格有所上涨,成本上对尿素价格支撑较强,开工率预计将保持低位或进一步下跌。综上预计,近期尿素价格或将高位持稳,需关注环保形势和冬储进展情况。
从理性——舆论的效果设想看,理想主义者将舆论看成了一个消除权力因素的新的方法。与超国家机构、武力相比,他们更坚信基于各方达成一致的舆论的力量。英国人就认为“知情的民众形成的舆论”是最强大的武器,甚至认同国联达成和实施决策的工具不是武力,而是舆论(Loegaire Humphrey,1987:44),这严重忽视了各国达成协议的进程,将协议或决策看作是一个理论家现成的设计产物,而不是国家权力过程的政治产物。因而,对于一战以后形成的条约和国际联盟,事实上很难因为执行而具有效力,包括1929年《华盛顿协定》也是将保障建立在“道德谴责”上,而不是具体违背集体行动的可操作制裁条款上。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932:5)甚至认为“舆论的制裁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制裁之一”,这一信条让道德谴责和舆论没有产生超越这句话本身的任何意义。最终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没有被谴责和舆论制止,它也同样没有制止德国在欧洲的扩张行动,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只要退出缺少强制性法权义务的国联这一集体行动就跳脱了受到道德制约的囹圄,而威尔逊忽视国联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产物,其基于“全世界普通民众(而不是政客或精英)”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上的“文明人类共同体”在没有物质性力量参与的情况下不过是一个乌托邦。
1.“多数——少数”的隐含基础的批判
和平是有条件的,它并不天然地诞生在无政府的状态之中,泛泛而谈“维护和平是全世界的利益”,这种说话既违背现实,又是一个制造的假命题,具有强烈的迷惑性。和平在现实主义者那里是战争状态的另外一种形式,即“战争不仅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托马斯·霍布斯,2017:95)。也就是说在不确认彼此放弃武力的情况下,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准备状态,因为和平不是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意义就在于获利。在这一点上理想主义者是虚伪的,因为和平可以保证它自身的安全和既得利益地位,战争则改变这种分配的现状。因而和平关系到了切身利益,和平就变成了自身的目标的一部分,并成为利益实现和维持的前提。理想主义者大肆宣言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是共同责任,这种违背和平的武力手段是不道德的。一战即便是战胜国英国的海外利益也开始被动摇了,这对英语世界的舆论以及英语影响世界舆论的和平主义影响是严重的。然而对于德国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法国人,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在二战前多基于国家生存和领土收回而予以价值和功能上的肯定,沙俄也因领土的急速扩张而予以重视的传统。对于和平的本质,爱德华·卡尔(2005:51)就认为“维护和平掩盖了一个事实:有些国家希望不必发动战争就可以维持现状,另外一些国家则希望不必发动战争就可以改变现状”。因而,和平是利益的一部分,那是对于既有利益而言的,在分配不均的世界中,和平不是全部国家的利益所在。和平作为一个现状的维持,在这个现状中既得利益者需要获利时间,而利益损失者或者较少者则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现状,或者认为具有和平途径的希望。因而和平与战争一样,都是一种手段,使用的可能取决于权力的机会、成本和效果,珍惜和维护和平,往往是珍惜和维护谁的和平。
(二)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现实原则解构
政治经济基础的现实原则经历了三次结构,分别建立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上。自亚当·斯密创立自由放任经济之前,欧洲经济结构上是小生产者时代,“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个部分。……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以利润为生”(亚当·斯密,1983:240)的三个阶级和其他依赖于三个阶级的其他群体间分工和分配上利益往往是相对和谐的,即被认为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完全一致、密不可分”的观点。这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在缺乏公共空间的那个时代,人们在无意识的生产和工作中,确实促进了本意中并没有包含的公共目标,即实现超越自我利益的他人利益。这种18世纪利益和谐在后来为道德提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和认知上的先验,甚至出现了“好的经济理论与好的道德之间是一致的;经济上正确的事情,政治上也是正确的”的政治伦理与经济伦理高度同向一致观点(Adams,1980:400)。然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让自然发生的18世纪利益和谐出现了危机。机器设备和资金参与分配,将工人日益变为他们的附庸,无产阶级的出现让“好的经济理论”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效率之外,出现了无产阶级并非出于道德的被动的利他行为。财富分配既成为无产阶级最关系的问题,也成为工业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根本问题,这个关系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它决定了国家之下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道德将成为国家的意志和道德。对18世纪利益和谐论并没有立即崩溃的原因,爱德华·卡尔(2005:45)总结了它延续的三个原因和内涵:“第一,它缓和了生产者之间对市场的竞争,因为新的市场不断出现;第二,它使贫穷阶层从整体财富增长中获得利益,因此延迟了阶级矛盾的爆发,而阶级矛盾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财富的平等分配;第三,它创造了一种对现在和未来幸福生活的感觉意识,鼓励人们相信世界的秩序基于理性的安排,这种安排就是利益的自然和谐。”据此可以看出,可供开发和占领的殖民地市场减缓了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争取了和谐的时间,这种利益和谐显然是建立在殖民地的附属地位和痛苦基础上的,这种不公平是没有被考虑进资产阶级道德理性和西方的“文明人类共同体”之中去的,而作为利益自然和谐的“理性的安排”,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理性安排”,或者资产阶级利益和谐,可见19世纪理想主义是强国间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是深深地根植于对弱国和殖民地世界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完毕,新的市场无限扩大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谐论假设前提的消失,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让国家冲突走向了前台,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统一战争,资本主义国家间和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没有因为基于多数人的理性的自由民主和基于舆论的道德谴责而有减弱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使用了权力因素。在经济缺乏道德性的国家既不能避免内部冲突,也不能阻止外部冲突,好的经济理论不是无条件好的,好的经济理论不是天然的好的道德。
爱德华·卡尔(2005:72)对公共利益理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审视关于公共利益的诸多理论,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是为某种利益服务的,但又有着绝妙的伪装。”根据自由理想主义的利益和谐理论,坚持这个标准的国家,应该将全世界的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这样就使得基于民众个体“具有实体、客观和道德性的普遍政治的生活”(卡尔·洛维特,2006:328)的国家这一共同体处于内部道德相悖的境地。主导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用这一所谓的利益共同体,不过是通过权力分配来维持某种利己的现状。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都展示了主导大国、既得利益与国际和平间的关系。而到了爱德华·卡尔的时代“集体安全”也不全是它们自身宣称的自身安全与整个世界安全和谐利益的表现,而在这个集体之外,这个集体安全仍然是相对于集体之外国家的单方面安全。那种将国家利益最大化等同于世界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过是强权者的道德伪装,威尔逊总统、汤恩比教授、塞西尔勋爵在广义上都将英美利益等同于人类利益,这种解释在英语国家很常见,直到今天,也依然有“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价值观同盟”“安全共同体”等等的声音存在。它们往往是由主导国家或主导国家集团创造出来,然后通过舆论以理性的方式将自私的国家利益装扮成普世利益,这种道德分配和一些国内政治如出一辙。德国的俾斯麦在国家统一进程中生产的国家主义意识则完全不同于理想主义,它首先是利己的,即德国首先是德国人的,而不是首先是世界的。
四、利益、理性单元与权力原则
LOGGWO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计算如下:计算种群中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的时间复杂度为O(N),N为种群规模;个体位置更新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为O(N2+klogn);群体循环迭代的时间复杂度为O(N2),所以,LOGGWO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2)。
(一)公共利益与和平道德的伪命题
1.20世纪利益共同体的片面性
未来企业竞争的焦点就是现代物流技术和物流管理体系,所以“微利模式”下的中国制造业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自己找寻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断的实现经济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2.“目的论”的和平陷阱
作为理性途径的舆论的假设——第一,舆论发挥主导作用;第二,舆论的一贯性——也被现实一一解构了。首先的,舆论的主导作用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舆论无条件正确性,它忽视了舆论的国家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可能,将无差别的善的道德凌驾于国家和人群的区别之上,成为一种抽象的绝对的道德, 如威尔逊就认为,“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淡漠,理性的人类共同目标取代了国家的目标”(Stannard,et al,1927:259)。他希望以理性的民众之声让意大利政府放弃对亚得里亚海岸的主权,结果是谈判的破裂。事实上,基于现实基础的舆论站在相对位置上认识和立场是不同的,更何况民众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国家认同差异,民众的理性之声多大程度上成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是无法被保证的,但这些并不被理想主义者考虑在内。其次,只有共同的知识(认知和立场)才可能的形成共同的舆论。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占领苏台德等东部地区时,英国的媒体一开始是中立和乐见的,几天后在政府干预下,才转向了反对的立场。这种案例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等情况下并不减弱,西方媒体和政府在国别和时间差序上的不一致性都得到了体现,就是不仅是基于各自利益的认知是难以同步的,而且是对这种危害的行为评估和立场表达也是有差别的,因而舆论的一贯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愿望。而“布莱恩(Bryan)条款”将协调替代仲裁,不仅大幅降低了国联的权威,而且,其争端发生12个月内不得诉诸武力而企图让理性回归的“和平时间”,事实上也仍然是各方不放弃武力的“战争状态”。基于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性的假设模型的国际政治,它严重背离了现实,也损害了寄希望于此的弱势国家的利益。
乌格尔耶莫夫表示,第一阶段反应堆测试在核反应堆研究所的MIR反应堆中进行。产供集团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何时在商业机组中进行耐事故燃料测试,可能会在2020年。他还补充到,新西伯利亚化学浓缩厂(NCCP)参加了耐事故燃料研发计划,正在制造将在MIR中接受辐照的先导组件。
胜利油田定向井公司1991年从美国Sperry-Sun公司引进正脉冲定向MWD随钻测量仪器(简称DWD),1999年又从该公司引进了随钻地质评价仪器FEWD成套设备,测量参数包括定向参数、自然伽马、电磁波电阻率、中子孔隙度、地层密度及井下钻具振动量。目前,定向井公司的DWD共有Super slim、350、650和1200四类,其中350、650及1200系统又各有新、旧两种。
(二)国际政治的利益与道德单元
20世纪30年代理想主义的失败,引起了人们对理性缺失的广泛反思,如齐默恩(Zimmern)(1938)认为各国缺少对法律的共同的社会意识,再如汤恩比(Toynbee)将理性不足归结于的自私贪欲怯懦“邪恶说”,那些“心照不宣的预备条款”“假情假意所缔结的条约”,展示了缔约各方有“充分的恶意”去利用“有利的机会”发动未来战争。他们的看法或多或少是对的,但却是不深刻的,他们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无论是人的自私、恐惧抑或者知识不足、理解障碍,是出于社会现实的,如果在设计机制或发挥舆论的理性中,不考虑这种关于人性或认识局限性的客观事实,理想主义始终是一个空中楼阁。
19世纪自由理想主义者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时候,其隐含的假定就是: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这个少数人是谁却不是由舆论的或者是道德决定的,即便是最强国家行列,也没有人会站在道德高地上指定是谁。显然的,这个少数在国内是由生产资料分配和再分配的能力和地位决定的,同样的道理在国际层面,在经济上就是满足资本主义大国的需要,而牺牲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人民福祉,在政治上则是牺牲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地位。然而,谁成为那个不幸福的少数,更不是哪个国家出于超国家的超阶级的自我牺牲的道德的自主自愿的选择。一等强国会要求二等强国全面放开市场,二等强国会要求弱国全面放开市场,但面对一等强国时却采取贸易保护的关税政策,对于弱国而言,片面最惠国待遇就是自身地位的最好解释。因而,建立在牺牲弱国基础上换取国际利益和谐是一个假象,也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是多数国家的政治,还是世界政治,没有弱国参与的国际政治,是一个伪装的多数的概念。正如上述,假定的幸福多数的成员地位,在世界殖民战争中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让人们相信,权力成为国际地位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缺乏权力就无力获得多数的地位,也无法保障自己既有的利益,德国仍然可以在一战后进入国联理事国,靠的并非是英国和法国的怜悯和恩赐,而是德国力量的恢复对国家利益主张的支持和需求;成员国中国的正当利益诉求,却被日本窃取;美国缺席常任理事国席位,更在于对巴黎和会美国领导权地位的不满,这也反映了直到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政治现象仍然表现为欧洲的权力中心问题。
“将创造利益和谐视为政治行动的目标是一种观点,而认为利益自然而然处于和谐状态则是另外一种观点,两者完全不同。”(爱德华·卡尔,2005:50)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在经历两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式微,但创造利益和谐仍然作为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共识和习惯保留了下来,作为一个旁证,二战后国际关系学被广泛当作一个完全的学科被各国固定下来。后起的美国虽然以自身国内市场的开拓潜力,与欧洲相比国际政治和经济事物表现得更加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市场也因其国际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而作为一个目标备受欢迎,这与国内的情况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国内理想是由国际层面所没有的最高权力去保障的或进行的。
2.作为国际道德的单元
自由理想主义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个人之于社会的原理被移植到国家之于世界,爱德华·卡尔(2005:45)指出这种观点特征: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利益,因为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全世界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就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标榜“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不会与整个社会的真正利益和权利发生冲突的”(Green, et al,1986:166)。这个观点是值得批判的。
第一,“国家”认识的局限性。将个人之于社会的关系移植到国家之于世界是一个空想,后者并不存在前者那样的社会状态,即不存在一个必要的最高权力和最高道德,因为只有最高权力和最高道德的存在才是制约个人追求利益不至于过分地使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减损,个人追求自我利益与社会增加整体利益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和社会互为条件的自我辩解。而作为“独立状态”的国家(黑格尔,1979:249)其所处的世界并非是自然的社会状态,而是恰恰相反。而自由理想主义者那里之所以忽视彼时的现实,而泛指国家和世界,或许正如列宁(1984:161)所言“泛泛地谈论国家,即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在理想主义者那里在欧洲和美国之外,还没有哪一个地方被这些欧美政客和理论家当作一真正的国家看待,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有力支持,自由理想主义者那里的社会成员已经明确的变为较强竞争力的国家,就是人类社会和动物有机体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因而“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也必须用进化过程的尺度来加以衡量”(洛伊斯.N.玛格纳,1985:522)。于是,“国家”事实上成为一个强者的特性,而不是一个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属性。在国家间处于自由竞争的自由法则,事实上就是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然状态中,道德是非必要的,如果有那也是强者的道德,爱德华·卡尔(2005:49)就直接指出了“整个道德体系建立在弱者的尸体上”这种情形如同自由理想主义者对待“民族国家”一样,当人们年将道德和理性的单元放在每一个个民族上时候,就有了每一个民族都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是为国际利益的和谐做出贡献的国际主义观点,然而这恰恰是自由贸易的利益和谐论在对政治上的封建国家和帝国领土上的一种延伸,当这一切发生在英国、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那里的时候却有不得不变成了一个衰落的象征。对于此,阿德诺.J.汤恩比在 20世纪20年代时候还在颂扬民族主义是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在40和50年代又指责它是和平普世主义的障碍(肯尼斯·W·汤普林,2003:148)。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江苏省加强工程作业管理,注重管理队伍建设。一是制定合理施工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人员配置,合理分配任务,并明确到位,避免窝工;二是将工作量与工资绩效直接挂钩,落实工程责任制;三是强化质量责任意识,严格奖惩制度;四是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严惩违反生产安全制度造成生产事故的施工队伍;五是加强工地的安全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和执行严格的惩罚制度。
第二,世界利益中的国家利益不是无差别的。国家与世界之所以被认为是利益一致,在自由理想主义者那里,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工业社会后国家内部政治生活日益被阶级间利益分配所主导,仍然停留在基于市场开发的无限性的经济利益和谐论基础上看待国际事务。世界利益的增长,在不同国家那里的具体需求和获益程度千差万别,国际自由贸易不是自动地按照各国需求和均等原则自动实行分配的,它是基于经济和军事权力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一个权力分配过程和现状。如1891年俄国驻华代表代办发给俄国政府的电报就指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竭尽全力签署一个经济条约也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这样做,我们自己从中却无利可图,反而成全了其他外国人(例如,1891年签订的商业条约中包含了大量的利益,但实际上我们却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迄今为止所实施的政策,亦即获取领土”(爱德华·卡尔,2005:119)。到19世纪30年代危机,没有哪一个曾宣称自由贸易的国家不征收一般性关税,甚至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已经被赋予自治权的英国的殖民地海外领地,也开始使用关税自主权来保护发展本国的工业,应该说这就是在自由理想主义破灭后国家的最低理性——保护本国的利益,而不是国际道德优先。这种市场有限性的分配问题的出现,最终又将经济伦理直接转移和体现到国家的政治关系上去了,例如,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失败,也正在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独霸。
第三,在相互独立的世界中,基于利益的国家之于国家是没有道德要求和义务的,如果必须存在,就是国家基于组成部分的——个人的义务,而波及国家之外的同类。就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而言,因为其在生存资料的自给自足上,“国家”之间将不同于“人”之间,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赋予它进入“自然状态”的特征(Green,et al,1986:96)。在这种状态中,国家对另一国天然的无义务,也就没有道德。除非是基于国际法和条约,例如《战争法》基石就是不得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即便如此“不必要”也可能成为任何一方可以道德化的解释。在社会状态之前,国与国之间无义务关系,只有彼此相向的权利要求,这是现实主义的“自然权利”,因为作为国家的最低理性就是利己,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众的主权国,权力是法的基础。就如社会主义国家对阶段性经济实践——计划经济则是用无产阶级的道德理性安排去消除资产阶级理性安排造成的结果——利益的冲突,而这个过程又必须是动用国家这一权力机器去完成的,这个国家没有负有去让国际资产者实现利益和谐而放弃本国民众的公平的道德,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力去使其负有这样的道德。同时,“我们废除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列宁,1984:152)则展示了无产阶级国家道德和国际道德。国家就是道德、权力和利益的单位,国家利益是一切国际行为的出发点,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休斯(Hughes,1972:3)曾说过“对外政策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对外政策由国家利益所决定。国家利益或是源于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或是涉及历史视野的重大事件”。
第四,超国际机构的道德无效性。在爱德华·卡尔看来,接受“政治现实”是国际联盟区别于其他乌托邦的世界性机构的差别之处。然而,国际联盟自我解构力却在内部矛盾性的结构中一开始就存在着的,例如它规定了所有国家平等原则和大国永久多数地位、限制战争与诉诸武力的合法情形、实行经济与军事制裁和各国自主选择性(无标准和强制)、条款的模糊解释和政府抽象的政治家话语立场等等,都严重地侵蚀了国联成员的共同知识和理解,更难以有基于自愿的防止战争的共同行动。理想主义式的理性无论是民主或者国际法律、舆论,都缺乏对于这些理性的共同“社会意识”(李冈原,2011)。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而非共同责任,以各自的正义予以解释、引用和行动,在涉及非核心利益的世界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强制性。
(三)权力在道德中的回归
爱德华·卡尔在批判了理想主义者消除利己因素,将政治体系完全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空想,也批判了完全的现实主义的政治行为的纯粹利己而不利他,提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均衡”(爱德华·卡尔,2005:93)。他运用19世纪中国的困境和20世纪爱尔兰独立的例子,证明没有权力,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作为现实主义者,爱德华·卡尔并没有将道德置于不必要的地位,也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爱德华·卡尔对道德的思考既不是从道德理性出发,也不是根据道德理性的标准,而是集中于道德作为权力外部性因素的考察进行的,就是“为使用武力寻找道德上的理由”(爱德华·卡尔,2005:95)。鉴于道德无法建立国际政府或机构,他提出“权力是政府的根本条件,只要权力是国家的专利,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政府就不可能得以确立”他将国际领域的权力分成三类“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经济力量(Economic Power)和支配舆论的力量(Power Over Opion)”(爱德华·卡尔,2005:103),并认为权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以国联为例,认为国际联盟只有在被最强大的成员国当作工具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支持国联的舆论全然不再具有国际性质,而是成为某些国家的舆论,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国联实现国家政策和目标(爱德华·卡尔,2005:126)。这揭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国际道德只有获得权力的支持才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道德和理性,就如同国家首先有最高权力,它的治理才拥有道德而不是无政府状态;二是,道德有服务于权力和强国目标的潜能。
五、总结
爱德华·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是基于面对国际政治现实和对理想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基础上的,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者忽视道德的倾向和理想主义者排除权力的因素,他通过基于政治历史和事实的旁征博引,以理性和经验为格调,创造性地使权力从理论上得以回归,并将道德理性纳入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范畴,为我们审视和追溯国际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开端。爱德华·卡尔那个时代给他带来固有的局限,但他兼收并蓄的学术思考让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延展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开放性意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在爱德华·卡尔那里得到了回归,这种回归为二战后面对缺乏权力而让道德无效和缺乏理性而陷入安全困境的两难课题中,找到了理论突破的现实和希望。
参考文献:
爱德华·卡尔.2005. 二十年危机(1919-1939)[M]. 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黑格尔.1979. 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尔·洛维特.2006. 从黑格尔到尼采[M]. 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
肯尼斯·W·汤普林.2003. 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M].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肯尼斯·W·汤普林.2003. 国际思想大师[M]. 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少军.2014. 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列宁.1984. 列宁全集:第3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1984. 列宁全集:第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冈原,等.2011. 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国际关系[J], 浙江学刊(4):63-68.
洛伊斯·N·玛格纳.1985. 生命科学史[M]. 李难,等译.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秦亚青.2005. 权力·制度·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霍布斯.2017. 利维坦 [M]. 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黎,等.2012.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其贡献[J].当代法学(3):123-130.
亚当·斯密.1983.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
约翰·穆勒.2008. 功利主义[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余意.2006. 爱德华·H·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3):9-13.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2013.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STANNARD B R, EDWARD D W.1927.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3 War and Peace: 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1917-1924)[M].New York & London: Harper.
CARR E H.1939.Wassily Comte d’Ormesson[M].London:Longmans Green.
STIMSON H L.1932. The Pact of Paris:Three Years of Development[J]. Foreign Affairs (11)1: 5.
HUGHES.1972.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No.194,January 1924[R].New York: American Branch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MAYER J P, GROSSMAN R S H.1939.Political Thought: The European Tradition[M].New York: Viking Press.
ADAMS T.1980.The Epic of American[M].Santa Barbara,California:Greenwood Press.
GREEN T H, HILL T.1986.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Other Writing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IMMERN A. 1938.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J].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1939), 17(1):3-31.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he Retur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alism :Based 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Edward Hallett Carr ’s Thought
ZHAO Mingche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hando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Jinan 250014,China )
Abstract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Edward Carr, whose embodiment of ideological value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turn of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ealistic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path of idealism’s return to realism is a concentrated display of this achievement and the inherent logic. This path and logic are based on the primacy in epistem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ctivity, the critique of idealistic metaphys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realist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the debat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moral units and the return of subjects of power such a gradual layering of narratives. Revolving around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theory and practice, aspiration and reality,Carr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idealistic trend, but also realizes the correction of mora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self-denial. Thus, he made a basic argument for solving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weakness due to lack of power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power politics.
Key words : realism; Edward Carr; idealism; metaphysics; return of power
收稿日期: 2018-05-02
作者简介: 赵明晨(1984-),男,山东临朐人,博士,山东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9)02-0012-09
[责任编辑:萧怡钦]
标签:现实主义论文; 爱德华·卡尔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权力回归论文; 山东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