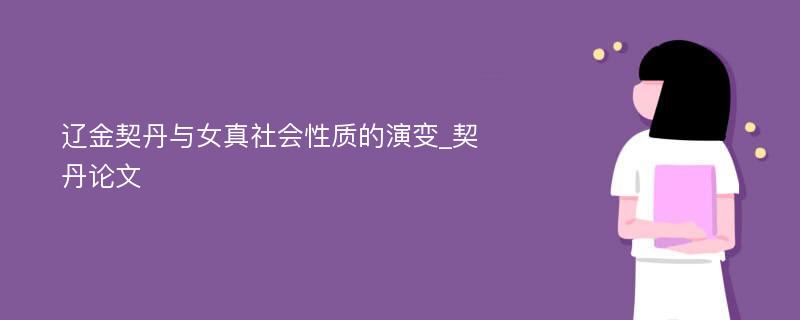
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契丹论文,性质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金立国前后契丹及女真族的社会性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还是经由奴隶制然后再到封建制?对此,学术界各执一说,迄无定论①。本文试从所有制及社会组织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说明这两个民族社会性质所以会如此变化的历史条件。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契丹及女真族地区私有制的形成
为了弄清辽、金立国前后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变化,首先得弄清私有制在这些民族中是怎样产生的。在契丹地区,私有制的产生首先是与汉人的大批流入及汉城、头下的出现相联系的;在女真族中,私有制的确立则导致以猛安谋克组织为单位的公有制的解体。
(一)头下与契丹地区私有制的产生
关于契丹早期的社会经济制度,文献记载非常贫乏。公元4世纪下半叶,北魏时期,契丹“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②。和龙即今辽宁朝阳,由此再往北数百里,即是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亦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草原,可见自北魏以来契丹人就生息繁衍在这里。他们在这片大草原上从事放牧和狩猎,“多为寇盗”表明在契丹社会内部早已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但仅限于可以抢劫和偷盗的动产,土地虽然是人们赖以谋生的最重要的资源,但还没有成为私有财产。此外,“多为寇盗”也表明当时契丹人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然而土地私有及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确立两点,正是私有制以充分发展的关键。
关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观念,原来契丹人是不明确的,土地被视为部族的附属物,为整个部族所共同占有。公元10世纪初,五代初期,“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③刘仁恭占据的幽州,与契丹地区相邻,他多次越过摘星岭发动攻击,迫使契丹人终于懂得了可以用自己的马匹购买原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牧地。这样契丹人才懂得了对土地的占有也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可以用其他财产交换得来的权利。不过在那时,土地仍然是整个氏族部落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唐末至五代,契丹人在同汉人交往的过程中,不仅逐渐产生了关于财产的观念,同时还开始学习创立自己的法律制度。“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陷幽州,燕之军民多为寇所掠。即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④当时历史文献中一再提及的所谓“立交法”,也就是指契丹部族首领在汉人协助下建立起有别于习惯法的法律制度。
契丹各部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最先明确以土地作为私有财产的正是那些与汉族接触最频繁的部族。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迭剌部在靠近汉族地区的滦河上游,他们将逃亡来及被俘获的汉人加以编制,建立汉城,于是该部的社会性质在契丹地区首先开始发生变化。《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载:
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
以上记载说明,正是汉人将契丹氏族社会原来所没有的首领世袭及土地私有的观念带给了阿保机等契丹贵族。这样,阿保机才认识到由他俘虏来的汉人所建立的汉城,包括其中的劳动者所开辟的农田,甚至还有周围可供利用的其他自然资源如盐池等,都是他的私有财产。其他人不能无偿获得他的盐池中生产的盐,当然汉城中生产的剩余农产品就更是归他所有了。
当时契丹境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汉城,这些汉城都是由头下构成的。“头下”是与契丹氏族组织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进行严密控制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户籍制度,而头下则是户籍制度遭到破坏的产物。唐后期以来,由于长期社会动乱,在某些地区出现大量外来人口,这些人脱离了原来的籍贯,从而不仅摆脱了封建国家的控制,同时也脱离了对原来主人的依附。封建地主为了把这些流动人口重新变成可以控制、可以供其剥削的依附农民,“团结”他们建立头下就成了最通常的办法。所谓“头下”即把若干人户编制为“团”、“保”等组织,并以其中一人充当“团头”、“保头”,其管辖下的人户即称为“头下户”。这种制度曾广泛存在于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寺户”当中。当大批汉人从中原逃入契丹境内以求躲避战乱和天灾时,这些外来人口不可能融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契丹部族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部族首领为了对这些外来人口实行有效的管理,以便于对他们进行剥削,于是就采用唐末五代时期已有的现成办法,即“团结”这些远离故土的汉人建头下。在分布有许多头下的成片的汉人居住区,又出现了统一管理这些头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称为“头下州军”,而且有比“州军”级别更低的单位:“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⑤。这样,头下就与契丹国家行政组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汉人都是“城郭以居”的,所以凡是在契丹境内新建起来的汉人居民点,一律都称为“汉城”。为安置大批逃亡来的汉人,契丹统治者“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⑥。所谓“树城郭”也就是建立汉城。汉城当中的基本社会行政组织就是“头下”。
最初,契丹境内的汉人不仅有自行逃亡来的,还有很多是被俘虏来的。这些人往往缺少人身自由,不仅生产活动,就连婚姻也都得听凭契丹统治者安排。但是,当他们作为头下户为契丹统治阶级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时,其身分并不是奴隶。契丹统治阶级并没有、同时也不可能改变头下这种封建经济形式的性质,更没有抛开头下另外创造一种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形式。契丹境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都是定居在头下州县当中的州县民户,其身分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
辽朝州县民户分为二等:正户和蕃汉转户。《辽史》卷三六《兵卫志》载:
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
析津(今北京市)地区与大同(今属山西)地区历来是汉人聚居的地区,其居民的构成与其他三京地区不同。上京、东京与中京三京地区的居民以蕃汉转户为多,南京(析津)与西京(大同)地区的居民则以正户为多。所谓“正户”即正式编入国家籍的编户,其身分是从五代的后晋延续下来的。《五代会要》卷二○载晋天福八年三月十八日敕:“其浮寄人户,有桑土者仍收为正户。”后晋实行的仍然是唐朝实行“两税法”以来的制度:“户无土客,以居者为簿。”只要拥有土地,虽非土著,也可以正式编入当地户籍而成为正户。辽朝沿袭唐、五代旧制,关于户籍并无新的规定。北方三京地区,原来并无很多汉族居民。这一地区的所谓“蕃汉转户”,是指唐末五代以来从其他地区转徙而来的人户。按照唐宋的户籍制度,这些从其他地区转徙而来的人户也就是与主户、正户相区别的“客户”。正户并非指契丹人,而是指辽南京及西京地区有恒产的汉人;北方三京地区的转户当中虽然有少量的渤海人,但主要也是汉人。这也就是说,正户与转户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即在土地关系方面,而不是在民族属性方面。
转户就是客户,这一点也可以在当时到过契丹地区的宋人的诗作中找到证明。苏辙在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1089)使辽,曾就途中所见赋诗云: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骆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⑦。
出了古北口,便是辽中京地区。苏辙这首诗反映的是这一契丹与奚、汉杂居地区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奚人是这里的土著定居者,契丹人则逐水草放牧。流落、转徙到此地的汉人“力耕分获得世为客”。这些汉人虽努力耕作,但必须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纳给主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世世代代都是为主人佃作的“客”。他们究竟主要是定居的奚人的还是游牧的契丹人的“客”呢?苏颂熙宁十年(辽太康三年,1077)使辽曾有一首题为《牛山道中》的诗,作者自注云: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⑧然而,为奚人佃作的客户仅仅是这一地区汉人中的一少部分。辽中京地区遍布头下州县,所以汉人中的多数应是控制这些头下州县的契丹皇家和大贵族的头下户。头下户也是客户。关于这一点,《辽史》卷三八《地理志》有明确记载:
咸州,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地在汉侯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
这些原在平、营等州即为客户的汉人因所迫被“招”到契丹境内,但作为客户的身分并没有改变,只是由原来依附于汉族豪强转而成为依附契丹朝廷、贵族。既辽中京、上京及东京地区普遍存在着头下州县,因此客户就应当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在《辽史》上有关客户的记载却很少,原因就在于客户的名称被更换成“转户”了。客户在辽朝北部三京地区普遍存在,也就证明了封建依附关系、租佃关系在这里是普遍存在的。
头下军州的客户、转户,绝大多数都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为主人佃作,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既然如此,他们对朝廷也就不能没有负担。辽朝农业税仍然沿用唐中期以来的两税法:不论主户还是客户,都要向封建国家缴纳夏税和秋粮。头下户作为客户,除了向主人交纳田租之外,则还应当向辽朝政府交纳两税。上引苏辙诗中说中京地区的客户、头下户“赋役稀少聊偷安”,然而比他早十几年使辽的苏颂在同一地区却发现农夫们“赋役百端闲日少”⑨,这种分歧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标准不同。不过他们之间有重要的一致之处,那就是都发现了当地农民有赋役负担。这些民户,不论是正户还是转户,都要向国家缴纳夏秋二税,故又称为二税户。
除了一般州县之外,辽朝诸宫卫管辖的各州县也都有大量的“正户”和“番汉转户”,“每宫皆有户口、钱帛,以供虏主私费”⑩。这些隶属诸宫卫的编户与隶籍普通州县的编户一样,也要承担赋役,不过他们税赋不入国库,而是缴纳给宫卫,以供皇帝本人享用。这部分人的身分与一般知州县民户是一样的。
辽朝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例如诸宫卫管辖的人口中称为“宫户”的那一类便是:“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11)这些居住在属于诸宫卫各州县中的俘虏、进献人口及没官口,都是属于诸宫卫的生产奴隶,其中既有汉人和渤海人,还有边远地区其他各族人。保宁三年(971年)“胪朐河于越延尼里率户四百五十来附,乞隶宫籍。诏留其户,分隶敦睦、积庆、永兴三宫,优赐遣之。”(12)胪朐河即今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来自那里的部族首领于越延尼里送来的人户都被留下了,成了隶属宫籍的宫户,延尼里本人则得到赏赐后被遣回。这里由进献人口转为宫户。宫户中还有很多是被籍没的罪犯家属。《辽史·国语解》云:“瓦里,官府名,宫帐、部族皆设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于此。”瓦里实际上是契丹部族的基层组织,因为宫帐本来就辖有若干部族,所以宫帐也有瓦里。契丹贵族如果犯罪,其家属没入瓦里,亦即被放到属于诸宫卫的部族中监管。这些人可能就是为宫卫从事牧业生产的宫户,而宫户中的汉人则可能有专门为契丹统治者从事手工业或副业生产的。据宋人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使辽所见,“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蚕丝户。”(13)这种“太后蚕丝户”也应是宫户。宫户在诸宫卫的全部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他们居住在属于诸宫卫的各州县中,身分与各州县的正户及番汉转户不同:他们没有正式户籍,故不包含在《辽史·兵卫志》所记载的诸宫卫所拥的“正丁”与“番汉转丁”的统计数字中。
总之,契丹立国之后,头下、汉城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在契丹族地区逐步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导致契丹氏族、部落内部出现了剥削阶级:拥有头下、汉城的契丹权贵成了封建主,他们不仅压迫、剥削外来的转户、头下户,同时也与一般的契丹部族成员处在对立的地位上。
(二)女真公有制的瓦解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居住在东北地区东部的女真人,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辽末虽然已有剩余产品,但人们仍然是物物交换以通有无。他们还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专门的手工工匠及专门以蚕桑为业者,屋舍车帐亦多自家制造(14)。当时的生女真人,既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压迫,也不懂得什么是法。《金史》卷一《世纪》载: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得利焉。”怨家从之。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你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字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
这是一段传说,但其中却包含了女真先民们对刚刚逝去的氏族社会生活的回忆:函普自高丽到女真人中间落户,正符合母系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子“出嫁”的古老习俗。法律规定杀人者可以用自己的牛、马、黄金等物赎罪,这说明牲畜及贵金属已经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了。土地则仍然为部族所公有,不同于个人所拥有的动产。
女真人“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5)。他们同姓居住在一起,村寨首领孛堇也就是氏族、部落首领。所谓猛安谋克,实际上就是以部族组织为基础的军事组织。他们以这种组织展开军事行动。当他们在新占领区定居下来时,猛安谋克就成了单独的、不与当地居民混杂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早在灭辽战争中,女真统治者就已经开始迁徙女真猛安谋克人户到新占领区屯田了。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阿骨打曾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吉林白城市)。据《金史》卷四六《食货志》载:
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迁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作,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徙欢、奚达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
辽泰州人烟稀少,昱等考察了那里的土质以后,向阿骨打报告说“可种植”,说明原来那里是未经开垦的荒原。女真人屯驻那里一方面从事开垦,另一方面则为了戍边。这纯粹是军事屯田,金朝向屯田的猛安谋克户提供耕牛,而土地原本是无主荒地,是屯驻这里的猛安谋克户集体开垦的,自然被视为集体所有。
女真人占领中原之后,也像攻占辽泰州那样迁徙猛安谋克户屯田。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1133)九月记载:“是秋,金左副无帅宗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16)此外张棣《金虏图经》还记载:
废伪齐刘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治均田。屯田军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马,殊不多,余并无支给。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种,亦无不足之叹。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设官府亦在其内。(17)
金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令其管辖原属北宋统治的黄河以南地区,而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从一开始就打算直接由他们自己统治。因此,向这两个地区移驻猛安谋克户是分别进行的。
最初,金朝是将汉人的耕地占夺为“官田”,然后,再对屯田户“计其户口给官田”,这的确很像魏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所以张棣在《金虏图经》中就径称为“均田”。正如均田制下农户以“受田”名义占有的农田并不都是国有土地一样,金朝猛安谋克户所分得的土地虽名为“官田”,其实政府对这类土地并不以国有土地论。金朝“官田曰租,私田曰税”(18),使用“官田”者,与封建国家构成租佃关系,但仅限于汉人。明昌元年(1190)八月,敕“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19)“百姓”即区别于猛安谋克军户的汉人。猛安谋克获得土地,与百姓佃种官田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对金朝政府不存在租佃关系,因此也不向政府交纳田租,而是向朝廷缴纳牛头税: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真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有奇,岁输粟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20)牛头税不是地税,因为屯田军户从政府领得了耕牛,所以要交“牛具税”。至于分配给他们的耕地,则既不交租也不纳税,因为这些耕地仍然被视为猛安谋克集体所有,每个成员都有权按规定无偿使用。
中原与泰州不同,这里并不是泰州那样荒无人烟的未开垦地区,而是早已开发的地区。移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立即陷入汉族封建经济关系的汪洋大海之中,并受到影响。他们在分得土地以后,很快就将这部分耕地视同私产。在有了土地私有观念以后,首先是女真权要、猛安谋克官员额外广占田产,兼并汉族农民及一般猛安谋克户的耕地,于是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金史》卷四七《食货志》载: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上曰:“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括者,亦当同此也。”又谓宰臣曰:“山东路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
但是,既要给予猛安谋克以及其他女真权贵以种种特权,金朝政府从来不曾认真限制包括女真权要在内的封建地主广占耕地。女真在中原广占流人耕地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公有制并接受了中原地区固有的封建制。
女真人早在金朝建立以前及尚未进入中原时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度,既占中原以后,短时期内奴隶的数量曾有很大增长,但当时女真人的奴隶制度仍然是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后来,当土地私有化的过程瓦解了猛安谋克组织之后,金朝的奴隶仍然如同辽宋时期一样,不过是封建制度的补充。女真人的奴隶制度始终未形成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此时社会上存在的具有奴婢身分的人户与女真早期的奴隶制并无联系,而是从辽宋时期延续下来的。例如作为奴婢的宫籍监户,实际上就是辽朝遗留下来的“宫户”(21)。金朝的官私奴婢有多种,除宫籍监户与官户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驱口”。“驱口”这个词很明显与中原地区早就存在的“驱使人”有关。敦煌文献中的驱使人,也就是辽朝文献中的“驱使人”及后来金朝“驱”和“驱口”,其中的“驱”字只能是“驱使”之意。驱口也有籍,称“驱籍”。辽道宗时期,检校大师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在上京城北创建静安寺,现存《创建静安寺碑铭》(咸雍八年)载:“工徙之役,算曰酬庸,驱籍一毫不取。”(22)意思是这一工程完全不使用具有“驱籍”的劳动力。依照唐制,“驱”作为私家的奴婢,应与主人一同记入国家的户籍。辽朝驱口有“籍”这一事实表明,辽朝的户籍制度将唐朝户籍制度中管理奴婢的办法接受下来,以作为管理“驱口”的制度。金朝“驱口”的数量虽多,但仍然是作为封建制度的补充由历史上继承下来的。
金朝的奴婢还有“人从”、“人力”、“女使”等名目。所谓“人从”,可能就是指“从己人力”。“人力”早在北宋就有。北宋的“人力”是指那些受雇于主人从事家务或生产劳动,并与主人签订限期契约的男仆。金朝的“人力”既然是由上中户轮差驱丁充当,则“人力”的地位,当与驱丁无异。此外,金朝“从己人力”是官员的仆役,并由官府依射粮军例支给钱粮。金朝的射粮军是被刺面在军中充杂役的,不仅地位低下,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女使”本来是受雇于主人的女仆,北宋时期与“人力”一样,与主人也是契约关系,然而在金朝统治下,“女使”同“人力”一样,也已经降为奴隶,主人可以将其转让,嫁女时用作陪嫁。尽管这些奴婢的身分到金朝时期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但正如其名目所表明的,他们的存在并不是女真人氏族社会末期固有的奴隶制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他们进入中原地区接受了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后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
二、国家机构取代部族组织
辽、金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契丹及女真部族组织从此不完全被国家机关取代了。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区,国家机构取代部族组织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在契丹和女真人中间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过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辽朝采用的是将契丹人的部族组织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的办法,而当金朝的国家机构逐渐强化时,女真部族组织则无可挽回地解体了。
(一)契丹部族怎样纳入国家政权体系
契丹人立国前后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阶段,部族首领还是靠习惯法维持统治,没有成文的法规和各司其职的设官制度,皇帝也不是真正的世袭,而是由各部权贵参加“世选”。天显元年(926)初,阿保机攻克渤海上京龙泉府(黑龙江宁安县东京城),灭掉了这个有200年历史的“海东盛国”。当时,契丹王朝还没有建立起后来那种兼治蕃汉的政治体制,而只具有治理契丹部族的简单机构。从总体上看,这时的契丹王朝仍然是一个徙具王朝之史的部落联盟。
当他们灭掉渤海以后,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渤海人虽然与契丹地区的汉人一样也从事农耕,并且过定居生活,不过他们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除逃到高丽的之外)一起落入契丹统治之下。这样一来,如何统治广大的渤海地区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契丹统治者面前了。阿保机以及各部族首领不可能将这几十万渤海人都迁往契丹地区建头下,将他们消化掉,于是只好将整个渤海地区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中。然而在契丹原有的部族联盟旧体制中,各个氏族、部落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渤海却是一个封建社会经济关系业已发展起来的、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的地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各部族,其上是契丹部族联盟,如今又要加进来一个按地域分居民的渤海地区,契丹统治者只能将其视为部落联盟的一个新成员,这样就有了“国中之国”的方式:阿保机下令改渤海为“东丹”,命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于是东丹就成了契丹王朝内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王朝。它与契丹王朝仍然保留部落联盟旧制的情况不同,而是“置左、右、大、次四相,一用汉法(23)。
会同元年(938),后晋将幽蓟等十六州“割献”给契丹。契丹对这十六州的统治也基本上采取统治东丹的方式:辽朝将这一地区的全部统治机器接收过来,令其照常运转。当时辽太宗曾对契丹中央官制进行一些变革:“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24)。这些官署虽然后来多隶属于南面官,但仅此而已,还不能说是已经形成了南面官。
这种可以称之为“国中之国”的统治方式是直接从部落联盟的方式中派生出来的。一直到公元947年灭了后晋,辽太宗耶律德光也仍然并没有发现什么更适当的统治方式,还是想沿用这种旧方式解决后晋的问题。他对后晋的百官说:“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25)耶律德光之下有多达二十七个“君长”,他本人就是这二十七个氏族部落组成的联盟的首领。正如灭掉渤海以后,东丹王朝被契丹人视同联盟之内的一个部族一样;占领幽蓟及后晋地区以后,他们对这两个地区也同样如此看待。
不过,契丹统治者在辽朝建立之后仍然继续维持这种“国中之国”部落联盟旧制的同时,已经在开始加强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早在耶律德光即位后不久就逼走了东丹王,东丹国已经名存实亡。至世宗时期,北、南面官体制确立,契丹王朝中央统治机构中出现了专门管理农耕民族事务的“南面官”,从而得以对汉人以及渤海人聚居地区实行直接统治;而北面官系统的形成也使得各部族首领变成了朝廷的行政官员,各部族组织形式虽然依旧,但就其性质而论却已经变成了契丹王朝统辖下的行政单位。北面官虽然主管部族事务,但它本身并不是在原来的部族联盟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南面官一样,也是依照中原王朝的设官制度建立起来的。北面官的核心机构是北枢密院。它显然是依照后晋枢密院的模式建立的。
(二)女真人血缘组织的解体
金朝立国初期同辽朝刚建立时一样,虽有王朝之名,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阿骨打攻下辽南京(今北京)时,进了大内,还“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26)。当时女真人保持的氏族社会的平等观念,比起契丹立国初期还要多些。尽管女真人的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私有制,并且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沦为奴隶,但氏族联盟的旧体制仍然继续维持着。那时的女真人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在大面积农耕出现以前,五十万人在地球的任何一部分共同生活并在一个政府之下发展起来是不可想象的。”(27)金王朝建立初期,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女真统治者同立国初期的契丹统治者一样,也曾试图在部族联盟体制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金朝廷虽然有皇帝,但却没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设官体系。官员们仍然沿用部族联盟时期的称呼,称“勃极烈”。朝廷管辖下的基本社会组织仍然是女真村寨,而且是以村寨来领导村寨。皇帝居住的地方亦是村寨,即所谓“御寨”,又叫“皇帝寨”,此外还有“国相寨”、“太子庄”之类(28)。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还没有形成,从上到下,金王朝的全部行政系统都还是以女真人的血缘组织为基础。直至阿骨打将其势力扩张到辽东地区之后,仍然在那一地区推行生女真人这种以村寨领导村寨的行政体制。收国二年(1116),“东京州县及系辽籍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9)东京州县自辽朝初年以来就一直有渤海人和系辽籍女真(即“熟女真)居住。渤海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经和当地的汉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早在辽太宗时期就明确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30)。在辽朝南、北面官的中央行政体制之下,渤海人与汉人一样,都隶属南面官系统管辖,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系辽籍女真”也早已成为州县民户。金朝统治者废除了辽东地区行之已久的州县组织,而代之以生女真人那种原始的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组织,此即所谓“一如本朝之制”。
如果说金朝统治者在辽东地区渤海人这样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推行“一如本朝之制”还勉强能行得通,待到灭辽夺取燕京及大同地区之后,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内推行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度、“一如本朝之制”就行不通了。首先,如果普遍强制变更社会行政组织,这种严重的骚扰势必要遇到汉族人民的抵制;其次,即使在汉族地区可以强制推行猛安谋克之制,女真统治者仍然不得不继续利用降辽官员,然而让这些人放弃原来拥有的汉官称号而改称“勃堇”,在他们看来等于是将他们这些州县官降为乡长、里正一级,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金朝只好放弃在这些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而让女真猛安谋克村寨与汉人的州县行政体制并存。燕京地区由设在燕京的枢密院管辖,大同地区由设在大同的枢密院管辖,这两个枢密院都是按照辽朝的南枢密院即汉人枢密院的制度设立的,分别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掌握“东朝廷”和“西朝廷”的女真权贵同时还掌握着进驻这两个地区的女真军队,而远在上京的金朝朝廷却因为只有一套女真部落联盟的简单机构,其权力所及,只限于附近地区。这种混乱状况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组织与按地域划分居民的封建行政体制不相容,所以女真人也只好像当年的契丹人一样采取“国中之国”的方式统治新占领区。所谓“东朝廷”和“西朝廷”实际上就是以燕京和大同为中心的两个国中之国。不仅如此,在原来属于宋朝统治下的黄河以南地区还先后建立起了两个傀儡政权,即伪楚和伪齐,无疑也是国中之国。
金初三个“朝廷”与两个傀儡政权并存的混乱的政治体制最终得以结束,同样不是靠女真人原有的部族联盟体制,而是靠在投降的辽宋官员参与下建立起来的汉官制度。金朝没有像辽朝那样单独设立一套管理女真部族组织的行政系统,而是通过实行汉官制度彻底废除了朝廷管理女真村寨的勃极烈。因此,汉官制度的全面推行,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女真人血缘组织的消亡,意味着与汉族社会融为一体。
金朝从什么时期开始实行汉官制度呢?《金史》卷五七《百官志》载:天会四年(1126)“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依照这种说法,早在灭北宋以前,金太宗就已经实行了汉官制度。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因为直至天会十年(1132),在确定完颜亶为谙版勃极烈的同时,太宗还任命其子宗盘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31)。这说明直到那时,至少金朝廷还没有实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二年(1134)正月,金太宗以“初改定制度,诏中外”(32),然而还未来得及实行,他就死了。真正实行这一改革的是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三月,即太宗死后两个月,熙宗诏讼以粘罕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随后又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太为右丞(33)。粘罕的地位表面上大大加强,此前,他不仅控制着云中和燕京地区,而且还实际上操纵着伪齐傀儡政权,金熙宗推行汉官制度,召粘罕回朝任宰相,让他掌握朝廷大权,不过是暂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解除他的兵权,不让他再继续掌握屯驻在中原的猛安谋克,这种策略就是所谓“以相位易兵柄”(34)。解除粘罕兵权之后,金朝才初步得以在两河地区通行朝廷政令。
天会十五年(1137)左丞高庆裔以赃下大理寺并被处决,粘罕成了孤家寡人,无力再与熙宗较量,不久愤闷而死。伪齐刘豫也完全失去了靠山,很容易就解决了。
金熙宗虽然除掉了粘罕并且废除了伪齐,但要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朝廷远在数千里之外,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要直接统治中原地区是很困难的。所以,挞懒、宗盘等人主张将原属伪齐的领土全部给宋朝。此事遭到兀术的反对,他向熙宗密报,说挞懒、宗盘等与宋朝勾结。其实这是兀术要借熙宗之手除掉自己的政敌。果然,熙宗除掉了宗盘和挞懒之后,兀术的势力就又膨胀起来。
废伪齐之后,金在汴京置行台尚书省,后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名义上,行台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据《金史》卷五百《百官志》载:
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
由于宗盘、挞懒等人主张以河南地归宋,所以行台建立不久就从汴京迁到燕京。天眷二年(1139)宗盘、挞懒以谋反伏诛,行台大权归宗弼(兀术),不再以河南地归宋,于是又将行台迁回汴京。熙宗以宗弼领行台尚书省,同时兼都元帅,又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35)。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都由兀术一人兼领,于是,燕京以南直至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的军事、行政大权统归兀术一人掌握。除掉了粘罕,又出现了一个与其权力相当的兀术,金熙宗的一切努力之所以会得出事与愿违的结果,正说明女真部族联盟旧制如不彻底废除,就不可能有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强大朝廷。直至海陵迁都燕京以后,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才“罢行台尚书省,改都无帅府为枢必院”(36)。后来,遇有特殊需要,仍临时设置行台。但这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了,而是中央行政机构尚书省名副其实的派出机构。
金朝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对中原实行有效的治理,同时在女真地区也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取代了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族组织。例如上京地区“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37)废除女真发祥地的特殊地位,将其视为与其地区一样的按地域划分居民的行政区,这样,女真人的血缘组织在其发祥地也不再继续存在了。
三、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历史条件
公元8-13世纪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先是塞外的契丹人与流落到草原上的大批汉人会合,然后是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南下屯驻中原,直到与汉族融为一体。契丹和女真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创造自己的文明史。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8)当时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不仅有本民族的历史遗产,同时还有对他们的发展起更大作用的汉族封建文明。他们的社会发展究竟走什么道路,正是由这样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如果契丹及女真人与非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孤岛上的土著居民一样,处在与外界隔绝的地理位置上,那么,他们在技术和制度诸领域就都得自己创造,他们的社会发展也会像上述地区著居民一样缓慢,并且也将逐步地由一个阶段迈向下一个阶段。然而由于契丹及女真族处在与封建经济、文化业已发展起来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之中,受外界影响,他们不能够、也不必要在制度和技术方面保持自己的纯一性,而是都成了混杂不纯者,于是社会发展也必然呈现跳跃式。
在涉及契丹及女真人早期历史的文献中,的确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祖先独立创造自己的文明史的记载。例如《辽史》卷二《太祖本纪》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好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
我们只要认真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以上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匀德实既然是契丹游牧部族的领导人,他或许曾在提高畜牧业生产方面有所作为,但说他“始教民稼穑”却与基本史实不符。契丹人并不曾放弃游牧而从事农耕,在契丹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是来自中原的汉人,这些汉人自然不待习德实教他们才懂得稼穑。辽朝置铁冶多在辽东地区,那里的居民除汉人之外就是女真和渤海人,当阿保机之父撒剌的在世时,契丹人的势力可能还不曾达到这里。至于兴板筑、置城邑、种桑麻、习织组等,都是流入契丹地区的汉人带来的新事物,将开创之功归之于阿保机叔父一人更不足凭信。
契丹直到立国初期还并没有完备的史官制度。辽兴宗以后曾多次追记、补修圣宗以前诸帝实录和国史。因此,上引关于契丹文明起源的传说必然形成甚晚。契丹统治者在辽、宋分立的形势下,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同宋朝全面抗衡,于是就仿照黄帝以及神农氏等的传说编造出一段契丹人独立创造文明的神话。我们如果据此断言契丹人当时就在农业及手工业生产诸领域中如何如何,显然是靠不住的。
在宋金对峙的历史条件下,女真人也曾编造过自己的文明起源史。宋人苗耀《神麓记》说:随阔“教人烧炭炼铁,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风。”(39)。这些得自女真人的传说。如此说来,早于阿骨打四代的绥可(即随阔)就已经知道烧炭炼铁了。然而《金史·世纪》记载:生女直旧无铁,领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这是绥可以后三代即乌古乃时期的情况,足证前说无据。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领域中,人们都不会抛开别人已有的可资借鉴的成果,去干重复“创造”的蠢事。尽管在长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上曾经有过成百上千的种族和民族,但世界各地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却只有几个,中国这块土地就是其中之一。以黄河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南到珠江流域,北至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间山水相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在这一广大范围内生活的古人类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在亚洲东部及更广大范围内有巨大影响的中国封建文化。从文化类型来看,契丹及女真人的文化当然属于他们参与创造的中国古代文明世界。综上所论,归结到一点,即: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变化的历史过程是在当时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参与下实现的,这也同样证明了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附记:本文经老同学陈智超兄帮助斟酌修改再三,其中所言不谬者都包含他的心血。
注释:
①参阅宋德金《建国以来辽金史若干问题的研究》,载《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魏书》卷一○○《契丹传》。
③《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④《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⑤《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南面方州官》。
⑥《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
⑦《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⑧《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后使辽诗》。
⑨《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后使辽诗·牛山道中》。
⑩余靖《武溪集》卷一七《契丹官仪》。
(11)《辽史》卷四九《礼志·吉夜》。
(12)《辽史》卷八《景宗本纪》。
(13)《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引《乘轺录》。
(14)《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15)《金史》卷四四《兵志》。
(16)《大金国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纪》也在天会十一年记载:“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17)《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四。
(18)《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9)(20)《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21)详见拙文《金朝的宫籍监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2)《全辽文》卷八。
(23)《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24)《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25)《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26)《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二《北征纪实》。
(27)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9页。
(28)《大多国志》卷二《太祖武元皇帝纪》。
(29)《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30)《辽史》卷六一《刑法志》。
(31)(32)《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33)《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34)《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纪》。
(35)《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36)《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37)《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39)《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