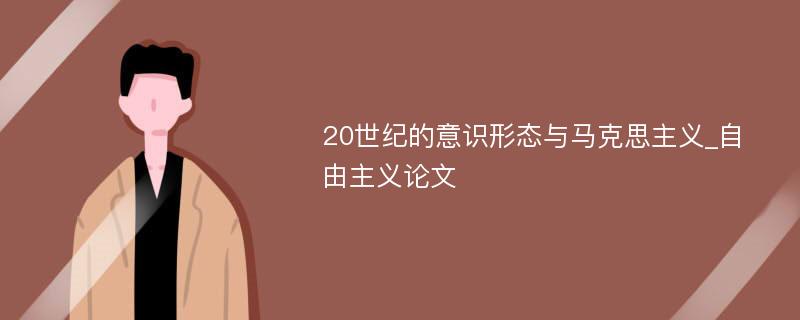
20世纪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常常被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这不仅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峙几乎贯穿于整个世纪,也因为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显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这种意识形态的兴盛本质上是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世纪的此起彼伏。回顾和反思这个世纪的意识形态运演历程以及由此凸现的问题,对于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如何掌握领导权、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资产阶级思想界充满着失望、自卑和非理性的情绪。意识形态的危机使整个西方社会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酝酿着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主张。这个主张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极为重要的。有些人由此认为,十月革命是意识形态推动的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发展的产物。例如,葛兰西认为,十月革命是“与《资本论》向左的革命”。[1](P136) 他还用赞扬的口吻说:“不,机械的力量在历史上从来不能起决定作用:是人,是意识和思想赋予外部现象以形式并最终取得胜利……人的顽强意志取代了自然规律,取代了那些所谓的学者提出的事物的必然发展过程。”[1](P229) 从实践过程的一个阶段看,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列宁无疑是成功的。然而从长远看,仅仅强调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建设是难以将革命坚持下去的。列宁无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他就号召全党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是,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社会学说的基本精神?换言之,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究竟能否意识形态化?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在很多人看来,意识形态化是对马克思社会学说合乎情理的发展。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正式形成。这种对峙除了表现为经济上的“限制与竞争”、政治上的“对抗与冲突”外,还突出地表现为思想上的“对立与论战”。在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计划经济效应的显现,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在苏联变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对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模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积极抵抗着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进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在苏联,一批批文化作品反映着人民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同时激发着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一切曾一度引起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方面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颠覆,另一方面也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同时,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特别是2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全面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凯歌高扬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暗含于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理论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对于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超越的社会机制究竟是什么?人民是否能够坚持不渝地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自己真实的政治信念和社会态度?
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产生了它的怪胎——法西斯主义。信仰自由、理性的思想家们在抗拒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对为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会产生如此怪胎进行了痛苦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这些反思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广泛分析和批判对于人们认清法西斯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他们注意把心理学、社会学方法引入意识形态批判,使意识形态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然而,西方学者们往往只是把批判局限在意识形态本身的圈子里,并以软弱无力的人道主义说教和自由、理性的乌托邦作为主要的原则,而未能把目光投向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批判指向苏联社会主义。霍克海默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都是本质相同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模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党性原则。
二
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时代走进了历史,蒙在苏联身上的厚厚面纱被无情拉开。一些正直的人所不愿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获至宝的某些史实逐渐大白于天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后遗症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本来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封闭的正统信仰体系,人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官方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官方的解释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可是后来苏联理论界在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中并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辩证精神。他们不是从总体的社会生活中探索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与根源,而仅仅把问题归结为领袖的人格缺陷;他们不是通过反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而是走上了一条人道主义的理论道路。人道主义似乎成为对历史纠偏归正的一帖灵药。1960年3 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提出,苏联社会主义以关心人为最高原则,“人道主义、人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活动的主导原则之一。”“全民国家”、“全民党”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逐渐成为苏联共产党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中不容改变和动摇的核心内容。[2](P9—10) 这就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越来越软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也因此而变得愈益贫乏,不是充斥着教条主义的东西,就是执行着投降主义的路线。应当看到,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具有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原因,但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批判功能是不是仅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是否也包含着对现实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同时,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如何坚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似乎与之遥相呼应,在50年代的西方出现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宣称,作为政治概念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文化和艺术。他说:本来使激进的知识分子获得革命冲动的意识形态、本来作为幻想性观念同义词的意识形态、“本来成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已经走进了死胡同。”[3](P369) 其实,这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给人们展现的一幅西方世界歌舞升平的幻象。这种宣告“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的。可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件文化的外衣,开始作为“全人类共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四处蔓延。而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文化上一方面屡屡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消除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一些人甚至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暗送秋波。结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取得居高临下的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逐渐陷入了困境。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分外明显。资产阶级不停地向全世界兜售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表面上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实质上是它们自己的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攻势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一步步地从有条件地接受资产阶级的观念走向无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的观念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后退到只是批判资产阶级说一套做一套(即言行不一致),好像只要言行一致,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就没有什么缺憾了。在一方步步紧逼、一方步步退让的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失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批判精神,只能在消极防御中惨淡经营。无疑,这是20世纪末社会主义走向低谷的一个深层原因。
三
20世纪70年代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成为党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而稳妥地探索着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迁,社会思想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那种思想文化取向的一元性逐渐被多样化所替代,各种思想文化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自己的位置,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这种现象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处在主流地位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代中,获得了新的形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和实践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学术界几乎形成一定气候的非主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又具苏联后期思想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并以此抽象地反对种种非人道的社会现象,开启了以抽象的道德标准消解具体政治标准来评判历史的先河。这种“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好像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特质,然而人道主义终究是一种只能激扬文字不能落脚现实的思辨。三是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精心打扮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些知识分子以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为幌子,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极力消解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不过是角度不同罢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自我贬损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知识分子实质上并不是真的要坚持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他们只是策略地把马克思当作贩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面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既快速发展又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时代。虽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道理在理论上被论证了无数遍,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市场经济就像潘多拉盒子,随着它被慢慢地打开,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欢快地飞了出来。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终于潇洒地卸去外在的面具,直接以本真的面目登堂入室了。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现代自由主义是整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而相对应的整体主义是以东方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应当看到,这两种理念各具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当今它们的冲突,并不是两种理念本身的冲突,而是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的冲突——资本主义和被资产阶级看作整体主义象征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弥漫于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被大量引介。柏克、托尔维尔、哈耶克、伯林等人的著作几乎流行于整个知识界,他们的格言甚至进入了大众传媒,似乎成了毋需存疑的公理。另一方面,一批学者热衷于为自由主义争取中国显学的地位。他们努力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变成“纯粹学术话语”和“大众生活话语”,或者致力于在中国历史上挖掘自由主义的渊源。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展示了中国在21世纪的希望。言下之意,似乎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应该说,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盛行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和世俗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其盛行的土壤,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输入和主流思想文化对自由主义的宽容是其盛行的条件。自由主义作为一个被马克思社会学说所超越的思潮虽然在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基本的原则和取向并没有变化。为什么在当今中国,自由主义能够如此张扬地与马克思主义唱对台戏,好像要反过来超越马克思主义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四
由上观之,20世纪意识形态运动的主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彼此消长。这种消长必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力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斗争相联系。同时,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以普世性文化的面目向全世界扩张,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是清醒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获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
第一,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离开实践的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和遐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P40) 因此,马克思主义无意强调某一种状况的合理性(因为在它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既有的状况都会失去其原有的合理性),它的任务是证明前进运动的合理性。所以,它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为某一种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社会状况进行辩护的保守功能。
第二,马克思主义把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争取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也是真正指向未来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5](P282) 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因而是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P307) 因而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283)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它毋需向人民隐瞒什么,毋需将外在于人民的思想强加给人民。换言之,人民就是它的现实主体,它就是人民的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否定和超越了伪普遍性和伪人民性的意识形态。
第三,在实践性和阶级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与实践、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直面社会的现实,以科学的精神探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逻辑地提出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从单纯道德批判中产生的脱离现实的“应然”道德理想,而是扎根于现实又指向未来的真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P40) 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马克思把革命的人道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唯物而辩证地加以分析。马克思既无意掩盖自己的社会观点,也无意掩盖社会的真实状况。因为在他看来,理论越是科学,就越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同时,马克思厌恶以前那种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思想家将自己的思想视为永恒真理的做法,强调自己的理论在社会发展中将不断地改变自己,实现与无产阶级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认为,理论一旦成为教条,就必然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马克思的社会学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系,因而它鄙弃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永恒性和伪真理性,指导着无产阶级创造性地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面对着20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的演变,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原初理论中挖掘其精要,继承其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并将其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牵引现实,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并引导人们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不断地从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纷扰中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使命。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