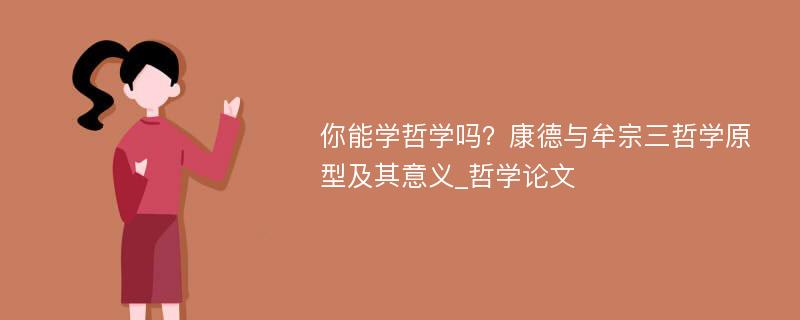
哲学可学吗?——康德和牟宗三论哲学原型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原型论文,意义论文,康德和论文,可学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5-0052-06
哲学可学吗?此问题不是说哲学因人之才情的不同,天资聪明者则可学,鲁笨者则不可学,抑或有兴趣者可学,无兴趣者则不可学。若然,则“术业有专攻”,任何一门学问皆可作如是之问。这当然不是此问题之本义。此问题是说:从哲学的本性来看,可不可学不是人之使然,而是哲学的本性使然。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和牟宗三由于对哲学本性的不同把握而作了不同的思考。牟宗三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智慧的重新阐释,发现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优长与不足,从而为他创造性地融通中西哲学提供了可能。
一、康德的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章中说:
因此,在发生自理性的一切学问中,只有数学才是能被学习的;哲学,除只依历史的样式去学外,决不能被学习;就那于理性相关者而言。我们至多能学着去作哲学的思考(philosophise)而已。[1](P.657)
在此,康德提出一重要概念“依历史的样式去学”。根据这一概念,他把知识分为“历史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由此我们即可明白他产生上述结论之因由。
1.“历史的知识”和“理性的知识”
何为“历史的知识”?何为“理性的知识”?康德有了进一步的解析:
如果我把客观地视之的知识的一切内容皆抽掉,则一切知识,主观地视之,皆或是历史的,或是理性的。历史的知识是由所与而来(cogitio ex datis)的知识;理性的知识是依原则而来(cogitio exprincipiis)的知识。一种知识,不管它是如何地根源地被给与,就其关联于得有之的个人来说,如果此人知此知识只如其从外面而被给与他那样地知之,此从外面给与他的而给与他的,不管是通过直接的经验,或通过记述,或通过教导(象在一般知识的情况下),只要是从外面而来,则此种知识仍然只是历史的。[1](P.655)
依康德的观点,“历史的知识”是由材料堆砌而成的知识,而材料是由外部给予的,这样,这种知识必须呈现于人的感觉经验中,而经验是因人而异的,因而一种普遍必然的知识,是不能来自感觉经验的,只能来自于剔除了感性质料的纯形式(概念或原则)中。当然,对于这种纯形式的来源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实在论者认为是对经验材料的抽象,而康德则认为,这些概念或原则是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形式条件,因而必须是先于经验而有的,即先验的,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是发自于人类的理性的。因此,康德把这种依原则而来的知识(先验的知识)称为“理性的知识”,只有这种知识才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是指人人皆可具此一套知识,你没有这一套知识只是你自家的理性没有豁显出,从而把握住这一套。在此,始显出“学”的意义来。故“学”即是依于这种知识来豁显自家的理性,一旦理性豁显出,则我们从自家理性中亦可获得这种知识,而这种获得是定然不可移的(即具普遍必然性),此即是康德所谓的“可学”。而“历史的知识”因来源于经验,而经验又是人人可异的,因此,这种知识的获得是或然的,可被甲学到,不一定能被乙学到,所以,这种知识没有普遍必然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认为“历史的知识”不可学。
依康德之意,一种知识除非完全存在于人类理性的本质中,否则便不能称为理性的知识,因而亦不可学,至少不是康德所意会之“学”。于是,康德认为,在一切的学问中,惟有数学可被称为理性的知识。他说:
数学知识,教师能引生出它的唯一根源,除存于理性的本质的而且是真正的原则里面外,无处可以存在,因此,它不能为初学者从任何其他根源获得,而且它亦不能被争辩;而这不能被争辩转而又由于这事实,即:理性的使用在此是具体的,虽然同样亦是先验的,亦即是说,是在纯粹直觉中的使用,而且确然因其如此,所以它是不会有错误的,它排除了幻相与差错。[1](P.656)
依康德之所说,数学的知识之所以能被学习,乃因为:其一,除了从各人自家理性中获得之外,不能从其他地方获得,而理性只有一个(虽云理性的知识从各人自家理性获得,但我们不能说你的理性不同于我的理性,这正如不能说你的良知不同于我的良知一样,不然,道德便不能讲),因此,这种知识在主观上便不可能产生争辩;其二,在数学的知识中,理性的使用是具体的,即在纯粹直观中的使用(即时空先验感性直观形式),因而在客观上是不会有错误的。
那么,哲学的知识是不是理性的知识呢?在此,康德区分了哲学的知识和数学的知识的不同。他说:
一切发生自理性的知识或是由概念而被引生出,或是由对于概念的构造(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而被引生出。前者名曰哲学的知识,后者则名曰数学的知识。[1](P.656)
依康德,哲学家(“经院式哲学”的哲学家,非“宇宙性哲学”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理性的技匠,哲学的知识(准确地说,应该是给经验材料提供统觉的诸范畴)与数学的知识皆是发自理性的知识,我们不能从任何其他根源得到,这一点两者并无二致,关键在理性(即范畴或概念)的使用上,哲学的知识是不是像数学的知识那样,是在纯粹直观中的使用呢?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康德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不论是数学的还是哲学的),最终总要和可能的直观发生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东西里面,所作出的判断只是分析判断,依康德,分析判断并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只是使概念更加明晰而已)。否则就没有对象把它给予出来,从而我们不知道它的实在性,也就不能称其为知识。可是一个先验的概念,要么就是在它的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种纯粹直观(如果是这样,它就是可以构成的),要么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只是没有先验地被给予出来的可能直观的综合而已。前者形成数学的知识,后者形成哲学的知识。在数学的知识里,因为理性的一切概念在那里都必须立刻具体地在纯粹直观里显示出来,于是在这些概念里,一切无根据的和任意决定的东西都立刻暴露出来,因此,数学的知识是不会有错误的。在哲学的知识里,我们想要对于一个概念作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就必须越出这个概念以外,而诉诸这个概念在其里面被给予出来的直观。那么,这种直观是怎样的直观呢?康德以实在性、实体、力等先验的概念加以说明。他指出,这些概念既不是一种经验性的直观,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直观,而只是经验性直观的综合,而这种直观,由于是关涉到经验的,是不能被先验地被给予的,因此,如果这些概念试图撇开经验而直接地先天地把握自然,它就并不能像数学的知识那样获得一种实在性。哲学之所以成为先验知识,是因为它给经验性直观提供了统觉的先验统一性规则,而这些规则由于没有与之相应的纯粹直观,所以这些规则就不能产生任何具有确定性的综合命题,而只能产生关于可能的经验性的种种直观的综合的原理,这样,这些原理仍然是经验性的(机械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产生必然的且不可争辩的命题的。依康德,由于哲学的知识需要有经验直观(材料)的参入,而材料是外部给予的,非发自理性的,因此,哲学的知识仍然是历史的知识。这样,哲学当然不能像理性的知识那样被学习,而只能依着“历史的样式”去学着作哲学的思考,“即依照理性的普遍原则,依据某一现实地存在的有利于哲学者的尝试,去练习理性的才能”。[1](P.657)
以上是康德对此问题的思考的理路,清楚明了。不过,在康德看来,人类的实践理性高于思辨理性,因此,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由思辨理性的运用所成的知识论式的哲学系统。康德认为,人类的理性无须任何材料便可以给自己一个最高最后的对象——最高善,哲学应该是把所有知识都统摄到这个对象之下的学问。康德把前者称为哲学的“经院式的概念”,后者称为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那么,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是不是也是“历史的知识”,同样不能被学呢?康德进一步思考。
2.哲学的“经院式的概念”和“宇宙性的概念”
关于哲学的“经院式的概念”,康德说:
迄今以往,哲学的概念只是一经院式的概念(scholastic concept)——一个知识系统的概念,此概念只在其为一学问的性格中被寻求,因此,它只筹划这系统的统一,即以知识体系的统一为学问的目标,因而结果,它不过是知识的逻辑圆满(logical perfection)。[1](P.657)
在康德看来,这种经院式的哲学,尽管亦试图筹划系统的统一,但只是追求知识的逻辑圆满,其结果,这些哲学家在这种筹划和追求中只不过是理性的技匠。然而,康德认为,人类理性最关切的不是知识的逻辑圆满,而是给自己规定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人类理性的目的有两个层次,一为人类理性的那些基本的目的,二为依着理性的彻底统一性而趋向的惟一的最高或最终的目的。前者是自然哲学,讨论一切“是什么”(that is)者;后者是道德哲学,讨论那“应当是什么”(ought tobe)者。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目的的两个层次并非平行的,前者必然地被当作工具而与后者相连系,因此,后者亦称为终极目的,此终极目的乃是人的全部天职。于是,相应地,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开始虽可以在两个特殊的体系中,然而最后必然地也要包含在一个惟一的哲学体系之中,这个体系的全部天职乃讨论理性的终极目的。康德把这样的哲学体系称为“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conceptus cosmicus)。
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康德亦把它称为哲学原型。在康德看来,除非我们能找到这一哲学原型,否则我们便不能学习哲学。然而,哲学原型何以可学?康德认为,哲学原型并不是一个逻辑圆满的知识体系,而是理性的一个理念,既如此,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即哲学原型就并非“历史的知识”,而是“理性的知识”。依康德之意,这自然为可学者。但问题是:其一,现实中存不存在哲学原型呢?若没有,则其二,我们如何能成就哲学原型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康德说:“在哲学一词的这种意义上,去称一个人为哲学家,并妄以为他已等于那只存于理念中的模型,这必是过情的虚誉”[1](P.657),此即意味现实中并不存在哲学原型。对于第二个问题,康德说:“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种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此,它不只含有自然的法则,亦含有道德法则,它把这两种法则首先呈现于两个不同系统中,然而最后则呈现之于一个整一的哲学系统之中”。[1].(P.658)这是康德所表达的“理境”,至于如何使两个不同系统呈现于一个整一的哲学系统之中,他并没有说。康德对“哲学可学否”这一问题的解答,只到这个程度。
我们现在来检讨一下康德的思考理路:像他这样一位以豁显人类理性(康德认为:人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即为启蒙)为使命的哲学家,自然不满足于哲学仅仅为成就科学知识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历史的知识”由于只能依着历史的样式去学,则对于每个人来说皆是或然的,而不可强求,故世间有各别不同的专家学者。但是他认为,每个人有义务必须为一个对象服务,在此处是必须被强求的,这个对象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理性的终极目的——最高善;哲学也应该为这个对象服务,于是他提出了哲学的“宇宙性的概念”(哲学原型)。由于这种哲学纯粹由人的理性所提出,故人人的理性中本应有此一套,你没有只因你的理性没有豁显出(即没有启蒙),但你若依此哲学原型豁显出了自家的理性(即启蒙了),即可见此一套,这是康德“学”的意思。但问题是:现实中并无此一套,我们又不知如何得到此一套,则这个“理境”上可学的,实并无“可学者”在,于是便成了一套挂空的理论。牟宗三认为,康德这位理想的哲学家的一番思索实属不易,他“较准确地决定了哲学所规定者”,但他只是指明了方向,并未作透辟的解答。于是,牟宗三把问题接了过来。
二、牟宗三的解答
牟宗三认为,尽管康德没有给出最终的解答,但这并不表明康德不行,实乃是他的传统所限,康德所提出的哲学原型的概念,是站在西方知识论的传统基石上,用概念分解的方式,以一个哲学思考者的姿态所或然地摸索到的一个“影像”,尽管他提出“物自身”的概念而把知识严格限定在现象界,但由于他没有把“物自身”的意义彰显出来,因此,他最终很难成就哲学原型。于是,牟宗三把它拿到中国哲学里来解决。
在中国,儒者们早已摸索到了康德的那种“理境”。程明道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王阳明亦云:“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为天地万物而为一也”(王阳明《大学问》)。那么,程明道和王阳明所说的“理境”是不是也像康德那样以哲学家概念思考的方式所摸索到的一个“影像”呢?王阳明明说:“非意之也”,即不是这样的。他说“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为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即这不是一种思考所达的“应然”,而是一种实理实事的“实然”,但究竟如何会是“实然”。王阳明之言“浑无罅缝”,牟宗三在此把它“十字打开”,他的解答即从这里开始。
1.对康德“现象”和“物自身”的省察
康德说人类理性的立法有两种对象——“自然”和“自由”。开始呈现于两个不同系统中,最后则呈现于一个统一的哲学系统中,他把此一系统称为哲学原型。在康德的哲学中,“自然”属于“现象界”,“自由”属于“道德界”(实则不可说“道德界”,因其中无物故,只一些纯粹实践理性的理念,如自由,灵魂不灭,上帝等),依康德之意,哲学原型是就着“现象界”和“道德界”进行拉扯和形构。这样行不行呢?表面上看,儒家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好象也是就着“现象界”(物)与“道德界”(仁者)而说,问题是:儒家所说的“物”是不是“现象界”的“物”,在此,牟宗三见出了儒家与康德的极大的不同。
众所周知,康德把“存有”分为“现象”和“物自身”,但在他的哲学中,“物自身”是一消极概念,它既不属于“现象界”,亦不属于“道德界”,只是人类知识的极限,这样,“物自身”仅仅是一个限制性的空洞概念。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物自身”就是一个冥阍,人们不知道康德提出这一概念有何意义。于是,牟宗三把它的意义给阐释了出来。
依康德,上帝只创造“物自身”,并不创造“现象”,然“物自身”既是上帝创造,自然是一有限存在(在西方,无限存在只能有一个,即上帝)。康德又认为“物自身”不在时空之中,即无时空性这种必然属性(康德之意是:若上帝创造“物自身”时赋予了它以时空性,则必定把上帝自己带入时空之中,即上帝须以时空性为先验条件才能创造,康德认为这是荒谬的)。一个有限物又不在时空之中,这如何可能呢?牟宗三认为这是很可疑的。有限物之所以为有限物正因其有物质性,有物质性而能无时空性吗?牟宗三认为既是有限物就必然有时空性,这时空性也不会对上帝构成威胁,他说:“上帝的直觉是创造,不是表象,所以在他亦无所谓先验条件:他是无条件地创造了一个有时空性的物自身。他何以能如此,这是上帝底奥秘,无人能知。——我们不因上帝造有限物而说上帝亦有限,当然亦不能因有限物之有时空性而说上帝亦有时空性。”[2](P.109)在牟宗三看来,既然康德承认上帝创造了作为有限物的“物自身”,则“物自身”的时空属性是要必然地被肯定的,不在于康德承不承认。如此一来,在康德的系统中便产生了矛盾,因为他的基本主张是:时间和空间是主观先天的直观形式,不是物的必然属性。这问题将如何解决呢?问题就出在这“物自身”上。牟宗三认为:如果承认康德的基本主张,而否认“物自身”的时空性,则“物自身”必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如果认为“物自身”不是一空洞的概念,而含有丰富的真实意义,则它决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只有在此一转上,它始可不是一决定性的有限物,因此,始可于有限物上而说无限性或无限的意义。如此,始能保住它不以时空为必然属性,并保住时空之超绝的观念性,而否决其超绝的实在性。”[2](P.111)但这一转折,牟宗三认为,并不是上帝创造说所能极成的,上帝创造说必然会陷入康德系统矛盾中的,除非我们承认这悖理是宗教中的奥秘。我们若要极成无时空性而有价值意义的“物自身”而说其无限性或无限性之意义,这不能从上帝创造来说,必然在我们身上转出“自由的无限心”方可。牟宗三根据《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义理,认为“自由的无限心”可坎陷而为“有限心”,“有限心”以其“执”(感性的时空形式和知性的范畴)成就“现象”,“无限心”以其“无执”而成就“物自身”。这时的物自身是一种怎么样的存有呢?牟宗三彰显其意说:
在自由自律的无限心之圆觉圆照下,或在知体明觉之神感神应下,一切存在皆是“在其自己”之存在。圆觉圆照无时空性,无生灭相,“在其自己”之存在当然亦无时空性,无流变相,它们是内生的自在相,即如相:如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实相。无时空性,它们不能是有限(决定的有限);但我们亦不能说它们就像“无限心体”那样的无限,它们是因着无限心体之在它们处著见而取得解脱与自在,因此取得一无限性之意义。[2](P.112)
这样的“物自身”显然不是像康德那样去设定一个空洞概念,而是一种落实的“存有”(因我们的“智的直觉”可直觉之)。正是在“物”的这个意义上(“物自身”意义上),儒家方才可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乃一“无限心体”,但此无限心“不是空悬的无限心,而是即于现实的物自身之存在而为无限心,故物自身之存在亦成无限而永恒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以一切物自身之存在作为吾之物自身之存在之内容,而亦不丧失天地万物之各为物自身之独自的无限性与永恒性”[2](P.118)。这正如天台宗所说佛必具九法界而成佛一样,“无限心”之所以为“无限心”是即着“物自身”而然,“物自身”之所以为“物自身”乃因着“无限心”而然,此即是“自由”(无限心)与“自然”之整合于一。此“自然”虽为“物自身”之自然,非“现象”之自然,然当无限心随机而转而显识心之执,即为“现象”之自然。故康德所说的现象界的“自然”与“自由”之整合亦无问题,其奥秘惟在这一机之转。然此“机”非思考所致,乃实践而成,即须于心上做工夫。
2.“道德的形上学”成就哲学原型
在中国的传统中,“自由”和“自然”之整合于一虽不成问题,但这并不表明此一整合便是一哲学原型,因为康德明说哲学原型乃“自然界”与“道德界”之整合,因惟有此两界之整合方可开世间各别不同的哲学子系统。在康德那里,“自由”是属于“道德界”的;而在中国,“自由”则不一定属于“道德界”,因为儒道释三家皆可显“自由的无限心”,而道、释两家则无有道德义,既无道德义则不属“道德界”,故此二家所整合之系统亦属于哲学原型下的子系统。就义理来看,此二家之“自由的无限心”只有荡相去执的作用义,而非有像儒家一样的创生义,此作用义是依着万法反显上去(即否定)而成者。既如此,这二家“自由的无限心”之妙用须有一可供妙用之“物”在,此“物”惟有在儒家之系统中方可创生。
牟宗三认为,依儒家之义理,“自由的无限心”(本心)在道德践履中呈现。就“本心”言,是道德创造之“体”;就践履所成之“德业”言,乃承“体”所起之“用”。这种“体用”在道德践履中必是直贯的,这只是就道德行为本身而言:“体”是道德创造之“体”,“用”是道德实践之“用”。但在践仁尽性之无限扩大中,因着一种宇宙的情怀,这道德的“体用”即刻就是本体宇宙论的“体用”,“体”是创造万物的生化实体,“用”是收授万物的繁兴大用。至此情此境,必有一“形而上学”出现,而儒家之能至此境自始是要靠那精诚的道德意识所贯注的,故是一“道德的形上学”。这样,儒家通过道德性的生化之体直贯下来,自必打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之隔绝,此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义,若以系统言之,则依“自然法则”所成之系统(实然)和依“道德法则”所成之系统(应然)合一,即哲学原型。此时的“自然”,“不复是那知识系统所展开的‘自然’,而是全部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为道德性体心体所通澈了的‘自然’:此就是真美善之真实的合一。”[3](P.152)而康德自始至终缺乏一个儒者的襟怀,遂使他不能有一个“道德的形上学”,只就“自然界”与“道德界”本身着眼,以其抽象精巧的思考去形构,自然“不是一康庄的大道,只有辅助指点的作用,不足以尽担纲的说明”。[3](P.152)
然而在儒家看来,当实践理性充其极而达至“道德的形上学”之完成,则这一个圆融的智慧义理本身是一个圆轮,一个中心点,以康德之语言之,即为一哲学原型。依牟宗三,人若不能提得住,得其全,则这个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个不同的系统或哲学。牟宗三分次其大宗者如下:
(1)上下的开。“道德的形上学”一旦完成,则上帝亦可内在化,人若不能随此内在化而提升生命,则多从人的负面性(如罪恶)与有限性着眼而蛰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威严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态。
(2)内外的开。此圆轮(因其包容一切)本无所谓“外”。此“外”意谓:若转到某处而停滞,并且见到此处有独立性,依着此处而开。在宇宙论方面:“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主义走,建立那客观建构的宇宙论;以20世纪来的物理、数学、逻辑底成就为底子,以美学情调为基本灵魂,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原始基型为接合传统的归宿点。”[3](P.160)此即怀特海式的宇宙论。在存有论方面:“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的独立的存有本身之体会走,建立那客观自性的存有论,上而拉开与宗教的距离,使宗教超然而独存,不与哲学纠缠在一起,内而倒转那自由、无限、神性为中心的方向伦理,展现伦理而为以‘存有’(实有)为中心的‘存在伦理’:面对实有而站出来,把自己掏空,一无本性,一无本质,然而完全服役于实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即真实存在的人”。[3](P.160)此即海德格尔式的存有论。
(3)正负的开。从正面的践仁尽性达到圆熟之境,则一切平平,一切落实,即儒家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实处,只见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胶着于事相上,则易从负面着眼,从“空”、“无”两方面来观察宇宙人生。从“无”方面说:“无”却那相对事相的执着、人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显那自然无为的境界,此即为道家。从“空”方面说:“空”却那事相缘起流转的自性而当体证空,此即为佛教。
(4)最后,践仁尽性而至圆熟平平之境,则“抬头举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知体”即良知本体,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体著见”,而只见到“抬头举目”之生理活动,如是,只去研究这生理活动本身,此即为科学。
牟宗三根据儒家圆融的智慧义理所开列的主要四点,包括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各个方面,这实际上就把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各个不同的义理系统给统摄了进来。这正合康德所提出哲学原型之意,他认为哲学原型可开列每一主观哲学,并可对每一主观哲学作出估计,而主观哲学则是千差万别的。但在哪一个层次上始出现哲学原型,康德却并没有做到;而牟宗三认为,只有在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完成时,始可出现哲学原型。所以,牟宗三归结说:“人生真理底最后立场是由实践理性为中心而建立,从知性,从审美,俱不能达到这最后的立场。”[3](P.162)“如是,我们只有一个哲学原型,并无主观的哲学可言,一切主观哲学而千差万别者皆是由于自己颓堕于私智穿凿中而然。如果它们尚是哲学的,而不自我否定的魔道,则客观地观之,它们或只是一孔之见,或只是全部历程中之一动相,而皆可被消化。由各种专题之研究而成的各种哲学当然是被许可的。然这一些不同的哲学并无碍于哲学原型之为定然,皆可被融摄于哲学原型中而通化之。因为‘哲学就是一切哲学知识之系统。’”[2](P.469)
3.“哲学的可学”之义
依牟宗三之疏解,实践理性(或本心、无限心)之充其极而达至“道德形上学”的完成,这一圆融智慧即是一哲学原型,是则哲学原型非依人的思辨理性而知解之,实则依人的实践理性而朗现之。当然,常人因受感性的牵扯,实践理性很难全幅朗现,是以哲学原型惟赖圣人之生命而朗现。但就实践理性的存有之量而言,则常人于圣人毫发不少,常人与圣人之区别不在实践理性的存有之量上,而在实践理性之开显程度上,圣人因应物而不累于物,故其实践理性周流无穷,常人因应物而累于物,故其实践理性滞于一隅。故常人须“学”,这里的“学”是指依圣人之教开启人之理性并通过各种实践以纯化生命而达至最高的理想之境,是“以自家真诚心与圣人底生命,以及与依圣人底朗现而规定的哲学原型,存在地相呼应相感通之谓也”。[2](P.466)因此,“学”必须是“觉悟”义,“学者觉也”,这便是“哲学的可学”之义。依圣人之教(依牟宗三,此“圣人之教”为惟一能决定“哲学原型”者)而启发人之理性生命而与圣人之生命相呼应相感通,则就历史的哲学事实(圣人之教)而言是“学”,是模仿,似乎是外面给予的;而就“与圣人之生命相呼应相感通”而言,这种“学”却是“觉”,终不是外面给予的。故“哲学的可学”随时是“学”,亦随时是“觉”。“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因此,不觉则已,一觉就是这一套,不能有其他更替,亦不能有任何歧出。主观性格(觉悟)与客观性格(原型)一起皆是定然的,同由一根(无限心)而发,同依一根而呈现。一如在数学方面,教者与学者皆由‘理性底本质的而且是真正的原则’而引生其知识,他们不能有任何其他来源”。[]2(P.465)如是,哲学原型既定,便可通过觉悟而为定然地可学。
最后,牟宗三认为,哲学原型既是实践理性之充其极而立,则无所谓哲学原型之可言,即哲学无哲学相,而只是在与圣者之生命智慧相呼应者之呼应中,上达天德之践履,并在此践履中,呼应者(或学者)便可如如证悟与如如朗现之。也就是说,哲学原型若客观地视之是一义理系统。但既是一系统,就有系统相;既有相,就有限制。这里的“限制”并不是说此义理系统的义理的普遍性有问题,而是说用一定的名言不能说尽一切,此一系统只是一时方便之权说。因此,当我们面对一既成的义理系统时,须要破除其名言上的限制而去体会其义理的普遍性,是之谓“开权显实”。但如何开权显实呢?这不能从系统处着眼,因为再圆满的系统都有相,有相就有限制,因此,开权显实只能从体会义理的生命处着眼。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对此都有深切体会。所谓从生命处着眼即是说:惟有提升了生命境界方能把握此一义理系统。若分而言之,从把握义理系统看,是一知识追求;从提升生命境界看,是一道德践履。若合而言之,则知识追求和道德践履实是一回事。惟有至此时此境,哲学才能真正达到康德所追求的把一切系统统摄到人类理性的终极目的——最高善之下。
三、衡定与评述
我们知道,天人合一乃中国哲学的境界,但其实,无论中西哲学,讲到最后必然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哲学原型),宇宙和人生终究要打成一片,天道和人道究极是要贯通的。就西方哲学而言,自苏格拉底倡导“美德就是知识”以来,即欲扭转人们只对纯粹的自然知识的探究,而欲把知识归属于道德和伦理的目的之下。康德显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提出哲学原型的概念即意在纳知识于道德目的之中。但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康德,他们只是不满于人们只进行纯知识的探索而完全无视于人类的终极目的(最高善)的态度,而他们提出这些理念的思考方式却仍然是在西方知识论传统之中的,例如苏格拉底就把“善”作为一个外在的认识对象而去与人争辩以求得“善”之所以为“善”的知识。但无论是“善”还是“哲学原型”,既然是理性的理念而不是外物,就不能只是认识到了即可了事,它须要在践履中始得落实。牟宗三之所以探讨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即欲扭转康德的思考方式并弥补其不足。在牟宗三看来,康德只是哲学原型义理系统的表诠者,他之所以做如此之表诠乃是因为他正视了人类的理性,而做道德践履的圣人则是哲学原型义理系统的人化者,圣人之所以能人化之乃因为他的生命全部是理性(理性化了自家生命)。正视人类的理性是哲学家的反思工作,理性化自家生命则是圣人的实践工夫,而哲学原型真要落实就不能仅仅只作正视理性的反思工作,因为反思仍是从思辩理性入的,须要从实践理性入而去做理性化自家生命的实践工夫。从为“学”上看,既然学哲学(原型)须要做理性化自家生命的实践工夫,以是,这种学习便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的践履,至此始能真正扭转人们只追求纯粹知识的态度,这正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用心所在。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只能从终极意义上说,否则便会否定知识的价值),依上述之疏解,这应是中西哲学所共许的名言,而牟宗三根据康德所提出的问题而做的这步融通工作,正是要彰显这一共许。只有在这一共许之下,中西哲学的会通才成为可能。而中西哲学也只有在这一共许下的会通,才能以自家的优长来弥补对方之不足(中国哲学的优长在德性之知,其不足在见闻之知,而西方哲学则正好相反)。
[收稿日期]2003-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