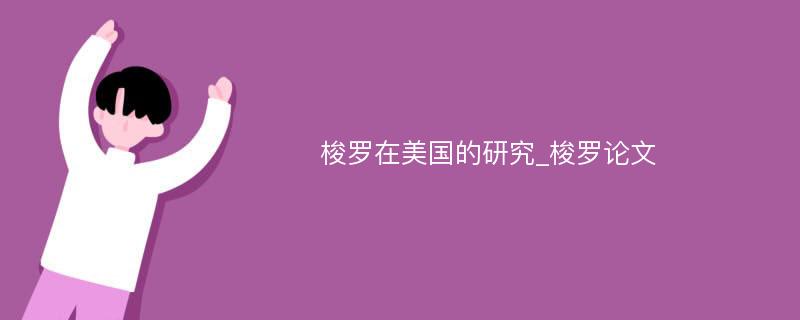
美国的梭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梭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6—0099—05
如果把1862年爱默生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梭罗论”作为梭罗研究的起点,那么美国的梭罗研究已经有了144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对梭罗的认识与接受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与反复,但是今天,梭罗已被公认为美国经典作家。在为新普林斯顿版《瓦尔登湖》所作的序言中,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认为,就19世纪美国文学经典作家——霍桑、惠特曼、爱默生、麦尔维尔而言,梭罗对美国的思想与文学贡献最大[1]。如今,研究他的各种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学术团体有成立于1941年的“梭罗研究会”(Thoreau Society)和成立于1975年的“梭罗研究所”(Thoreau Institute),学术杂志有《康科德漫步者》(Concord Saunterer),《梭罗季刊》(Thoreau Journal Quarterly),《梭罗研究会报告》(Thoreau Society Bulletin),《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等。
在美国文学史上,梭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曾引起各种观点不同的批评。最初,美国作家J·R·洛厄尔(Lowell)和英国作家A.E.史蒂文森(Stevenson)等都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只不过是对爱默生的模仿,一个业余自然主义者,充满野性的懒汉[2]。虽然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与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ester)等早期学者肯定了梭罗的艺术成就,认为梭罗一生追求的是真、善、美,但是他们也认为梭罗的设想和经验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道德和美学来看都没有产生最大的效果,因为他只沉湎于自我之中,而没有放眼宇宙[3]。
梭罗研究的最大转变出现于1941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F·O·马西森发表了《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与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现》,从语言和文体上对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五位作家做了影响深远的研究。马西森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和H·L·门肯,弗农·帕林顿(Varnon Parrington)等学者一样,认为文学批评离不开历史意识,十分热衷于解决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冲突。他对T·S·艾略特的“感受力的分离”一说很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这是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体现。当时,美国还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马西森对纳粹极权统治对西方民主价值的威胁分外担忧,希望通过遴选美国文学的经典文本来强化国民反对纳粹的士气。在《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与惠特曼时代的艺术与表现》一书中,作者将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的乐观精神与霍桑、梅尔维尔的悲剧论调进行对比,并将美国文学中的过去分离出来表现当时的两种文化潮流,从而将美国的经典作家从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分离出来,重新放到他所设计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内。这本书既标志着作者与帕林顿、布鲁克斯等文学史家经济社会要素论的分离,同时又与当时的新批评派保持一定的距离。马西森认为新批评学派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必要增补,历史主义过分强调过去的文化价值,忽视现在的价值,以牺牲现在为代价,而新批评则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寻求平衡,在此背景下,马西森希望通过挖掘过去来认识现在的内在价值。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再加上他本人又是一个对历史与文化深切关注的学者,因此,马西森教授想完成两项工作:一是重新定义美国文学,提高美国文学的传统,二是通过定义和挖掘美国经典作家,挖掘出遭到极权主义者威胁的极其有价值的文化传统,通过吸收过去的文学名著,将之运用到当时的历史发展环境中,运用活生生的传统来维护民主价值。在此书的序言“方法和范围”的结尾,马西森说道,真正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应该是“用来为人民大众谋取幸福,启迪人民大众,而不是用来纵容某个阶层的人……在一个民主社会,检验公民权利的基本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是运用天赋来支持还是反对人民。”[4] 其中更是把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解读,他的解读得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的详细论证,也使得梭罗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
从50年代开始,美国的梭罗研究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现象,大体经历了传记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生态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而且各种研究中还体现出了彼此的交叉性。
一、传记研究
1873年,梭罗的好友钱宁曾写过一本梭罗的传记,《梭罗:诗人—自然主义者》,记载梭罗的生平。后来,贾普、马布尔、索尔特、桑蓬等都写过梭罗的评传[5],但是真正具有影响的却是谢尔曼·保罗1958年发表的《美国的海岸线:梭罗的内心探索》,在这部传记里,保罗强调他所书写的是一部“精神传记”,解读的是梭罗的作品而不是梭罗的生活。他关注的是书写的文字,自我生活的写照。他主要关注的就是“梭罗内心生活的逐渐发展”。保罗认为,梭罗追求的就是在自然中实现自我。保罗的工作就是让人们理解梭罗的生活目的和作品主题。50年代美国的批评思潮依然受着新批评的影响,因此保罗即使在评传之中也依然强调梭罗的文本意义,不过他已经注意到了梭罗的内心世界,并且竭力想挖掘出梭罗的心路历程[6]。 但对梭罗生平和文本勘订投入最多的则是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他是一名一生致力于梭罗研究的学者。曾经是梭罗研究会的主席。他个人收集的梭罗研究资料就达到15,000种之多。在以往的研究中,评论比较关注的是梭罗的创作生涯,而哈丁则将关注焦点集中到梭罗这个人身上。在《梭罗的日子》(1965)一书中,哈丁着力去还原梭罗这个人,将他从社会和评论界所蔑视的怪人、隐居者形象中解脱出来。作为梭罗研究会的创始人和终身会员,哈丁对塑造和巩固梭罗的文学形象起了很大作用,并对确保梭罗传记和梭罗作品的准确性产生了很大帮助。经他之手编辑的梭罗材料就有:《梭罗的日子》(1965),《亨利·戴维·梭罗通信录》(1958),《梭罗手册》,《梭罗:一个世纪的批评》(1954),《亨利·戴维·梭罗:研究与评论集》(1972),《新梭罗手册》(1980),新版《梭罗日记》(1984),《同辈眼中的梭罗》(1990)等。因此他的传记材料和校订的梭罗文本对梭罗研究者来说收益匪浅。
二、文学研究
马西森早年的梭罗研究是将他放在美国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潮中去加以分析和研究。从1974年开始,评论界开始接受比较学派的影响,从欧洲浪漫主义的语境中去研究梭罗的思想,其主要代表是麦金托什教授。麦金托什《作为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者的梭罗:他对自然态度的变化》延续了浪漫主义研究的传统。书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探讨早期的梭罗。麦金托什的研究表明,他关注的是梭罗的自然意识,并且最终认定梭罗和其他19世纪中期的美国作家一样,关注的是一种新的人类认同观。自从谢尔曼·保罗的作品发表以来,梭罗被视作“筋肉”,而爱默生则是他身后的“大脑”,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但是这一次,剧情换了。爱默生出局,歌德走了进来。充满戏剧色彩的唯心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开始出现。在多重浪漫主义理念的基础上,麦金托什区分了“浪漫主义的反自然主义者”和“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前者如布莱克、雪莱和费希特,后者如歌德、华兹华斯和谢林。从精神上来说,梭罗与后者心心相印。反自然主义者“或忽视自然风景或审慎地爱着它。与此相反,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者感到分离的思维(separated mind)对自然所产生的彻底占有的欲望导致的是对已经观察到的世界所产生的一种自私和危险的曲解,减少了他们的生存源泉,是对他们需要的一个上帝的扼杀的方式。因此他们试图将想像与自然融合起来,不是为了控制自然,也不是彻底改变它;他们是在心智和自然之间寻求一种想像中的平衡”。[7] 麦金托什关注的焦点就是体现在梭罗身上的这种心智与自然二分法。自然与想像之间的分离意识经常成为梭罗艺术的主题。麦金托什写道:“综观整个研究,论点的关键就在于浪漫主义自我意识必然将浪漫主义观察者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无论他是多么后悔这一分离……对梭罗而言,自然与心智,或精神,或自我,或想像之间存在着一个变化不定的区域。[8] 梭罗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挣扎。麦金托什认为,梭罗强调的是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这一古老观念,因而走得比爱默生、科勒律治,甚至华兹华斯要远。他十分醉心于“自然内富有创造、不断变化的活动”。[9] 他想入世,但事实上他面临的是分离。他的思想一直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这也是此书的亮点之一。
后来,弗雷德里克·加伯教授延续了这种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研究。在1977年发表的《梭罗的赎回性想像》中,加伯教授对梭罗的日记等比较散乱的作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将梭罗的思想发展史放到欧、美浪漫主义语境中去加以考察,认为梭罗既不是爱默生的学生,也不是卢梭的门徒,而是他自己,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他的内心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一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冲突。虽然梭罗描写了自然的循环变化,但是这种更迭并没有解决他浪漫主义追求中所出现的内心深层次冲突。[8] 而亚当斯和罗斯借用梭罗的作品《瓦尔登湖》中“冬天的访客”一章中的一句话来命名他们的研究。在《修订神话:梭罗主要作品的创作》中,两位作者合作阐述了他们的主张:第一,关注梭罗的文本修订阶段;第二,收集梭罗所运用的神话,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编造出来的,作为理解的一种手段和阐发主题的一种媒介。第三,强调梭罗对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目标和艺术程序的投入。两位作者对各个文本的主题、结构、修辞所做的仔细分析贯穿着作者对文本阶段和创作意图的研究,在亚当斯和罗斯的描述中梭罗各个作品之间彼此对应。亚当斯和罗斯与大多数梭罗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在1851—1852年之前,梭罗在其偏爱的论题和体裁、对上帝的再现、人与自然或诗歌与想像的构思中,并非一个浪漫主义者或超验主义者。相反,他的方向是新古典主义。在创作了《瓦尔登湖》后,他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于是开始皈依浪漫主义,衷心拥护爱默生、华兹华斯、科勒律治的思想。这一皈依促使他对瓦尔登湖的经历进行重新修订,在修订了C版(1849)后,发现和认识到他的理想形式——一种追求浪漫主义,其英雄成了一个具有远见的神话创作者。[9]
三、哲学研究
美国浪漫主义的代名词就是超验主义,作为欧洲哲学思潮的一个演化,超验主义影响着美国19世纪的思想和文学创作。1972年,卡维尔教授开始从哲学角度去研究梭罗,从《瓦尔登湖》中找出美国的思想和作者的创见,将他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中解救出来。卡维尔教授认为梭罗的作品对黑格尔和康德以降的欧洲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和修正。这并不是要分裂,而是要表明哲学思想的延续性。作者认为《瓦尔登湖》涉及的是西方哲学从笛卡儿至今西方哲学中最深层的问题,为此,梭罗十分看重语言,语言不仅是梭罗传递其超验主义真知灼见的手段,或创作充满诗意的散文的工具,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涵,意义深远。[10]
此后,每隔10年都会有一部从哲学及语言的角度去探讨梭罗作品的专著。沙伦·卡梅伦教授1985年发表的《书写自然》可以看作是对卡维尔教授哲学解剖的后现代回应。对卡维尔来说,梭罗的语言就是再现经验,其最终结局就是自我与世界融为一体,而对卡梅伦而言,语言就是经验本身。卡梅伦对梭罗的大量日记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在日记中人们可以发现,“自我”被重新定义成外部关系的客体,遭到了抹杀,而这一抹杀带来的是对浪漫主义自我与自然等理论的一大解构。卡维尔的观点可以说是后浪漫主义,而卡梅伦的姿态则是解构浪漫主义。[11] 同卡梅伦教授一样,评论家们的研究范畴开始扩展到《瓦尔登湖》以外的作品上。在《梭罗的清晨工作:〈河上一周〉,〈日记〉和〈瓦尔登湖〉中的记忆和感知》,佩克教授认为梭罗通过书写自然来获取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和记忆补偿,探索三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谓清晨工作,佩克概括为记忆和感知的工作,因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梭罗的宇宙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至少有三点他们是认同的:1.他们一致认为梭罗是一位哲学思想家,其思想和过去与现在的人类经验密切相关,这一定位使得他们的论述不同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叙述,因为后者主要是如何给梭罗定位;2.他们给梭罗的作品重新定位,认为他的作品是一种心智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陈述(这里面明显见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3.他们研究梭罗作品的着眼点就是关注他们哲学定位的内在戏剧性。[12]
四、生态学研究
早在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利奥·马克斯教授就注意到了梭罗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与现代技术问题。在《闯进花园的机器》(1964)一书中,马克斯教授注意到了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注成了他一生研究的课题。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技术决定论者的一个分水岭,越南战争、酸雨、全球变暖等现象说明技术本身并不推动历史,相反,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人,就是人如何做出决策去利用技术,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新技术有可能掩盖结局的选择。马克斯认为,在梭罗的作品里,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梭罗的作品体现的主要是西方田园文化传统,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化倾向对传统农业的侵蚀,认为现代工业是跑进花园中的机器。[13]
哈佛大学的比尔教授综合了已经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涯,并对环境问题体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心,被人称作生态批评的教父。1995年,比尔教授发表了《环境的想像》一书[14],延续其早期对美国超验主义研究中的观点,但更加注意自然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由于虚拟世界和科学技术的出现,美国人开始同自然疏远。实际上,比尔认为“田园想像”能够颠覆以人为本的思想或至少为生态中心价值铺平道路,认为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好好地生活,就应该学会更多地从生态意义上去思考问题。比尔教授的研究显然受到了后现代、解构、重构、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将研究视角从文学理论扩展到了思想史和人文思潮中,他的研究目的就是从美国文学传统中引导出对生态问题的注意,希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帮助美国人摆脱帝国主义、欧洲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的思想,使美国人想像出一个更为和谐的与自然相处的环境。
五、文化研究
文化上,学者们从心理学、文化研究等角度对梭罗进行研究。约翰逊[15] 教授从现象学的角度去分析梭罗,认为《瓦尔登湖》并非是一部只对切身经验感兴趣的“感官日记”,也非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实用指南,而是一部主体(作者/读者)在客体(世界/文本)中找到自我的一种文本表现。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仔细勾勒出梭罗的观点,从中找出非二元、互为关照的视角,在其中,人类的感知和事实的本质元件融为一体,从而揭示物质、科学和精神观都是认识者感知行为中彼此互补的组成部分。约翰逊教授因而认为《瓦尔登湖》是部阐释学文本,因为它培养和强化读者阅读时的感知能力,将阐释问题融进方法论中。和丹尼尔·佩克教授一样,约翰逊教授认为现象学研究法是走出后结构主义丛林的唯一途径。
罗伯特·米尔德[16] 教授结合心理学家爱里克·艾里克森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观点,在精神分析和文本细读方法中寻求平衡,从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社会进程和文学形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研究梭罗,认为梭罗的写作植根于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居住的康科德镇这一微观世界和他个人天性的内在需求,是作者调停他与市民同胞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理想自我,从而为实现该种自我而在语言修辞方面的努力。作者不同意梭罗后期的创作开始衰退的观点,认为梭罗的创作是一条上升的弧线。《重塑梭罗》既是研究梭罗如何通过变化文体来实现其抱负,从而重新想像自己,同时又探讨了他如何在作品中通过牺牲美学意义上的完整性来体现自己的重新塑造自我过程,因而开拓了梭罗研究的视野。
在《经济学家:亨利·梭罗与企业》一书中,诺伊菲尔德[17] 认为《瓦尔登湖》是对成功指南之类习惯做法的严肃戏仿。为了验证这一点,诺伊菲尔德重新构建了日益变化的梭罗工作的社会和文学语境。他追溯了康科德镇如何从沉睡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熙熙攘攘的商业城镇,并探讨了梭罗对这一转变所持的模棱两可的心态。然后,诺伊菲尔德又追溯了梭罗对《瓦尔登湖》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仔细探讨了他的讲演稿“没有原则的生活”,借以说明梭罗如何将他正在浮现的商业文化中的企业价值与他自我耕作的非传统的个人经济观点进行对比。在书的结尾,他还运用《瓦尔登湖》中的战略来戏仿传统惯例。词汇与语义操纵;重新将经济构建成词汇术语和与其他术语相关的概念;还有打破常规,运用第一人称面具的修辞表演。诺伊菲尔德综合了社会史和思想史中的技巧和素材以及后形式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评。作为一个持不同意见者,梭罗不可能逃避语言,而且也无法逃避权力的束缚,但是诺伊菲尔德认为他的语言有其局限性,因而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揭露或从语言逻辑或修辞手段去消除历史上的伪事实的责任与义务。诺伊菲尔德最终强调《瓦尔登湖》中刻意采取的不稳定性和戏仿者面临的局限性。
在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还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探讨梭罗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1931年,阿瑟·克里斯蒂首先披露了梭罗跟印度、波斯和中国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后来,莱曼·卡迪在《美国文学》上发表文章,罗列了《瓦尔登湖》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引用[18]。但是探讨东西方文化互动的优秀研究论著当属艾伦·霍德的《梭罗的狂喜式目击》。霍德正确地认识到,梭罗对亚洲信仰的了解非常浅薄,但是这些了解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印度教的兴趣。而亚瑟·维尔修斯的研究则清晰地描绘出了亚洲思想对梭罗的影响。[19] 不过他认为亚洲的精神理念对梭罗的后期创作没有产生影响的说法则遭到了不少评论家的质疑。比如艾伦·霍德就认为,梭罗最深切的关心是精神问题,如果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对阐释他的生活和作品就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霍德是一位比较宗教学教授和新英格兰文学学者,他的研究构筑了一个梭罗精神发展的叙述。他认为梭罗的精神基础就是“灵感和自然世界的欣快经验,他将此习惯地称之为狂喜”。[20] 年轻的时候,这种狂喜自发地来到他身上,尤其是在听到自然的声音和音乐之后。1840年起,他发现了佛教和印度教文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文本帮助他理解了自我超越和自我丧失时的狂喜时刻。霍德探讨的东方对梭罗的影响揭示了19世纪初“东方复苏”中所蕴涵的十分复杂的文化意义。霍德不同意谢尔曼·保罗等人的观点,即1850年之后梭罗陷入了因禁欲而加深的精神危机。相反,霍德认为梭罗在审慎地挖掘自己的精神,直到他进入一种顿悟式的超然境界。
收稿日期:2006—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