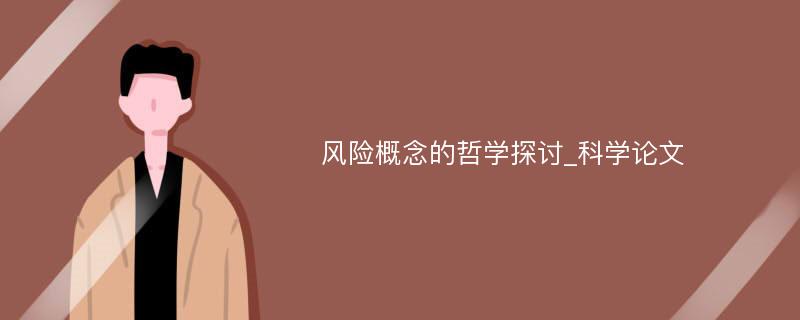
风险概念的哲学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哲学论文,概念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7-0071-08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已经成为人们需要经常面对的重要事务。现代社会生活无论形式与内容都空前丰富,但在显示“强大”外象的同时,又“矛盾”地呈现出非常“脆弱”的一面。人们几乎每一天都自觉不自觉地评估着各种风险,在利害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人们如何认识、理解、评估、接受和管理风险与现实生活当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生活(态)环境维护、交通体系安全、食(药)品质量保障等方方面面息息相关。
很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都关注风险及其相关问题。虽然各个学科对风险的理解侧重点不相同,但所有风险的概念都有一个共同前提: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考察风险。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都与风险具有关联,这其中既有来自自然界的、不可抗拒的灾害,也有人类自身引发的能源、环境、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电磁辐射、食品安全等危机与隐患。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风险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有时人们对于这些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见(期),应对措施缺乏充分的准备,破坏后果缺乏完整的认识。同样对于学界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理论及研究挑战。风险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又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风险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厘清和把握准确的风险概念对于后续诸多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容易引发后续活动的冲突。“一个有效的决策过程,无论个体还是社会作出的,在基本术语方面需要取得一致。没有这些概念上的澄清,就会出现混乱和错误的沟通。”①
一 风险概念的多元表达
当今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崇尚追求更安全、舒适、健康和便利的生活。在这些生活目标逐渐实现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相对于以前的时代,人类也不得不面对和应付影响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来自各方的威胁和风险。在自然环境意义上,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不计后果地“掠夺”自然资源,造成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科学技术方面,追求技术的创新促使研究人员不断取得科技突破。这些科技突破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有利于人类朝着美好社会的理想前进。但不可否认,有些高科技应用到人们生活之后,直接带来或潜藏着难以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危害,人们为此将会或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核电站放射物质的失控、核武器的威胁、海洋石油开采的泄漏、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的隐患、移动通讯设备的辐射、生物技术中的生命制造以及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病毒和漏洞,等等。
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未曾有过的风险。幻想放弃现代科技或者阻挡现代科技的潮流都是无法行得通的。对于社会和公众来说,更加切近实际的是,思考和追问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生存论意义和价值。斯塔尔(Starr)和惠普尔(Whipple)甚至将此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他们在1980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上的文章说到,“确定哪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议题。”② 承担风险是现代人在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或许人们现在并不能完全确认风险在什么时候发生、规模多大、影响多广、程度多深,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社会必须做好应对以及付出代价的准备。
现代社会风险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风险研究首要面对的问题是风险的概念问题。这个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准确回答。什么是风险?风险的定义是什么?学界没有统一的意见。比如,按照罗萨(Rosa)的看法,“虽然关于风险主题的研究文献仍然在快速增长,但事实上很明显人们对于风险意味着什么很少取得一致。”③ 奥尔索斯(Althaus)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总结了风险的理解④:科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客观现实;人类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决策现象;心理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行为和认知现象;艺术(包括音乐、诗歌、戏剧等)把风险看成是一种情感现象;历史学把风险看成一种讲述(story)。埃文(Aven)和雷恩(Renn)也认为“没有一致的风险定义。如果我们考察风险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风险概念被用作一个期待值、一种概率分布、不确定性以及一个事件。”他们还总结了十种风险的定义:“(1)风险等于预期的损失;(2)风险等于预期的失效;(3)风险是某种不利后果的概率;(4)风险是不利后果概率和严重性的测量;(5)风险是一个事件和其后果概率的混合;(6)风险是一系列事态,每一种都有一个概率和一个后果;(7)风险是事件和相应不确定性的二维混合;(8)风险指结果、行为和事件的不确定性;(9)风险是一种情景或者事件,其存在使人类有价值的事务处于危险之中,且其后果不确定;(10)风险是与人类价值有关的活动及事件的不确定的后果。”⑤
虽然风险概念很多,各学科也有自己不同的风险理解,但总体上可以从三个大的维度来概括:第一是时间维度上的未来指向,比如概率和预期值。风险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预见的、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第二是结果维度的消极指向,比如,事件/后果和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两个方面,客观属性体现为事件发生的频数,主观属性体现为当事者价值损失的程度。第三是行为维度的情境指向,如人的现实活动。风险需在实际情境中现实化、具体化。
从哲学的角度看,对于风险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技术的取向和文化的取向。技术取向和文化取向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关于风险概念的不同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观点。这两类不同取向的风险概念对于风险评估、沟通、接受与管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风险研究中可能最根本的分裂在于两种矛盾的风险概念的支持者之间。一方将风险看作客观给予的,由物理事实所决定。而另一方将风险看作独立于物理事实的一种社会建构物。”⑥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将风险看作一种物理现象,也即一种与主观价值相分离的客观事实。将客观地指称物理世界环境作为解释风险的出发点,把价值判断排除于社会风险之外。风险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概念,具有物质的实体性,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到有效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斯塔尔和惠普尔等人是这种风险概念的典型代表。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将风险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也即一种与主观价值(道德、世界观、行为模式等)紧密相连的社会建构,突出强调在风险形成、评估等过程中价值判断、道德信念等所起的重要作用。风险是一种集体的建构物,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过程。道格拉斯(Douglas)和怀尔达沃斯基(Wildavsky)等人是这种风险概念的典型代表。
二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
斯塔尔1969年在《科学》发表的《社会收益与技术风险》和斯塔尔与惠普尔1980年合作在《科学》发表的《风险决策的风险》这两篇经典论文可以看作是风险概念技术向度的代表性论述。“风险方面的文献非常之多,其中涉及到科学、行业和政府组织同普通公众在风险感知理解上不匹配的问题。斯塔尔1969年的经典论文首次从科学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⑦ 在学界系统化研究风险之初,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主要采取的是技术取向。当时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多安全才算足够安全”,即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确定可接受的风险的水平,以帮助做出恰当的风险决策。
斯塔尔认为⑧,历史地看,通过尝试、犯错误和随后的纠正措施,社会已经在技术收益和社会代价之间实现了可接受的平衡。关于技术收益和社会代价,斯塔尔提出了一种量化的测量,采用历史上经济风险和利益的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斯塔尔所选择的社会代价也即物理风险的表现指标是公众所从事活动的事故死亡率,并且这些活动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所选择的技术收益的表现指标是金钱等价物。这种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即一种新科技的可接受的风险被定义为与不断发展的活动有关的安全水平,这些活动对社会有着普遍的利益。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坚持从“科学”的方式出发就可以揭示事实、消除影响、平缓公众的不安甚至恐惧心理。这种技术思维的背后暗含的是每个个体为“理性行为者”的预设。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统一一致的科学精细分析面前,为什么不同的人对风险有着不同的反应?心理学家对此问题十分感兴趣,并以此为着手点开展风险的相关心理学研究。菲什霍夫(Fischhoff)等人⑨ 将斯塔尔提出的风险分析方法称作“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方法。他们提出了另一种风险分析方法,叫“表现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采用问卷去测量公众对于不同活动的风险和利益的态度。以菲什霍夫和斯劳维克(Slovic)为代表的心理测量范式延续了风险概念的工程技术思维,但有所不同的是,心理测量范式在社会科学的范围里,纳入了更多的因素考察风险。
风险分析的早期研究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哲学思维方式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尽管其后陆续有其他的范式出现,但实证主义的范式一直处于重要地位。风险概念技术立场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科学活动是客观的,科学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事实,与价值判断无关。只要遵循科学的形式和逻辑,风险评估(理解)就能够在科学范围内不依赖其他因素(社会、文化、政治等)而纯粹独立地进行,其结果是普遍和有效的。“在风险领域保持着一种广泛接受的信念,现实的风险数字可以随着特定技术、事件或者活动的逐渐精确而被计算出来。这种主导的流行态度促进了技术评估重要性的提升。”⑩
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表现出以下特征:
(1)本体论预设是客观主义或称作实在论。世界独立于观察者的感知而存在,外部世界的属性与人的存在无关。风险是真实的、客观的,独立于主观知觉。风险是纯粹事件或者事件后果的概率问题。概率的估计就是风险的本质,即风险等同于消极事件及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理解风险就是理解概率及其相关物。按照斯塔尔和惠普尔的观点,对事件概率的认识是认识风险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对风险而言,概率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问题。
(2)认识论预设是:风险扎根于现实世界,风险就是即将来临的、有形可见的、致人负面影响的危险、危害、威胁或者损失、损害。因此适用科学的追问方式。作为客观现实的风险可以不受主观影响地进行客观的标准化测量,可以通过系统的科学方法进行测量、控制、预测与管理。风险成为科学方法可以探索与测量的对象,风险评估于是也就成为关乎科学事实和相应概率的科学问题。
(3)价值论预设是科学理性至上。风险涉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判断。人们经常面临选择的情景,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种情景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决策判断不可能包含所有结果的信息,因此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就涉及到“应生”风险。专家基于真实风险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分析地研究风险,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等;公众则基于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主观、非理性、直觉地看待风险。专家与公众不同的风险认知反映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高度复杂、技术化的社会,专家和公众对“风险”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早期对风险的理解是从工程技术思维出发的,在工程安全体系进行风险分析时,将风险看作消极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后果(包括范围和严重程度)。工程技术思维中尽管认识到风险评估蕴涵价值负载,但在实际当中往往忽视或者难以兼顾价值意义。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进行风险评估时往往容易从“风险认知”滑向“风险现象(事实)”。风险的工程思维即从技术的角度分析风险存在一些缺陷,也受到了不少批判。
从消极影响(结果)可计算性来讲,消极影响(结果)不是简单的客观存在,当事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文化传统、行为习俗等会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结果评估、风险接受等。仅用经济指标等量化消极影响(结果)过于简单。同时,现代社会一些风险事件的形式与内容非常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最主要的是消极影响(结果)往往超越“时空”边界:空间地域渗透力强、辐射面广,时间广度延展性高、后续性强。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越发加剧,信息传播迅捷、人员流动频繁、事务联系紧密、传统“边界”消融,这些特征决定了现代风险的消极影响(结果)未知情况突出,传统技术分析的概率值、伤亡率、经济损失情况难以对消极影响(结果)进行全面计算。数字所把握的抽象图景远不能详述具体的现实状况。“在一些领域,新风险的诸多特征使得通过概率估算获得对风险的充分分析完全不可能。……技术—理性范式的真正危机源自于一种分离的社会—政治的发展。”(11)
从风险应对和管理的角度上讲,在面对重大突发性灾难时,相关行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制度安排、行动效果容易暴露出缺陷和失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极有可能加大风险事件的消极后果。风险的技术分析往往忽略“制度错误与风险”之间关联这个重要方面。任何理论都有其有限的“边界”,风险的技术分析也同样如此,它也不应当成为风险的确认、评估和管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化风险分析的框架具有它的局限性。技术化的风险分析有不足之处,但也有自身价值。无论是自然灾害、突发事故,还是社会动荡、人为祸患,人们都是在现实而具体的情境中遭受风险事件,承受相关后果。风险的技术分析能够提供预期或已然的物理损害和经济损失的科学数据,为相关风险管理部门的决策以及相关当事人的行为选择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保障所有当事人及社会的利益。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可以提供模型,为未来风险事件的评估、应对与管理奠定基础。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专家的技能知识以及专家系统的运作体系应当得到尊重和信任。如果出现广泛的对专家系统的不信任,那么对整个社会而言,必将出现更大的混乱,更是一场灾难。对风险的技术分析应当持有乐观的心态,不仅不应停滞反而更应加强风险的技术分析的研究。认真对待风险的技术分析的有限性,而非一味彻底否定风险的技术分析是理智的做法。
三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
风险的科学评估与公众的风险感知之间存在裂隙。这些裂隙的原因在起初阶段往往被归结为公众的知识局限或者公众的非理性观念。为什么这样归因呢?因为相信科学能够提供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但实际情况是,科学在提供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方面并非无可挑剔和没有犯错误的可能;而且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也只是理解风险的一些方面,不是全部方面。精确的计算和确定无误的事实之外的方面更主要是人们现实的生活体验和生活价值,生活体验和生活价值突出的特点是主观性很强,这些主观性容易被划归成公众的知识局限或者公众的非理性观念。然而很清楚的是,体验和价值来源于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生活经历,它们有着广泛的渗透力和强大的说服力。与科学提供的相关“概率”或“不确定性”的抽象数字相比,生活的原发性要丰厚许多。专家与公众有着不同的风险理解思维。卡斯普森(Kasperson)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风险研究既是一种科学活动,又是一种文化表达。”(12) 津恩(Zinn)等人也认为“随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认识到风险感知中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13)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主要是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来推动与完成的。关于风险问题,心理学家的研究起初集中在决策制定领域。风险在工程技术专家看来是技术计算的问题,而在心理学家看来却是做出决策的问题,并且认为做出这些决策具有普遍的法则。心理学家希望知道人们是如何感知风险的,并主要从风险属性的角度研究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力图找到稳定的风险感知的模型,从而能够预测和解释人们对风险的行为反应,确定人们接受风险的水平,并为社会政策的决策制定提供意见。
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怀尔达沃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化理论有力促进了风险概念的文化理解。(14) 文化理论认为,影响人们感知和作用于周围世界的重要因素是文化,具体说就是社会面貌(social aspects)和文化信念(cultural adherence)。文化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特殊能力,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现实生活环境中逐渐培育和养成的。在现实生活环境中人类感知世界的各种事物,获得丰富的经验积累,这些经验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来,繁衍生息。人们把这些生活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通过语言、文字、习俗、制度、信仰等方式将生活经验象征性、符号化地加以固着,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代际间的继承与传递。这个过程就可以看作是文化。文化既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风险认知与人们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学习紧密相关。
在文化理论中“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决定“生活方式”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维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共同秉持的文化立场;行为偏好的策略。隶属于特定社会关系模式产生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一种“文化立场”。反过来,隶属特定的世界观和文化立场将带来相应的社会关系类型。可将文化划分成四种类型:(1)等级文化(hierarchist),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组织界限,高度合作,事先制定好规则和程序;(2)平等文化(egalitarian),特点是高度的团队参与决策,倡导参与、授权和过程;(3)宿命文化(fatalist),特点是合作少,规则限制管理,集体行动缺乏承诺;(4)个人文化(individualist),特点是个体对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低的责任感。文化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原则,从理论上论证文化信念和社会学习如何影响人们感知和理解风险,试图说明个体如何形成对危险的判断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认为,科学活动不是脱离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而存在的,它与主观的价值判断有着关联。奥特维(Otway)认为,“利用形式方法尽可能地达到客观也不会模糊这个事实,对大多数风险而言都重要的是,风险的客观成分里仍然包含一种很强的主观元素。”(15)
风险概念的文化取向表现出以下特征:
(1)本体论预设是主观主义或称作建构论。世界就是我们所解释的世界,所有的知识都是主观的和再解释的。风险不是作为现实的客观事实而存在,风险是由社会建构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而存在的。没有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现实(实体),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是不可分离的,也不可能脱离任何一方解释对方。风险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一种物理现象,也不是社会所定义的种种危险的“看台”。风险不等同于危险,“尽管危险是真实的,但风险是社会建构的。”(16) 社会建构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完成。作为主体的人将相关事务确立为风险。其间发生的意义与解释不仅体现当事人的状况,而且体现蕴含价值观、符号象征、历史及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概念。人们对什么东西害怕、恐慌以及如何表现出害怕、恐慌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这种主观选择与人们所处的文化中的社会关系相一致。在此意义上,风险是社会建构的过程。
(2)认识论预设是,风险的本质特征不是一个单一的属性。风险不能看作独立于人的经验、认知、道德立场及行为模式的一种纯粹科学事实。按照概率、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不能够完全理解风险。风险认知依赖于情景,风险是诸多属性的混合体,如意向性、自愿性、概率和公平。技术立场的风险概念认为风险是“遭遇伤害、蒙受损失和发生损害的机会”。同时,风险所体现出的未来时间指向上的概率大小以及未来结果消极影响的程度均可以通过物理的过程、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进行测算,也即所谓风险评估。文化立场的风险概念认为,脱离社会和文化情景无法全面理解风险。风险不是外在于文化及作为主体的人而存在那里的,风险是内在主观的。风险形成及体现在社会互动及文化中,反映出制度设计、个人及群体信仰体系。
(3)价值论预设是,形成对危险的诸多判断与社会文化情境密切相关。有些风险被错误地放大,而有些风险无人问津,文化理论就是要解释风险是如何被建构和被选择的。风险不仅是安全问题,更与权力、正义和法律不可分割。任何特定个体观念的形成都受制于他所属的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对风险的态度、风险判断、社会正义的模式、责任政府均放至于文化关系当中,即人们所属各自群体的期望和价值系统。公众理解风险不只是不确定条件下的概率或决策过程,公众的风险经验与专家的定义和概念范畴也不全然一致。风险建构是一种学科的混合体,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强调风险评估的主观反应以及风险现象发生的情景。
文化理论将风险看作一种社会过程,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于文化的集体意识当中。风险不是物理现象,不存在于客观现实当中。风险的文化理论优点在于有很强的概念包容性,将风险选择、客观性、科学、理性、公众认知等涵盖进来。但文化理论的缺点在于风险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界限模糊,体现出还原论和决定论色彩。
四 走向融合的风险概念
可以用“科学的逻辑”和“生活的道理”来概括风险的技术分析的特征。也就是,风险的技术分析的优点表现为专注于“科学的逻辑”,而缺点是忽视了“生活的道理”。所谓专注于“科学的逻辑”,是指进行风险的技术分析时,专家对于消极后果的确认标准、概率概念的认定、概率与后果程度的考量等方面遵循了学科要求的严谨性和学术规则。所谓忽视了“生活的道理”,是指在学科要求的严谨性和学术规则之下,对于消极后果的确认标准、概率概念的认定、概率与后果程度的考量并不能完全和充分地表达个体以及社会所经历风险的现实体验和生活内涵。与风险相关的许多现实因素没有包容进风险的技术分析当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界出现了对风险技术分析的系统性反思,90年代以来从技术与文化两种取向相融合的角度理解风险概念成为明显的趋势,进入2l世纪这种融合的趋势依然是风险研究领域的主导特征。邓肯(Duncan)在考察社会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原子能的社会影响的几十年历程之后,提出“存在一种稳定的进化,在这当中问题首先被定义为科学的和技术的,随后被定义为经济的,再之后被定义为本质上是社会的和政治的。”(17)
总的看来,从技术与文化相融合的角度理解风险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是基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考虑。引入价值或者说重视价值是相对于工程(计算)思维而言的,其最终指向又与政策决策、制定及实施有着重要关联。最初阶段从技术角度理解风险有着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随后一个非常直观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为何在工程思维中价值维度容易被忽视、省略和遗忘呢?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理解价值(或者说价值观)以及它们如何在风险感知中显现出来。价值的显现与风险的属性紧密相连。价值维度内涵同样丰富,并且价值维度并不排除科学概率,需要从两者对立思维转变为互补思维。工程思维忽视价值维度,价值维度又容易自视优于并先于科学测量。价值层面的因素如何融入风险的技术分析是一个难题。风险的技术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活动,秉持传统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中立(value-free)”的观念。因而通常将价值层面的因素排除在风险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认识到价值因素的重要性,但在选择指标将价值因素在风险表达、测量和解释时显得“粗糙”,如仅用金钱来体现价值因素。
雷思认为,风险是一种心理建构物,风险的概念化有多种建构原则,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各种的风险概念。不应抽象地探讨风险观念,而应当在风险治理等活动中,以具体实务内容为载体、从事实与价值相兼容的角度来理解风险。风险治理涉及风险感知、风险分类、风险评估、风险沟通等一系列环节,其中判定风险的“可容忍性”和“可接受性”是重要内容。而判定风险的“可容忍性”和“可接受性”既要基于证据要素,又要基于价值要素。风险实务的整个过程应当以科学分析为主导,包括自然(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18)
汉森(Hansson)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角度认为,风险既负荷了事实也承载着价值,包含客观的和主观的元素。正确把握风险概念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晰与风险相关联的事实与价值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技术取向的风险概念看重的是与价值分离的“客观事实”,文化取向的风险概念则强调事实与价值不可分离。基于一些科学哲学的思想,汉森认为科学活动可以区分为“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价值。“认识论的”价值指对科学知识本身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比如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对科学论证的一丝不苟,对科学解释力的不断深化,对任何科学错误和瑕疵的零容忍。“非认识论的”价值指与科学活动相关的工具性的、道德上的和美学体验上的诸多方面。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即使技术取向的风险的科学分析,价值元素也能够从物理世界的事实中派生出来。同时,文化取向的风险分析也应当充分重视事实本身的属性。(19)
第二种是基于社会认知上的考虑。风险概念的技术取向承认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的分歧,并把这种分歧归结为对“概率”的不同理解。也就是仍然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由此关闭了从其他途径考察相关问题的可能性,并且坚信科学的方法、科学家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能够消除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的分歧,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的差异一直是风险研究中的争议问题。风险分析的技术取向视概率为风险的本质,理解风险就是理解与概率相关的因素。这些概率因素弄清楚了,风险就把握清楚了。专家是研究概率因素的主体,他们专业知识与技能对概率因素的概括与总结可以主导整个社会对风险的认知。专家的工作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情况却总是,公众对风险的反应与专家的意见经常背离、冲突。早期学界还认为是公众知识局限的原因,但这一思维逐渐被摒弃,更多聚焦在社会认知的维度上,主要体现在对概率的理解从狭义转变到广义。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关注不是完全依赖伤害概率的数学表示,而是有着关于技术如何满足并受制于社会系统的更多方面的考虑。概率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仍然是风险的重要方面,但是概率已经不是简单、纯粹的数学概念和数字形式,它承载着复杂、丰富的社会元素和生活内容。概率内涵的转变代表着风险概率的纯技术分析走向技术与文化分析相融合。在整个风险实务当中,风险概率不仅是科学问题,还涉及风险决策的政治问题、风险感知的心理问题、风险信息沟通的社会问题、风险行为选择的文化问题。
第三种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贾桑诺夫(Jasanoff)从方法论立场出发倡导从技术与文化相融合的角度理解风险概念或者说进行相关风险研究,将技术的风险分析归为“量化研究”,而文化的风险分析则为“质化研究”(20)。这种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认为作为“质化研究”的文化取向的风险分析可以弥补和完善作为“量化研究”的技术取向的风险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质化研究”能够成为指导量化分析的一种可检验假设的资源,进而提高风险评估、风险沟通与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质化”的风险分析相对于“量化”的风险分析优势反映在,它能够随着情境的变化吸纳更多的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表现出灵活的“情境适应性”以及“知识的联系性”,带来完全不同的分析进路和管理实践。另外,“质化”与“量化”的风险分析相融合可以丰富研究范式,更深刻地审视先前的一些固有结论,理性看待社会政策,追求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这一思路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注释:
① B.Fischhoff,S.Watson & Hope,“Defining Risk”,Policy Sciences,17,1984,p.136.
② C.Start & Whipple,“Risks of Risk Decisions”,Science,208,1980,p.1114.
③ E.A.Rosa,“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Post-normal Risk”,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1998,pp.15-44.
④⑦ C.E.Althaus,“ A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f Risk”,Risk Analysis,2005,25:p.567,p.572.
⑤ T.Aven & Renn,“On Risk defined as an Event Wher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2,2009,pp.1-11.
⑥(19) S.O.Hansson,“ Risk:Objective or Subjective,Facts or Values”,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3,2010,p.231,p.236.
⑧ C.Start,“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Science,165,1969,pp.1232-1238.
⑨ B.Fischhoff,P.Slovic,S.Lichtenstein,S.Read and B.Combs,“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Policy Sciences,8,1978,pp.127-152.
⑩ Simon Gerrard,Judith & Petts,“Isolation or Integ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R.E.in Hester,R.M.and Harrison,(ed.)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Cambridge,UK:The RoyalSociety of Chemistry,1998.
(11) (13) J.O.Zinn,P.Taylor-Gooby,“Risk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Risk in Social Science,Edited by P.Taylor-Gooby,J.Zin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5-26,p.20.
(12) R.E.Kasperson,“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8,1988,p.177.
(14) M.Douglas and Wildavsky,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
(15) H.Otway,“Public Wisdom,Expert Fallibility:Toward a Contextual Theory of Risk”,Social Theories of Risk,S.Krimsky and D.Golding(eds.),Westport,CT,Praeger,1992,p.220.
(16) P.Slovic,“Trust,Emotion,Sex,Politics,and Science: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Risk Analysis,19,1999,p.690.
(17) Otis Dudley,Duncan,“Sociologists Should Reconsider Nuclear Energy”,Social Forces,57(1),1978,p.19.
(18) O.Renn,“Risk Governance:Combining Facts and Values in Risk Management”,H.-J.Bischof (ed.),Risks in Modern Society,Berlin and Heidelberg,Springer,2008,pp.61-126.
(20) S.Jasanoff,“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of Risk Analysis”,Risk Analysis ,13/2,1993,p.128.
标签:科学论文; 社会风险论文; 感知风险论文; 风险价值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