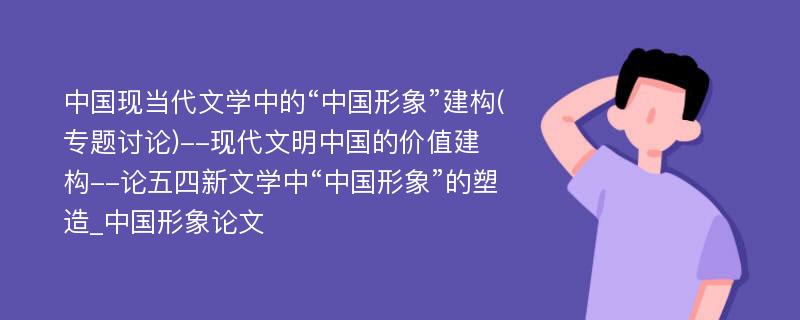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专题讨论)——现代文明中国的价值建构——略论“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象论文,新文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现代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晚清文学开了塑造新的“中国形象”之先河,以构筑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方式,展现出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思想情感,那么,在经历了民国初共和制国家建立的兴奋期之后,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学,则对晚清以来塑造“中国形象”的主题路径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设置,其特点是改变了晚清文学对新中国形象的单一性认知和塑造的价值取向,强调了赋予“中国形象”的现代文明内涵的重要性,突出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建构。
无疑,晚清文学表现出了一种对新中国热烈企盼的强烈愿望,其“中国形象”定位和塑造路径大多围绕“新=未来”的轴心而展开,抒情性强,叙事风格宏大,幻象性特点鲜明,民族国家认知度高,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就清晰地勾勒出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等小说,基本上都是沿着梁启超的这种路径设置而来的。然而到了“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对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与宣传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作家在认识到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塑造“中国形象”的现代文明价值建构理念。而对于“五四”新文化来说,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如陈独秀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为“五四”新文学塑造“中国形象”,打开了新的创作思路。它一方面使新文学作家在共和制的民国建立之后,仍然将以颠覆、批判和解构“旧中国”为主导,以消除“旧中国”的历史惯性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构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反思现代中国的现实境况和发展出路,勾勒未来新中国的现代文明形象的基本轮廓。
不言而喻,“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形象重塑、价值重建和意义重构。它一开始就突破晚清文学那种幻象性、单一性塑造模式的限制,突出在以个人主体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以现代文明为价值尺度的重塑“中国形象”的创作理路,目的是要使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具现代文明的意义内涵,展现获得新生和觉醒、觉悟之后的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由此,“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设置了三种主题路径:一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描绘“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展现对“老中国”的反思与批判;二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表现“中国形象”的崭新风貌,展现对“青春中国”的赞美和抒情,三是以自省叩问的忧思方式,指出“中国形象”的负面特征,展现对“弱中国”的哀诉与消解。三种路径都是以现代文明价值建构为中心指向,展现塑造现代“文明中国”形象的创作理念。
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描绘“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展现出对“老中国”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以鲁迅及“文学研究会”和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为代表,特别是鲁迅对“老中国”的反思和描绘,表现出“五四”新文学对“老中国”形象的颠覆、批判和解构所达到的认知高度。鲁迅曾表示,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②。可见,他对“老中国”的那种心理感知和反思,更多地是侧重于如何展现“老中国”必然消亡,以及如何改造“老中国”的思想认知。他认为:“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而形成中国“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③的现实境况。在他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颠覆和解构“老中国”形象,批判“老中国”儿女们的劣根性,就不可能展现出现代文明中国的形象特质。鲁迅以其“特立独行”的思考,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比作“吃人”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对“老中国”最为深刻和最为形象的本质描绘与概括。鲁迅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对于“老中国”的深刻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老中国”的“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所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的重要方式,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整个民族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鲁迅揭示出“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谱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文明,在现代中国处于变革与转型时期,其实还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根源与文化根源。在现实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现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广大的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尽显愚昧、麻木和无知之状。显然,鲁迅对中国形象聚焦,不是在有关贫苦的国民在物质层面上的窘迫和贫穷,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及其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的变异。不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在散文、杂文创作,鲁迅所展现的“中国形象”,都不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欣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的老态及其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在鲁迅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和乡土文学的诸多作家也大多沿着这种主题路径来展开“中国形象”的塑造,如叶圣陶对灰色市民生活和性格的描绘,实际上也是以透视国民性的方式来展现“老中国”及其儿女们的那种卑琐、投机、苟安的形象。乡土文学作家,如王鲁彦、巴人、许杰、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对古老的乡土中国的形象展示,大多也是与生活在乡土中国的农民,那种残酷、暴虐、蛮性、蒙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对“中国形象”的一种理性思索,同时也在努力地为现代中国探寻一种全新的文明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可能性。
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表现“中国形象”的崭新风貌,抒发出对“青春中国”的赞美之情,主要表现在郭沫若及“创造社”、“太阳社”诸成员的创作上,贯穿其中的仍然是对现代文明中国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认同。换言之,它不是对现代文明中国的概念性图解,也不是廉价的情感宣泄,而是一种被现代文明唤醒之后的心灵觉悟的表现,是出自对未来中国热烈企盼的心灵情感的抒发。在这当中,它一方面弘扬了晚清文学的传统,传达出整个民族对迈向强大、富强、自由、文明中国的向往心声,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和方式,对新旧转换时期中国出路进行认真思考,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以“凤凰自焚”的自我否定方式,表现出一个民族要走向新生,就必须认真反思自身缺陷,勇于否定自我,勇敢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现代思想。又如,在《天狗》中,他以“尊崇个性”、“个性解放”的新思想为创作取向,展现出以个人主体对应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思路。在整个《女神》创作中,郭沫若以塑造庞大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方式,重塑“凤凰涅槃”后的“像爱人一般”的“青春中国”的形象,也即“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小我”(个人主体)和“大我”(民族国家主体)有机融合的“文明中国”形象。它体现的是整个民族主体觉醒的现代性理路:宏大、开阔、豪迈,富有进取心和现代文明意识,充满激情,感召力强,同时所展现的也是将现代中国作为“时代强者”来进行重塑和展示,从而使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加富有青春朝气和现代文明气息,表现出获得新生之后的现代中国的充分自信力。其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创作,如成仿吾、田汉、叶灵凤、张资平等人也基本上是沿着这种路径而来,抒发出迈向现代文明中国的心灵情感。
郁达夫及其他自叙传作家,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不同,其特点是以个人哀诉的方式,展示历史行进中的背面形象——“弱者”(“零余者”)、“弱中国”形象,表现出获得新生之后的中国,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性和曲折性,尤其是“弱中国”在现代文明面前所显示出来的种种负面形象及所带来的巨大历史包袱,尤其是给现代中国人所带来的种种心理困惑。在郁达夫的笔下,自省、自责、叩问、哀诉的忧思之情是溢于字里行间的。以《沉沦》为例,小说重点是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我”的最后沉沦,虽然有自身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弱中国”所带来的无法排遣的精神压迫感和心理苦楚感。显然,郁达夫塑造的“中国形象”,充满了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并夹杂着一种时代性的颓废、忧郁和消沉情绪,个人的不幸也总是反映出民族国家的不幸,因为这一切都是“弱中国”的罪过。不过,这种以“时代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也提示人们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中,必须正视“弱者”的生存境况,正视历史行进中个体被忽略的问题。如果忽视“弱者”的生存权利,忽视“弱中国”给现代中国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甩不掉巨大的历史包袱,消除不了国民的劣根性,现代的个人主体性,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将无从建立,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文明也将无从实现。郁达夫所宣泄的虽然是个体的不幸遭遇和心理困惑之情,但其价值建构同样是具有现代性的,同样是意在唤起整个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其他的自叙传作家,如王以仁、庐隐、倪贻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也基本上是沿着这种主题路径而创作的,在个人情绪的哀诉中,也夹杂着纷纭复杂的现代社会心理和现代中国人的困惑、迷惘与失落的情感。
总之,“五四”新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不是像晚清文学那样注重显性层面的幻象性、单一性的形象塑造,而是注重在深层次的多维意识层面上,确立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和心理认同,以构建新的“中国形象”的心灵映像,并昭示人们:现代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文明的价值重建和意义重构,只有这样,一个现代文明中国的形象,才会真正地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注释:
①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②鲁迅:《热风·三十六》,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3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