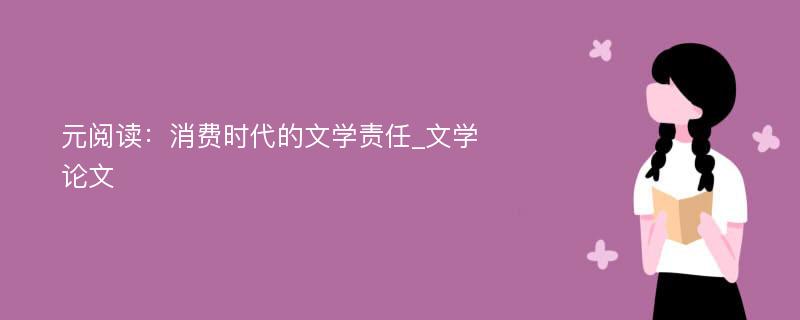
“元阅读”:消费年代的文学担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合法转型期,冠名为“消费年代”。
当消遣型、商业化的电子娱乐像沙尘暴覆盖国民的精神天地时,“文学”还能做点什么?
诚然,这个带引号的“文学”不包括印刷垃圾,它是指民族暨世界史上,以经典名著为标识的、旨在丰润、充实乃至提升人类心灵的严肃“文学”。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不仅是指该作品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传播的空间宽度和时间长度,远远超出相应作者的行为限度和生年限度,更重要的缘由在于,该作品在给定历史时空所呈现的文学想象,可能蕴藏着李长之所说的“感情的型”。这“感情的型”既是特指某一能长久迷人的艺术造型,更是泛指一切赋予普世性情思范式以不朽魅力的诗哲符号。何其芳则誉之为“文化共名”。所以当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说,有助于人类迈向文明的普世价值谱系,是在经典中保存得最好、亦最纯粹,这不但表明赫钦斯无愧于大教育家的美名,同时显示他对文学名著的人类意义颇具敏感。
何谓“文学名著的人类意义”?它是指,每一敬畏生命且又想活出意义的读者,只须他愿意,他是可以在文学名著中眺望或走近其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
纯个体生存,就其生理学过程而言,无所谓意义。意义,本是在日后被文化历史地渗入的。故有人说,人生犹如空杯子,看你装什么:要么空虚,要么充实。空虚是你体会不到意义,充实是你亲证了意义。而文学名著委实有此神奇功能,它可在诱发你的再造想象之同时,又将其蕴涵在字里行间的忧思与深情,像细雨般地湿润你的眼帘,直至你原先生涩的心灵的某一块悄悄地变软,柔得像海绵一样有弹性,极富吸吮力。
有时一部好书在握,好到你爱不释手,夜不能寐,直到东方欲晓,你才书卷掩面,昏昏入梦。此刻的你,虽然还是身份证上的那个你,但醒来后你重新打量人生、历史与世界的眼光可能全变了。
有首儿歌这般唱: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作为类比,也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内心有无精神家园,其生存质量大不一样。有精神家园者会活得坚实,有目标、有追求,此追求可落实到日常生存细节,这就宛如一棵树,根扎得深,树冠也不缺花果锦簇,沉甸甸的;反之则像柳絮过于轻盈,随风漂泊,最后可能坠入泥潭而难以自拔。
无怪有人感慨:一个人若能堂堂正正地走过其沧桑尘世数十年,不降志,不辱身,不苟且,做自己爱做的事,同时也裨益社会,这需要读多少好书啊,才可能撑起“独立、自由”的志士脊梁。
但有意思的,当这群志士还不是志士,只是一伙青涩小子,却又仰慕“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先哲时,他其实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可能连“什么叫诗”、“什么叫小说”都说不清,但这并不妨碍他依然能从文学名著读出一种莫名的乃至深入骨髓的感动——这份感动有的甚至能伴随他生命的全程。我将这种不凭借专业学养而直接从价值层面去领悟文学的阅读,称为“元阅读”。我猜测,大概正是这种“元阅读”效应,才为文学名著在人类精神领域所享有的高贵地位提供了最雄辩的理由,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价值根基,这更是“文学”在面对消费年代的滚滚红尘时,务必坚守、不能放弃的最后一座“狼牙山”。
将消费年代的文学担当隐喻为“坚守狼牙山”,并非纯属修辞,倒是恰巧印证了文学担当的现实限度与道义责任。
所谓“现实限度”,是指文学担当对社会语境的文化校正,从宏观角度而言,当属弱势。这是不对称的对垒:一边大军压境,另一边一夫当关。然这至少表明,消费主义的电子娱乐浪潮虽猛,但还未猛到全国山河皆告沦陷,毕竟还有“狼牙山”权作屏障。我说的“狼牙山”,首先是指大学教育框架里的文学课程设置,大体无患。当文学对社会语境的精神感召力弱化,它就更应加固大学的堡垒,为人类高雅文化之延续留下火种。
这就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当年撰《狂人日记》时写的两段话:一是“救救孩子”;二是“不曾被吃与尚未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这两段话含意不浅。我揣摩鲁迅的潜台词大体有二。一是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其动机当想通过“立人”来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但一俟直面现状,他又清醒地痛感,并非所有国人皆能被“立”为新“人”,或许那群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才可能被“立”为新“人”,于是鲁迅只想“救救孩子”,至于孔乙己、闰土、祥林嫂、九斤老太、华老栓与阿Q之辈,则另当别论。这是第一层。还有第二层,鉴于“孩子”也大多来自宗族的大屋檐下,他的身上也不免有传统的胎记,这么一来,“不曾被吃与尚未吃过人的孩子”即使有,也恐怕不多了。这是否暗示当年鲁迅设定其“立人”目标时,也颇受制于“现实限度”呢?
什么叫“现实限度”?说白了,就是理智地去做给定条件下所可能做的事。既不上九天揽月,也不下五洋捉鳖,而努力去摘一串跳一跳能够着的葡萄。
诚然,“现实限度”之不如意,不应成为躲避“道义责任”的托辞。正是在这点上,鲁迅又堪称榜样,因为在同一篇《狂人日记》里,鲁迅即使想过最后得救的“孩子”可能寥寥,但他依旧沉毅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中去”。
这就给了当下语境一个警示:当严肃文学已肩负不起对社会大众的价值导向时,它为何不首先对正在大学渴望“精神成人”的莘莘学子有所担当呢?难道他们不正是当年鲁迅曾寄予厚望、命系民族文化生机,却又活在当今的“孩子”么?
这就是所谓“坚守狼牙山”的本义。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要让“元阅读”来“坚守狼牙山”?
这便涉及文学担当的针对性命题。
文学担当的针对性有二:“为谁担当”与“为何担当”。
先回答“为谁担当”。
当然率先是为在校本科生,为他们“精神成人”而担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此“大”,含义有二:一是现代大学理念从来是把本科生的精神成长,视为高校事务的重中之重;二是对每位本科生来说,在校四年,他能否“精神成人”对其一辈子的影响,将显然重于他能否“专业成材”。
本科四年,从十八至二十二岁,本是学子生命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灵魂发育的季节。坊间皆知人的生理发育有季节性,但很少讲人的灵魂发育也有季节性。其实,人的精神成长活像一棵树,假如它春天不开花,秋天就不会结果。假如二十二岁前的他对“如何做人”没有认真地思考,那么,等他毕业、就业后,就更难得从正面去自觉且持续地思考“如何做人”。因为他将被更现实的世务俗趣,诸如职位、薪水乃至油米柴盐所纠缠、所压倒。
再说,引导本科生在读期间从正面去领悟“如何做人”,也恰到时候。因为十八岁读大学,对绝大多数学子来说,实是其漫漫人生旅程的首次出门远行,他迟早会痛感,当他独自面对一片陌生的新世界,他在十八岁前所积累的读书暨人生经验,要么不够用,要么不适用了,进而,骤然丛生的“成长的烦恼”便会逼迫他从各方面(未必是正面)去体味与反刍“如何做人”。
能否说:无须专业学养,而直接从价值层面去领悟文学的“元阅读”正好能趁此时机,“对症下药”或“雪中送炭”呢?因为只须有慧眼,文学名著中委实有太多的优质资源,可推荐给大学生用来宣泄、舒缓、冰释乃至超越其“成长的烦恼”了。
当今大学生的“成长的烦恼”,固然有其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异的原因,但也无可讳言晚近十余年的宏观世变(这是中国文化千年未遇的又一变局),烙在这代人身上的印痕。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对增强综合国力,对提升国民日常生活质量,当是大好事,但未臻健全的市场经济所激发的负面效应,诸如物欲横流、拜金教、迷信物质刺激、凡事只讲实惠甚至唯利是图……对生于1984—1988年间,一路伴着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与电子娱乐走来的大学生(尤其是都市籍同学),不可能纤尘不染。事实上,“无边消费主义”作为愈益汹涌、难以遏制的时尚潮流,已经大面积地玷污大学生的品性,也颇有人开始将日常物质消耗水平高档与否,视作其生命格局中的最高目标来追求了,相反,对更应付诸心力的读书、做人倒不甚了了,浮躁至极,甚至为了眼前的蝇头微利,没了廉耻。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它表明:本被视为命系民族未来的新生代,正当他们灵魂发育的关键季节,消费主义思潮已在其心灵根部浸出霉点。不是说人的正常物欲不应得到正当满足,而是说,当人将物欲之超常满足视为人生第一目标时,他就不是将自己尊为价值主体,而是将自身沦为物欲载体了(比如“房奴”、“车奴”之类)。不错,每个人身上都长物欲,但与同样从身上长出的爱欲、自尊、求知欲、道德感、渴望自我实现的责任感等相比,物欲的价值含量毕竟偏低。所以当消费主义将一代学子懵得凡事皆被物欲推着走,这确凿表明大学生的心灵根部已遭腐蚀。
何谓心灵根部?这是一个人所以为人的价值根基或道德底线,也是制约此人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的绝对律令。所以价值根基又可称之为“精神免疫系统”。若此“免疫系统”受创,则他将对世间种种非正当诱惑失却“价值抗体”,不误入歧途才怪。
如上所述,其实已经回答了“元阅读”在当下语境的“为何担当”。目的有二:“固本”与“祛病”。所谓“固本”,是为大学生一辈子走正路打精神底子,也可说是“价值奠基”。所谓“祛病”,是针对时势弊端向大学生敲警钟,这是一种迥异于坊间的清洁而清醒的声音,否则,恐于心不安,更于心不忍。记得梁小斌二十年前曾写诗,追忆抒情主人公从疯狂的“红色大街”流浪到荒野,才震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枚象征高贵良知的“钥匙”所以遗失,以致国人回不了精神家园,灵魂空荡荡得像弃儿,是因为那时街道只准涂一种颜色,只准说一种声音。而今街头背景换了,换得极为迅猛,原先高悬佩红袖章的偶像的墙面,已被一个个衣服愈穿愈少、胴体愈来愈露、眼神愈来愈火的辣妹顶替了。世界又被弄得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声音了。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红色”,现在是“黄色”。“红色”曾让人癫狂,“黄色”在诱人奢靡,其后果皆是勾魂摄魄,使其单向度化,对现存境况失却批判性的选择维度。
缺什么,补什么。正是在为大学生“精神成人”而“固本—祛病”这一层面上,以“元阅读”为契入点的文学担当,在当今高校是可以有作为的。
但“元阅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现行高校教务框架中的文学课程,尤其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中,旨在培训中外语言文学技能的学位教程设置。严格地说,这是两条内涵虽有互渗、目标却相径庭的课程路子。假如说,常规性的专业课程重在“授业”,那么,“元阅读”则重在“传道”(此“道”为“做人之道”)。若借用英国近代教育思想家纽曼的话说,则前者拟属“教学”,后者才堪称“教育”,因其目标是欲将大学生的品性提升到“博雅”高度。这是检测大学生“精神健康”与否的第一指标。纽曼对人的“精神健康”之关怀,丝毫不亚于对人的“身体健康”之重视。他说,就像一个人体格强健可胜任繁重劳务一样,一个人若“精神健康”,则他到社会上扮演任何公共角色,皆可能做好。所以他坚信,真正“大学的理想”并不在于将在校生一个个塑造成牛顿、弥尔顿或华盛顿,而在于为他们毕业后在世界舞台扮演牛顿、弥尔顿或华盛顿,夯实人格化的价格根基。
若把此夙愿落实到“元阅读”,则文学课程之设计务必重新定位,即一切将聚焦于大学生的“精神成人”,以其价值亟须作为甄别文学“教育”资源的第一参照,而不是随意地挪用常规性专业课程来凑伙。这当然不是说常规性专业课程不具人文品格,而是说旨在规训专业技能的常规性,终究是须把学科的知识学层面的系统性与规范性置于首位的。比如面对同一作家或作品,判断其能否入文学史,与考量其是否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所亟须,这全然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不合辙。若着眼于文学史课程,所以非讲某作家或作品不可,主要是因为舍此不足以呈示文学史在给定时空所达到的标志性高度。但若着眼于“元阅读”,则无须苛求某名篇是否真属该文学史的里程碑,或许它在思想与艺术上未必能独领风骚百年、千年,但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来说,却很可能是最合适,最紧俏,最能激发学子返身体认之情致的。
所以,若实话实说,在大学现有文学课程储备与它所应肩负的“文学担当”之间,已显露出结构性失衡。此失衡可表达为两个“浩如烟海”与一个“寥若晨星”之不对称。
“浩如烟海”作为数量化意象,主要指:资源与课程。就可能性而言,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能为大学生提供价值性“文学担当”的优质资源又岂止“浩如烟海”呵。再说课程数量,即便粗略累计,当今大陆高校(含高专、高职)已有三千余所,其所设专业必修暨非专业选修的文学课程名目少说也有上千种。而据权威部门新近统计,仅八十年代至今,大陆高校所采用的各式“大学语文”课程教材更达一千四百五十种之巨。这是另一种“浩如烟海”。但其中,能真正无愧于“文学担当”之使命且不乏原创性的“大学语文”教材,又有几种呢?恐“寥若晨星”吧。
这未必是好事,但又未必不是好事。文学课程境况虽远非一张白纸,但只要大学生渴望“精神成人”之普遍呼声在,只要“元阅读”确实能契合大学生的价值亟需,“文学担当”者总会出现,且最终走出一条不同于常规性专业课程之新路的。
关于强化文学课程的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流于知识性暨工具性规训的环节),这作为一种担当意识,其实是在晚近二十余年来,逐步地从朦胧走向明晰,从摸索走向执著的。鉴于“大学语文”是当今高校设置得最普遍的公选型文学课程,不妨以此课程教材演化为例,说明之。
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问世于八十年代初,堪称新时期“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开创者,也是至今国内高校该课程用书被选用最多的一种。抚今追昔,华师大版教材已走过二十五年历程,它从第一版到新近第八版的持续修订,显示了该书既“与时俱进”,又“永不放弃”的编纂品格。
所谓“永不放弃”,是指该书从初版时便确立的文化立场,即不论理念立意,还是选篇立章,皆以尊崇“圣贤襟怀”为标志的民族精神谱系为主轴,始终未渝。或许该书的编纂动机,在当初仍不乏知识性与工具性方面的补偿型考量,因为自1978年春陆续进校的大学新生(尤其是理工科),毕竟经历了十年浩劫,正常的学历教育程序被打碎,因此无论是基础写作能力,还是对中华文史的初步领悟,皆令人担忧。但十年浩劫所摧残的当不仅仅是国民教育机制,同时也是对亿万国民“人何以为人”的道德准则与心灵向度的强暴与践踏。所以,当荟萃圣贤诗文的《大学语文》昂首走进噩梦初醒的大学课堂,其意义,当不止在知识性与工具性方面有补偿功能,而更是在价值性方面:因为该书不仅是在竭诚接续曾被权力意志粗暴中断的中华文史传统,更是在试探着为浩劫后的文化废墟注入尚有现代生气的“国粹”。
诚然,岁月似水,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中国社会的经济景观与日常语境已发生急遽变异。为了感应时代的气象,华师大版教材第八版酷似老树新花,一改初版时的“国粹”原色。读者欣喜地发现,第八版所营构的“大学语文名人祠”的格局顷刻开阔:在原先敬供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黄宗羲等族国圣祖的牌位旁边,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作为近代欧美文学的光荣使者,已名列贵宾席;同时被接纳殿中的,还有参与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精英,从胡适、鲁迅、徐志摩、巴金、曹禺、施蛰存到宗璞、张洁与史铁生。何谓“与时俱进”?这就是。
但细心者不难觉察,第八版的“与时俱进”,并未在价值层面根本动摇该书于初版时的文化立场,这不仅体现在篇幅上,故国文言依旧占全书百分之六十五;更体现在统辖教材的内容构成的理念立意上,全书分十二章,其一“以民为本”,其二“心怀天下”,其三“和而不同”,其四“品格修养”……无一不是历代君子奉为“正心诚意”时务必铭记的儒家教义,也有人尊其为“中国文化要义”的。后学当不否认,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若有足够的智慧与胆略,真能从儒学遗产中提纯出仍具现代生命力的价值元素,而裨益于大学生的“精神成人”,功莫大焉。
若曰华师大版教材的文学担当颇具“中国特色”,那么,北大版《大学新语文》(以下简称《新语文》)则可谓“普世风格”。标志有二:一是《新语文》从其构思之初,便明确宗旨,应在本土语境担当起净化且优化大学生精神素质之天职,这就与国际化的现代大学理念(“重在育人”)径直接轨了;二是《新语文》的价值关怀的视界更宽,而不为族国的疆域所囿,它主张将包括儒学在内的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换言之,《新语文》之珍重中华文化,与其说缘自该遗产是列祖列宗的千古瑰宝,毋宁说是因为它们可能至今对人类文明演进仍不乏启迪,是值得信奉的普世价值谱系赖以构成且丰富的重大部件。
《新语文》凸显价值性的根由,是基于“大学语文”在高校现行课程中的定位。对非中文科班的诸多学子来说,“大学语文”不是专业课,而属公共课,你凭什么吸引同学愿听“大学语文”?出路只能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审美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这其实是把美学层面的“元阅读”,通过教材创新,而转化为不无操作性的课堂教学艺术了。
“元阅读”作为精神现象,几乎是每个同学从小皆亲证过的,这就是一卷在握(不论小说或诗歌),只须是你真正读进去了,或是你心灵的某处在不经意间被深深地触动,你皆会进入某种“得意忘形”之境。“得意”:是指你因得益于作品所蕴涵的意思或意味而情动于衷;“忘形”:是指你被感动时往往忘记追问该作品在艺术上是如何被形式地构成。甚至可说,一个读者学历愈低,愈缺乏有关文学的专业常识,他从作品中获得的审美享受或心灵的感动程度,可能会因其单纯而愈显美丽乃至圣洁。或许《新语文》所企盼的,正是“元阅读”有朝一日能被大学课堂所大面积地激活。
因为,事情正是这样:当你面对某种抽象理念,你是否真对它“信以为真”,进而转化为值得你用血肉去拥抱的刻骨信念,这并不取决于理解力或逻辑运演机能;相反,你会更珍惜那些从人生磨难中悟得的真谛,因为那是用泪水甚至血水浇灌的,是用你的整个生命存在作存根的,于是不由你不信。所以,《新语文》的选文方针是“现代人文,经典诗文”。前者为心,后者为身,灵肉一体,方可消魂。
也不是没有疑惑。说句老话,能为《新语文》提供经典文字的世界文学思想库存,岂止浩如烟海,就其资源类别而言,至少可分四块:一是千年中华文学暨文化遗产;二是近现代西方哲贤文豪的汉译佳作;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现代精英的不朽文字;四是自1978年前后当代中国在其“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历程中留下的珍贵情思。关键是要发明这一“中介”:该如何选编,才可能让教材成为大学生愿来与普世价值资源相逢且相约的“人文廊桥”?因为,远非一般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字皆能感召学子。《新语文》的做法是:紧扣普世价值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的关系,不惮淘洗、精心寻觅这么一串立章成书的结构性主词,使其蕴有双重含义:即它既是契合当下学子的青春境况、能启迪其“灵魂发育”的“精神主题”,同时也是可从古今中外的相应典籍提炼出来的“文本母题”(且又文辞优美、文气丰沛、文体别致,能在情感、情怀或情操等方面,令学子不读则已,一读惊喜而亲切),合二为一。结果便有了如下编纂程序:从“大学”→“青春”→“仁爱”→“情恋”→“自由”→“良知”→“敬畏”→“乡愁”→“记忆”→“英雄”→“坚忍”→“希望”→“自审”→“反讽”→“诗意”→“自然”,再由编委分工,围绕各主词累月搜集,定期集体筛选,反复斟酌,互补充实,巧手编排,独立成章,最后百川归海,整合成书。
一往情深地贴着学子的心去编撰,这是《新语文》别开生面的做法,无怪学界不少人叹喟:“想不到‘大学语文’书还可以这么编!”但有识者看得更深,比如北大教授乐黛云便表示:《新语文》的文学担当,实是表达了某种“文化自觉”。
乐教授说费孝通在晚年最想做的事便是“文化自觉”。有两条很有意思。一是用今天的眼光到传统中去寻找有生命力的遗产。这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释古”:既要弄清该传统在当时语境中的本意,又要搞懂该传统流传至今,哪些有生命力的成分亟待后人去提取。《新语文》想做的就是此事,即主张把包括中华瑰宝在内的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拿来做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营养。“文化自觉”的第二条,是应探寻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资源从何而来?就是从人类的普世价值谱系里来。这也是《新语文》最想做的。
有意思的是,当费老这般思考“文化自觉”的时候,未必获悉北大出版社正与一群中年学者联袂合作《新语文》。费老当是乐教授的师辈,而《新语文》编委对乐教授又当执弟子礼。这三代学人对“文化自觉”的观感可谓所见略同。或者说,在如何让文学在消费年代担当道义责任一案,这三代学人是可以用不同的声部唱“同一首歌”的。
平心而论,与六七年前相比,国内认同文学(或人文教育)应担当对青年成长的道义责任的声音相对多了。这很重要。其实,在同一片天空下,本就有不少人心里揣着同一个梦,脚下踩着同一条路,但因疏于沟通,彼此隔离,以致对共同价值的苦苦寻觅,在各自的生存环境竟形似“另类”。但假如走向一个更舒展的空间,你会发觉,这样的寻觅者并不见得就珍稀到普天下只剩你一个。以前读陈寅恪传记,曾揣摩传主的内心痛苦应是“前驱之苦,莫大于孤”。大概所有人(哪怕是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强者)也不免有心灵脆弱的时候。假如确信有一群人都在像自己那般寻觅,那么,路途再艰难,你也能咬咬牙担当;假如没有同行者或不知天涯有无同行者,则你也就很难再持久地默默坚守,甚至还可能会倒过来置疑自己的担当是否值得。
毕竟,一个担当者要像小说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始终特立独行地活在消费年代,亟需极强的信念支撑。罗曼·罗兰将此信念喻为“心的光明”。这不禁让我想起《新语文》编委在2004年夏于东海小岛所经历的一个场景。会期间歇,编委去看岛上一个由采石场变成的景点,酷暑,每个人的背上晒出的汗都结成了盐。有人感言,《大学新语文》想做什么?就是做这样的事:背着太阳晒盐。太阳是什么?是一种“心的光明”。任何追求都是一种负担,最重的负担只能用背来驮。当你驮着太阳,太阳把你的背晒出盐,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为学子的“精神成人”有所付出,这些付出其实是成全了你自己。把自己的汗晒成盐,而盐在圣经里是隐喻人类的精华。这更像是当孩子的父母:往往是儿女教会了我们怎么当父母,因为只有你当了父母,你才领悟父爱、母爱的滋味,于是瞬间我们成熟了,不仅在生理上见证了生育力,更在精神上赢得了无愧于父母亲角色的尊严。
2007年春于沪上学僧西渡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