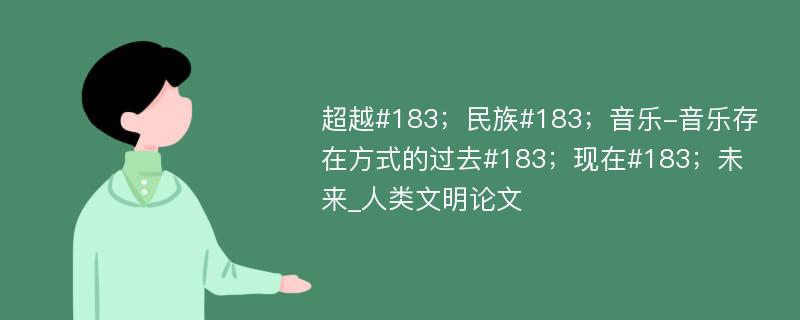
超越#183;民族#183;音乐——有关音乐存在方式之过去#183;现在#183;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论文,民族论文,未来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隶属】音乐哲学/音乐社会学/民族学/人文进化学
小引
有关“超越”、“民族”、“音乐”之间关系的争论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乃至一个多世纪以上的时间。其间,尽管许多人都对此有关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且有许多专论问世。但是,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认真地历史哲学反思。
本文的任务是:继发表于1991年第8 期《人民音乐》之《民族与超越》一文之后,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一步的历史哲学反思,并进一步明确所谓“音乐存在方式”之“过去·现在·未来”的坐标。
一、非价值论的超越与有价值论的超越
当代前沿的哲学和科学业已开始觉悟:长宙广宇无时无刻无地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地行运;在宏观网络之中的各种“扰动”,无一不经受着“放大”或“衰减”之命运的选择;“扰动”一旦被宏观网络“放大”,便突破了原先“负反馈自稳”的临界限度,开始了新一轮“正反馈自生”的创造使命;使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说,“生机”一旦被“缘会”加强,便突破了原先“阴”、“静”的临界限度,开始了新一轮“阳”、“动”的创造使命;新的结构、新的功能、新的性质、新的属性、新的过程、新的历史随之而开始了自己的生命;系统随之发生突变,并进入新的“法脉”与“器象”往复循环之超循环的新的“负反馈自稳”层面,换言之,进入新的稳态。
本文所谓的“超越”,正是如此这般在“人文进化”、“一般进化”的超循环机制中进行。质言之,所谓“人文进化”、“一般进化”,如果没有“阳”、“动”或“正反馈自生”,则“化”不可能“进”之;如果没有“阴”、“静”或“负反馈自稳”,则“进”不足以“化”之。所谓“超越”,正是在“阳”、“动”与“阴”、“静”或者“正反馈自生”与“负反馈自稳”之“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之中,“阴”、“静”向“阳”、“动”或者“负反馈自稳”向“正反馈自生”的转化;正是在“进”与“化”之“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之中,“化”向“进”的转化。(注: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Human-Culture-Civiliza- 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 》(《人文进化学与一般进化论》),纽约、伦敦、 巴黎、 蒙特勒、 东京、 墨尔本1990年第30卷《World Futures——The Jo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来——一般进化论杂志》); 《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北京1992年第5期《哲学研究》; 《“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太原1992年第3 期《晋阳学刊》)。)
所谓“超越”,有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同一系统和不同系统之间的差别。如不论其价值,在同一层次、同一系统,新的结构、新的功能、新的性质、新的属性、新的过程、新的历史,相对于旧的结构、旧的功能、旧的性质、旧的属性、旧的过程、旧的历史而言,当然是处于“超越态”之中。一旦前者完全取代了后者,它的“超越态”便旋即消失。更新的一轮超越,又将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然而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系统,某一新的、在总体上超越的层次和系统,即使是这个层次、这个系统中某些相对于本层次、本系统而言已经丧失“超越态”的结构、功能、性质、属性、过程、历史,相对于其它落后的层次和落后的系统,有时仍然具有超越的态势。
然而所谓“超越”,并不仅仅是狭义的“推陈出新”。正是因为新鲜对陈旧的不断超越,才形成了新鲜与陈旧共济耦合、同时并存的无数子系统合成之巨系统的万象世界。
纵观全部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文明“耦合共生”,乃是人类文明不断累续发展之必然的规律。
所谓人类文明的进化,即人文明进化,并非只有不断异质发生之纵向的进化,而且也有不断层垒叠加之横向的进化(注: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另参牛龙菲《评刘靖之著〈新音乐史论〉》,北京1997年第1期《中国音乐学》。)。
所谓不断异质发生的之纵向的进化,是指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中世文明的后续发生,以及依次类推在中世文明的基础上,近代、当代文明的后续发生等等。
所谓不断层垒叠加之横向的进化,是指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中世文明之后,古代文明并非立即消亡灭绝,而是其全部或部分的文明因子,继续保持存在,与中世文明耦合共生,以及依次类推在中世文明的基础之上,异质发生了近代、当代文明之后,古代、中世文明并非立即消亡灭绝,而是其全部或部分的文明因子,继续得以存在,与近代、当代文明耦合共生。
除此而外,就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言,由于地理、交通的制约,不同起源之起先相对独立的文明,在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也有一种或相互隔离而共时并存或相互交流而耦合共生的空间关系。
对于人类所有的文明而言,其中既有历时的关系,也有共时的关系,还有历时、共时交织的关系。
现实生活中,并非只有各种不同时序之文明的历时关系,要是果真如此,所谓“历史传统文明”,将因后续文明的发生而立即消亡灭绝。一切诸如“古与今”即“传统与当代”、“过去与未来”等等的问题,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在当代中国,所谓传统音乐的“母语环链”,并非真的已被“铰断”。要是果真如此,所谓“中国传统音乐”,将因欧洲音乐的取代之而不复存在。一切诸如“东与西”即“中国与外国”、“华化与欧化”等等的问题,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由些看来,所谓“超越”,不仅有历时的意义,而且有共时的意义。就耦合共生、协同进化的意义而言,那些能够与更多的系统耦合共生、协同进代的系统,相对于那些只能与较少的系统耦合共生、轩同进化的系统,便处于超越的态势。就信息的贮存和传播而言,某种能够突破时空界限的信息,相对于那些不能突破时空界限之信息的事物,相对于那些没有负载突破时空界限之信息的事物,便处于超越的态势。就事物为人所用的意义而言,某种能够突破时空界限之对全人类有益的事物,较之那些不能突破时空界限之仅对某一部分人有益的事物,便处于超越的态势。
这里,我们已经不再仅仅是谈论一般的、非价值论意义的“超越”,而开始接触到了特殊的、有价值论意义的“超越”。
但是,所谓“超越”,即就价值论的意义而言,也不仅具有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而且也具有新旧鲜陈生死的标准,在某些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如体育活动之中),还具有高低快慢强弱的价值标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无论在何等恶劣的境地,从来没有一时一刻地止息。真、善、美,相对于假、丑、恶,就价值论的意义而言,无论它处于多么微弱的地位,总是具有超越的特质,总是具有超越的可能,而且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于超越的态势。然而即使是无论多么尽真、尽善、尽美的事物,也可能永恒地存在。新鲜而又富有生命活力的真、善、美,总是在逐渐地、不断地取代着陈旧而又业已失去意义的真、善、美。人类之命运,正在于不断地超越以往,正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
“超越”,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前进。“超越”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然而,“超越”就是“超越”。超越,总是有所前进;超越,总是有所抛弃;超越,总是有所创造;超越,总在有所否定。这是历史的逻辑,生命的属性,天地之正道,宇宙之铁律。
“超越”可以是局部地超越。“超越”也可以是全盘地超越。修修补补可说是局部的超越;改天换地无疑是全盘的超越。可真、可善、可美的事物,进化尽真、尽善、尽美的事物,是所谓局部的超越;虚假、凶恶、丑陋的事物,被真实、善良、美丽的事物取代,正所谓全盘的超越。
“超越”是人类本真的渴求;“超越”是历史进化的轮轴。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才诗人李白的浩歌,正是“超越”不灭的精魂。
二、血缘、物缘的民族与信缘的族类
长宙广宇中一切事物及其属性,都有其发生、演进、衰落、死亡的历史过程。世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及其属性。所谓“民族”也不例外。
在人类历史的长期演进过程之中,群居动物之古猿分支的后裔——人类,起初是由于处于主导地位之人类人口生产的“血缘”,结成了一定的社会群体,这便是人们所谓的“氏族”、“部落”,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血缘民族”。后来,由于处于主导地位之人类物资生产的“物缘”,在血缘民族的基础之上,又结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这便是人们所谓的“现代民族”——“物缘”(地缘)民族”。当代,由于处于主导地位之人类信息的生产,在血缘民族、物缘(地缘)民族的基础之上,又结成了一种更大、更新的社会群体,这便是人们所谓的“人类信息共同体”。此所谓“人类信息共同体”,已经很难再说是什么“民族”,而只能把它称之为“信缘族类”。(注: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人文进化学是一般进化的高级综合阶段》,提交1990年9月17-19日(南京)“全国自然哲学学术会议”之论文;《我观〈中国音乐年鉴〉》,西安1990年9月第3期《交响》;《民族与超越》,北京1991年第8 期《人民音乐》;《且来念念“文化经”》,惠州1993年3月18 日《企业形象报》第3版;《“衣冠”与“禽兽”——服饰文化漫谈》,海口 1993年第7-8期《中国服饰文化》。)
所谓“民族”,由于人类历史的进化,其内涵一直在不停的演变。对于“血缘民族”而言,种族、姻亲是其主要的内涵;祖先崇拜、性器崇拜是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对于“物缘”(地缘)民族”而言,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出产大地及其地表的动植物以及其它物质材料是其关注的主要对象。随着农业的发展,对于农作物生长有着重要意义的日月星辰、风雷云雨崇拜和大地山河、动物植物崇拜一起成为物缘、地缘民族的主要意识形态。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长足进步,在现代,组织社会生产的“国家”,业已取代“物缘(地缘)民族”,而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组织形式。对此,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国家民族”。在某些这种“国家民族”中,商品、金钱崇拜业已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甚至,“科学”也已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所谓“物缘(地缘)民族”,相对于“血缘民族”而言,早已“不同民而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它的肌体内不知流着多少“血缘民族”的不同血液。我们之所以能以仍然称其为“汉族”,主要是就其地缘、物缘的关系而言,更是就其信缘的关系而言。换言之,现在我们所谓的“汉族”,早已经不再是一些“民族学家”所谓的“血缘民族”甚至都已经不再是“物缘(地缘)民族”,而只不过是一种“文明共同体”的习惯代称而已。所谓“汉族”,相对于一般的“血缘民族”或“物缘(地缘)民族”,已经是一种相当超越的“民族”形式。(注:参牛龙菲《“雅”、“俗”本义之说明》,北京1994年第1期《人民音乐》。)(案:在人类历史上, 还有只依靠血缘、物缘和信缘联系,而没有“共同地域”的“民族”,如“犹太民族”。)
在当代,由于“全球一体化的信缘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早已超越了“血缘民族”和“物缘(地缘)民族”甚至某种“文明共同体”(如“华人文明共同体”、“基督教文明共同体”、“伊斯兰文明共同体”等等)的局限。在当今世界,除了有特殊学术动机和特殊职业兴趣的“民族学家”之外,除了有特殊政治动机和特殊功利目的的“民族斗士”之外,“民族”已经不再是人们存在的唯一前提。超越“民族”的偏见和局限,业已成为当代社会中健康社会成员的必要良好品质。
卡尔·马克思曾经自称为“世界公民”;而且提出过“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口号。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当今世界,“世界公民”业已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个体存在方式。对于这些“世界公民”而言,原先自己归属的“血缘民族”、“物缘(地缘)民族”,甚至“国家民族”,主要是在“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类智慧基因”的方面继续影响着他的观念、行为、个性、人格。历史不同时期的“血缘民族、物缘(地缘)民族,甚至国家民族的遗产”,对于这些处于“信缘族类”之中的,“世界公民”而言,业已成为个性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而不再是生活的唯一律令。
综合上面的分析,当代社会学的民族观,显然已与早先“原始的”甚至“民族国家的”民族观有所不同。当代“民族学”的研究,理应对此有所反思,可以说,某种“文明多元一体”论的“信缘族类观念”,正是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而“超越”了“一般民族学”的常规。那种“博物学”式的“民族学”,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对于当代人类的日常生活而言,新的、更加开放的“族类观念”,显然更加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不仅要在操作的层面,熟悉本学科的常规方法,而且应当在哲学的层面、历史的层面反思本学科的常规方法,以适应历史前进,突破常规方法的局限,超越常规方法的局限,把握生活的跳动脉搏,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民族学”的研究,也自不能例外。
三、部落、国家的音乐与族类的音乐
所谓“人类社会”,业已经历了“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以物资生产为其主导的物缘(地缘)社会”、“以信息生产为其主导的信缘社会”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注: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人文进化学是一般进化的高级综合阶段》,提交1990年9月17- 19日(南京)“全国自然哲学学术会议”之论文;《我观〈中国音乐年鉴〉》,西安1990年9月第3期《交响》;《民族与超越》,北京1991年第8 期《人民音乐》;《且来念念“文化经”》, 惠州1993年3月18日《企业形象报》第3版;《“衣冠”与“禽兽”——服饰文化漫谈》,海口1993年第7-8期《中国服饰文化》。)。
在“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之中,音乐艺术尚处在自发的状态。音乐艺术主要是在“生殖崇拜”的“交感巫术”中发挥着自己的特殊功能。这种充满“生殖崇拜”内涵的“原始”音乐,其实践的主体,是以血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的“氏族部落”群体。其地缘的规模,除了后来某些上层人士之较远距离的“通婚”之外,大多被局限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男女两性“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使这种以“血缘”为其内涵的“原始”音乐,具有某种空间定位的性质。这个时期的“音乐传播”,主要是关联于部落的迁徙。
在“以物资生产为其主导的物缘(地缘)社会”之中,音乐艺术开始向自觉的状态过渡。随着“物资生产”逐渐蜕化为“商品生产”的历史进程,音乐艺术也逐渐进入了“商品经济”的“市场交换”。这种逐渐渗透“商品意识”的近代音乐,其实践的主体,是以物缘(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国家民族”群体。其并不一定具有直接血缘关系、且已分离异化的“立美”、“审美”主体,或者说已经分离异化的“构象”(指“作曲”)、“运象”(指“表演”)、“品象”(指“欣赏”)主体,已经突破了“空间定位”的局限。由于现代资本主义跨越国际之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其地缘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到全球的范围。这个时期的“音乐传播”,主要是关联于商品的交易。
在当代正在形成的“以信息生产为主导的信缘社会”之中,音乐艺术将达到自觉的状态。它的形成,将经历一个剧烈变化的历史时期。
由于当代“工业文明”建立了势力强大的“文明工业”,并左右着世界范围的“文明市场”;音乐艺术的传播,第一次真正具有了全球的规模。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当今世界,尚未形成某种名符其实之一统的天下的“世界音乐”。血缘部落的音乐、物缘(地缘)国家的音乐、信缘族类的音乐,都耦合共生、同时存在于当今世界。当今世界的音乐艺术,因而呈现了极其复杂的面貌。
然而就历史的趋势而方,由于全球规模的经济联系,更由于族类层面的信息传播,特别是由于当代信息传输技术的发达,以往那种局限于血缘之“部落空间定位”的音乐、局限于物缘(地缘)之“国家民族本位”的音乐,将必然逐渐被某种“信缘族类”的世界音乐所取代。这里所说的“世界音乐。”,是在以往血缘部落的音乐、物缘(地缘)国家的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元一体的音乐。这种多元一体的“世界音乐”,以作为“世界公民”之独立个人为其实践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重组以往的“音乐基因”,从而实现某种“突变”,并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可见,向未来开放和向世界开放的“音乐之民族的特性”从来都不是静止、凝固的。
就空间维度而言,无论是“血缘”的、或者“物缘(地缘)的民族,各民族之间的信缘相互交流,必然使得某一民族的音乐艺术,对其他民族的音乐艺术发生一定的影响。此一民族对彼一民族音乐艺术的接受和欣赏,恰正说明:作为文明形态之一的音乐艺术,就其传播交流而言,其本身就具有超越本民族局限的本质特性。否则,某一民族的音乐艺术就断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欣赏。
就时间维度而言,“民族特性”也从来都不是静止、凝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化,音乐艺术以及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变化。就此而言,不但民族音乐之片面、偏狭的一面应该加以超越,而且民族音乐之优秀、精华的一面也应该加以超越。正如上文所析,所谓“超越”,不仅具有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而且也有新旧鲜陈的价值标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多么尽善尽美,也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人类之命运,正在于不断地超越以往,正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
如果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1827年还仅仅是提出了有关“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的愿望的话(注:《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第113页。);那么,二十一年之行,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指出:“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于是从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中便形成一个全世界的文学”。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的说法,正是基于《共产党宣言》立场之上的立论。
时至今日,对“血缘民族”以及“物缘(地缘)民族”的“超越”,在当代世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业已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内涵。当代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全球一体”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作为“类”即“信缘族类”的存在,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正是这个存在的现实,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注目于“对民族的超越”。如果说,1943年闻一多先生在其《文学的历史动向》还只是就不同文明的“互相吸收、融合”而预言:“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牛案:指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四个古国的文明)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牛案:即文明)只有一个世界的变化(牛案:即文明)。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注:参《闻一多全集》(四卷本),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原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8月北京重印版,第201页;《闻一多全集》(全十二册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 12册,第16页。)。如果说,1948年T.S.艾略特在其荣获诺贝尔奖时的《获奖演说》还只能就“诗歌的伟大意义”言及“诗歌的超越民族价值”(注:参《T.S.艾略特诗选》,在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的话;那么,在当代,人们不约而同的提出“超民族化”(注:参李曙明《论音乐的超民族化》,北京1989年3月31日《中国音乐报》。)“超民族主义”(注:参A.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78页。)、“超民族”(注:参J.M.费里《关于超民族》,(法)《神灵》1991年, NO.11,PP.80-93,转引自北京1992年第4期《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人类共性”、“世界性”(注:参马任《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上海1993年2月18日《社会科学报》,第3版。)、“超越民族”(注:参北京1993年第5期《读书》之《文讯·民族性·世界性》。)、 “超民族性”(注:参周炽成《从哲学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看我国哲学研究的关景》,上海1993年6月24日《社会科学报》第3版。)等等的概念,业已具有了物质、经济的现实基础。
综观当代世界有着历时性质之共时存在的各种层次的音乐艺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所谓“电子音乐”即“信息技术音乐”。它不仅加大了“信缘族类音乐”对“血缘民族音乐”、“物缘(地缘)民族音乐”的超越速度,而且已经引起了音乐艺术之内涵的某种变化。
当代社会,最具时代特征的事物,是所谓的“信息技术”。当代信息技术,既具有某种抽象的性质,又具有某种具象的性质。一方面,它的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即形式运演的本身,无关于人类的生理姓别,无关于人类的性格差异,无关于事物的具象存在,无关于事物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无论是它的数据存储、还是它的数据处理,一言以蔽这,当代信息技术的具体运演,则完全是可测量、可计算、可控制、可操作的物理弱电运动。可以说,当代信息技术已经把符号系统从理念的天国迁回了物质的世界。而所有这一切,都与音乐的特殊艺术本质更加吻合。
过去时代的音乐,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运演”到“形式运演”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瞎子阿炳当年是在二胡,以“具体运演”的方式,奏出《二泉映月》这样的妙音;而聋子贝多芬是在谱纸上,以“形式运演”的方式,写出《第九合唱》这样的佳曲的话;那么,现代的音乐家们,已经可以使用电子合成器、乐器数据库等等的现代电子作曲技术,把“具体运演”和“形式运演”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同时既奏出妙音,又谱出佳曲(注:见牛龙菲《人文进化学》,第200页。)。 当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使用各科不同的电子乐器,对器乐教学和演奏的艺术实践提供即时的数据分析,并随时比较分析文本乐谱和演奏记谱的细微同异。现代信息技术,真正实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道器统一”的理想,并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扬弃了以往社会分工所造成之“立美”、“审美”主体、“构象”、“运象”、“品象”主体的分离异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程序运演”和音乐艺术的“行象建构”(注:参牛龙菲《行象简论》,(意象艺术国际研究讨会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版。),都具有“生生不已”、“逝者如斯”的“动态”属性。二者之间的“同态”(注:参牛龙菲《新的音乐艺术模型——“自同态转换群集”概说》,广州1992年第2 期《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北京1992年第8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6音乐舞蹈研究》。),使得音乐艺术和信息技术具有某种本质的“亲缘关系”。当代“多媒体”的信息技术,已经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把这种“同态”,具体地呈现出来。具有开放思维的音乐学家,将随时注目于未来一切可能的发展。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稿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二稿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稿
一九九六年三月四日四稿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五稿
[收稿日期:1998年12 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