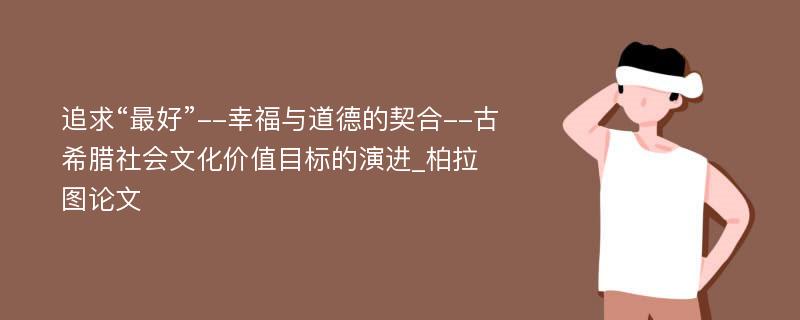
追求“至善”——幸福与道德的匹配一致——古希腊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社会文化论文,至善论文,道德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建构了自己的文化世界。但文化世界一旦应运而生,它就超越了个体心理和个别社会而存在,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客观世界。因此,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秉有自身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还必然具备着通过自我确认并内化为民族心理的价值认同系统。这个系统一经形成,就象经纬参差的“文化神经”一样,牢牢地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该系统的核心,它一方面以最高的普遍性统一着全社会成员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指示着该社会的未来期待,因此它对维系文化范式的稳定与惯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实际上是“好”(good),它涵括着道德与幸福匹配一致的意义。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对于拉丁文bonum (相当英文的good)一词所指称的那种东西,德文却有两个十分悬殊的概念,并且还有同样悬殊的语辞das Gute(善)和das Whol(福)两字与bonum一字相当”[1]。由于西文中的good对应于中文的“好”与“善”二词,因此good通常被中国学者翻译为“善”。本文为了顾及传统译法及其留给读者的习惯心理,仍然沿用“至善”作为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只是提醒读者要从“好”的意境来体味“至善”。
众所周知,早期希腊人在民族迁徒和海外经商活动中受到自然界的残酷压力,这种压力常使人们处于艰险莫测的“命运”之中,因此,前期的希腊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把关注人类的目光投向自然界,去探索造成人类“命运”的因由。从思维逻辑看,人类必须首先了解制约他们实践的客观环境,然后才能确立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价值,而这也决定了早期思想家们必然把研究的兴趣置于宇宙论之中。前期哲学家们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尽管他们都相信人类的“命运”是由宇宙决定的,但又不甘心匍匐其下而无所作为,因而他们把哲学诠解为“爱智慧”,决心用自己的智慧破解禁锢人类“命运”的奥秘,并把这一行为厘定为“趋善”的幸福;如赫拉克利特就曾表示:幸福不是肉体的快感,而是追求真理,寻觅世界运动变化的“逻各斯”(命运),这是人的最大幸福。
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兴趣转向以人为本位的价值主题,然而这一转向是与当时希腊城邦制的危机密切相关的。在规模上,旧有的城邦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难以容纳日益扩大的生产力。在思想上,城邦文化的狭隘性已凝固为理性的封闭状态,“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2],因此,公民们愈是执迷于城邦文化的一体感, 就愈是僵持着“严华夷之分”的孤傲态度,自诩为“天之骄子”而视周邻民族为“野蛮人”。这就难怪他们无视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 —前323)对地中海地区造成的革故鼎新局面, 丧失了回应时代挑战的能力,从而使城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氛围下,城邦的思想家们被迫对城邦生活进行根本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力图用推陈出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重新“为城邦立法”,以此挽救危机四伏的故土旧制。哲学家们通常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从自己的理想范本出发,首先考察人性根本的“本然”——人的本性是什么?然后借助“本然”假设出理想的“实然”——人依据本性的实际生活是什么?最后由“实然”推出作为最高价值的“应然”——人性完全实现的全景应该是什么?“应然”对“突然”说来是一种评判尺度,并且是植根于“本然”的价值归依,因此,它为人们引发出一种可期望于“未然”的最高理想远景。[3]
一、苏格拉底:追求“有知”而“公正”的“至善”境界。
苏格拉底首开先河,在本然”方面提出了“人性本善”论。他把早期哲学家的自然“命运”改造为神赠给人类灵魂的礼物——“善性”,并据此推论:人的本性是趋向于“绝对之善”的,因为此“善”是一切德行的共同本体,是神旨的合目的安排,因而它与人性之“善”保持着关联。苏格拉底以“定义”的形式描述了“绝对之善”与具体德性的那种离而不断、即之弥远的状态,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祈想、可追慕的理想境界。例如,灵魂中包括勇敢,勇敢有时是善,有时则不是,究其根由,关键就看是否符合善性的“勇敢定义”,接受善性定义指导的勇敢为“善”,反之则是危害人性之“恶”。其余如虔诚、自制、爱等,都是这样。
在“实然”方面,苏格拉底认为:“善性”表现为“美德即知识”。在苏格拉底的眼中,人们能不能实现“至善”,关键在于能不能获得善性知识。因为:1.知识是“至善”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苏格拉底说:“公正以及所有别的美德都是明知[的一部分]……凡是能够辨别、认识那些事情的,都不会选择别的事情来做而不选择它们;……因此,明智的人总做光荣的和好的事。”[4]这就是说, 人们只要掌握了“至善”的知识,就必然会从善如流而嫉恶如仇,因为趋善是人性的本能。而如果有人择恶去善,那么该人肯定是最大的无知。2.知识是履行“至善”义务的能力基础。苏格拉底指出:能在各行各业中建功立业并造福于社会者都是那些深谙业务的人。这说明:“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却能从美德产生好的东西。”[5]也就是说, 知识能使人赢得成功并造福于他人,因而体现出“善”的价值。反之,一个技劣的匠人,一个屡败的将军,连其本分都不能尽,更谈不上履行社会道德责任了。根据以上原因,苏格拉底指出,正因为美德是受知识指导的,无知识不能为善,所以人们要想“至善”,就必须不懈地求知,“认识你自己”,而“未经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在“应然”方面,苏格拉底断言:达到“至善”境界的标志应该是“公正”。在他看来,人们经由“美德即知识”的修练所获得的知识,实质上是认识了的“灵魂”内部状况,因此它是内在统一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这种统一的灵魂知识,就会在任何场合都凸现出道德内质。这种内在合一的“善性知识”是一个体系,它的核心内容为“公正”,而其余的德性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如“自制”是以理性实行公正,“虔诚”是以神圣守护公正,“勇敢”是坚持公正而宁折不弯,“爱”是对公正一往情深,“智慧”是参悟公正。苏格拉底据此总结道:只有人人都按照“善性知识”过“公正”的生活,才能实现城邦的“至善”胜境。
苏格拉底以“有知”与“公正”为古希腊设定社会文化价值目标,其目的在于:举荐品学兼优并心向“至善”的栋梁之材来治理城邦,以此挽救江河日下的城邦民主制。苏格拉底反复批评过“鞋匠、铜匠、农民、批发商”参政,但他并非不屑这些人的身份,而是愤恨他们不肯钻研“善性知识”,却带着经济的自私原则(如何能贱买贵卖等)来参与政事,以至把民主制搞得俗不可耐。由此可见,苏氏所反对的是把民主制平庸化的形式主义,如会场喧闹,抽签当官等,他并不反对公民自主参政、法制而非人治、思想批评自由的民主制精髓。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确实包含了某些千古不废的人生至理:其一,它昭示出人的幸福并不系于冷面无情的“命运”,而存在于人自身的“趋善”(做符合人性之事)心灵与追求真理(知识)的实践,因此人是自我成全的。这尤其表现在道德价值上,道德价值是人的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它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灵在反观自照中力求境界提升的那种自律的努力中,因此它并不过多地依赖外部条件。一个人想做道德高尚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自我成全。例如,富时可以富而不骄,贫时可以贫而无怨;达时可以“兼济天下”,穷时也可以“独善其身”。人在正常的条件下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人在非正常的条件下——例如被迫做了奴隶或是被禁束而做了囚徒——依然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道德的人。总之,在道德的向度上,重要的是主体自己的求取,而不是外部条件的改变。其二,追求真理与完善道德是一个过程。因为既然美德是受真理(知识)指导的,那么真理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人对真理的探索本身也就体现为“至善”的道德行为。这尤其表现在历史上的某些非常时期,当谎言承载着权势者的利益与淫威而恣肆漫涌,流毒天下时,敢不敢坚持事实与真理,确实是有德与无德的界线。这种氛围中的直言者虽然几乎命定是悲剧人物,但他们确实留下了彪柄史册的道德价值。当然,苏格拉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他的“人性本善”论难以说明城邦的公民的驳杂生相;而“美德即知识”过于强调理性道德却偏废了感性幸福;更重要的是,他把“公正”限于个人的内心层面,而“公正”若不通过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苏格拉底的挽救城邦方案无法被城邦公民所接受,而他为坚持自己的见解直至杀身成仁,这不能不引起后继者伯拉图的更深刻的思索,并进而提出自己的思理。
二、柏拉图:创建等级分工的“至善”社会。
柏拉图承袭了苏格拉底的思绪,并对此进行了转折性的重新解释。
首先,在“本然”问题上,柏拉图承认苏格拉底的“人性本善”说,但把善性区分为壁垒严明的等级。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绝对的“理念世界”,另一个是相对的“感觉世界”,前者是后者的本质与目的。“感觉世界”中的每一事物都追求相对应的“理念”,因此理念是“多”而不是“一”,这许多理念又分成不同的等级,“善的理念”居于等级的金字塔首,因而是最“真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善”自身又是绝对的“美”,这样,柏拉图就构筑起一个真、善、美统一的宇宙本体。在他看来,“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当然也是人性萌发的根源,因此,人性天生是趋善的。然而,柏拉图又进一步指出:鉴于神塑造的各类人的灵魂是等级不同的,因而人们赋有的“善端”也层次分明,并且追求“至善”的品位也是等差有别的。
其次,在“实然”问题上,柏拉图高扬苏格拉底道德理性的旗帜,却又添加了感性幸福的内容。在柏拉图看来,既然与人类本性对应的“善的理念”是真、善、美统一的和谐本体,因而它赋与人性的也必然是道德理性与肉体幸福相容互补的结构机制,由此决定了人所选择的“至善”生活也肯定是感性与理性、智慧与快乐协调一致生活,他说,这里有两道泉在我们身侧流涌着,一道是快乐,可以比作蜜泉,另一道是智慧,可以比作清凉剂,我们必须让这两道泉酿成无以复加的可口合剂。但他又认为,在混合生活中,理性和智慧应该占据指导的地位,因为它们是人自身的“理念”——灵魂的属性,所以理应成为肉体快乐的追求目标。据此,柏拉图断言,真正的快乐是伴随着节制的快乐,是作为德性指导下的快乐;总之,为所欲为的纵情只配称为“劣的快乐”,因为它扰乱人的灵魂。
最后,在“应然”问题上,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个人德性之公正扩大为社会分工之公正,从而别具一格地假设了等级制的“公正”城邦制。柏拉图认为:人类趋善的价值理想——德福一致之和谐,不仅要烛照个人的心灵,还须外衍为社会模式,这才是人类“应然”的“理想国”。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人类分有“善的理念”的三种“善性”: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者具有不同的品格与职责:理性禀具智慧,居上;意志体现勇敢,居中;情欲则应加以节制,居下。这三种人性的合谐一致就体现出最高的德性——公正,因为“合乎公正的人不允许他内心的各个原素不属本分的任何工作。也不允许灵魂中各个阶层彼此干涉,而要实实在在地使他内部秩序井然”。人的这三种本性外化于社会,就孕育出三大等级:仅求感官满足和肉体享受者,属国家的劳动阶级,享有“节制”美德。追求荣誉和成就而意志刚强者,为国家的军人阶层,具备勇敢品格;而专心陶冶情操和追求真理者,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赋有智慧“善性”。柏拉图还借助于高深莫测的神喻,指称这三个等级分别是由铜铁、银和金铸造的,由此规定了人类天性的不平等和不可僭越性。他认为:这三个等级“各起各的自然作用,不起别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6]这就是说, 只要国家中的各类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就等于理性、意志、欲望各司其职;智慧、勇敢、节制配合默契,从而体现出“公正”的理想社会。反之,则与人类本性和城邦公正互相矛盾,意味着国家的分崩离析。
柏拉图借助人类本性“分有”并向往“善的理念”的学说推绎出等级分工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有其历史逻辑根据的:鉴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不能为城邦公民所认同,因而民主制无法以“道德更新”与“贤者在位”的形式起死回生;柏拉图不得不设定的“善的理念”的等级力量来强制实行“贤者在位”与“提升德性”,试图改用专制的模式拯救城邦制,其居心之良苦可见一斑了。事实上,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还真渗透了某种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指南:人作为理性的社会实践者,本质上是一种“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同时即是一种“自由”——有别于动物的“他由”——的存在。因此现实的人无可规避地生活在二重性中:人不仅生存于当下可感的境遇中,人也超越可感的当下为自己设想和规划一种更值得作为自己生存之所的世界,而且这种设想和规划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当着起先的价值目的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相当程度地如愿以偿之后,人的心灵又会从这既成的新境中跃起,为自己设想并规划更新的天地。柏拉图的“理念论”无形中感通了人类本质的这种渴求。倘若依据柏拉图的初衷体会“理念”:“理念”提示着某种“应然”的批判方向,它为现实的人文世界竖起一个度之弥远的价值目标,使其不致在一井之天中自足而萎顿;“理念”也赋与理想以活力,它使人得以不断超越既得的生存对象而开拓出更值得自己生存的新环境。此外,“善的理念”还不断地引导着人们内心世界的提升与纯化。然而柏拉图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也有其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缺失:在“本然”方面,它将人类趋善的动力归因于外在理念的牵引,抹杀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实然”方面,它使理性对感性的调控趋于极端,未能为德福一致规约出合适的“度”;在“应然”方面,它所设计的等级“公正”恰与人类认同的平等公正背道而驰;因此自然不能在按民主制惯性运行的城邦中实行。柏拉图拯救城邦制的希冀无可奈何地流于失败,这从反面启发了后继者亚里士多德,促使他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路向探讨挽救城邦制的新方案。
三、亚里士多德:信守中庸的“至善”之道。
亚里士多德一改苏氏、柏氏从外在本体阐释“至善”的旧途,采用从人类自身说明问题的新方法。他指出:
第一,在本然方面,人的“善性”并非外在理念赋与的人性,而就是内在于人性中的理性。人的理性之所以表现为“善”,是由于“人们自然具有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7]。因此人能用理性支配行为、控制欲望, 使之合乎“善”。而这就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因为“理性的沉思活动则好象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能所能有的愉快,而且具有自足性、优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于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8]。
第二,在“实然”方面,人类“至善”的实践不应走极端,而应遵奉德福合度的中庸之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善性”的外在形式是“公正”,而公正则体现为中庸之道,因为“公正处于做不公正的事和受不公正的待遇之间,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多,另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少,公正则是一种中庸,而不公正则是两个极端。”[9]因此, “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10]据此,亚里士多德倡导:每个人都应遵循中道,因为“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德性……唯有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节制、勇敢以及其他的德性也是如此。”[11]例如,勇敢是中庸,因此称美德;而过分勇敢则为鲁莽,缺乏勇气沦为怯懦,因此都是“恶”。沿循亚氏的中庸原则可以导出:道德理性在人的“至善”生活中不得过分僭越,而应为感性欲望留下一席之地。事实上,亚氏也把“幸福”归结为一个和谐结构,他指出:幸福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尚、最快乐的事;最高尚的事情是最公正的事情,最优美的事情是健康,最快乐的事情是欲望得到满足。
第三,在“应然”方面,公正之“善性”向社会辐射,不是形成尊卑有秩的等级国度,而是在各个领域都实行合度之中道。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按照这个意思,中道应覆盖社会所有领域:在个人领域,中道要求每个人都否定极端,言行一致地履行公正。亚里士多德说:“合乎德性的行为,本身具有某种品质还不行,只有当行动者在行动时也处于某种心灵状态,才能说他们是公正的。”[12]这就是说,单纯客观行动上的公正,尚是“他律化”的行为, 只有在主观动机上也出于正义感的正义行动,才不愧为真正的公正。在经济领域,中庸应成为国民拥有财富的标准。在亚氏看来:极富和极贫形成两个极端,不符合正义原则,因此是社会纷争的原因。于是,他要求遵循公正原则分配财富,力求使人人拥有恰当而适度的财富。他指出:“分配性的公正,是按照所说的比例关系对公物的分配”。[13]在具体执行时,它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其数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财物在数目上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14]而“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15]在政治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滥竽充数的民主制与尊卑森严的等级制各趋极端,都与公正的美德格格不入,因此都不能采纳。公正的政治应体现为自由与法制的统一。据此,他把自由限制在法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又把权力定性为“以公共利益为归”的法律权力,力图使政治公正的功能表现为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保障公民的共同利益,稳定国家的政治秩序。在他的视野中,由于中产阶级追求的是“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16]的生活,因此,只有中产阶级才能身体力行以法律为准绳的中道,使贵族和贫民、民主和法制处于和谐的状态之中。他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17]。
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学说达到了古希腊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最高峰,它既超越了苏格拉底的倚重德性境界而鄙薄肉体幸福的片面之“善”,又扬弃了柏拉图的听天由命、等级依附的“他律”之善,把“至善”发展为主体可操作的德福一致之中道,从而第一次使“至善”摆脱了纯粹乌托邦的假设。此外,他的中道思想也确给人类生活留下了某种不可磨灭的价值,这具体表现在:从广阔的宇宙背景看,人类社会不过是宇宙自然创造力的延伸,因此二者的演化法则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这决定了人类生活在根本上不能不受到宇宙法则的影响,从而双方形成相映成趣的对称现象:宇宙法则在常态下表现为统一美好、和谐均衡、刚正有秩;与此相对应,人类的常规生活也肯认自由正义、平等合理、循规适度的价值,而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在一般情况下,中庸之道是不应被违背的,违背了它,便表现为偏颇自私、专横跋扈、非理性和过分追求,从而扰乱人类的正常生活。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只要人人做到刚健中正,不偏私过欲,不偏激过分,按规律办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就一定能达到德福一致的生活目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缺陷,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他依然眷恋于已成历史遗物的城邦制,从而既否定了个人独立于城邦的价值,又封闭了应有的世界眼光(这二个缺陷以后分别由伊壁鸠鲁与斯多葛派补救),因此他试图借助中产阶级挽救城邦制的企图,与苏格拉底感召民主制、柏拉图倡导等级制的同类目的殊途同归,都不免流一失败。
然而,尽管古希腊思想家们挽救城邦制的直接目的流于失败,但他们为西方文化设立社会价值目标的工作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设立的“至善”目标,后经古罗马哲学和基督教的拾遗补缺,至少成为中世纪以内西方人们认同的生活价值。究其原因,“至善”的价值无形中契合了人类本质的发展渴求:人作为理性的实践者,按其本性总是生活在可感的“实然”世界与追求“应然”世界的二重境遇中;而且只要人类不愿意在相互为“恶”中毁灭自身,其价值的天平在总趋势上总是倾向“至善”。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最终意义上的“至善”(至高的道德与充分的幸福极完满地匹配一致)在感性世界中也许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它的灵犀之光却始终吸引着人们“趋善”的心灵。人对幸福的向往,人对道德的企盼,人对二者协调一致的追求,并不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个民族的特殊意向,它具有终极意义,因而它属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在古希腊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创立中,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显示出感通“至善”的思想境界,柏拉图的“理念论”提供了追求“至善”的动力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设定了实践“至善”的具体标准,从而共同为这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注释:
[1]康德:《实践理性批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0页。
[2]转引自顾淮:《顾淮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67页。
[3]“实然”、“本然”、“应然”的提法, 出于黄克剑:《柏拉图“理念论”辩证》,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可参看。
[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51页。
[5][8]《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9页, 第237页。
[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7][9][10][11][12][13][1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00、32、27、20、95、25 页。
[14][15][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4、235、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