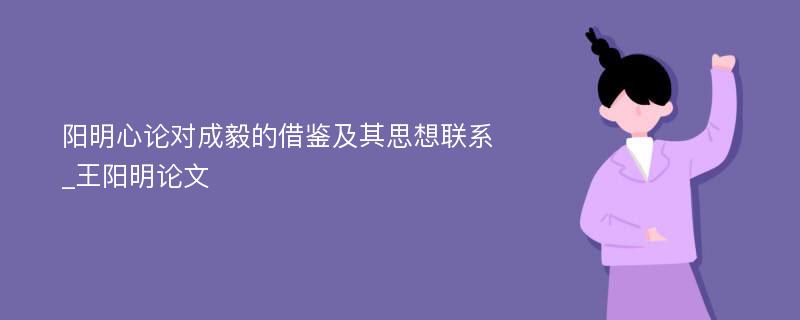
阳明心学对程颐的借鉴及其思想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说起阳明心学的渊源,一般不会想到主理派的程颐。但实际上,程颐于阳明心学厥功甚伟,而海纳百川的王阳明也确实借鉴了不少程颐的智慧和理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吸纳程颐的圣人之志,反思其“格物致知”的成圣之方 王阳明十二岁就志在圣贤,这自然跟他所处的时代浓厚的程朱理学氛围分不开。成圣成贤原本就是理学家的人格理想,如其表叔张载讲程颐:“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张载集》,第280页)程颐也自云:“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二程集》,第189、318页)程颐的圣人价值观对王阳明是有引导作用的。王阳明生平就极为重视立圣人志,曾对门生言:“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王阳明全集》,第135、102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正是在圣人之志的激励下,王阳明精进不息,百折不挠,日后终致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境界。 早年一度困扰王阳明的问题即是如何成圣。为此他专门叩问过理学家娄谅,后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可必学而至’”,阳明“遂深契之”。(第1228页)显然娄谅教给王阳明的就是程颐朱熹格物致知以成圣人的方法。程颐曾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明确表示,应“学以至圣人之道”。(《二程集》,第577页)其门生吕希哲也说:“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己必欲学而至于圣人。”(同上,第420页)程颐指出学以成圣的根本就在于格物致知:“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于理者。”(同上,第316页)他说须先格物致知,才能意诚心正身修国治天下平,才能内圣外王成圣人。对成圣的关键——格物致知,他又说:“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二程集》,第188、193页)程颐认为天下万物皆含天理,人因受气禀所拘利欲所蔽,使心中之理障而不显,故人们需从外物包括一草一木中去探究至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这样日积月累,就会豁然贯通,达到对万物所蕴天理的认识(也即豁然开显自己心中固有的天理)。他的这套格物致知的成圣之方后被朱熹、娄谅等继承。王阳明追踪程朱,身体力行格竹子,期望从竹子这一具体事物中格出至理来。但他折腾了七天,劳神焦思,却一无所获。当然他理解的只含道德伦理的天理不同于程朱既含伦理又涵物理的天理。在外物中找寻不到天理的焦虑一直困扰王阳明,直至其被贬贵州。在万山丛棘、瘴毒弥漫、野兽成群的龙场,他“日有三死”,身心极度困顿,于是静思默想:若是圣人到了如此境地,何道自处?终于在一个深夜他大彻大悟:成圣之道,吾性自足,过去格物致知向外求索实乃舍本逐末。这就是王阳明顿悟“心即理”、理在心中的龙场悟道。日后他还把格物致知发展为致知格物、致良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程颐的圣人志向及成圣之方催生了阳明心学。 二、借鉴程颐的本体论思考,力图圆融心本论与理本论 关于程颐的本体论,笔者认为他有一个从早年的理本论、心本论并持,到后来专宗理本论的过程,其中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根据《二程集》,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程颐论本体有二处,一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吕大临向程颐问学的《东见录》,内中心本论和理本论尚平分秋色,如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同上,第13页)他视心和理均为绝对的存在本体。二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程颐入关中讲学的《入关语录》。但个中已全然不见心本论的踪影,理本论之东风压倒了心本论之西风。程颐申明理本论:“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同上,第162页)程颐早年之所以是“二本”架构,主要跟其受佛学的熏染有关。他为了重振儒门、抗击佛教,曾出入佛学几十年,他的天理论即是其借鉴佛教的本体论等思辨方法重塑儒家道德伦理的结果。而中国佛学主要是主客观二个本体共存。如华严宗,虽讲“真如(心)本觉”,但它更强调法界是宇宙万物之终极归依,因此华严宗终究是以客观精神为本体。再如天台宗,纵有“一念三千”说,可它更在意的是真如缘起,以为大千世界皆以真如本体为存在依据,故天台宗也是以客观精神为本体。慧能言心尽管有真心义,但他更倾向于具体心。正如赖永海先生所说,惠能“最带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现实之‘人心’”。(赖永海,第62页)要之,慧能以主观精神为本体。玄奘的唯识宗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以为万有俱为心识阿赖耶识所现,而此变现万物的阿赖耶识也就是主观的精神本体。此外,对华严经学尤为熟稔的程颐也深受《华严经》的浸渍,而《华严经》也是主客观二个本体并行不悖。像佛驮跋陀罗的六十卷《华严经》,一方面肯定客观的法身本体的存在,以为宇宙万象皆是其显现,其是众生成佛不可或缺的外缘;一方面又认肯主观的佛智本体的存在,认为一切智慧皆依它而存在,是众生觉悟佛道的内因。 那么,程颐为何在后来归宗理本论呢?原先他未能察觉“二本”并重的不妥,但随着其天理论的成熟,他已不能允许心本论的存在了,主要缘由是心本体容易跟私欲、主观意识等具体心相挂搭。程颐说:“‘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二程集》,第256页)他笃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十六字心传”,认为人有义理之心即道心,也有从欲之心即人心,人欲之心危殆不安,道心虽是正心但精微难明。程颐也极叹主观意识之变化无常:“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悬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见《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720页)正因为心本体与具体心有粘连,程颐担心若重复早年所言的“心生道”、“心,道之所在”(《二程集》,第274、276页),就不免影响到天理的纯粹性神圣性,所以他不想再以心作为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万物之存在根据,他最终弃心本体而转为纯客观的理本体。程颐曾在元丰三年作《雍行录》,言其本人在旅途中遗失了一千文钱,而同行的六七人竟然对此事反应各异,这使他非常感慨,特意记录下来以示人心无准。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程颐彻底走向了理本论,因为写于《雍行录》稍后的《入关语录》中,他开始有了以理统心的言语,而且自此坚守理本论始终不渝,老而弥笃。 但是程颐开创的理本论到王阳明时已日显僵化、教条和虚伪,世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王阳明追究根源,认为是程颐等分心理为二使世人忙于在外物上穷索其理,不知求理于吾心,遂致“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第31、299页)在他看来,心理分二,天理不根植于心,人们的行为就会流于形式走向伪善。为了将天理真正地扎根于心,充分激发主体的道德自觉,王阳明一方面批程颐等的心理分二:“伊川所云‘才明彼即晓此’,是犹谓之二”(第168页),因程颐曾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二程集》,第193页),意即物我体现的是同一个天理,穷格物理的同时也即致我心之知。王阳明认为,程颐视理为外在的超越的本体,视心只是认识心,主张在事事物物上去探寻至理,而不是把理看成是我心之发用,这都是分心理为二。另一方面王阳明大倡“心即理”:“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此我立言宗旨。”(第133页)明言讲“心即理”,是热望人们在心上做工夫,实现道德主体的自觉自律。不仅如此,王阳明还讲“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第168页),谓心是万理乃至万物的存在根据,万事万物包括忠孝等伦理准则皆是心体之外现。故当学生问起程颐说的“在物为理”时,王阳明修正道:“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第133页) 当然,王阳明也非常清楚程颐等理学家摒弃心本论专崇理本论的原因,因此他又力图克服心本体可能导致的滞于私欲、断以己意等弊病,于是他用天理来严格规范心体。如他言:“理一而已……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第83页)说心就是凝聚理的主宰。再如,程颐言:“心要在腔子里”(《二程集》,第96页),王阳明发挥道:“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第19页)这是说程颐所言的腔子也只是天理而已。人心即便是终日忙于应酬也不该跃出天理的框范,这就是在腔子里。他还进一步指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第294页),以为理不仅是心的本质规定,也是心之具体条理;承载着天理的心才是万物的存在根据,才是即主体即本体。后来王阳明发明致良知说,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第67页),又严格规定良知的内涵即是天理,“良知只是一个天理”。(第92页)同时声明:“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孰无是良知乎?……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第296-297、117页)认为良知既内在又超越,合主体和本体为一。总括上述,王阳明的心(良知)本体可以说是在心学角度对心本体和理本体的有机统一,是在心学角度对程颐本体论思维的一大发展。 三、继承和发挥《伊川易传》,弘扬其人生智慧 《伊川易传》是程颐被贬官涪陵时写就的,也是一部忧患之作,穷尽了程颐毕生的心力。明永乐十二年修纂的《五经大全》,其中的《周易大全》就含纳了《伊川易传》。随着《五经大全》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伊川易传》被时人奉若至宝,其对包括王阳明在内的明代士子的影响自不待言。 王阳明被贬到生存条件极其严酷的贵州龙场后,在一个自名为“玩易窝”的洞穴里品味《易》理,含英咀华,著有《五经臆说》。从仅存的他对《周易》之三卦《恒》《遁》《晋》的解读中,可看到他对《周易》特别是对《伊川易传》的继承和发挥,显然后者是王阳明解《易》不可或缺的中介,从中可以看到《伊川易传》给予他的精神资粮和生存智慧的启发。 先看《恒》卦。 程颐注《恒》卦“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时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二程集》,第861页)即谓恒之道可达致亨通而无灾祸,但要保持恒久就应合符正道,失去正道就非恒久之道了。他的创新是强调“贞”(正)字,认为恒道必须是正道,只有正道才会长久。王阳明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贞即常久之道……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贞,则天地万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贞。”(第1026页)可见,王阳明承继了程颐关于贞是常久之道的思想,其对程颐的发展,一是提出“贞”涵理和诚,认为天地交感万物化生之理,圣人感化人心天下和平之诚,皆是贞;二是把贞上升到本体高度,认为天地、日、月、四季、圣人所以能常久不已是因为仰仗着贞,天地万物以贞为存在根据。 《恒》卦的卦辞和彖传都表明,《易》之恒道有“不已”和“不易”二义,“不已”是说天地的运行之道是恒久不息的,“不易”是说自然之道及圣人所秉持的人伦之道是永恒不变的,这二义俱为程颐和王阳明所传承,而后者的诠释又显然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如对《彖传》“利有攸往,终则有始”,程颐强调了不已之道:“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二程集》,第862页)即言天下之理没有不动而能永恒存在的,只有变动才能终而复始,恒久而无穷。凡是天地所生之物没有不变的,因此恒久非固定之谓,固定就不能恒久了。惟有随时变易才是常道,故而人不能泥常。王阳明的解释明显是对程颐的“照着说”:“‘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滞而不通,止而不动,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实者也,岂能常久而不已乎?”(第1026页)认为常道不是滞而不通、止而不动的,而是能够终而复始、周流不已的,如若滞止不动,也就是泥于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实,也就不是长久之道了。再看对《彖传》“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的疏解,程颐又阐述了不已和不易之恒道:“日月……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二程集》,第862页)提出观察日月之久照、四季之久成、圣人之道之长存之理,就可以发现天地万物之情理了,这就是在不已之道中有着不易之道。而王阳明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昼而夜,夜而复昼,而照临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时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复春,而生运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圣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复成,而妙用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巳也。”(第1026页) 对《大象》“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程颐解为“君子观雷风相与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变易其方所也”(《二程集》,第862页),强调君子要恒久其德性,立足大中之道而不易其操守。王阳明借鉴程颐的诠释,联系自己的处境加以阐发:“《恒》之为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簸扬奋厉,翕张而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而所以为风为雷者,则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体夫雷风为《恒》之象,则虽酬酢万变,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是乃体常尽变”。(第1026页)《恒》卦上震下巽,震为雷,巽为风,雷动风行,气势磅礴,交相开合,像是天下发生了巨变。而所以能为风为雷,乃是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这就是天下的至恒。君子体悟雷风恒之卦象,就应该酬酢万变但又卓然而立不易之体,这就是体常尽变,也就是在不已中有不易。无疑,《恒》卦更坚定了王阳明在风雷激荡的龙场岁月固守大道、从容应变的心志。 再看《遁》卦。 程颐根据儒家积极经世、刚健有为的原则,对《遁》卦进行了创造发挥。他主张君子不一定要完全归隐而无所作为,即使是阳消阴长,也应趁着阴气尚未强盛,匡扶正道并遏制小人之势。如他注疏《遁》之卦辞:“虽小人道长之时,君子知几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齐,与时消息,无必同也。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二程集》,第865-866页),可见程颐对《易传》所言隐退则亨通的说法是有所保留的。他指出小人道长之时,君子察知迹象而退避,这固然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应据时势来决定进退,没有必要搞一刀切。当阴柔生长尚未强盛之际,君子仍是有可为之道的。再如他对《彖传》的疏解:“虽遁之时,君子处之,未有必遁之义。五以刚阳之德,处中正之位,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应,虽阴长之时,如卦之才,尚当随时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诚自尽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遁藏而不为,故曰与时行也。当阴长之时,不可大贞,而尚小利贞者,盖阴长必以浸渐,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贞其道,所谓小利贞,扶持使未遂亡也……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同上,第866页)这是说虽是退遁之时,君子却未必隐去。九五既中且正,又与六二相应,即使是处于阴长之时,从卦的性质看尚可见机行事。如若可以尽力,就应竭诚匡助正道,不一定非得隐遁而无所事事。当阴长之时,虽不利于有大的举措,但还是可以有小的作为。这是因为阴气的生长一定是渐进的,不可能骤然强盛,君子还可以有小的举动,也即弼助正道使其不至于马上沦亡。圣贤尽管知晓道之将废,但怎肯坐视天下大乱而不救?在时局没有大坏之前一定会倾尽全力地扶正抑邪,以图天下得到暂时的安定。 王阳明接续了程颐这种担当社稷、扶危定倾的宏愿,他解读《遁》卦:“虽当阳消之时,然四阳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虽当阴长之时,然二阴尚微,而六二处下应五。盖君子犹在于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进,势犹不敌,尚知顺应于君子,而未敢肆其恶,故几微。君子虽已知其可遁之时,然势尚可为,则又未忍决然舍去而必于遯,且欲与时消息,尽力匡扶,以行其道”。(第1027页)认为《遁》卦虽然阳气消减,但仍有着四个强劲的阳爻,九五爻也占据着尊位;阴气虽然渐增,但初六、六二的力量尚微,六二爻处于下位还知顺应着九五爻。这说明君子犹在位,还有一帮得力的友朋,小人虽新进,但力量还不敌君子,尚知迎合君子而不敢肆意作恶。君子虽知隐遁之时已到,但看到势犹可为,则又不忍心决然归隐,他们还想顺应时势,尽力匡扶正道。王阳明还曰:“虽有可亨之道,然终从阴长之时,小人之朋日渐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是将以救敝而反速之乱矣。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修败补罅,积小防微,以阴扶正道,使不至于速乱。程子所谓‘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者,是乃小利贞之谓矣。”(第1027页)说君子的积极有为虽能使正道有所亨通,但毕竟处在阴气渐长、朋党日盛之际,若一下子裁之以正,小人将不能容忍,势必大肆作恶,这样一来,本想救弊反致速乱。故君子应对小人虚与委蛇,弥缝补罅防微杜渐,悄悄地扶持正道,使天下不至于速乱。而这些措施也就是程颐所说的“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 对付小人之道,《大象》讲“不恶而严”,程颐解为“若以恶声厉色,适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庄威严,使知敬畏”。(《二程集》,第867页)王阳明深以为然,这也有他的切身体会。正德元年,以刘健、谢迁为首的内阁大臣试图除恶务尽,一举全歼以刘谨为首的“八虎”,结果招致后者的凶猛反扑,彼等宵小肆无忌惮地残害贤良,使大明政坛空前黑暗。当仗义执言却被杖责贬黜的王阳明在玩易窝重温程颐的上述语句时,焉能不生同感?正德八年他给友人的信中犹言“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则安之而已。处之未尽于道,或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第174页)不激怒小人,同时矜庄自持,阴扶正道,这也成了他日后与小人周旋的法则。 最后看《晋卦》。 王阳明对《晋》卦初六的爻辞、象辞及《大象》的疏解,也汲取了程颐的慧思。 《晋》卦初六的爻辞是:“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刚开始长进就遭到摧折抑制,守持贞固可获吉祥;不能见信于人,暂且宽裕待时则无咎害。程颐解释说:“初居晋之下,进之始也。晋如,升进也。摧如,抑退也。于始进而言,遂其进,不遂其进,唯得正则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进,岂遽能深见信于上?苟上未见信,则当安中自守,雍容宽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故裕则无咎,君子处进退之道也。”(《二程集》,第875页)初六位于《晋》卦最下面,是前进的开始。晋如是上进之意,摧如是受到挫折而后退之意。对于刚开始的初六爻来说,无论是进或不进,只有坚守正道才能得到吉祥。“罔孚”,是指初六爻在《晋》卦的最下面且刚刚开始前进,怎能马上深得上面的信任?如尚未取信于上,就该安于中正自守,雍容宽裕,不要急着求信于上。总之雍容宽裕就无害,这是君子应对进退出处的方法。程颐的新见是:“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则悻悻以伤于义矣,皆有咎也。”(同上)是说如果急于求得上面的信任,不是躁进导致失去操守,便是怨忿而有伤义理,二者都有害。 《晋》卦初六的象辞是:“晋如催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上升之初就受摧折抑制,故初六当独自践行正道;宽裕待时则无咎害,因为初六尚未受到任用。对此程颐在继承的同时也有发明:“无进无抑,唯独行正道也。宽裕则无咎者,始欲进而未当位故也……圣人恐后之人不达宽裕之义,居位者废职失守以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进未受命当职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职,一日不可居也。”(同上)他说无论进升与否,只要坚持正道即可。“宽裕则无咎”,是因为刚想升进还没有官职在身的缘故。圣人恐后人不解宽裕义,把废弃职守当作宽裕,故而特别强调:初六宽裕而无咎,是专对那些开始进升但尚未有官职的人说的。其意思很明确,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不能算是宽裕。他还指出如有了官职但不能取信于上并且失职,那么这个官位是一日也捱不下去的。 王阳明承续了程颐的上述思想,如说:“初阴居下,当进之始,上与四应,有晋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进,不暇与初为援,故又有见摧之象。当此之时,苟能以正自守,则可以获吉。盖当进身之始,德业未著,忠诚未显,上之人岂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于求知,则将有失身枉道之耻,怀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来必矣。故当宽裕雍容,安处于正,则德久而自孚,诚积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盖初虽晋如,而终不失其吉者,以能独行其正也。虽不见信于上,然以宽裕自处,则可以无咎者,以其始进在下,而未尝受命当职任也。使其已当职任,不信于上,而优裕废弛,将不免于旷官之责,其能以无咎乎?”(第1027-1028页)他说初六居下,与九四相应,有前进的迹象。然九四正自谋上进,无暇对初六施以援手,故初爻又显被摧折之象。此时若能以正道自守,则可获得吉祥。因为刚求上进之际,德行、业绩和忠诚还不显著,岂能即刻见信于上。倘这时急迫地寻求这种信任,将会有失节、枉道的耻辱或心怀怨恨、耍弄心计的非议,从而必然招致懊恼或责难。故此应当宽裕雍容,安于正道,就会积德而增加自信,积诚而自我激励,这样又何咎之有?初六虽刚开始上进但终究不失其吉祥,这是因为能独行正道吧。虽不被上面信任,然以宽裕自处,就可以无咎,这是因为初六刚开始上进地位卑下,未尝有一官半职的缘故。假如已有职责在身,不被上级信任还废弛政务,将免不了渎职之问责,焉能无灾祸呢? 同时王阳明也有自己的创新。《晋》卦《大象》云:“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即谓光明出于地上,象征升进;君子由此明白要自我彰显其美德。程颐诠释道:“君子观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二程集》,第875页)君子看到光明出于地上且愈益鲜明盛大的卦象,以此领悟需自我彰显其美德:一是通过除去私蔽和格物致知而显美德于己,再就是通过昭示美德于天下而显美德于外,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要靠自身主观的努力。显然程颐把格物致知看成是明明德的主要途径。而王阳明的疏解是:“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第1027页)意即心之德就像太阳本无不明,之所以有时晦暗无光是因为被遮蔽了。只要除去私欲,人心又会焕发出它本有的光辉。就如太阳是自己出来的,与天无涉,君子之彰显美德也是自觉自愿的,并非他人干预的结果。可见,王阳明在解《晋》卦时已摈弃了程颐向外格物的路径,确立了其内求的心学路向。他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自觉,去私除蔽,恢复心体之本然,自我成就光明俊伟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