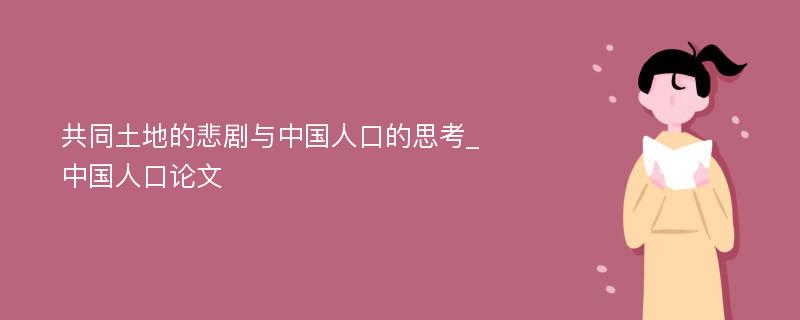
“公用地悲剧”与中国人口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公用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其副标题是,“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技术,它需要更为广泛的道德规范”(The population problem 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it requires a
fundamental extension in morality.)。有趣的是,这篇由解决人口问题而引发讨论的论文,一直未被人口学家所关注,但却频频为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所引用,并成为博弈论中集体行为选择困境的一个经典例证。诚如哈丁指出,人口、环境以及核武器军备竞赛等这类人类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依赖技术途径,而是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观念的转变。重温“公用地悲剧”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和观点,检视当今世界二元人口格局,相信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2 “公用地悲剧”与社会悖论
哈丁认为,有限的地球只能承载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不可能无止境增长下去。然而,现实世界中人口生育是自由放任的,而这种自由放任的生育终将会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那么,“公用地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呢?哈丁以公共牧场上牧民们可以自由放牧为例描述了“公用地悲剧”的发生机制。哈丁指出,作为每个理性的牧民,都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公共牧场上,牧民会有意或无意地问自己“增加一头牲畜会给我带来有多大的效用(utility)”,这个效用有正负之分。正效用是增加了一头牲畜带来的好处,即牧民获得出售这头牲畜的好处,牧民可获得几乎全部的正效用+1。负效用则是由于增加了一头牲畜而产生的过度放牧。过度放牧的后果被全体牧民所分担,所以对每个做出增加牲畜头数的牧民来说,其负效用仅仅是若干分之一,分母越大,牧民承担的负效应就越小。正负效用计算的结果,使每个理性的牧民都会增加自己畜牧头数,而且会不断增加。在有限的公共牧场上,由于牧民们可以自由地放牧,牧民每增加一头畜牧都会给自身带来利益。然而每个牧民做出这种对自身有利的理性选择,则会使公共牧草地上的畜牧头数不断增加,其累加的结果则是公共牧草地上过度放牧,最终导致牧草地贫瘠、荒废。这就是哈丁著名的“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的论断(Hardin,1968,p.1244)。在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选择问题上,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正效用大于负效用,并且正效用为个人独得,负效用则为集体均摊。如果不做这种选择,不仅不能维持原有利益,而且会使原有利益遭受损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必然会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而每个人这种选择则终将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美国社会学家Robyn M.Dawes对过剩人口、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所引发的“公用地悲剧”称之为社会困境或社会悖论(social dilemmas),他概括了这些社会悖论的两个特征:如果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有两种行为选择,非合作(Defecting Behavior)与合作(Cooperative Behavior),那么,其一,非合作选择(D)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合作选择(C)所获得的利益;其二,全体非合作选择所获得的利益则要小于全体合作选择所获得的利益。用数学公式表达社会悖论的两个特征则是:(1)D(m)>C(m+1)(0<m<N-1)。也就是说,在N个人的博弈中,在只有部分成员(m)选择合作的情况下,选择非合作(D)所获得的利益大于选择合作(C)所获得的利益;(2)D(N)<C(N),即在N个人的博弈中,全体选择合作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全体选择非合作所获得的利益(Dawes,1980)。实际上,这些社会悖论都是典型的N人囚徒困境。
哈丁在论文中最后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公用地上自由生育的必然性”,只有尽快停止自由的人口增长,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自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终止“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3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人口悖论
3.1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困境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强烈关注。就在1968年哈丁发表“公用地悲剧”的同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奇(P.Ehrlich)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埃里奇也认为,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与过剩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埃里奇曾预言,人口的迅速膨胀会导致饥荒、资源枯竭、不可避免的环境恶化以及生物圈毁灭(Ehrich,1968)。虽然,哈丁和埃里奇所谓的“人口悲剧”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在不少人口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饥饿、贫困、环境恶化却一直存在。
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就有着明显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发达地区0.83个百分点,到2000年,二者差距增加到了1.31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正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突飞猛进增长,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50年,世界人口仅为25.2亿,半个世纪以后,世界人口已突破了60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由17.1亿增加到48.7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由67.9%上升80.4%。
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有众多的赤贫人口。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2000a,p23,2001),60亿世界人口中近一半人口(28亿)每天生活在不足2美元中,1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12亿贫困人口中,44%分布在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占24.3%,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23.2%,都分布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除东亚地区以外,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继续增加,如南亚地区的贫困人口从1987年的4.74亿增加到1998年的5.22亿,拉丁美洲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上升了20%。20世纪曾是人类历史上财富增长最快的世纪,但并没有遏制贫困人口的增加,而且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这种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扩大了1倍。在富国每100名儿童中寿命低于5岁的不到1人,而在最贫穷的国家则多达5人。同时,富国儿童在5岁以下营养不良的不足5名,而在穷国中50%的5岁以下儿童都有儿童营养不良现象。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人口增长是导致贫困、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哈丁在“公用地悲剧”中描述的人口增长、资源环境、贫困之间的制衡关系却是存在的,人口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是存在的。美国学者Kelley和Schmidt的最近研究发现(世界银行2000b,p67,2001):1960~1995年之间的85个国家中,人口快速增长都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减缓作用。而经济发展的迟缓、人均收入提高的缓慢又必然对消除贫困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肯定,不少人口可以无任何限制自由生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过快增长拖累了经济发展,从而无法摆脱贫困,无法摆脱“人口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地区都存在着哈丁所谓的“公用地悲剧”的色彩和印迹。
表1 20世纪后半叶世界及发达、欠发达地区和中国出生率、增长率变化
‰,%
年份 全世界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中国
(不含中国)
CBRPGR CBR
PGR
CBR
PGR
CBR
PGR
CBR
PGR
1950~1955 37.3 1.77 22.0 1.21 44.4 2.04 44.7 2.12 43.6 1.87
1955~1960 35.5 1.85 21.1 1.18 41.9 2.15 44.7 2.43 35.9 1.53
1960~1965 35.2 1.98 19.6 1.10 41.8 2.36 43.6 2.49 37.8 2.07
1965~1970 33.8 2.04 17.3 0.81 40.3 2.53 41.8 2.49 36.0 2.61
1970~1975 30.9 1.95 16.1 0.79 36.3 2.37 39.9 2.44 28.3 2.21
1975~1980 28.3 1.72 14.9 0.65 32.8 2.08 37.6 2.34 21.5 1.48
1980~1985 27.4 1.71 14.5 0.57 31.4 2.07 36.0 2.35 20.3 1.38
1985~1990 26.6 1.70 13.9 0.60 30.2 2.02 33.5 2.21 21.9 1.53
1990~1995 23.9 1.46 12.3 0.41 27.1 1.75 30.4 2.00 18.3 1.10
1995~2000 22.1 1.33 11.2 0.28 24.9 1.59 28.1 1.84 16.2 0.91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1999
不过,就在哈丁当年极度担心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公用地悲剧的时候,哈丁并没有料想到发达国家会陷入另一种人口困境、另一种“公有地悲剧”。
3.2 发达国家的人口困境
就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我们在发达国家看到了另一种图景,发达国家的人口落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从理性出发,都从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益最大化出发,个人、家庭都不愿意生育养育孩子而失去个人或家庭的“享受”;另一方面,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不愿意生育,集合的结果是地区、国家的总人口、劳动力人口呈现出老化和衰减,而人口的老化和衰减又影响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体人口的福利提高。从表1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经历了50年代的“婴儿热”之后,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世纪60年代,其人口增长率降到了10‰以下;90年代,降到了5‰以下。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率,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
比较几个重要的发达国家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变化情况(见表2),或许会看到发达国家这种人口困境的后果,会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二战以后,美国、日本、德国等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尤其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创造出了亚洲奇迹,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大有超越美国之势。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欧盟的经济进入停滞、波动时期,失去了持续的经济活力。对于这些同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这种不同经济发展差异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就人口学家所关注的人口要素而言,可以看到,美国与日本、欧盟区国家有很明显的不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在经历了短暂的“婴儿热”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开始减慢,日本、欧盟等国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总和生育率(TFR)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到20世纪末,日本、德国更是降到了1.4以下;不过,美国有所不同,生育率水平虽然一度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徘徊在TFR2.0左右。与此同时,由于生育水平的不同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差异也很大,日本、欧盟等国的人口老化水平不仅在20世纪末明显高于美国,而且在20世纪后半叶,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尤其是日本。从1990~20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12%上升到了17%,增加了5个百分点,德国增加了1.4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仅变动了0.1个百分点。日本人口迅速老化与经济衰退和乏力相重叠。20世纪80年代,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3.8%,处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进入90年代,GDP年均增长率滑落到1.3%;而美国80年代为3.4%,90年代为3.3%,保持长达近20年的高增长水平不变。与日本情况类似,由15个发达国家组成的欧盟,由于13个成员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都达到或超过了15%,各国人口增长率接近零或已负增长,所以,欧盟区也面临着由于出生率下降使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持续性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1.5%。此外,欧盟区国家由于近年来有大批非法移民涌入,对欧盟各国的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又构成了威胁。日本、欧盟今天的人口现实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生育率迅速降低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另一种人口困境,与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压力加重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和持续性,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其它社会问题,如社会稳定,民族冲突等。
表2 发达国家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比较亿;%
年份美国日本德国
法国
英国
人口
65+ 人口
65+ 人口
65+ 人口
65+ 人口 65+
19501.58
8.3 0.83
4.9 0.68
9.7 0.42 11.4 0.51 10.7
19601.86
9.2 0.94
5.7 0.73 11.5 0.45 11.6 0.52 11.7
19702.10
9.8 1.04
7.1 0.78 13.7 0.51 12.9 0.56 12.9
19802.30 11.2 1.17
9.0 0.78 15.6 0.54 14.0 0.56 15.1
19902.54 12.4 1.23 12.0 0.79 15.0 0.57 14.0 0.58 15.7
20002.78 12.5 1.26 17.0 0.82 16.4 0.59 15.9 0.59 16.0
资料来源:同表1
如果说,哈丁当年观察并预料到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过快增长会影响到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公用地悲剧”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困境则是哈丁时代所观察、所料想不到的。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要素条件是劳动力充足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上述发达国家之间20世纪后半叶人口比较已经发现,美国不仅保持稳定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人口活力(较慢的老化速度),而且,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明显占据优势。在2000年由美国《有线》杂志咨询各地政府、工业和媒体界人士评选出的46家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中,美国有13个,而日本和德国分别只有2个和3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因此,2002年8月最后一期的英国著名杂志《经济人》撰文指出,美国和欧洲大陆在未来50年人口发展趋势完全不同,美国人口将继续保持活力,并将在2040年甚至在此之前,人口总数超过欧洲;而欧洲人口则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将继续老化。由于人口较之于社会、经济力量是一个影响人类前景更为持久的、广泛的变量,人口变化不仅被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更为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所关注。所以,毫无疑问美国仍将在21世纪至少上半叶保持人口活力,保持其强大的国力。并且,由于移民人口结构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将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了世界人口的二元格局,看到了世界人口的两种困境,一种是哈丁所发现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公用地悲剧型”;另一种则是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口困境,可称为“后公用地悲剧型”。在哈丁的“公用地悲剧”中,个人和家庭在理性驱动下选择多多生育,其集合的结果是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过快增长意味着有限的、自然的公有资源会被加速占有、加速耗尽,最终制约发展,危机人类。在哈丁看来,发展中国家每多增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在公用地上多增加了一份负担。孩子对每个家庭虽然是幸福的,但对集体却是悲剧性的。在发达国家的“后公有地悲剧”中,个人和家庭在理性驱使下选择不婚、不育、或者少生,其集合的结果是人口趋于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这样的人口状况意味着一个国家可拥有的最基本的公共人口资源在减少在恶化,而人口资源的减少和恶化又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长远的综合国力(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发达国家每少生一个孩子,就意味公用地上少了一份财富(即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其结果是,不仅自身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各种社会福利难以为继,而且,这块“公用地”还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口所迁入、所占用(如欧盟的非法移民)。不育、少育对每个家庭虽然是幸福的,但对集体却是悲剧性的。实际上,无论是在哈丁的“公用地悲剧”、埃里奇的“人口爆炸”里、还是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背后,西方这些学者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口变迁模式怀有着深刻的忧虑。毕竟我们人类自身、我们每个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追求持续辉煌、永恒长存的偏好。
4 关于中国人口的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迎来了战后和平时期的人口恢复性增长,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迎来了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表1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人口虽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有些差距,但都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中国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平均保持在35‰以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则在40‰以上。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人口变化的分水岭,也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人口变迁轨迹分道扬镳。实际上,就在哈丁、埃里奇等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忧心忡忡的时候,由占世界人口近1/4、占发展中国家人口近1/3的中国人口大国引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开始显著下降。毫无疑问,中国人口对整个世界人口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从2.37%下降到2.08%,降低了0.29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下降了0.73个百分点,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只降了0.10个百分点。显然,中国人口增长迅速下降带动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下降,其带动下降的贡献率高达75%以上。进入21世纪,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肩,甚至还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所以,在20世纪末也迅速的迎来了老龄社会。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大大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水平(4.5%),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口会迅速老龄化。21世纪初,中国人口再次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三低”状态,生育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不必要再担心中国人口会落入哈丁所谓的“公用地人口悲剧”。其实,中国最需要担心的是要避免陷入这样一种困境:经济实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却由于人口迅速老化而失去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避免和延缓20年后出现今天日本和欧盟所出现的人口老化和经济乏力的状况。根据联合国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5)预测,从2020年到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由12%上升到17%,相当于今天日本的水平。日本二、三十年前并未料到今天人口迅速老化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而如今刺激其人口回升却已回天无术了。未来人口的这种局面是我们应当要警惕和回避的。
应该承认,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二元格局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既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也有早生多育的生育观念的影响;同样,发达国家人口趋于不生、少生,也有强烈的生育观念、幸福价值观的支配和影响。这些人口多生或少生问题诚如哈丁所言,不是一个仅用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会涉及到人类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问题。对于一个致力于调控未来人口发展的政府而言,必须要重视人口变化的复杂性,要把握人口发展的变化规律,要把握调控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机,而不是一味只重视主观意志对人口数量的控制。的确,中国宏观人口政策到了该反省和重估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无视发达国家的人口经验,将我们的人口迅速推向“后公有地悲剧”,减弱我国持续发展、持续繁荣的能力。
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有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还不到位。其一,是对人口变量自身变化规律认识不足,即人口变量变化的周期性、惯性、滞后性等。例如,虽然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人口就进入了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一、二十年。再如,要避免未来20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小和迅速老化,现在就必须调整生育水平。由于人口变量的这些特点,我们调控人口必须要有前瞻的眼光和足够的耐心,任何急功近利的人口措施都会带来后患,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其二,我们对确定性问题相对重视,而对不确定性问题缺乏警惕。人口数量、人口压力一直是我们当下以及今后长期关注和重视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而,对于人口结构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于不确定于现在而发生在未来,所以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越是只关注规模问题、只注意尽快解决数量问题,就越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如果不加以警惕,这些问题很可能为中国所独有,既不会像传统的发达国家(如法国人口老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不会像战后日本人口迅速老化是发生在经济发达以后。同时,还有可能带来许多现今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结构问题(如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民族结构的改变而引发的民族冲突等)。
5 余论
对于有限的地球资源和有限的地球空间而言,世界人口不可能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由于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因此,大大地遏制了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哈丁所谓的“公用地悲剧”的发生,对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人类人口有可靠的记录以来,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举足轻重,一直占世界人口1/4强。随着世界其他国家人口在“地球公用地”上的继续增长,中国人口的比重会明显下降,200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已降到了1/5。2050年,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TFR为1.9),中国人口比重会降低到17%以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口这种变化是为人类人口避免“公用地悲剧”做出了“牺牲”。如果中国继续维持严厉的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后公用地悲剧”之中,这不仅使中国人口承受重大损失,使中国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也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损失(李建新,2002)。在新世纪人口政策问题的抉择权衡中,我们需要高瞻远瞩、需要大智慧、大战略。我们要吸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变迁的经验,摒弃两种人口悲剧的“风险”,超越“左右”,寻求中国人口发展的“中庸之道”,即既不在有限的地球公用地上自由放任人口增长,也不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还在继续放任或鼓励人口增长时追求减少人口。人口发展的“中庸之道”是避免世界人口发展的两种极端,是寻求兼顾解决数量和结构问题的最佳结合点,是寻求现时与长远、微观与宏观、家庭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是寻求中国与世界人口平衡的最佳结合点。就目前中国、世界人口形势和各国人口经验而言,坚持二孩生育政策,坚持人口数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统一,坚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就是这种“中庸”、“中和”大智慧在中国人口政策选择中的具体体现。只有这种追求和选择,才是保证中华民族世代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