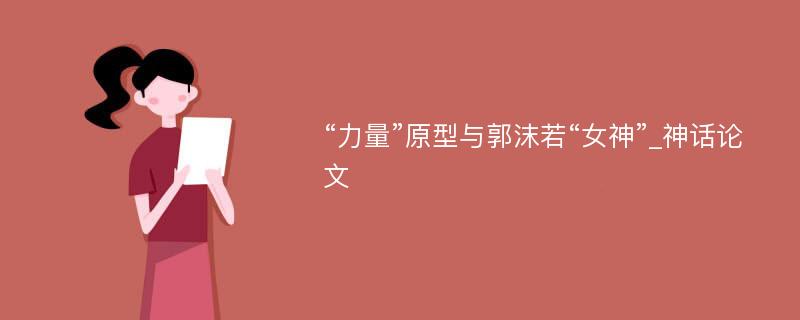
“强力”原型与郭沫若的《女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原型论文,女神论文,强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力”原型是上古神话积淀给中国文学的一大原型
回视上古神话世界,我们会深深地惊异于那个以“强力”为核心的世界,惊异于那一系列“强力”性的神话形象。开天辟地者盘古,曾以巨力左手势凿,右手持斧,将浑沌的天地一分为二。这一伟业体现了初民在无序的自然界中生存斗争的伟力。“人头蛇身”的女娲,更令人起敬,她以神气抟黄土作人,以智力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而且以巨力“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注:《淮南子·览冥训》。)她是中国神话系统中的一位智能高强的富于巨力的人类创造之神。共工怒触不周山,对世界秩序(人群秩序与自然秩序)作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注:《淮南子·天文训》。)共工的伟力使世界秩序走向平衡、稳定。夸父、精卫、后羿、大禹等,均以强力饮誉后世。神话世界是一个以“强力”为音符的世界。“强力”是上古神话中反复显现的联通每一神话的精魂,是上古神话中的一大精神内质。
西方哲人对此早有所悟,亚里士多德认为,象征性地表现自然的力量,是一切早期神话的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把自然力形象化”。原型批评理论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同样认为:“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其人物性格具有最大可能的行动力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处境中的先哲,均以慧眼洞察出人类早期文化的特征,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呼应。由此我们更加确信下述论点的科学性,即“强力”是上古神话重要的精神内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精神原型。
儒家文化导致“强力”原型的失落
上古神话因其强力精神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审美主体的心灵,然而中国古典文学却未能真正地将其精神原义承续下来,“强力”这一深远的文学原型,在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中,几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显现自己本质的形式。
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适应着宗法式农业社会的需要,“强力”不再受到崇拜,以力为核心的原始文化哲学精神被新兴的儒家文化所取代。儒家文化的盛行是神话“强力”原型失落的根本原因。《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他所推崇的是德治文化。他希望以仁、义、礼、乐等观念统一人心、统一艺术。他从“思无邪”原则出发,对当时的代表性作品作过评判。他认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注:《论语·八佾》。)是好的作品,而《武》乐尽管乐舞很美,思想内容却并非“德至”的作品,它歌颂的是武功,与仁义道德相背,所以是“尽美也,未尽善矣。”(注:《论语·八佾》。)《韶》则不仅美,而且歌颂了孔子理想的礼让政治,所以他誉之为“尽美也,又尽善矣。”(注:《论语·八佾》。)“善”才是儒家审美取舍的最重要标准。怪、力、乱、神非善也,所以被抑制乃至衰亡。孔子倡导的“温柔敦厚”即“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发展到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占统治地位的审美原则,统摄着主体的意识乃至潜意识层面的艺术创造心理与鉴赏心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直接导致了中国上古神话“强力”原型的失落,正如鲁迅先生在《
超越、回归、超越:对《女神》“强力”原型的破译
普雷斯科特[F.C.Prescott]认为“神话创作者的心灵是原型;而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注:普雷斯科特[F.C.Prescott]:《诗歌与神话》,转引自卡西尔的《人论》第96页。)这一精辟的论断,道出了诗人与神话作者艺术心理本质上的共同性。“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其文化艺术心态正是神话式的“强力”心态。那个时期最流行的口号是个性解放,青年人高喊着“上帝死了”的口号,他们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要打破一切现存的秩序与权威,而以自己的尺度来审视一切。深受传统文化压抑的郭沫若,一旦接触到西方新的主义与思潮,呼息到新的时代气息,其心理便十分地昂奋。加之,他本是一个主观倾向十分强烈的人,所以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打破偶像的要求,自然比一般人来得更为强烈。中国封建文人那种“静美”的精神在他那里荡然无存。他完全超越了几千年来中和的封建传统,“温柔敦厚”心理被强烈的自由意志、个性精神所取代。郭沫若这种酒神心态在本质上回归到人类远古时代的“强力”原型心态上。因而,他具有“原始的幻想能力”,对原型特别地敏感,强烈地渴望通过艺术形象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欲望、经验转化为外在的世界。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并不意味着丝毫的倒退,与封
所以,郭沫若自觉不自觉地与神话建立起了直接的心理联系,使自己明显地区别于封建文人,在酒神精神状态下营构自己的艺术宫殿。这是《女神》之所以成功的创作主体自身的心理根源。
在奔腾不息的文学长河中,《女神》凭借创作主体的“强力”原型心态,成功地实现了对封建文学的超越。封建文化主静不主动,封建文学在儒家话语控制下,更是以“静穆”为美的极至,未能真正地表现出神话所显示的人类固有的“强力”精神,中庸之气笼罩文坛。陶潜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心远地自偏”正是大多数中国封建文人艺术心态的写真。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完全突破“温柔敦厚”、“思无邪”等传统的审美原则,“力”的意识淡薄了。即使是一些豪放派文人如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诸人,在封建文化下虽以艺术家的良知与胆识,或凭籍历史的非常时期,或以艺术的特殊方式,发自内心地表现了“力”的精神,但那只是一些受封建文化限定的“力”,受儒或道思想改造、净化过的“力”,因缺乏神话之气概和现代理性的烛照而显得不力。他们在表现“力”时,常常用的是如下审美物象:大漠、黄河、塞北、孤烟、西风、长剑、楚天、金戈铁马、虎狼、五岳、烽火等,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大都为半开放型的大河民族的文化物,是农业民族封闭性思维的联想物,表现的仅仅是宗法——农业社会的气势。与之相比,《女神》则完全突破了一切因袭的封建传统与经验,超越了几千年来的束缚“力”的表现的
在超越封建文学的同时,将其精神回归到神话“强力”原型那里,将种族记忆中的“强力”以诗的形式显现出来,从而与人类的共同经验建立起直接联系,与人类的底层欲望进行直接对话,这是《女神》所显示的超越时空的文化意蕴。荣格认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文学艺术的创造过程就是神话母题(原型)被翻译成现代语言重新显现的过程,伴随着原型的显现,将会出现一种神话式的转化情境。当这种情境出现的一刹那,“总是以一种感情上的罕见的强度为特征,宛如我们身上从未奏响过的心弦被拨动了,又仿佛是我们从未想到的力量得到了释放。”(注:The Spirit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C.G.Jung London 1966,第81页。)这是一股神奇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乖戾蛮野的创作欲望,主宰着作者的审美走向。有趣的是,郭沫若曾透露了自己创作《凤凰涅槃》时类似的情境“《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内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的意趣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
《女神》的精神内质是创造力、破坏力,《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神话“强力”原型的载体,她的人格结构的支点与核心是神话“强力”精神。1919年,郭沫若在《立在地球上放号》中,以惊人的气魄,勾画了一幅充满神力的自然景观:“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诗人对毁坏之力、创造之力作了直接的赞美:“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他那亢奋的心理一旦接触到“力”,仿佛便找到了归宿似的,在不能自己中,深层的压抑过久的“强力”情绪得以释放,他感到了特别地轻松、兴奋,似乎回到了渴慕已久的陌生而又熟悉的精神家园。
上古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在《女神》的艺术世界中复活了,她们以当年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力量与气概,面对无序的现实,高喊着“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她们要以自己的力量使无序的世界重新走向有序,使黑暗的现实充满光明。郭沫若的“女神”是“神话女神”在现代的艺术显现,它激活了“五四”以来一代代审美者身上处于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强力”记忆,由此,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
在《创造者》里,诗人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取向:“我要高赞这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这个“大我”具有超凡的开辟鸿荒的人格,是能与力的集大成者。他崇拜的是具有神力的物象:“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这是一股能冲破一切的“怪力”,它对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这个“大我”不仅具有创造、破坏的精神力量,而且崇拜自我本质,把自我本质力量神化:“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这是一种爆炸性的自我膨胀,人的价值、尊严、力量第一次得到了完全肯定。
回归到神话原型,充分表现了生命之力与宇宙之力,由此与人类深层的心理积淀、心理欲望进行直接对话,从而发出了人类的共同声音,抒发了人类的共同情感,这是《女神》的重要魅力所在。
然而,如果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回归,那么《女神》还不会具备那样大的划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女神》并未停留在机械地回归到神话“强力”原型的层面,而是以现代文化作基础,在回归的同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的超越。
神话所显示的“强力”原型,虽然具有非凡的气势,体现了原始初民的生命形式与本质,但它是直观的原始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未经修复的非理性的力量,它的指向意识不明确,它是初民在蒙昧中对世界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股本能力量,所以缺乏现代人所追求的主体意识。而《女神》所蕴含的“强力”精神则是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自然科学为背景,是一股乐观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力量,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它是以反封建偶像与创造新的世界为目的的。与神话原型“力”的本能性相比,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在矛盾斗争中,它永远居于主导的支配的地位。神话原型“力”虽然具有非理性的超常的力度,但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初民生活视野的极端狭窄,他们只能直观地发现眼前的与自己生活极为有关的事物,对外界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封闭性的世界,这就决定了神话所负载的原型“强力”是一股封闭性的力量。而《女神》之“力”则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完全突破了陆地文化的束缚,是一股现代性的开放性的力量。《女神》的抒情主人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与宇宙,而不是偏狭的一隅,他不仅向扬子江、黄河问候,而且向着恒河、印度洋、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他要驾驭的是现代文明的X光,Ene
综而言之,郭沫若的《女神》超越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学,回归到神话原型“强力”那里了。它所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了永恒的王国中,将个人的命运纳入到了人类的命运中;同时,又以现代文化为基础超越了神话“强力”原型,从而使初民的文化哲学精神即“强力”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使“强力”原型在现代意义上得以复生,由此激活读者“种族记忆”中的“强力”心理,使他们找到了回返最深邃的生命源头的途径,使他们在现代物质文明压迫下充满自信心,驱除迷惘情绪,使他们受压抑的意识得以释放,心灵得以补偿。《女神》的人类文化精神与艺术生命之谜即在此。
标签:神话论文; 论语·八佾论文; 郭沫若论文; 神话创造论文; 文化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上古神话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