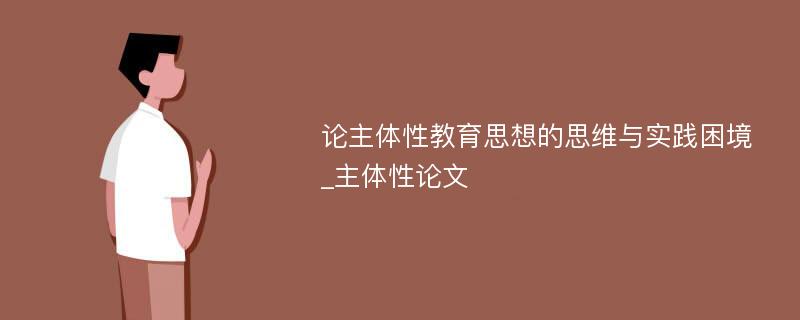
试论主体性教育思想的思维和践行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教育论文,试论论文,困境论文,主体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相反,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界却愈发强调教育对象的主体价值和能动作用,认为人不是被动消极的客体,而是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自主的人”;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实然中强调并调动起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就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充分挖掘出人的潜能,张扬学生的个性,培养出知、情、意合一的全面发展的人;进而造就出学会学习和学会生存的人,从而就能使个体和教育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激烈的社会竞争。然而只要加以深刻地省思,我们就会发觉这种强调主体的主体性教育思想,在学理上是有待商榷的,在践行上是问题重重的(实际上,诸次教育改革所不可解决的迷惘均与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为理据和指导有关);而且我们还会发觉这种教育思想远没有进入现代哲学和教育学的思维境地。
主体性教育就其历史发展而言,实质上包括自然性主体教育、科技理性的主体性教育和价值理性的主体性教育。自然性主体教育是以近代唯物论为哲学基础的,把人归结为一个自然实体,用物的特性来把握人,认为人的发展服从于自然发展的规律。如17世纪的夸美纽斯就把“教育适应自然”的原理作为一个主导原则贯彻其教育思想的始终,并落实到他所设计的“新学校”中。卢梭提出了“归于自然”的纲领,主张把儿童置于大自然中,把人培养为自然人。在自然性主体教育中虽注意了个体人,打破了宗教神学关于人的超验的观点,但人被贬为物一样可改造的客体,人的自主性沦为物的可改造性。在科技理性的主体性教育中,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人类之间的竞争作为生存的原则,如哲学家和教育家洛克和康德分别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这种发展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理性发展的教育无疑是教育的进步,但这种教育仅仅重视占有性个人主体的发展是错误的,这种主体性导致了人本质的异化,人成为欲望的奴隶,成为工具。价值理性的主体性教育针对科技理性的教育只注重人技术理性的发展,忽视了人价值方面的情感、意志的发展,提出教育强调人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如存在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就主张“让教育为个人而生存”,教育应启发受教育者对自己生存和价值的认识,启发个体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但这种教育思想有着顽固的精英主义情结,而且过于理想化,往往仅仅停留于学理上。
可见主体性教育思想,一般是指教育应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为前提,运用充分发挥教育对象主体性的教育方式,以形成学生自我发展和完善,以及自律的能力和品质为目的的教育。它实质上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以培养能驾驭、控制并推动自己不断完善和发展,进而成为独立、理性、自为和自由的主体为目标;二是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发挥其创造性和能动性,强调学生的自主建构,即教育对象的精神世界是自主地能动地生成的而不是借助外部力量形成的,进而反对“师道尊严”和被动式的教育模式;三是在教育内容上重视唤起教育对象自我意识的内容,反对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化要求的内容。可见,主体性教育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无非就是以唤起学生的自我意识为前提,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主体性的道德人格(即所谓的独立、理性、自为、自由的人格)。无疑“主体”在主体性教育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因而对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反思理应以省思“主体”为突破口。
主体性教育思想非常重视唤起教育对象的“自我意识”,注重“个性”张扬,强调培养“独立、理性、自为和自由”的道德人格,反对规范和强制,藐视标准化等。可见主体性教育思想视阈下的主体被理解为一种个体化的理性主体,是一种脱离生活世界的抽象个体;对这种主体的运思方式,实际上是把人看做是单体式的人。这种“单体式的人”的概念实质上近代哲学思维的产物。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作为一切哲学的绝对基础,于是“哲学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出发点是绝对确定的‘我’,我知道这个‘我’呈现在我心中”。[1]这就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以思维为原则,自我即思维主体,认识主体成了认识论的前提,它所确定的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先在确定性。甚至以近代唯物论为基础的自然性主体教育也摆脱不了从抽象来诠释人和历史。如卢梭认为人类在社会和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曾经处于按照自己的“天然本性”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在此状态中没有工业、农业,没有住所;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道德上的善恶观念,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显然,他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是不科学的,历史上实际上并不存在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自然人。[2]近代主体性改变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国家关系的理解,堪称实现了一场“革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近代主体陛并没有达到关于“人的形象”的真理:它从人的本质出发,视自我意识为人的本质,全然否定了自我意识也有预设和前提,阻断了人的本质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即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人永远都是社会关系的人,人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生活世界而成为自在的抽象的个体。由于共同的对抽象“单体”式人的认同,因而主体性教育思想有着主体性思想相同的理论和践行困境。
第一,主体性教育思想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者对自我的限定,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这必然导致教育对科技理性的认可和崇拜。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主体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把社会视为一个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不管这个部分是国家的政治公民,或联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忽视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而且无视生活世界的整体构成了观察问题的具有优先性的整体背景。[3]科技理性是一种被限制于工具而非目的领域的理性,它追求知识、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科技理性原本是指向自然的,但当人们控制自然取得“成功”以后,这种理性得以向社会延伸,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在思维领域表现为“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则表现为“科层体制”(bureaucracy)的形成。主体性教育思想指导下的现代教育是高度科层化的:整个教育系统、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都是等级化管理的,校长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甚至学生干部与学生之间,都是一种合法的权威等级关系。课程中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是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式,力图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学生由此获得的是一种理性化社会的理念。而且,人们无意识地混同了“经济中的人”和“教育中的人”,用市场经济规律取代教育规律,如认为教育效益就是规模效益。当学校教育完全按照理性原则组织起来以后,个人与群体之间原本交融的有机关系变得支离破碎。人际间的合作、理解、关爱和同情会日益衰微,学生的自杀率和犯罪率也越来越高。学生可能会取得很好的学业成绩,但却以牺牲健全人格的发展为代价的。
第二,主体性教育思想的还必然导致理想主义的缺失,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泛滥。这种主体思想实质上抽调了生活世界中的共同规范和普适性原则等,重视个体的意义诠释和追求,过分强调现实、具体和个人的价值,必然导致自我意识的膨胀。主体性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学生(如现今的很多美国学生)动辄就甩出自我设计、自我包装和自我奋斗的话语,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忠告,一有一些新思想、新感觉就谈自我超越。他们在自我设计的中心里进行自我欣赏。而且这类所谓“主体”的自我中心是经不起太多敲打的。在设计不成功,奋斗受挫后,又自然“跟着感觉走,管他有没有”了。要么,由于缺乏对意义的执著和追求,他们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以“他人为导向”的人格。如,只会称赞别人并以别人为楷模,对自己却永不满意;形成过度依赖以及听任权威的性格,学生的创造力、审美及敏感性日益萎缩。他们原本完整的人格结构支离,迷失在外在的观念、权威、功利、名誉和物品之中(如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为了日后的工作,他们盲目地追求分数、奖学金、证书等外在的东西),而忘记对意义的追寻。
第三,主体性教育思想(除至今仅仅停留于学理上的价值理性的主体性教育思想)遮蔽了实践中受难性等负面因素对人的影响。主体性教育思想,喻示着个体只要积极进取和乐观实现,就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以及人内在本性的圆满实现,却对实践体系中蕴涵着的令人惊异的打击、挫折、恐怖、破坏、残酷等估计不足。就连存在主义教育家波尔诺夫也直接指出:“人的生命,原则上不是在单纯的‘有机的’成长中发展,因而只能通过危机才能把握住其本人的存在。”[4]德行是在战胜挫折、面对困境和反对邪恶中发展壮大。没有对感官的痛苦和对恶行的恐惧就不会有勇气;没有快乐的刺激,就不会节制。不义在旁观者或受害者心中引起公正的观念和正义的情感,谎言和欺骗使真理和诚实有价值,残忍和恶意构成了对灵魂的温柔和高贵的陪衬。正如包尔生所说:“除去所有邪恶,你就废除了生活本身,邪恶确实是邪恶,灾祸确实也是灾祸,可他们决不是不应存在的东西。然而,它们决不是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善的缘故而存在。”[5]见忽视、无视甚至逃避一切负面因素的教育作用,实质上是天真的盲目自大、是对课程资源的狭隘理解。
第四,主体性教育思想就是精英主义的突显和民众性立场的弱化和忘却。突出个体的力量及其主动性、主体性,更多地是反映着有足够能力自主并在社会中体验更多自我尊严的那部分个体的心声与感受。教育必须适应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成功的教育必须根据不同个体的心声与感受,进行不同的教育,即因材施教。因而无视社会中那些非精英非成功人士的身心特点,无视个体差异的教育,也必将是失败的。由于精英主义的突显,主体性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民主、合作和对话的教育过程还往往流于形式,实然中民主、对话也往往成为学生一人的单独建构,教师真的成了“服务者”、可有可无的“顾问”了,同学之间的合作也变成机械的分工,所谓合作的成果也往往演变为个体成果的简单拼凑(这于现今一些学校开展的研究性学习中表现尤为明显)。更何况,如果个体均是精英,那么每个个体均不可轻视,既然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说明平等、协作的低成本高效益,那么当代个体就很有必要扬弃个人奋斗、倡导团队协作的价值观了。
第五,主体性教育思想虽强调了主体性的培养,但未必能达致它所期求的学生独立、理性、自为、自由人格的形成;在鼓励学生不断创造“为我性”客体和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不断创造与学生相对立的“非我性”世界(如学生为应试而死记硬背,劳身劳心);通过主动、自愿(而非被动、被迫、消极)的人际合作产生出来的并不一定就是参与合作的学生所向往的、对他们有积极意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主体性呼唤其实是一种廉价的片面性,远没有进入现代教育学的思维境地,即强调主客体的融合,强调对生存的关注和回归生活世界本身,从而使个体全面承担责任,进而达致真正的自由。揭开现代教育序幕的杜威就直接指出:“个人不是一组确定的态度,而是有活力的并不断变化着的行动者,一直处在生成中但永不会彻底完成。社会环境不是某种外在的静止的东西,它一直在影响着和塑造着我们,但这个本质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环境就是一个互动的产物。”[6]其实,杜威一直关注的核心便是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力图超越主客体的决然对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组或改造。《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报考的主题。它是21世纪教育所致力的目标,是继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学会生存”(主要致力于解决教育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后,教育观念、伦理观念和教育发展方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与创新,它标志着世界教育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针对社会的进步与个人全面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学会学习》建议推行一种进行以下重点转移的新的教育体系,即从促进教育的统一性转变为促进教育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从促进竞争转变到促进合作;从强调为私人利益而学习转变到为公众利益而学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