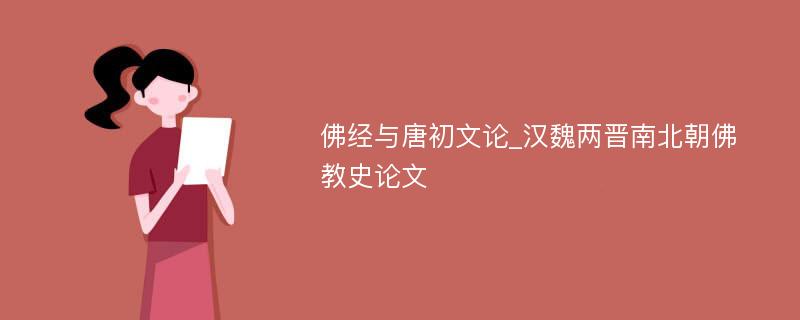
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佛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最早将佛经科判与一般文学相联系的是梁启超。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六“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中指出: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则组织的解剖的文体之出现也。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著名之诸大经论,恒经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著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例愈剖而愈精。此种著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而此为著述进化一显著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注:《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近代名著重刊”本,1988年版,第130页。)
梁氏主要举出的是儒家义疏文体与佛典疏钞之学问可能存在的关系(注:即使就这两者的关系而言,梁氏的说法也未免模糊含混。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十二“论义疏之文体”批评道:“任公先生盖见群经义疏与释典之疏均有科分,发现其有相类似之点,其意似欲从此点论儒家义疏在文体上所受浮屠影响,而辨认未明,语意含混,既未指明释氏经疏之分段落,亦未说出儒家经疏之体若何,仅由‘同时发生’一语囫囵推之,谓其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以意测之,梁先生所欲言者,殊未透彻。”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5页。),至于科判之学影响及一般文学究竟何在,则语焉未详。
本文所试图解决的是佛教和唐代文学理论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具体地说,一篇文章或一首长诗的写成,往往需要分成若干段落或层次,此在今日几乎成为文学常识。但从历史上来看,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最早出现在初唐。而这一理论之能够形成,则来自于佛经科判的启示。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注意,故撰作此文,以作嚆矢之引。
二 佛经科判略说
科判,又称科分、科文、科段、科章、科节等,指的是僧人解释经论的一种方法。据《佛光大辞典》说,就是“为方便解释经论而将内容分成数段,再以精简扼要之文字标示各部分之内容,称为科文”(注:《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年第五版影印,第3923页。)。关于佛经科判,以往的研究并不多见。最有代表性的,是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书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对于“科分”在中国的起源及特点,有简明扼要的陈述。此外,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慈怡《佛光大辞典》、中村元等《岩波佛教辞典》也专列“科文”条,并有详略不等的解释。尚永琪《六朝义疏的产生问题考略》一文亦有所讨论,更趋深化(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1-415页。)。兹结合佛教经论义疏,参酌前贤议论,对佛经科判之学略述如下:
佛经科判的基本特点是将经典一分为三,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汤用彤指出:
震旦诸师开分科门,实始于释道安,而道安则称“科分”为“起尽”。……其所分为三分。按道安注疏中有《放光般若起尽解》一卷。《法华文句》有云:“起尽者,章之始末也。”可见起尽者,即后人所谓之科段也。(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8页。)
中国的科判之学始于道安,乃古今之通说。如慧皎《高僧传》卷五“义解”《道安传》云:
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注:《大藏经》,第五十册,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馆《大藏经》委员会据日本新修《大正藏》影印本,1955-1957年版。)
所谓“为起尽之义”,即区分章段。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卷上一云:
然诸佛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分经以为三段:第一序说,第二正说,第三流通说。序说者,由序义,说经之由序也。正说者,不偏义,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义,通者不拥义,欲使法音远布无壅也。(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315页。)
天台湛然《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云:
古来讲者多无分节,至安公来,经无大小,始分三段,谓序、正、流通。(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2页。)
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上一云:
解本文者,先总判科,后随文释经。……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译《佛地论》,亲光菩萨释《佛地经》,科判彼经,以为三分。然则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435页。)
据良贲所说,印度的《佛地经论》也是以三分“科判彼经”,尽管彼此皆闭门造车,却能出门合辙,于是有“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之叹。
何以至道安时代乃有科判之说,汤用彤曾指出科判之学有一个从“佛教义学”到“经师之学”的转变,尚永琪也指出“义学的兴起”是科判之学的重要背景。然而佛教义学颇受玄学思维的影响,概言之,即“得意忘言”和“举本统末”,此皆出于王弼。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注: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609页。)王弼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时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注:《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第633页。)本着这一逻辑,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指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注:《王弼集校释》,第591页。又可参看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二章第四节第三小节“‘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149页。)其基本精神是注重大义而轻视言象。道安对此深有会心,他对于当时的佛教讲经“致使深义隐没未通”的状况颇多不满(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108页。),于是提出了改变的方式:“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注:《道行经序》,《出三藏记集》卷七,《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7页。)“率初以要其终”和“忘文以全其质”其实就是“举本统末”和“得意忘言”的另一种表述,科判之说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诠解经文而兴起的一种注释方法。从道安的实践来看,在当时也是成功的。《高僧传》这样评论他“为起尽之义”的工作效果:“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注:《大藏经》,第五十册,第352页。)道安自己说他的注经工作是为了帮助初学者了解佛教经义,其《安般注序》云:“魏初康会为之注义,义或隐而未显者,安窃不自量,敢因前人为解其卞。”(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3页。)又《了本生死经序》云:“然童蒙之伦,犹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释未训。”(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5页。)又《十二门经序》云:“敢作注于句末,虽未足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6页。)又《大十二门经序》云:“今为略注,继前人之末,非敢乱朱,冀有以悟焉。”(注:《出三藏记集》卷六,《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46页。)由此可以推知,佛经科判之学的兴起,不仅与佛教义学有关,而且也涉及到佛经义理的启蒙教育问题。运用科判的方式,可以使段落清晰,经义豁然,也更便于初学者把握。后者与文学科判说的产生具有类似之处,特于此表而出之。
科判之学初起之时,由于以“得意忘言”、“举本统末”的思想为基础,必然较为简略。汤用彤又指出:“科分经文,至刘宋而益盛。”(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99页。)从发展趋势来看,科判之学兴盛之后,实有越来越琐细的倾向,因此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天台湛然《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指出:
自梁、陈以来,解释《法华》,唯以光宅独擅其美。后诸学者,一概雷同。云师虽往,文籍仍存。吾钻仰积年,唯见文句纷繁,章段重叠。寻其文义,未详旨趣。……故碎乱分文,失经之大道。……若细分碎段,非求经旨者所宜。……昙鸾北齐人,斥云:细科经文,如烟云等为疾风所飏。飏者,风飞也。(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3页。)这里提到的“光宅”,指的是梁光宅寺法云法师,他撰有《法华经义记》八卷。据其自述,略可见其繁琐。《法华经义记》卷第一云:
今一家所习,言经无大小,例为三段。三段者,第一詺为序也;第二称为正说;第三呼曰流通。然今三重开科段。第一开作三段,自有三阶。……次第二重,又就此三段之中各开为二。……次第三重,开科段者,减一名义,通、别两序各开为五;明因辨果,二正说中各开为四;化他自行,二流通中各开为三也。(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574-575页。)
一般的科判只是将经典一分为三,法云则“三重开科段”。第一重是一分为三,第二重则三分为六,第三重则六分为二十四。将一部经典分为二十四段,详细解释,愈衍愈繁。故汤用彤指出:“至若科判,则亦时愈后者分愈密。……而佛教义学颇转而为经师之学也。”(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400页。)这当然是就六朝佛教而言。至唐人科判,则又转而化繁为简,依然以三分为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刘宋以来,科判极为流行,但这只是僧人解释经典的一种主要方法,而非唯一的方法。如天台智者大师《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一指出:
夫震旦讲说不同,或有分文,或不分文。只如《大论》,释大品不分科段,天亲《涅槃》即有分文,道安别置序、正、流通,刘虬但随文解释。此亦人情兰菊,好乐不同。意在达玄,非存涉事。(注:《大藏经》,第三十三册,第255页。)
又吉藏《法华义疏》卷一云:
问:寻天竺之与震旦,著笔之与口传,敷经讲论者不出二种:一者科章门,二者直解释。……答: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患为主,统教意以开道为宗。若因开以取悟,则圣教为之开;若由合而受道,则圣教为之合。如其两晓,并为甘露;必也双迷,俱成毒药。若然者岂可偏守一径,以应壅九逵者哉?(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452页。)
以上两段材料,大致表达了三方面的意思:其一,从解释者来说,自有其习惯或偏好使用的方法;其二,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其目的皆在于传达经中义理;其三,方法的选择,与受众的资质也有关系。有此三因,故“或有分文,或不分文”。不可固执一端,“偏守一径”。又区别章段,也只是以三分为常,并非一成不变。如吉藏《法华义疏》卷一云:
问:有人言经无大小,例开三段,序、正、流通。是事云何?答:领向圆通之论,开道息患之言,足知众途是非,宁问三段之得失耶?必苟执三章,过则多矣。(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452页。)
又隋释慧远《大般涅架经义记》卷第一之上云:
问曰:诸人多以三分科判此经,今以何故离分为五?释言:准依《胜鬘经》等,三分科文,实有道理。故彼经中十五章前,别有由序;十五章后,别立流通。此经判文,不得同彼,以第五分非流通故。又诸论者作论解经,多亦不以三分科文。(注:《大藏经》,第三十七册,第614页。)
总之,科判之学兴盛以后,解经者以区分章段为常;而区分章段又以三分为常。吉藏《法华义疏》卷一云:“推文考义,三段最长,宜须用之。”(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452页。)并且从十个方面说明三分科文的意义。应该说,这代表了佛经义疏之学的常态,尽管我们也不应忽略其变态。
三 佛经科判与儒家义疏
科判之学兴盛以后,一般佛徒在研习或解释经论时皆从事于兹。僧祐《十诵义记目录序》自谓“章条科目,窃所早习”(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94页。),即可为代表。而这种区分章段的注释方法,也就影响到儒家的经典义疏。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注:参见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载《注史斋丛稿》,第239-302页。戴君仁《经疏的衍成》,载《戴静山先生全集》(二),戴静山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1980年版,第93-117页。)。兹踵事增华,更作推衍,以略见佛经科判影响之广大深远。
六朝义疏之受佛教影响,乃一既在之事实。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指出:
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6页。)
又《礼记正义序》云:
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见于世者唯皇(侃)、熊(安)二家。熊氏违背本经,多引外义。(注:《十三经注疏》,第1222页。)
可见,在六朝儒家经典的义疏中,用佛教之说相比附,以外义解经并非罕见。只是这些内容多为孔颖达所刊落,故难以寻查。但科判的痕迹,在今日所存六朝至唐宋的儒家义疏中,却班班可考。
六朝时代的义疏之著流传至今者,惟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最为完整可信。其卷一“论语学而第一疏”下云:“《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为科段矣。”(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案:据《梁书》卷四十八《皇侃传》,此书原名《论语义》,《隋书·经籍志》作《论语义疏》,敦煌写本作《论语疏》,今通称《论语集解义疏》。据《梁书》及《南史》本传,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以儒释相比附。)又于“学而时习之”章下云:“云‘学而时习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为三段:自此至‘不亦悦乎’为第一。……又从‘有朋’至‘不亦乐乎’为第二。……又从‘人不知’讫‘不亦君子乎’为第三。”(注:《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页。)此科分章段,且一分为三。孔颖达虽然批评了六朝儒家义疏“多引外义”比附经说之弊,但他自己也同样受到佛经科判之学的影响。《周易正义》卷一自“文言曰”至“利贞”下云:
从此至“元亨利贞”,明乾之四德,为第一节;从初九日“潜龙勿用”至“动而有悔”,明六爻之义,为第二节;自“潜龙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论六爻之人事,为第三节;自“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至“乃见天则”,论六爻自然之气,为第四节;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节复说乾元之四德之义,为第五节;自“君子以成德为行”至“其唯圣人乎”,此一节更广明六爻之义,为第六节。今各依文解之。(注:《十三经注疏》,第15页。)
这很类似于良贲所说的“解本文者,先总判科,后随文释经”,仅仅是将“段”改称为“节”。又孔颖达《礼记注疏》原目“文王世子第八音义”下云:
此篇之内,凡有五节。从“文王之为世子”下,终“文王之为世子也”,为第一节。……从“凡学世子”至“周公践祚”,为第二节。……自“庶子之正于公族”至“不剪其类”,为第三节。……自“天子视学”至“典于学”,为第四节。……自“世子之记”以终篇末,为第五节。……各随文解之。(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1年版。)
又邢昺《孝经注疏》“开宗明义章第一”下云:“章者,明也,谓分析科段,使理章明。……凡有科段,皆谓之章焉。”(注:《十三经注疏》,第2545页。)分章分节,皆与佛经之分科分段一脉相承。又邢昺《尔雅注疏》卷一“释诂第一”下云:
此书之作,以释六经之言,而字别为义,无复章句。今而作疏,亦不分科段。(注:《十三经注疏》,第2568页。)
《尔雅》为字书,自然无法对之区分科段,但要特别作一说明,亦可见在唐宋以来的儒家经典注疏中,也以分科段为常态,以不分科段为变态。
汉儒的章句之学自然也要分章断句,如赵岐《孟子注》,其题辞云:“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注:《十三经注疏》,第2663页。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二引张镒云:“题辞即序也。赵注尚异,故不谓之序而谓之题辞也。”中华书局影印本,1998年版,第1176页。)所谓“章别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旨”。但这种分段极为简略,《孟子》原本七篇,于是各分上下为十四篇(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云:“赵岐字台卿,后汉人,为‘章旨’,析为十四篇。”《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639页。)。这与佛经义疏科判之繁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儒家的义疏之学,从其形成来看,显然还是与佛教有关。
不仅儒家经典注疏讲究科判,文学典籍的注释也受其影响。唐代的文学注释,最有经典性的便是以李善为代表的《文选注》。我曾就义疏之学与合本子注对唐代《文选》学的影响,探讨了唐代的文学解释受到佛教和儒家经典解释影响的问题(注:参见张伯伟《得意忘言与义疏之学——魏晋至唐代的古典解释》,载日本《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39号,白帝社2001年1月版,第65-78页。)。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科判或许也是其影响之一。据李匡乂《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载: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注:《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李善对于佛教并不陌生,《文选》中收录的作品中,如孙绰《游天台山赋》、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王巾《头陀寺碑文》、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皆与佛教有关。从李善的注释来看,他引用到的佛教经论注疏数量不少(注:参见平野显照《唐代文学と佛教の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李善の佛教”,朋友书店1978年版,第209-228页。)。钱谦益曾指出:“今注诗者动以李善为口实,善注《头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赋》,消释三幡,至今法门老宿,未窥其奥。”(注:《复吴江潘力田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1352页。)以此推论,李善熟悉佛教义疏之体,因而也熟悉科判之学,并进而受其影响,固在情理之中。佛经科判之学的影响既如此深远,于是在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强调“科别”的回响。
四 佛经科判与文学“科判”
初唐文学理论中提到的“科别”、“科分”或“科位”,实际上便同于佛经中的科判,讲的是文章段落。不同的是,经论讲疏中的“科判”是为了便于解释对佛经所作的段落分析,而文学理论中的“科别”则是为了写好文章提出的一种写作原则。
初唐文论中有关科别的材料,集中在日僧空海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一书中。《文镜秘府论》纂集了中国自南朝以后至中唐以前的文论资料,因而也保存了许多在中国已经亡佚的文献。市河宽斋《半江暇笔》云:
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式》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卮言,尽在其中。(注:转引自池田胤《日本诗话丛书》第七卷《文镜秘府论》解题,文会堂书店1921年版,第215页。案:据林衡在文政三年(1820)所写《市河子静墓碣铭》,市河宽斋著有《半江暇笔》五卷,又日本《国书总目录》及《国书人名辞典》亦载其目。但如今在日本遍觅不得,不知是否亡佚或藏在私家,待考。)
初唐文论有关科别的论述,见于《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和“定位”的前半部分,以及北卷“句端”。由于《文镜秘府论》乃采摭诸书而成,又往往略其出处,所以对其中各种文献的来源,中外学者曾做过许多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有“考文篇”和“研究篇”)。此外,如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和我的《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注:此书初名《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后经全面修订,易名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均有程度不同的考论。兹就其中“论体”、“定位”及“句端”的时代和作者略说如下:
关于“论体”和“定位”,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认为出于《文笔式》,王利器认为出于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兴膳宏认为无疑是隋至初唐间的著作,但对于“定位”一节,则认为出于《文笔式》的可能性大。我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中认为,根据现在可考的《文笔式》中的内容,出于其自创者实不多见,而大多与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和上官仪的《笔札华梁》相联贯,所以很难作十分确切的甄别。但三家所说宗旨一贯,后出者便不妨既引述袭用,又有所增补附益,这也是古书中的一条通例(注: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卷四“辨附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虽然将“论体”和“定位”归于《文笔式》,但对于其中的理论,应该看作是与刘善经、上官仪一脉相承。关于《文笔式》的产生年代,罗根泽《文笔式甄微》认为出于隋(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1935年1月版。),王利器也认为“此书盖出隋人之手也”(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小西甚一则认为作者当与上官仪同时或稍后(注:《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日本讲谈社1951年版,第42页。)。我确定此书年代在稍后于《笔札华梁》的武后时期(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68-69页。)。
关于“句端”,由于在日本藏有平安朝写本《文笔要决》,作者为初唐人杜正伦,两相对照,即可知“句端”乃出于《文笔要决》。
无论是《文笔式》还是《文笔要决》,在中国皆早已亡佚。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这两种书都有著录。又借《文镜秘府论》的引用,《文笔式》就和其它几种唐人诗格一样,遂得以保存至今。
初唐文学理论中的科判说,其提出实与佛教有关,兹略作申说如下:
首先,从表达的术语来看,“科别”、“科分”、“科位”等名称皆来自于佛教经疏。《文笔式》“论体”云:“必使一篇之内,文义得成;(谓篇从始至末,使有文义,可得连接而成也。)一章之间,事理可结。(章者,若文章皆有科别,叙义可得连接而成事,以为一章,使有事理,可结成义。)”(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80页。)又“定位”云:“故自于首句,迄于终篇,科位虽分,文体终合。”(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82页。)又《文笔要决》云:“属事比辞,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势义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41页。)《文笔式》所谓“章者,若文章皆有科别”,“科别”即分章段,一如《法华义疏》所云“敷经讲论者”的“科章门”之法。佛教经论科判多作三分,故又称“科分”(汤用彤即用“科分”指称)。至于“科位’,也是从佛经科判说中转换而来。《出三藏记集》卷八载释道朗《大涅槃经序》云:“余以庸浅,豫遭斯运,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试标位,叙其宗格,岂谓必然窥其宏要者哉?”(注:《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59页。)又卷十一载释僧肇《百论序》云:“(鸠摩罗什)常味咏斯论,以为心要先虽亲译,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寻者踌躇于谬文,标位者乖迕于归致。”(注:《大藏经》,第五十五册,第77页。)这里所用到的“标位”一词,即标明位置、划分章科之意,而“科位”与“标位”也是名异义同,“科位虽分”就是“章段虽然有所划分”的意思。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概念和术语,有自身直承者,有横向移植者。就后者而言,有的来自于儒家、道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性著作,有的来自于人物品评,也有的来自于音乐、绘画、书法批评等,这是唐以前文论概念横向移植的主要来源。但就唐宋以下的概念移植而言,佛教与禅宗典籍成为文论术语的重要来源,初唐文论中的“科判”说亦为明显一例。
其次,佛经科判虽然以解释经文为主,但具体到如何科判某一经典,则还需要兼顾到经文本身的文势与义脉。吉藏《法华义疏》卷一在回答何以要科分三段解经时,从十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便是“一者圣人说法必有诠序”(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453页。)。因此,科判经文就要注意到其本身固有的“诠序”。如天台湛然《维摩经略疏》卷第一云:“今寻经意趣,傍经开科,而非固执。”(注:《大藏经》,第三十八册,第563页。)又其《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云:
但文势起尽,用与不同。如释通序,则句句须四,通贯正宗及流通故;若释正宗,则本迹各三,义通四种;若释流通,还须具四,通收正宗。……又序中约教,须观文势。……若解斯文,则一部经心如观指掌。(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6页。)
“起尽”本来就是指“科判”,道安所使用的就是这一名词,故其书名《放光般若起尽解》。《法华文句记》卷第一上亦云:“言‘起尽’者,章之始末也。若分节已大小,各有总别起尽。”(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2页。)但如何科判,还是要以“文势起尽”为依据。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读者或听众对经中所蕴含的圣人的用心,即所谓“经心”(或称“圣心”),就能“如观指掌”。反之,若固执一端之偏见,则“纵不全违圣心,终是人之情见”(注:《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154页。),横生系累,毕竟是不可取的。
佛经科判与文论中的“科别”、“科分”,虽然前者是就解释经文而言,后者是就文学写作而言,但在区分章段之际,必须考虑到文势和义脉,则是两者的共同点。这也是佛经科判能够影响文学理论的基础。《文笔要决》指出:“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势义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41页。)恰当地安排文章的“科分”,是为了达到“势义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的目的。这里的“势义”,指的也就是文势与义脉。《文笔式》“定位”在讲到确定科位的四种技巧和避忌时,就有两点与势义相关:
三者义须相接。(谓科别相连,其上科末义,必须与下科首义相接也。)四者势义相依。(谓上科末与下科末,句字多少及声势高下,读之使快,即是相依也。)……义不相接,则文体中绝。(两科际会,义不相接,故寻之若文体中断绝也。)势不相依,则讽读为阻。(两科声势,自相乖舛,故读之以致阻难也。)(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81-82页。)
由阅读文本时的科判需要重视“势义”,到写作文章时的科判需要重视“势义”,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转换。而在文章科判之外、之前同时兼顾文本“势义”的,惟有在佛经科判之中。因此,文章科判说之提出,由佛教的启示和影响所致,应该是可以断言的。
第三,初唐文论中提出“科别”、“科分”或“科位”的诸书作者,就可考者而言,与佛教似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文笔要决》的作者杜正伦,《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云:“正伦善属文,深明释典。”(注:《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41页。)据《历代法宝记》载,四祖信禅师寂灭后,“中书令杜正伦撰碑文”(注:《大藏经》,第五十一册,第182页。)。又《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记显庆元年(656)高宗敕书,“玄奘新翻经论,文义须精”,乃命杜正伦等人“时为看阅,或不稳处,随事润色”(注:《大藏经》,第四十九册,第577页。)。可见,他对佛教的浸润非同一般。《文笔式》作者已不可考,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这部书的内容与刘善经《四声指归》、上官仪《笔札华梁》相联贯,三者不易作十分确切的厘清。而上官仪与佛教也是因缘颇深的。《旧唐书》卷八十《上官仪传》载:
私度为沙门,游情释典,尤精《三论》(案: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兼涉猎经史,善属文。(注:《旧唐书》,第2743页。)
又《文笔式》一书也颇受释家重视,空海大师既录之于《文镜秘府论》,镰仓时代释了尊复征引于《悉昙轮略图钞》。初唐文论作者精通释典,那么,受其影响,援佛经科判之说以论文,亦为顺理成章之事。
唐代诗学的核心是诗格,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之后又由诗扩展到其它文类,而有“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其性质是一致的。唐人诗格的撰写动机有二:一是以便应举,二是以训初学。实际上,就指导应举者写作而言,其接受对象也多是初学者。如杜正伦《文笔要决》云:“新进之徒,或有未悟,聊复商略,以类别之云尔。”(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41页。)上官仪《笔札华梁》云:“故援笔措词,必先知对,比物各从其类,拟人必于其伦。此之不明,未可以论文矣。”(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67页。)王昌龄《诗格》云:“但比来潘郎,纵解文章,复不闲清浊;纵解清浊,又不解文章。若解此法,即是文章之士。为若不用此法,声名难得。”(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72页。)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云:“金针列为门类,示之后来,庶览之者犹指南车,而坦然知方矣。”(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51页。)徐夤《雅道机要》云:“以上略叙梗概,要学诗之人,善巧通变,兹为作者矣。”(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48页。)王梦简《诗格要律》云:“夫初学诗者,先须澄心端思,然后遍览物情。”(注:《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74页。)可见,从初唐到晚唐五代,指导初学习作,是诗格类著作不变的功能。前文讲到,佛经科判说的提出,与佛教经义的启蒙有关。而文学科判说的提出,也与文学创作的启蒙有关。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似性,或许也并不是偶然的吧。
初唐文论中的“科判”说,与唐代诗格中的许多论述一样,性质上属于“规范诗学”的范畴,其本身所包蕴的理论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对“科判”说的理论内涵作进一步阐说,并从“历史诗学”的角度予以定位,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已经轶出本题的范围,我将另有专文再作探讨。
标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 文学论文; 唐僧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十三经注疏论文; 佛经论文; 出三藏记集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佛光大辞典论文; 大藏经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