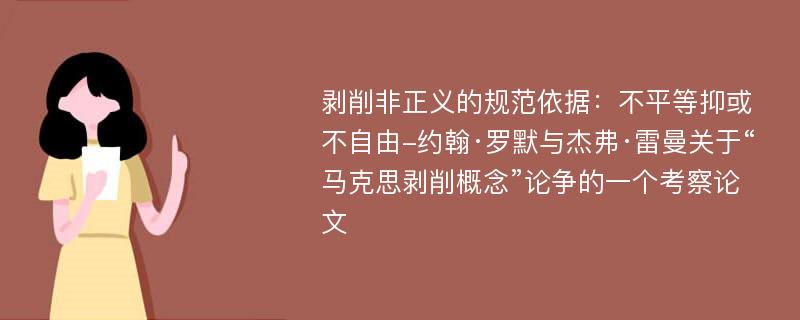
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不平等抑或不自由
——约翰·罗默与杰弗·雷曼关于“马克思剥削概念”论争的一个考察
徐如刚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是约翰·罗默与杰弗·雷曼关于“马克思剥削概念”论争的核心议题。罗默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包括“不平等交换”和“财产关系”两个定义,二者分别阐明了在消费品交换中形成的不平等占有和由生产资料决定的不平等占有。因而,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是不平等。雷曼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应当是“包含强迫”定义,包括“未付酬劳动”与“结构性强迫”两个方面,因而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是不自由,罗默误解了马克思所说的剥削。罗默回应了雷曼的批判,但其观点不能容纳雷曼的批判,同时雷曼也存在理论困境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二者的论争虽与自由主义话语存在“亲缘”关系,但蕴含着马克思正义理论可能的规范进路,而这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剥削;财产关系;不平等交换 ;强迫
从当前学界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研究来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看待其建构性。学界对此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马克思批判脱离物质条件的抽象思辨,所以批判、拒斥正义,其设想的正义图景是超越正义,因而正义不具有建构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通过“盗窃”“抢劫”等用语给予道德谴责,隐含着其应当持有的正义观念,因而马克思必然介入正义的论说。以上两种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路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特质,但存在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在前者,基于历史的视角却否认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维度,背离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在后者,基于抽象的道德层面确证了马克思正义的可建构性,脱离了应有的社会经济基础,陷入了马克思所反对的正义空想。回顾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研究历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英美学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罗默(John E·Roemer)(以下简称罗默)与杰弗·雷曼(Jeffrey Reiman)(以下简称雷曼)关于“马克思剥削概念”的论争(1) 约翰·罗默(1945-),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 《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1988)、《分配正义论》(1998)等,因重建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被广泛关注。杰弗·雷曼(1942-),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美利坚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正义和现代道德哲学》(1990)、《道德自由主义批判:理论与实践》(1996)、《尽可能的自由和公正: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理论》(2012),因批判罗默和G.A.柯亨(G.A.Cohen)对马克思剥削概念的重建而受到关注。关于马克思剥削规范性内涵认识上的差异,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存在于约翰 E·罗默、G.A.柯亨与南希·霍姆斯特姆(Nancy Holmstrom)、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理查德 J·阿内森(Richard J.Arneson)等人之间,但均未就剥削为什么是非正义的予以详细论述,也未在理论界公开争论。从约翰·罗默与杰弗·雷曼的争论开始,两种观点才真正交锋,并将马克思何以批判剥削是非正义的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掀起了第二波争论浪潮。 ,将当时学界聚焦的问题从“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引向剥削与自由、平等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关系中探讨了剥削何以是非正义的,进而阐明了马克思正义的可能规范进路。重新审视二者的论争,或许对于破解当前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中的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何以关涉正义
“剥削”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并未在其著作中予以明确定义。为了替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辩护,罗默与雷曼尝试从规范层面建构剥削,进而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剥削何以关涉正义的问题。
罗默认为,马克思通过剥削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平等,因而剥削关涉正义。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含有技术性和规范性双重内涵。就技术性内涵来说,剥削解释了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就规范性内涵来说,资本主义的剥削包含不平等性。因而剥削既包含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又包含对其非正义性的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之所以是非正义的,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消费品交换中存在不平等关系。罗默认为,不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劳动交换与否,资本主义交换中必然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即包含在消费品中的劳动(通常仅指工资收入)少于工人提供的劳动。”(2) John E·Roemer,“Should Marxists be Interested in Exploitatio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14,No.1,1985,pp.30-65. 在这种交换中,因对消费品投入劳动时间的差异而产生剥削,交换中的不平等决定了剥削的非正义性。其次,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是不平等的。“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通过类似劫掠、奴役以及盗窃这样的进程确立不平等的资本所有权的起点。”(3) 约翰·E·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段忠桥,刘磊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页。 这种形式的初始分配,形成了生产资料占有的非正义,因而被“继承”的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性就成为剥削的本质特征,所以资本主义剥削是非正义的。柯亨这样响应罗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实质上是一个关于分配的问题,其非正义性在于分配的不平等。”(4) G.A.Cohen,“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8,No.4,1979,pp.338-360.
雷曼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中包含着不自由,因而关涉正义。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社会结构中,一个阶级的劳动被另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未付报酬且结构性地强迫榨取,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剥削的。”(5) Jeffrey Reiman,“Exploitation,Force, and the Moral Assessment of Capitalism: Thoughts on Roemer and Cohe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6,No.1,1987,pp.3-41. 因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包含两个方面,“未付酬劳动”(unpaid labor)和“结构性强迫”(structural force)(6) 结构性强制是雷曼理论的核心概念,在2012年的著作《尽可能的自由和公正: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理论》中,用structural coercion来表示,与文中的structural force 意思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区分。 。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另一方面这种占有是强迫性的,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自由的。因而,资本主义剥削是非正义的。雷曼进一步认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中隐含着对工人提供无酬劳动的强迫性,而这必然体现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7) Jeffrey Reiman,“Justice and Modern Moral Philosophy”,State of Connecticut—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48. 劳动力的交换看似在自由中进行,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隐含的强迫性,现实中工人的劳动及剩余价值的占有均是强迫性的。尽管强迫的形式与前资本主义时期有所不同,“且有时差异性足以模糊了潜在的相似性。”(8) Jeffrey Reiman,“Exploitation,Force, and the Moral Assessment of Capitalism: Thoughts on Roemer and Cohe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6,No.1,1987,pp.3-41.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的,就暗示有道德谴责的意思。”(9) Jeffrey Reiman,“Moral philosophy: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ideology”,edited by Terrell Carver,“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43. 如果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仅具有技术性内涵而不包含道德评价,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通过批判剥削非正义在道德上谴责了资本主义。
罗默与雷曼从经济关系的科学分析与价值评价相结合的两个维度重建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突破了以往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对立范式。在对剥削何以是非正义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也阐明了经济关系中的平等与自由何以成为规范正义的可能进路。但就这种进路应当是自由还是平等存在分歧,而这体现在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是不自由还是不平等的论争中。
首先,“不平等交换”定义可否排除强迫而判定剥削是非正义的。如前文所说,罗默认为的“不平等交换”定义大意为,不论存在劳动交换与否,“从整体上来看,剥削都会存在于已生产产品的交换中。”(10) John E·Roemer,“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9. 即是说,在消费品交换中,当一个人应当耗费在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多于自己通过交换所得的消费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他就是被剥削者,反之则是剥削者。因而,剥削的非正义性在于交换中的不平等。雷曼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剥削的功能是解释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换言之,即是解释价值的扩张。然而,价值扩张的前提中只有包括自由与否的道德判断,才能产生剥削正义与否的判断。因而,只有依据表征经济关系中不自由的“强迫”才能判定剥削是否正义。“在不涉及交换是否被强迫的前提下,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定义为‘不平等交换’是不恰当的。”(11) Jeffrey Reiman,“Exploitation,Force, and the Moral Assessment of Capitalism: Thoughts on Roemer and Cohe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6,No.1,1987,pp.3-41. 基于不平等而判定剥削非正义也是不正确的。
二、罗默与雷曼关于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之争
稀土矿非法开采、乱采滥挖现象,不仅严重扰乱了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还由于开采技术含量低、工艺落后、采富弃贫,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污染、河道淤塞、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1-3]。因此,加强稀土矿监管、保护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其次,“财产关系”定义可否忽略“强迫”判定剥削是非正义的。罗默这样描述“财产关系”定义,假设将社会中的一个群体看成S,剩余群体看成S’,若是“对社会生产资料再次分配,如果S将会受益,而S’则会遭受损失,那么S就被S’剥削。”(13)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0-97. 具体说来,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社会中出现一个群体受益增加而另一个群体受益减少,那么原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在这个定义中,蕴含一个检验剥削存在与否的“撤回原则”,即通过对现有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以检验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而判定剥削的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平等。可以看出,“剥削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表现,剥削的消除只能通过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才能实现。”(14) Joh Elster,“Roemer versus Roemer: A Comment on‘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Politics & Society,Vol.11,No.1,1982,pp.363-373. 所以,剥削产生于生产资料的分配中,分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剥削的非正义性。唯有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说明马克思批判剥削非正义时暗含的前提。雷曼认为,罗默的“财产关系”定义弱化了马克思批判的“锋利性”。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的奴隶主与奴隶、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奴役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异,“证明后者(无产阶级)就是现实中的奴隶。”(15) Jeffrey Reiman,“Exploitation,Force, and the Moral Assessment of Capitalism: Thoughts on Roemer and Cohe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6,No.1,1987,pp.3-41. 罗默仅仅将社会代理人分为“穷人”与“富人”,忽略了阶级之间的“强迫”关系,其所说的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具有抽象性,因而“财产关系”定义偏离了马克思剥削概念的“轴心”即阶级理论。由此做出剥削非正义的判断难以证明是马克思意义上的。
大极虎的目光落在站在萧飞羽身后的只手拿云身上冷冷地道:“我就奇怪晌午怎会有人持黑旗令传喻本镇居民。”只手拿云错愕,因为他知道此事,但与黑旗会所属同赴安和庄还没时间弄明白这事原由,不过他也很快恍然大悟全镇居民关门闭户是源于安和庄。他道:“我与传喻之事无关,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位是三少,也是安和庄的主人。”看到只手拿云脸上的歉意,太极虎脸色骤沉。“你该是与安和庄暗通款曲坑了去安和庄的本坛所属。”
罗默通过批判“包含强迫”定义,阐明了雷曼批判的不合理性。罗默设想了例子1,假设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拥有一些生产资料,使用相同的技术且需要相同的消费品,市场上允许生产资料和所有消费品的交换,每个人依据生产资料总量的平均份额,工作六小时即可满足生存需要。在消费品交换结束以后,每个人获得了他需要的生活资料。那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获得同样的消费品时,占有生产资料多于平均份额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可以少于六小时,而少于平均份额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则需多于六小时。“尽管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劳动交换,但在已生产的消费品的交换中存在剥削。”(12)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0-97. 罗默认为,这个例子证明了,即便是没有劳动交换也可能产生剥削关系,而雷曼的定义并不能确定这种状况是否存在剥削。由于不存在劳动交换,就不存在“未付酬劳动”,也谈不上资本家对工人的“强迫”。因此,“不平等交换”定义可排除“强迫”而判定剥削是否正义。
罗默回应了雷曼的批判,认为基于其定义中的“强迫”做出剥削非正义的判断是非马克思的。罗默设想了例子3(16) 罗默为驳斥雷曼而设计了四个例子,由于例子2主要论述强迫对生产的积极意义,例子4主要为了说明“财产关系”定义与“不平等交换”定义的区别(详见罗默文章“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与雷曼争论的核心问题关系不够密切,所以文中只涉及了反映二者分歧的例子1和例子3。 ,“亚当在生产资料初始分配中获得一个大机器,而鲍勃获得一个小机器,这种分配是不平等的。鲍勃能够通过小机器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但是亚当愿意雇佣鲍勃,由此,鲍勃取得生活资料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使用自己机器所需要的,且劳动所得的工资能够保障较好的生活水平。”(17)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0-97. 可见,鲍勃并未被强迫为亚当劳动,但亚当却依赖于鲍勃的劳动生存。罗默认为,在这种情况中,尽管不存在强迫,但由于初始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公,致使鲍勃被亚当剥削。相反,若是亚当和鲍勃分别拥有每个机器的一半,在不考虑他们的休闲和消费偏好的前提下,就不会存在剥削。这个由“财产关系”定义得出的结论,却不能从“包含强迫”定义中得出。在这种条件下,若雷曼基于其定义做出剥削非正义的判断则是非马克思的。此外,对于雷曼批判罗默背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罗默认为,“我是依据他们的初始天赋和偏好来定义代理人的,而且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是理性且受限制的经济行为的结果。一个代理人的阶级地位可能决定他的社会行为,也包括他的孩子的喜好,但是基于前在的原因推断阶级地位要比将其看作界定代理人的特征要真实得多。”(18)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0-97. 即是说,代理人的划分要依据“初始天赋”“偏好”等个人因素,只有将个人因素作为原因,而非仅仅将其作为特征,才能真正揭示代理人所处阶级地位的形成过程,而这首先需要将社会代理人划分为“富人”与“穷人”。由此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内涵。显然,雷曼忽略了这一点,做出的批判也是没有道理的。
随后,为了解决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全党再次掀起调查研究的高潮,征求群众意见,最终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这一规定载入了1962年9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从而为调查研究成果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保证。
在罗默看来,传统的剥削定义即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剥削的实质,应当用“不平等交换”(un-equal exchange)、“财产关系”(property relations)定义来代替。而剥削的非正义性在于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雷曼批判了罗默的定义,认为马克思的剥削应当是一个“包含强迫”(force-inclusive)的概念,具有“未付酬劳动”和“结构性强迫”双重内涵。因而,判定剥削非正义的依据在于概念中包含的“强迫”。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钻孔灌注桩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发展迅猛,在成本效益意识日益增强,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半湿孔作业法将凭借快速、节约、稳定及环保等优点给工程建设质量提供了更多保障。本文是基于郑州西部地层特性桩基半湿孔成孔的可行性讨论,对本区域桩工建设及其他地区类似地层提供参考。
再次,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剥削非正义的同质性依据是不平等还是不自由。罗默认为,“财产关系”定义阐明了马克思剥削概念暗含的意思,即在封建主义条件下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差异性(19) 参见John E·Roemer,“Property Relations vs. Surplus Value in Marxian Exploitatio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1,No.4,1982,pp.281-313. 。在封建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可被当作剥削的重要依据,占有生产资料即可对劳动者实行剥削。而这种建立于生产资料占有基础上的强迫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证明了,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因而,“财产关系”定义不但能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的不同,而且确证了剥削在两种条件下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唯有基于不平等才能从整体上判定剥削是否正义。雷曼认为,尽管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中的“强迫”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者可以公然地通过暴力夺取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通过“经济关系中缓和的强迫”来剥夺。“这种强迫不是传统的奴隶和封建主义的直接奴役,而是因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不占有所导致的间接强迫关系。”(20) Jeffrey Reiman,“Justice and Modern Moral Philosophy”,State of Connecticut—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48. 所以,“封建主义剥削转向资本主义剥削”只不过是转变了“强迫”的形式。雷曼依据《哲学的贫困》以及《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来说明这种转变,马克思将“对无产阶级的奴役”比作“间接奴隶制”,将“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作为“直接奴隶制”(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说明他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同样的“强迫”。因此,不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都是非正义的。但在罗默看来,雷曼通过将奴隶制或封建制中的剥削理解为“强迫性的未付酬劳动”,进而“将资本主义的剥削看成奴役关系是错误的。”(22)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6-97.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奴隶制、封建制形式的“强迫”,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因而,依据“强迫”断定剥削是非正义的,实质上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
其二,罗默的思想实验过于理想化和片面化。罗默主要通过如前文所提到的例子1和例子3表达了与雷曼观点的不同。在这两个思想实验中,首先,罗默将人设定为只关注初始生产资料分配的人,过于抽象地定义了现实意义上的人。事实上,“较之于社会生产结果分配的平等,初始生产资料分配的平等并不是人们最关注的。”(23) Jeffrey Reiman,“Why Worry about How Exploitation Is Defined?: Reply to John Roemer”,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Vol.16,No.1,1990,pp.103-113. 由于生产结果直接关系到生活资料的分配,较之于初始生产资料分配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更关注的是社会生产结果的分配,在忽视这一点的前提下追求正义的分配,可能产生新的非正义。即便如罗默所说,每个人应当分得生产资料的平均份额,那么随着人口的变化,人口增加较快的家庭自然就会分得越多,且任何人均可通过多生孩子减少其他人的合法份额,也就使原有的分配方式失去了现实意义。其次,罗默例子中的人不反对分配中的不平等。在罗默的例子中,不论是初始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还是消费品交换中的不平等,均应当被罗默认为的“穷人”反对,或者说通过斗争改变现有分配方式,以实现平等的分配,但罗默并未对此展开说明。可见,罗默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例子中的人过于抽象化了。再次,罗默的例子中不包括“强迫”的一面。雷曼根据罗默的例子3,设计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罗默的不足。与亚当和鲍勃一样,艾莉森和比尔分别拥有大机器和小机器,艾莉森以一定量工资雇佣比尔为两人生产生活资料。然而,比尔可以一边在艾莉森的机器上工作,一边在自己的机器上工作。对于比尔来说,较之以前他可能没有任何损失也没有更多收获,只要他不以不平等的所有权反对艾莉森,且愿意为她工作,也就说明二者之间不会存在非正义关系(24) 参见 Jeffrey Reiman,“Why Worry about How Exploitation Is Defined?: Reply to John Roemer”,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Vol.16,No.1,1990,pp.103-113. 。在罗默的例子中,亚当之所以能够剥削鲍勃,可能是因为他拥有控制鲍勃的手段或权力,如鲍勃想要使得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降低到六小时以下,就只能接受亚当的剥削,这事实上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强迫关系。可见,在罗默的观点中,非正义的存在与强迫的不存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其举出的例子也就具有片面性。一个人被强迫得越少,表现出的自愿性越多,且只有能够放弃一些权利才能真正说明强迫的不存在。然而,罗默的例子中并未真正体现鲍勃被雇佣的自愿性,也就不能排除“强迫”。罗默的例子未能解释为什么剥削不应包含“强迫”以及“强迫”何以不能作为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
三、罗默的观点不能容纳雷曼的批判
综观罗默与雷曼的论争,笔者认为罗默的观点并不能容纳雷曼的批判,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罗默误解了雷曼所说的“强迫”。雷曼所认为的“强迫”是“结构性强迫”,其判断剥削非正义的根据在于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中的“强迫”或不自由。罗默所认为的是现实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强迫”,这种“强迫”因资本主义社会契约关系中的“承认”而不存在。这说明,罗默实质上回避了雷曼的批判。罗默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质上赋予占有者强制剥夺的手段。尽管劳动力以及其它商品交换均是以“自由”为前提,但罗默未排除生产资料占有者“不劳而获”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剥削包含“强迫”的可能性。
几年来,农业生产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创造了一定基础,但农产品有效供给无法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升级,造成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上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明显不合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达极限而绿色生产极度缺乏,农民增收传统动力减弱而新动力跟不上等问题依旧突出;解决好增产与提质关系、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问题、库存高企而销售不畅的挑战、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矛盾依旧紧迫。
其三,罗默的定义存在内在矛盾。首先,“不平等交换”实质是关于劳动的交换。罗默通过区分劳动交换和消费品交换,认为在资本主义交换中,不论劳动交换是否存在,消费品交换却一直存在。所以,只有从消费品交换中才能从整体上判定剥削关系。罗默通过例子1证明了,“马克思的剥削是一个整体性现象,即便是不存在劳动市场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25) John E·Roemer,“What is Exploitation? Reply to Jeffrey Reiman”,Politics & Public Affairs,Vol.18,No.1,1989,pp.90-97. 。但是,在罗默所说的消费品交换中,由于已生产的商品本身代表一定劳动价值量,交换的不平等性实质上体现为双方提供的劳动价值量的差异,这说明商品交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交换,并非其所说的不存在劳动交换。不难看出,罗默在“不平等交换”的定义中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雷曼所批判的,罗默在例子1中事实上证明了劳动的不等价交换中不包含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其次,“财产关系”与“不平等交换”定义并不能作为剥削概念的两个定义。罗默认为,“财产关系”定义优先于“不平等交换”定义,更加接近马克思剥削概念的本意。“不平等交换”定义的剥削必须是以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这说明罗默的两个定义并不是独立的。沃尔夫(Jonathan Wolff)在批判罗默的剥削定义时指出,“定义就是要给出绝对可靠的方法以挑选出哪些对象是或哪些对象不是其所指。”(26) Jonathan Wolff,“Marx and Exploitation”,The Journal of Ethics,Vol.3,No.2,1999,pp.105-120. 显然,罗默关于剥削的定义与“定义”本身的内涵是矛盾的。罗默所重建的两个定义或许只能作为剥削概念的两个部分,且不能确保概念的周延性。由此认为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在于不平等是不充分的。
四、雷曼的理论困境及其对马克思的背离
虽然罗默的观点难以容纳雷曼的批判,但并不意味着雷曼是免于批判的。其一,雷曼的思想实验中将人设定为合作关系,违背了其认可的阶级理论。根据前文可知,雷曼认为剥削关系应当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且雷曼也以此批判了罗默。然而,在其通过艾莉森和比尔的例子来驳斥罗默时,却未能有效证明自己定义中的“强迫”。艾莉森与比尔不能代表两个阶级,即便是可以假设为两个阶级,也不应是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阶级与占有较少的阶级,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不占有阶级。雷曼虽指出了罗默的理论缺陷,却难以说明艾莉森和比尔之间的强迫关系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强迫。雷曼还认为,只要比尔不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非正义性反对艾莉森,就不形成剥削关系。事实上,雷曼定义中的“结构性强迫”说明,只要这种蕴含“强迫”的社会制度或生产关系存在,就会存在非正义的剥削,而不是以阶级之间是否“反对”来判定。可见,雷曼在处理剥削的重建与阶级理论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其二,雷曼在对剥削概念的重建中,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雷曼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剥削非正义的目的在于,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强迫”,进而消除剥削。然而,雷曼所说的剥削的消灭,可在生产发展中实现,也可在生产倒退中实现。只关注“强迫”的消除,而不关注社会生产的发展,实质上与马克思认可资本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相反,陷入消灭“剥削”却可能带来生产倒退的境地。纳维森(Jan Narveson)批判雷曼所说的“强迫”忽略了生产效率提升为人类带来的“自由”,暗含着对历史倒退主义的认可。“自然的法则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搬到撒旦的磨坊对人类来说具有进步意义,若如雷曼所说,马克思应当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27) Jan Narveson,“Reiman on Labor, Value, and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The Journal of Ethics,Vol.18,No.1,2014,pp.47-74. 显然,纳维森指出了雷曼的根本缺陷。雷曼忽略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辩证视角,片面且抽象地理解了剥削中的“强迫”。“马克思是通过在历史视域中描述剥削,进而对价值理论等相关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的。”(28) Gilbert L. Skillman,“Value Theory vs.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x’s Account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Science & Society,Vol.71,No.2,2007,pp.203-226. 可见,雷曼将不自由作为剥削非正义的规范依据,同罗默的观点一样具有片面性。
其三,雷曼剥削概念中的“强迫”并未脱离自由主义话语。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均体现于自由主义话语中。马克思认为剥削非正义的“自由”依据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29) 王峰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第3页。 即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二重性。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另一方面是指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这说明,马克思认为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自由的。但同时劳动条件被资本家占有的事实决定了,工人必须依附于资本家,将劳动能力用于交换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而劳动力交换则“使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能力的支配权,说明工人要服从资本家设定的生产目的以及资本家对劳动的监督”(32) 张峰,徐如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非正义的前提批判》,《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63页。 ,工人阶级又是不自由的。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自由理念产生基础的揭示,还原了自由主义自由的悖论性,并在超越这种自由的基础上,批判了剥削的非正义性。由此,马克思认为,“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和混乱。”(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而雷曼则在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中探讨了剥削何以非正义,脱离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综上,雷曼和罗默围绕“剥削何以是非正义的”展开了“马克思剥削概念”的论争,也指出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可能规范进路。二者的理论努力意在对抗马克思正义理论解读中的自由主义话语,但由于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严格区分,反而陷入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致使其所重建的马克思剥削概念与自由主义存在“亲缘”关系。当前,由政治哲学复兴导致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自由主义正义的批判已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热点。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实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建构,不但是对抗自由主义话语的需要,也是指导过渡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罗默与雷曼论争中体现的规范诉求启示我们,马克思正义理论在当代具有建构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蕴含在经济关系中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之中。即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分配中的同等所有权,消除自由主义自由与平等及其自反性存在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分配中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由此,为每个人参与社会再生产奠定基础,进而实现社会成员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诸环节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统一。这说明,只有在生产资料正义分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正义,即在二者的统一中才能从整体上实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事实上,也只有这种途径的建构才可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也才可能真正超越自由主义正义,有效指导过渡阶段社会的发展。
Inequality or Illiberality as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the Injustice of Exploit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bate of “Marx ’s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between John Roemer and Jeffrey Reiman
XU Ru-gang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the injustice of exploitation is the core issue in the debate of “Marx’s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between John Roemer and Jeffrey Reiman. According to Roemer, Marx’s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includes the definitions of “unequal exchange” and “property relation”, which respectively clarify the unequal possession formed in the exchange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at determined by means of production. Thus,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the injustice of exploitation is inequality. In contrast, while holding that Marx’s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should be a “force-based” conception, involving “unpaid labor” and “structural force”, Reiman stated that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exploiting injustice was illiberality and Roemer misunderstood Marx’s exploitation. Although Roemer responded to Reiman’s criticism, his positions were not compatible with Reiman’s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Reiman also faced a theoretical dilemma and partly deviated from Marx. Despite their argument’s kinship connection with liberal discourse, it contains the possibly normative approach to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which is of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Key words : exploitation; property relation; unequal exchange; force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9)06-0086-07
[收稿日期] 2019-06-2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5AA020)
[作者简介] 徐如刚(1983-),男,河南项城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张文光]
标签:剥削论文; 财产关系论文; 不平等交换论文; 强迫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