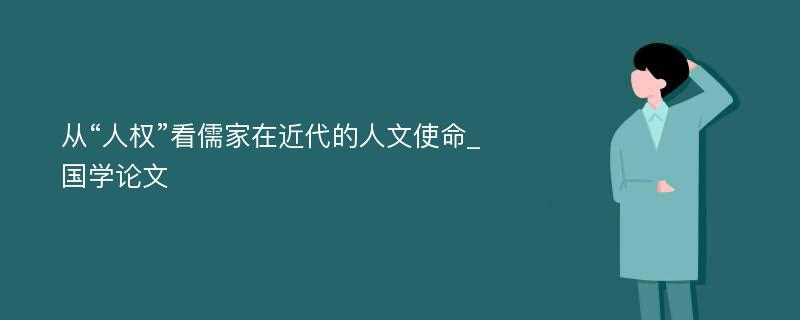
在“境界”与“权利”的错落处——从“人权”问题看儒学在现代的人文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人权论文,使命论文,人文论文,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作为“成德之教”(一种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为己之学”(一种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其经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分际的孜孜探求。“人权”观念诚然有着终极意趣上的人性背景,但总的说来,它属于“权利”范畴,而不属于“境界”意识。“权利”是有所依待的,“境界”是无所依待的。从这一层理致上看去,“人权”问题虽不能说与儒学无缘,却也毕竟只可勉称之为拓展中的儒学的一块可能的“飞地”。
“人权”意识在中国的自觉,受启于近代西方。但最早萌生“人权”意识的一代中国先知,却是在儒学的熏炙下获得其人文教养的。从“人权”在这一代人那里遭逢到的亲切和难堪,或正可以看出“儒学”在接受一个新的时代时所必由的曲折蹊径。
一
严格地说,“人权”观念的初萌,并不早于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尽管这个从格劳秀斯开始而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那里臻于完成的学派,其学缘可上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哲学。按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照“理性”而生活,按照“自然”而生活亦即是按照“德性”而生活,斯多葛派所认可的“自然”、“理性”、“德性”的三而一、一而三的理路对此后“自然法”的“自然”内涵的贞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伊壁鸠鲁由原子的“偏斜”所引出的原子间的“冲撞”,则第一次为所谓“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哲学依据。黑格尔曾恰当地把它们称作“自我意识哲学”——其所祈向的主要在于境界意味上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人的个我权利的证可与分辨。
当古罗马的法学家以后期斯多葛派和西塞罗为中介把斯多葛派的“自然”范畴作为某种终极设准引入法学领域时,含着明确的权利指谓的“自然法”观念产生了,这同罗马法学家把斯多葛派的希腊文著作译为拉丁文时生造了“自然法”(iusnaturale )这个词的事实是可以相互说明的。在查士丁尼时代,御纂的《法学总论》认可了这样的提法:“根据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页。)。 人的“自由”权利被认为是自然所赋予而出于“自然理性”,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已可说是开了近代“人权”意识之先河。但当时这一观点毕竟还在所谓君权神圣信念的笼罩下,且它也并未妨碍它的宣示者对奴隶制的必要性的认可。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个体本位原则及其所必致的“社会契约论”,显然还在罗马法学家的视野之外,但它毕竟曾唤起过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灵感。这位古代的思想启蒙者对原子“偏斜”所蕴涵的个体自由原则是别具慧识的,他甚至触到了与原子因“冲撞”而结合之意味相贯的所谓社会起源于契约的假说。
中世纪是经典的基督教信仰时代。罗马法典所透露的“权利”意识这时被淹没在对“上帝之城”的深情向往中,“法”和“政治”在中世纪的神学家那里更多地被处理为带着神圣背景的伦理学的一个支脉。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把人的心灵引向一种“境界”,但在这“境界”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是他律而不是自律。自然法学说在这里延续着,但“自然”的自己是自己的未可致诘的原因的意识没有了,它必得从“上帝对创造物的合理领导”这一“永恒法”那里获得凭借。“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7页。)。 当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界说“自然法”时,“自然法”的着眼点已不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国家的尊严。与此相应的是,“自然法”的神学阐释者虽然也认为“克服暴政弊害的办法应以公众的意见为准”(注:同上书,第59页。),但对“公众的意见”的看重却并不要引出作为“人权”的某种对象性表达的所谓人民主权,而是在于证说“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
所谓近代自然法理论,属于见解远非一致的一批思想家;它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贯穿在其中的某种前后相承的旨趣须得在一种动态流变中去悉心把握。如果就近代自然法学说对“人权”观念的酝酿与提撕看,几位著名的以自然法为逻辑公设或法律拟制的思想家,对这一学说的主要贡献或可作如是评断:格劳秀斯的奠基性工作在于为自然法作某种脱开神祗的独立宣告;对法的理念的认可使这位宗教信念极强的思想家有理由指出,即使上帝被认为不存在或不过问世俗的人事,自然法的效准依然存在。自然法的自律、自性的品格使“法”获得了神或世俗权力不可浸涉的地位,公正或正义因此得以超越经验的存在而被永恒地确认。霍布斯的最有价值的话题则在于原子式的“个人”;这个把思维归结为一种“加”或“减”的“计算”的英国人,以分析(“减”)的方法在经验的国家和社会中找到最后的不可再剖分的因素“个人”后,又以个人的重新组合(“加”)推演出了在他看来真正合理的社会和国家。在他那里,个体意志以契约方式的联合最终取消了个体意志,但正像从格劳秀斯之后以人性为依据的“永恒的正义”的信念成为此后自然法学者的共同信念一样,从霍布斯之后,每个有意志的个人被——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认为是社会或国家的权力之源。洛克从“自然状态”的悬设中推出了人的个体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的“人权”价值,这使他成为近代自然法学说的经典的阐释者,并且,正是从“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出发,他得出国家主权在于人民的结论。孟德斯鸠沿着洛克开出的方向系统地阐说了“法的精神”,并补正和完成了在洛克那里已初见格局的以权力制衡为归着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承认“洛克是以完全一样的原则处理了和我一样的题材”(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山中书简》第6 书,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译注。),但无论如何, 在洛克更多地突出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意味后,卢梭已开始注意到“权利”意识的孤峭化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后果。因此,他一反启蒙思潮的乐观信念,把至可珍贵的“权利”意识重新关联于以“良知”(“天良”)为主题词的人的道德境界。而这一点,甚至决定性地影响了此后康德哲学的大致走向。
二
中国儒家立教,其命意尽收于一种自律的“境界”。它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这“外王”的道理只是属于“境界”范畴的“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径直推出。“内圣”的涵养为“外王”的从事者提供一种当有一资格,却并不为“外王”作某种必要的“权利”意识的分辨。而且,一般说来,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致多是克就“治人者”的状况提出的,它对于被认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于人者”少了一份“权利”认可上的切近感。
“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注:《孟子·滕文公下》。),诚然不必理解为孔子对“君人者”的仰赖,但入“仕”的急切毕竟表现了儒门创教者在君主治制下的被动,——他必得经由“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当道”这一“正君”的途径,才可能求达他意想中的“国家”以至“天下平”(注:《孟子·告子下》、《孟子·离娄上》。)。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孔、孟、荀诸大儒作如此表述的初衷而言,确然包含了对“君”、“父”们的相应境界或相应德性的期待和要求,不过,它最终是一种被视为纲常的“礼”,而“礼”者,则如荀子所言“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者也”(注:《荀子·礼论》。)。儒者即“仁”而言“人”或即“人”而言“仁”,有“仁者,人也”(注:《中庸》、《孟子·尽心下》。)之说。就“仁”是人所以为人的依凭而言,这界说对于君臣父子一类隶属性关系确有超越的一面,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这超越是道德“境界”上的超越,它并不引发“权利”对列意义上的那种竟或潜在于人心的“人权”意识。
单从“境界”上说,儒家“圣王”——唯有“圣”者才有资格作“王”者,或“王”者必至成为“圣”者才是真正的“王”者——的理想,其本身亦可视为对“君”者、“王”者的鞭策,然而这鞭策落到现实处,也仍不过是一种道德提撕,并不能构成对“君”或“王”的可能行为的赋有“权利”效准的规范或限制。倘分解地说“圣王”,“圣”是一种道德人格,“王”是一种“权利”人格。从道德人格向度上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是说得通的,因为尧舜所启示的“圣”的“境界”是“人皆可以”趋赴的;但从“权利”人格上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说不通的,因为尧舜是“王”者,他的“王”的“权利”并不是“人皆可以”致取的。因此,由“圣王”推出的“内圣外王”的儒者的承诺,在其整全意味上便只可能是“圣”而“王”者(如尧舜等)或“王”而“圣”(“王”者通过修为成为“圣”)者的承诺。它无法普遍化是因为它终于不得不倚重于既在其位的“君”、“王”。荀子谓“君者,民之原也”(注:《荀子·君道》。),“君者,国之隆也”(注:《荀子·致士》。),似是对孔孟意致的歧出,但其未始不可溯寻到“内圣外王”的本然理境。孟子是紧紧扣住“内圣”论说“发政施仁”的道理的,但他也只能由“推恩”而说到“惟仁者宜在高位”(注:《孟子·离娄上》。),至于对有志于“修其身而天下平”的非在位的“君子”,他便只好诫勉以“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注:《孟子·尽心上》。)了。
道德“境界”更多地通着人生所趣之“高尚”,“权利”却更多地关联着人所当求的“幸福”。“境界”同“权利”的分辨,或正在于“德性”与“幸福”这两种不同向度上的人生价值的底蕴的相去。“德”、“福”配称一致固然意味着人生价值实现上的某种理念式的圆满,但不同时代运会下或不同民族境遇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总会在二者间畸轻畸重。孟子有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这段话是儒家对其赖以立教的“义利之辨”的经典意向的宣吐;“生”与“义”的兼“欲”是“利”与“义”或“福”与“德”的并举,在“不可得兼”的两难抉择中“舍生而取义”,则是“成德之教”在价值取向上的最高断制。这一断制出自生命的德慧,它表述了中国古代儒者乐天而又忧世的沉重的悲剧感。不过,所谓“生”与“义”或“福”与“德”“二者不可得兼”,只是在境遇到了非抉择不可的那一度才可以如此去说的,分际把握上的任何差迟,都可能招致有背于这一断制的初衷的后果。孟子是在一个病态的时遇背景下立论的,因此,即使他这样的大儒、亚圣,有时也不免因着对与“生”相联属的“欲”的负面效应估想过重而在理致上有所偏至。宋明儒所谓“革尽人数,复尽天理”(朱晦庵),“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的不无立“义”衷曲却终致寡于“生”理的说法,或正可溯源到孟子,孟子确曾这样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心)不存焉者,寡矣。”(注:《孟子·尽心下》。)毋庸赘释,“义”或“德”属于心灵境界,对“福”或“利”的追求则关联着个我权利的认可。从逻辑上说,“德性”(“义”)并不排斥“幸福”(“生”),“境界”也不必与“权利”相抵牾。但同一逻辑也表明,“幸福”并不能由“德性”推衍而出,而“权利”也并不派生于“境界”。在中国古代儒者那里,“境界”上的“德”、“义”价值的孤峭化和“福”、“利”价值相当程度地被轻觑,一个留给历史的后果是“境界”向往对个我“权利”意识的内在羁勒。
清末民初以来,一些对儒学经典持反省乃至批判眼光的人们,多以为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注:《论语·颜渊》。)的说法有着太多的宿命意味,其实那看似无可奈何的言说中却正涵泳了一层只是圣哲、大儒才可能有的生命潇洒。“死生”、“富贵”是对际遇有所依待的,也并不就是人生最内在的价值;唯道德、人格不假外求,只须在心性修养上下工夫便可葆之不失。既然这样,人便尽可以顺天由命,不以夭寿、爵禄为念,一意于使人成其为人的“仁”心的修持。孟子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注:《孟子·尽心上》。)所谓“求在外者”,即“死生”、“富贵”,其“得之有命”,徒“求”是“无益于得”的;所谓“求在我者”,即德性、人格,唯“求”才可以“得之”,倘“舍”便会“失”去,所以是“求有益于得”。“求在我者”当求而不舍,“求在外者”既然“得之在命”,便不能不俟“命”待“天”了。以孟子的“求在外者”得之有命理解孔子,可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正解,由“境界”而不是“权利”的入路才可能触到孔子的心灵。对孔孟的说法仍是可以批评的,但这须是在另一种审视向度上。以淡泊“死生”、“富贵”的境界律己,必致律己者无心于个我“权利”的求取;以同样的境界诲人,则必致对受诲者的个我“权利”观念的消解。至于对“治于人者”的“民”,孔孟确乎并未与“君子”一例相绳,但“德化”信念在儒者那里是根深蒂固的,这足以使有智慧对包括“民”在内的每个有生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作出贞定的圣贤们,不再把眼光投向对于他们来说卑而不高的“权利”。他们也许并非不屑以贞定每个有生的个人的权利为己任,只是高卓的德性境界充斥了他们的整个人生视野。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注:《孟子·尽心下》。)这是儒家成德之教启示给世人的人生境界。“善”、“信”、“美”、“大”、“圣”(“神”)构成这递升的境界的不同层次,而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注:《孟子·尽心上》。),则是趣于这境界的亲切而必由之蹊径。可以说,从先秦到宋明,儒者在心灵境界的拓辟方面是自成一家教路的,但根于人性而系于每个个我的人的“权利”意识,却始终未能在儒学中达于自觉。“权利”的贞定须得见之于“法”,儒家也谈“法守”,但儒家对其有所轻正像法家对其有所重一样,“法”在中国古代尚主要落在起督责、惩罚作用的刑法上。孔子是不赞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但这只是从他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论语·为政》。)的赞赏那里才可得到中肯的理解。对“法”偏于“刑”的不以为然,并不是要对法作一种向着“权利”规范方面的扭转,而是要由此导人于帅“德化”于其中的“礼”治。孟子引《尚书·泰誓》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乃至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注:《孟子·公孙丑上》。),看似对“民”的某种“权利”的申论,然而究其根蒂,这些极富“民本”——“民为邦本”而非“主权在民”——思想的话,乃是从“治人者”的一种必要或可期的“境界”上说起的,其意谓同近代以来渐自西方的“人权”观念终究还隔着一层尚待穿透的逻辑上和意致上的膜。
三
“人权”是每个个人的未可让渡的权利,对它的肯认意味着这样一种人文意识的确立,即作为“实体”的每个个体优先于必至诉诸“关系”的社会或政治团体。先前,人们总是立于社会、国家或者君主(“朕即国家”)的位置判说个人的存在价值,从“人权”学说脱颖于近代“自然法”之后,人们变换了一种视向,开始由每个个体的权益攸关处审看社会组织、国家形式和以“朕即国家”自许的君主,这是价值主体的重新认可,也是人生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中土儒者立教,应当说是从个体生命存在的亲切处入手的,所谓“仁义礼知,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注:《孟子·告子上》。)之“我”,乃是指称每一个个我。但这“我”是从一种反观自照的境界上说起的,正由于这一点,“我”在际遇中的“权利”非但不能因此而确定,反倒可能因此而消解,因为从“境界”上看,个我对“权利”的要求本身便不足称道。儒家教化从无对待的自“尽”其“心”、自“尽”其“性”的根本处成全人,却又在有对待的既得的社会治制下不免于委屈人,这是一种富有悲剧感的扞格,这扞格到了西风东渐的近代,尤其因着它的典型发露而引人瞩目。
康有为堪称第一个试图以儒学方式汲取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人,他的措思重心在“政”、“教”间的移易曾清晰不过地透露出儒学与“人权”间的亲比与抵触。当康有为说“人人皆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注: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时,他显然认可了近代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但没有疑问的是,这被引来作政治变革的观念在他那里是衍自被重新诠释过的孔门之学的。在“戊戌”前后的他看来,“不忍人之心,仁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注:同上。)这“仁”既是万物之本,并因此而使万物相通,显发于人,则“仁为‘相人偶’之义,故贵于能群”(注:康有为:《长兴学记》。)。同是以“能群”推及社会治制,荀子崇礼,把“能群”归结于“能分”,因而更多地肯认“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注:《荀子·礼论》。)的等级秩序,康有为却以“仁”释“通”,以“通”释“群”,强调人的“能群”的博爱本质和人在“群”中应有的“独立平等”的地位。所以他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注:康有为:《中庸注》。)“立教”与“立治”的相贯,把儒家道德“境界”上的“推己及人”同近代“权利”意味上的“自由平等”关联了起来,这是托始“孔子改制”而重新解释过的儒学对“人权”观念的吸纳。然而,“人权”的“权利”向度从自律的道德境界中直接推出终是粗率了些,这使得康有为在“辛亥”前后不再能守住其理致的初衷。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托始“孔子改制”,从儒学中推衍出“人权”观念,原只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梁启超)罢了,对“经术”本身的反省乃至损益或可说是机智的,却远不是深刻的。“人权”多系于人对“幸福”价值的追求,所以“戊戌”前后他解释孔教说:“孔子以人情为道”,“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圣人因人情所不能免,……其术不过为人免其苦而已。”(注:康有为:《大同书》,《日本书目志》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然而儒学为“成德之教”,其主要价值取向在于德性的高尚,因此当康有为在“辛亥”时期更大程度地认同传统儒学的本真时,他又说:“今举国滔滔,皆争权利之夫,以此而能为国也,未之闻也。《孟子》开宗,《大学》末章,皆以利为大戒,使孔子、孟子而愚人也则已,使孔子、孟子而稍有知也,则是岂可不深长思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5—906页。)对康有为在“戊戌”、“辛亥”间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当然可以作政治的或社会的乃至人事际遇方面的分析,但至少,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的未必通透——对儒学与“人权”、“境界”与“权利”的扞格不曾自觉省察,也当被了解为这位不同凡响的人物的理趣未能一以贯之的缘由之一。
同康有为差不多同时代的严复,在“儒学”与“人权”问题的措置上是另一种情形。他在“戊戌”、“辛亥”(以至“五四”)间,从断言“今日之政, 非西洋莫与师”(注:《严复集》第1 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到称叹“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注:《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的转变,以典型的方式把儒学与“人权”相扞格的一面对象化了。可以说,严复在“戊戌”时代是相当彻底的“西化”论者,但这“西化”的涵谓又毋宁说只是今人所说的近代化或现代化。他把近代西方人所以能够做到“去伪存真”、“去私为公”归结于人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并由此为中国“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设想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 册,第23页。)的文化方案。在严复那里,从“自由”到“民主”的理路的推绎是这样的:“言自由者,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注:《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此所谓“自主之权”即是“人权”,它是人的“自由”价值在“权利”向度上的认可。“戊戌”时期的严复,对人的自主之权的看重同他对“富”、“强”——以救治中国之贫、弱——所必要的“力”的求取是一致的。“富”“强”价值一元论使他的“天演”、“进化”理论别具一种刺激民族奋发的魅力,却也使他对人生的德性乃至审美价值有所轻忽,以致一向被尊崇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也被他贬称为“宗法社会之圣人”。“辛亥”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从对功利价值的“富强”的追求,转向对系于德性价值的“人心”的关切。这时,德性价值一元论又使他尽弃对“富强”之“力”的向往,返回被视为民族“一线命根”的孔孟之道。“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注:《严复集》第3 册,第661页。)严复的这一充满悲情的自白是真诚的,却也是惶惑的。他曾以“富强”为鹄的鼓吹“人权”而放逐了儒学的成德之教,他又以“先王教化之泽”为归依由冷落“富强”而冷落了“人权”。严复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称引“自由”并以此论中西文化的,遗憾的是,“自由”的内(德性之自律)外(权利之自主)向度,在他那里终于未能以贯而不隔的慧识予以整全地开决。
孙中山是康有为之后又一个在“儒学”与西方近代“人权”意识间寻找契合点的人物,他的所谓“独见而创获者”在于其“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民权”是相对于“君权”的,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代西方一个演自“人权”学说的命题——“主权在民”。事实上,孙中山确曾如是界说“民权”:“夫民权者,谓政治上之权力完全在民。”(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但西方近代“人权”学说所认可的究极的价值主体在于每个对于他人、社会、国家有着契约承诺的个人,孙中山的“政治上之权力完全在民”的论断后面被确定的价值主体却更大程度地是所谓“国家”。“民权主义”的创设者一再提起西方政治家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因而分外看重“人民”,然而“人民”的抽象化使“个人”在“国家”那里不再有“自由”可言。孙中山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在近代西方“人权”学说那里,“国家”的价值要从它对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保障作用上去认取的,而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这里,“个人”的价值则要视其对“国家”的“强盛”所做的贡献乃至牺牲而定。这诚然是儒学“境界”背景下谋图民族富强的先觉者对近代西方“自由”概念的随机运用,却也标示了“民权主义”之“民权”对近代“人权”学说的悄然乖离。
在孙中山看来,孔孟告诫治人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表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只不过“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罢了(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页;第7卷,第60页。)。其实, 称引孔孟以诠释“民权”,正是民权主义学说的底蕴的自我托出。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不必领会为对“君权”的倚重,但其伦理要求所必致的“境界”上的修养,所成全的多在于为君、为臣、为父、为子的个人的人格守持与自尊,却并不能在“权利”向度上为不同职分的个人的自由、平等作出贞定。孟子曾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子·梁惠王下》。)诚然是立于“仁”而由“教”议“政”,但对“诛一夫纣”所作的“未闻弑君”的决绝评断,反倒在“教”的高度上肯定了“君”位(而不拘于某一君主)的神圣。孙中山是否弃“君”位的,他称引孔孟并非简单地重复孔孟,但“民权”之不同于“人权”,却正如“民本”还不就是“民权”。对德性修养和民族本位的倚重,使他理所当然地引述孔孟,而这也恰恰使他的“民权”未能相契于“人权”。
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这被推崇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原是政教一体、德法不二的,但看似“教”对“政”的“境界”笼罩的格局却往往落于“政”的既有“权利”规范对修德之“教”的制约或匡限。孟子曾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孟子·离娄上》。)这显然是“外王”出于“内圣”的又一种说法。不过,推天下之本于个人的“内圣”境界,所彰明的价值仍只在修德的向度,它并不在“权利”的意味上为了揭示属于“人权”范畴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儒学的“外王”是从“内圣”推出来的,但“内圣”的修身功夫只给予既得的“外王”架构以内在生机,从而把这一架构内的“外王”事业尽可能推向极致,却并不更主动地为“外王”架构本身的改变(以求一种更好的架构)提供足够的动力。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说:“以往二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但是,“在以前可以说是如此,在现在则是不够。修身齐家在这个时代,不能直接推出治国平天下;不能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这就显出现代化的意义”(注: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356、357页。)。这是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之规的不无深度的反省,也正可看作是对孙中山引儒学以立“民权”的“民权主义”学说的一种回应和检讨。
四
对个人“权利”观念的启迪,也许只是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那里才以典型的方式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变革。与这一启蒙思潮相伴的,是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代“摩罗”式人物对儒学的苛刻而至于偏至的批判。“人权”在被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引荐给中国人时,它也被明确地宣布为源自近现代西方。
胡适在1919年11月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对“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总括性评估是深中肯綮的,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注:《胡适文存》第1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728页。)“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即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五四”主流知识分子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价值程准则在于以“个人之人格”、“个人之权”等为内涵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以“自由”为价值中枢,并因此确认“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的当年(1915年)就曾指出:“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也;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也;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66页。)可以说, 陈独秀的这一“个人主义”祈向是“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通祈向,而它也正是近现代西方“人权”观念的中心命意所在。
“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利己主义并不相干,在其究竟处,它意味着对利己利他概念的超越。这种“个人主义”是重人格的,但它主要是从人的“独立自主”的格位上——而不是从道德的格位上——贞认人格的。因此,就人生意义的追求而言,它主要地不是像传统儒学那样定向于人的德性的高尚,而是归落于人的身心幸福。胡适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人生的究元意义上提出这样一个为“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大体认同的命题:“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幸福”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命的润泽,也意味着心灵在不役于他物的境况下才可能有的那种自尊、愉悦和宁静;高尚则意味着人秉持德性孜孜以求良知的自觉或心灵境界的提升,它为人指示一个“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生命向度。传统儒学未必排斥幸福,但“幸福”不被作为刻意求取的目标却有可能因着凸显德性而使儒学趣于道德价值一元论。道德价值一元论在其末流那里,必致以幸福为价值指向的事功的被轻贱,也必致道德在寡头化、训诫化(他律化)后有悖于儒者初衷而流于缘饰和虚伪。“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尤其是胡适)批判儒学,相当大程度上是对着教条化、他律化因而桎梏人的幸福欲求的礼教的,他们更多地从人生意义的幸福取向上逼近人性或人道之全。他们的“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的信念同他们对“人权”的张扬,对“科学”、“民主”的鼓吹是协调一致的。但人生趣于“高尚”的独立意义未被自觉提到应有高度,却可能由人生“幸福”取向的偏执带来人生神圣感的失落。因此,正像有必要对批判儒教的“五四”主流知识分子作一种同情的理解一样,这里也愿对批判“五四”的当代新儒家学者们作一种同情的理解。
所谓当代新儒学,是指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20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其主旨或可一言以蔽之谓“返本开新”。“返本”,即是返回孔孟“成德之教”的本根;“开新”,则在于从儒学的本始生命处开出科学和民主等时代的新机相。在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等看来,“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这里所谓使每个“自我”在政治上“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的问题,属于“人权”问题;而以“心性之学”为出发点“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则表明了问题的提出者以“儒学”的名义对“人权”问题的解决所作的承诺。当代新儒家学者是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对儒学与“人权”以泾渭相判后重新把二者关联在一起的,这再次的关联本身蕴含着深刻而动人的文化悲情。
新儒家学者是这样设想每个“自我”作为“道德的主体”与其作为“认识的主体”的关系的:“此道德的主体之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为一认识的主体时,此道德主体须暂忘其为道德的主体。即此道德之主体,须暂退归于此认识之主体之后,成为认识主体的支持者。直俟此认识的主体完成其认识之任务后,然后再施其价值判断,从事道德之实践,并引发其实用之活动。此时人之道德的主体,乃升进为能主宰其自身之进退,并主宰认识的主体自身之进退,因而更能完成其为自作主宰之道德的主体者。”(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其实, 这也正是他们对“自我”作为“道德的主体”与“自我”作为“政治的主体”的关系的设想,全部问题只在于所谓道德主体的“暂忘其为道德的主体”,或所谓“暂退归于此认识之主体(及政治之主体)之后”。倘作一种分疏,“暂忘”、“暂退”的意蕴则略可归结为两层:一是“道德主体”为究极主体,“认识主体”、“政治主体”终究不过是道德主体的转出,因而道德价值是归极性价值,认知价值或由政治之理念所体现的公正或正义价值最后仍涵摄于道德价值;二是“认识主体”、“政治主体”或认知价值、公正价值未尝不可以相对独立地确立,但人的认识主体、政治主体地位的贞定或认知价值、公正价值的认可虽不必由道德主体或道德价值直接推出,却仍须从道德价值处曲折地开决。在这相贯的两层意蕴上,新儒家学者有其“返本开新”的共识,但就义理的表达而言,对第一层意蕴说得透彻而直白的莫过于唐君毅,对第二层意蕴说得清晰而尽致的莫过于牟宗三。第一层意蕴重在“返本”,因而最能展示“儒学”的风致;第二层意蕴重在由“本”而“开新”,因而只是从这里才显现出新一代“儒学”的所以“新”来。
“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的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注: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6页。 )当唐君毅这样表述道德价值与包含公正价值在内的其他文化价值的关系时,我们或者有理由称他为道德价值一元论者。如何由这一元的道德价值开出诸如求“真”、求“美”、求“公正”等文化价值显然是一道难题。为破解这道难题,牟宗三提出了“曲转”、“曲通”、“自我坎陷”等概念。他说:“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在此一转中,观解理性之自性是与道德不相干的,它的架构表现以及其成果(即知识)亦是与道德不相干的。”(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台湾学生书局增订新版, 第58页。)这里所说的“与道德不相干”,不过是“暂时与道德分开”,既然“观解理性”是由道德理性“自我坎陷”而来,它便终究为道德理性所涵摄。从尚未自我坎陷的道德理性到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再到自我坎陷的扬弃,这是道德理性从开到合而自我丰富、扩充的过程。新儒学以近乎黑格尔的“正、反、合”的逻辑掩住了它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悲剧性,然而,正是在这里,道德理性的泛化也清楚不过地露出了新儒家逻辑上的薄弱环节。
在牟宗三看来,“创造之所以为创造的实义要从道德上见”,“道德性的‘创造性自己’人格化就是上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由于上帝意欲这个世界;为什么意欲?因为爱这个世界;为什么爱而意欲?因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如此说来创造性的原理还是GOOD,这是道德的。”(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17页。)这可谓是新儒学的泛道德理性论的点睛之笔。GOOD 固然是“道德”的,但GOOD并不尽于道德,它也涵盖着“真”、“美”、“幸福”等并不能为“道德”尽摄的价值。况且“创造”还须有相当的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或对象化的创造。牟宗三有鉴于康德,在“德”(道德)“福”(幸福)配称一致的意义上探求“圆善”(至善、圆满的善),但他不仅对“幸福”并不能从“道德”中开出——哪怕是曲折地开出——这一分疏有所忽略,而且他也忽略了“圆善”的真正可能诚然在于价值(GOOD)肯认的真切,也还在于为价值(GOOD)所导引却并不就是价值决断本身的“力量”的足够。
五
当代新儒学对道德理性的过重依托是儒学在可能的限度内的一种挣扎,这挣扎或可给予人们以这样的启示:既然“成德之教”或道德之学(亦即道德之“觉”)如康德所说,“并不是教人怎样求谋幸福的学说,乃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那末, 我们便不必把对包括“幸福”价值在内的圆满的善的追求,悉托于所谓道德理性。儒学或儒教在中国“依理性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一己之生命”(牟宗三语)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当代新儒家一再向世人提撕这一点不仅在学术上功不可没,更是对文化的民族格局“生命化”的重要贡献。但儒学毕竟是需要作时代反省的,而且这反省并不能由新的圆通的诠释所替代,经由批判的反省而有所演革的“教”(教化),作为一种通着人生意义的终极关切的价值系统,把人生趣于高尚的道德价值贞定在“制约者”的地位依然是必要的,但这除开道德德目的重新厘定(例如“忠”,过去是用来维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的,现在则正可以用于人与人的对列关系——人的相互忠诚),还需要把德性不能覆盖的其他价值(诸如美、真、幸福等)把握在涵养人性之全的恰当分际上。中国学人仍可以儒学为背景,——因为道德价值虽不必对真、美、幸福等价值作寡头的独断的领属,却仍可以在引导或相对制约的意义上被赋予“制约”其他价值的地位,——因此使自己作为一个儒者而立于世界人文学术之林,但却不必执著于标称自己的学说为新儒学或更新的儒学,一如康德、黑格尔在基督教背景下创学立论而自成一家之言却不必相许以新的或更新的基督教学说一样。儒学或儒教从此当作为一种虚灵不滞的教养涵淹于东方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而不再被执定为一个边缘清晰、同其他若干学派相轩轾的学派。这是“教”对“学”的松开,一如近代西方基督教对诸多哲学、人文学说的松开一样。其实“教”对“学”的独立性的成全,或正是“教”在空灵的超越意义上的自我成全。
倘如此,对“儒学”与“人权”关系的研讨,便可能转换为带着儒者教养的学人对“人权”问题自身逻辑的研讨。就是说,“儒学”与“人权”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在这里被扬弃了,它被扬弃在有着儒者教养的学人对“人权”问题开放得多的探索中。可以预期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人文自信的近代西方学人所提出并解决的“人权”问题,在把儒学或儒教作为必不可少的人文教养的东方学人那里必会获得相应的解决。这解决是受启于西方的先行者的,但它是在由儒学或儒教为东方学人提供的教养背景下才可能达致的。就东方学人对“人权”问题的解决毕竟脱不开儒教对解决者心灵的熏炙而言,这可能的解决当然可以说是“儒学”式的解决。不过就“人权”终究是一种对待性的“权利”,而儒学也终究是重心落在德性境界处的一种教化而言,亦可以说这解决是非“儒学”式的解决。总之,儒学是一种“教”,一种不无宗教意味的教化,“人权”则是每个个人的非可让渡的最后“权利”,儒学不可能否弃作为每个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权”,但“儒学”也终于只为有着“人权”的个人以不同于其他“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方式提示一种人生境界。它不必在万象森然的人文世界中事必躬亲,而只须让由它陶冶出的仁心内在而不耻于学的儒者去不懈努力。这正像基督教不必去过问高等数学而只让它的信徒牛顿、莱布尼茨去过问,不必去过问“人权”而只让它的信徒格劳秀斯、洛克等去过问一样。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自然法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康有为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