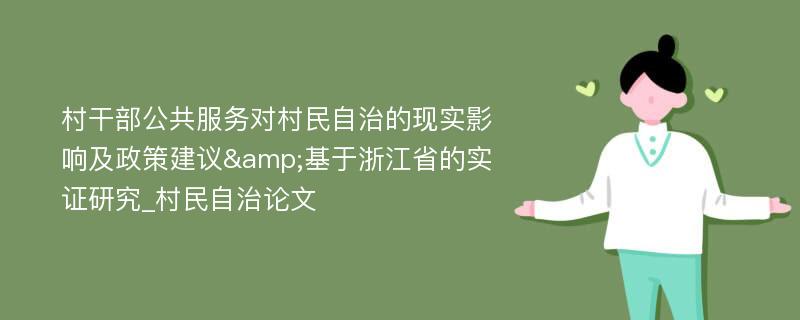
村干部“公职化”对村民自治的实际影响及其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职论文,浙江论文,村干部论文,村民自治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5-0067-06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方法
村干部“公职化”不是指把村干部变为公务员,而是对国家把公务员管理的某些做法变通移植到村干部管理上的一种通俗性概括。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村干部“公职化”举措日益彰显,突出表现在:中央明确提出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建立村干部报酬和养老保险资金保障机制(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十七届四中全会,2009),即坊间俗称的“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和养老保险”,从而把原来的地方性做法上升为国家行为。
村干部“公职化”引发了争议。学界总体上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损害并扭曲了村民自治制度。因为其一,村委会是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治组织负责人的报酬就理应由自治组织自身来解决,这是“村民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村干部工资“由上级发放”的做法损害了本来就很不稳固的基层民主,如果村干部端起了政府的“饭碗”,村干部就变成了“政府雇员”,那么政府“指挥”、“领导”村干部,不是就“名正言顺”而且轻而易举了吗?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因此,村干部工资政府发放,不符合村民自治的真义,必须坚决反对[1]。政界实务界对此则持肯定态度。他们基于的是村庄治理的实际状况和需要——中国绝大多数行政村已沦为“空壳村”,自治组织难以支付村干部报酬。无钱何以治理?无报酬谁来治理?由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瘫痪村”。因此,村干部报酬由国家财政支付,既能吸引更多更好的各类人才来担当村干部,又能减轻村级集体的负担,从而能实施有效的村庄治理。至于理论(能否自洽)问题,他们就没考虑得那么多了。
那么,村干部“公职化”的实际效应如何?特别是它有否造成学界所普遍担心的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的侵害?如有,则又在哪些方面构成了实质上的损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课题组一行2010年暑期深入乡村实地进行了调研①。
选择何样的观察视点来测度村干部“公职化”政策的实际效应才具科学性?仝志辉、贺雪峰运用“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框架对四种理想类型的村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2]。金太军则把以乡政组织为载体的“乡政”权力引入村庄治理结构,建构了“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从而将村庄权力的“外部研究”与村庄权力的“内部研究”勾连了起来[3]。我们认为村干部“公职化”直接点击的是国家(直接表现为乡镇或街道)与村级自治组织负责人之间这个活穴,但却是牵动上下的中枢之穴,“因为在村庄权力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中,村庄精英属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构成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3]。因此,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上来考察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际影响:其一是在村干部们与乡镇(街道)的关系的层面上,看其对乡镇(街道)是否增强了依附性。其二是在对村级事务的治理的层面上,观察村干部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行为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其三是在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的层面上,看其有何种方向的流变趋向。这三个层面在实践中,往往是相互交叉的。三层交集中的一个关键观察点是:当上级意图与村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村干部的利益代表性或利益代表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或偏差,或者说,村干部们的“角色”代理是否发生了转换或偏差。这个问题乃至本课题的实质,是国家与自治域或曰基层自治组织间的关系,简称“国家-村庄”关系。观察在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即村干部“公职化”政策下,“国家-村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发生了何种趋向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没有对作为中国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内在价值设计或内在制度特性造成损害特别是实质性的损害。据此,我们的访谈和问卷围绕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来设计并展开。
为了便于对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公职化”模式下的乡村、同一“公职化”模式下的不同类型的乡村进行比较,我们的调研集中在浙江省L市展开。L市处于浙江省的中上发展水平,该市从2008年正式开始施行村干部的“公职化”政策,至今已两年有半。其“公职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Ⅰ乡镇模式,即村主要干部(村主任、书记)“工资”和养老保险“政府全额支付”模式。每人每年近4万元全部由政府给予,且明文规定不允许再到村里拿酬金。Ⅰ乡镇属比较富裕的乡镇。一种是其余乡镇模式,即“1+1”模式,或曰“政府部分支付”模式。村主任、村书记“工资”和养老保险=政府给予部分+村里给予部分,其中政府支付部分L市统一为1125元/月,全年1.35万元/人,再加上养老保险每人1000元/年。我们首先选取了Ⅰ乡镇,作为第一种模式的代表,在第二种模式中我们选取了经济水平相对较好的Ⅱ乡镇和地处偏僻山区相对欠发达的Ⅲ乡镇。考虑到同一乡镇内,各村也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是否“老板”等因素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可能对村干部“公职化”效应发生影响,因而,我们在Ⅰ、Ⅱ、Ⅲ三个乡镇各选择了3个行政村作为调研点,力求综合体现上述各方面的差异因素。这样我们一共调查了L市3个乡镇(Ⅰ、Ⅱ、Ⅲ)和9个行政村(Ⅰ、Ⅱ、Ⅲ各3个行政村)。
我们的调研以三个层面、两种方式进行。我们先在乡镇层面与乡镇书记或主管副书记和有关乡镇干部进行结构式访谈;然后下到村级层面与村书记、村主任和其他村干部进行结构式访谈;最后,深入农户,进行了访谈式问卷调查,形成有效样本数184个,其中Ⅰ乡镇60个,Ⅱ乡镇64个,Ⅲ乡镇60个。问卷共14个问题,围绕三个方面,其中,“公职化”对村干部角色行为的影响,设4个问题,“公职化”对村-乡关系的影响,设3个问题,“公职化”对村干部-村民关系的影响,设3个问题。加上对村干部“公职化”总体认知,设2个问题,对村干部竞争与改善,设2个问题。
二、问卷统计与综合分析
(一)问卷统计
1.“公职化”对村干部的角色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村干部的利益代表性更加政府化。对村民样本的统计显示,与“公职化”前相比,当上级政府与村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村干部站在村民一边由46%下降到32%,站在政府一边由42%上升到48%。特别是当政府不正当地强力侵害村民利益时,只有27%认为村干部“帮村民”,挺身维护村民利益,近三成是“帮政府”(28%),占多数的是“双方都不得罪(40%),置身风浪之外做骑墙派,关键时节角色行为失范。从而,决定了对村干部角色代理的总体评判。只有30%认为“公职化”后村干部仍是“村民当家人”,24%认为是“政府代理人”,更多的选择两重角色兼杂(46%)。
“政府全额支付”模式下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政府化更加显著。实行“政府全额支付”模式的Ⅰ乡镇,“站在政府一边”比“政府部分支付”的Ⅱ、Ⅲ乡镇高出三成,“站在村民一边”比以前下降两成;从而,认为村干部是“政府代理人”的比例比Ⅱ、Ⅲ乡镇增加18-19%,认为是“村民当家人”的减少20-24%。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村干部利益代表行为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别。
2.“公职化”对乡-村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村干部更加听命于政府,与乡镇的关系更加紧密。统计显示,有高达76%村民认为,“公职化”后村干部或多或少比以前更加听政府的话了;有57%村民认为政府下达的政务比以前完成得更好了。
“政府全额支付”模式下村干部更加听命于政府的趋向更加明显。实行“政府全额支付”模式的Ⅰ乡镇,“更加听政府的话了”比Ⅱ、Ⅲ乡镇高出8-12%左右。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没有太大影响。
3.“公职化”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一些作用,两者的关系总体趋缓。统计显示,有28%的村民认为,村干部拿政府的“工资”和养老保险后“比以前更热心(负责)帮村民做事”了,22%认为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可见,“公职化”对村干部的村务、服务工作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不是很大,60-70%的村民认为跟“公职化”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另有8%认为还不如以前。
“政府全额支持”模式下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的改善甚微。“全额支付”的Ⅰ乡镇,与“部分支付”的Ⅱ、Ⅲ乡镇相比,“比以前更热心帮村民做事”减少了22-25%,“跟以前一个样”增加了15-17%,“不如以前热心”增加了7-10%。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则几乎没有差别。
4.“公职化”政策对吸引村中能人效应明显,村干部的竞争更激烈了,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更好了。统计显示,有79%的村民认为“公职化”后村干部位置的竞争更激励了,33%认为实施“公职化”政策后村干部队伍整体上比以前更好了。“公职化”对吸引村中的能人来村上承担公共管理事务、从而改善村干部队伍效果明显。
5.基于以上认识,村民群体对“公职化”政策基本取赞成态度。对于“政府为什么要实行支付村干部‘工资’等‘公职化’政策(多选)”的问题,“让村干部更卖力工作”成为村民的首选(52%),其次是“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村干部”(46%),再次是“减轻村里(集体)的负担”(44%),说明村民群体较多地把“公职化”政策理解为使村干部更听话、更卖力地工作。但村民也认为,“公职化”也有减轻村里的负担,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村干部的实际功效。况且“更卖力地工作”不仅包括上级下达的政务,也包括村庄自身的治理事务。基于此,村民群体对“公职化”政策更多抱赞成态度(68%)。
两种“公职化”模式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的村民群体在此问题上的评判没有多大差别。村干部群体略有差别,“部分支付”模式下的村干部更倾向于赞成“公职化”政策,比Ⅰ乡镇赞成度高10%。
(二)综合分析
结合我们与乡镇领导和村干部两个层面的访谈材料,作如下进一步分析。
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效应正负兼收。从正面效应来看,它减轻了村集体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中国绝大多数的“空壳村”有了正常治理的物质基础;它使村干部安心于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工作,更积极地为村民服务做事,从而使村干部与村民群体关系也得到一些改进,巩固了村庄治理的群众基础;它使政府下达的政务也完成得更好,乡镇与村的关系也得到一些改进;它吸引了更多的村庄能人来竞选村干部,使村级治理者队伍整体得到改进,改善了村庄治理的人才基础。总之,“公职化”政策有力地支撑和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村民自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关系。
“公职化”也给村民自治制度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最突出的是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更加政府化,更加听命于乡镇(街道),当乡镇与村民发生利益矛盾时,特别是乡镇不正当地损害村民利益时,村干部更多地站在政府一边;村干部办理乡镇布置的政务的积极性明显高于料理村务和百姓事务的热情,对村庄内部干群关系的改进作用明显不如外部与乡镇关系的改进,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看,“公职化”政策没有对现有的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格局造成实质性改变,它只是强化了现有的乡镇主导的乡-村关系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格局。它有两层涵义:第一,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乡政村治”,村级名义上实行自治,是自治组织,与乡镇不构成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现实运行中,村级组织实际上沦为乡镇的下级,构成实际上的“命令-服从”关系,也即村干部们原本就是听命于乡镇政府的。“公职化”政策并没有改变现有的乡镇主导的乡-村关系,但对现有的乡镇主导的乡-村关系格局起了强化作用。第二,在现有乡村关系格局下村干部听命于乡镇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往往以不激起村庄较多村民的群怒为基准,“公职化”政策并没有使村干部们改变这一基准。这也正是仍有32%的村民认为当上级与村民利益矛盾时村干部是会站在村民一边的,特别是在乡镇损害村民利益时仍有27%村民认为村干部会帮村民(只比“帮政府”低一个百分点),更多的是“双方都不得罪”(40%),以至仍有30%村民认为村干部是“村民当家人”(高于“政府代理人”的24%)的原因所在。这揭示了村干部的真实状况,
在与乡、村两级干部的访谈中,乡、村干部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关键时刻,村干部与乡镇是保持一致的。但这在“公职化”前,甚至是村干部没有报酬(钱)的时期也是如此。第二,上级与村民利益发生矛盾但矛盾较小且涉及农户不多时,村干部一般站在有理的一边,如村民的利益合理则向政府反映村民的诉求,如村民无理政府有理,则帮政府做村民的工作。如政府执意要做,则尽力帮政府做工作。第三,如政府与村民的矛盾酿成较大民怨时,村民有理自然坚决站村民一边,即使村民无理,村干部也会站在村民一边。“当老百姓达成共识,站起来时,即使老百姓只有10%-20%,哪怕是老百姓无理,无论拿不拿‘工资’,村干部也肯定站在老百姓一边”(乡镇书记语)。
与村民问卷相互印证,我们认为基本反映了村干部们的真实情况。可能犯疑的是,为什么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后,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与前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即发生我们所担心的完全“傍政府”呢?这得益于村民自治制度内部两种机制的制约。一是受村民选举制度的制约。三年一度的村委会、包括村党组织的换届选举对村干部的行为是一种很大的牵制,受访的村干部都表示,发生矛盾时不帮村民讲话,下届选村主任、村书记时还想不想当。“即使是村书记,现在也要‘两推一选’,不是乡镇能定的”(村书记语),以至一位村书记如此说:“只要选举制度不改变,不管发不发‘工资’,村干部想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村民的问题。”二是受制于村民考评村干部制度。政府的“工资”如何发?发与不发,发多发少最后都要经过村民考评这一关。虽然是政府发的“工资”,但只要政府有村民利益的理念和导向,在年终考评时,召集村民考评一下村干部为村老百姓办事和治理村务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评完成政务的情况,甚至只是乡镇机关关起门来考评,就能对纠正村干部拿了政府“工资”后可能出现的行为偏向发挥很大的预防和制止作用。此外,还有村庄“熟人社会”、“面子”观念或曰道德舆论压力机制的制约。村干部普遍说:“村干部,村干部,就是生活在‘村’里的干部,总有一天不当村干部了,还是村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长期在村里生活,肯定要为村民说话的,否则要被村民骂的。”
三、对“公职化”政策的改进建议
如何破除“乡政村治”下村民自治之自治性不足的问题,是一个乡村治理的整体制度框架如何重构的长期性问题,中外学者已有许多论述。本文只是想基于“现有的”村民自治的实际制度状况,对“公职化”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1.应强化对村干部的以村民利益为导向的广大村民参与的工作情况的考核。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实施后最担心的是村干部更加成为政府的代理人,利益代表行为更加政府化,也就是屁股完全坐到政府一边,对村庄本身的和百姓的事务消极怠工等等,为防止克服这种政府化倾向,除了三年一次的村干部竞选外,就靠一年至少一次的对村干部的考核,并把考核情况与“工资”发放挂钩。这是防止“公职化”负效应的关键一步,必须重视和强化。实地调研中,虽然村干部群体100%都认为有年度考核,但受访村民中只有26%认为乡镇每年有对村干部的考核,认为“没有”的占29%,“不清楚”占45%,两者相加达到74%。调研中,我们还发现有的乡镇对村干部的年度考核只在乡镇政府大院内进行(机关部门和乡镇领导班子打分),与老百姓无关,本村村民根本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乡镇组织的考核必须有广大村民群体参加。让村干部的服务对象也是村民自治的主体(村民)来判别村干部工作的好坏,由此决定“工资”的有无与多少,让村干部不但畏忌乡镇政府,也畏忌广大村民。这种考核可采用村民(代表)大会群众测评的形式,不能仅由乡镇部门和班子来考核。第二,乡镇对村干部的考核内容应以村民利益为导向。不能仅考核乡镇布置的任务完成得怎样,更应考核村庄本身(自治)的事务做得怎样,社区服务工作做得怎样,以提高村干部服务村庄服务百姓的意识和能力,变“眼睛向上”为“眼睛向下”。那种乡镇大院关起门来仅仅乡镇人员参与的,以完成乡镇任务状况为内容的考核作为对村干部全部考核的做法必须废止。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职化”极易带来的村干部行为政府化。
2.村干部“工资”以“政府部分支付”模式更适宜。这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实践绩效的证明。实施统一标准的“全额支付”模式的Ⅰ乡镇,其正面效应不如“部分支付”的Ⅱ、Ⅲ乡镇,其负面效应大于Ⅱ、Ⅲ乡镇,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额支付”模式下(不许到村里再拿酬金)造成一些村的村干部的报酬还不如以前高,有的甚至还下降很多,村干部不但不买政府的好,反而对政府有怨言,挫伤了工作的积极性。二是理论上的自洽。理论上说,村干部办理村庄事务,应由村集体支付报酬,办理政府下达的政务,应由政府支付“政务代办费”。因此,村干部一年的工资,就是政府一块(代办费)加上村里一块(误工费),也就是“政府部分支付模式”。这样桥归桥路归路,道理上清清爽爽。“全额支付”模式虽然是政府出于好心,减轻了村里的负担,但却有越俎代庖之嫌,破了理。第三,“部分支付”模式具有灵活性或曰弹性。反之,“全额支付”模式刚性有余灵活性缺失。“部分支付”模式下,政府的“工资”是固定的,不论穷村富村都一个标准,但村里支付部分则可视村务的工作量、村集体经济的状况等,给多给少由各村自定。这样,国家固定的“工资”一块,加上村里灵活的一块,形成不同村庄村干部的不同报酬收入。而“全额支付”模式因为要考虑到同一乡镇内村干部“工资”的统一,因而往往难以顾及不同村庄工作量的大小,村集体经济的好差,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一刀切,整齐划一,缺失政策的灵活性,反而挫伤了富裕村村干部的工作热情。“今年想适当提高村干部‘工资’标准,但又担忧超过乡镇机关水平,引起机关职员的不满”(Ⅰ乡镇书记语)。
3.政府支付村干部“工资”政策应让广大村民至少是村民代表人人知晓,以杜绝村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访谈中了解到,许多村民对政府支付村干部“工资”的新政并不知情,村干部故意隐瞒,造成“部分支付”模式下许多村的村干部原村里支付的报酬仍一分不减全额领取,政府支付的部分又大幅度增加,类似暗中领取“双份工资”,只有少数村相应减少了村干部的村内报酬。因而,应在村民中广泛宣传、让村民广为知晓政府支付村干部“工资”的新举措。一方面,使广大农民群众感知国家的支农惠农之恩,另一方面,也加强对村干部报酬的监督,让村干部“工资”在阳光下运行,防止村干部的暗中捞取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
4.调查中,有部分村干部提出了“全额支付”和“部分支付”外的第三种模式选择:由政府每年给村里下拨一笔数目相当或更多的“村级工作经费”。不名曰村干部“工资”,而叫做“村级工作经费”,村里用这笔下拨经费,既可用作办公经费,也可用作村干部“工资”,也可用于其他工作经费,其中的村干部“工资”发多发少,由各村的村民代表会议自己决定。“如政府发,不如一年给村里一笔钱,比发个人好,一般村干部不是冲着工资来的”(老板村干部语)。解读他们的意思主要有:一是政府戴帽给村干部发“工资”,村干部拿了政府的“工资”就要听命于政府,似乎建立了一种明确的雇佣关系,不利于作为自治组织负责人所必需的独立性;而政府下达一笔“工作经费”给村里,就可免除这种直接雇佣关系的不良印象。二是,村干部明确拿政府的“工资”,就可能懈怠村里老百姓的事务,“眼睛朝上不朝下”,反正主要是政府考核,不把村民的意见放在心里;而政府下达“工作经费”,主要由村定村发并考核,就可有效免除这类偏差。三是“村级工作经费”的方式更符合“政务代办费”理论。如上述,政府所以给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发工资,是基于“政务代办费”之说:自治组织原本用于办理区域内的自治事务,但对政府下达基层的政务有“协助”义务,因为是本职外的“协助”义务,政府就要随下达的政务给自治组织一笔相当的“政务代办费”。如果村干部“工资”就是“政务代办费”的一种形式,那么“村工作经费”显然比“村干部工资”更合适。因为政府下达的政务的办理不仅村主要干部参与了,而且村其他干部也参与了,甚至村组长等下一级干部也参与了,“工资”(代办费)只发给主要村干部,其他村里的干部都没有份,显然有失公允;而且“代办政务”不仅消耗的是村干部的人力,还有村里的物力,只补偿人力,不补偿公共物力,或者说把村里物力消耗的补偿也转化为村干部人力消耗的补偿(“工资”),全给了村干部,显然也是冬瓜账记在西瓜账上,转公为私了。而以“工作经费”形式下达,则可免除这些问题,不仅其他村里的干部皆可一体均沾,而且还可用于村里办公用品的补偿。四是现在村干部“工资”只发给村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极易引发村干部间的矛盾或其他村干部们的不满(下述)。当然以“村级经费”形式下发也有弊处,就是以现在的“工资”形式村主要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多拿酬金,“反正是市里规定的,戴帽给我的”,这样反倒是少些矛盾纷争,减少或免除了博弈成本,政府也实现了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的有效性策略。若以“工作经费”形式下发则主要村干部与其他村干部之间多大酬金梯度合适必经一番博弈。因而,“村里拿,不如政府那儿拿”(村书记语)。
5.村级主要干部实行政府“工资”后,要防止因村干部间拉开了报酬差距而引发的村干部间的矛盾,即班子内耗局面。调查中得知,不仅村民、村民代表对村主要干部由政府发“工资”政策不知情,而且村其他干部也不知情,因此才有前述的普遍存在的村主要干部原有的村发报酬一分不减(原本就比其他村干部高),总体报酬水平(加上政府“工资”)大增的现象。村主要干部(村书记、村主任)与村其他干部的报酬差距暗中大大拉开了。“其他村干部现在不知道,知道了肯定心里不舒服”,“他们会说,既然你们拿那么多,工作就都由你们来做”(村主要干部语)。预防的路径,就是让其他村干部、村民代表、全体村民都知道政府给村主要干部发“工资”这件事,让他们通过桌面上的公开协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把村干部们的总体酬金约定在一个合理的梯度内。
注释:
①孙少菲、赵志涛、陈小腊、张雷、翟于荟、林杰、郭伊帆参加了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