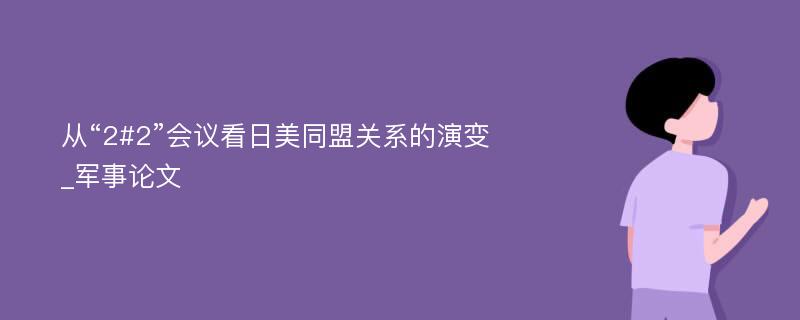
从“2+2”会议看日美同盟关系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同盟论文,关系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10月3日,安倍自民党联合政权成立后的首次日美“2+2”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方外相岸田文雄及防相小野寺五典、美方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出席了会议,这也是日美两国外交及防务负责人首次齐聚日本召开此种会议。会议以应对所谓的21世纪“新的威胁”为口号,声言要“基于日益严峻的亚太安全环境”和“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协商中长期的日美安全合作和驻日美军整编等议题”,[1]并高调发表了名为《迈向更强的同盟和分担更大的责任》的共同声明。会后,日美有关方面对此次磋商及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2]标志着日美近20年来第一次真正扩大军事同盟,将对今后十年的同盟发展起到指引作用。[3]那么,此次会议“新”在何处?是否具有重大影响?
历史对比中的日美“2+2”会议
由两国外交防务负责人出席的新日美“2+2”会议机制,正式始于1994年,并从此后形成每年举行一到两次磋商的惯例。[4]多年来,日美“2+2”会议机制在其双边安全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的新旧两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和1997年)均由该委员会决定并公布。平时,“2+2”负责促进日美两国政府间的相互理解与安全合作,并就构成日美安保基础的问题进行协商,同时由“2+2”(及其)之下的日美安全高级事务协商(SSC)以及专门用于协商“实施日美地位协定”的日美合同委员会(JUJC)进行政策磋商和情报交流。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后,为有效推进其中规定的防卫合作,日美又决定建立“总括机制”和“调整机制”。其中,“总括机制”以“2+2”为顶点,由包括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DC)、共同计划研究委员会(BPC)等在内的五级机制构成,并于1998年桥本内阁时期正式启动。
进入21世纪后,日美多次不定期地举行“2+2”会议。每次日美“2+2”会议及其共同声明,几乎都有特定的主题并取得一些主要成果。例如,2005年的两次会议及其声明,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及驻日美军整编,制定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以及评估明确双方的角色、任务和能力分工。2006年的会议则敲定了实施整编的日美协作路线图。[5]2007年的会议是根据形势发展微调并重点强调了一些与防范中朝、加强与澳印东南亚合作等有关的共同战略目标,还鉴于周边的弹道导弹问题日益“严重”而重点确认了强化导弹防御合作事宜。2011年的会议,除了涉及3.11后的救灾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外,其主要特征还体现在以日本新《防卫大纲》出台及中日岛争为背景,日本政府向重新强化同盟迈出实质性“回调”步伐,日美从调整新形势下的共同战略目标入手,重新确认进一步联手应对中国崛起、着手打造全球同盟并共治“全球公域”、日本配合美国“重返”并分担责任等。当然,这些设想由于民主党政权极度不稳而未及系统落实。
21世纪以来的日美历次“2+2”会议及其声明,不变的口径和固定项目是宣示要通过深化和拓展合作来强化同盟,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并强调中国的“军力发展问题”。在这三点上,“2+2”的设想和规划多呈现一种“延续”中的“创新”。同时,“2+2”会议往往受双方外交安全领域的军政精英主导,共同文件的磋商和起草也是由双方中高层职业军政官僚担任,而他们在政策倾向性上多具有专业封闭和思维保守等自我惯性。21世纪的“2+2”文件和同期三份美方著名的“阿米蒂奇报告”的基调和结论不谋而合,原因盖在于此。
此次日美“2+2”会议的看点和意义
对比2005年以来所有各次“2+2”会议,从双方发表的共同文件看,本次会议的新意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6]
第一,最大的看点是对同盟的一种“准重新定位”,日本被赋予更大的“责权”,同盟渐显“相对均衡化”趋向。说是“准”,一是因为其意义在宏观战略上尚不抵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定义”的那一次,二则其“将来时”的成效尚待观察(包括此次会议的一些成果主要是日方态度更主动的结果)。尽管如此,与以往会议显著不同的是,此次会议上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调整本身即成了重要话题之一,并且调整的具体措施还罕见地被写入了共同声明之中。同时,对日本在安全防卫政策上的自我“解禁”和“松绑”这一重要调整——包括安倍首相及其内阁的外交防务负责人对参会的美方代表就“积极和平主义”政策、设立日本版“国安会”、行使集体自卫权、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增加防卫预算进行的说明,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日本意欲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等等,美方在双方的共同声明以及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出了正面首肯和积极欢迎的姿态。这应当说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信号,其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今后日美关系的发展演进中逐渐明晰起来。
第二,作为以上定位的集中体现,会议决定2014年年底前完成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制定未来15年到20年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的“路线图”。日美认为,1997年版“防卫合作指针”的安排已经过时,对日本“限制”太多,日本强烈希望通过重新分配职责让自卫队承担起更多“矛”的作用。日方提出要重新审视或修改“指针”,至少在小泉内阁的2006年“2+2”会议上就已开始,其后民主党政权下的森本敏防相和长岛昭久防卫政务官在2011-2012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此类要求,但美方并没有给予很积极的正面回应。此次修改的背景,被认为主要是应对钓鱼岛争端、“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扩张”和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谋求亚太“再平衡”,但却是心有余力不足,不得不考虑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
第三,比起以往,双方在强化安全及防卫合作上落实具体措施,大幅推进了具体化与可操作化进程。一方面,拓展合作,联手应对“新的威胁”及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公域(网络和宇宙等)的规则制定和秩序管理方面。例如,双方就应对网络攻击每年举行两次部长级会议及日美两军相关合作,制定“网络防卫政策工作会议(CDPWG)实施要纲”等,在联合实施“太空状况监视(SSA)”(包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向美方提供SSA情报)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另一方面,深化合作,双方就进一步在联合作战计划精细化、反导(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情报·监视·侦察(ISR)、基地共用(特别是具体指出为了加强日本的西南群岛防卫而推动共同使用日美基地)、装备技术合作(特别是日本参与F35战斗机的制造)、共同训练、情报保密等领域采取具体推进措施达成了诸多共识。这些事项在之前的每次“2+2”会议多少有些涉及,但总体上都不如此次会议在“具体措施化”和“细节化”上那么明显。
第四,对地区安全进一步显示出高度的关注和介入。此次会议的共同声明将“地区一项”作了“计划单列”,并决定日美要联手加强地区及第三方的能力建设、确认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对比之下,之前的会议往往是将国际和地区放在一个条目里加以论述,并且开列的内容科目一般是强调以日美同盟为主来带动地区的人道支援和灾害救助(HA/DR)、海洋安全保障、多边合作等。显然,在中国崛起、日美应对乏力乏术等地区变局的背景下,日美这一做法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第五,进一步整理“旧账”,推进驻日美军整编及加强相关威慑。会议共同声明进一步细化了推进美军整编及基地搬迁的具体措施。应该说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什么新的战略意义。不过,这些措施中有两项连带效应还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日本通过支付“搬家费”的方式,正式获得了自卫队走出国门与美军共同使用关岛及马里亚纳群岛训练场的可能(而不再仅仅是驻日美军单方面使用在日基地)。另一方面,美军更具“高度能力”的尖端武器“大搬家”,扎堆移师日本,如鱼鹰战斗运输机、P-8新型反潜机、全球鹰无人侦察机、F-35战斗机等。日美两“军”的“一出一进”,既反映了美军以实际行动“重返”并给日本壮胆打气,也体现了两国扩大军事合作、完善分工以及日本正在扩大责权作用的事实。
第六,进一步联手应对中国崛起。此次日美修改“合作指针”并强化双边同盟,进一步推动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合作等举措,都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在内。较之以往,此次会议及其文件所涉内容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一是日美联手在海洋问题上明确指责并施压中国。日美首先在共同声明中不点名(实际等于点名中国)地指出“以实力损害海洋安定的行为”是日本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之一,继而又在双方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提出钓鱼岛问题并共同表示要“坚决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尝试”,“反对任何侵害日本施政的单方面的行动”。这些语调和措辞比之前任何一次会议都要来得更直接、更严厉。二是继2011年会议提出要“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行动规范”后,又一次直接点名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行为准则”。日美接连通过共同声明的形式明确敦促中国“遵纪守规”,其意在于承认中国已经作为大国崛起的现实,并要求中国在全球公域(尤其是网络和海洋)作为“后来者”要遵守美日等西方主导的规则和制度。这反映出日美开始联手在全球层面切实应对后危机时代新格局下的中国崛起问题。
当前日美各自的算盘与博弈
此次日美“2+2”会议双方看起来可谓各有所求、一拍即合。如果日美真按照以上决定和部署来推动今后的安全及防务合作,那么双方的相关合作尤其军事一体化之路将越走越远,日本趁机自我松绑和筹谋坐大,双方管天(全球公域)又管地(地区,尤其是中国),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形成巨大的挑战,会带来众多不确定负面因素。以此而论,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对今后若干年日美同盟走向将具有重要的规划意义。
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从今往后日美能够一直推动并顺利实施会议确定的中长期设想和规划吗?尤其是,日本安倍政权能如其所愿并在同盟框架和美国的看管下顺利实现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并发挥相应的作用吗?
安倍近期在美国发表了三场重要讲演[7],其中心思想一以贯之且非常明确,就是对内要振兴经济、维持并增进国力,同时松绑不利于“国防正常化”的各种束缚;对外要以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来担负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包括安全和民生等领域,但显然安全军事领域是发力点和增长点,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二者相加的核心要点就是日本要全面振作崛起、不做“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要有操盘的主导权。
美国是影响日本外交安全战略(实际上也是国家大战略)成否的关键变量。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如果不能“理顺”并充分利用日美同盟关系,日本的任何大战略都无法顺利实施。鉴于此,安倍集团在美国身上打的主意是积极配合、为我所用,目标是借船出海、摆脱束缚、借机做大。美国相对衰落,奥巴马全球战略并非果敢主动,其“重返亚太”也是困难重重,全球格局的大变动和大调整则方兴未艾。面对如此形势,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尤其是战略派精英们似乎嗅到了一种“时机”的来临。在日美关系上,他们已不满足日本仅仅在同盟之下做“盾”,也想拥有进攻之“矛”,恢复并拥有“正常”的军事能力和足够的“自主”防卫力量,同时部分改变日美安全体制的非对称局面,构筑权力分享或对等伙伴型同盟。其用意非常明显,即在于搭乘美国“重返之需”和日美同盟强化的便车,加速走向军事大国,积极谋求“军事崛起”;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军事地位与作用,借以提高和发挥国际影响力;通过“挟美抑华”来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
美国对此不能说就毫无知觉和警惕,实际上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底线的,会对日本单方面“暴走”行动不予首肯并采取制动措施:一是对日本能力的过度松绑和扩张,如彻底修宪、军事完全“正常化”等。作为具体表现,就是在会议前后,美方对防卫大臣小野寺声称日本应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所言“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象国家可包括亚洲各国,以牵制中国”[8]等过激主张,一概不予首肯并扣发“通行证”。二是当日本把和邻国的关系搞得过度紧张,导致美国可能卷入战争或消耗过多外交资源之时。这包括日俄、日韩、日中关系,但主要还是日中关系。例如,此次“2+2”会议正式召开之前,日本政府代表在双方起草联合文件的磋商过程中就一直图谋塞进自己的“私货”——用较大篇幅表达对中国和朝鲜的“担心”。然而,美方在自己的声明草案中没有提到任何国家,并且以“联合文件的着眼点是日美同盟的前景,没有必要把焦点对准特定国家”[9]为由,拒绝了日本的上述要求。最后,作为照顾盟友面子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双方最终达成妥协方案: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中国,但不涉及钓鱼岛;在联合会见记者时双方都谈钓鱼岛问题,以便对中国进行一定牵制。日本现下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美同盟在军事安全上威慑或吓阻中国,而美国从全球战略及其国家利益需要出发想的是对中国保持一个总体平衡政策,并不想在某一局部领域过分地刺激中国或与中国对立,这就是日美在对中国态度上的区别。崛起的中国是促使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因素,但美国在此问题上并不会轻易地“随日起舞”,美国总的战略从来没有根本动摇并改变过,那就是在中日之间周旋,搞战略平衡,选择性地利用中日来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
在这两个方面之外,面临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崛起等问题,急欲“重返”亚太的美国需要依靠或借重日本这个重要的帮手和战略支点,要求日本为其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鼓励日本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军事及安全领域要求日本在同盟架构内更多地承担责任和分担“负担”,支持日本“适度”加强军备,原本就是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中具有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此前提下,美国是默许甚至乐见日本搞“解禁松绑”,即部分扩军“修宪”的。其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一路开“绿灯”是为了要日本替自己出钱出力甚至出人,维持全球霸权。
日美各自的算盘敲得很响,中短期内似乎可以弥合不悖,但将来的博弈则尚难预料,需拭目以待。不过,不管他们之间算盘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历次“2+2”会议磋商的结果显然正使日美同盟日益增强其攻击性、排他性和全球性。日美在历次“2+2”共同声明中一再声称“日美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10],但以现在的这种演变与蜕变趋势,它不仅不能成为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而且反会给亚太安全形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